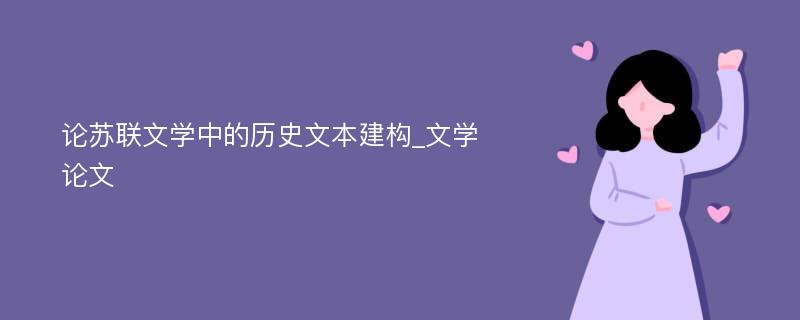
试论苏联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试论论文,文本论文,历史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文本就其本质而言都隐含着对历史的个人感受、折射出对历史的理解,直接或间接完成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无论作家对人的微妙心理做何种体察都蕴含着作家内在的、当下的历史感。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察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应从狭义上而不是广义上去理解文学对历史的解读,即探讨历史如何进入作家的审美视野,作品的艺术世界是怎样呈现历史的。就苏联文学而言,19世纪俄罗斯经典作家遗留下来的对历史进程高度敏感的传统的影响(如屠格涅夫的《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处女地》、《烟》等一系列表现社会历史进程的小说,列夫·托尔斯泰的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等),同时作家在极为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之下形成的对历史问题超乎寻常的关注,20世纪苏联的历史进程一直是苏联文学非常重要的主题,而考察其针对不同的历史文本的诠释对理解文学揭示历史的文本建构的规律性问题不无裨益。
苏联作家对历史的高度关注与苏联历史的特殊性不无关系。20世纪的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开始,到1991年国家的分崩离析,这充满了鲜明的复杂性、悲剧性,这也为作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阐释空间。但是,复杂而悲壮的历史进程也在考验作家:如何在历史的文学文本化过程中洞察历史内在本质的规律,而不只是呈现外在表象的历史事件。作家审视历史眼光的高低与其对自身创作主体性的把握有本质的联系。失去了主体独立性,他们对历史的观照难免肤浅与表面,对历史的文本建构也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50年代之前,这种现象在主流文学作品中普遍存在。
苏联主流文学关注历史话题,官方意识形态的诱导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十月革命产生了新的苏维埃政权,新政权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公平与正义的乌托邦理念付诸社会实践的伟大尝试。为这个历史巨变唱赞歌、颂扬伟大创举和证明其无可置疑的合理性,成为国家乌托邦主义对文学的必然要求。因此,表现苏联历史的进程成为十月革命之后主流作家们最热衷的主题之一。然而,热衷的背后却是历史感的缺失。这体现为作家在纷呈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丧失了独立的判断力,迷失在一个个历史事件的漩涡中无从判断,无力对历史进程的本质进行深刻的洞察。大多主流文学作品试图再现历史的真实面貌,但文本构建出来的历史面貌,只是官方意识形态观念剪裁下的历史片段,是意识形态观照下的历史印象,缺失的是个人本真的独立的审视眼光。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中的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剧本《列宁三部曲》(《带枪的人》、《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悲壮的颂歌》),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纪实性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教育诗篇》以及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都体现了这点。
以既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去建构历史,势必将原本复杂、丰富和鲜活的历史进程简化为由既定观念拼接而成的“观念的演进”,从而使历史的演进成为观念的佐证。阿·托尔斯泰的《阴暗的早晨》力图展现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经历的不平凡岁月。作为苏联文学的大文豪,他把握宏观历史的能力较强,但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统摄下,他对历史的审视也失去了深刻的洞察力,只能依附于国家乌托邦精神在作品中做出一番回应,框定一下历史进程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包戈廷的剧作《列宁三部曲》同样“标准化”地展现了十月革命到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延续的合理性、必然性。
在主流文学构建的文本世界里,历史事件依然维持着外在的原貌,作家试图展现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在《阴暗的早晨》、《列宁三部曲》和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我们领略到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中一个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十月革命、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在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的纪实性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茹尔巴的纪实性小说《普通一兵》里,我们也可以领略到真实的卫国战争的氛围。
真实的历史事件只是表象,它不足以揭示历史的真实性。对历史真实性的揭示一方面依赖于作家独立于意识形态观念之外客观的眼光,另一方面,在于作家透过事件表象、探究历史本质的思辨能力。缺少这两点,文学文本构建的历史,要么是一个被任意裁剪的不完整、不全面的历史,并且被部分遮蔽、掩盖的残缺的历史,要么是一个被历史表象所迷惑、被严重误读的历史。这都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和《普通一兵》都是以真实人物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写成的纪实性作品,展现的历史事件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在作者强烈的政治意识驱使下,小英雄们的行为没有得到真实的诠释,甚至军民顽强抵抗的历史画面也被阐释为:一切英勇行为都来自苏维埃意识的鼓舞。卫国战争英雄被灌输了一种政治说教:他们只有自觉地融入高度的苏维埃政治教化中,才能成长为英雄,他们的英勇得益于乌托邦精神的熏陶。这显然违背了历史的真实。读过老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人都知道,俄罗斯人对故土都有着神圣的情感,它超越了一切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并赋予他们巨大的力量。在苏德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很多等待枪决的红军将领在临刑前被告知去前线指挥部队。他们把一切怨言、怨恨埋在心里,为了国家忍辱负重、英勇作战。拯救苏联的正是这种悲壮的精神。可是,这一切在作者的视野中消逝了,作者竭力让人们相信,只有听命于官方乌托邦精神的宣扬,真诚地信仰官方乌托邦神话,并以此框定自己的言行,才能成为真正的英雄。这几部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据的作品从根本上偏离了历史的真实性。我们不怀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试图展示历史真实的愿望,但强烈的意识形态观念使他无法真正地洞察当时的社会生活本质,无法真实地展现历史,只能对当时的历史事件做表面的叙述,用官方话语对其做教条化的阐释。①作者丧失了对历史的独立思考而依附于意识形态的统治话语,最终导致对历史的肆意篡改,置表象的历史真实于不顾。《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便是典型的例子。作者洞悉战争期间远东输油管道铺设的历史事实,却在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驱使下,篡改了真实的历史面貌,将囚犯铺设石油管道的真实事件描述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积极分子的伟大壮举。
苏联主流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呈现出滑稽的悖论:作家俨然以历史主人的姿态,以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裁剪、割裂和组装历史,他们成为构成那段荒诞历史的一员,演绎了历史的荒诞滑稽性,成为历史统治下的一粒可怜的尘沙,最终被历史所抛弃。
苏联主流文学作品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面临的最大尴尬是:随着历史的变迁,作品对历史的文本建构越来越显出作家历史眼光的局限性,无法超越当下的现实语境而获得对历史的透视。对真实历史表象的追求无法掩盖对其内在真实性洞察的缺失,陷入现实话语泥潭的作家无力面对历史的变迁对作家思想的拷问。当年热情讴歌农业集体化的作品无法经受住当下读者的质疑。残酷的历史变迁击碎了作品对历史描述的虚妄,暴露了作家历史眼光的肤浅。但一些非主流文学却保持着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力,超越了当下的语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中篇小说《一切都在流动》、索尔仁尼琴的长篇纪实报告文学《古拉格群岛》、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格拉西莫夫的中篇小说《夜半敲门声》、别克的纪实性小说《新的任命》以及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囚车》,构成了主流文学之外的引人注目的风景线。这些作品在完成之际无法正式出版,面临着被历史尘封的命运。而与红极一时的主流文学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对历史的进程做出了不合时宜但发人深省的思考。他们与主流文学作家最显著的区别在于:他们不依附于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凭借自身的思考对历史做出独立的判断。精神的独立使他们能够透过历史发现其背后隐藏的悲剧性。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以苏德战争为背景,表现了苏联战争前后的历史变迁。作家对官方宣扬的卫国战争神话、国家乌托邦神话进行了深刻而独到的消解,达到了历史阐释的深度。“斯大林建设的一切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人的需要。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这是南北两极,一端是国家的需要,另一端是人的需要,它们是永远不会一致的”。(格罗斯曼299-301)小说中德国军官对被俘红军将领说的一番话颇具意味:“您自以为在憎恨我们,但这只是一种错觉:您憎恨的是你们自己,我们不过是你们的化身而已”。(443)格罗斯曼说:“胜利的人民和胜利的国家之间无声的争论仍在继续。这场争论关系到人的命运和人的自由”。(755)长期以来,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成为苏联官方宣扬国家乌托邦精神的招牌,而在格罗斯曼笔下,这一招牌被彻底击碎了:随着对德战争的胜利,人民从一种专制的铁蹄下走出来,又跳入了另一个专制的火坑。格罗斯曼对比两个集权者。他们以各自的专制政体共同构建了国家乌托邦的神话。李慎之先生在《美丽新世界》中文版的序言中分析了这两种左和右的乌托邦,指出经过20世纪,人类进一步体悟到最可贵的是个人的自由。而对自由的渴望,正是《生活与命运》这部被评论界称为20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巨著思考着历史最核心的思想。格罗斯曼的独立意识使他透过社会现象,对历史进行了超前的思考。这部小说对苏联历史、卫国战争神话的颠覆是空前的。格罗斯曼的绝笔之作《一切都在流动》也以冷峻的历史反思,解剖了苏联历史诸多悲剧的根源。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人性的扭曲和压抑、农业集体化之后农村易子而食的人间悲剧,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极端虚伪性和高度政治意识形态化等都迫使人们重新体验那个时代压抑的氛围。
与格罗斯曼相类似,索尔仁尼琴以卷帙浩繁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完成了他对苏联人苦难史的回望与思考,该书是超越了政治层面的人的精神苦难的观照。在此基础上,作品对民族历史进行了彻底的反思。作家深刻批判了苏联历史进程中国家乌托邦主义的方方面面。在他对苏联整个悲剧性历史的严峻审视中,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乌托邦国家神话一个个覆灭。以独立的主体意识反思苏联历史的悲剧性,在一些禁书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别克的绝笔之作《新的任命》反思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兴衰历程;雷巴科夫的长篇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尖锐地揭示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恐怖气氛;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凭着记忆的权力》揭露了个人崇拜泛滥时期的历史真相,描述了国家乌托邦主义给人带来的巨大灾难;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囚车》解构了其十多年前创作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还原了苏联三四十年代充满痛楚的历史原貌。
这一类作品对历史的深刻洞见不仅源自作家不依附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独立的精神意识,更因为作家书写过程中倾注的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当时表现为对自由的渴望,并赋予作家超越历史表象、挖掘深处悲剧性的眼光。因此作家对历史的阐释避免了主流文学作品的“时效性”。这些作家以过人的勇气,拨开历史表象的光环、直面残酷的历史真相。针对历史的客观真实性而言,这些作品显然要高于主流文学作品。尽管这些“不合时宜”的作家比主流文学作家更有直面历史真相的勇气,但他们对历史的文本建构主要依靠作家对历史的理性的批判,作品的审美因素没有与作家对历史的体悟完美地融合起来,艺术审美成分,如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心理层面的挖掘往往游离于作家对历史的思考之外。因此,历史是没有变形地、“非陌生化”地直接进入作家的文本,读者对历史的感悟并非全部来自审美体验的结果。作家对历史直接的、非审美性的理性判断限制了读者感悟历史真谛的权利,缩小了读者自由体验的空间,削弱了文学具有的对事物本质的洞察性、穿透力,虽然这为持不同历史观念和政治理念的人提供了支持或反对该文本的理由,但没有实现文学对历史超越性的阐释。
文学对历史的感悟是间接的,而非直接观念性的阐发。历史唯有与作家创造的审美的艺术世界水乳交融,成为这个艺术世界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才能给人们提供无限想象与体悟的空间。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才是真正成功的。
就苏联文学而言,文学通过两种途径来实现对历史的文本建构:一是通过对人的命运的展示,透过人物精神世界的波澜,表现个人在历史的漩涡中挣扎与彷徨,以此来透视历史的面貌。文学作为人学,归根结底应当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涌动。对历史进程的体悟如能建立在对人的心灵的深刻挖掘之上,才可获得真正的深度。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诗化小说《日瓦戈医生》等作品便是典型的例子。
在苏联主流文学作品中,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是一部身份极为可疑的作品,这部作品居然被苏联官方接受和认可,并一度被视为主流文学中的一部“红色经典”,这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背景。关于这部作品的蹊跷已有许多考证文章进行了论证。该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描述的历史背景的颠覆,其反乌托邦情感很明显。这部巨著真实地表现了哥萨克人在革命动荡岁月中的经历。他们的心酸、苦楚和旺盛的生命力、对土地的眷恋、蛮性与善良相交织质朴的本性在男主人公葛利高里和女主人公阿克西妮娅、娜达莉娅身上都得到了体现。他们的痛苦与悲哀、欢乐与幸福都来自他们真实的人性。而葛利高里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犹豫和迷茫,隐含着社会的悲剧和历史的荒诞。小说一方面出色地描绘了哥萨克人本真的生活,劳动、恋爱、繁衍,淳朴并焕发着生命的激情,葛利高里与他的情妇阿克西妮娅之间的情爱正体现了他们生命力的旺盛与冲动;另一方面,小说刻画了布尔什维克们的残酷与冷漠,他们在作家笔下成了革命的机器、政治原则的化身,他们的自觉性与葛利高里的本真性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布尔什维克领导的红军将革命风暴带到了宁静的顿河上,自由自在生活的哥萨克农民被迫迎来了历史的变动。葛利高里在这场残酷的动荡中必须做出人生的选择。他选择的标准其实很朴素: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只要能使他自由地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想吃什么就种什么,想爱哪个姑娘就去追求,无拘无束地过日子,那么他就跟谁。葛利高里是个自由纯朴的哥萨克,他在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徘徊正是出于这种朴素简单的生活要求。可是,如此简单的要求,在那个残酷的年代却无法实现。无论是红军还是白军,都无法满足葛利高里最基本的生活愿望。最后,他也只能抱着冤死的阿克西妮娅的尸体,缓缓地走向没有出路的未来。革命给普通的哥萨克农民带来了什么?从小说主人公悲剧性的结尾中可以感受到作者的某种暗示。小说对国家乌托邦主义的颠覆是相当明显的。也因为其鲜明的反乌托邦性,使得它在苏联20至50年代的主流文学中显得十分显眼。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悲剧性、历史进程的悲壮性,通过哥萨克农民葛利高里悲剧性命运的折射,得到了深刻而真实的展现。
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抒情巨著《日瓦戈医生》也以一曲优美的爱情之歌写出了苏联历史的沧桑与悲剧,其反乌托邦精神是划时代的。作品是作家对俄国1917年两次革命,特别是十月革命前后动荡岁月的历史沉思,作者说它“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45年的历史”。(Борис226)小说涵盖的历史事件表明了作家宏大的历史视野。美国人埃德蒙·威尔逊将它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小说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之下,通过传统知识分子日瓦戈的人生遭遇(尤其是爱情经历),表现了作家对历史的感悟。威尔逊把《日瓦戈医生》概括为“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颇为精当。小说浸透了对基督教教义的评论,关于生命与死亡、自由与真理的思考、历史与自然和艺术的联系的思考,作者以某种不朽的人性,以先验的善和正义等宗教人本主义观念作为参照系来审视革命运动和社会历史变迁。这一切都是通过主人公日瓦戈医生的视角来表现的,作家对历史的审视完全熔铸到对人物心灵历程的表现中。在他身上可以清晰地体现俄罗斯知识分子具有的对世界和生命的体悟方式。他以俄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方式生活着,思考着知识分子才会琢磨的问题。上帝、死亡之谜和俄罗斯母亲的命运,这曾萦绕在果戈理、老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文学巨匠心头的疑虑,是帕斯捷尔纳克通过主人公加以思考的纯粹的俄罗斯式问题。当年这部小说在苏联不能出版,因为作家对历史的价值判断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话语相悖。从根本上说,作品对俄国历史的考量是非政治性的,是个性的、自主性的对当时集体意识的批判性思考。从哲学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审视,是知识分子以独立的理性精神审视世界的可贵方式。《日瓦戈医生》对俄国历史思考的非政治性,正是其对历史感悟的价值所在,它决定了这部以哲学与文化的反思超越了当下社会意识形态层面,揭示了“人的存在”的意义和悲剧性色彩等问题的小说具有了对历史的深层次体悟,揭示了在历史巨变中人的存在的悲剧性、历史进程的荒诞性,这部小说成为“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重要事件,是与20世纪最伟大的革命相辉映的诗化小说”。(赵一凡35)最可贵的是,小说对历史进程的体悟与探寻都以诗的意蕴呈现出来。这部历史视野宏大的小说,首先是一首诗,一首爱情诗——“拉拉之歌”,从而使其包含的有关历史的思考具有震撼力。西班牙作家略萨称这部小说是“抒情诗般的创作”(略萨214),苏联学者利哈乔夫把它看做是“对现实的抒情态度”(利哈乔夫35)。《日瓦戈医生》的独特性就在于以诗的韵味审视了俄国革命历史。这首“拉拉之歌”表达的“革命、历史、生命哲学、文化恋母情结”主题,是那些充斥着激昂的国家乌托邦主义政治说教的伪文学无法比拟的。作家对历史的沉思和文学建构,是从日瓦戈和拉拉的爱情中折射出来的,作家幻想出一个只属于日瓦戈与拉拉这两个充满人性光芒的人物的世界,这里充满诗意,精神、艺术和大自然浑然一体,心灵高度自由。然而,美丽的童话般的世界在诗人的笔下被无情地摧毁了,这个迷人的世界无法与国家乌托邦主义的实践相对抗,等待它的只能是悲剧性的毁灭。通过日瓦戈医生的悲剧,作家“抒情地”表达了对历史的悲剧性进程的批判,他日瓦戈医生这个人物心灵历程的诗性把握,成就了作家对历史进程的独特的感悟。
《静静的顿河》和《日瓦戈医生》的作者,一个是20岁的涉世未深的青年,一个是幼稚单纯的诗人,他们都缺乏足够的历史经验的积淀来构筑宏大的历史叙事。但是,他们都有窥探人的情感世界的冲动、把握人物命运的欲望。他们通过对人物命运、精神世界的自由的领悟,建立起了观照历史的坐标,不经意间触及了历史的脉搏。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两姊妹》和《1918》在艺术成就上高于第三部《阴暗的早晨》,因为前两部对历史进程的展示只是通过作家对主人公精神探寻的表现实现的。主人公对生活意义的思索构成了作品的基本内容。在俄罗斯经历着灾难深重的历史背景下,主人公们渴望着生命的自由与完善,这与第三部《阴暗的早晨》中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话语截然不同,读者能够通过主人公复杂的心路历程感悟历史进程的脉搏,而不是只看见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历史图景的简单图解。
成功实现对历史的文本建构的第二条途径是突破历史的宏大叙事模式,摈弃再现历史事件表象的企图,以隐喻、象征的方式表达对历史内在真实性的哲理化思索。这种叙述方式早在20世纪初白银时代的小说中就已经出现,如安德列·别雷的象征主义小说《彼得堡》,而之后的再次出现是20世纪70至90年代。
安德列·比托夫在他的小说《普希金之家》中,通过对奥多耶夫采夫一家三代知识分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命运与精神状态的展示,揭示了国家乌托邦主义对人的精神的压抑,揭示了苏联历史进程的荒诞性,这种体悟隐含在作家颠覆性的调侃叙述中,这与索尔仁尼琴、格罗斯曼式的“愤怒的呼声”格调迥异。小说对官方历史话语的颠覆力来自作家非传统写实主义文学创作观和“消解性”的世界观。作家在小说中呈现了异样的创作观念,他力图表明与自由相对立的不是强权,而是现实的虚假性。现实被虚假的替代物、一整套假定的意义和丧失了原始真品的复制品所充斥。作品最本质的意义就在于启发人们去思考苏联历史进程中最隐秘的精神机制——虚假性。这种社会机制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不会随着外部政治环境的变化而轻易改变。在比托夫看来,斯大林的死并不意味从独裁桎梏下解放出来的自由时刻的到来,相反意味着虚假性的延续,意味着全社会都将在一种虚幻的“胜利”中延续着一种实质的悲哀。比托夫认为,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代不仅没有动摇苏联社会这一根本性社会机制,反而使其更加隐蔽,实质上使之更加完善了。他试图说明,非现实性就是生活的存在条件。这确立了小说主人公虚假的生活,并具有强大的解构力量,它解构了现实社会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比托夫在70年代初的思想观念比德里达和波德里亚诺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更早地表达了对现实生活虚构性的看法。他以此观念对苏联历史荒诞性进行审视,剥去其一层层神圣而虚假的外衣,显露出历史本质的真实性。
维涅季克特·叶罗菲耶夫的小说《莫斯科——彼图什基》通过小说主人公——工人维涅季卡·叶罗菲耶夫的荒唐经历,颠覆了“发达社会主义”的国家乌托邦神话。主人公是一个醉鬼,整天处在半醉半醒之中。作家在表现这个醉鬼非正常的语言与思维的过程中,戏谑地展现了历史进程虚伪的表象,对国家乌托邦的神话进行了调侃,以怪诞反讽的艺术风格实现了对官方勾画的历史图景的颠覆。
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长篇小说《地下人,或当代英雄》则以反讽、调侃、冷峻的语言,消解了苏联时代官方文学对历史的抒情化、激情化的叙述风格,在刻意的碎片化、肢解性的反讽叙述中,表达了对苏联直至解体之日动荡历史的滑稽荒诞性。作家对历史的感悟更具反乌托邦色彩:当大多数俄罗斯人在憧憬着改革的光明前程时,冷静而睿智的马卡宁在无情地消解人们天真的幻想:“哪里也不像俄国这样,任何一种思想过一段时间都要翻新一次。我们不是各种思想的受难者,而是它们痛苦改变着的受难者……”(马卡宁158)苏联历史的震荡与变迁,俄罗斯人在历史的衰落中社会身份的荒诞性转换,如昔日的党棍与今日的民主派斗士的身份转换,作品通过地下室人“阿地”和作者自己这双重视角的反讽叙述,呈现出了其本身的滑稽性、荒诞性。哈里托诺夫的长篇小说《命运线,或米洛舍维奇的小箱子》则有意将历史视为随意拼贴的碎片,借助主人公将无数个记载历史事件的糖纸任意组合,得出对历史不同的描述,显示出对历史进行多样阐释的可能性,表达了人们对历史进程荒诞性的无奈。
无论是比托夫、叶罗菲耶夫、马卡宁,还是哈里托诺夫,在他们对历史的文本建构中,都刻意凸显出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被动性。他们都意识到了个人的渺小与无奈,但从根本上真切地把握了历史进程的荒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认识历史的主体;而从官方意识形态出发、以宏大叙事来把握历史的主流作家则相反,他们在建构历史的文学话语时,自认为是历史的主人,实际上只是一颗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尘沙,成为历史嘲弄的客体。
历史一旦被阐释,就成为文本。文学之为文学,是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探寻。故文学对历史的文本建构是为了探寻历史中的人及其对历史的个性化体悟。在此基础上折射出来的作家对历史的认识势必是个性化的,带有个人观念的烙印,如法国文论家卢波米尔·道勒齐尔所言:“历史小说家可以自由地将某些历史事实包括在他的虚构世界里,将另一些历史事实排除出去”。(道勒齐尔189)作家的这种观念究竟是独立的自由意志的产物,还是被强加于己的外在的立场,究竟是作家审美体验的结晶,还是理性观念的宣泄。这些不同决定了作家对历史的文本建构的深度。肆意篡改历史事件固然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但仅局限在孤立的真实历史事件上也会远离对历史的深刻把握,作品对历史把握的深刻离不开作家对历史和历史中人的超越性思考。
注释:
①参见余一中《历史真实性是检验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重要标准》,《俄罗斯文艺》2004年第3期。
标签:文学论文;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日瓦戈医生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小说论文;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论文; 静静的顿河论文; 战争与和平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读书论文; 长篇小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