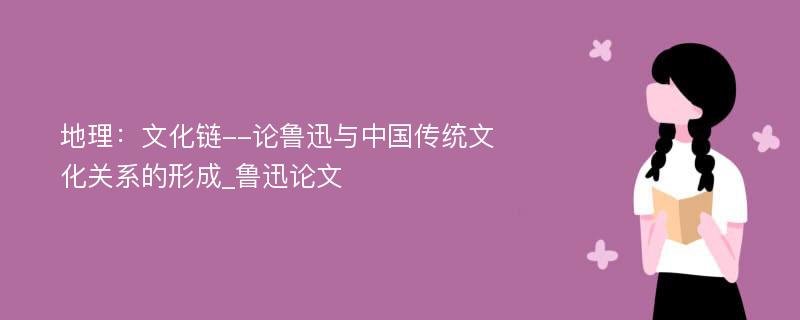
地缘:文化之链——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生成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地缘论文,中国传统文化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鲁迅之被称为“民族魂”,决定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是怎样形成的呢?鲁迅的全部著述表明,他汲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墨、法等思想的精华;但是,如果将此视为一种对这些传统思想因素的简单积累与综合,其结果必然失去了鲁迅。因此,探讨鲁迅怎样以他特有的个性方式形成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就成为研究得以展开并深入的关节。
显然,这里涉及到研究的思维方式的变革。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旧序中反复强调,采用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往往对于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思维方式的变革则要求我们,在大量现象事实的材料中,找到最能体现鲁迅个性特征的典型现象,并以此为“中间环节”,深入到具有本质性意义的,与传统文化联系的个性方式之中;而要找到这一“中间环节”,个性化的研究就显得至为重要。
提出个性化的研究,不仅因为这是学术研究深化的必然要求;而且,个性化研究的客观依据,就存在于研究的对象——鲁迅自身。
鲁迅产生的时代——“五四”,是一个人的个性意识充分觉醒的时代,如刘纳同志所说:“五四时期变革中的现实生活为我国人民,特别是我国知识分子个性解放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比起古代人来,现代人更多地属于他们自己”①。刘纳着眼于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这两大作家群的特征迥异的性格比较,发现在他们身上,分别深深地打上了中国儒、道两家思想所造就的“儒雅”与“风流”这样两条并行的文人传统的印记。显然,鲁迅既不“儒雅”也不“风流”,他的以及回忆他的文字材料,都可以反映他的个性特异,如他自己所说:“我觉得我在中国人中,的确有些特别”②。请看如下鲁迅个性的独到的观察——
他的敌人说他多疑,神经质,阴郁,他的爱人说他“感受的黑暗居多”,“以悲观作不悲观”,他自己则说他因了“经验”,“也就比农民更加多疑起来”,“自觉脾气实在坏得可以”,他纵酒,他焦躁,他有时为了不舒心的事,在家里长时间的不说,不动。作为他感情活动的一种特征,敌、友、己从不同动机出发,却在各自的感受中,达到了某种一致,这反映了他的某种心理素质,某种感情面貌,某种精神气氛所显示出来的稳固特征,即其特有的个性气质。③
坎坷的遭遇使他从小便带有阴郁、怀疑、憎恶的眼神看待眼前这个世界,并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内向、孤僻又略带偏执的性格。④
这确实反映出鲁迅个性的某些突出侧面。依此,我们进一步对鲁迅个性形成进行文化溯源,显然,简单地从儒、释、道、墨、法等思想出发,是无从给以解释的。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上观察所体现的个性化的研究方式,即不囿于固有的“结论”而转向“过程”,对鲁迅个性的形成,追溯于他的幼年至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影响和特殊的经历。
可以给我们的研究以启示并拓展思路的,是大量现象表明,作家较之一般人,其个性、气质与他们所在地域或民族的文化背景,有更直接、更深刻的联系。比如,恩格斯批评歌德的“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就归因于他的故乡——莱茵河畔的商业中心法兰克福的小市民的庸人气息的影响。⑤果戈里是这样评价俄国近代文学之父——普希金的:“命运好象故意地把他抛掷到那个地方去,……高加索唤起了他灵魂的力量,毁坏了依然束缚在自由思想上的最后的锁链。大胆山民的自由的诗意的生活,他们的格斗,迅速的,不可抗拒的袭击,俘虏了他;从这时候起,他的画笔就获得了使刚刚识别俄国的人为之惊奇和倾倒的那种广阔的规模、敏捷和大胆”。⑥
同样,鲁迅的思想性格、个性气质,鲁迅的文化个性,正是植根于故乡文化的土壤之中的。对此,人们已经作了多方面的说明与研究。比如,周作人曾谈到,绍兴人的“浙东性”,即“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⑦。“绍兴师爷传统”所蕴涵的法家的人生态度、思维方式及其外在文字表现形式,对鲁迅一生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⑧。又如,鲁迅身上为人称道的“越人卧薪尝胆之遗风”,他自己解释说:我“还是脱不出往昔的环境的影响”——“总觉得复仇是不足为奇的”⑨。
瞿秋白从鲁迅与故乡的精神联系出发,更有独到的说明——
他的士大夫家庭的败落,使他在儿童时代就混进了野孩子的群里,呼吸着小百姓的空气。这使他真象吃了狼的奶汁似的,得到了那种“野兽性”。
……(他)是永远没有忘记自己的乳母的,虽然他也很久的在“孤独的战斗”之中找寻着那回到“故乡”的道路。……他从他自己的道路回到了狼的怀抱。⑩
故乡文化哺育了鲁迅的个性。鲁迅以故乡文化为“中介”,形成他与传统文化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他从自己植根于故乡文化的个性出发,对传统文化的择取与拒斥。一方面是择取,鲁迅与“魏晋风度”、“六朝文学”的关系即属此列。魏晋名士的蔑视礼法、“非毁典谟”、傲踞竹林,与清代绍兴人的“浙东性”,即章学诚所说的“逆于时趋”,“辩论之间,颇乖时人好恶”(11)的质性,是内在相通的,缘于窥破世态人心而与时趋相背,愤世疾俗的铮铮傲骨。在这方面,魏晋名士较之“浙东性”人物又有过之无不及,而为鲁迅心神所往。而且,“孔融作文,喜用讥讽的笔调”,“专喜和曹操捣乱”(12),嵇康的《难自然好学论》等文揭示“人性之恶”,为司马氏深恶;这与涵有“法家的苛刻的态度”的“绍兴师爷笔法”亦是相通的,表现出透视人情世故的极端冷酷与尖刻。在这方面,“师心以谴论”的“魏晋文章”较之“绍兴师爷笔法”亦有过之无不及,而为鲁迅取之融会笔端。鲁迅对“魏晋风度”、“六朝文学”的择取,同时又是对以“名教”包藏祸心诛杀异己的司马氏之流的拒斥。鲁迅进而理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榜“仁义道德”以“吃人”的一脉,置于自己五四时期反封建思想文化的中心位置,给予最为有力的揭露与批判。这种择取与拒斥,贯穿中国古今,显示出鲁迅的惊人的洞察力与分析力。
被尊为“民族魂”的鲁迅正是这样,以故乡文化为“中介”,形成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
二
着眼于鲁迅与故乡文化的联系,应该看到,绍兴古称会稽,在久远的历史变迁中,固有文化的封闭状态被打破,其文化内涵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并存的。因此,进一步要提出的问题是,在这种多元文化内涵中,构成鲁迅与故乡文化联系的核心与纽带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提出所针对的,即是以往的一些研究仅仅局限于“鲁迅与绍兴文化”的关系中,因而得出的结论是似是而非的。从鲁迅言及故乡的全部文字可见,绍兴文化在他的感性体悟与理性审视所形成的价值取向中,在总体上是被否定的。鲁迅神往并追寻的,是故乡文化的历史层面。一些同志就鲁迅对吴越文化传统的继承问题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但是,探讨鲁迅与吴越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应该首先把吴、越文化置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中加以考察,如谭其骧先生所说:“论文化则要注意到各种文化现象的地理分布和地理差异。”(13)人们习惯于吴、越视为一体而并提,实则,远古吴、越两地地理特征不同而自然生态环境迥异。春秋时代的吴、越大体是以钱塘江为界:江之西为吴地,吴地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江之东为越地,则临江倚海,西南山岭重叠,山洪漫流,海潮侵袭,造成越地先民生存条件的艰难性,故古有越人“随陵陆而耕种,或逐禽鹿而给食”的记载。不同的地理特征及自然生态环境,使吴、越两地的文化表现,诸如语言、信仰、风俗、生活习性,以至文化心态明显不同(不排除有相同的一面)。今人以“小巧”概括吴文化特色,“小巧”又可谓江南文化的总体特征。鲁迅对此的批评甚为尖刻,说:“中国士大夫之好行小巧,真应‘大发感慨’,明即以此亡。而江浙尤为此种小巧渊薮”(14)。周作人曾谈到这种“小巧”文化自明代以后对越地的渗透,(15)鲁迅为此也曾“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16)。鲁迅心神所往的是越地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越地先民断发纹身,辟草莱,浮大泽,用自己强旺的生命之力,外化为一片膏腴之地;越人血战前行的历史所内化成的精神酵母,使越文化在江南文化偏于柔弱、纤丽的格局中,独标一种刚健、豪放的风骨。他在为绍兴《越铎日报》创刊所写《〈越铎〉出世辞》中说:
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逸,先后络驿,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基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17)
以后他又多次不无自豪地引用明末文人王思任的话来说明故乡文化的历史传统:“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18)并一再表示:“自为越人,未忘斯义”(19)。越文化传统正是鲁迅与故乡文化联系的核心和纽带。
但是,正如一些同志所指出的,远古越文化的固有形态,在19世纪末的越地已不复存在:那么,鲁迅对越文化传统的感悟与认同,以及他自身突出的越文化个性是怎样形成的呢?
金克木先生在《文学的地域学研究的设想》(20)一文中,提出考察文学(文化)的地域性特征的几种方法,意在说明:地域文学(文化)在岁月流逝中不论发生何等显著的变化,也不可能在根本上脱开其所植根的自然地理特征的内在制约。吴、越文化即是一例。因自然地理特征不同,自然生态环境迥异形成的远古吴、越文化的深刻差异性,在尔后漫长历史岁月中,不仅使吴、越两地的地域分界始终存在,而且对两地文化一直保持影响,并呈现对立状态——
首先是地域划分上的沿革。吴、越以钱塘江为界,钱塘江流贯浙江,将浙江划为浙东、浙西。“两浙”之称由来已久。唐代置浙江西道、东道,宋代改称浙江西路、东路。据清代乾隆元年刊刻进呈的《浙江通志》记载:
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地域划分上的沿革,反映了地域文化差异的延续。吴、越文化之差异,滥觞了浙西与浙东的民性、民风、民俗之不同。明末的浙东临海人王士性在他的著名地理著作《广志绎》中说:“两浙东西以江为界而风俗因之。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蜕,多巨室大豪,若家僮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浙东俗敦仆,人性俭啬椎鲁,尚古淳风,重节概,鲜富商大贾。”此种状况,衍及近代。浙东金华人曹聚仁在《我与我的世界》中历陈浙东、浙西民性之不同,说:“浙西的事,跟我们浙东人毫不相干”——“浙西属于资产阶级的天地,浙东呢,大体上都是自耕农的社会”。周作人对浙东社会的自耕农特质有具体的说明:“读外乡人游越的文章,大抵众口一词地讥笑土人之臭食,……绍兴中等以下的人家大都能安贫贱,敝衣恶食,终岁勤劳,其所食除米而外,唯菜与盐”(21)。鲁迅则从中感受到浙东地理历史文化传统:“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22)——“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
“两浙”民性不同,学术与学风亦殊异。清代著名史学家,浙东绍兴人章学城在《文史通义》中说:“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世推顾亭林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州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23)。浙西尚经学,浙东重史学,浙东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近人何炳松先生在《浙东学派溯源》一书中认为,浙东学派的史学传统的发展存在着南宋和清代两个互为承续的高峰,且与宋明理学始终“水火”不溶(24)。清代浙东浓厚的历史研究的空气,对鲁迅颇有影响。鲁迅自幼即喜读史书,尤其是野史,一生倡导“治学要先治史”,研史以透视社会人生,以至周作人也把他推为“偏于史”的浙东学风的“代表”。(25)
“两浙”民性及学术之不同,又深深渗透于文学艺术之中。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一文中提出:浙江“近来的三百年的文艺界”的“两种潮流”:一为“飘逸”,“如名士清谈,庄谐杂出,或清丽,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含妙理而自觉可喜”;一为“深刻”,“如老吏断狱,下笔辛辣,其特色不在词华,在其着眼的洞彻与措语的犀利”(26)。周作人将这两派“特色”上的不同,归源于地方民性的濡染;显然,“飘逸”派主要与浙西民性相渊源,“深刻”派则深深植根于浙东。周作人又谈到,“飘逸一派”,“王张(指王季重、张岱)的短文承了语录的流,由学术转到文艺里去”(27);其实,更能体现由学术而文艺的是“深刻”派,他所举代表人物如毛西河、章学诚、李慈铭等,多为浙东史家。何炳松也认为,浙东学派“盛也其途径乃由经而史”,“其衰也乃由史而文”(28),他概括的浙东史学的“无妄与怀疑”(29),也与周作人所说的“深刻”派“特色”相通。周作人与鲁迅分别继承和发展了“飘逸”与“深刻”这两派,则是明显的事实。
综上,浙东民性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浙东史学,浙东“深刻”派文艺,作为浙东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其形成,都可以追溯于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
鲁迅与浙东文化有深刻的联系,浙东文化是他感悟、认同并追寻远古越文化传统的现实基础,他与故乡文化的联系,也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三
将浙东文化置于鲁迅与故乡文化联系的核心位置,实际上已经切入了构成鲁迅背景文化的“地”之“缘”。地缘,一种文化之链。从地缘关系入手,可以进一步使研究深入到鲁迅与浙东文化本有的内在联系之中。
地缘之于作家,在以往的研究中,习惯于对二者作以人为本位的历时性线性勾勒。如鲁迅,注重他与浙东先贤诸如勾践、陆游、明末文人、清末民初志士的精神联系。这种研究显然有局限性。比如,鲁迅重“史”的思想特点,明显与浙东史学传统有相承之处;对此,周作人早有说明,但却为研究者不予承认。原因在于,对浙东史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鲁迅在著作中几无论及,对李越缦的人品,鲁迅又颇有微词。如果仅仅局限于鲁迅与浙东史家的关系,他与浙东史学联系的研究必然搁浅。我们是否可以换一个角度,把研究从显在联系转向潜在影响。实际上,作家在其幼年至青少年时期,更多地受到的是所在地域文化的潜在影响,他尔后产生的明确的乡邦文化意识,即直接发孕于这种潜在影响。可以作为例证的是,鲁迅民元前后蒐集他所能见到的“越先正著述”,并辑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如他所说,他辑录先贤撰著、弘扬乡邦文化之愿,始萌于幼时所感受到的故乡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30)
我们实际上提出了在作家背景文化研究中与前述“线性”研究不同的“面”的研究,即地域之“缘”之于作家的意义。丹纳的《艺术哲学》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走了极端,但他看重文学与地域的关系并没有错。地域不仅指山水、土壤、气候等自然现象,还包括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等人文现象,由此构成文学之地缘。地缘与作家之关系,可以从多方面得到解释。在西方有着很大影响的心理学家荣格,在他的分析心理学中依据考古学、人类学提出的最重要的假设——“集体无意识”,如果把这一建立在科学依据之上的假设,运用于历史人文地理学的范畴之中,可以说明,为什么同一地域的人都有着大体相近的语言、信仰、习俗、生活方式以至文化心态,并能从中找到该地域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鲜明印记。地域文化正是以这种“集体无意识”方式进入作家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与作家结下不解之缘的。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难以割舍的“地”之“缘”,几乎每一位中国现代作家身上都或微或著地潜藏着随岁月的流逝和踪迹的迁徙也难以消蚀的“恋乡情结”;即使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的鲁迅,也同样有着植根甚深的“恋乡情结”,那种“思乡的蛊惑”直至他的晚年“依然存在”。
前述地域文化与作家之缘,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一种文化的共时性内涵进入作家的文化背景之中的。当我们进一步寻求对文化背景的时空合一的研究,就不能不提出作家地缘关系中更为重要的历时性内涵,这自然要涉及到作为文化载体的人,但这是一种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人的历时性联系。
着眼于血缘关系,首先需要提出的是,血缘较之地缘,更具有文化传承的稳定性与持续性。这不仅是因为人类血型由化学结构十分稳定的遗传基因所决定,改变一种血清血型约需长达二、三百万年的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血缘关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所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了它所脱胎的血缘氏族社会的特质,为保障血统的纯正而形成种种严格的等级、礼法规范,诸如婚姻讲门当户对,血缘定远近亲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血缘意识在宗法社会里的中国人,尤其在士大夫阶层中是根深蒂固的。
着眼于血缘关系的作家背景分析的客观依据,还存在于我们的研究对象——鲁迅自身。如前所述,血缘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凸现,因而血缘关系分析又一定程度受到研究对象所处时代与社会环境的制约。鲁迅出生在19世纪末的封建社会末期,为封建士大夫家族的长子承孙,他多次强调自己是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31)这决定了由血缘关系所承续的文化基因在鲁迅身上存在的必然性。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血缘与地缘是相依而存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专门以“血缘与地缘”为题,做了这样的阐述:“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长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32)他提出的“血缘性的地缘”这一概念,可以说明,正是因为植根于血缘关系,为地缘关系所决定的地域文化才能够深深地渗入于作家的血脉之中,成为几乎不可更易的因素。
在鲁迅的“血缘性的地缘”关系中,周介孚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这不仅因为周介孚是覆盆桥新台门周家的族长,鲁迅是他的直系长孙;而且因为,周介孚对于鲁迅自幼开始的文化哺养,个性成长,以至人生之路的改变与选择,都直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介孚就是一个极富于浙东文化特征的人。比如,浙东史学传统在他身上就有明显表现:他不同于一般书香人家,为本族子弟开蒙择定的教材是史书《鉴略》,本族子弟学做文章也是从史论开始的。(33)他又藏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为子弟很早就熟读。又如,周介孚身上明显有弥漫浙东乡间的“师爷气”——早年在京的散馆殿试中,对辅考大臣恃才傲视,后改放江西金溪县任职,对上官从不谄谀迎合,话不投机,就当面顶撞,言及“皇上家”也据理驳诘。由于愤世疾俗,“他平时很喜欢骂人,自呆皇帝昏太后(即是光绪和西太后)起头直骂到亲族中的后辈”(34),“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的”(35)。周作人说鲁迅,“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36)。
地缘以及地缘与血缘的依存关系,使我们找到了对作家背景文化的时空合一的研究方式:从地缘关系所决定的共时性文化濡染,和血缘性的地缘关系所决定的历时性文化传承,这样两个紧密联系的不同侧面,深入于作家的文化背景之中。
由此形成了我们探寻鲁迅与浙东文化内在联系的途径:从家族血缘文化背景与早年生活文化氛围入手——一方面,鲁迅的先祖是种地的农民,“逸斋遗教是桑麻”(37),自耕农文化意识从深层自律性地影响着家族后系子孙;另一方面,鲁迅出生在一个有着百年历史,曾经鼎赫一时的封建士大夫家族,贯穿这个家族升沉起落的是儒文化意识。家族血缘背景中的儒文化与自耕农文化所蕴含的“浙东性”,构成鲁迅与他早年生活文化氛围中的浙东经史文化、浙东民间文化联系的内在根基。鲁迅从中对“浙东性”的感悟与认同,自觉追寻浙东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传统,从而形成他与浙东文化,进而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联系。
本篇余论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浙东文化的秘传与积淀,仅仅构成鲁迅文化心理的基础。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主体意识的参与最终形成。这一形成过程表现为——
1.复活。这是最基本的过程,表现为由地缘与血缘关系所维系的文化基因,在鲁迅主体意识参与下的“复活”。在中国封建社会伦常秩系的僵死格局中,“复活”是顺其自然的。作为晚清封建士大夫家族的长子承孙的鲁迅,无可避免地在很大程度上承续了这一过程。鲁迅对浙东地理历史文化传统的感悟与认同即属于这种情形。
2.变异。“变异”与“复活”相反相成。如果说,“复活”是一种“古而今”的承续,那么,“变异”则是一种“今而古”的承续,是鲁迅主体意识并未有异质文化的参与下的变异性承续。“变异”在鲁迅身上首先是由“家庭变故”引起的——一个百年旺族的急遽败落,随之而来的是长辈的怨愤,亲友的辱骂,同族的倾轧,世人的冷眼,使生性明敏、感应深切的鲁迅,过早过多地承受了世态炎凉的煎熬、摧折和人事变幻的惊异、震悚;随着鲁迅的人生与社会视域的不断扩展,他所目睹的又是与他的家庭变故几乎同时开始的中华民族最为耻辱的一幕,家难与国难集于一身,“变异”在鲁迅身上的产生就是一种必然,表现为:他本有的以浙东文化为根基的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被一定程度地打乱与调整,其中的传统文化因素或强化、或弱化,这促成了鲁迅不同于他的同胞、同乡子弟的独特的文化个性。
3.升华。这是最重要的过程,是在“复活”和“变异”基础上的“升华”,最集中地体现了鲁迅主体意识的参与作用。“升华”在鲁迅身上的产生,首先是与他执着于现实的品格分不开的。在严酷的现实中,面对一次次“血的代价”,触发的是鲁迅“无情面地解剖自己”,更加执着地摸索、探寻自己的人生之路。“升华”在鲁迅身上的产生,从根本上说,与他的“大家族”出身相联系,缘于他不断超越现实的精神特质——这与那种暴发户得意时的沾沾自喜、破落户失意时的顾影自怜的“小家子相”迥异,表现出开阔、恢弘的胸襟,清明、洒脱的气度,自由、开放的心态。鲁迅一生中出走南京,东渡日本,南下广州、上海,以及他醉心于进化论,求索于“超人”哲学,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真理,都显示了这种精神不断超越的“大家风范”。正是这种对现实的执着与超越,使鲁迅能够不断打破自身个性与传统文化的契合,不断消解传统文化的负累,最大限度地摆脱了古老鬼魂的纠缠,从根本上挣脱了任何在消极意义上的与传统文化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最富有积极意义的联系。
鲁迅成为“民族之魂”。
注释:
① 刘纳:《“五四”时期的两大作家群》,收《论“五四”新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版。
② 《书信·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8页。
③ 张建生:《鲁迅个性气质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2期。
④ 吴俊:《鲁迅深层意识管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2期。
⑤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⑥ 果戈里:《关于普希金的几句话》。
⑦ 周作人:《雨天的书·自序二》。
⑧ 参见钱理群:《心灵的探寻》第95页。
⑨ 鲁迅:《坟·杂忆》。
⑩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29《上辛楣宫詹书》。
(12)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3) 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复旦学报》,1991年第1期。
(14) 《书信·致江绍元》,《鲁迅全集》第11卷第567页。
(15) 周作人:《陶庵〈梦忆〉序》。
(16) 《书信·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8页。
(17) 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
(18)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
(19) 《书信·致黄苹荪》,《鲁迅全集》第13卷第306页。
(20) 载《读书》1986年第4期。
(21) 周作人:《看书集·苋菜梗》。
(22) 徐梵澄:《星花旧影——对鲁迅先生的一些回忆》,《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
(23)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卷五《浙东学术》。
(24)(28)(29) 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25)(35)(36) 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26)(27) 周作人:《地方与文艺》,《周作人早期散文选》。
(30) 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序》。
(31) 参见许广平:《欣慰的纪念·元旦忆感》。
(32) 费孝通:《乡土中国》第72页,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33) 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师爷笔法》,岳麓书店1988年出版。
(34) 周作人:《知堂乙酉文编·五十年前杭州府狱》。
(37) 周作人:《数典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