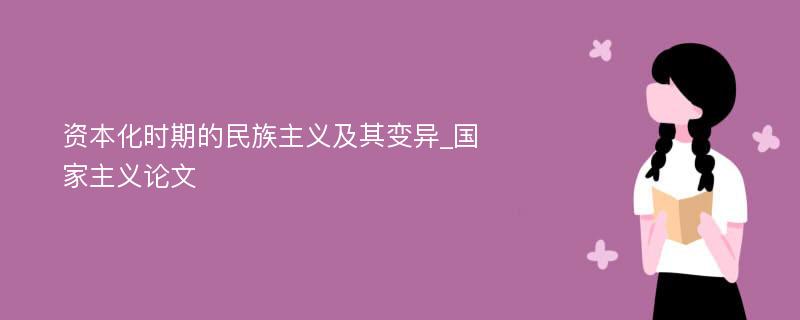
资本主义化时期的国家主义及其变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家主义论文,资本主义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国家主义是一个民族传统中积淀的政治文化制度的最高概括。它意味着种族、社群、家庭、占有制等一切社会关系都必须置于国家体制的约束和箝制之下,政治也被理解为某个群体有权决定国家政务的集体主义目标。本文旨在说明国家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激进主义思潮、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权威主义架构、众多农业文明国家的民粹主义理想等政治思潮的影响,以及这些国家主义变异在未来发展中的潜在作用。
[关键词] 国家主义 市民社会 乌托邦主义 次生的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
就历史实相言之,国家主义并不是一种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概括,而是具有类似历史文明和文化传承的制度要素的表征。它不受时代和体制变迁的影响,始终具有不可抗御的时间超越性和社会融合性。当资本主义文明产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以后,国家主义的思想建构一方面要在传统主义的环境中继续寻觅政治合法性的窠臼;另一方面又在理想主义的推动下扩展道德合理性的基础,这样,资本主义化时期的国家主义形态就变得更加迷离和复杂。
从本源上讲,国家主义是从国家形式运作中逐渐积淀的文化精神要义。它在长期的权力实践中又逐渐趋向系统化和理性化,并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催化下,发生各式各样的变异。随着资本主义文明对传统国家形式的批判和否定,国家主义的内在质素也越来越纷杂,它作为一种理性的统治,不仅有民主程式的变体,也有专制独裁的变体。在类似英、法、美这样的早期工业化国家中,国家主义与集体主义、乌托邦主义结合的直接后果,是导致了形形色色的激进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出现,显然这是一种大众政治的产物;在那些封建体制强劲的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主义与威权主义、专制主义结合得更加牢固,出现了象德、俄、日这样的军国主义加王朝政治的政体形式,这显然又是极权政治的某种变体。
在更多的政治文化落后的地区,那些恪守传统体制的国家,由于很少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渗透,国家主义仍然深深地植根在本国的政治结构和文化传统中。它们或是以大众革命的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君主体制,或是由上层改良的形式,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制度,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抛弃了封建化的某些形式,却在整体上保留了国家主义的内涵。
一、近代文明对国家主义的批判
近代启蒙是激烈抨击传统国家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过程中,最关键的是理性(Yeoson)在伸张自由和平等时产生的思想引领作用,它最终取代了对外在权威——无论是宗教意识还是政治权力——的顺从与依附。启蒙运动产生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这些是与国家主体结构的意识形态相对立的。代表旧制度旧势力的文化传统和统治方式,反映的是依靠宗法伦理和国家力量来获取特权和特殊利益的封建贵族的意志,这是传统国家建构的思想基础。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则是为了摧毁既存的君主制和贵族世袭制,建立独立的政治机构以及法律保障体系,取消门第特权。保障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集会、结社的自由,提倡权力平等,实行民主制度。这一切,由于并不仅仅是中产阶级的要求,也涉及到所有的人,因此中产阶级有可能建立起以他们为中心的新型国家。
这种近代政治国家的特征在于:国家可以接受个人有利于社会的欲望和要求,并保护他们的权利,包括私有财产、平等和自由等不可转让的权利,这实际是满足了市民阶层保护自己及其私有经济免遭国家权力压制的愿望,进而保护了整个社会不受国家侵害的理想。这种国家形式承认自由和平等是人类的最高福利,任何一个公民都不应富得足以奴役其他人,任何一个公民也不应穷得出卖自己。所以追求幸福和人权必然导致由国家确认私有财产的权利,而每一个人都可能因追求幸福而焕发自己的创造力和自由精神。正像卢梭(Rousseau)所说的,当人民遵守国家意志也像遵守自然法则一样,并且在认识到人的形成和城邦的形成是由于同一个权力时,人民能够自由地服从并能够驯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羁轭。
由于财富的源泉来自人的创造力,因此,能够决定国家富足程度的最关键因素是释放人的创造力的制度,这种制度把权利交给个人和社会,把限制加诸国家。这样,对于市民社会来说,重要的是确立保护公民自由创造财富的制度,否则,如果公民通过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不断被国家掠取或充用,他们创造财富的热情便不会持久。人们只有在有权利正当地占有劳动成果时,才会放手去创造财富,这就否定了传统国家主义的财富独占原则,并要求制度必须为创造者提供有效的条件和保障,公开承诺权利平等和人身自由的原则。这种原则仅仅表现为尊重产权、创造自由以及市场规则是不够的,它必须通过法制和分权来约束国家的权力,并通过公民参与的法律程序来确定他们的权力代理人。
近代的文明理论,导致了以自由意志和普遍福利为基础的国家理想模式的出现,这种国家形式,显然是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的制度化结构。它使每一个成员可以在不受国家权力侵害的情况下,去实现经济平等和政治自由,但国家公共权力又必须约束所有公民的行为,体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相一致的原则。这种理论的内在逻辑是:资本主义增加了生产效率,大大扩充了整体财富,虽然财富的分配未必是平均主义的,但国家目标可以保证每个个人所能得到的,能够超过以往任何历史阶段所能达到的水平。
近代文明理论对国家主义的持续批判,为建立资本主义新型国家确立了思想和伦理的基础,开创了将社会福利普及融入工业化的进程。这种工业化国家的特征包括:(一)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体制,它以市场规律为基础,通过法律精神和伦理体系把个人的自利纳入对公共利益有利的轨道,以此扩充社会财富,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二)尊重个人的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权利的民主政治体制,它注重从宪政制度上通过分权制衡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防止权力的滥用以及政治的腐败;(三)体现平等和正义的道德文化机制,蕴藉其中的是多元、开放和宽容,同时又具有充满活力的创造精神和文明生活的内容。这种由自由经济、民主政治和文化多元共同构成的社会发展模式,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在制度上有了严格的分界,它不仅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也能切实保障个人和社会免受国家公共权力的伤害,体现了国家目的与社会繁荣相一致的原则。
二、乌托邦理想的扩张
在历史的某一特定时期,国家主义与乌托邦主义能够有效地结合起来,将内蕴的大众政治的民主理想与平均主义的浪漫精神加以具体化。换言之,国家主义偏重于经济制度方面的重新组构,而乌托邦主义则强调政治革命先于经济改造,因为自由经济的失败,又唤起了集权控制的有效方式。在一些资本积累较早,经济和利益的自由竞争较为激烈的欧洲国家,各种政治思潮都是以国家为目标,主张从权力基础上进行彻底改造,这是依据进化论的历史主义模式,把国家组织的再造视为一种机械式的转换,所以,在主张人本价值的同时,更强调民粹主义的价值,并将这些价值延伸到政治秩序和社会制度中。于是,它们的基点都是寄托在国家机器和大规模社会组织中掌权的那些人的更替上面,希望通过国家所起的独占作用和再分配功能,来解决贸易与工业,富裕与贫困等一切问题,把社会的共同福利集中在国家权力的支配之下。
强调道德共同体的价值高于道德个体的价值,强调社会、历史、整体、关系等非个人因素在人类伦理生活中的绝对性,并将社会的正义与公平在道德范畴加以具体化、模式化,是乌托邦主义的基本特征。所以,在孔子和柏拉图之后,曾有过无数的乌托邦理想,把政治哲学引入人和人的生活,以期建立新的天国。它追求整体社会的秩序美、和谐美,并通过允诺人民的最大幸福——寻找一个先前不曾有过的外化世界,并从那里找到公平和正义。乌托邦主义是从国家可能消亡的角度,来设计国家威权对个人和社会的包容性,从伦理上塑造平等和自由的可欲性,并利用国家的力量来促进社会福利的普及。但乌托邦主义对集体价值的配合效率往往是凭空演绎的,因为它过高地估计了每个人的道德倾向,特别是那些在权力系统中主宰社会的人们的品德和意志。虽然乌托邦主义总是试图用传统、神话、符号、种族、荣誉等文化因素来补偿这一缺陷,但毕竟是一种比较简陋的意识形态系统,因此,为了实现社会改造的目标,唯一可行的方式便是从国家主义的义理中挖掘新的思想建构,作为精神价值的来源。
将乌托邦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民主程式联结在一起的目标是承诺人民有选择政府的权利,但不否认暴力作为社会变革的接生婆的不可避免性,相信彻底摧毁传统社会结构是包治一切的好办法,这将孕育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强制性国家的乌托邦社会的到来。这种新秩序从道德上排除了国家变成庞大官僚机器的可能,所以国家作为公民权力的最高代理形式,将废除私人企业,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而对生产、分配和交换工具实行国家所有和集体控制,而社会本身将通过它的政府组织来提供资本,并在保证公共福利和企业发展的基础上,满足劳工的报酬以及生活条件的改善。但是,从世界上所有地区的全部历史来看,政治统治和国家管理所能达到的公平与正义的程度,并非完全依靠理性的判断,而是取决于社会实际存在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条件。乌托邦主义是在资本原始积累和残酷竞争阶段的普遍绝望中权衡社会发展模式的,它的批判性意向容易从历史主义的超前或滞后的因素中,寻找那些用以对付不公正和不平等的东西。
显然,乌托邦主义是根据一个详细的计划来设计整个社会的,这一计划是预先概括的,所以这将是一个静态的和严格的社会图式。它的共同体主义的性质和结构,是以思想权威和道德典范来作为国家的中心结构,并确信这种特定模式的社会在运转中不会发生偏差,人们也不会超越社会所限定的价值目标,按照某种异端的动机或利益行动。所以,乌托邦主义希望通过大众化的道德认同或诉诸严格的逻辑理智,来推动产生理想的行为或活动,并使人们坚持理想类型的可欲性以及情理判断的道义性,相信个人欲望的任意放纵与私有财产毫无节制的膨胀,同属于一种不公正或不平等,从而把对旧制度的批判意识同改造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大众政治的变体。
乌托邦主义意识形态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产生的一种社会理想。资本主义的国家建构起源于思想启蒙和产业革命,因此这种制度一开始就拥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和道德的基础,自由主义得以壮大和发展以后,可以不采取过于激烈的暴力手段或政治行动便可以作为一种稳定的制约因素。而乌托邦主义仅仅是一种理想类型,本身并不具备建立社会制度所必需的经验和条件,这样,就必然从传统主义的历史经验论出发,寄希望于一些极端的手段,来补充物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力量的不足。乌托邦主义与国家主义相互结合的结果,是孕育了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 Capitalism)的形式,它的宗旨是首先颠覆那些掌握权力和财富的高等级阶层的统治,充分利用国家的力量来扫荡一切,以促进平等和利益一致的原则;它毫不妥协地敌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将集体劳动和合理分配的价值模式国家主义化,并力图拥有更大范围的道德合理性。这种社会正义的理念发端于对国家非本质意义的理解,即国家有可能会成为依附的力量,促使一个阶级对抗其他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建构通过对国家的美化而虚设了一个道德的共同体,其核心是国家的权威机构能够大众化和伦理化,而这正是乌托邦主义精神得以扩充的真正源泉。
历史已经表明,早期资本主义在经历长时间的艰难发展之后,逐渐摆脱了它所面临的各种困境。随着科技在工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经济和服务行业的迅速扩大,出现了大量的“白领阶层”。虽然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工资而出卖劳动的被雇佣者,但他们的利益和同情心已经与产业工人不一样:他们多数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或知识阶层的成员,甚至是潜在的资本家或商业利润获得者。由于这一部份人的数量有了惊人的增长,所以社会的中间阶层日益扩大的结果,大大减缓了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致使新的社会革命在发达工业国家取得成功的希望愈来愈渺茫,乌托邦主义的理想也愈来愈遥远地退缩到历史的阴影之中。
三、次生资本主义的特质
19世纪后半期,当西欧和北美的工业革命全面展开的时候,诸如德意志、俄罗斯、土耳其、日本这些地理位置独特而君主体制强固的国家,也相继开始了资本主义化的进程。为对付内外的压力和挑战,主张搞工业化的上层统治集团考虑并制定了有限改革的计划,目的在于加强国家权力并提高整体的实力。当教育、工业和政治制度开始有了惯性并产生一批参与发展进程的新型利益集团时,变革的速度就逐渐加快了。这种变革标志着从农业和农村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工业的和城市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持续的过渡时期,变革是靠内部力量发生的,它导致了一种次生的(Secondary)资本主义形式。
在这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缓慢增长的资本积累,以及工业技术领域的逐步扩大,促使传统的贵族阶层和武士阶层开始分化,并激发了新的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来适应这种变革。但是,一些基于民族立场和自身政治利益的集团,主张国家主权必须以某种强制形式维持自己的领土和人口的连续性,等级制度的隐性差别也使维护各自环境中的强权关系成为社会秩序的真正基础。尽管这些国家并不排斥目标具体的政治术语,诸如自由、平等、民主、权利之类的符号,但无法与自己的传统相衔接。这些维护传统体制的理论,是以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皇权主义的相互整合为核心的,它显然比“朕即国家”的理论更具合法性,也更适应次生资本主义形式的内在要求。
在德国,政治统一是依靠武力征服来完成的,它保留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传统。在国家强权政治的支配下,贵族、地主及其新生的大资产者,构成了社会的强大的统治力量,他们是现存资源和历史能量的最大拥有者,可以在较快的时间内,建立起新型的工业体系。但工人数量的剧增,并不是通过缓慢的社会分工或群体市民化形成的,而是国家对马克公社式的村社组织实行强制改造的结果,它使一部分农民发生了身份的转化,但意识形态仍旧停留在农业文明阶段。德国知识分子也多是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寻找力量,来适应城市变革的压力,这使得德国的激进主义运动都具有向后看的民粹主义性质,工人自治运动也带有浓厚的农业乌托邦因素。
俄国则是一个巨型的封建农业国家,同西欧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既是整个欧洲文化的积极参与者,也保留了独特的斯拉夫式的宗教文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次生类型的显著特征,许多现代企业的出现,都是在国家体制的范围内,由官僚和贵族兴办的,这些企业往往是国家主义化的。由国家强制实行的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主要是造就了大批的新式小农,并有少部分直接转入工人队伍。以贵族知识分子作为明显的反叛势力,是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的,并将民粹主义运动推向高潮,这对于俄国的国家主义思想的泛化,有着直接的影响。
土耳其(Turkeg)和日本(Japan),也是次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几乎很少有自发的资本主义因素产生,但因独特的地理政治位置缘故,使它难以抵御西方势力的渗透,在经济上有效仿西方工业化的强烈要求,但又把目标寄托在王朝政治的上层改革上面。土耳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帝国崩溃后激起的国家主义思潮推动下开始的,具有西方保守主义与伊斯兰复兴运动相互交汇的多元特征。日本是一个由同一种族的岛国构成的政治共同体,当西方文明逐渐融入的时候,它小心地不与外界发生这种接触,幕府政治乃至天皇制度的强固,使日本在选择西方工业化时,能以最小的损失改造以前的农业社会基础,其结果是使一部分高级武士贵族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成为工业化的中坚力量,而作为激进派的下级武士集团,并没有采取向前看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与本土化的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相结合,并把它们的价值标准转而整合为全体国民的精神形态。
德、俄、土、日这些次生的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不仅有相似的政治传承和社会背景,也有相同的意识形态维系。因为君主制国家的统治者,并不仅仅作为国家权威的象征,而且也把宗教领袖和道德权威的身份溶化在权力系统的威严中,它涵盖了民族的传统信念,全民的存在意识以及国家的皇权观念。这种精神和权力核心的概念,不一定局限于国家形式,但必须归属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化。所以,政治权力的合法范围不仅限于对民众外在行为的约束,而且通过宗教、理想、符号深入到民族的价值伦理中。在某些特定时期,这种国家主义的膨胀,极易产生一种狂热的扩张心理和仇外情绪。
历史上,类似德、俄、土、日这样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都是缘起于世界多变的动荡时代。它们进行的专制主义的改革,是国家内部力量催化跃变的结果。它们虽然都采取了废除传统农业制度的措施,但解放农奴的运动毕竟简单,更没有触及封建专制的基础。在吸收西方工业文明的同时,仍旧隐藏着原有的专制独裁下权力与资本相勾结的互动因素,这是成为独特的国家垄断兼容私人垄断的混合型经济的直接原因。由于国家资本的形成先于市民社会的形成,中产阶级的力量十分单薄,社会的支配力量则包括了仍旧守护着旧制度特权的贵族官僚,凭藉宗法势力暴富的新有产者,以及国家确认私有制以后出现的新地主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与国家权力结构共处于一个利益板块之中,所以,社会变革与资本积累的目的,都是为了适应具有自我生成能力的国家主义的膨胀。
在这些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下层民众与上层集团始终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迫使国家必须扩大它的社会强制功能。这样,国家主义也逐步变为一种普遍的蒙昧主义的运动,它和地缘政治,种族排外,宗教歧视,以及传统的不宽容、迫害、狂热混杂交融在一起,既是进一步走向专制集权的精神力量,又是走向垄断资本的帝国主义的政治基础,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某种变异,像后来德国出现的法西斯主义,俄国出现的苏维埃主义,日本出现的军国主义,以及土耳其出现的凯末尔主义等等,就是明证。
四、民粹主义与农业社会形态
众多的不发达国家由于深受农业社会文明方式的影响,其共同的特征是落后的农业生产占主导地位,人民普遍的生活水平很低,少数穷奢极侈的权贵集团凌驾于贫困的群众之上,阶级差别十分悬殊,社会对抗的形势始终无法缓解,民众朝思暮想要打倒剥削压榨他们的那一小撮人,后者则利用国家的暴力来维护其特权。但是,以暴力实现公平或维持特权的筹略,只是导致了统治层与非统治层之间频繁的权力转换,绝大多数的民众处境并没有得到多少改变。因为依靠暴力实现公平的道德传统不仅使社会自身结构不断遭到破坏,也往往产生追求人道与追求富足相互抵牾的负面效果,人们最终得到的只是形式上对平等、权利的空洞期许,而事实却不得不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庞大特权集团,只是将旧主子换成新主子罢了。这样的社会政治演变在广大的落后国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作为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国家的共同体形式不仅要从政治体制上维系一个民族整体的存在,而且必须参与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分配,为其成员提供相应的生存环境和合理秩序。所以,农业社会中一种普遍的趋势,便是民本主义思想与国家观念的契合,并蕴藉着组构最佳秩序和社会关系的愿望。与民本主义一样,源于相同历史脉络的国家主义,因此涵盖了传统伦理对社会共同体的全部认识:一是确认社会成员的政治归属和现实地位,二是承诺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及人身安全。这样,国家主义通过政治的领域性,血缘的亲合性,自然的道义性等方面的整合,使秩序有了共同的基础。
在大多数的农业国家,小农对宗法制度和皇权结构的依赖,反映了土地国有制下贵族统治农民也控制财富的社会特征。小农软弱分散的经济地位,迫使他们必须依靠宗法制度的保护,依靠国家的超经济强制来平衡可能出现的社会失序。由于人格依附和经济依附产生的政治归属感,小农阶层又滋衍了理想和权利被某种权威形式代理的观念,即由贵族、官僚中的知识分子构成的权威形式作为小农与国家之间的中介,这种中介并不具有被明确代理的身份,但有鲜明的道德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将民本思想与国家观念揉合起来,便形成了农业国家的最普遍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Populism)的思想建构。
民粹主义以建立公正的农民国家为宗旨,将农业文明的图式予以无限的美化,因此作为落后农业国家维护传统体制、抵御工业文明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对付自由、平等、权利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最有力的武器。民粹主义认同国家从身份上解放农民,并依此增强民族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凝聚力,但结果往往限制了对传统体制的突破;民粹主义认为减轻劳动阶层的困苦是政府的义务,但主观上又认为消灭差别、消灭贫困既不现实又不可行,因为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和生存条件本身就有先天的不同;民粹主义在某些方面沿习了国家一向是专制和压迫工具的思想,把改朝换代作为社会变革的唯一方式,主张全力进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来贯彻以暴力实现公平的历史主义的模式,但这常常成为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工具。所以,民粹主义在落后的农业国家的泛衍,既满足了民众摆脱贵族压迫的心理愿望,又为国家实行专制集权提供了道德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民粹主义既可以同外来意识形态接通,又可以与本土的传统制度融合,适应了农业社会的文明方式。
民粹主义来自农业国家知识阶层的精英意识。因为知识阶层通常是农业国家中官僚制度的补充体系,构成文人、缙绅、官僚的三位一体,他们一方面承当社会管理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又是乡土社会的精神领袖,人生目标和政治仕途都是和国家制度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农业国家并不具备西方工业社会的环境和条件,缺乏民主政治的内涵,所以多数人并不具备类似自由知识分子的素质,即抗拒暴政的勇气,批判现实的意识以及引领大众的能力,只要国家体制不过分地损害他们的利益,知识阶层便能够与统治阶级一道,共同维护现存的秩序。而那些反叛的知识分子在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同威权政治较量时,唯一可行的便是从民粹主义那里汲取思想的来源,结果自然又是陷入国家主义的桎梏,重蹈救世和治世的老路。
这些落后的农业国家,教育的政治用途是非常明确的,国家主义能够彻底地运用教育为国家目的服务。它不仅重申传统主义的文化保守气质,而且努力培育新的狭隘的效忠精神,包括灌输崇拜国家和个人的某个特定时期的荣耀或历史,因为粉碎旧的忠诚确立新的权威需要不同的偶像,这实际成为对文化系统的肢解。在普及大众教育方面,都是贯彻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行为说教,并以传统的最小损失来看待外来文化的吸收,所以只注重器物而排斥价值和观念。在传统体制下,知识阶层通常对社会变革并不热心,但对国家权力却十分崇拜和敬畏,所以能够自然地承担官师治教的教化使命。
落后国家一般都处于较低水平的自然经济和简单生产的阶段,社会的维持机制是以伦理纲常作为核心。政治结构向民间社会的渗透,构成了一个关联密切的秩序空间,切身的亲缘关系与近邻关系成为这种秩序的共同出发点,但这并非是一个完整的法的共同体,而是一个由共同秩序观念衔接起来的亲情和伦理的共同体,它从家庭、宗族、乡党的地方社会到以官僚体系为媒介的州府、朝廷,构成了国家一体化的共同体领域。在国家的封建化早期,民间社会的共同性、全体性不一定隶属于国家,它们自身是自立的,但是随着国家主义向民间社会的深层渗透,民间社会的共同性便从属于国家了。国家主义的超越性发展,使社会既没有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界限,也没有市民阶层和市民社会的概念,它一方面通过群体与国家的关系保障民族的统一,另一方面又通过区域与国家的关系来维持差异和分散。这种形式,既体现了领土的连续性,又保留了传统的完整性,是国家主义涵容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理想图景。
但是,当落后的农业社会方式沿着国家主义的建构来确定自己的政治领域时,往往面临无法克服的矛盾:其一,当运用民族文化的价值来促进社会进步和抵御外来干涉时,民族的共同利益要求对文化建制进行全面的反思,但政治的伦理方式却要求对文化传统的忠诚;其二,当运用自由经济的价值规律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并增加整体财富时,虽然社会的共同价值要求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但政治的传统机制却要求对全社会的集权;其三,当运用个人的创造力为社会提供文化和财富的来源时,个人的存在价值要求伦理体系对自由、平等、权利给予认同,但政治结构中的集团利益或群体取向却要求个人对威权的屈从和妥协。这样,以民族、社会、个人为责任能力的价值系统很难在这些落后国家的社群关系中确立起来。
Nationalism during the Capitalistic Period and Its Variation
Gao Hongji
[Abstract] Nationalism is a highly condensation of political-c-ulture system accumulated on the tradition of a nation.It means all human relations in society such as race,community,family,possession s-ystem have to be controlled and restrained within the state system wh-ile the politics is regarded as a target of collectivism,which a cert-ain group possesses the power to make decisions for government affair-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ismon some political trends of thought,from radicalism in the early stageof capitalist countries,to the frame of authoritativeness in its laterstage,then to the ideal of populism in many agricultural countries wi-th civilization.It is also expounds the potential role played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by the variation of nationalism.
[Key Words] nationalism
socety of urban inhabitantsUtopiasecondary capitalism
populism
标签:国家主义论文; 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贵族精神论文; 自由资本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贵族等级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体制化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