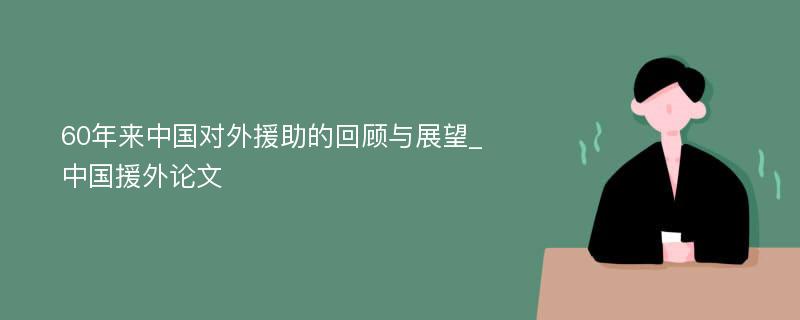
中国援外六十年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六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国与国之间众多的交往渠道中,对外援助是一条受关注程度不高、但涉及面和影响力都极其深远的渠道,它上达国家首脑,下通黎民百姓,在国家关系中扮演着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作用。在当代多种外交工具中,对外援助是形式最为多样的一种,它既可以政治面貌出现,又可以经济生产、财政预算、建筑工程、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许多方式出现。此外,对外援助所承载的使命也极其丰富,它的目标不仅限于建筑的完工、服务的提供、资金的拨付,而是通过这些任务的完成去体现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国际发展,乃至人类诉求。有鉴于此,在中国对外援助60年之际,有必要重新认识对外援助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并探讨中国对外援助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中国援外六十年的成就
在60年的中国援外历程中,有很多可歌可泣、可书可表的往事。最广为人知的故事是:1950年,新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家百废待兴,财力和物力都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毅然向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朝鲜和越南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援助,战争结束后又将援助扩展到经济和技术领域。1955年万隆会议后,中国援外的对象逐步从社会主义国家扩展到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为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提供了真诚无私的援助,并且把这种援助看做自己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看做朋友、兄弟和同志之间的互助。毛泽东主席说,“已经获得革命胜利的人民,应该援助正在争取解放的人民的斗争”①,表现的就是这样一种“同志加兄弟”的互助性国家关系。中国帮助兄弟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兄弟国家帮助中国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围堵和孤立。
“同志加兄弟”式国家关系的本质特征是大小国家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体现在中国对外援助中就是周恩来总理亲自制定的“八项原则”。“八项原则”提出:中国政府根据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对外援助,从来不把这种援助看做单方面的赐予,而认为援助是相互的;中国政府在对外提供援助的时候,严格尊重受援国的主权,绝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政府对外提供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而是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政府派到受援国帮助进行建设的专家,同受援国自己的专家享受同样的物质待遇,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②但中国对外援助原则中体现的这种平等的国家关系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在有关国际关系的论述中却遭到忽视、曲解甚至指责。
尽管如此,中国对外援助并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从中国和受援国的实际出发,相继提出过“平等互利、讲求实际、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四项原则。进入新世纪以后,又制定了对外援助的“五大举措”③、对非援助的“八项政策措施”,创建了“中非合作论坛”机制,提出了以人为本、关注受援国社会民生等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和政策,树立了“南南合作”的典范。在庆祝中国援外6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评论员热情地写道,“60年援外之路,‘中国模式’独树一帜”。④
对外援助的“中国模式”,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对外援助,的确取得了难以估量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得益于多重的制度和政策保障,更得益于往往被国际关系评论者们忽略的中国软实力。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时代,中国曾经在涉援各省及部委设立“援外办公室”,形成了条块结合和全国一盘棋的网络体系,在中国自身能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有效地调动了全国的各种资源,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的援外攻坚任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中国又在全国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尝试了政企分开等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在援外项目招投标、分段管理、标准制定和监督检查等方面进行了无数次探索,制定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一些援外管理程序和办法。更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援外人”——从事援外工作的中国建筑工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疗队员、青年志愿者们,是他们在异国他乡经受了恶劣气候、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甚至战争环境的考验,用他们的辛勤劳动、无私奉献、敬业精神、精湛技艺、平等态度和英勇牺牲,在受援国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佳话。在很多非洲国家,当地人见到中国人,就会竖起拇指,连称“工作、工作、工作”。正是那些来自中国各地和各界的中国民间大使们,通过他们在受援国的援助工作,为中国人赢得了“忘我工作、不知疲倦”的美誉,⑤赢得了来自受援国人民的“中国人不能走”的呼声,⑥起到了其他外交渠道起不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中国和受援国之间的发展合作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典范。
二、对外援助的时代目标和时代主题
进入21世纪以后,对外援助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逐渐得到重视。新世纪伊始,18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领导人就《联合国千年宣言》达成了一致,承诺在2015年以前将全球贫困人口比例减半。宣言包含了8项“千年发展目标”,⑦以及相关的18项具体目标和48项指数。宣言还呼吁加大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承诺,特别是要使对非洲的援助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增加一倍。
上述这些目标虽然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但要想实现这些目标,还需要通过可行的方式,整合利益不同、制度各异的各主权国家和其他国际行为主体的努力和行动,形成合力。然而,国际援助领域里的现实情况是:各主权国家和国际行为体对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还存在着不同的认知,在从事对外援助工作时抱有不同的动机,它们实现援外目标的方式也很不相同。虽然联合国号召在国与国之间加强合作、调动社会各界(包括政府部门、私营企业、民间团体、普通民众以及新闻媒体)的力量,参与到国际发展的事业中来,但是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目前在国际发展援助领域里仍然存在着差异很大的政策目标、实践活动和话语体系。
美国在“9·11”事件以后恢复了对援外事务的重视。国际安全局势的变化和非对称战争的出现,使对外援助这种具有多重对称或非对称特点的对外政策工具显示出独特的优势。2002年美国和欧盟经过磋商,决定大幅度提高对外援助的力度,并为此重新调整了美国援外的机构和政策,其中包括赋予美国军方以实施驻在国经济技术援助的权力,使美国对外援助更显出其“战略化”和“政治化”特征。欧盟自2000年以来就一面承诺提高对外援助额,一面推动各成员国之间对外援助政策和实践的“互补性”、“协调性”和“一致性”,加紧调整援外战略、政策和机制,提升对外援助在对外关系中的作用。欧盟在发展中国家的外交人员中,有多达50%-70%的人力在从事对外援助领域的工作,对外援助作为欧盟主要对外政策工具的特点也十分明显。
美国和欧盟在对外援助的主体目标和实施方式方面有相同之处,但也存在不同的侧重。美国将反恐和防恐作为援外的首要目标,认定“脆弱国家比进攻型国家”更容易滋生威胁美国安全的恐怖主义,⑧要通过对外援助投资,将“脆弱国家”改造成“民主”国家,借以根除恐怖主义的土壤,因此“民主输出”就成为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重要主题。欧盟及其成员国共同构成世界上最大的援助方,这个松散的整体需要将大量财力和人力用于统一政策目标、协调援助行动、规范衡量标准等内部事务,还需要通过一致性的行动来扩大和规范世界经济贸易秩序和规则,使之有利于欧盟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贸易体。“规则”和“秩序”无论对于欧盟内部事务还是对于欧盟的世界地位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欧盟援助将“稳定受援国的秩序、管理冲突、控制移民、促进投资、增加欧盟在受援国的市场份额、获得受援国的友谊”⑨作为主要目标,而“维护秩序”、“推行全球治理”则是欧盟对外援助的时代主题。
美国和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内部政治程序,导致它们在对外援助政策制定方面采取某种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从发达援助国援款拨付的程序来看,最能够打动拥有投票权的国会议员们的议题是由他们确认的国家利益和外交考虑。因此,如果将对外援助“与外交考虑脱钩”而只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就会使这些国家的援外拨款“不可持续”。⑩援外可持续的动力不仅来自外交战略,而且来自这些发达援助国内部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参与。例如,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的首要目标是西半球战略,经济目标和人道目标要补充战略目标,而在具体援助项目的批准过程中还夹带着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不同关注,如通过粮食援助解决美国粮食过剩问题。欧洲共同体“援助联系贸易”的目的不仅是维护欧共体在世界上已经占有的工业和贸易优势,还包括通过一系列由援助国指定的测量指标,来满足欧洲社会对于“援助有效性”的要求。这种根据援助方制订的标准而确认的“援助有效性”,是援外性拨款的重要依据。援助国自身的政治规则和政治偏好,使它们的援助“从重视提供项目和服务,戏剧性地转变为一种关于权利和治理的语言”(11),进而变成让受援国感到厌倦的说教。
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它们在新时代的共同诉求,是无可争辩的时代主题。以“官方发展援助”名义提供的国际援助,无论是以资金,还是以技术、知识,或是以基础设施项目、人才培训等形式出现,都在发展中受援国受到欢迎。来自多边和双边渠道的各种援助用途非常广泛,有些可以用于提高受援国政府的威望,有些则用于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还有些可以视作为受援国提供各种发展机遇。虽然有不少受援国对“什么是发展”和“怎样发展起来”还有不同的认识,但是它们都希望借助外来援助,实现自己在新世纪的发展目标。
从受援国的角度观察,西方援助大体集中在民主建设、国家治理、观念传播、非政府扶持等“软”领域,项目选择往往以援助国为主导。因为传统的西方援助国需要同时照顾国内社会各界的利益和意见,所以很难做到急受援国之所需,在扶危解困济贫等活动中也要按照自己的规则行事,难以设身处地从受援国的发展规律着想进行规划。这种援助倾向并不为受援国喜爱。虽然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接受了西方的发展观念和思路,但是这些观念和思路距离现实发展需要过于遥远,也缺乏成功经验的支撑。此外,西方援助者即使是抱着提供援助的善意,也常常会以一种居高临下和指手画脚的态度对待受援国,让受援国感觉受到“羞辱”。(12)这种高人一等的地位还特别地体现在援助者的个人收入上。很多受援国抱怨说,西方援款的25%,甚至更高的份额,都被作为援助国专家的报酬而返回了援助国,这些费用应当从援款中扣除。
相比较而言,中国援助虽然在数量上无法和传统援助方相比,但是却通过自己成功的发展经验,为尚未发展起来的国家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使受援国看到了发展的前景并增强了自主发展的信心。这种认识最近十年来在受援国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和认同。此外,中国援助以高效、雪里送炭和急人所需而著称。连西方观察者都注意到,中国总是能快速地向受援国提供它们最急需的项目和物资。(13)更重要的是,在发展中受援国看来,来自西方的财政援助固然数额巨大,但是如果这些资金的使用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按照受援国自己的国情投资于优先发展的领域,那就不仅是在国际援助关系中继续保持着国家间的不平等,而且就发展规律来说也是本末倒置的。受援国欢迎中国援助,不仅是因为中国援助不附加政治条件、有效率、讲质量,还因为中国援助比较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水平,尊重受援国的国家主权和尊严,并且能够通过大量的基层发展工作使援助国和受援国人民发生接触,满足受援国切实的发展需求。在多数情况下,中国工程人员和专家的待遇甚至低于受援国的相关水平。中国援助从物资、工程到人力都体现了优质、高效和低廉。
从中国的角度看,中国是一个具有成功实践经验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采取过许多措施,将外来援助与自身发展密切联系起来,摸索出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引导、规范和管理外援的方式,这既是中国人民的财富,也是人类减贫和发展事业的财富。西方观念普遍认为,国际援助并不直接导致发展。但是中国却能在接受国际援助的过程中,坚持“以我为主”和“为我所用”,主动地把国际援助作为发展的工具,作为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和观念的渠道,这一经验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对外援助。在中国向受援各国提供援助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发展中的问题,不断地创新方式,使世界发展出现了一个良性的梯形进程,中国在向前向更高处发展的同时,也将发展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传导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形成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
中国对外援助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快速调动和充分利用国家在各个方面的资源,除了经验的资源以外,人力资源和市场力量资源在中国对外援助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84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部发出《关于巩固建成经援成套项目成果的意见》,提出在援助项目建成后加强与受援国方面的技术合作,并且根据受援国的现实需要,参与中国援建项目的经营管理。中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根据协议,在援助项目结束后留在受援国一段时间,将工程技术和管理技术传授给受援国的相关人员,体现“授人以渔”的发展理念,也有利于增进人民之间的合作与友谊。上个世纪80年代,外国私营资本追随官方发展援助涌入中国,给中国发展带来了加速度,这使中国注意到国际援助对于带动国际投资、进而带动发展的作用,并开始有意识地与国际多边援助组织和基金合作,对非洲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和服务。这种趋势逐渐受到受援国政府的重视和欢迎。1995年10月,中共中央在改革援外工作的会议上提出: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吸引更多的外国企业投资,以便增加收入和就业,更快地发展起来,中国将鼓励中国企业以合资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参与受援国的发展事业。因为这将“有利于政府援外资金与企业资金相结合,扩大资金来源和项目规模,巩固项目成果,提高援助效益”。(14)为此,中国在物资援助、现汇援助、低息和无息贷款等传统援助方式的基础上,增加了贴息优惠贷款的援助新方式,投资了受援国不少有发展潜力的领域,如能源、交通、信息等,加快了受援国的发展速度,受到了受援国的欢迎。通过对外援助,把中国的发展和受援国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共同发展既是受援国的需要,也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历史经验证明,中国不可能脱离外部世界而孤立地发展起来,帮助其他国家发展也就是帮助自己发展。对外援助带动了包括观念、经验、技术、资金、物资等在内的多种要素的跨国流动,这是成功的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也是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途径。在未来的世界上,不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事业需要中国的支持,而且广大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发展需要,正在成为中国继续保持快速稳健发展的动力和保证。
中国的成功发展还得益于一个多样共存的国际环境,只有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充分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15)的条件下获得发展,才能证明中国发展道路的可行性,并保证其可持续性。
同时还应当注意到,对外援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可以起到规范市场力量行为、弥补市场力量不足的独特作用。不少资源型非洲国家能够比较快速地发展和繁荣起来,有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利用外来援助,投资那些私人资本不愿意投资或者没有能力投资的领域,获取和掌握对于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16)在这方面,中国援助和贷款做出的贡献已经在国际上得到承认。(17)
对外援助使中国和受援国的人民能够进行近距离的交流与沟通,从而增进人民之间的友谊与理解,破解对于中国形象的歪曲,创造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多的发展合作机遇。因此,围绕着发展主题开展对外援助,既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求,也应当是中国对外援助的基本方向。
三、展望中国援外事业的发展
随着中国的全面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对外援助的力度可望继续加大。邓小平早就预言说,将来中国发展了,会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作更多的贡献。(18)他在1986年会见马里总理特拉奥雷时特别强调:“要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将来发展了,但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把帮助穷朋友摆脱贫困作为自己的任务。”(19)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秉承邓小平的遗训,多次就发展中国家的减贫与发展问题发表讲话、制定方针和措施,承诺并切实增加了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贫穷国家的援助。
中国对于发展事业的贡献不仅是数额上的。在短短60年的发展历程中,新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的发展经历与西方发展历史最大的区别是,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发展的过程中逐步消化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没有将这些负面影响推向外部世界,没有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和世界战争。这种渐进性的发展有大量值得总结和可供人类分享的财富。此外,中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的发展经验不仅鲜活而且更加接近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中国援助最初集中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工程建设领域,帮助受援国建造了公路、铁路、桥梁、电站、水利设施、公共场所等基础设施;而后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国又开始向受援国提供社会民生设施、教育培训基地等。中国在总结自身发展经验的时候发现,投资教育是发展的捷径和必由之路,于是在对外援助中注入了更多的教育、培训、知识传播和技术转移内容。中国在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认识均衡发展、绿色发展的同时,也在对外援助项目中设计了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环境的因素。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将更加有意识地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并且通过对外援助,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传播更多的宝贵和切合实际的经验。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对外援助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在中国庆祝援外工作6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强调得更多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改进工作,使中国援助能够更好地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服务。在2010年8月14日全国援外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做好新形势下援外工作要在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帮助受援国自主发展和完善中国援外体制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努力。(20)温家宝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进措施,包括:援助要向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国倾斜,应当根据不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需求,提供受援国急需和受当地人欢迎的民生项目,应当加强对援助项目的可行性评估、搞好项目招投标和监督、培养好援外队伍、调动民间和企业力量参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积极性等等。所有这些政策和措施都是针对发展和发展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的,都反映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发展主题。对于把中国对外援助看做抵消西方援助的投入和努力的误解和批评,(21)这是一种温和有力的回应。
四、加强有关对外援助的研究
与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相比,中国有关对外援助的研究显得十分滞后。除了石林主编的《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1989)一书比较完整地记述并分析了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政策、措施、体制和实践以外,中国对外援助的丰富生动的史实大都散见于中国领导人的文集、文稿、文选和年谱、当事人的回忆录、以及大量与外交史相关的著作和文章中。讨论对外援助的论文则多数聚焦于史实的澄清和政策的讨论,缺少深度的理论探讨和深入的实证调查。在国际上,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研究却出现了比较热闹的场面:与恶意炒作中国对外援助的潮流相对照,以黛博拉·布罗蒂加姆教授的《龙的礼物:中国在非洲的真实故事》(22)和孟洁梅教授的《非洲的自由铁路:一个中国的发展项目是如何改变坦桑尼亚的生活和生计的》(23)为代表,出现了一些有关中国对外援助的严谨求实的研究成果。美国和欧盟的一些政策部门也开始组织对中国对外援助成功经验进行实地调查研究,作为它们修订自己政策的参考。
中国对外援助研究的滞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理论工具和方法论的匮乏。对外援助是跨部门的工作领域,涉及多种专业知识。对外援助将中国与发展中受援国的关系具体化为诸如项目的贷款、体育场馆的建设、公路桥梁的架设、医疗服务的提供、培训课程的制定等业务,如果对于这些业务一无所知,例如对于统计方法缺少概念,对于医疗卫生规律全无了解,对于经济贸易知识一知半解,仅凭少量的国际关系理论话语是无法就对外援助开展深入研究并获得真知灼见的。
此外,对外援助的提供者具有各自不同的援助动机和援助方法,这也是研究对外援助的一个难点。研究者需要在聚焦于一个方面和一个角度(外交角度,抑或是经济技术角度,或者其他角度)的同时,了解这个角度在复杂的援助关系中的具体地位,避免以偏概全。
在当今世界上,无论援助者出于怎样的动机,都难以绕开对外援助的时代主题: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世界的均衡发展。发展的议题不仅包括经济贸易和技术发展,更包括发展的所有方面,包括市场的培育和规范、政府的职能与效率、社会结构与社会分配、教育进步与知识创新、文明程度与理论研究水平等等。中国在综合发展研究方面缺乏理论积累和基础训练的缺陷,也暴露在对外援助的研究领域。
在最近几年间,中国的研究者对国际援助这个“冷门中的冷门”(24)议题表现出了更多的关注和兴趣,相关的分析也越来越多。但是理论的研究仍然明显地落后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当我们的研究者面对受援国代表的时候,他们只会用很少的言语来表达对中国对外援助的感谢和赞许,会用我们熟悉的语言来称颂国家间的友谊,但是却会用更多的时间询问中国在建设的方方面面是怎样取得成功的。他们会细致地询问:中国针对外国援助的制度设计理念和方法是怎样的?中国农场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怎样管理一所医院?甚至怎样撰写社会服务人员的工作简章?如果我们的研究不能深入到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就不可能打破西方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国际话语体系,也不可能指导中国对外援助事业的纵深发展。
因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实践经验丰富深厚,对外援助研究的领域天高地远,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也意义重大,正当其时。
注释:
①《毛泽东主席接见非洲朋友的谈话》,《人民日报》,1963年8月9日。
②参见周弘:《中国对外援助与改革开放30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11期,第33-43页。
③即2005年胡锦涛主席在联合国所宣布的有关部分商品零关税、免债、优惠贷款、抗疟疾药、加大培训力度等“五大举措”,人民网,2005年9月16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8198/52409/52414/3702055.htm.
④人民日报评论员:《平等互助 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8月14日。
⑤中国公司员工比在当地工作的欧洲和日本同行的工作时间更长、更努力、更负责。R.Kaplinsky,D.McCormick and M.Morris,"The Impact of China on Sub-Saharan Africa",IDS Working Paper 291,2006,p.8.
⑥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38页。
⑦包括消灭贫穷饥饿、普及初等教育、促进两性平等、降低儿童死亡、改善产妇保健、与疾病作斗争、环境可持续力和全球伙伴关系等。
⑧Andrew S.Natsios,"Five Debat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The US Perspective",Development Policy Review,Vol.24,No.2,2006,pp.131-132.
⑨本文作者2010年10月对欧盟委员会发展总司官员访谈纪要。
⑩Andrew S.Natsios,"Five Debates 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The US Perspective".
(11)Rachel Hinton and Leslie Groves,"The Complexity of Inclusive Aid",in Leslie Groves and Rachel Hinton,eds.,Inclusive Aid:Changing Power and Relationship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London:Earthscan,9004,p.4.
(12)Deborah Brau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149.
(13)Bernt Berger and Uwe Wissenbach,EU-China-Africa Trilater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Common Challenges and New Directions,Bonn: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ltik,Discussion Paper 21,2007,p.13.
(14)王昶:《中国高层谋略·外交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68-169页。
(15)江泽民:《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载《江泽民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9-110页。
(16)Goran Hyden and Rwekaza Mukandala,eds.,Agencies in Foreign Aid:Comparing China,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anzania,Macmillan,1999,p.19.
(17)Ai Ping,"China's Cooperation with Tanzania,1965-1995",in Goran Hyden and Rwekaza Mukandala,eds.,Agencies in Foreign Aid:Comparing China,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anzania,p.192.
(18)参见邓小平:《实现四化,永不称霸》和《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2、194-195页。
(19)《邓小平会见马里总统特拉奥雷时的讲话:中国将来发展了仍属第三世界》,《人民日报》,1986年6月22日。
(20)《人民日报》,2010年8月15日,第1版。
(21)Bates Gill,Chin-hao Huang,and J.Stephen Morrison,China's Expanding Role in Africa: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A Report of the CSIS Delegation to China on China-Africa-U.S.Relations,November 28-December 1,2006,p.3.
(22)Deborah Brantigam,The Dragon's Gift,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23)Jamie Monson,Africa's Freedom Railway:How a Chinese Development Project Changed Lives and Livelihoods in Tanzania,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9.
(24)笔者在《对外援助与国际关系》一书(2002)发布会上曾经说过,有关国际援助的议题是“冷门中的冷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