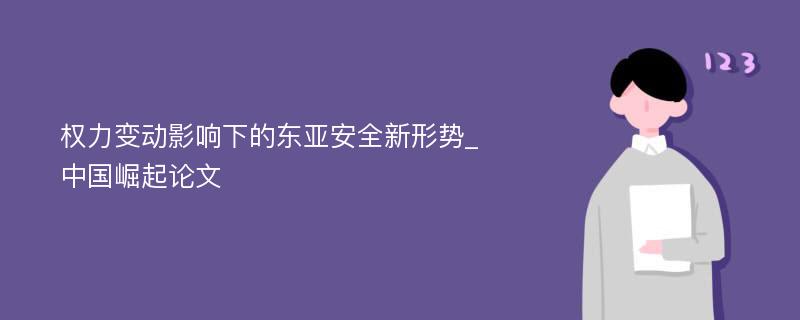
权力变迁冲击下的东亚安全新态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态势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2-09-12]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9550(2012)10-0132-17
21世纪头十年,世界经济和政治的重心“东移”趋势明显,亚洲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权力场(powerhouse)”。东亚地区安全最突出的“问题转变”是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发展。尽管学术界对于中国崛起有着各种不同的分析,有人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候补超级大国”,有人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大国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人认为中国有可能和美国重回“两极体系”,然而,中国崛起迄今所带来的变化并非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而只是带来了有限的“权力变迁(power shift)”。①之所以有诸多的猜测和观察认为中国崛起带来了国际权力结构的决定性再分配,很大程度上是主观因素。即便如此,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确实已经成为重组东亚区域安全新格局的重要力量。中国周边大部分国家担心中国崛起之后会实行扩张性政策,开始转而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和防务合作以及增加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来牵制和防范中国。在此背景下,“美国因素”反而在心理和观念上更容易被接受,“中国因素”却常常由于缺乏“亲近感”和“不确定性”,在后冷战时代上升为地区安全最主要的防范对象。②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针对中国崛起的战略调整究竟基于什么样的意图和目标,美国是重在继续接触和影响中国,还是将实质性地转向遏制和包围中国?显然,分析东亚安全新态势的核心要素并非是权力结构或者权力再分配等这些传统型的结构变量,而是在于各国相应的政策与战略考虑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东亚安全格局演变的未来,形成新的一波安全互动关系。为此,本文将分析东亚权力变迁背景下主要国家的安全与战略选择,力图解释权力变迁所产生的安全影响。
一 “权力变迁”与“权力转移”:理论内涵的差异
主张中国崛起有可能带来国际动荡的诸多看法很大程度上与权力转移理论有关。奥根斯基(A.F.K.Organski)完成了权力转移理论概念的构建与核心假设的提出。③“权力转移”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基本定义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因为工业化进程的影响和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同的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会因为其权力表现的不同而发生决定性的变化,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而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这一难以避免的权力变化过程。国家在国际权力分配结构中地位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权力竞争和冲突,因此,战争更多的是爆发在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逆转、相互权力对比开始接近的时刻。奥根斯基断言,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传统地位接近于发生转变,就是大国间的权力转移,而非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权力政治带来战争和冲突。
权力转移理论本身并非是国际关系学界的主流理论,但其所提出的理论命题却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权力转移理论的缺陷是抛弃了影响国家间安全互动的诸多核心要素,例如对威胁的认知、安全政策的决策过程、国内政治要素以及军事技术手段的变革等,而过度集中于自己理论的基本假设: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出现某个“特定时刻”最容易产生冲突和战争。例如,一代又一代的权力转移理论学者认为,当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的权力对比达到6∶5或者5∶4时,最容易产生权力更替而引发军事冲突。今天的国际关系学者接受奥根斯基所提出的权力转移将导致冲突的基本认识,但并不简单地认为权力转移一定就产生战争。朱锋和罗伯特·罗斯(Robert S.Ross)认为,在宏大的权力变迁过程中,主要大国之间的政策与战略互动是判断和决定这一过程究竟是否带来冲突甚至战争的主观性原因。④即便按照权力转移理论观点,权力转移导致冲突,但奥根斯基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单纯性、绝对性的权力对于国际格局的调整并不具备实际意义。只有当权力的变更导致主要大国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决定性的变化时,引起冲突的权力转移才会出现,才具有真正的实际意义。⑤换句话来说,权力转移理论并不认为一般性的权力变迁会引起冲突,而是认为主导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权力对比出现了决定性变化,即权力对比已经达到了“相对平衡”程度,战争的“节点”就出现了。由此权力转移理论把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大国总是追求有利于自己权力优势的“相对权力”狭义地定性为“相对平衡”,并以此作为主导性的指标来分析大国间的战争与和平关系。
随着大国崛起,权力转移事实上是一个持续的权力变迁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究竟对已有的权力变迁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权力变迁究竟如何影响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对于这些更加具体和现实的国际关系问题,权力转移理论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权力是国际政治的基本要素,在国际或者地区格局中权力的变迁与安全关系密切相关。“权力是一种可能有用的手段,明智的政治家总是力图拥有适度的权力。在重要关头,国家最终所关心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安全。”⑥“安全”这一词汇的意义在古代汉语中基本以“安”字来表示,直到现代汉语,“安全”才最终成为一个一体化的词汇。⑦从西方的词源上来说,“安全”就是“有信任、保证和确定性的基础”。⑧在西方思想史上,安全与自由和财产权联系在一起,体现为一种基本的价值观。⑨进而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里,秉承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基本理念价值,把安全视为国际政治的基本价值观。⑩权力变迁过程将难以避免地导致国家间安全互动关系的变化。“安全”在国际政治中的定义随着人们认识世界的不断深化而进一步丰富充实,不同学者对其定义不尽相同,有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区别。尽管如此,权力变迁也是引起非传统安全认识与互动变化的直接动力。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奥利·维夫(Ole Waever)在其著作《新安全论》中提出了“新的综合性安全分析框架”,将只重视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传统安全观发展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五个领域互动的新安全观。(11)但非传统安全的本质是希望提醒现实世界的学者们不要将权力变迁过程中的安全视角只单纯狭隘地局限在传统的军事、外交和战略领域。
权力变迁之所以先于权力转移产生安全关系的变化,是因为权力仍然是国际关系中实现安全的必要手段。权力变迁必然会引起安全感的消长、新安全议题的出现、安全纠纷的深化以及安全关系的调整,地区安全格局的变化常常因此而在所难免。“国家能够而且确实在追求其他目标,但安全是其最重要的目标。”(12)在现实政治中,安全的稀缺性是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常态,各个行为体都在增强自我安全感,竭力弱化威胁或者增强自己应对威胁的能力,保证在体系中处于相对的权力优势地位,这种方式使得行为体之间往往以敌对者或者竞争者身份去界定彼此,“安全困境”由此产生。为了增强自身的权力,保证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一国往往采用增强军备、加强同盟、分化潜在威胁对象国等打压方式强化自身权力,这种做法会被其他国家视为威胁,进而导致基于安全问题上各行为主体难以跳脱的历史“周期率”——安全困境的产生。(13)
问题是,权力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并以什么样的方式导致安全关系的调整和地区性安全结构的重组?权力转移理论在论及此问题时,没有直接提及权力与安全的关系,而是将权力转移与国际(地区)秩序做了直接的链接,认为权力的相对增加或者降低将导致权力要素的重新流动和配置,进而撼动国际(地区)秩序,使之进行符合现实权力的变革。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地区)秩序的变化是通过一系列具体过程和事件体现出来的,安全关系的变更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全”是一个综合性的、涵盖广泛的概念,既包括具体安全战略和安全同盟,也指观念性的相互安全认知。权力变迁促使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大幅度调整在世界历史中屡屡发生,有时以极端形式——例如烈度较强的局部战争或者世界大战——来完成,有时以和平过渡的形式完成转移。奥根斯基敏锐地看到了权力转移的实际结果是国际(地区)性安全格局和安全秩序的变化,认为国际(地区)安全秩序是否能和平演变,将严重影响大国间的权力转移结构。但权力转移理论对地区秩序的研究只是集中在权力转移与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重在一个新的地区秩序是否能包容、和平地接受传统主导国家与新崛起国家之间的决定性权力对比关系的变化,并没有深入研究这一安全秩序与大国间的安全互动过程究竟有什么样的因果联系。通过对近十年东亚安全的动态研究,笔者认为,奥根斯基的权力转移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中国崛起背景下东亚区域安全的新形势。并非是决定性的权力转移、而是大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本身就已经足以产生国家间安全互动关系的新变化。这一变化和调整的过程,不仅将决定未来是否出现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更将决定权力转移会产生什么样的国际(地区)秩序。
二 权力变迁进程中的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2001-2011年是东亚权力变迁明显加速的时期。这10年的最大变化是中国军费持续两位数的增长,中国经济也保持了平均9%以上的增长幅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美国在这10年中继续深陷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产生了美国实力相对下降的趋势。中美实力对比的“一升、一降”让世界印象深刻。美国对华战略自冷战结束以来开始酝酿变化和调整。2011年11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在夏威夷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议,美国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14)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高调宣传要“重返东亚”,强调了东亚安全在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但客观来说,美国从来没有离开过东亚,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说到底就是美国开始调整全球安全态势,重新明确美军未来的战略重点,确保所谓亚太地区是美国本世纪内的全球战略重心。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不仅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上,而且也在同盟与防务体系的建设上都将出现美军全球安全态势决定性向亚太转移的趋势。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的东亚安全战略一直以防止出现竞争性的“同等实力的大国(peer competitor)”作为战略重点,其主体是美国的前沿驻军和同盟体系。2003年之后,这一体系又进行了主次关系的调整,转变为更具有战术战役展开能力的“轴-辐体系”。但这一波美国亚太战略调整最显著的特点,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第一次在亚太地区扩大军事存在,美国利用南海、东海和黄海问题来扩大“制衡中国”的区域体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设立新的军事基地、在菲律宾部署美军军事力量、与越南加强防务合作以及在新加坡派驻新型濒海战斗舰等。2012年6月,美国防长莱昂·帕内塔(Leon Panetta)又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到2020年,美国海军60%的舰艇将集中到亚太区域。
第二,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与中国有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防部长帕内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在五角大楼联合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题为《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军事战略评估报告。(15)这份报告具体规划了美国国防战略未来以亚太为重点的调整计划。其核心内容主要包括三点:首先,美军战略利益评估报告建议放弃同时打赢两场战争的战略原则,改为要求美军只需具备在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中作战的能力,同时在另一场可能突发的冲突中发挥“干扰破坏”潜在敌人的作用,被称为美国新的“1+”战略。该报告建议美军从欧洲再撤出一个陆军作战旅,只在欧洲大陆保留两个旅的驻军。其次,调整经济发展与国防开支之间的关系。美国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目前,美国经济的困境与其动辄滥用武力密切相关。2012年为美国大选年,经济状况直接关乎奥巴马政府的政治命运。有效解决国内经济发展、医疗体制改革和就业等民生问题,日渐成为考验政府合法性的关键指标。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不得不尽快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对已造成沉重负担的军费开支进行削减,(16)进而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做出新的调整,但亚太地区的军事活动不仅不被削减,还将继续走强。最后,美国将重新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军事安全,明确了以中国的军事能力评估为基础的未来美军军事作战能力规划。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美国国防部正在实施的“空海一体战”部署。其直接用意是压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区域介入”的军事能力发展。2012年1月17日,美国防部正式推出了“空海一体战”的作战规划报告。(17)
第三,改变2009年奥巴马上台伊始美国在中国政策上的所谓“一头热”做法,从鼓励中国和美国一起“分担责任”和“分享领导地位”,到转而强调所谓“中国崛起”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谋求全面提升美国的领导地位,不再寻求任何给人以“中美两国集团(G2)”印象的外交和战略操作手法;将稳定和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作为实现区域内国家与美国全面合作的“政治保证”。2011年11月10日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在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发表演说时提出,“今天,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有挑战和影响最大的双边关系之一,需要进行审慎、稳定和动态的管理”。(18)在这样的措辞中,中国对美国的“威胁度”甚至被视为超越了二战时期的日本和德国,也超越了冷战时期的苏联。在美国的中国政策定义中,这样来形容中国还是第一次。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特意强调,让美国“在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与此同时,在对华政策上强调“立足现实、注重实效,忠实于美国的原则和利益”。(19)
第四,在外交、经济和战略等领域“多管齐下”,谋求美国从亚太经济中获益和让亚太区域贸易成为美国出口振兴战略突破点的同时,主导区域经济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为此奥巴马在2009年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一直将推动TPP框架的成型作为美国参与亚太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进程最重要的手段。美国务卿希拉里在檀香山表示,美国将在未来十年从外交、战略和军事等方面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
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并不意味着美国就此寻求与中国的全面对抗,因为无论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看到“新冷战”。(20)然而,该战略的出台表明,美国意图在安全和经济两条战线上把握东亚区域政治发展的主导权,维持区域内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心和同盟依赖,宣誓美国牵制中国崛起的决心,削弱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消极周边地区效应,充分获取中国崛起给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诸多战略红利。因而也不能认为美国针对中国不断崛起的“能力”是在真正进行自冷战结束后的全面军事和战略回应。(21)
三 权力变迁视角下东亚区域安全关系的调整与变化
在奥巴马政府宣布“重返亚洲”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出台之前,东亚地区安全局势步入21世纪后一直在发生变化。区域内国家在面对中国崛起之际,都在相应地进行安全政策的调整。这些变化和调整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军事同盟体系不断增强,东亚区域内以美国为中心的双边同盟体系出现了向各种形式的三边防务对话与合作升级的显著趋势。“亚洲版”的北约——美国将双边同盟体系打造为多边同盟体系虽然还未最后成行,但近10年来东亚同盟关系事实上已经远远突破了只是局限在双边的原有范围。
美国一直试图把已建立的双边军事同盟逐步整合为多边军事联盟体,从而在亚太地区建立强大的军事联盟集团。2001年美国布什政府上台之后,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TSD)”得以建立和发展,以共同应对亚太地区的“新威胁”。九一一事件后,美国为了争取日本对其反恐战争的支持,公开鼓动日本“借船出海”,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完成了从本土防御到保卫周边地区再到向海外派兵的转变。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与到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帕内塔举行了会谈,就安全领域深化日美同盟达成一致。日本表示“日美同盟的根基在安全问题,日方愿同美方保持密切合作,力图提高防卫能力”。他同时提到:“东日本大地震让我更加坚信,日美同盟是我国外交与安全的基轴”;帕内塔回应称:“美日两国50年以上的同盟关系才是保障太平洋地区安全的基础所在”,确认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22)韩国李明博政府上台后,已经全面推进韩美军事同盟,韩国军方在2010年1月做出了重新评估加入美日导弹防御体系的决定。韩国和美国在2010年7月于日本海举行为期四天的联合军演,这是韩美34年来规模最大的海上联合演习。韩国推迟了原定2012年转交的美国在战时对韩美同盟的军事指挥权,正在积极考虑加入美国主导的东亚战区导弹防御系统。(23)
2010年3月的“天安舰”事件使得朝鲜半岛局势下降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天安舰”事件发生之后,日韩防卫合作迅速升温,实现了互派军事人员观察军演的合作步骤。在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去世后,美日韩三国迅速进行协调,在军事方面做了充分的动员和预警,统一协调立场和方案,体现了美日韩三国在面对重大危机事件时在同盟框架内的协调一致,已经优先于与其他区域成员的政治与外交合作。美日韩三国密切合作应对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后的局势及核问题,并于2012年1月在华盛顿举行了三方会谈,就朝鲜半岛局势、缅甸局势以及其他涉及共同利益的地区性和全球性问题进行磋商。
2001年7月,美国与澳大利亚两国防长举行会晤,提出建立美、澳、日、韩“四国安全磋商机制”,以应对“地区潜在威胁”。(24)在美国的支持下,2007年3月,日澳两国签署了《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称将在涉及共同战略利益的事务上加强合作与磋商,从而标志着以美国为核心的亚太地区三方安全同盟的形成。(25)2011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宣布自2012年起五年内向澳大利亚增兵2 500人。
澳大利亚和日本的防务合作也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增强。2010年5月,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了《日澳相互使用军事设施的防卫合作协议》,这是继2007年《日澳安全保障合作协定》签署以来日本与澳大利亚防卫合作的新高度。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曾主动提出要求美国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26)2011年4月,澳总理朱莉娅·吉拉德(Julia Eileen Gillard)访日,表示将在安保领域“加强同日本和美国联合的意向”。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自2007年起开始进行联合海上军演,三国在日本九州西方与冲绳海域进行联合军演。2011年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宣布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文莱海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2012年2月,美日澳在关岛进行联合军演,这是日本航空自卫队首次与美澳举行的联合军演。2012年5月,澳大利亚与日本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以确保澳日两国在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情报时不会泄露情报,该协定的签署旨在强化美日澳三国在安保领域的协作。新西兰也在2012年5月和美国共同发表了新的防务合作声明,强调进一步密切与美、澳的新军事同盟关系。与此同时,日韩军事合作也在起步。2010年5月,日本作为观察员参加美韩军事演习,到2012年6月就实现了美日韩三边军事演习。虽然日韩军事情报协定签订的搁置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日韩防务合作的深化,日韩防卫合作的基本态势还将继续延续下去。美日韩三边军事合作是美国长期追求的战略梦想。(27)
其次,美国及其主要同盟国家都在纷纷拉拢亚太区域内的另外一个崛起国家——印度,通过笼络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以避免中国崛起带来竞争性的战略集团的建立,并通过实质性地强化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力求主导中国崛起过程中亚太区域“均势重建”的历史性进程。
冷战期间,美印关系整体上处于一种比较冷淡的状态。冷战后由于缺少了苏联这个制约因素,两国关系开始逐渐改善。奥巴马政府稳步推进美印之间的各项关系,尤其是在防务合作方面。2009年10月,美国和印度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陆军联合演习。这次演习表明美国和印度之间已经把对方当做一个实质性的军事合作伙伴。2010年6月,美国与印度的首次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两国在联合声明中承诺,将寻求在美印间建立起“全球战略伙伴关系”。美国声明美印之间不仅有“共同利益”而且有“共同的价值观”,“美印关系将成为21世纪决定性的伙伴关系”。美国声明坚决支持印度的崛起。未来印度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事务中。美国和印度提升双边关系是奥巴马上台之后与新兴大国合作趋向的重要体现,也是印度方面积极谋求参与国际事务的举措,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2012年6月,美印展开了第三轮战略对话。美印战略合作的深化是21世纪以来亚太安全态势的重大事件。
美国、日本、印度政府于2011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了首次三边对话,议题虽有意模糊指向“有共同利益的地区与全球性问题”,但《华尔街日报》一语挑明:“中国是三方未说出的潜台词”,美日印首次三边对话意欲打压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长久以来日本和美国一直在敦促印度举行三边会谈,并不断向印度施加影响,称印度为“亚太地区一个长期、坚定的盟友”。美日印三国有意定期轮流主办三方会谈,甚至考虑今后将会谈升级为部长级会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报告显示,随着美印军事关系的日益密切,两国联合军事演习也明显增加,其中2011年就有56次合作,比印度与其他任何国家之间的军演都多。除军事演习之外,美印还定期举行双边海军参谋人员交流,进行港口访问并加强了各级军官互通往来,美印之间防务关系的纽带日益紧密,印度已经成为21世纪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环节。(28)美印战略关系紧密化的根本原因是西方国家相信中印两国有不可避免的战略竞争,因而可以利用印度“有效地牵制”中国,而印度则需要通过“制衡中国”的决心来为自己提升战略地位和获取影响西方印度政策的筹码。这是美国和印度一拍即合的“交易”。(29)
日本和印度之间的防务合作也在稳步进行,制衡中国的战略性需要使两个国家走到了一起。(30)日印的防务合作开始于小泉纯一郎任职期间实现日本“正常化”的进程中。印度是新兴大国之一,虽然暂时不具备挑战国际体系中大国的能力,但是其国土面积、资源状况以及对特定事件的角色和影响力是大国不能忽视的。新兴国家处于成长上升期,具备成长为大国的能力和意图。印度多年保持6%-8%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促使其谋求在亚洲国际事务中形成“独立”和“有影响力”的角色定位。而寻求扮演超越传统美日安全同盟的更多的区域安全角色,一直是小泉政府以来历届日本政府的基本对策。日本在紧跟美国的全球和区域战略选择之外,对地区和国际事务也一直在努力发挥更为活跃的作用。
2000年,印度与日本建立全球伙伴关系。2004年起,印度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开发援助对象。2005年3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印度,两国发表了加强双边关系的联合声明,旨在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是日本首相近五年来首次访问印度,也是日本政府制定的南亚战略的重要步骤,此次访问也敲定了日印首脑隔年互访的基本格局。2008年10月,印度总理辛格访日,两国发表了《印日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和《印日全球战略伙伴关系进展联合宣言》。日印同是构建亚洲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重要力量,再加上“制衡中国”的共同需要,日印防务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2012年6月,在中日关系因钓鱼岛问题激烈摩擦之际,日本海上自卫队与印度海军在日本神奈川县举行了首次联合军演。
印度与日本之间的防务合作是在地区层面制衡中国的组成部分之一,这种合作关系被看作是亚洲安全构架牢固基础的催化剂。(31)戴维·康(David Kang)认为中国崛起能带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则认为同属新兴国家的印度从未从属于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中,印度在寻求制衡中国。(32)除了都被核问题牵绊以外,中印两国本没有共同利益。但是中国在亚洲的优势地位以及新兴印度在亚洲地区政治和经济中的突出实力地位加速了弥合日本和印度两国鸿沟的需求。(33)虽然日印两国对于通过公开的军事联盟反对中国持谨慎态度,但是它们认为强有力的防务合作能够阻止中国成为“挑战性国家”。这一系列新的区域防卫与安全合作关系的扩大和深化,都具有“绕着中国走”的性质,是区域内国家因应中国崛起和区域“权力变迁”的重要结果。
最后,将东南亚作为美国获取新的战略资源、避免中国地缘战略影响力扩大的重要领域。为此,美国不仅强势插手南海主权争议,制造美国从“航行自由”角度关注在南海的美国“国家利益”,更进一步通过将南海问题强行纳入东亚首脑会议,力压中国接受在南海问题上的所谓“多边架构”。南海已经成为中美在东南亚争夺地缘战略利益的重要领域。
美国在强化与传统盟友关系的同时,努力以多种军事合作形式(如获得军事设施使用权、签署部队访问协议、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等)加强与南亚、东南亚及中亚一些国家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的联盟体制和军事存在被视为地区安全方面的稳定因素,实际上整个东亚一直都赞同这种观点,即使面对中国的担忧,美国也不必在对这二者的维护上采取守势立场。(34)2002年,印度尼西亚恢复了与美国的安全合作会谈,并购买了大量美制武器装备;马来西亚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配合美军进行作战军演,提供港口供美航母停靠。新加坡和菲律宾是与美军合作最积极的国家,合作的领域包括提供港口、配合军事计划、签订军售合同等内容。正因为新加坡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有利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才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存在提供便利。新加坡在2005年与美国签订了《新美战略框架协议》,强化了两国之间的防务和安全关系。菲律宾与美国在1999年签署《访问部队协定》,2003-2004年度美军参加在菲律宾举行的军事演习次数增加一倍,在菲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地区联合军演,菲律宾成为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非北约主要盟国”。2010年以来,围绕着“南中国海”是否被中国宣布为“核心利益”的问题,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急剧变化。越南正在通过加强美越军事合作、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甚至考虑开放金兰湾军港租借,引进“大国因素”来对抗中国和强化所谓越南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主权争议。新加坡国防部长张志贤在2010年亚洲安全“香格里拉对话”上,大谈所谓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区域安全的不确定因素,反映了东盟国家在安全态势变化后的战略选择。但强调和中国保持友好合作、避免美国对中国采取“遏制”政策,仍然是东盟的基本主张。
四 权力变迁与东亚地区安全秩序的未来
东亚近十多年的地区安全新变局已经充分揭示,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即便在没有出现权力转移事实的条件下,权力变迁本身就足以带来重大变化。产生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并非主要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实质性变化,即使在力量对比变化开始之初,当美国这样的主导国家对自身“单极霸权”战略目标的维护,日本、澳大利亚这样的美国霸权体系内的受益国对已经产生依赖感的安全利益的认知以及众多中小国家利用大国相互制衡以获取更大自由空间的欲望结合在一起时,必然产生权力变迁过程中安全利益再分配的显著变化。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一贯坚持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战略方针,但中国的善意与合作并不能阻止和改变其他国家以中国为目标的安全政策及战略的调整。这一过程客观上来说和中国采取什么样的外交与安全政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而只是全球和区域层次上国家间权力分配开始发生变化的直接结果。东亚安全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权力变迁必然是一个更加复杂、微妙、甚至动荡的安全互动过程。
权力变迁的过程同样也是地区安全秩序重组的过程。为了维护东亚地区安全的稳定、和平与繁荣,重视大国崛起必然带来的权力变迁的复杂效应,需要我们对于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
首先,各国之间应该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特别是防务政策部门之间的对话与合作,管理东亚区域内正在不断上升的安全困境。
权力变迁并不必然导致国家间的敌对和冲突,但却起到必然恶化大国间安全困境的作用,增加战略疑虑和战略不信任。(35)如果安全困境不能有效地得以管理和控制,战略疑虑和不信任很可能继续发展成为敌意性的行为,并实质性地恶化大国间的安全与战略关系。按照布赞的观点,安全、安全化与主体间性密切关联。安全议题的设定、安全化也必须被作为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e)”的过程来理解。(36)领会安全化的动力和过程则有更大意义,因为如果人们知道谁能够、在涉及什么问题和什么条件下“制造”安全,有时它将可能调整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并因此抑制安全困境。(37)安全困境可分为一般性安全困境和结构性安全困境。一般性安全困境是一个普遍的概念,由具体安全问题引发的攻防守备,都可被涵盖在这一范畴中。因为这一困境类型具体化的特点,安全困境问题可以在某些议题上预防或得到解决。结构性安全困境则与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一般不易发生经常性变动,相对稳定并且难以根除,这一困境类型是地区或全球性危机冲突事件发生的原因之一。然而在国际政治领域中安全困境的作用随着权力关系的调整变得日趋强烈。权力的变化引起主体间相应关系的调整,伴随着为改善自身安全状况而采取的多种措施的施行,如升级军备、结盟行为、增加军费、具体战略重新部署等,一旦出现类似地区性结构性权力因素的重新配置,意味着将会对该地区安全态势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其次,大国彼此之间的战略和政策的调整必须采取慎重的立场和态度,减少民族主义情绪和国内竞争性政治利益的干扰和影响,保持国家间关系的开放和接触,是避免权力变迁所产生的安全不信任演化为军事冲突点的关键。
权力的变迁将不可避免地引发相关各方战略的调整和重新部署,主导性大国战略的调整是重要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地区安全格局。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与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中美两国在地区性问题乃至全球性问题上的战略姿态做了相应的调整。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逐渐从地区性大国成长为地区性强国。中国的崛起带来了国际社会多种不同的声音,目前的挑战是针对中国崛起的权力制衡体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区域内和平、合作与稳定的需要?权力政治的平衡与中国的崛起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热门研究点。现实主义者一致认同“现状大国”会主动平衡一个新兴大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关于中等国家会做出何种反应却不存在一致的观点。经典现实主义理论学者认为中等国家的反应视具体环境而定。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除了个别实力极其弱小的国家外,大部分国家都会采取制衡战略。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美国和日本等国是坚定的“制衡中国派”。但美国“制衡中国”的核心,究竟是为了限制中国的军事能力,还是为了巩固美国的单极霸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东亚是美国霸权的支点之一,在欧亚战略的平衡上美国一度将欧洲确定为全球战略的重点,与欧洲形成巩固的盟约关系。在21世纪成为“美国的太平洋世纪”后,美国的战略重心由大西洋区域转移至亚太区域,东亚的重要性对美国战略部署的意义越来越凸显。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布局以双边安全合作为主要模式,同时辅以经济多边主义,而且强调安全双边主义与经济多边主义相辅相成。(38)最近这一波美国的“再平衡”攻势集中在自身军事力量的扩大以及同盟关系与战略伙伴关系的强化。美国与其亚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重新整合,这是关系东亚安全态势的核心因素。这一态势说到底是美国想要继续维持单极霸权体系,不仅是要以美国为核心主导区域的均势体系,更是要将权力变迁进程中的“均势重建”继续牢固地掌控在以美国为核心的“霸权稳定”的框架之内。
最后,除了传统的军事同盟之外,区域内的国家应该共同努力,建立起一个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区域安全制度,在不断引进和扩大区域安全多边主义的基础上避免单纯的权力制衡机制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制衡效应”。同时通过不断扩大多边合作的范围,降低主导性国家在地区安全秩序建设进程中的压倒性话语和战略优势。
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在坐收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战略红利”。一个总是在战略上无法接受中国崛起的日本加剧了与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争夺,并在谋求增加军事开支和军事力量以制衡中国。这样的日本永远是美国保持东亚战略优势地位的关键支撑,希望利用美国因素以平衡中国影响力的东南亚则成为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战略支点和军事上的必争目标。(39)与此同时,对美国衰落的担心也使得区域内的部分国家开始主动寻求对美国的战略支持。澳大利亚2009年3月通过了新的国防白皮书,宣布将在未来20年增加军费760亿美元,采购新的F35战斗机、大型水面作战舰只和增购新的潜艇来应对“中国威胁”。澳大利亚与日本的防务合作也得到了新的提升和增强。韩国正在积极强化与美国的防务合作关系,包括推迟了美韩同盟军事指挥权的转交,发展新的军费计划,并考虑加入美国主导的东亚战区导弹防御体系。在南太平洋区域,美国是澳大利亚的盟国、是澳大利亚防务的核心支柱,日本是澳大利亚“关键性的战略伙伴”,韩国是同澳大利亚有着共同对美同盟关系以及相互利益的国家。以澳大利亚为中心,美国加强了南太平洋区域的安全防务链条。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区域内国家愿意看到中美全面战略对抗,更不意味着区域内国家愿意在中美之间重新“选择”。东亚区域内的主流安全认知是同时保持和中美两国的良好关系,以实现区域内的共同繁荣、稳定与发展。例如,印度不得不继续在与中国发展经济关系、争取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的领土争端以及渴望在国际地位上不被中国“压倒”之间求得平衡。除非中国主动采取对印度的军事挑衅,印度将很可能努力继续现在的做法,让美国和中国相互制衡,把制衡中国的主要经济和政治成本转嫁给美国。(40)中等国家的结盟政策并不由特殊的历史因素或者共同的文化特征来决定,而是由那些跨文化的、不随时间而改变的决定外交政策选择的因素所决定。(41)建立和建设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通过制度合作的方式使得地区摆脱单纯受“均势战略”影响而产生的不断深化的安全困境,又避免只是栖息在美国主导的“霸权和平”架构之下,应该是未来东亚安全的基本出路。
五 结论
我们没有必要回避中国崛起带来的权力变迁已成为推动东亚区域安全局势出现新变化的深刻根源。在权力变迁发生后,区域内国家面临新兴大国崛起时其安全战略的选择是多样化的,有一部分会发展与新兴崛起大国的关系,而另一部分则会保持或者强化与现有盟友的关系,地区安全架构必然发生相应调整。目前,东亚地区复杂的安全态势为各方提供了安全战略再调整的“竞技场”。东亚的安全局势表明,并非权力转移,即便是权力变迁也将导致大国安全关系的复杂化、甚至是局部的尖锐化。
在东亚权力变迁的过程中,虽然中国崛起带来了区域内国家在安全关系上“向美国靠”的明显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地区内国家愿意重新选边站,或者愿意跟随美国对中国采取敌对性的安全战略。权力的变迁对中等国家而言,并非完全意味着“弃中求美”或者“弃美联中”这样的重新“选边”,而是意味着在中美两个大国间寻找最为有利的权力制衡空间,通过中美之间的相互制衡,为自身赢得最大程度的安全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对那些不具备大国实力的国家来说,它们对一个新兴大国将采取何种政策,主要取决于现状大国的政策及新兴大国的崛起对其周边势力均衡产生的具体影响。(42)中国周边的部分中小国家担心中国在力量崛起之后会实行强制性的和扩张性的政策,因此转而利用美国因素,通过增强自己的军费和防务开支、加强同与中国有对抗关系的大国之间的合作来牵制和防范中国。与此同时,区域内各国渴望稳定、反对中美冲突、避免东亚出现地缘战略分裂、希望继续与中国保持紧密合作的呼声和趋势同样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东亚安全的新秩序本质上取决于东亚各国的共同努力,而并非只是由大国关系决定。未来东亚安全的新秩序不应只是建立在权力制衡基础上的均势体系,更应该建立在能够规范和处理更多安全争议的、更具包容性的地区安全合作制度的框架内,在均势与制度合作的双重进程中重建东亚安全的未来。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与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具体分析参见江忆恩、陈喜娜:《中国崛起:对概念运用的探讨》,载《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1》,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版,第70-88页;Chen Dongjin,"Examining the Rising Dragon:A Review of Foreign Affairs and Foreign Policy's Article on China in 2008," Asian Politics and Policy,Vol.1,No.4,2009,pp.779-789。
②朱锋:《东亚出现冷战后第二次大调整》,载《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4日第14版。
③关于权力转移理论的相关内容参见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 A.F.K.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The War Ledger,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④朱锋、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Ronald L.Tammen,Jacek Kugler,Douglas Lemke,Allan C.StamⅢ,Mark Abdollahian,Carole Alsharabati,Brian Efird and A.F.K.Organski,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⑥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⑦《辞海》对“安”字的第一个释义就是“安全”,并在与国家安全相关的含义上举了《国策·齐策六》的一句话作为例证:“今国已定,而社稷已安矣。”参见夏征农等主编:《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版。维基百科对于“security”的解释是:免于遭受危险、破坏、损失和罪恶的程度。
⑧Bill McSweeny,Security,Identity and Interests:A Soci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7.
⑨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存在于安全之中”,参见Emma Rothschill,"What Is Security?" Daedalus,Vol.24,Vol.3,1995,p.67。
⑩阿诺德·沃尔弗斯指出,“安全是一种价值观”,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参见Arnold Wolfers,"National Security in an Ambiguous Symbol,"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67,No.2,1952,pp.482-511。
(11)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2)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等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13)美国政治学家约翰·赫兹(John Herz)、英国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首先提出了安全困境的阐释,一致认同安全困境是一个“悲剧”。在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论中,它是指一个国家为了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反而会降低其他国家的安全感,从而导致该国自身更加不安全的现象。
(14)奥巴马总统当时对这一战略的介绍,参见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7/remarks-president-obama-australian-parliament 。
(15)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Sustaining U.S.Global Leadership: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January 2012,http://www.defense.gov/news/Defense_Strategic_Guidance.pdf。
(16)美国国防部要求2013财年的国防预算为6 130亿美元,这是继九一一事件以后美国国防预算的首次下降。今后10年内,美国将削减4 870亿美元国防开支。
(17)有关该报告的具体内容,请参见U.S.Department of Defense,"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 January 17,2012,http://www.defense.gov/pubs/pdfs/JOAC_Jan%202012_Signed.pdf。
(18)"Obama to China:Behave like a 'Grown Up'" Reuters,November 14,2011.
(19)Hillarv Clinton."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November/December 2011.详细介绍请参见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page =full。
(20)有关奥巴马政府2011年11月发起的对“中国攻势”的深入分析,请参见朱锋:《奥巴马政府的转身亚太战略与中美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5期,第1-8页;朱锋:《美国发起对华战略新攻势》,载《人民论坛》,2011年12月增刊;朱锋:《中美会进入地缘政治对抗吗?》,载《环球时报》,2012年1月13日。
(21)Mark E.Manyin,et al.,"Pivot to Asian-Pacific:The Obama Administration's Rebalancing towards Asia,"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March 28,2012.
(22)资料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0/28/c_122200040.htm。
(23)有关亚洲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的分析,请参见Sumit Ganguly,Andrew Scobell and Joseph Chinyong Liow,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London:Routledge,2010; Evan S.Medeiros,et al.,Pacific Currents:The Responses of U.S.Alliance and Security Partners in East Asia to China's Rise,Santa Monica:Rand Corporation,2008。
(24)李学江、黄山:《美在中国边上拉联盟》,载《环球时报》,2001年8月7日第8版。
(25)信强:《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第51页。
(26)Reuters,"Kevin Rudd Fires Back the U.S.over Wikileaks:It's Your Fault," Sydney Morning Herald,December 8,2010.
(27)Michael R.Auslin,"Japan and South Korea:The New East Asian Core," The Orbis,Summer 2005,pp.459-473.
(28)Richard Haass,The United States and India:A Shared Strategic Future,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2011.
(29)Mohan Malik,China and India:Great Power Rivals,Boulder:Firstforum Press,2011; Jonathan Holslag,China and India:Prospects for Pea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 Ashley J.Tellis,Travis Tanner and Jessica Keough,eds.,Asia Responds to Its Rising Powers:China and India,Seattle: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2011.
(30)Joshy M.Paul,"Emerging Power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Asia," RSIS Working Paper,December 20,2010,p.3.
(31)Joshy M.Paul,"Emerging Power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Asia," p.19.
(32)Amitav Acharya,"Will Asia's Past Be Its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8,No.3,2003/2004,p.150.
(33)Joshy M.Paul,"Emerging Power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Asia," p.19.
(34)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著,曹洪洋译:《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版,第281页。
(35)Kenneth Lieberthal and Wang Jisi,"Addressing U.S.-China Strategic Mistrust," i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John L.Thornton China Center Monograph Series,No.4,March 2012.
(36)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42页。
(37)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新安全论》,第43页。
(38)Ralph A.Cossa,"US Approaches to Multilater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in Foot Rosemary,et al.,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93.
(39)胡德坤:《美国东亚遏制战略与日本对东南亚经济外交》,载《世界历史》,2002年第5期,第35-42页。
(40)陈琪、刘丰主编:《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41)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编,刘江译:《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42)威廉·W.凯勒、托马斯·G.罗斯基主编:《中国的崛起与亚洲的势力均衡》,第119页。
标签:中国崛起论文; 军事论文; 亚太再平衡战略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国际秩序论文; 东亚研究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同盟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