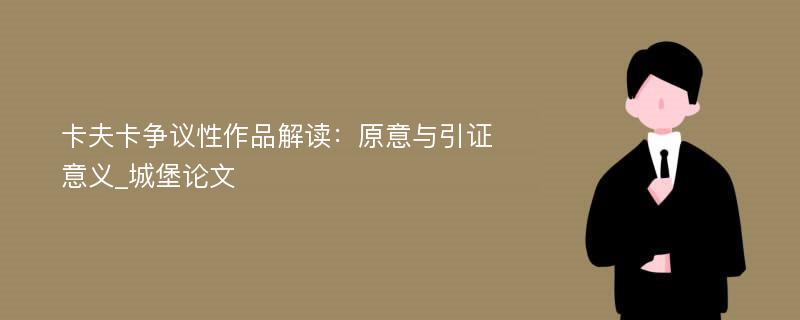
关于卡夫卡争议作品的解读:本义和引申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义论文,卡夫卡论文,作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是国内外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以卡夫卡的生平和人生经验作为出发点,对争论颇多且较为费解的《城堡》、《在流放地》和《判决》进行论析,意在探讨卡夫卡作品的本义,并对诸多学者分析卡夫卡作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卡夫卡/解读/本义/引申义
Kafka's highly debatable fictions reinterpreted
Lin Xuejin
(Liberal Arts College,Shantou University,515063)
Abstract In connection with Kafka's life experience,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some of Kafka's fictions which are beyond understanding or in much controversy such as The Castle,In the Penal Colony,andThe Judgment,with a view to fathoming his different motives behind these literary creation amongst all the dissenting comments from the manycritics.
Key words Kafka/reinterpretation/motive behind literary creation/comment from critic
二战后国外学术界对卡夫卡的研究形成了一门新兴的“卡夫卡学”。维也纳出生的美国学者、曾协助卡夫卡生前好友马克斯·勃罗德编纂第一部六卷本《卡夫卡全集》(1935年)的海因茨·波里策,自恃研究卡夫卡长达40年,在他编著的《弗兰茨·卡夫卡》一书的“导言”中断言,在卡夫卡研究中“任何想得到结论或解释谜底的企图必然归于徒然”[①]。卡夫卡某些作品很费解是事实,美国女作家乔伊斯·欧茨就说过:“对许多读者说来,卡夫卡还是一个永恒的谜。”[②]而且不无夸张地说:“‘解开’这个谜就意味着‘解开’人生的真谛。”[③]可是,如果断言“任何想得到结论或解释谜底的企图必然归于徒然”,则有一笔勾销各国几代学者研究卡夫卡的成果之嫌。事实上,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卡夫卡学”学者,从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多方法对卡夫卡作品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包括从哲学、神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各自的文学理论和意识形态,对卡夫卡作品都提出了作为一家之言的解读。我赞成这种观点:“解读作品主要在于这种读法是不是可以成立,不在于对或错。当然不能强词夺理随意附会。”[④]基于这种认识,我对卡夫卡某些作品的含义,提出一些看法,也算是一种解读吧。
《城堡》要告诉我们什么
卡夫卡的长篇小说《城堡》,写K多次想进入城堡而不得,城堡分明座落在前面山岗,但K却永远到达不了,永远无法进入城堡。到底卡夫卡想告诉我们什么?作家的创作初衷,即是什么原因引发卡夫卡写下这部迷离恍惚的作品?最早对《城堡》作出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好友、奥地利作家马克斯·勃罗德写于1926年的《城堡》第一版《后记》:“这座K未能进入、令人不解地连接近都未能真正接近的《城堡》,正是神学家们称之为‘仁慈’的那种东西,是上天对人的命运的安排……是不该得到和不可得到的东西,它超越于一切人的生命之上。”[⑤]这种宗教上的诠释,认为小说的主题是表现人试图进入天国而不得的痛苦,我们只能把它作为一家之言。事实上,从宗教意义上去解读《城堡》,也不只是勃罗德一人。英国学者埃德温·缪尔于1939年写的《弗兰茨·卡夫卡》中也这样说:“《城堡》一书,乃是一幅关于寻求得救之途的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关系的图画。”[⑥]埃德温·缪尔是《城堡》的英译者,他甚至说:“《城堡》同《天路历程》一样,是一则宗教寓言。”[⑦]法国学者丹尼·梭拉写于1934年的《论〈城堡〉》一文认为,“《城堡》是一部寓言……但是故事中并没有片言只语透露寓言的意义。它没有提供任何哲学的暗示,有的只是一系列不可理解的事件”[⑧]。这里已提出“不可理解”这一说法。也许是受30年代纳粹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处于种族灭绝的处境所影响,犹太血统的勃罗德(卡夫卡也是犹太人)从《城堡》中读出了另一种含义:“‘犹太人’这个词并没有在本书中出现……然而你几乎可以具体看出:卡夫卡在《城堡》中已经展示出一幅伟大的悲剧性图景,描写进行融合不过是徒劳;在这个简单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⑨]《城堡》又成为犹太人在寻找家园、渴望与其他民族融合过程中的悲惨处境的文学写照。勃罗德终于把《城堡》从神学、命运的上天境界拉回到犹太人人间的悲惨现实中来,这是勃罗德对《城堡》解读的重大转变。但是,生于捷克的美国学者埃利希·海勒却认为“《城堡》不是寓言小说,而是一部象征小说”[⑩],“寓言总是可以合理地破译,象征能否破译,取决于社会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否能从根本上谐调一致”[(11)]。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比较切合实际。但要补充一点,首先我们要研究的是“城堡”到底象征什么?要从小说的本义入手。
从我国的理论框架来理解,把“城堡”看成国家机器的缩影似乎顺理成章。我国研究卡夫卡的专家叶廷芳就持此看法:“城堡在这里是一种权力的象征,是整个国家机器的缩影。这个高高在上的衙门,看起来就在眼前,但对于广大的在它统治下的人民来说,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12)]我国另一位学者杨恒达也同意把城堡看成是官僚机构:“卡夫卡写《城堡》是为了突出这个官僚机构的荒谬性。”[(13)]另一位学者杨小岩也写道:“整部小说,充分反映了小人物与国家统治机器之间的疏远和对立的关系。而这个神秘莫测的城堡则是整个资本主义国家机器的缩影。”[(14)]
出生于维也纳的美国学者W·H·索克尔却不同意以上的解读,他写道:“K愚弄了小说的大部分读者、评论家和注释者。K在某个晚上流浪到城堡管辖下的村庄,他自称受城堡召唤并被任命为土地测量员,他使我们相信城堡当局拒绝批准他的要求是对他不公正,是剥夺了他应有的权利……把K看作没心没肺的官僚制度的牺牲品,或者精心去构想有关K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解释方案。于是在文学评论中,《城堡》成了对官僚制度的讽刺,对极权主义的预示,成了社会不公正的寓言,或者人类坚决要求正义及上帝恩典这类宗教问题的寓言。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评论家受了K弥天大谎愚弄的结果。”[(15)]那么索克尔如何解读《城堡》呢?他用了这个较为笼统、宽泛的提法:“卡夫卡在《城堡》中描写了现代人的根本处境。对现代人说来,无论世界还是他的自我,都不是既定和确定的。”[(16)]这样,《城堡》就成了表述现代人境遇的长篇小说了。
笔者同意对《城堡》这样分析:“卡夫卡笔下的《城堡》,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城堡,而是一个象征物……象征着一种不可企及的目标。”[(17)]问题是这个“目标”是什么?创作《城堡》前后,卡夫卡主要在想些什么?他要抵达什么目标而不可企及?《城堡》写于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上半年,如果我们考察这段时间对卡夫卡影响最大的生平大事,我认为应当是爱情。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已为大家熟知。1919年10月,捷克女作家密伦娜·耶森斯卡·波拉克写信给卡夫卡,请求卡夫卡允许她把《习炉》译为捷克文。密伦娜比卡夫卡小12岁,敢作敢为,追求自由,但婚后生活并不幸福。卡夫卡曾向勃罗德描述过她:“她是一团熊熊的火。”[(18)]卡夫卡很欣赏她那篇《习炉》的捷克语译文,后来他们相互通信至堕入爱河。密伦娜的朋友玛格雷特·努爱尔曼说:“她(指密伦娜——笔者)对卡夫卡一见钟情。”[(19)]卡夫卡在给密伦娜的信中写道:“眼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简直难以相信。我的世界崩溃了,但它又建立起来了。”[(20)]这里的“我的世界崩溃了”,应当是指卡夫卡三次订婚都以失败告终,爱情似乎与他无缘。但密伦娜的出现,又使他感到世界“又建立起来了”。1920年6月底,他们一起在维也纳度过难忘的、幸福的四天,爱情似乎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似乎看得见摸得着,但是密伦娜在1920年8月初写信给卡夫卡,说她不能离开她的丈夫。大约在这段期间,卡夫卡写成了他的《城堡》初稿。
至此,笔者有理由认为,《城堡》是卡夫卡一生三次订婚三次解除婚约,后来又与密伦娜有过一年左右的热烈爱情生活,当这段爱情生活终于不得不结束之后,卡夫卡写下《城堡》,表达了他一生感情生活的挫折以及他对爱情的渴望和认识,即“目标之不可企及”,爱情应当是激发卡夫卡创作《城堡》的动因。从时间上看,他与密伦娜爱情结束后完成了《城堡》的创作,这不是毫无关系的巧合。爱情的殿堂对卡夫卡来说曾经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但它是始终无法到达的所在。这样解读并不排斥对《城堡》的其他看法,特别是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兴起之后,读者对文本的不同解读更是十分正常的了。
如何理解《在流放地》
《在流放地》写一个因深夜站岗过度疲劳而没有每小时打钟时向上尉的门口敬礼的士兵,被判死刑送上杀人机器。但令人不解的是,最后那位参与发明杀人机器的执法军官为什么自己操作杀人机器杀死自己?如何理解这篇情节荒诞的小说?德国学者赫伯特·克拉夫特认为:“《在流放地》描绘了一幅现实的图画。”[(21)]“在历史上,被告者因为犯了小得令人可笑的错误而受到超重的惩罚,这是事实。而许多人被迫去观看执行死刑,这也是事实”[(22)]。“流放地是一个比喻,它说明,在现存的非法制的社会中,人没有故乡”[(23)]。“反对非人性的体制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24)]。显然,克拉夫特是从政治体制和人类处境来理解这部小说的。美国学者奥斯丁·沃伦则从宗教与人道主义的矛盾来解读这篇小说:“地球是块流放地,我们都被判有罪。曾经有这么一架精心制作的机器,建立在玄妙的神学基础上,作宣布判决之用,还有一套复杂的基督教会的系统来进行操纵。现在,它正在消失:老司令官(上帝)死了,虽然有个传统(你可信也可不信),说他还会回来……新司令官则是一位人道主义者。”[(25)]“两个对话人中有一个是旧军官,对机器发明者仍然忠心耿耿,另一个是旅行家。前者是旧神学的幸存者,上帝和罪恶的信徒中残留的一员;后者是位自然主义者、科学家,赞成他那世俗的一代人所持的人道义观点”[(26)]。沃伦有一点是说对了:“这篇故事……从头到尾都是寓言式的。”[(27)]问题是怎样解读它。苏联学者德·弗·扎东斯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流放地》的主题思想仅只是对所描述的恶的明确批判,以及这样一种坚定信念:恶到头来必然要灭亡。至于像这样的看法,诸如杀人机器象征着世界大战、奥地利的社会制度或整个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卡夫卡在这个中篇里奋起反对他周围现实中确实存在的不公正。”[(28)]笔者以为,这种分析似乎不符合卡夫卡的性格。众所周知,卡夫卡在日记中写下了这两段话:“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29)]。我从生活的需求方面压根儿什么都没有带来,就我所知,我与生俱来拥有的仅仅是人类的普遍弱点”[(30)]。卡夫卡在作品中很少明确表现出对“恶”的批判或“奋起反对”的倾向,他倒是主张“我们周围的一切苦难我们也得忍受”[(31)],卡夫卡的许多小说,最后大多是善良无辜的人遭到毁灭,很难得出“恶到头来必然要灭亡”的结论。我国学者杨恒达对《在流放地》作了这样分析:“小说的寓意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卡夫卡要表现现代文明和军事机器的残酷性矛盾的意图是明显的。卡夫卡在作品中表现出惊人的预言性:机器在代表现代文明的观光客面前将军官刺穿并自动瓦解,象征着一切残酷的军事机器将被现代文明粉碎。”[(32)]这也是对本文前面提出的为什么军官要躺到机器之下自杀而死的一种解读吧。这是不是卡夫卡的原意,可以讨论。我国著名学者叶廷芳则这样认为:“在揭露反动统治阶级的罪恶和残忍方面,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在流放地》最为惊心动魄。”[(33)]那个军官为何要操纵机器杀死自己呢?叶廷芳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一个决心与自己的杀人机器同归于尽、甘为旧制度殉道的死硬分子的狰狞面目”[(34)]。这种观点出现于80年代中期,那时国内卡夫卡研究还刚刚启动,应当可以理解。但最近才出版的斯默言编的《卡夫卡传》提出的看法就不能令人信服了:“《在流放地》也许不令人吃惊地预先指出战争的死亡营,他虽然未亲自经历过战争的死亡营,他虽然未亲自经历过战争,但是他的妹妹们经历过,并在这样的死亡营里丧生。”[(35)]这种提法有两点不能令人信服:其一,把卡夫卡看成未卜先知的预言家;其二,卡夫卡妹妹死于德国集中营是在《在流放地》创作的20多年后,在卡夫卡去世的10多年后,怎么能跟卡夫卡写作《在流放地》发生联系呢?
笔者从德国学者瓦根巴赫的看法中得到启发,提出另一种解读。由于《在流放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的1914年11月问世的,瓦根巴赫认为“《在流放地》中那个旅行者的目光,就是卡夫卡看待战争的目光”[(36)]。笔者在拙作《卡夫卡式略论》中提出:“《在流放地》中关于发明杀人机器的军官最后被机器所杀的构想,是对人类发动了战争最后又在战争中大量死亡的一种象征的表现和认识。战争机器是人制造出来,但最后人又被战争机器所杀。这篇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国皇储斐迪南被刺和奥国对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小说写于1914年11月),更值得我们注意。”[(37)]卡夫卡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持反对态度,他在日记中记下他对挑起战争的人的憎恨:“我愤恨地诅咒他们,让他们见鬼去吧!”[(38)]1914年7月底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不久全国总动员,卡夫卡两个妹夫应征入伍。同年11月初,二妹夫约瑟夫·波拉克负伤回家休养,向卡夫卡讲述了前线见闻,讲到部队里军官对士兵的体罚严酷,大冷天把士兵绑在树上,使他们全身冻得发紫。又说到多亏一只鼹鼠才使他免于死等等。这些前线见闻有可能成为《在流放地》的创作素材,起码有启发作用。笔者认为,在卡夫卡脑中,战场就是人类的流放地、苦役营,战争就是杀人机器,你杀死别人,最后自己也将被杀。
关于《判决》和“父子冲突主题”
1912年9月22日晚上卡夫卡只花了8个小时就写成了《判决》,这也是一篇颇为费解的小说。卡夫卡在题词上写下了“献给费丽丝·鲍小姐的故事”,并多次向别人朗读,是他自己比较满意的小说之一。《判决》写年轻商人格奥尔格·本德曼写信告诉一个远在彼得堡的朋友,告知他自己刚订婚的消息,无端遭到蛮不讲理的父亲的责骂,本德曼顶撞了一句,就被父亲判决,要他立即投河自溺,于是本德曼飞快跑到河边投河自尽,临死前低声叫喊:“亲爱的父母亲,我可是一直爱着你们的。”[(39)]《判决》是较早表现“父子冲突主题”的小说,我国不少读者只觉得它“莫名其妙”。勃曼德在他的《卡夫卡传》中称“这个短篇是‘这样一个暴戾的故事’,尽管儿子善良恭顺,却仍被父亲视为执拗残暴,遭到判决而终于‘自溺而死’……这个短篇,乍看起来,似乎是一目了然地按照心理分析学观点来写的,然而几经体味,其含义却变得越来越隐晦”[(40)]。赫伯特·陶贝尔曾经从宗教的象征观点来解释,认为“父亲是……上帝的一个侧面”[(41)],这样,父亲的语无伦次可以归之于神的神秘莫测。克劳德一艾德蒙·马尼则从字面意义来理解小说,认为父亲的语无伦次是因为失去理性,马尼夫人说,这个短篇代表了“对疯狂的深刻意义的发现”[(42)]。美国学者凯特·费洛里斯却认为《判决》与卡夫卡的爱情经历关系密切,他写道:“《判决》是卡夫卡第一次遇见鲍威尔小姐时所处窘境的产物,一种为了个人利益断然不能同她结婚的文学表现。”[(43)]并断言“格奥尔格·本德曼的独白,就是卡夫卡的独白”[(44)],小说的情节核心是父亲判决自己的儿子跳河自尽,而儿子又顺从执行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生死不明的人》(又译《美国》)、《判决》、《变形记》、《致父亲的信》都表现了父子冲突的主题。这种父子冲突的主题代表什么?父亲又是指什么?就《判决》而言,瓦尔特·本雅明认为:“父亲是一个惩罚者。他像法院官吏一样……在卡夫卡看来,官吏的世界和父亲的世界是一模一样的。”[(45)]凯特·费洛里斯写道:“在《判决》中……卡夫卡的父亲是父——神,既可畏又可羡,既不能逃避,又无法企及,既令人不可理解,又不能理解人。”[(46)]埃利希·海勒对小说中儿子顺从执行父亲判决而自溺作了如此分析:“他(指卡夫卡——笔者)赋予了一个平常的父亲以全能和全知的上帝的表征。他要求儿子交还他所给予的生命,儿子便服从了这个上帝的判决。”[(47)]这些都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理解这篇小说。赫伯特·克拉夫特则认为:“在小说父与子的冲突中,父亲代表现存的制度,因为他作出了判决”[(48)],“对《判决》小说中的‘父法’来说,弱者提出自己的利益要求便是罪过”[(49)],“它描写了等级制度,即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统治。父与子的冲突非常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社会结构”[(50)]。这又是从社会、制度来着眼分析的。也许是我国理论体系造成的思维定势的影响,笔者觉得关于父子冲突的主题,中国学者的分析更具说服力:“他(指卡夫卡——笔者)写父子冲突的主题……他不仅把父亲看作旧传统的代表,而且把父亲看作统摄一切的最高权威,有如上帝在西方文化哺育下的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写出人在这样一种权威面前的两难处境:人对他既恐惧又依赖,既想冲破他的束缚,摆脱他,又不得不请他指点迷津,乞求他的帮助,甚至感到对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既憎恨他,又对他怀有深重的负罪感。”[(51)]我赞同这样的看法:“《判决》这部作品中的父亲突然对儿子发出最严厉的指责,并宣判他溺死。这种不容分辩的权威态度,正是父亲形象在卡夫卡心目中的集中体现……表现出卡夫卡对父亲的恐惧心理。”[(52)]对父亲的恐惧,可能是激发卡夫卡创作《判决》的原始心理。卡夫卡对父亲的恐惧,在他写的长达3万字的《致父亲的信》(他始终没有勇气把它交给父亲)中已表露得淋漓尽致,在这封信中他还说:“我写的书都与您有关,我在书里无非是倾诉了我当着您的面无法倾诉的话。”[(53)]卡夫卡小说中的父亲形象,我们何不看成就是现实生活中他父亲赫尔曼·卡夫卡的文学典型;卡夫卡作品中的父子冲突,也可看成是现实中卡夫卡与其父亲关系的某种独特的文学表述。至于他的关于父子冲突主题的小说问世后,其社会效果大于他最初的创作意图,这倒是中外文学史上常见的文学现象,因为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读者可以有不同的解读。鲁迅先生就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54)]
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城堡》的本义是卡夫卡对其爱情生活的感受和认识,爱情分明就在前头,但却是可望而不可企及。令人费解的《在流放地》,可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卡夫卡脑海中经过加工创造的某种文学表述,战争机器是人创造出来,但这架杀人机器既可以杀死他人,也会杀死自己。《判决》中所写的儿子绝对服从父亲的判决,正是现实生活中父亲形象在卡夫卡心目中的权威体现,也表现了卡夫卡终生对父亲的恐惧。卡夫卡作品中父子冲突的主题,其本义最初也是现实生活中卡夫卡与他父亲关系的文学写照,只是后来的研究者对它的解读又多了许多引申义。
我国对卡夫卡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如冀桐先生的《卡夫卡与传统》一文,从卡夫卡与传统、继承的角度着眼,提出卡夫卡的创作也受到欧洲文化中的神话原型的制约与影响。认为出现在卡夫卡作品中最主要的原型意象有三个:父亲原型、追寻原型、西绪福斯原型。卡夫卡作品的叙述模式和结构框架都受到这三个原型意象的影响。父亲原型的功能在于显示世界模式及人同世界的关系;追寻原型的功能在于显示人在世界的行动原因和过程;西绪福斯原型则显示卡夫卡的主人公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他们陷入了“反抗与受罚”的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卡夫卡的神话原型负载了作家自己对现实的种种体验,如父亲原型就负载着对奥匈帝国残酷统治的神秘感和恐惧感。追寻原型响彻着要求生活权利、要求自我价值的呼唤。西绪福斯原型则蕴含着在强大权威面前所产生的困惑和无可奈何。所以,卡夫卡作品中的神话原型又具有现代文化意义,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新的神话[(55)]。这种分析跳出了单一的社会反映论的理论框框,较有说服力地指出卡夫卡作品(现代神话)多义性的深层原因,很有价值。但无论如何,解读卡夫卡的作品,弄清他创作的初衷,分析什么因素、什么人生体验激发他去创作,去写出一篇篇引起后人争论不休的作品,寻根溯源,对解读卡夫卡的作品应当有所帮助。这正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注释:
① ② ③ ⑤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5) (16) (25) (26) (27) (40) (41)(42) (43) (44) (45) (46) (47) 《论卡夫卡》,叶廷芳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8、678、679、20、66、173、45、81、179、179、673、676、121、121、123、136、137、138、148、149、30、157、218页。
④ 《KafKaesque——卡夫卡的作品与现实》,谢莹莹,《外国文学》,北京外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编辑,1996年第一期,第41页。
(12) (33) (34) 《现代艺术的探险者》,叶廷芳著,花城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3、33页。
(13) (32) (52) 《城堡里迷惘的求索·卡夫卡传》,杨恒达编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32、94、65页。
(14) 《卡夫卡文集·Ⅰ·变形记》,学思主编,第11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7) 《卡夫卡文集·Ⅲ·城堡》,学思主编,第28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 (19) (20) (35) 《卡夫卡传》,斯默言编著,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278、277、282、160页。
(21) (22) (23) (24) (48) (49) (50) 《卡夫卡小说论》,〔德〕赫伯特·克拉夫特著,唐文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9、88、90、90、77、77、78页。
(28) 《卡夫卡和现代主义》,〔苏)扎东斯基著,洪天富译,第55页,外国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
(29) (30) (31) 《卡夫卡随笔集》,叶廷芳编,黎奇等译,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259、23页。
(36) (38) 《卡夫卡传》,〔德〕克劳斯·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04,103页。
(37) 《卡夫卡式略论》,《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9年第2期,第48页。
(39) (53) 《卡夫卡小说选》,孙坤荣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541页。
(51) 《城堡里迷惘的求索·卡夫卡传》,杨恒达编著,第64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4年版。这段话在斯默言编著的《卡夫卡传》(东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页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抄一遍。
(54) 鲁迅《集外集拾遗·〈绛洞花主〉小引》。
(55) 参见《卡夫卡与传统》,冀桐《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