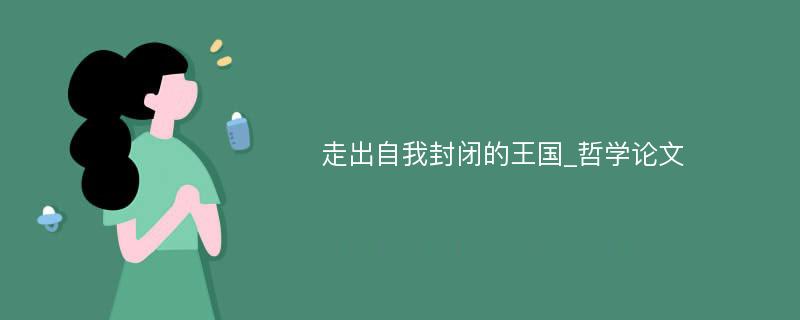
走出自我封闭的王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国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走出自我封闭的王国,这是当今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在学术争鸣中,我们要注意摒弃和防止不同形式的自我封闭现象,要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作者在文中提到的“二世现象”和“始皇现象”,的确是发人深省的。
改革开放,不仅使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代,而且也使我国的理论工作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代。
八十年代以前,由于我们处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中,理论工作也一直处在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盲目性中。所以,虽然五十年代中期中央便提出了“百家争鸣”的政策,但在“文化大革命”前却从来没有实现过。因为,按照当时的看法,所谓百家,实质上只有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所谓争鸣,无非是为了“教育”人而树立一些反面教员;或者说,为了肥田而除一点毒草。在这种情况下,何来争鸣之可言呢?八十年代初开始,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国外的先进科技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我们引进了,国外的多种主义和思想进来了。如果说,以往实际上我们只承认一种主义,即马克思主义的生存权,那么,今天我们却不能不承认多种主义的生存权了,也就是说,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多元的世界正在形成,或者说,多种主义争鸣的局面正在形成。不过,我们肯不肯承认这个事实,敢不敢承认这个事实,似乎还有点问题。直到九十年代初,“多元”一词还是忌讳的。今天虽然不再公开谈不能用了,用之似乎仍有制造混乱的嫌疑。在我看来,这便是十多年来理论工作步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
“文化大革命”中有一句名言:“党外无党,帝皇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如果在政治领域中尚且如此,那么在学术领域中则更是如此了。在任何一个学术领域内,都不可能由一个学派包打天下;在任何一个学派内也不会是铁板一块,没有不同的意见。
这种情况,在哲学学科中比在别的学科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所研究的都是某种给定的对象。如生物学所研究的是生物现象,它并没有必要先去证明生物现象是客观存在的,然后再去研究其特性和规律。哲学却必须追问自己研究对象的存在的客观必然性。所以,现代生物学不会再问自己:生物学研究什么?但现代哲学却仍如两千年前一样,在追问哲学研究什么?人们可能会这样想,如果两千多年来,始终在追问自己研究什么,这岂不是在原地踏步吗?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而哲学的进步恰恰便表现在这里,即表现在不同时代的不同答案中。所以,学习哲学的人,一定要学习历史上重要的哲学理论(代表性人物的代表性著作),否则便不可能真正理解哲学;学习生物学的则不然,不必从学习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开始,便可直接学习现代分子生物学。
既然科学中不同观点的存在是必然的,是任何一个科学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事实,那么,百家争鸣便是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违背了这一客观规律(不管人们当时的主观愿望如何),只会造成对科学工作的破坏,只能形成倒退。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理论分析的逻辑结论,也是很多人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所以,多元的局面不一定是一件坏事,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能不能用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它。
不要以为承认了多元的局面,就是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丧失了自己的立场了。承认一种客观事实是一回事,对这一客观事实持何种态度又是另一回事。如果因为我们对这一客观事实持否定态度,便否定这一事实的存在,这不是背离了唯物主义、陷入了主观主义吗?
但是,时至今日,仍然有人认为这不是主观不主观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有自己的立场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会对客观事实视而不见呢?抽象地说,就是因为他们还没有从真理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迷梦中清醒过来。
五、六十年代,在我国的哲学界,甚至整个理论界,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看法,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唯一正确的哲学。如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各家各派的哲学,可能还有点合理因素的话,那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的其他各种哲学,便没有任何合理的内容可言了。真理已经集中在一家,除此以外的各家,当然都只有谬误了,因此,对它们便无争鸣之可言,只有“批倒批臭”了。当时,对这种情况,我们都没有觉得其中有什么不妥之处,反而认为这是革命性的表现。所以,这种片面性便越演越烈,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中,便把这种片面性推到了极端。这场否定一切的所谓“革命”,对我国的文化、经济,乃至整个社会,造成了至今还难以估量的破坏。
物极必反,错误走到了极端,它会帮助一些人从中觉醒过来,促使他们去重新思索:这种否定一切的态度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吗?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这种物极必反又可能反到另一极端,即对否定者的否定。八十年代中上叶出现的所谓“信仰危机”,就是这种极端的典型表现。即原来的“绝对真理”在相当多的一部份人那里,一下子变成令人厌恶的谬误了。
所谓否定一切,其实就是宣布否定者便是绝对真理的化身。但是,这种观点恰恰便是前马克思主义的、非常陈旧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般的情况始终是这样:一种新的哲学出现了,便宣布前此的一切哲学都是错的。只有它才是唯一正确的。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曾形象化地说,哲学史就这样成了古尸陈列馆,在这里,充满了已经被推翻了和已经死亡了的体系;而且每一个这种自称发现了永恒真理和永恒正义的新体系,不久又被宣布为谬误,也被送进了古尸陈列馆。……这样,哲学史便成了死亡体系的王国。那些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走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条通向死亡体系王国的道路,它能不损害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群众中的威信吗!
说得严重一点,自以为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恩格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谈到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意义时,曾经指出: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一个哲学体系可能是绝对真理总和的幻想,这就是因为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按照辩证的观点,真理不是表现为一个或一堆结论,真理是个过程。当然,黑格尔并没有能把这一革命精神贯彻到底,所以才产生了通常所说的体系与方法的矛盾。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恰恰便充分发扬了这一革命精神,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年代谈过,这一新思潮的优点,就在于它不是要颁布适合于任何时间与任何地点的永恒真理的教导,而是要在批判旧世界中去发现新世界。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结束真理,它只是指出了一条在实践中不断认识真理的道路。
所以要想发展马克思主义,重新树立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眼光放宽些,要多了解一点别的学派的观点。毛泽东在谈到团结问题时曾说过,一个人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要听取反对过自己,又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的意见。我以为,这一精神也适用于学术争鸣。因为,这既体现了某种宽容精神,又没有放弃原则。如果一个人在争鸣中能持这种取彼之长补己之短的态度,它必然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走出自我封闭的王国,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发展的当务之急。从客观形势看,在这个大众传播媒介日益广泛深入的时代,要封闭是封闭不住了。但是有个别人在绝对真理的王国中,过惯了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生活,对这一大好形势,总觉得有点格格不入,有点怨气想吐,但是没有这样的客观氛围,于是便设法放点暗箭,喷点毒汁,对这种人,我们只能说:不破坏自己学者、教授的面貌,不是可以活得更轻松一点吗?
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人。在博士论文答辩中我觉得有两种现象是值得注意的。一种存在于研究西方哲学博士论文中,我把它称为“二世现象”,即学什么便信什么。学习海德格尔,就要成为海德格尔二世。这些同志念书念得很细,很踏实,这与以前书也没有看过,便对之进行批判相比,是个非常重要的进步。谦虚踏实是对的,但为什么不能同时有点“彼可取而代之”的战略眼光呢?没有这种战略眼光,严格说来,就不能算是研究。研究就是要有创新。我相信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另一种现象,我把它叫作“始皇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论文中。这些同志仍然固守大一统的观念。他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哲学不作一点比较研究,冥思苦想,创造一点新概念,然后便进行铺陈推演,说是填补了什么什么空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此,我颇不同意。我总要劝这些青年朋友多读一点书,有雄心壮志是好的、对的,但是,要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是不容易的,不要以为提几个新名词,就有了新理论了。现在报刊上有些热闹的争论,实际上其思维方式和理论内容,并没有什么根本分歧,只是名词的争论。围绕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争论,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性质的争论。
这两种倾向正是两种自我封闭。扬弃这两种片面性,把刻苦钻研和勇于创新的精神结合起来,我们的哲学就会大有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