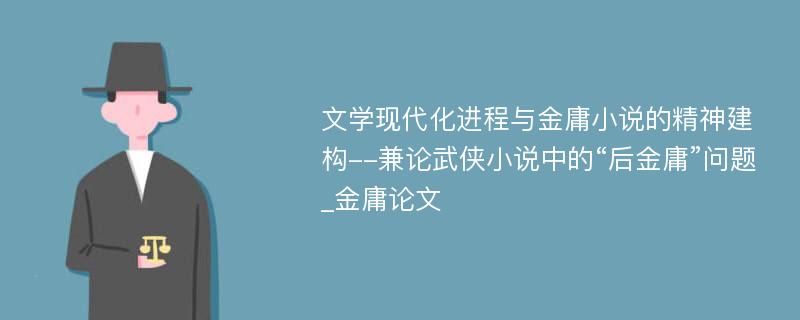
文学现代性进程与金庸小说的精神构建——兼谈武侠小说的“后金庸”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金庸小说论文,武侠小说论文,进程论文,精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1世纪正以不可阻遏的脚步向我们走来。回眸这即将成为过去的有喜有忧的百年文学现代性进程,我们不难窥见在整个世纪文学大潮影响下通俗文学所经历的由传统向现代嬗变的精神轨迹。站在这样的时代转型的高度来考察金庸,我们对其武侠小说在现代性方面所作的贡献就会有一个更明晰、更准确的把握。众所周知,武侠小说在我国源远流长。即使撇开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以及他所标举的游侠精神不计,从唐传奇算起,迄今也有1200年的历史。它是最受国人欢迎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通俗文学。然而,延至晚近,随着统治阶级文化控制手段的进一步严酷以及其他种种复杂因素的制约,武侠小说中的“揄扬勇侠,赞美粗豪”(鲁迅语),追求适性自恣、狂放不羁的精神内涵逐渐萎顿,作品主人公也渐从啸傲江湖、替天行道的侠客英雄,堕落为依附王公巨卿们的“御猫”式奴才,丧失了个体意志与独立人格。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话来说,就是“终必为一大僚隶卒”。这一精神畸变,简单地用“奴才文学”来概括恐不尽妥当,但它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个性思想的严重缺失,也直接招致了武侠小说整体艺术质量的明显下滑。因此,如何在精神涵量上进行提升与重建,实际上就成了振兴武侠小说,使之与20世纪整个文学现代性进程保持大体同步相对应的关捩所在。
应该承认,对于上述问题,五四运动以来,不少武侠作家如王度庐、还珠楼主、梁羽生等也都有所洞识,并且顺应现代转型的历史潮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武侠小说的现代性尤其精神的现代性问题,根本上说是时代的产物,它绝不是某个或少数几个天才所能独立解决得了的。作为新武侠小说的杰出代表,金庸超越前辈与同辈的地方,正在于他在这方面作出了继往开来的、集大成的特殊贡献。他以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的解放及其现代性的时代精神为基点,充分吸纳传统和民间的丰富养分,用精英文化的人文精神对武侠小说精神内涵的三个基本支撑点即侠客崇拜、技击崇拜以及由此而生的侠客情感理想模式崇拜作了全面的、富有创意的诠解,并对其中非现代的陈旧落后的文化思想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
一
若论金庸武侠小说的精神构建,最突出的表现,恐怕莫过于他对传统良暴二元对立命题所持的批判改造的艺术立场。
自古以来的武侠小说,都可千篇一律地纳入“除暴安良”的主题模式中。良暴对立冲突的先验设定与展示,乃是传统侠客崇拜的中心内容,事实上亦是一切武侠小说得以存在的心理基础。不过,同样是“除暴安良”,彼此的精神指向是大有区别的。唐时的武侠小说将“除暴安良”定位在为江湖行侠仗义,主人公一俟锄除人间不平事后即飘然远去,“深藏身与名”;清代侠义小说却把“除暴安良”的立足点移向了朝廷,侠客如黄天霸、展昭之类的侠举,有时似专为统治者的封赐而作。民国后的作家,由于受民主观念的熏陶影响,其“除暴安良”又复由将价值取向从朝廷下移至江湖。这样做不只是撇开了一个清官来“总领一切豪俊”,更重要的是恢复了侠客做人济世的尊严、责任以及武侠小说自由不拘、至情至性的精神本质。金庸的“除暴安良”显然属于后者。所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将侠客之救民于水火与国家民族的兴亡动荡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而并不斤斤计较于个人复仇与江湖争霸。这一点,在《神雕侠侣》中可见,金庸借郭靖教导义侄杨过的一番大义凛然的话,就道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他的作品,除少数的《侠客行》、《白马啸西风》外,竭心尽智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意向。“除暴安良”往往有两种视角:一种是民间的视角,人民作为个体无力抗暴,于是希望有侠客出来为民除害,伸张正义;一种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视角,统治者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不能容忍恶势力过于放纵,于是也就有了为国除害的问题。金庸的“除暴安良”则立足于民本立场而又有所超越,它已融入了知识分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对千百年来人民所遭受的不幸与苦难有着真挚的同情之心,所以较之一般的现代武侠小说不仅显得境界开阔,在主题思想的表达上也更细腻曲折而富有意趣。
但这仅仅是金庸小说“除暴安良”所表现的一个方面。更为难能可贵的,还是它内中寓含的那份执着的个性、独立的思想。金庸并不因强调个体对群体的责任而漠视个体的价值。比如说杨过吧,他在描写这个多少有些类型化的“神雕大侠”的同时,始终没忘记他身上自幼培养的愤世独立甚至有些过分自我的心理因子:“谁对我好,我就对谁好;谁对我不好,我就加倍地对他不好”。这种个性使杨过后来欺师叛祖地做了古墓派传人,并公然对抗礼教大防,娶师父小龙女为妻等等。对这些,金庸在小说中不但浓墨重彩地加以展现,而且在字里行间热情地赋予了自己的同情与尊敬。不仅是杨过,其他如《倚天屠龙记》中的张无忌、《天龙八部》中的萧峰、《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等等,几乎金庸笔下所有的大侠包括不顾一切为国效力的郭靖在内,他们个个都以铲暴除奸、拯世济难为己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甚至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全然无恤:这种精神意蕴既是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所使然,同时更是他们独立人格和率真天性的自然流露。而在小说中写出了这一点,凸显“除暴安良”命题与弘扬武侠小说固有的自由不羁精神便达到了完满的一致。个人主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是个老话题,古往今来说法多矣。理想地说,它们彼此不应是单向度的,而应在双向互动的交融中求得统一。金庸对此所表现出来的“人,总是既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又要保持独立的人格,两方面都不可偏废”(严家炎)的思想,正是从这一种理想的角度,反映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因此,这就使其作品中有关“除暴安良”的描写在本质底蕴的先进性上较之一般雅文学虽慢半拍,但却与整个20世纪的时代主潮基本保持了一种“随大流”的状态,成为中国文学现代进程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当然,我们这样说是建立在武侠小说作者对“除暴安良”类型化母题认同赞肯的思想基础之上的。这也是绝大多数武侠小说包括金庸前期武侠小说创作的基本前提。至于良暴观念本身的思想内容实质到底是什么,囿于文体的限制,似乎就无人细究,也不敢细究了。而金庸却根据对历史和现实认识理解的深化,从《倚天屠龙记》开始,表现出了对这个传统古老命题的深刻质疑:虚拟的“除暴安良”命题虽然为武侠小说所不可避免,但从历史真实和人性本质上看,又毕竟过于原始朴拙。为此,他一反传统作法,对传统良暴观念重新作了阐释诠解。他不仅描写世俗视为“暴”的江湖邪教黑道并非铁板一块,照样存在着一心向善的正人君子,而且也揭示所谓的名门正派中亦错综复杂,内中不乏有很多小人和坏人等问题。愈到后期,他的这种创作意向表现得就愈明显,他几乎是毫不留情地将各名门正派为传统权力话语系统所遮蔽了的丑恶纤毫毕现地暴露给人们看:如《天龙八部》中诡计多端、野心勃勃的全冠清;《连城诀》中卑鄙无耻、龌龊下流的花铁干;《笑傲江湖》中阴险毒辣、流氓无赖的岳不群、左冷禅等。如此全面地打破正邪、良暴壁垒,将正邪人物、良暴人物无情地置于一个平等的道德水平线即以人性的标准对他们进行公平的审视,并对传统“正邪之分”、“良暴斗争”神话极尽贬嘲反讽之能事,这在武侠小说创作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它表明了作者对人性本质和人的异化现象的洞察和理解,也反映了作者在良暴问题上超越传统壁垒的开放情怀。但看淡了良暴、正邪之争,不等于无是非善恶。在改定本《射雕英雄传》的结尾,郭靖说:“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这话其实是金庸的心曲流露。冲破狭隘的民族、地域观念,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此一现代人文的民本观念,就是金庸后期考察问题的最高是非准则。也正是基于此,尽管他看到了良暴判断的复杂,却还是大胆地进行了“反武侠”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赋予了这一两极对立的传统命题以难得的艺术张力。
二
批判继承传统文化中尚德修身的思想,糅以民间赏善罚恶的价值取向和现代人对生命生存包括对气功的独特感受,把武侠小说的武功描写富有意味地内化和提到一种精神本体的高度作评判,这是金庸武侠小说精神现代性的又一重要表现。
韩非子大约是最早将武力与侠客联系在一起的人。他很干脆地说:“侠以武犯禁”。但他所说的“武”与后来言说的武侠之“武”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大致还停留在“暴力”这个层面。武侠之“武”比这显然要精致得多,也丰富得多,至少包括了民间的技击崇拜;至近世,这种技击崇拜甚至还升华为部分国人无可化解的技击救国情结。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和政治热情的作家,金庸对此当然抱着积极肯定的态度。《鹿鼎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韦小宝带着他的双儿跑到俄罗斯,结果初通中国武术堂奥的双儿在俄国竟把那些蛮横之徒以及觊觎她美色的登徒子们统统打得满地找牙。对此,金庸毫不掩饰地插话评论道:科技文明,中国不行;武术技击之类,大鼻子们不行。他对中华武术的崇仰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由此也产生了一个怎样写武侠之“武”的问题。如果将武侠小说中的“武”仅仅落实到技击上,终嫌单薄。它可能好看却不耐看,况千百年沿袭不变,也太让人失望。即使像郑证因等人所写的一招一式拆解开来可做武术教科书的《鹰爪王》之类,看多了也会失去魅力。可能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现代一些武侠作家开始有意识地将武功描写纳入到中华文化观念体系中进行运作,藉以提高其武功描写的档次。平江不肖生后期有些作品认真探寻佛道,颇具文化内涵;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尽管有类似《封神演义》的无稽描写,但它将儒释道三家思想学说融合为一体的尝试,亦不乏自我作古的勇气,在同类作品中实属罕见。到了金庸,这方面的追求就更自觉,层次和境界也更高。他不仅完全跳出了旧武侠小说武功描写过于无稽的俗套,而且凭藉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和深厚扎实的国学根底,在前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把武功与文化结合并提到了“妙参化境”的高度,并使文化成为其基本的精神支柱。这之中,金庸用力最多也是最具创意和深度的,我们认为就是他的道德至上的武学思想。《笑傲江湖》中,一代侠隐风清扬认为令狐冲人品好,且生性自由洒脱、无拘无束,颇合“独孤九剑”之微旨,就把这套绝世武功传给了他。至于令狐冲本人一招一式的技击功夫如何,内功基础如何,倒又在其次了。在金庸小说中,总是很看重这类人品境界的描写。他坚定不移地认为,从长远的发展眼光看,武学修养上的功夫将最终决定技击功夫的高下。当然,由于每个人个性禀赋不同,武学修养上的入门手段也各各不同,但万流归宗,“仁”、“以德服人”、“神武不杀”始终是金庸标举的最高境界。我们看到他在表现“除暴安良”主题和弘扬侠义精神时,从来都没有流露出依靠武力解决一切问题的倾向,而是执著地从武德和人生境界两方面来界说“武”的效能,并把武德的高尚与否视为决定武功高低的根本原因之一。他区分“正派武功”和“邪派武功”,主要也根据中国式的社会道德与文化道德,看它们是否“为国为民”、“适性而行”或“上天有好生之德。”郭靖、张无忌、袁承志等大侠之所以能功成“正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人品皎洁、武德高尚;洪教主、东方不败等人身怀绝技而下场可悲,原因主要也在他们卑下邪恶的武德。中国文化是一种德性文化、中庸文化,它强调人内在的自我完善功夫,强调人际关系和谐自然,认为“内圣”才可“外王”。金庸的描写,正显示了他对传统文化此种特性的深知和对它的现代回归与重建的渴望。他实际上是用最通俗形象的形式向我们阐释了最深奥、最迷人的以“仁孝”、“中正平和”伦理道德为本位的中国文化的精核。
如果说在武功与武德的关系问题上,金庸强调前者为用,后者为体,那么,对武功本身的描写,他则明显表现出重内轻外的创作意向,我们这里说的就是他那为人称道且又别具一格的内功描写。尽管这不是金庸的专利,在其先贤与同辈作家如梁羽生、古龙、萧逸、司马翎、云中岳等人的作品中也可以读到,更远还可溯及晚清的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等。但严格说来,他们在武功描写中所涉及到的文化部分,大多只是道具式的,仅仅作为文化涉指符号存在,引不起读者多大的审美联想。而金庸则不然,他不仅以其神奇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思想、非凡的智慧,将中国文化最精微重要的儒道释各家许多关于人生理想观念的东西和气功中的合理成分相互融通,并化入武功描写之中,还与主人公独特的生活经历乃至生存生命感受结合起来。这样,他笔下的比武打斗,通常就能跳出暴力拼杀之窠式,从而构成一套自然流动的、能体现出一定文化理想的符号象征系统。金庸从其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就开始了这方面的自觉努力。他写陈家洛武功大进,主要得益于他忽然理解了庄子逍遥游精神的达观与随意。在以后的创作生涯中,金庸大凡写到打斗场面,便采用这种以文化或气功来解说武功的路数,无非说得更透辟、更周全。如《碧血剑》中,袁承志打败温家五老,当得益于他对“功由静生”旨趣的默察;《射雕英雄传》中郭靖的“降龙十八掌”,则与《易经》宣扬的早期儒家的刚健精神有一种气质上的互通关系;而《天龙八部》中段誉的“六脉神剑”,又和中医人体经络学说关系极为密切……这样的武功描写,虽不能说与感观刺激全然无关,但毫无疑问,我们阅读及此,可更多地享受到与祖先展开精神沟通、交流、对话的愉悦,甚至可从中窥见到列祖列宗庄严形象的吉光片羽。
三
在金庸小说中,有关侠客情感理想模式的表现,是争议较多的一个问题。不能否认某些批评不乏合理因素,但如果我们比较全面地考虑到武侠小说的文体独特要求,平心论之,金庸在这方面所作的革命性、现代性的改革与创新,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历史贡献仍属于第一位的。
侠客情感理想模式崇拜虽从侠客崇拜与技击崇拜派生而出,但它在整个武侠小说精神涵量的构成中意义非同寻常,代表着由千百年劳动人民集体无意识积淀的一个文化之梦:人民在这个梦中设想了一种人与人之间脱俗纯洁、超越一切现实功利和宗教法规及以情感为本位的人际关系,以此来对抗现实的残酷与龌龊。从《水浒传》直到现代的武侠小说,用来表现这种纯洁关系,反映同性手足间至情至性的“惺惺惜惺惺”,是它们的一个共同题旨。然而清代之后,由于主流意识形态加大了渗透改造的力度,很多儒家忠君孝悌式的封建礼教的东西被掺了进去,遂使武侠小说中的“惺惺惜惺惺”往往不再成为人的自然率真本性的表达方式,而不知不觉地蜕变为承载陈旧落后封建伦理观念的情感表现模式。曾几何时,这种滞后的“惺惺惜惺惺”的情感理想是很顽固的。即使像颇受五四运动新文艺思潮影响的王度庐,在其《剑气珠光》等作品中触及到这类问题时,也是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
金庸在创作中涉笔此一情感理想,态度是审慎而灵活的。“惺惺惜惺惺”,毕竟仍有不少可取之处,至少它对纯洁情感追求的坦率、坚定就是值得肯定的。因此,金庸的小说如《书剑恩仇录》、《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鹿鼎记》等数部代表作品中就有不少正面歌颂“兄弟情深”的文字。但从另一方面看,金庸立足现代社会思潮中男女平等与自由恋爱思想而构建的“携手走天涯”的另一套男女情爱故事模式,却从更高更广的层面上,真正展现了他的情感本位的价值取向。这是作者崇尚的现代自由精神和民间纵横无束思想在情感上的具体体现。我们可以看到,金庸作品中的男女恋情,总是发源于无端即所谓的一见钟情。唯其无端,所以爱才显得一尘不染。而在这“爱”之光的照耀下,金庸笔下的男女双方作为个体就是绝对自由的,他们以各自的性情、禀赋,苦苦寻求走到一起的路。传统的情感话语系统中,女性根本没有说话地位(所以过去的武侠小说只有“惺惺惜惺惺”),而金庸却以其丰厚的现代人文意识在其武侠文本描写中,为女性争回了这早就该有的地位。不仅如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还十分强调女性是完全独立于男性的自由感情个体。她们可能会为某一个男孩爱得死去活来,但这和传统女性只能依附在男人的羽翼下生存而爱男人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她们有自己爱的自由,也有自己收回爱的自由。像《倚天屠龙记》中,殷离原来一直苦苦追求着张无忌,但当张无忌终于接受她后,她却觉得张无忌其实并不是自己理想中的爱人,便又毅然离开了张。这类根植于现代个体自由意识基础上的“携手走天涯”的爱情故事,无疑较之“惺惺惜惺惺”的表达模式,更能从通达灵性的诗意境界上,将武侠小说既张扬自由个性,又强调纯洁精神自律的理想情感模式酣畅淋漓地表现出来。
当然,金庸的男女爱情故事描写历来也不乏批评争议。将他“携手走天涯”的故事剥离开来,可以发现内中明显地存在着一个“众星追月”的所指:老是几个女孩共同追求一个男孩。不妨可以这样说,在金庸的武侠世界里,男女双方在感情上还不是完全平等的,作为一位男性作家,他的情感价值取向多少还残留着某些非现代的男性中心的痕迹。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宜对金庸如是描写作过分的苛求。因为武侠小说从文体本质上讲就可堪称为男性的文学:是男性作者写的给男性读者看的文学,所以,男性的标准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武侠文学的标准。在20世纪文学现代性的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并且确实不断地在进行着破除这种堂皇的男性中心叙事的努力,但同样也期期不可地反其道而行之,以贬损男性与生俱有的外向性、进取性、阳刚性等雄性特征为代价去求取所谓的现代性。那样,对武侠小说的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它也不是真正的现代性。梁羽生的女性意识比金庸还要进步,女侠在颇多情况下往往就是他小说中的中心英雄,但人们却常因此感到他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缺乏应有的豪情,比起金庸笔下的英雄人物逊色太多。不少女读者甚至也因为在他作品中体验不到武侠小说一贯张扬的阳刚气韵而驻足不观。由此可知,在武侠作品中把握好男女关系描写的分寸,是很困难的,至少现在还没有令人满意的理想范本。比较起来,金庸的创作还是成功的,如黄蓉、李秀眉等形象,由于作者较为丰满有力地展现了她们自主、自立、自强的性格,它已隐然具有破除“众星追月”倾向而又暗合武侠文体规律的现代品格了。
四
金庸是整整一个时代的武侠小说创作的巅峰。但金庸之后,历史毕竟揭开了新的一页,武侠小说如何超越金庸模式而“后金庸”呢,自然就成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20年前,金庸在其创作高峰时期,忽然宣布金盘洗手,封笔退出武侠文坛,是否意味着他已感觉到武侠文体机制在向现代转换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深层问题难以克服?在金庸封笔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武侠创作的整体态势由盛渐趋平淡乃至衰退,只产生了温瑞安、黄易等少数几位有影响的后进作家。个中原因,除了作家们的素质涵养和思想艺术境界普遍不高、远不如金庸外,金庸武侠模式中未曾解决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文学现代性步伐的加快,暴露得日益明显,恐怕更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对武侠小说中传统伦理道德尤其是女性观念如何现代性, 作家们大都犹豫不决,把握不准。如前所述,武侠文学某种程度上就是男性的文学,以男性为标准来考察问题往往在所难免。但现实的发展和女性地位的改变却对此提出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事实上,这一文体特征要求与现代观念变迁如何相适应的问题,在金庸时代就已颇露端倪,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表现得如今天这般尖锐,所以,金庸还可以动情讲他的“众星追月”故事。但在今天,却再也没有一个男性作家充满自信地这样做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套既符合文体特征需要,又顺应时代发展的理想叙事模式。
2.对传统人文信仰包括“除暴安良”的功能作用问题, 金庸愈到后来愈感怀疑了。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重要话题,即个体拥有自由和能力的限度问题。“侠客能拯救我吗?”古龙似乎充满了悲观绝望,于是他笔下的侠客更多的只会喝酒,借酒消愁。这对传统侠客的“除暴安良”神话实际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讽刺。在现实英雄匮乏、理想消解的年代里,作家怎样点燃人文信仰,以何方式表达他的理想激情,的确让人感到棘手。当然,我们可以说武侠小说就是“梦的文学”。但“梦的文学”也要有现实的底蕴,起码作家的创作要有解释的激情,有人文的激情,这是文学创作最基本也是最宝贵的原动力。唯其写的是远离现实之“梦”,这就更需要作者主体的激情投入。遗憾的是,在金庸之后的时代里,武侠小说缺少的恰恰就是这种激情。
3.在金庸之后,像金庸那样超长篇的、 多重互涉文本的构建是否可能?金庸之后,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不少作家的武侠故事越写越短。这当然与他们对武侠信仰激情的消退不无关系——缺乏足够的精神自信,要想像前辈们一样用宏篇巨制来建构一个完全独立于现实的武侠世界,难度可想而知。然而,从武侠小说精神趣味的展现以及种种最为引人入胜、曲折幽微的情节的表达来看,它却需要有一个足够长的和复杂的文本构造。文体机制的要求与客观现实之间产生了矛盾、牴牾。古龙与温瑞安尝试着将许多现代派的写作手法引入武侠小说,想以此改造人们长期形成的阅读心理定势。但他们的努力很难被视为成功。这倒并不是说现代派手法不能被引入武侠创作,但一定的手法总与一定的精神趣味、价值取向相联系。总的看来,武侠小说的精神内涵至今仍然倾向于古典与传统,属于新守成主义文学思潮的范畴,要使它和现代文化形态全面接轨,实在是一个非常艰苦而复杂的改造工作。以为将一些现代派文艺的写作模式引入武侠小说,就完成了对武侠文本的“现代改造”,这肯定是一场误会。
当然,我们这样说仅仅只是提出问题,并无意于赞同或推导出这样一种宿命的结论:武侠小说发展到今天已寿终正寝了。恰恰相反,对未来武侠小说的前景,我们还不无乐观的希望。在我们看来,武侠小说所讴歌的“除暴安良”的侠义精神,作为历史的真实虽然无法实现,但作为文化的真实,其行为和理想却有着不可磨灭的价值意义。从文学与人的关系看,诚如有人所指出的,尽管随着时代发展和法制不断完善,我们的社会终将趋向更公正、更平等,但它并无法消弭或取代武侠小说作为精神性、情感性文体生存的基础。道理很简单:即使有健全的法制,它也不可能解决人的精神情感问题;精神情感包括消费性的精神情感,它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物质富裕的时代更是如此。
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地深入。随着社会的变化发展,科学技术的昌明,武侠小说所提倡的那些道德情感、信仰准则是否也将越来越失去价值意义?不少人实际就是抱着这样的态度。但这过分乐观的社会进化论观念实在包含着很大的认识误区。马克思·韦伯早就指出,科技昌明决不能代替人类的终极关怀,相反,它倒或可能将人类存在与世界存在之间的种种矛盾关系凸显、激化。对自我生存的无尽关注与焦虑,是每一个个体无法摆脱的宿命。因此,怎样提供一种艺术的佳构,使个体灵魂得以栖居和安身立命,就成了现代艺术的努力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武侠小说所展现的那古风饶朴的生存图画,那份将传统理想生存境界诗意提纯并升华的飘逸美丽,不正是对现代人苦寂心灵的一种莫大安慰么?至少,它所流露的对传统无尽依恋之情的文体属性,就可提醒每一个现代人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前人的世界”(雅斯贝尔斯语)尽管在物理形态上已属过去,但在精神世界上,它却将永远自足地存在,并对现代人类整个精神文明构成起着积极的作用。而且,武侠小说是宣扬英雄精神的,它将这古典形态的精神气质“保存”至今天,这对后工业社会尤有一种灵魂唤醒与拯救的作用。倘若据此而立论,武侠文体的艺术潜质不是被挖掘殆尽,而是远远未得到应有的开发。这,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金庸之后,武侠小说何以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并将能够继续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从目前创作实践来看,情况虽不堪乐观,但多少也有了一些可喜的征兆,它确确实实地预示了金庸之后武侠小说还有发展、突破的可能性。这方面黄易或许是一位值得注意的作家。他的《寻秦记》、《大剑师传奇》等作品,尽管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憾,包括庸俗化的致命缺点,但这些作品的出现,至少从观念到操作技法上都对武侠小说如何“后金庸”有着可贵的启迪作用,如比较开放的女性观,站在全人类高度观照侠义精神,打破历史真实的束缚而自拟自创文化背景,对现实的讽喻与对人类未来的预言等等。正是立足于此,我们对武侠小说的“后金庸”发展前景仍寄予比较乐观的希望。当然,这些在现在说来,更多的恐怕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真正的结果还有待于未来实践的检验。
标签:金庸论文; 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倚天屠龙记论文; 金庸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武侠小说作者列表论文; 情感模式论文; 现代性论文; 侠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