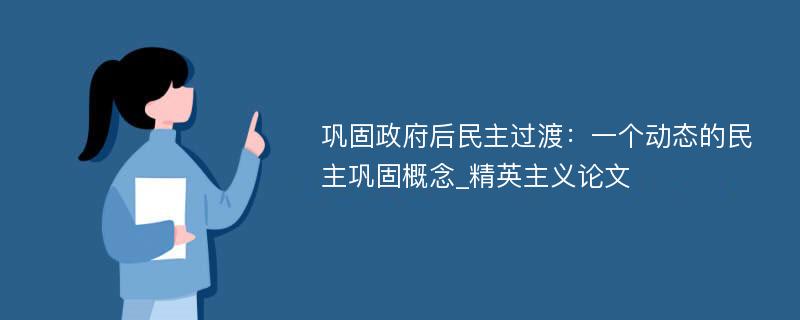
后民主转型的政体巩固:一个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政体论文,概念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99(2008)05-0001-07
二十世纪后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领域,人类世界经历了一系列引人注目且对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皆有影响的重大社会发展与变迁,经济方面的突出现象就是各国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前苏联解体为标志的冷战结束则预示着全球国际关系进入到后冷战的一超多强和多极化的时代,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开放和交流也见证了主要基于民族、种族和宗教差异之上更加广泛而带有全球性质的文化交融、互动与冲突,在全球政治领域,最主要而又最有影响力的现象莫过于人们常说的因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而得名的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1]。
一、问题的缘起
从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现代社会政治发展轨迹来看,不太符合罗斯托(Dankwart A.Rustow)民主转型的四阶段动态模式[2]:A、背景条件,即需要国家统一;B、准备阶段,即艰苦奋斗为民主转型准备好经济和社会条件;C、决定性阶段,即民主规则得到社会认可和实践而实现转型的关键阶段;D、习惯阶段,即民主的原则、规范等在社会生活中逐渐成为人们行为处事常规的阶段。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实际往往是出现了“C、决定性阶段”,但“B、准备阶段”远远不具备,有的国家甚至还不太具备“A、背景条件”,因此,第三波民主国家在转型后多数面临民主政体的维系和巩固问题。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民主巩固概念在比较政治学中成为一个频繁使用的概念被用来研究拉丁美洲、东欧、东亚和南欧等地区的政治[3]。民主巩固的英文是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或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在实际的应用中,两者没多少区别,往往被交换着使用以表达同一意思①,本文主要采用democratic consolidation来称谓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研究。很难准确定义民主巩固,但它的最初来源是用来分析那些已经历了第三波民主转型的国家[3],分析这些国家在民主转型后所面临的诸多体制稳定和巩固问题。学者们对民主转型后的民主巩固研究投入了极大的热情,随着民主巩固研究的扩展和深入,出现了两种极端,一方面,一些学者将民主巩固等同于民主化国家转型后对这些国家所有政治问题的研究[3];另一方面,原本用来研究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概念也开始被用来研究那些老的、传统的西欧民主国家[3]。在民主巩固研究繁荣多样的背后是概念的混乱和不统一,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写到“在目前概念混乱的情况下,民主巩固的研究被斥责为停滞不前。这一令人振奋的‘巩固学’亚学科停留在不清晰、不一致和没有限制的概念里,并因而根本没被限制在任何地方,而是漂浮在一片黑暗的水域里”[4]。种种触目惊心的研究混乱和不一致,本文认为学者们的分歧点大体在于民主巩固概念的出发点和目的点不一致,这两点大体相近于谢德勒归纳民主巩固概念的各种定义时所依据的两方面——“我们在哪(我们的经验观点)”和“我们的目标在哪(我们的规范视野)”[4]。面对民主巩固研究如此混乱不堪的概念现状,有的学者干脆就抛弃了民主巩固这一用语,如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认为民主和巩固是两个具有不同发展逻辑的概念,将两者作为一个词汇来使用将毫无意义[5]。大多数学者依然应用民主巩固概念来分析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政体巩固问题,本文也认为民主巩固概念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需从新的角度理解民主巩固,同时不宜将民主巩固概念的使用扩大化。
二、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
为使民主巩固概念在学术上具研究价值,本文并不赞同如奥唐奈那样弃民主巩固概念而不用,但本文同时认为如不从新的视角理解民主巩固概念,则这一概念可能真如谢德勒所说那样永远停留在一片黑暗不固定的概念混水里。学者汉森(Stephen G.Hanson)认为应构建民主巩固的动态理论[6],受此启发,本文也尝试从众说纷纭的各家观点里找到一些可能的共同出发点和可能的概念重合点,以这些出发点和重合点为基础,综合各主要观点从一个新的动态角度来理解和阐释民主巩固概念。
(一)民主巩固观点的简单综合
自罗斯托关于民主转型的开创性文章以来,凡论及民主化的著作,多数都会涉及政体转型后的巩固问题,罗斯托文章所选的两个国家——瑞典和土耳其就不是第三波民主国家[7],但他的文章里也隐含了对转型后民主体制巩固问题的分析。然而,如今的民主巩固概念已不限于用来分析第三波民主国家,对非第三波民主国家体制巩固问题的分析也被一些学者冠以民主巩固研究的称谓。尽管出现了概念应用范围的扩大,但多数学者还是只对第三波民主国家使用民主巩固概念,本文认同这一观点,只分析综合这类多数学者的观点。
许多著名学者专门论述过第三波国家民主转型后的政体巩固问题,这些学者包括亨廷顿、奥唐奈、林茨与斯蒂潘(Juan J.Linz and Alfred Stepan)、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谢德勒(Andreas Schedler)等人②。综合各种民主巩固概念的观点,民主巩固概念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第一、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第二、民主巩固的定义和判断;第三、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由于民主巩固的定义决定着对民主巩固的判断,学者们多数由于定义的不一而导致对民主巩固的判断大不相同,因此民主巩固的定义和判断是一个紧密相连的理论分析内容。绝大部分学者的民主巩固观点涉及以上三部分内容的一部分或全部,涉及全部者如林茨与斯蒂潘,他们指出了民主巩固的三个前提条件,并认为应从三个方面来判断民主巩固,同时认为民主巩固与五个领域的因素相关[8];涉及部分者如普沃斯基,他与其他学者用大量数据分析了民主维系巩固与经济、制度、国际政治气候(International climate)和政治经历(Political learning)等因素的关系[9]。
在表面上毫无共识的各家观点里,主要学者的观点在两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第一,关于民主巩固概念中的民主及民主体制的定义,大多数学者都以达尔(Robert A.Dahl)多头民主(Polyarchy)所列之八项社会制度保证[10]为基础定义民主及民主体制,并且几乎都是以程序来分析民主,对民主体制的定义也包括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并非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才是民主体制。比如奥唐奈,针对南美民主国家的现实,将达尔的多头民主定义做了一定扩充,认为多头民主还应该包括:在宪法规定的任期结束以前,不得随意撤销选举产生的官员(包括一些指定的官员);选举出的政府权威不应受到其它非选举人员(特别是武装部队)的严格限制、否决和被排除在某些政策领域之外;应有一个无争议的清楚界定选民人口的国家领域;对公平选举程序及其相关自由的普遍期望一直延续到无尽的将来。[5]第二,对如何判断民主巩固,观点虽各异,但“林茨与斯蒂潘在本书中提出的民主巩固定义特别有影响力”[11]。林茨与斯蒂潘对民主巩固的判断体现于对巩固的民主所做的“操作化定义”(working definition):“行为上(Behaviorally),当没有具影响力的族群、社会、经济、政治或国家机构内的行动者使用有影响力的资源试图通过创建非民主体制或通过从国家分离出去的方式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时,民主体制在一国内就巩固了。态度上(Attitudinally),当绝大多数公众即使身处重大经济困难和对现任政府极度不信任时依然相信民主程序和制度是管理集体生活的最适当方式,当对反体制选择的支持相当弱小或者一定程度上被隔离在支持民主的力量之外时,民主体制就巩固了。宪政上(Constitutionally),当政府或非政府的力量遵循和习惯于在新民主程序规则认可的专门法律、具体程序和国家机构框架内解决冲突时,民主体制就巩固了。”[12]在林茨与斯蒂潘之后,尽管学者们的具体判断内容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都从人们的态度、行为和宪政等方面来定义和判断民主巩固,尤以从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两个维度来判断民主巩固最为学者们接受,比如戴蒙德就从规范、行为两维度和精英、组织、公众三层次的综合标志来判断民主巩固[13]。在庞杂无序的各种民主巩固概念里,上述两方面的有限共识表明某些理论一致性还是存在的,这些有限的共识正是本文动态民主巩固概念的出发点,没有这些共识,我们根本无法合理阐释任何民主巩固概念。
在对主要观点的综合分析中,我们看到民主巩固概念主要包括前提条件、定义及判断和影响因素三方面,虽然在民主巩固的判断上存在一些有限共识,但观点的分歧也主要集中在民主巩固的定义及判断方面。本文动态民主巩固概念的动态性主要表现在民主巩固的定义和判断上,因此本文也主要从这一方面来具体阐释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
(二)动态的民主巩固定义
许多学者都将民主巩固视为一个过程(process),奥唐奈前期的观点将民主巩固称为从民主政府(democratic government)到民主政体(democratic regime)的第二次转型[14],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认为民主巩固是一个涉及“局部体制”(partial regimes)构建的过程[15],而戴蒙德将民主巩固视为民主体制合法化(legitimation)扩大和深化的过程[13]。本文认为,将民主巩固视为一个过程只是动态民主巩固概念的一个方面,而它的另一方面,而对民主巩固过程的结果、终点的观点才最能体现本文民主巩固概念的动态方面。对于民主巩固过程的终点,奥唐奈前期的观点认为是民主政体,即“已巩固的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y),大多数学者都这么认为,包括林茨与斯蒂潘、戴蒙德等(见前文所引各注释)。然而,即使在林茨与斯蒂潘的观点里,他们也认为“巩固了的民主”是一个由低到高的系列,并不存在唯一巩固了的民主体制[12]。谢德勒写到“民主是一个移动的目标、一个终点开放(open-ended)的发展的事物”[4],但他并没有将此观点与自己的民主巩固概念联系起来,本文认为同样应将民主巩固过程的终点视为一个移动的目标、一个终点开放的发展的事物。学者汉森(Stephen G.Hanson)认为,“如果‘民主巩固’要成为理论上有用的概念,我认为,它必须被重新定义为一个较大动态过程的某一阶段,而非一个静止的终点”[5]。本文认同汉森的观点,应以动态的、无终点的观点定义民主巩固。奥唐奈近期的观点抛弃了民主巩固的概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民主”与“巩固”分别表达了不同的发展逻辑,前者是延续的逻辑,后者是静止的逻辑,将它们同置一处并称“民主巩固”并不合适[5],本文认为如将民主巩固界定为一个动态、无终点的概念,则可很大程度上消除奥唐奈对“民主巩固”称谓的批评。总之,本文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包括两方面内涵:一方面,民主巩固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第三波国家民主政府的建立;另一方面,民主巩固作为一个过程是无终点的动态过程。在描述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民主巩固过程中,本文并不完全排斥民主巩固所具有的受奥唐奈批评的“目的论”(teleology)色彩[16],正如谢德勒所说,某种程度的目的论在民主巩固概念里很难避免,但其对概念的损害并不大[4]。本文认为,只要是民主体制则必然存在一些相似点,在第三波民主国家民主体制的巩固过程中,它们的民主体制可能会表现出与老牌民主体制所共有的一些相似点,从这一角度看,民主巩固确实具有目的论色彩,但我们更应将各国的民主巩固看作一个民主体制曲折发展、有所反复而又各具特色的过程。
因此,本文这样来定义民主巩固:第三波民主化中已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之民主政治体制得以维持并不断强化的动态过程。
(三)动态的民主巩固判断指标
作为一个动态过程的民主巩固,本文认为用“已巩固的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y)这一类静止的标准来判断它并不合适,应从相互对比的角度来判断民主巩固的情况,可从横向与纵向两方面判断,横向判断基于不同国家相同时期的对比,而纵向判断基于同一国家不同时期的对比,结论也不应被表述为“已巩固的民主”(consolidated democracy)或“未巩固的民主”(unconsolidated democracy),而表述为“民主体制较它国更巩固或更不巩固”或“民主体制较前期更巩固或更不巩固”则较为合适。在民主巩固判断的标准上,本文认为用指标(index)比标志(indicator)更合理,没有任何标志(indicator)能够表明民主已巩固,但有许多指标(index)可以被用来比较并判断民主巩固的具体情况。
综合各主要学者关于民主巩固如何判断的观点,本文认为民主巩固指标应包括三方面。首先,核心方面。以较为流行的林茨与斯蒂潘的观点(见前文)为基础,将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视为判断民主巩固的核心方面,关于林茨与斯蒂潘所言之宪政方面,正如戴蒙德所论,它已包含在行为里[13],他们的三个维度可简化为两个维度。因此,本文认为民主巩固的核心方面为“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其次、基础方面。谢德勒认为民主巩固概念应仅涉及民主体制的生存(democratic survival)问题,即民主巩固概念应采用他所总结的“消极”(negative)定义[4],本文认为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民主政体的存在是本文所言之民主巩固的前提条件之一,而民主体制在建立后的存在和维持问题也应该是民主巩固概念应涉及的基础问题。但本文认为民主巩固不应只限于谢德勒所说的消极巩固,也应包括部分他所说的“积极”(positive)民主巩固的内容[4],即民主巩固还应包括民主原则、规范和制度不断得到人们遵从和接受的过程,只有这样,民主体制才能真正存续。本文民主巩固判断指标的基础方面就是民主体制的维系。第三、制度方面。民主体制建立后对人们的态度、行为都会产生影响,因而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是判断民主巩固的核心方面,而民主政体的维系也是判断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本文认为民主制度本身的制度化情况也应作为判断民主巩固的重要指标。新老制度主义观点都提醒我们关注制度所具有的独特意义[17],而多数学者在民主巩固概念的分析中都直接或间接地论及民主体制的制度化问题,奥唐奈更是进一步提醒我们关注非正式规则的制度化对民主存续的影响[5]。本文民主巩固判断指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民主体制的制度化。民主巩固的判断指标与影响因素往往不易区分,比如政治文化既可作为判断民主巩固的指标,也可作为影响民主巩固的主要因素。虽然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区分民主巩固的判断指标与影响因素的现实意义不大,但在民主巩固概念的分析上,这种区分却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同义反复。本文以各主要学者的观点为基础,较主观地认为直接体现民主原则、规范的态度、行为和制度以及民主体制的生存是民主巩固的判断指标。概括起来,在本文的动态民主巩固概念中,民主巩固的判断指标包括三个大的方面:民主政体的维系、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和民主政体的制度化。
1、民主政体的维系
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转型后面临亨廷顿所说的三类问题——转型问题、情景问题和体制问题[1],第三波民主国家经常面临的迫切问题是转型问题和情景问题,这些问题常常影响着民主政体的稳定和生存。本文认为对转型问题和情景问题的分析与处理主要属于民主巩固的影响因素所分析的内容,此处关注的是哪些转型问题和情景问题是判断民主政体巩固程度的指标。本文认为用反面指标来判断民主政体的维系是可取的,在这一指标里,最基本的指标当然是民主政体没有垮台,比如,2006年泰国出现了成功的军事政变,由于民主政体已垮台,此时谈及泰国的民主巩固问题已无意义。因此,民主政体维系这一指标主要指那些虽然指向民主政体但并未导致民主政体垮台的因素。这些指标包括:政变、地区分裂、反叛活动、恐怖活动和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等,如这些指标出现频率低且影响较小,则民主巩固程度较高,否则,民主巩固程度较低。
2、人们的态度与行为
戴蒙德将民主巩固的标志(indicator)划分为规范(norms)、行为(behavior)两个维度,并从精英(elites)、组织(organizations)和公众(mass public)三个层次分析[13,18]。本文基于戴蒙德的划分来分析人们态度与行为方面的民主巩固指标,但具体指标的含义有几点重要之处区别与戴蒙德的观点:第一,戴蒙德的巩固标志是具体的静止的指标,而本文民主巩固的指标处于一个很宽泛的开放区间,并没有具体指明到何处民主就巩固了,只是说明应从哪些方面判断民主巩固的程度。这也与上文动态民主巩固的定义是一致的;第二,本文将戴蒙德观点中的规范维度界定为态度维度,名称不一,但内涵相近;第三、本文仅从精英和公众两个层次分析人们的态度、行为,不含戴蒙德观点中的组织层次。在转型后民主巩固的过程中,公民社会中的各种组织多归于沉寂,其领袖和活跃分子或进人政界或进入商界,公民社会重归弱小状态[19],因此本文不专门关注公民社会中的组织群体;军队的严格等级制度决定了军队首长的核心作用,本文将在精英里分析军事精英,不专门将军队作为一个组织分析;对于最重要一类组织群体——政党,本文将分析政治精英,而在下文的制度化里将专门涉及政党制度,此处也不专门分析政党;基于上述这些理由,本文民主巩固的指标分析不含戴蒙德观点中的组织层次。
本文从精英、公众两个层次来分析人们态度、行为方面的民主巩固指标。精英层次,与伯顿(Michael Burton)等人划分精英的逻辑不同[20],本文依照戴蒙德的观点按职业和领域划分精英,但不象戴蒙德那样几乎涉及各种精英,本文仅分析在多数第三波国家中起关键作用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军事精英,这三类精英在态度、行为方面体现出的民主观念最重要,与民主政体的巩固和稳定息息相关。公众层次,并非关注每一位公民的态度和行为,只需关注大部分公众的情况,用戴蒙德的标准就是70%对15%[13],即大多数的公众赞同民主政体,但本文认为某一固定比例的标志过于静态,不符合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关注的焦点应该是这一比例的变化。概括起来,本文在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上的民主巩固指标主要分为四方面:精英的态度、精英的行为、公众的态度和公众的行为;精英的态度和行为在转型后的初期阶段尤其重要,长期来看,公众的态度和行为是判断民主体制长期巩固的关键指标。由于本文主要借用戴蒙德的分析,而戴蒙德已用表格较具体完整地分析了如何在人们的态度和行为上判断民主巩固,本文的具体指标大体与戴蒙德的分析无异,因此我们不再分析人们态度和行为上的具体指标,只是在具体应用时需特别注意前文已分析的差异之处。
3、民主体制的制度化
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学者们用来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稳定,比如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21]。关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政治稳定,即民主巩固问题,其实也是更大意义上关于政治稳定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森认为应从更广的制度巩固视野来审视民主巩固,要从包括非民主体制等所有体制的巩固分析中找到有利于民主巩固的因素[6]。本文认为研究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制度化理论同样可用于民主巩固的制度化研究。关于制度化的解释很多,本文不详叙,只介绍亨廷顿的观点,他认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21],亨廷顿对制度化的解释主要针对体制的稳定,而民主巩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体制稳定,因此本文引用亨廷顿的制度化观点分析民主巩固中的制度化问题。
在民主国家的政治体制里,行政官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要性最突出,本文主要分析这五类制度的制度化情况,以它们的制度化程度作为判断民主巩固的指标。在亨廷顿的制度化分析中,以适应性(adaptability)、复杂性(complexity)、自主性(autonomy)和凝聚性(coherence)等四方面的特征来衡量体制的制度化[21],本文借用亨廷顿的分析,从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这四方面来衡量体制的制度化程度。因此,民主巩固在民主体制制度化方面的判断指标就包括:民主的行政官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在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等四方面的制度化程度。在具体的分析中,制度化四方面的特征在五类制度中的重要性不完全相同:在行政官僚制度和政党制度中,四个特征皆需重点分析;在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中,更应关注它们的适应性和自主性;在司法制度中,自主性问题最突出。
从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出发,我们采纳了一些学者的主要观点,特别是林茨与斯蒂潘、戴蒙德等人的民主巩固观点,将民主巩固的判断指标划分为民主体制的维系、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民主体制的制度化三大类,每一大类下还有更具体的判断指标。三大类指标并非毫无关联,其重要性也非毫无差别,可从两方面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第一,相对重要性方面。人们的态度与行为在判断民主巩固的三大类指标中居于核心地位,如果不分析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仅以民主政体的维系来判断民主巩固还远远不够,比如菲律宾,其民主体制先于韩国建立,但它的巩固程度显然不如后者。普沃斯基等人就认为巩固不仅仅是时间延续的问题,也不是某种习惯性或机械的制度化问题[9],而戴蒙德也认为要回应奥唐奈在制度化等方面对民主巩固概念提出的挑战,必须退后一步关注主要政治参与者的行为和信仰模式[19];反过来,也不能忽视政体的维系和制度化问题,民主政体维系是民主巩固的基础,而民主体制制度化本身也具有促进民主巩固的作用。第二,相互关系方面。只有民主体制维系才能使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稳定下来并促进对民主原则、规范和体制的遵循与认同,而人们在态度与行为方面对民主的认同决定着民主政体的长久延续和稳定;人们民主态度与行为的习惯化和重复化显示着民主体制的制度化,民主体制的各项制度也时常规范着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民主体制的维系、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民主体制的制度化三者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结语
第三波民主化至今已三十多年,但除了那些在此波民主潮流中最先转型的南欧国家,其它地区的第三波民主国家多数依然受各种各样的体制存续和稳定问题所困扰。虽然没有明显征兆预示着威权政体回潮的可能,但困扰第三波民主国家的政体巩固问题依然需要全面深入的分析。不幸的是,尽管学者们对民主巩固问题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著述也比比皆是,但民主巩固概念的分析却相当混乱,理论的共识和一致之处很少,这与民主巩固问题本身的重要性极为不符。如希望对实际的民主巩固问题理解得更全面和更深人,并进一步对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实际政治生活有所帮助,可能的方式是澄清理论的混乱并找到更多的概念共识,以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民主巩固概念。本文正是基于上述想法,在对学者们的民主巩固观点做了一些综合之后,我们认为在概念混乱的表象下,一些定义的共识和一致还是存在的,从这些共识和一致出发,本文提出一个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这种动态的民主巩固概念可能有助于厘清民主巩固问题分析上的混乱和回应部分学者对民主巩固概念的批评。
注释:
①也有学者将democratic consolidation与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区别而更常使用the consolidation of democracy,比如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参见菲力普·施密特:《有关民主巩固的一些基本假设》,载于猪口孝(Takashi Inoguchi)等编、林猛等译《变动中的民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8页。
②就民主巩固问题来看,国内对这些学者之观点进行分析的文章并不多,纵观之下,分析得较全面的是对戴蒙德观点的分析。参见杨仁厚.拉里·戴蒙德民主巩固理论述评[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5-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