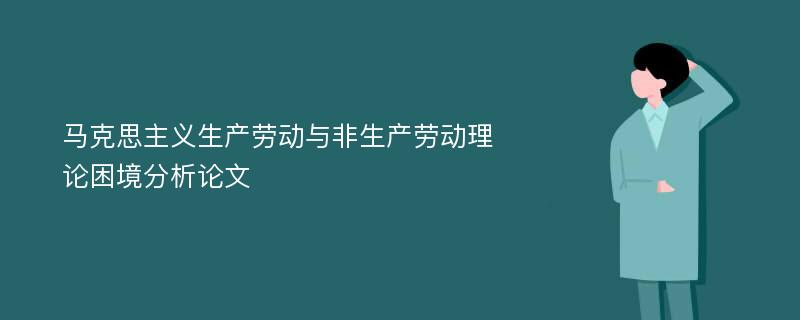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困境分析
朱 阳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进行了符合当时社会实践的定义。在数字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应该综合多方面因素。在充分认识劳动本质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的生产关系,结合社会的发展变化,将劳动置于生产的全过程中来认识。
关键词: 生产劳动;非生产劳动;非物质劳动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直是存在着较大分歧的问题。长期以来,各学派和不同学者对其理解并没有达成一致。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始,到目前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以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运用为标志,劳动和生产的形式发生剧烈变化。加深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内涵的理解和辨析,将有助于科学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的性质。
一、马克思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解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最初的研究者戴韦南特、配第是在重商主义剩余价值的理论基础上进行分析的。戴韦南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劳动不但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可以给国民资本带来增长,这种劳动就是生产劳动。配第认为,土地耕种者、海员、士兵、手工业者和商人,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能为国家带来财富的增长。
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最直接和最集中的论述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理论的分析和批判中展开的。马克思认为:“亚当·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二重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的定义也是如此。”[1,p142]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提出了两个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定义。第一种定义认为生产劳动是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非生产劳动是同收入相交换的劳动。斯密说:“有一种劳动,加在物上,能增加物的价值;另一种劳动,却不能够。前者因可生产价值,可称为生产劳动,后者可称为非生产劳动。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会把维持自身生活所需的价值与提供雇主利润的价值,加在所加工的原材料的价值上。反之,家仆的劳动,却不能增加什么价值。”[2,p304]在此基础上,斯密又将生产劳动定义为生产资本的劳动,又是同资本相交换,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斯密的这个定义是将生产劳动置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指出资本积累与生产劳动的关系。与之相对应,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同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动)。第二种定义认为生产劳动是固定在物质上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上的劳动。斯密提出:“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可以固定并且实现在特殊商品或可卖商品上,可以经历一些时候,不会随生随灭。那似乎是把一部分劳动贮存起来,在必要时再提出来使用。”[2,p305]在这里斯密认为生产劳动能生产现实存在的、有形的商品,而且这种劳动是有价值的生产。他认为诸如君主、官吏、海陆军、牧师、律师、医师、文人、演员、歌手、舞蹈家等类人的劳动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但不能称为生产劳动。“这一类劳动中,就连最尊贵的,亦不能生产什么东西供日后购买等量劳动之用。”[2,p305]第二种定义中的生产实际上与第一中定义中的生产具有不同的内涵,它并没有考虑剩余价值的因素,而是单纯地将劳动视为劳动者转移自己工资所代表的价值量的劳动过程。通观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以看出,第二种定义受到重农主义理论的影响。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条件下,重农主义认为只有来源于土地的农业生产才能产生财富的积累。斯密进一步认为工业制造也能产生财富的积累。综合来理解,斯密的第二个定义实际上是将所有能够增加社会财富和产生资本积累的劳动都称为生产劳动。
斯密的两种理论在当时各有一定的支持者。第一种定义的支持者有李嘉图、西斯蒙第。第二种定义的支持者主要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反对者如热尔门·加尔涅认为所有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马克思认同斯密的第一种定义,即认为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相交换的劳动,并认为这是斯密的“巨大科学功劳之一”[1,p148]。但是,他仍认为斯密的两个定义是矛盾的。在斯密对生产劳动理解的基础上,马克思对生产劳动进行两个层次的阐释。第一个层次是:“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3,p47]这一论述是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核心定义,体现了整个社会生产关系中劳动的本质属性。第二个层次是对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即“生产劳动是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3,p61]。这两个层次的定义与斯密的理论十分相似,但是实际上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与斯密的第二种定义是具有不同含义的。补充定义的限定条件是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认为,决定劳动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并不是由劳动的特殊形式决定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劳动的外在形式。同一种劳动,既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区别的标准仅仅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4,p109]。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定义,超越了斯密对劳动的具体形态的研究,而将其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条件下,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代,都更具有普遍意义。
二、当代社会非物质生产领域内生产劳动内涵的争论
根据马克思的定义,在物质生产领域,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他仅对“服务”进行一定的阐述。关于“服务是否是生产劳动”这个问题,马克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马克思认为,一切服务都是非生产劳动。因为服务提供者的“劳动是由于它的使用价值而被消费,而不是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东西被消费,是非生产地消费,……,所以服务不是生产劳动,服务的担负者也不是生产劳动者”[4,p102]。但是,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角度来考察,非物质产品生产中消耗的同样是人的抽象劳动,这一点同物质产品生产没有区别,因而马克思认为“服务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1,p149]。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十分有限,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越来越普遍,这就需要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进行定义和区分。
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论时,对生产劳动具体形式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深入、不断扩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对于生产劳动的认识,马克思首先是将劳动主体由“生产工人”扩充到“总体工人”,而后将生产劳动从使用价值的生产扩充到使用价值的运输,继而扩充到使用价值的流通环节。随着社会发展,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认识也应该不断扩展与深入。因此,在当今社会,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不能认为全部是非生产劳动,因为现代社会的第三产业相当一部分已经与使用价值的创造联系起来,成为创造使用价值的前提条件和初始步骤,可以认定为生产劳动。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使机器可以独立地完成某种类型的生产工作,这时也应该结合时代的变化对生产劳动的含义进行一定的扩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工智能和机器生产的结合将极大提高生产力和解放劳动者,是达到马克思构想的人的全面解放的社会的一条重要途径。这种生产形式在表面上虽然缺少人的抽象劳动的参与,但由于它仍然是人发明、主导和控制,源于人的脑力劳动和对机器、能源等生产资料的使用,因而结合社会的发展来看,基于人工智能的机器生产可以视为生产劳动。
1)实验的进行不能顾此失彼,对于单桩竖向抗压承载力实验来说,为了避免荷载过重造成仪器损坏,影响实验数据的准确,必须进行必要的操作过程设计规范和细节控制说明,比如:当地基周围土壤隆起时,其观测点的荷载-沉降曲线必然出现陡降,实验中要注意记录陡降前后的荷载数值。此外,当地基基础桩后一次的沉降幅度超过前一次沉降幅度的2倍时,表明沉降过程尚未稳定,因此,要注意记录前一级的荷载数值。最后,在细节把控上,荷载-沉降曲线一定要按照信号传感器反馈的时间曲线进行绘制,必要的情况下,增加辅助曲线,增加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三、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重新审视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或资本的最大化,因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时,评判的标准即是围绕剩余价值展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非公有制要素,但是仍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因此,区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社会的标准,而应该看其劳动成果是否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部分具有公共保障或公益性质的劳动,如退耕还林还草并不会带来物质财富的增值,但是促进了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满足了人们对绿水青山的需要,可以认定为生产劳动。
从毛泽东同志的“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到习近平总书记“梁家河这个地方有大学问”,所反映出的是我们党一贯具有的求真务实精神和始终植根于人民大众这片沃土的民本情怀。面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中存在的各种挑战和增进人民福祉的热切期盼,我们的党员干部们只有常接地气、祛除娇气、摒弃傲气,才能激发出更多干事创业的朝气、攻坚克难的锐气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正气。不论是从培育好干部的“五个标准”来衡量,还是从增长党员干部“八个本领”的现实需要出发,机关党员干部在农村开展“三同”实践锻炼,堪称是一个好平台,是一个悟初心、践初心、强初心的好载体。
(一)正确认识劳动是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前提
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前,首先应该对“劳动”本身有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0,p201-202]在表面上看,马克思将劳动限于物质生产方面,但是从上下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是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劳动的基本内涵,是以物化劳动为例来说明劳动的本质。马克思又指出:“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10,p208]因此,劳动应该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都可以称为劳动。其一,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禁止的活动中,某些也创造了使用价值,例如生产毒品、私制枪支和滥用职权等行为,这些活动违背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秩序和方向,因而不能被评价为劳动。其二,某些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是偶然的、个别的、不具有生产目的的行为,也不能评价为劳动。例如,个人利用废旧物品的改造活动,虽然创造了使用价值,但是仅能满足特定个体的需求,且没有生产目的,不能认定为劳动。再如,朋友之间出于好意的修理、辅导、修改等帮助行为,虽然可能创造使用价值,也不能认定为劳动。
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中,近年来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非物质生产”理论采用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同的思路,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首先提出“非物质生产”的概念。他认为“非物质生产被界定为生产商品的信息内容和文化内容的劳动”[6]。生产商品信息内容的劳动指:“在工业和第三产业中大公司内工人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变化,在那里,与直接劳动相关的技术逐渐变成由控制论和计算机控制(以及垂直的和横向的交流)的技术。”[6]这种劳动不直接生产出商品,而是获取、传递商品生产所需的信息。文化内容的劳动则是指:“界定和确定文化与艺术标准、时尚、品味、消费指针以及更具有策略性的公众舆论等不同信息项目的活动。”[6]在这一理论基础上,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和《大众》中进一步对非物质生产进行阐述。在《帝国》中,他们将非物质劳动界定为“生产非物质商品的劳动”,并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已经被信息化和被融汇了先进通讯技术的大工业生产劳动,分析创造性的和日常象征性的劳动,人类交际和互动的情感性劳动[7]。在《大众》中他们修正了对非物质生产的定义,把非物质劳动定义为“生产非物质产品,比如知识、信息、交流、关系或一种情感反应的劳动”,并把它划分为两种主要的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是指智力的或语言的劳动,比如问题的解决、象征的和分析的任务、语言的表达,它所生产的是观念、符号、规则、文本、语言图形、想象以及其他这样的产品。第二种形式是“情感劳动”,生产的是放松、幸福、满足、兴奋或激情这样的情感[8]。哈特和奈格里对非物质生产进行独特的定义,主要目的是为当代社会的新的不同于工业社会的劳动形态进行统一的概括,使其能够用来阐述当今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并对社会形态产生支配作用的力量。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建议把非物质劳动理解为“生命政治劳动”(biopolitical labor)[9]。他们的理论显然是与马克思的定义采用完全不同的路径。从定义上看,这种“非物质劳动”仅仅是通过劳动产品的外在表现形式进行归纳的一个集合。马克思对劳动或生产的定义,并不是建立在劳动的具体形态上,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上。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本质属性提取出来,因而更具有普遍性和抽象性。但是,“非物质劳动”理论在当今数字经济时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看到这一类“非物质劳动”对于世界巨大的影响力:决定新的全球劳动分工、改变其他的生产方式、导致劳动社会化的急剧扩张,因而可以称其为“非物质性劳动霸权”[9]。
(二)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要结合具体的生产关系
数字经济时代呈现出以往不同的劳动形态,非物质劳动产生的影响力远超传统劳动,生产劳动的内涵也发生巨大变化,而且还在发生不断变化。因此,如果以生产劳动范围的“宽”“窄”来衡量生产劳动必将是不准确的。但是,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劳动形态下,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的标准,来重新审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三)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要结合社会的发展变化
关于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能否成为生产劳动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且严格按照马克思文本的定义来理解生产性劳动。认为只有直接的物质生产才能创造价值,是生产劳动;而艺术、科学研究、教育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不能创造价值,因而是非生产劳动。第二种意见认为,应该改变劳动价值论的规定性,认为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能创造价值,也是生产劳动,对生产劳动的范围划定更为宽泛。这种观点的支持者最多,以程恩富的“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5]为代表。第三种意见对生产劳动的界定范围介于前两者之间,他们主张在基本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适度扩大生产劳动的范围。这种意见可以视为对前两种意见的折衷。
石羊河流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经济司司长高俊才…………………………………………………………………(5.4)
(四)区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应该在生产关系中考察
早在马克思对生产劳动的研究中,就已经将其置于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来考察,马克思将生产劳动从使用价值的生产扩充到使用价值的流通环节就是一个例子。单独看流通环节,它并没有创造出使用价值,只是实现了商品的商业价值,但是马克思将它纳入到生产劳动中,就是在生产关系的整体上进行考察。在分工日益细化、越来越复杂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个产品或一个服务的产生需要多个部门的协作,生产劳动越来越具有整体化、社会化甚至全球化的特征,单一环节可能并没有立刻而现实地创造出使用价值和产生价值的增值,但是却是整个生产环节中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数字时代,互联网作为生产工具,无论是在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中,都使得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显著。无视生产的全球化而单独审视生产中的某个环节,很容易对生产的性质得出片面结论。
(五)生产劳动应是具有流通属性并且可以被消费的劳动
价值反映的是劳动者之间交换彼此劳动及劳动成果的一种社会关系。无论是物质领域的生产还是非物质领域的生产,产生的劳动成果只有进入流通领域才具有社会价值。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和军人等虽然也付出了劳动,但体现的是国家职能,最终取得工资报酬。这些劳动不能被所购买和消费,也没有产生使用价值,不能认定为生产劳动。对比来看,农民的部分农业劳动可以自给自足,但劳动产品仍然可以流通和消费,具有流通属性,因而是生产劳动。在数字时代,网民在网上发布的购物评价、朋友圈和微博,从个体看来虽然并不具有流通属性,但是经过大数据的统计整理,便可以被用来流通和消费,因而在非物质领域,是否是生产劳动也要具体分析。但是,不能说具有流通属性和可以被消费的劳动即是生产劳动。如贵金属和稀有矿石的开采,这些劳动的产品可以参与流通和交易,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是这种开采劳动的成果没有凝结抽象劳动,不能认定为生产劳动。
(六)劳动产品的具体形式不是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依据
劳动产品的具体形式与劳动的属性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而在一定时间内使生产劳动更多地以物质形式呈现出来。同一劳动成果的最终形式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如文艺工作者的表演活动,可以是现场演出,也可以固化到存储介质上作为商品出售。即使是同一外在形式的劳动成果,要评价其是生产劳动还是非生产劳动,也不能一概而论。如数字形式的软件、音像制品,对于作者的创作、出版发行商的制作、发行来说是生产劳动。但是,发行商一旦购买版权和完成制作后,出售行为只是对前述行为成果的无成本复制,应该视为非生产劳动。还应注意,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也不能全部视为生产劳动,还要剥离劳动的外在形式,具体分析劳动的本质。如国家工作人员、司法工作人员和军人的劳动、纯粹的商品贸易劳动显然都没有创造价值,都不能视为生产劳动。
1.灌输式、被动的接受性教学仍是当前高中政治课堂教学的主要模式,教师仍然起着绝对的主体作用,霸占着课堂教学的话语权,学生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充分体现。教师习惯一讲到底,惟恐学生听不懂,总认为讲得越细越好。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6卷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5]程恩富.科学地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兼立“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J].财经研究,2001,27(11):3-9.
[6]毛里齐奥·拉扎拉托,高燕.非物质劳动(上)[J].国外理论动态,2005,(3):41-44.
[7]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杨建国,等.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340.
[8]Hardt M, Negri A. Multitude: war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empire[M].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04:108.
[9]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何吉贤.帝国与后社会主义政治[J].天涯,2004,(5):72-81.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Analysis of the Predicament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of Marxism
ZHU Yang
(College of Politic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abor theory of value, Marx carried out the definition of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ocial practice at that time. In today’s society with highly developed digital economy, various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in distinguishing productive labor and unproductive labor. In the premise of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work, work should be placed in the whole production process to be acknowledged,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pecific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and society.
Key Words: productive labor; unproductive labor; immaterial labor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15(2019)02-0121-05
DOI: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2.023
收稿日期: 2018-09-21 修回日期:2018-12-30
作者简介: 朱阳(1985-),男,土家族,湖北宜昌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校对:孙尚斌)
标签:生产劳动论文; 非生产劳动论文; 非物质劳动论文; 国防大学政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