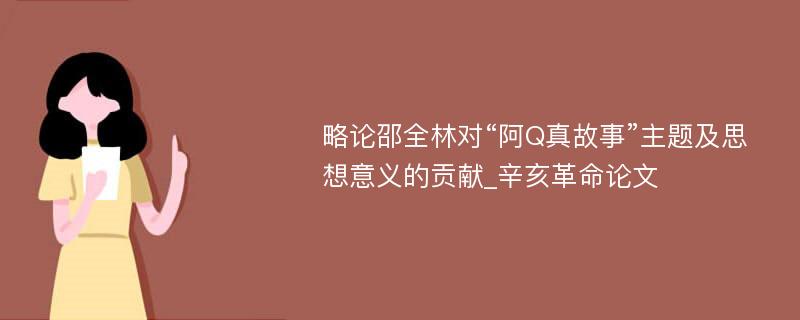
略评邵荃麟等论述《阿Q正传》主题和思想意义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传论文,论述论文,贡献论文,意义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四十年代桂林文化城的一些鲁迅研究专家对《阿Q 正传》的主题作了相当深刻的探讨。邵荃麟的“暴露国民的弱点”的观点与欧阳凡海的“追求革命动力和发掘革命的种子”的看法具有互补性。认为特别是当时邵荃麟关于《阿Q 正传》思想意义的论述更具有空前的全面性和深刻性,至今仍能给人巨大的启迪。
关键词 作品主题;作品思想意义;阿Q主义;典型性格内涵; 社会政治寓言;教育价值;社会价值;思想价值
《阿Q正传》的主题和思想意义是《阿Q正传》研究中的复杂问题之一,40年代桂林文化城的鲁迅研究专家们也曾就此问题展开讨论。
1942年5 月桂林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欧阳凡海的巨著《鲁迅的书》认为,鲁迅在写《知识即罪恶》时的认识已经起了变化, 因此“在《阿Q正传》中的热情,起了一种目的意识性的变化,这便是说,他不仅仅单纯地寄他的同情心于阿Q身上,并且……想从阿Q身上发掘革命的种子。”他又说:“作者由于思想跨进,想在阿Q身上发掘革命的种子, 无形中使《阿Q正传》所欲表达的主题复杂化了。 ”邵荃麟不同意欧阳凡海关于《阿Q 正传》的主题是“追求革命动力和发掘革命种子”这种提法,专门写了一篇《关于〈阿Q正传〉》的长篇评论,发表于1942 年10月桂林出版的《青年文艺》(双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在论证欧阳凡海的看法不能成立之后指出:“一部《阿Q正传》与其说是奴隶的革命史, 无宁说是奴隶革命失败史,或者说是奴隶的被压迫史,从这部血泪的历史中间使我们不仅清楚地看到奴隶是在反叛着,而且更看清楚奴隶自己的弱点,使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奋斗,并且和自己的弱点去奋斗,只有从这种奋斗中间,才能够孕育新的革命种子,然而却不在阿Q的身上, 而是在阿Q的后代——中国新的农民的身上了。”因此,“《阿Q正传》还不仅是阿Q 的奴隶根性暴露史,并且也是所有中国人奴隶根性的暴露。这就是鲁迅先生所谓国民弱点的暴露。”即认为,《阿Q 正传》的主题是“暴露国民的弱点”。
从当时至现在,鲁迅研究又前进50多年了,今天回头去看,对于《阿Q正传》主题问题的这些分歧,应当怎样评价呢?
我们认为,首先值得肯定的是,他们两人对主题这个概念的认识都是正确的。50年代以来不少文学史和文艺评论文章将主题这个概念胡乱运用,使初学者往往难以辨清。例如有人说什么某作家喜欢描写恋爱的主题、某作家喜欢描写改革的主题,其实这些主题指的是题材;又如有人说:“鲁迅的小说,不论是《狂人日记》还是《祝福》、《离婚》,都是一个主题:反封建。”这里的主题实际上是指作品中所提出的基本问题。另外还有人把主题与思想意义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其实思想意义主要是指读者对作品的思想内容的认识说的,在文学研究中属于比较主观的流动的东西;主题则主要是指作者对生活的认识说的,在文学研究中是比较客观的固定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作品的基本题材所表现的作家创作的思想意图。欧阳凡海和邵荃麟说的《阿Q正传》的主题, 都是说《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所以对主题这个概念的认识, 他们都是正确的、科学的。
其次,邵荃麟认为《阿Q正传》的主题是“暴露国民的弱点”, 显然比较正确,这因为它是根据鲁迅自己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中说过的:“《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同时, 这提法完全符合作品的实际。而今已为许多研究者所公认。50年代,李何林正是以这些为根据,进一步具体概括出“《阿Q 正传》的基本主题和基本思想,是对于辛亥革命前后各阶层人的精神胜利法的揭露和批判。”〔1〕
再次,我们应当指出,对于《阿Q正传》主题的提法, 邵荃麟的虽然比较正确,但是并不完满,欧阳凡海的提法不够准确,然而也有科学的成分:其一,他说“《阿Q正传》所欲表达的主题复杂化了”, 这就是说鲁迅在《阿Q正传》里所表现的主题不是一个, 至少是两个以上,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因为一个作品一般只有一个主题,但是,比较大型的或比较复杂的作品,往往也出现多主题的现象,有的在一个正主题之外还有一个副主题,有的在一个正主题之外,还有几个副主题。众所周知,《阿Q正传》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作品。其二,在《阿Q正传》主题研究史上,如果说邵荃麟是代表比较正确的一派的前辈,欧阳凡海似乎可说是倒“副”为“正”一派的叔祖。1960年7月14日《天津日报》发表南开大学中文系1956级写的《阶级论还是人性论?》一文就认为:“鲁迅先生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提出了农民的出路问题,这就是‘阿Q正传’的基本主题基本思想。”1977年9月由某所师范大学编写的《鲁迅作品选讲》认为“在《阿Q正传》里, 鲁迅通过对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农村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高度艺术概括,揭露了辛亥革命的事实,指出了中国进行一场新的革命的必要性;说明了农村阶级关系没有丝毫的变化;封建的统治没有被摧毁,农民的命运没有得到改变,既是辛亥革命失败的证据,也是这场革命失败的原因,又是中国需要一场新的革命的理由;还表现了农民身上蕴藏着的强烈的反抗要求,说明他们应该而且必将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显示了对革命前途的信心。”不难发现,欧阳凡海的看法与后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间接亲缘关系。其三,欧阳凡海提出的鲁迅“想从阿Q 身上发掘革命的种子”说虽有不准确之处,把它当作《阿Q正传》的第一主题尤其不妥, 但是在欧阳凡海之后,40年代末茅盾也提出了鲁迅的小说进行对革命力量的探索,50~60年代,以陈涌为代表的研究者们,更以阶级分析的方法,把鲁迅小说置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革命力量的高度去考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所以,如果欧阳凡海把上述提法修改为鲁迅通过《阿Q 正传》也探索了中国革命问题——批判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和提出了农民参加革命诸问题,就恰好是对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主题说的补充。
因此,研究了邵荃麟与欧阳凡海关于《阿Q正传》主题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这样概括:在集中暴露以精神胜利法为核心的“国民性弱点”的同时,彻底地批判辛亥革命的妥协性,并揭示农民既有革命的要求,而其革命要求又有严重的局限性等等,这就是《阿Q正传》的主题思想。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桂林文化城关于《阿Q 正传》主题问题的讨论是有收获的。然而收获最大的却不在此,而是邵荃麟在论述了他对《阿Q正传》主题的看法之后作进一步阐述:
……《阿Q正传》不仅暴露了奴隶的弱点, 并且也暴露了民族衰弱的根源;不仅是奴隶的失败史,并且是民族的失败史。从阿Q这个典型人物上,鲁迅先生是把辛亥时代中国社会以及民族的基本矛盾一起抉发出来了,并且藉此展开了社会思想形态的战斗。而在这中间,我们更看到了鲁迅先生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爱。《阿Q正传》的伟大思想内容和伟大的艺术价值, 我想是应该从这里去认识吧。
真是太中肯了,《阿Q正传》的伟大思想意义就应该从这里去深入理解。以下我分五点来阐释:
第一,“《阿Q正传》不仅暴露了奴隶的弱点, 并且也暴露了民族衰弱的根源。”这个提法是非常深刻的。因为在《阿Q 正传》中所批判的阿Q主义,不仅仅是被压迫者的许许多多人的精神弱点, 而且“是我们中华民族在意识形态、历史传统、行为方式等方面缺陷的总综合”。正如当今鲁迅研究者所认识到的:“阿Q 主义是中国人民在漫长的封建专制和蒙昧主义奴役下形成的慢性精神萎缩综合症。”有了这种病症的人,分明是愚弱落后却仍自命不凡,不知振奋,只图眼前一点小利,而好夸大,吃了亏也心造幻影,替对方想出最坏的方面,自以为得到了精神上的胜利,满足现状,不求上进;即使感觉到外国人有许多方面优于我们,也硬是从鸡蛋里挑骨头,以别人一些微末的缺点而全盘否定其优长,甚至美不过别人,就同人比丑,不以丑为耻,反以丑胜人为荣。因而,《阿Q正传》揭出我们民族的阿Q主义,就是“从特定的角度,揭示出了中华民族文化落后、经济落后、智力退化、社会停滞的根本原因。”〔2〕总括为一句话,就是邵荃麟说的《阿Q正传》“暴露了民族衰弱的根源”。鲁迅深知我们中国百姓有自卑自贱的一面,更有自尊自大的一面,极不愿意正视自己的缺陷,因而,“鲁迅不愿用理想化的方式来加固中国民众的自大心理,相反,他用极其锋利的精神解剖刀,点示出中国民族灵魂的全部痛快。”鲁迅暴露和批判了阿Q主义, 就为治好我国人民和民族的慢性精神萎缩综合症提供了可靠基础,也是20世纪人类学上的一个重要发现,“为现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民族精神综合症病例,为人类治愈和预防阿Q 主义病作出了卓越贡献。”〔3〕
第二,《阿Q正传》“不仅是奴隶的失败史, 并且是民族的失败史。”前面说的是阿Q典型性格内涵的深层意义, 这里说的是作为社会政治寓言的悲剧意义。阿Q作为文学典型人物, 自然就不是社会上的单个人,而是一个社会群体的代表,即封建社会里的奴隶——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在几千年来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就同阿Q一样, 不是不曾举行反抗,甚至当革命风声传来之时,敢于首先喊出“造反了!造反了!”可是他们由于不知革命的真正意义,从“彼可取而代之”的观念出发,错误地以为革命就是报复,就是攫取财物和占有妇女,要什么就是什么,想要谁就是谁,结果大都成为一些野心家篡权夺位、换朝改代的工具,以至成为伪革命和反革命的牺牲品。从秦末直至清末,无数贫苦人民参加过无数次的“起义”、“革命”,其结局不是基本上都同阿Q 一样么?因此,阿Q的失败史就是奴隶的失败史。 而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次最完整意义的民主民族革命。这次革命虽然取得一定的胜利,但总的说来是失败了。《阿Q 正传》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从兴起到失败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一部形象的中华民族的失败史。这部中国奴隶失败史和民族失败史的深刻意义是为中国革命提出了农民问题和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不启发群众觉悟、不发动群众参加的革命必然失败;农民具有潜在的巨大革命性,但不可能自发地找到一条解放自己的道路;革命党人决不能对封建势力妥协;在革命过程中,尤其在革命胜利的时刻,要特别注意阶级敌人混进来从内部破坏革命。
第三,《阿Q 正传》“把辛亥时代中国社会以及民族的基本矛盾一起抉发出来了”。鲁迅暴露和批判阿Q主义的意义, 一般研究者都是认识到了的,尽管有深浅的不同,但是对于《阿Q正传》所揭示的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社会条件和这作品的故事背景意义,论及的人却很少了,而邵荃麟则是最早将它提到应有的高度的人之一。事实正是这样,作品所显示出来的辛亥时代中国社会和民族的基本矛盾特征是极为鲜明的,人民大众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到处存在并一直发展着。辛亥革命前,封建统治阶级横行霸道,贪婪无耻,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被压迫到无法维持生计而仍不觉悟,统治阶级内部也勾心斗角。辛亥革命高潮到来,地主豪绅慌作一团,但他们善于投机,很快就混进“革命党”,农民被排斥在革命队伍之外。辛亥革命后,社会没有什么大变样,原来做官的还是做官,不过改了名称罢了,革命党动手剪辫子,但许多人只是把辫子盘在头上,监牢里关进的是交不出祖父手上欠下陈租的农民,想“造反”的阿Q被诬为盗犯遭枪决了, 人民群众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更尖锐了,但人民群众仍不觉悟,封建地主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继续明争暗斗,呈现此消彼长之势。无论辛亥革命之前和之后,中国社会都是专制统治,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或为主子,或为奴才,彼此之间没有平等的关系;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脱离,他们没有致富的手段,但并不安分。只要产生阿Q主义的这些社会条件依然存在,阿Q就决不会“断子绝孙”。《阿Q 正传》就是表现了辛亥时代中国社会以及民族基本矛盾如此鲜明深刻的历史图画!
第四,《阿Q正传》全面“展开了社会思想形态的战斗”。 这是邵荃麟对《阿Q正传》教育价值和社会价值等深层意义的揭示, 是至今仍有待我们深入研究的新课题。鲁迅创作《阿Q 正传》并不是只是“想把阿Q好好骂一顿”,而是要通过阿Q对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负面思想、观念、意识形态进行总批判。因此,我们翻开《阿Q 正传》第一章《序》就可以看到,作者以意含嘲讽的文字,表面上是叙述要为阿Q 作什么体式的传记以及为阿Q考定是什么姓氏、名号和籍贯之困难, 实际上是描准中国几千年来的种种腐朽思想意识左右开弓,几乎每一句话就是一支锐利无比的箭矢。例如第一段中的“从来不朽之笔,须传不朽之人,于是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究竟谁靠谁传,渐渐的不甚了然起来”,就是对整个封建传统权威和传统的思想观念的否定。第二段中的“传的名目很繁多”“而可惜都不合”,则是对“正名观念”和写作公式主义的批判。第三段写阿Q说自己“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赵太爷斥骂阿Q“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是对典型的家族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揭露。综观全篇批判到的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计有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历史观念上的尚古主义,人伦观念上的孝悌主义,血缘关系上的家族主义,人际关系上的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唯上主义、幸灾乐祸意识,男女关系上的礼教思想,自我感知上的自大主义,行为方式上的因循守旧主义和盲从主义,对待革命的投机主义,自己处于优势时的拳头主义(黩武主义),自己处于劣势时的自卑主义及和平主义,哲学思维上的机械主义,宗教思想上的宿命论观念和“轮回”意识,……总括起来说就是,《阿Q 正传》对中国形形色色的腐朽的社会思想形态都展开了战斗,褫其华衮,暴露尽了其可耻可笑的面目。
第五,《阿Q正传》是伟大的爱国主义作品。这是《阿Q正传》的最高思想价值。文学作品是作家精神劳动的产物,它必然渗透着作家的思想、观念和态度,寄托着他的人生理想。这就成为作品的思想价值。上面已经引述过的邵荃麟的“而在这中间,我们更看到鲁迅先生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爱”,就是指《阿Q 正传》具有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言的。对此,有些人可能不能理解甚至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鲁迅创作《阿Q正传》是以“暴露国民的弱点”为目的, 怎么谈得上是“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爱”呢?鲁迅对《阿Q 正传》里的人物不都是表现憎恶之极吗?我们认为,说鲁迅对阿Q 及其周围人物表现憎恶是确实的,然而鲁迅的出发点却是爱,特别是对于阿Q和其他劳动人民, 他因为爱之深而不觉恨之切,他是恨铁不成钢。鲁迅的“暴露国民的弱点”是根源于“对于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爱”。鲁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弃医从文就是企图运用文艺的武器达到唤醒国民的觉悟、改变国家民族积弱的目的。他分明知道说人家好话会得到感谢,说人家缺点的会令人厌恶,但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暴露国民的弱点”。这是表现了对于国家民族何等巨大的责任感和伟大的爱啊!在生活正常的年代,一个人听到别人说几句好话是不难的,但要听到别人出自真心的批评和规劝则真是难乎其难啊,除非是自己的父母、恩师和知友。然而即使恩师和知友,也往往只有你表示愿意接受的时候才指出你的缺点;唯有做父母亲的,不管儿女愿不愿意听、甚至于表示反感,都反反复复地指出你的缺点。鲁迅在《阿Q正传》里“暴露国民的弱点”、 抉发“中国社会以及民族的基本矛盾,并且藉此展开了社会思想形态的战斗”,这的的确确是“对于民族和人民伟大的爱”。70~80年代,苏联鲁迅研究专家索罗金也看到了《阿Q正传》这方面的伟大思想意义, 他正确地指出:鲁迅之所以把一个不幸的雇农作为主要的讽刺对象,是因为阿Q 的精神面貌是旧中国整个生活方式的产物。“鲁迅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帮助祖国的人民迅速地与一切阻碍前进的事物一刀两断,其中也包括群众心理上的消极因素。鲁迅的无情批判,其实正是他对人民所具有的一切优秀品质的热爱的表现,这是一种对丑恶的现实不可忍受的强烈追求的爱。”在《阿Q正传》中,“表现出鲁迅的革命爱国主义精神”〔4〕。
邵荃麟对于《阿Q正传》思想意义的论述,在40 年代具有空前的全面性和深刻性,直至90年代的今天仍能给研究者不少的启发。但可惜从它发表的时间(1942年)算起,整整五十多年过去了,几乎没有引起重视,这真是“历史的误会”。现在是我们应该充分认识这份文化遗产的宝贵价值的时候了!
本文于1995年6月2日收到。
注释:
〔1〕李何林:《文学理论常识讲话》(红专大学函授教材), 高教出版社1958年出版。
〔2〕〔3〕万书元:《〈阿Q正传〉与〈围城〉的意义》, 《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10期。
〔4〕转引自武生:《近十年的苏联鲁迅研究》, 《鲁迅研究年刊》,1984年。
标签:辛亥革命论文; 鲁迅论文; 阿q正传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邵荃麟论文; 阿q精神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革命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