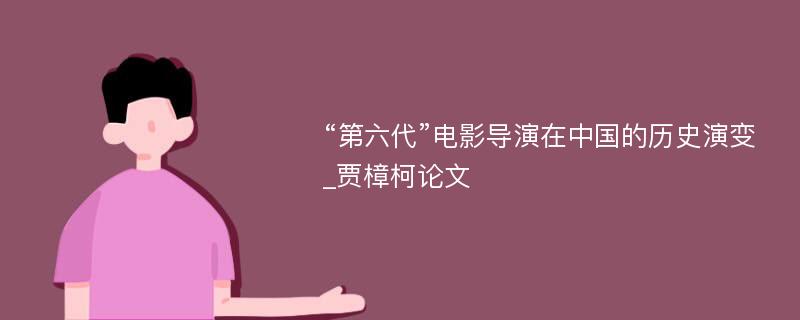
关于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历史演进的主体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电影导演论文,主体论文,第六代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论我们把张元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妈妈》(1990)视为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的开山之作,还是把“第六代”导演走出电影学院(1989)作为他们艺术之旅的起点,“第六代”在中国影坛上都已经行走了15年。回首这15年的中国电影史,“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尽管数量并不很多,但是其彰显的艺术个性与产生的广泛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目前,在整个中国电影历史格局中,“第六代”导演已经从边缘地带逐步走向中心地带;从过去的“地下”作者、体制外的“另类”,进入到电影的中心地带、主流电影的领域;从过去那种半地下的,非主流的生存状态,进入了主流电影的生产体制和电影的文化消费市场。对这样一个电影创作群体的总体性演变,显然到了进行历史描述的时刻。作为当代中国电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希望能够把对“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分析与对于他们本人创作理念的研究相互结合,能够把他们所处的文化语境的变迁与他们艺术创作旨趣的转向相互对照,从而为中国电影的历史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理论模式。我们不认为只有那些被岁月尘封的东西才叫历史,我们更不认为只有那些被时间隔绝的东西才有历史的价值。“第六代”电影,这样一种与中国的社会生活具有切近关联的影像叙事体系;“第六代”导演,这样一批与中国的普通大众具有同样现实感受的创作群体,在中国电影的艺术舞台上具有毋庸置疑的历史性。
我们反复强调:用“划代”的方法来描述电影的历史发展,评价不同时期的电影艺术风格,是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一个创举。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这种“划代”的前例。但与此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因为电影的历史,并不是根据数字的逻辑来发展的——它不可能一代接一代地往下排。在中国电影艺术的发展历程中,一部影片是否有价值在于电影自身的艺术力量,而并不在于影片的导演是属于哪一代人。从这种意义上说,“代”仅仅是一个划定不同导演群体的历史概念,而不能够上升成为一种判断电影艺术作品的价值标准。
“第六代”的美学宣言
在“第六代”电影导演的历史研究中,有一个现象特别值得注意,这就是:中国的“第六代”导演与第四代导演一样,都曾经提出过明确的美学宣言。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重要代表人物张暖忻,在1979年与李陀合写了《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① 一文。 文章指出:中国电影“必须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加速电影语言的更新与进步”,“创造出能体现我国民族独特风格的现代电影语言”。这篇文章被誉为“探索片的纲领”和“第四代导演的艺术宣言”,不仅在理论上引起人们对电影艺术自律的关注,而且翻开了新时期电影美学观念的新篇章。1993年《上海艺术家》杂志第4期上以北京电影学院85级导、摄、录、美、 文全体毕业生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一次中国电影的谈话》的论文。这篇2700多字的文章里, 他们直接把题旨锁定在第五代导演的奠基之作《黄土地》(1984)及其第五代电影对中国当代电影的影响上。
世界电影史上几乎所有的美学宣言都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当时处于霸主地位的电影。《黄土地》当时在中国电影美学界无疑处于一种霸主地位。“第五代电影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创作的一种标准。不论是膜拜、是模仿,乃至于后来的背离与抛弃,第五代电影都成为电影艺术创作无形中的一种美学参照系,一种创作标准。那种通过不完整构图和散文化叙事情节建构的影像世界作为一种‘不在场’的角色,一直占据着中国电影的历史舞台。”② 当时凡是谈到当代中国电影, 几乎言必称《黄土地》。所以对于一代立志迈进中国电影历史大门的新人,《黄土地》必然成为他们审视、反省直至颠覆的对象。所以,在这篇历史性的美学宣言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称《黄土地》即“不像一开始人们所反对的那样一无是处,也不像后来人们传说的那样神秘和伟大”。③ 他们甚至认为:“这个‘新浪潮’的运行方向也是偏颇的。”而且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即在《黄土地》之后,“中国电影进入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混沌时期。而且这个现象延续、甚至仍在左右着中国电影的发展。”④ 正像第四代导演的批判锋芒直接指向了电影的传统形式“戏剧性电影”, “第六代”导演的批判锋芒则指向了当时电影的流行样式“散文化电影”。他们强调当时的电影界对《黄土地》的美学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读“说《黄土地》真实再现了黄土地上人们的生活状态,倒不如说它把这种生活风格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黄土地》的追求成为之后中国电影的一种时尚,并在一种貌似深奥却是很幼稚的层次上进行效仿,这样也就完全阻断了《邻居》(1981)、《沙鸥》(1981)、《见习律师》(1982)的良好发展趋向。”⑤ 由于“电影制作界对于这种个人电影的追求,导致了一种以浮浅的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甚至精神分析解释自我作品的风尚,这使中国的电影导演们始终处在一种欠清醒的状态中。”⑥ 这些话的潜台词是:这样一个混沌的、盲目追逐风格化的电影时代应该结束了。虽然这篇美学檄文发表在1993年,但是它的写作时间和叙述背景是在1989年左右——即如文中所指的《黄土地》诞生的5年之后。
作为一篇全面审视中国电影的美学檄文,论者不仅对于中国电影的艺术创作,而且对于中国电影的理论批评——特别是对于当时把电影批评界搞得沸沸扬扬的“谢晋模式”的讨论,他们一针见血地提出:“所谓的‘谢晋模式’的讨论则成为对谢晋本人喜好、文化素养、思想背景的评判。显然,它把中国电影作为一种所谓的文化现象来理解,显然扩大了电影有限的社会功效,却再次离开了电影本身。”⑦ 对于中国电影的创作现状,他们认为在中国电影界“是观念领导创作,主义领导制作、读解领导作品”,表示出他们对理念驱动下的中国电影创作的鄙夷。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电影需要的,不仅仅是理论家、评论家,或者读解家”,不论就电影的美学样式、还是就电影的叙事形态,“中国电影需要的是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老老实实地拍‘老老实实的电影’。”⑧ ——这就是中国“第六代”电影人美学宣言的终极旨向。尽管这里并没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那样完整的艺术创作理念,没有新德国电影的《奥伯豪森宣言》那样尖锐的个性主张,也没有拉美第三电影的《光与火宣言》那样明确的文化爱国主义的激情,这篇美学宣言甚至也没有发表在当时电影理论的主流媒体上,而是发表在一个远离电影艺术理论研究与批评中心的、边缘化的地方杂志上,这个现象表明:整个“第六代”导演当时所处的那种没有话语权的文化境遇及没有市场空间的边缘化状态。直到今天,在我们一系列电影史研究的论文集中也没有这篇宣言的地位。但是,“第六代”的这篇宣言书式的电影理论文献,强烈地表现出中国新一代电影人立志改变中国电影历史版图的艺术热情与时代精神。他们在这篇关于中国电影的理论表述中对中国电影语言表现形式的分析,对中国电影创作态势的忧虑,对中国第五代电影的美学挑战,时至今日都没有被时间的流沙所掩盖,现在反而更显示出其不可取代的历史意义。作为一篇“富于理论觉醒意味并自我标示文化定位的文章”,⑨ 它已经成为我们寻觅这批电影人思想轨迹与艺术路径的一个重要历史文献。
“第六代”的历史身份
如果沿用代际划分的标准,我们所说的“第六代电影导演”,主要是指电影学院导演系85级和87级的一批青年导演。他们是路学长、王小帅、管虎、胡雪扬、王瑞、娄烨、张元(摄影系)等,后来相继汇入这个艺术群体的还包括章明、贾樟柯这样一批新生代导演。在许多关于这批导演的表述中,“第六代电影”、“新生代电影”、“地下电影”、“独立电影”往往是作为一种交叉概念来使用的,这并不仅仅是由于论述者对这批导演的历史身份不了解,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艺术创作的轨迹经历了一个从新生到成长、从“地下”到地上的历史,从边缘到中心的迁徙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在电影界的文化身份本身就具有多重的属性。由于我们还是在当代中国电影史的语境中讨论问题,所以,笔者在此依然确认“第六代”这样一种具有特定内容的概念来指称这批青年导演。
由于特定的历史境遇,“第六代”电影的作者往往是编剧、导演、制片人同时兼任,多种身份集于一身。从创作的角度来说,这种身兼多职的角色未必可取,不过从评判的角度上看,这反倒容易使人们更加全面地看到作者的艺术水准和创作能力。在整个中国电影历史格局中,“第六代”导演现在正从边缘地带逐步走向中心地带,从过去的地下作者、体制外的“另类”,进入到电影的中心地带、主流电影的领域。与过去那种半地下的、非主流的生存状态相比,“第六代”现在已经进入了主流的文化消费市场。其实《长大成人》(1997)在北京市场上达到了新生代电影的可人业绩,收入110万元;王瑞当年的《离婚了,就别再来找我》(1997)也取得了270万元的票房收入。包括张扬的《爱情麻辣烫》在北京的票房达到310万元,超过了同期的进口大片《花木兰》160万元和《玻璃樽》280万元的收入。⑩ 应当说,“第六代”所面对的问题,是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呈现的。他们所面临的历史语境是一种没有国家包产包销的传统体制的庇护,没有巨额资金的支撑,没有规范化的电影市场机制,所有这一切,是“第六代”导演群体必须直面的问题。现在,他们终于从生不逢时的阴影中走了出来,看到了充满希望的艳阳天。“第六代”导演对电影的创作正从个人的写作方式逐步转换到适应市场的大众化的写作方式。
“第六代”电影导演的影片之所以能够给予我们某种期待,是因为在电影的“被表述层面”上他们曾经给中国电影提供了新的表现题材;而在“表述层面”上他们曾经为中国的电影观众提供了新的艺术表现方法和新的视觉经验/心理体验。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管虎的《头发乱了》(1993)、娄烨的《苏州河》(1997)、李欣的《谈情说爱》(1996)、王瑞的《冲天飞豹》(1999)、王小帅的《青红》(2005)、包括王全安的《月蚀》(1999)、阿年的《呼我》(2000)都给了我们这种感受。他们的电影语言形态、电影兴趣点与我们过去看到的电影有所不同。他们也许觉得一个报仇未果反而使自己惊吓不已的情景比一个把强大的对手打倒在地的情景更有意思(《长大成人》);他们也许觉得一个不完整的、充满着个人感受的作品比一个完整的但缺少了个性特征的主流电影更有意思(《月蚀》);他们也许认为一个有缺陷的英雄比那种十全十美的人物更真实(《冲天飞豹》);他们也许觉得一段出现在画外的电视新闻节目比一段现场的纪实报道更有历史感(《呼我》)。与第五代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历史英雄,而时常是一种人格英雄。这些影片中的人物不肩负更多的社会使命和历史责任,但是在影片情节当中,他们依然遇到人在精神上、成长中所面对的种种抉择。《月蚀》里的出租车司机为了一个不期而遇的女子挺身而出;《长大成人》中的主人公冲进饭馆与疑犯拼命;《非常夏日》(2000)中搭车的过客也要与罪犯一争高下。当他面对凶恶的罪犯高声喊道“你可以杀死我,但不能吓死我!”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部影片所定位的英雄是一种人格英雄——他是以人格的缺陷作为叙事的起点,而以人格的成熟与完善作为叙事的最终点。在电影美学的意义上讲,与传统主流样式的影片相比,他们的主流影片表层形态上更逼近现实的原生形态,表演趋于平实、自然,接近生活的原始状态,戏剧性的痕迹更为稀少,更符合电影本身的美学规范,更接近观众对电影与生活保持“似真性”的审美要求。
“第六代”导演的许多影片在表层形态上都力图呈现出一种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原在感受”。普遍采用同期录音保持现实空间的环境真实;通过大量的移动摄影建立观众与剧中人物相同一的视觉心理感受;与此同时电影开始自觉地淡化演员的戏剧化表演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剧中人物自身的职业特点,给观众造成一种“目击现实”的心理感受。进而改变了电影仅仅供人娱乐、解闷的游戏性质,在弥漫着商业气味与低级娱乐的电影市场上,重新树立起中国电影透视社会现实、展现历史变化的美学旗帜。
“第六代”的历史转向
“第六代”电影,长期以来被命名为中国的“地下电影”,即一个在主流的电影制作、发行、放映体制之外的电影。这也许是“第六代”的电影因为题材涉及到社会的“阴暗面”及其“灰色地带”曾经被禁映;其次,是因为他们在参加国际电影节的运作程序上“违规操作”,有悖当时的电影政策。不管怎样,“第六代”电影导演的生存境遇与第五代那种国家计划经济的制片体制具有巨大差别,致使他们的生存策略也不可能完全一样。作为与“第六代”的成长历程平行移动的中国电影体制的改革,与“第六代”电影导演曾经有过三次重要的对话。这三次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在我们研究“第六代”电影的演变历史中应当给予必要的关注。
第一次,是1999年,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集团和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主办、《电影艺术》编辑部承办的“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作为此次研讨会的参加者,笔者体会到了那种被称为“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决策高层与独具文化棱角的新锐一代之间的双边互求、默然契合”的会议气氛。时值中国即将加入WTO, 对年轻导演群落来说,可谓幸运与挑战共存,希望与危机并生。诚如这次研讨会主办者在“会义宗旨”里所指出的:“尽管他们的作品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股年轻的创作力量,势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电影发展的主力军。关注他们的成长,鼓励他们的创作,研究和探讨青年电影的艺术现状,是十分适时、必要和有意义的事。”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赵实代表中国电影决策高层而作“开幕式”讲话指出:青年电影的创作,既代表着中国电影的未来和希望,同时,也体现了当前现实的需要,应给予切实、热情的扶持。时任北影厂厂长的韩三平则表示,在2000年将拨出资金,每部影片以200万元人民币为限,支持年轻导演拍摄20部左右的新作(当时中国电影的投资生死线被确认为是200万元)。 参加北京“青年电影作品研讨会”的导演包括路学长、王小帅、管虎、王瑞、毛小睿、吴天戈、李虹、阿年、田曦、王全安、霍建起、张扬、金琛。在这个阵容内除了“第六代”导演之外,还包括了许多来自于其他非电影学院毕业的新锐导演。“第六代”电影导演在被主流电影的体制接纳的同时,已经被集体改写为新生代导演。研讨会期间放映了新作12部。这些影片不仅在题材、风格、样式上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而且标志着此时的“第六代”导演已经“从早期偏于暗色的边缘化、个人化空间走出,显示了他们在主流与边缘之间的从容游移,在文化的前卫性与大众性之间寻觅某种富于弹性张力的可贵努力。”(11)
第二次,是2003年,11月13日,电影局在北京电影学院举行的座谈会。“11·13座谈会”曾经被认为是一次可以称为“改变中国电影方向的里程碑”的会议。这不仅仅是因为在这次会议上电影局向青年导演宣布了电影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性文件,而且这种面对面的交流,“由对抗到对话的转变是我国电影机制进步的表现”。在这次会议上宣读了广电总局第18号、19号、20号令。其中18号令《电影剧本(梗概)立项、电影片审查暂行规定》中第四条明确提到,影片摄制单位在申报电影立项时,只需向广电总局提交不少于1000字的电影剧情梗概、片名、片种、影片题材等材料,无需再提交完整剧本(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与合拍影片除外)。在第十一条中还提到,受广电总局委托的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应当成立电影审查机构,按照《电影管理条例》有关内容及技术质量审查标准负责电影审查工作。这意味着广电总局将终审权部分下放。这次会议之所以一直未能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公之于众,主要是因为在会议之初,“第六代”的与会者不希望让媒体进行“有倾向性的报道”,进而对现场的记者进行了干预。为了让电影局的领导“在最单纯的形式下”了解自己的意见。张献民代表“第六代”电影人宣读了他们预先准备的提纲。(12)
这个提纲提出的某些问题其实在当时“第六代”导演与电影局就具有共识。其中敏感问题主要是用电影分级制取代电影审查制和以往因违规操作而被“禁映”的影片能否公映的问题。座谈会是在电影学院的会议室进行的,参加会议的人有电影局、电影学院的领导、独立电影制作人、电影学院师生四个部分,一共100多人。“第六代”中的贾樟柯、王小帅、娄烨、张献民还有刘建斌、乌迪、何建军、章明、王超、李玉、耐安、吕乐都参加了会议。会议是从下午2点40分开始到下午5点左右结束。
第三次会议,是2005年12月9日至12日,由电影局、北京电影学院、中国影协、电影导演协会等主办、在北京电影学院召开的“青年电影创作座谈会”。会议期间放映王小帅、贾樟柯、方刚亮、曹保平等青年导演的影片。另外还就“拍什么”、“怎么拍”等话题进行讨论。召开此次会议的现实背景是:2005年我国电影产量达到创纪录的260部,2004到2005年期间45岁以下的青年导演作品达到75部, 超过这两年电影总产量的20%。青年导演的作用越来越凸现。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在会议上指出:“创造力决定了电影艺术的生命力”,希望年轻人尊重人民大众的要求,理解电影产业发展的要求,拍出既有艺术价值又能开拓市场的好电影。(13) 年轻导演对电影产业化起到的促进作用受到电影管理层面的高度关注。至此,作为群体的艺术创作力量,“第六代”电影导演基本上告别了他们的“独立时代”,而逐渐地被纳入到主流电影的运作体系之中。与通常的电影艺术创作会议不同的是:这次会议在象征的意义上还是一次“第六代”电影导演与“地下电影”的集体告别仪式,它标志着“第六代”已经离开了“地下电影”的历史路线图。
“第六代”的个人故事
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中其实一直贯穿着不同版本的“长大成人”的故事。电影,成为见证一代人精神成长的历史本文。这些与人生本文相互重叠的历史故事,是“第六代”导演的精神自传。电影对于他们来说不再为一代人代言,而是从个人体验出发,通过个体的生命经历和情感遭遇折射的自我心态。“第六代”导演的一系列电影作品路学长的《长大成人》、张元的《北京杂种》(1993)、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1993)、《青红》,娄烨的《周末情人》(1993)、贾樟柯的《站台》(2000),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管虎的《头发乱了》等作品都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他们描述了动荡不安、迷离困惑的边缘地带的年轻人的日常生活。包括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1995)、花清的《楠溪江》(2003),这一系列作品中对个人生活的历史性书写,已经成为纪录一个时代的人性记忆。从电影艺术的表现题材上看,如果我们将谢晋电影对过去时代的历史表述称之为“社会现实主义”,那么,我们则可以把“第六代”导演对过去时代的历史表述称之为“个人现实主义”。同样都是来自于对历史的真切感悟,“第六代”选择了一种更直接的个人化的表述方式。
在对当代都市生活的影像叙述中,“第六代”导演的电影中程度不同地分布着摇滚乐、街头暴力等都市的文化编码。在《北京杂种》、《头发乱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我们都看到昏暗、破旧的建筑充斥着画面,城市的悲凉感弥漫在一群喜欢喝酒、打架的年轻人周边,现实生活中的失落、自我的孤独感透出了青春的焦躁、无可皈依的城市的异己性、陌生感。影片中的主人公们以他们的逃避行为建立了一种对主流文化的对立关系。与第五代那种对历史、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挥写相比,“第六代”导演更关注作为个体的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的影片在题材上就具有一种“原创性”。《长大成人》里的高中生、《月蚀》中的歌厅小姐、《呼我》中送花的青年和卖血的青年,这些主人公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他们所处的那种特定的生存境遇正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普遍性。因为在未来中国的社会生活中,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国家对个人所承担的经济责任会越来越少,换句话说,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独立处理生存问题的责任会越来越多,诸如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等问题。总而言之,个体意义上的人群也会不断增多。为此,人的社会认同和身份归属会从原来的国家意义上分化出来,在现实生活中更多是通过自我的劳动和成果实现来完成“自我价值的确认”。在这种身份归属和社会认同转移、变化的历史期间,个体意义上的人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不仅仅是指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所谓的个体户,在目前的中国社会中,个体的劳动者还包括着不同阶层内的各种人——他们当中包括个体文艺工作者、商人、作家、独立撰稿人、自由职业者等等,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虽然不尽一致,但是他们的生存处境却是一致的,那就是他们都是在国有机构(企业、机关、事业单位)之外谋生。他们现实处境的一致性决定了他们在心态上的一致性,进而决定了以个体的人为主人公的电影作品必然有它潜在的“心理市场”。为此,关注人的个体的生存状态,并把这类题材的作品升华到对人的普遍存在意义的探究以及对人的整个精神世界的写照,那么这类作品无疑会获得更为广泛的社会反响。
低成本是中国电影目前所采取的一种普遍的谋生图存的“商业策略”,但是不能把它上升为一种电影艺术创作的普遍规律无边推广。中国电影近几年的商业胜利已经说明了这个事实。中国的“第六代”导演现在面临着如何把个人的审美趣味、电影的艺术观念与观众的需求、电影的商业市场相互“接轨”的问题。他们应当把一个人、一批人、一代人的文化视野升华到中国乃至国际所认可的精神领域,进而征服市场,赢得观众。中国的“第六代”导演在电影市场化的历史进军中,应当产生出在商业、类型影片中的高手。在这一代人当中应当出现恐怖、灾难、武侠、科幻、惊险、间谍、言情及各种类型影片的巨匠;应当诞生一代谙熟电影艺术规律、通晓市场运作的行家里手。这既是中国电影产业化时代的需要,也是历史对“第六代”导演所寄予的期望。
“第六代”的现实转型
中国“第六代”电影导演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开始出现明显的创作转向。这种转向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他们越来越关注他们面对的现实生活,特别是由于整个社会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所产生的历史巨变,对于他们的心灵产生了强大的震撼。管虎导演的电视电影《上车,走吧》(2000),看似是一个平民百姓的日常故事,他借助于每天来往于北京街头的面包车,把个体司机的生活与普通市民的生活平行剪辑。实际上作品却涉及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种种矛盾,包括人们内心世界激起的情感的波澜,这个在叙述的表层形态上具有很强的纪实性而在叙事的深度模式上具有很强的故事性的作品,创造了电视电影极高的收视率。路学长导演的《卡拉是条狗》(2003)在叙事的表层形态上依然延续了“第六代”电影中那种纪录式的真实感觉,而在创作的方法上开始把导演自己变成了一个站在摄影机背后观察、描述生活的叙事者,而不再是一个在摄影机面前自我表演的剧中的角色。作为一个生长在北京的人,路学长对北京市井生活具有亲身的体验,但是他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把追求所谓“京味儿”风格视为其艺术创作的主旨。他把自己对北京这座古老都市生活的体验,变成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真切描述。《卡拉是条狗》由于葛优的出演标志着“第六代”电影对电影市场观念的认同和向电影观众接受取向的靠拢。
在“第六代”的集体转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贾樟柯。“我的摄影机不撒谎”一度成为他的电影进入市场的文化标志,也成为他进入国际电影节的“通行证”。为此,贾樟柯另类的“县城影像”成为中国电影历史中不能忽略的一种叙事本文;甚至被一代电影的追梦者奉为圭臬的标志性作品。现在应当引人注意的是:在贾樟柯为他心目中的电影艺术东奔西跑的90年代初,其实正是中国电影开始逐渐倒向市场化、商业化的年代——贾樟柯却在一条与之完全相反的方向上义无反顾地奔跑。并且在极度窘迫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电影处女作《小山回家》。后来,他的电影感动了日本的北野武,他开始不断地为贾樟柯电影提供了投资支撑,从而使贾樟柯完成他的一系列个人化的“县城影像”。贾樟柯导演的《世界》(2004)被认为是他进入主流电影的标志性作品。他在《世界》里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日夜不分、季节不明的平面化的生活。他把这种时间的感觉建构在世界公园这样一个虚拟的、假造的空间景观上。他的文化想象在这个没有真正时间流程和空间变化的叙事体中还原出一种对人的自我精神状态的映现。只是他对普通人现实生活的直面书写,从过去的山西县城转变为现在的首都北京。如果这种空间的变化就是他转型的唯一标志的话,那么,贾樟柯的转型可能就仅仅是一个叙事题材的变化。因为贾樟柯电影的叙事主旨并没有因为一个叙事空间的改变而全部改变。一位韩国女记者曾经发现了一个连贾樟柯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就是在贾樟柯的电影里几乎所有的女主角,到电影结尾都不知去向了。她们都没有归宿,不知道去哪儿。这也许就是一个电影导演无法摆脱的历史宿命——无论是拍一种自传体的电影,还是在拍一种主流电影,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他内在的精神选择。
张元曾经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他90年代导演的影片《妈妈》(1991)、《北京杂种》、《儿子》(1996)、《东宫西宫》(1996)都是非主流电影的代表作。直到他拍摄了由一线明星赵薇和姜文主演的影片《绿茶》,其影片中迎合市场及大众趣味的商业旨向便浮现出来。尽管两位当红明星的出演为影片增加了必要的娱乐因素,使张元的转向更加受到电影公众的关注。可是,赵薇同时扮演的两个文化身份截然不同的角色,使观众的认同指向很难集中在一个方向,这种“意念大于感觉”的创作倾向表现出“第六代”导演转向过程中对观众的心理机制还没有明确的认知。此后的《看上去很美丽》(2006)对于儿童心理的透视力度远远超过了作者对一个时代的个人情感记录。尽管影像的制作指数在张元的电影创作中始终居于较高的水准,可是在电影市场上,这种专业品格的提升如果不能与电影观众的心理认同相互“缝合”,那么对这种专业指数的投资成本怎样回收就是一个难于解决的现实问题。
中国电影的“无代年华”
对于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标准率先提出质疑的是“第六代”。 在他们发表于1993年那篇美学宣言中指出:作为评论界的一次壮举,“代迹划分,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划分、风格划分,而当时中国电影的状态根本无法承担这样的重任。”这意味着在当时中国电影创作界,并没有在美学上提供一系列不同代际特征的经典作品。而且“代际划分无形之中把当时的中国电影制作界分为几个明显的年龄组,形成以年龄和作品为标准的制作集团,任何一部作品,任何一位导演,在他为人所知的同时,就已被分配到这样的集团中去,这已成为当时的习惯做法。于是这些集团之外的人,就会被忽视,或永远为之争论不休。”现在,中国几代电影导演的艺术创作轨迹在近几年来越来越呈现出分道扬镳的态势,本来就充满歧义的“代际划分”更无法用来描述电影创作的真实状态。第五代已经成为一种电影市场上的商业标签,一种争取市场的营销策略被广泛使用。它过去原本就并不清晰的美学涵义,在这种商业化的历史语境中与资本运作沆瀣一气,以此命名的影片真正能够兑现的商业价值又有多少更是难于断定。
“第六代”导演对电影的创作正从个人的写作方式逐步转换到适应市场的大众化的写作方式。他们的艺术创作的范围从单一的都市的、自传体的题材变成现实的、历史的、社会的表现题材。已经彻底放弃了早期作品中那种依靠个人叙事建构影像系统、不考虑市场、不考虑买方的电影观念。特别是对电影市场的关注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市场,并逐渐融入主流电影的创作队伍之中。目前进入电影导演行列的不再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毕业生。一批中国第一流的摄影师跨入导演的行列:顾长卫的《孔雀》(2005)、侯咏的《茉莉花开》(2004)、吕乐的《美人草》(2004)、花清的《楠溪江》,他们不仅为中国电影注入了一种新的视觉图景,而且带来了一种新的叙事形态。从文学编剧进入导演序列中的陆川以编剧和导演的双重身份标定了自己在电影创作的中心地位。演员出身的徐静蕾同时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2004)中担当编剧、导演、主演三个核心角色。导演身份的多元化,彻底改变了中国电影的“代际属性”。加之不同电影导演代与代之间的区别越来越趋于明显,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差异也日益凸现。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沿用代际的“说法”可能会消除了本来就不尽一致的电影导演艺术个性。有鉴于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电影目前已经进入了她的“无代年华”。“第六代”导演,作为一个电影的群体,他们电影总体性的美学边界正越来越淡出历史的地平线。
注释:
① 张暖忻、李陀《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
② 贾磊磊《时光的流转与影像记忆——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方法与评价体系》,《中国艺术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99页。
③④⑤⑥⑦⑧ 北京电影学院85级导、摄、录、美、文全体毕业生《中国电影的后“黄土地”现象——关于一次中国电影的谈话》,《上海艺术家》,1993年第4期。
⑨ 黄式宪《“第六代”被“命名”》,《电影评介》2000年第3期。
⑩ 贾磊磊《市场神话的破灭与新生代的来临》,见《中国广播影视》2003年第2期。
(11) 黄式宪《新生代的文化定位及其它》,《电影评介》2000年第3期。
(12) 《独立电影七君子联名上书电影局》, 《南方都市报》转引自http://www.grassy.org/view/CNContent.asp?CultureNewsID=21310.
(13) 杨林《“青年电影创作座谈会”在北电开幕》,《新京报》2005年12月10日。
标签:贾樟柯论文; 黄土地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电影导演论文; 第六代导演论文; 艺术论文; 电影市场论文; 长大成人论文; 头发乱了论文; 月蚀论文; 剧情片论文; 中国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