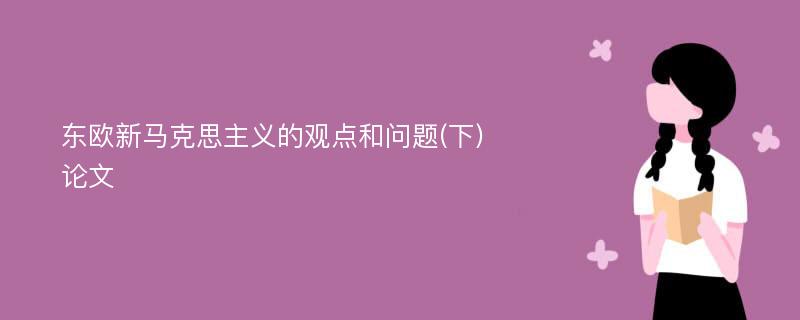
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问题(下)
[冰岛]约翰·P·安纳森(Johann P. Arnason)① 杜 红 艳,梁 雪 玉 译
(黑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哈尔滨 150086)
[摘 要] 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在苏共二十大后东欧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历史背景中产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改革的共产主义对捷克的内部反对派具有的影响较大 ,特别是布拉格之春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揭开了捷克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潮的序幕,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就是代表性作品,这本书对于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科西克理论自身的摇摆不定使这些影响被遮蔽了,锡克和乌尔也参与到了这种讨论中,他们对官僚制进行了批判,但官僚统治不足以解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问题。东德的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薄弱,且表现出了较为正统的特性,比较有特色的理论家是巴罗,巴罗的《东欧的抉择》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一种重新调整,属于一种新列宁主义。与巴罗完全不同,匈牙利的康拉德和塞勒尼批判了巴罗的观点,属于倒置的列宁主义,但康拉德和塞勒尼的观点过于乐观。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学派立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阐释,属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延伸,赫格居什更接近改革的共产主义,他对官僚制进行了批判,但是将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失败归为国家环境避开了改革的内部的结构性障碍问题;本斯和吉什更看重对东欧社会进行阶级分析,但他们对马克思的一些解释具有误导性;赫勒、费赫尔、马尔库什从微观层面分析了对需要的专政,这种讨论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东欧问题的最有前景的起点。
[关键词] 东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东德的新马克思主义;布达佩斯学派
五、布拉格之春的知识背景
1.对改革的共产主义现象的分析应该从短时段的历史形势(historical conjuncture)着手,而不是从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纲领出发。这一思潮始于改革者试图进一步超过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诊断及其所提出的对策,与此同时,也利用了赫鲁晓夫政策开启的自由空间。在某种程度上,改革的共产主义成功了,它创造了一场更广泛、更深刻的民主化运动。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一种过渡时期的现象。但是鉴于苏联内部的整体状况,这一胜利必定是微弱且短命的。它作为一种非主流的思潮,似乎无处不在,但仅仅有两次在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匈牙利的情况在这方面是反常的:首先,改革的共产主义的突破(纳吉政府,1953—1955年)发生在苏共二十大之前,且由于其孤立性似乎从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第二次机会在1956年到来,这次改革的共产主义派别的临时领导权只是一场失控的革命爆发的副产品。与早熟的、早产的匈牙利变体的毁灭不同,改革的共产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成熟较慢,根基更加坚实,并且为渐进的激进转化作了更好的准备。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的共产主义虽然产生于对苏共二十大较为滞后的反应,但是从1963年起获得迅速的发展[注] 停滞的斯大林主义政权直到1968年的普遍形象是十分具有误导性的。事实上,在斯大林去世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阶层的政策经历了很多转变。在第一阶段,捷克斯洛伐克的斯大林主义证明比其他地方更有复原能力(因此,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唯一在1953年后将50年代早期在东欧同时发生的肃反运动继续下去的东欧国家)。在苏共二十大和成功地镇压第一次“修正主义”之后,倡议保守主义为“前进运动”让路,其最惊人的表现是在1960年宪法中宣布社会主义的建设已经完成。坚决拒绝重新公开政治审判的问题是同一种态度的另一个表现。这个策略在苏共二十大和经济危机的共同影响下于1962—1963年瓦解。从1963年开始,诺沃提尼(Novotny)领导阶层采取了一种全新的政策,给予初期改革运动许多特权。 ;1968年这一运动的胜利对于基层运动来说是启动信号,这种基层运动既获得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也蔓延到了其他群众当中去。鉴于此,捷克斯洛伐克模式是改革的共产主义唯一成熟的模式。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这种模式也造成了在改革的共产主义理念和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性分析之间广泛的相互渗透。20世纪60年代期间处于成长中的改革运动吸引了不同学派和学科的知识分子,有时——尽管这一点这里不能被具体验证——还要以牺牲更具破坏性的主题为代价。甚至在苏军入侵之后,改革的共产主义的遗产也继续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内部反对派的思考,这种影响在程度上明显高于东欧的其他地区。
提出了基于磁开关的近方波LC-Marx发生器技术路线,该路线的主要优势在于结构简单,实现了所有开关的固态化,免去了专门的触发系统,基于同一套磁芯控制系统以保证各级导通放电的同步性。发生器基于多倍频电压脉冲叠加的原理,实现了近似方波脉冲的输出。设计了具备10 GW方波脉冲输出能力的Marx发生器电路结构。结果表明,输出脉冲能够满足要求。下一步工作主要是完善所提出的近似方波脉冲Marx发生器的理论分析,进行结构设计与场分布模拟研究,为实际装置的构建奠定基础。
正如事件所展示的那样,改革的纲领总是与苏联领导阶层的既得利益不相容。但是改革者的战略失误往往与他们整个意识形态前提相关。鉴于改革的共产主义运动的自发性和多面性,可能不能形成理论上的基本共识,但这两个无争议的动机,对斯大林主义的反叛和民主的重新发掘,仍然有充足理由产生一种共同话语。大家经常性使用和普遍接受的对斯大林主义及其造成的后果的描述是一种“畸形的社会主义”。不需要反思性的智慧就可以发现这个概念的致命缺陷,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这种反思性智慧进一步超过了官方对“个人崇拜”的斥责。当然,这种畸形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和解读。一方面,一些政论作家形成了批判官僚制的思想,并且提出了缅怀托洛茨基传统上反官僚制的改革的理想蓝图。[注]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罗伯特·卡利沃达(Robert Kalivoda)在《文学作品》中的文章(Literarni Listy in April and May 1968.Literarni listy)。 另一方面,更具典型性的党派内部的改良主义著作拒绝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制度,这种制度在革命之后一段时期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已经超过了其有存在理由(raison d’etre)的时期。
虽然出于策略上的考量,在言语上变得温和,但是“社会主义阵营”里对先锋作用的愿望还是清楚无误的。由于更加先进的前革命发展水平和更加民主的传统,因此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的民主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似乎更易实现。雄心勃勃的情绪使得改革者甚至反对“欧洲的社会主义模式”,转而将西方文明的珍贵遗产与斯大林主义亚细亚基础融合在一起。鉴于之后的经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的独特路径表明了一种不同的解读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新兴苏维埃阵营中捷克斯洛伐克是唯一一个共产党在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都得到大量支持的国家。这就使得权力的征服更加容易,并且革命后的政权更不易受攻击,但是,伴随着危机的加深,国内斯大林主义的原初有利条件变成了激进改革的驱动力。在1969后,胡萨克(Husak)政权追求的“规范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使改革运动背后的社会力量分裂和麻痹,并借此去消除复归的威胁。此外,回顾过去,于1968年显现自身的更新潜力似乎暂时性地阻碍了捷克斯洛伐克进一步的苏维埃化,而不是建立推动整个集团走向更深层发展的模式。
2. 在第一部分,我简要描述了意识形态的三个概念,它们可以作为更精细的改革战略的出发点。与此同时,与那时西方人对科学技术革命的广泛看法不同,“科技革命理论”能够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的这一想法是不适用的。[注] 参见吉多·内里(Guido Neri)的瑞奇特讨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变化”(Variazioni ideologiche del socialismo realizzato, inAut Aut,no.145-146,1977)。 正如拉多万·里奇塔(Radovan Richta)研究所发现的,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具有表面相似性,但是它增加了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中的技术元素,使其与一种连续不断的政党盲目崇拜相一致。
现在有很多银行都推出了一些“儿童账户”,得到了不少家长的欢迎。但是很多人的做法仅仅是用子女的名字开设一个账户而已,存款、取款的业务则都是家长包揽。其实,家长们不妨带上自己的孩子亲自办理一些基础的银行业务,告诉他们为什么要把钱存在银行里,不同年限的存款利率为什么会不同,如何填写存单和取款单,怎样给外地的爷爷奶奶汇款,等等。
政党将变为“科技革命的指导力量和组织者”,政党的领导作用将通过“监管机构的监管”得到发挥。科西克对这种理论的批判是贴切的:他谴责这种理论故弄玄虚,目的在于缩小必然转变的文化和政治方面,并忽视当代科技变化的矛盾特性。
教学实验室主要面向本科生,用于本科实验教学。学生通过实验课对所学课程进行感性认识和动手能力培训,该类实验室的特点是量大面广,人员流动性大。随着各学院组建集中的本科实验教学中心,形成了教辅人员准备实验、教师讲授实验、学生操作实验的格局,这种“管教学”分立的方式,优点在于分工明确,不足是三者之间的交流有时脱节,出现管理空档。同时学生实验课门数多,每门课的课时紧张,因此安全环保教育往往被忽视,也未施行准入制度,易出现操作不当引起的安全隐患、乱丢乱倒有毒有害物质。
我低着头回答:“好的。”心里却在想:完了完了,刚刚老师弹的时候我全没听,回家怎么练呢?真烦人!我只想回家后跟妈妈商量,能不能不学钢琴了。下课后,我和妈妈一起回家了。
另一方面,社会的再政治化引发了新的限制和问题。尤其是,新的统治制度需要拥有与前任一样多或更多的合法性。这里,苏联及其东欧附属国之间的差异尤其明显。在东欧,合法性——在要么全部接受,要么至少是缺乏明显的替代选择的意义上——由于明显的原因更难获得,且它甚至可能表达出一种长期的合法性危机。在苏联,现存的秩序已经具备了合法性,但是已经证明更难以使一种明确的合法性模式稳定。统治机构部分求助于更早的合法模式,部分试验一些新的模式,例如通过实质性的合理性而达到合法性。
在不那么官方的讨论之中,出现了相互分化的两条主要的路线。[注] 这些讨论,参见H. Gordon Skilling, Czechoslovakia’s Interrupted Revolution, Princeton 1976, and V. V. Kusin, Political Grouping in the Czechoslovak Reform Movement, London 1972。对于改良共产主义系谱外的观点参见Ivan Svitak, The Czechoslovak Experiment, New York 1971。 一些讨论者将“渐进主义者”与那些认为只有立即无条件接受多元化原则才能确保运动的长远胜利的人区分开来,大家讨论最多的问题是政治反对派的机构化。在5月和6月的观点发生了令人振奋的转变之后,这一问题在侵略之前的几个月被一些更紧迫的问题所遮蔽。虽然很多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并不认为1968年的情况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但是也没有理由去怀疑这一点,即许多改革的共产主义者将多党制度的采用看作民主化进程的逻辑结果。另外一些不同的方式虽然发展得更加缓慢,但是一些替代性选择在侵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旧是讨论的话题。对于一些改革计划的批判者来说,对其矛盾的补救措施应该在直接民主的混合物中寻找,而非在完全符合议会民主原则的理论中去寻找。从更加实际的角度来说,首先这意味着对自治的需要。在不确定的开端之后,这种关于“民主管理机构”的构想迅速发展,并且当“劳动人民委员会”(不要与狭隘意义上的工人委员会相混淆)引起人们的注意时,先前在民主和技术构想上的潜在冲突变得尤为严峻。在入侵和1969年4月全面正常化开始的7个月里,试图去保卫委员会是最重要的抵抗行为。回顾过去,这或许可以被视为战略上的先锋号,它之后在波兰被成功地应用:将改革的努力建立在党外社会运动之上。但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改革运动已经处于防御状态,像波兰一样的状况只能成为一种美好的愿景,要知道,它的境况对于这样一次重整来说实在是太脆弱了。
关于自治的讨论也涉及改良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三个支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和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经济改革。这些改革措施被讨论且在某种程度上在其他国家进行了实施,但是只有在捷克斯洛伐克,这个问题与普遍理性和政治复兴相关(在匈牙利,经济改革比东欧其他国家发展得更为深入,但是1956年革命的失败和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没落造就了经济改革所面对的社会背景;在波兰,经济改革方面的提议变得日益学术化并且失去了对60年代哥穆尔卡政策的兴趣)。虽然改革的具体历史在这里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关注,但是这种试图解释商品生产的幸存并且证明在计划和市场之间有一种更为平衡的联系的努力,触及了主要的理论问题。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者来说,在据称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已经被经验所证实,为了避免进一步犯错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解释。一方面,他们分析的局限性是因为他们认为经济结构的核心是不完整的且部分被破坏的社会主义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新的计划体制将把市场机制体现为调节工具。换句话说:“现实的社会主义”中市场关系的角色和作用要么被其结构背景的意识形态解读所掩盖,要么被其未来角色的实用主义色彩所简化。这一讨论的更深层次的缺陷在于它未能承担起对马克思的价值和资本理论进行一种系统化重构的任务。[注] 这是整个东欧反对派的特征,且不仅是由于官方禁忌。主要未公开发表的例外是马尔库什、本斯和吉什在《批判的经济学可能吗?》(Is Critical Economy Possible ?)中的论述,这本书以匈牙利语出版,因此当代的作者很难理解。然而,在这些局限性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学家阐明了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理论[注] 这个主题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最具权威的著作是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中的计划和市场》(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 Prague 1967),捷克版本于一年后出版。196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流亡者继续讨论这些问题,尤其是Kiri Kosta, Sozialistische Plan wirtschaft, Opladen 1975, and Radoslav Selucky, Marxism, Socialism, Freedom,New York 1979。。正如他们所见,现象源于技术和社会的两方面因素;虽然需要强调很多变量,但是凸现出来的最重要的因素分别为:生产力的不完全社会化(技术发展水平和超越更直接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国家所有制的盛行都限制了生产力)、工作的角色(仍然远没有成为一种基本的需要或自我实现的媒介),而且也很重要的是,持续存在的匮乏环境。
随着社会对结构张力和利益冲突的关注,这种由经济改革与其他方面的改革所预设和传播的社会形象揭开了20世纪60年代各种思潮的序幕。随着运动步伐的加快和危机的社会—政治维度被大家所公认,狭隘的经济理性化倾向失去其威信。当入侵终止了新路线的步伐时,重新定义经济改革仍旧是要讨论的话题。
3. 卡莱尔·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或许它是战后东欧出现的最具有影响力的哲学著作,前面我们已经简要地将其与研究相同问题的其他构想进行了比较(参见本文第二部分)。对于这部著作在捷克斯洛伐克语境下所起的作用应该再说几句。与当时知识界发表的著作取得的即时的巨大的成功所显示的东西相比,这本书的成功不那么直截了当。虽然在改革运动的背景材料和文字语言中都留有关于这本书的记录,但是人们仅仅是部分地认识到了它的理论潜力。科西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基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对后来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产生了影响,但是由于其他人对这些思考的单方面接受和他自身研究的连续变化,这些影响被掩盖了。
王屋镇古树名木资源较为丰富,有15种,分别是国槐、皂荚、黄连木、侧柏、龙柏、栓皮栎、橿子栎、白皮松、大叶朴、核桃、红豆杉、槲栎、七叶树、桑树、银杏,其中国槐所占比例35.1%,皂荚所占比例为17.0%,黄连木所占比例为13.8%,侧柏所占比例为12.7%,龙柏所占比例为6.3%,这5个树种共80株,所占古树名木比例达84.9%,为王屋镇的优势树种。
科西克最初的分析于1956—1958年间出版。在许多文章中,他支持一种非教条主义的且政治上坚定的哲学,直接指涉社会主义的批判性的自我审查。与此同时,他强调需要一种非辩解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且这种经济学与传统的经济决定论完全不同。在《具体的辩证法》一书中,科西克采取一种更独立的视角看待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但是大家普遍认为这本书的概念框架只是他早期的、更具尝试性的论题的一部分。这本书的积极内容离不开两方面的辩论:既反对苏联马克思主义,也反对波兰盛行的那种修正主义。科西克想要围绕“人是谁?”这一问题重新确定唯物主义哲学的核心,但是他既反对沙夫的残存的人类学理论,也不赞成科拉科夫斯基的极端人本主义学说。“人的本体论”学说要与劳动哲学联系在一起,并且通过劳动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联系在一起;更概括地说,这种学说将自身从各种以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分离出来,人没有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动物性或社会性中,因为他不是一个人类学的存在。相反,他以其实践为基础,把自己暴露在对存在的理解面前。因此,他是一个人类宇宙的存在。人们已经发现,实践是真正能动的中心的基础,是精神与文化、文化与自然、人与宇宙、理论与行动、实存者与实存、认识论与本体论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历史性中介。
对劳动概念的重新解读,直接反对自然主义的理解,提供了理解经济与社会关系的一把新的钥匙。沿着一些早期作者(特别是拉布里奥拉)的理解,科西克区分了经济结构(人们在生产中开始形成与生产方式有关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和经济因素(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系统化的表达)。但是他坚持这种区分的真正的历史内容:经济因素的概念反映了由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存在的瓦解”。现有逻辑的下一步应当是提出一个多元化结构的问题,与那些经济因素区分开来;如果经济结构“形成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一致性与连续性”,这种构造可能仍然被视为与其他总体化结构的融合。科西克对文化创造的分析是一种重建,而不仅是对这个方面的社会现实指向的反映。这将会得出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复杂性的更加普遍的结论,在这里相互依赖的因素的传统模式不再适用。但是科西克通过将经济结构的概念与以“唯物主义一元论”的名义所捍卫的经济的无条件的首要性联系起来,从而中断了这种论点。这个障碍由于他对劳动与实践之间关系的描述而被加强。虽然科西克批判了想要将这两者合并起来的广泛趋势,但是他对这种区分的解释却让人察觉到他在这两种模式中的摇摆不定。根据其中一种观点,劳动和实践对同一个基本结构拥有截然不同的视角——前者具有局限性,后者具有普遍性;另一种观点将实践视为多维的“本体-形成的”(onto-formative)过程,而将劳动视作实践的一部分。一般来说,作为劳动的第一种实践模式显而易见占主导地位。但是唯有第二种实践模式才可能有助于得出社会现实的多元化概念。
在后来阐释实践概念的努力中,科西克比之前更加强烈地强调实践(praxis)不可还原为劳动、实践(practice)、有意的活动。然而,反还原论者的推动力并未伴有一种正面积极的详细阐述。结果就是实践哲学丧失了许多最初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力量的分析。这在1968年科西克出版的“我们目前的危机”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了证实。[注] 这篇文章发表在《文学作品》(Literarni Listy )杂志1968年第7、8、10、11和12期。 Italian translation: La nostra crisi attuale, Roma 1969.虽然这些文章属于布拉格之春时期最引人关注的作品,但是它们与《具体的辩证法》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微弱的。正如科西克目前所看到的,斯大林主义的衰败提出了关于“国家和人类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这次危机的背景是一种全面操纵且普遍无责任感的体制,其逻辑已经导致了政治主体与社会阶层的死亡或瘫痪。
4. 1968年后国内外捷克斯洛伐克反对派的讨论主要围绕布拉格之春展开。1969年4月之后,虽然传统意义上改革的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是从它的失败中借鉴经验也绝不明显。并且,1969年后旧制度的恢复成为一种新的体验,并且和1968年时一样受到空前的欢迎,它使得在改革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愈加凸显。人们需要军事干涉去扭转这一趋势,但是在那之后,国家机构中仍旧根深蒂固的倒退力量依然强大且富于想象力。“普遍化”所带来的悲惨的文化上和道德上的后果不仅提示人们这一体制所存在的破坏性的逻辑,而且也包括总体上被改革者所低估的自我再生产的能力。
在修正过的框架之内,需要的概念获得了一个新功能:它被用来说明先前未知的统治形式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对需要的专政是一个“总体的社会统治制度”,在这个制度中对社会剩余产品的处理和占有被机构当作一个共同的实体来运用和认识,共同的实体仅构成了垄断性统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成分,凭借共同的实体进行全部的社会组织和社会交往。由于对需要的直接且强制的决定,新的统治形式调整了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学解释可以代替结构性分析。总体性统治制度有其自身的结构限制和制度复杂性,且这个理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去解释它们的工作。但正是由于其总体性特性,对需要的专政要求贯穿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实现权力的扩散,因此需要使以非极权主义的现代社会为典型的划分界线模糊不清(作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权力的唯一持有者的政党的关键作用不能被忽视)。出于同样的原因,如果这个制度的核心机制被保持完整,那么大量的再调整是可能的。这最明显适用于后斯大林时代的变化。
这个观点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官僚制在不依赖阶级概念的情况下被定义,并且阶级权力的征服因此仅仅被视为在积累过程中所迈出的更深层次的一步。因而官僚制的阶级特征是作为次要属性,而不是主要决定性因素出现的,它的阶级权力是作为团体所获得的所有物,而不作为基本的社会关系网来发挥作用。这种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模式本质上的弱点想要退回到对官僚制进行道德主义的批判的趋势中显示了自身,锡克提出对官僚制进行更加道德主义的批判,并将其运作规则谴责为对社会主义的一种“曲解”。
奥塔·锡克(Ota Sik),先前经济改革中最著名的倡议者之一,现在将“共产主义的权力制度”和阶级统治的官僚制形式等同起来。他的模式将苏联式社会描述为从部分控制到整体控制过程的官僚制的最后一个阶段。官僚制的根本特性源于它在传统的劳动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即组织与协调的专门任务;这种特殊的活动形式反映在有关权力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特殊利益上。在更先进的现代社会,官僚制的权力受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抵消机制所限制。伴随俄国革命带来的这些筹码的消失,以及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社会主义的集权概念,导致官僚机构成为完全垄断性的权力。因为这也涉及对生产手段和产品的全面占有,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官僚机构不容置疑地成为统治阶级。
虽然反对派关于1968年事件及其后果的研究著作数量很多,但是这些研究很少尝试超越对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再评估,并且为关于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更普遍的批判奠定基础。至今已经出现的少量的分析趋向于使用官僚制[注] 请注意:对于bureaucracy,一般应翻译为“官僚制”,而对bureaucratism,则译为“官僚主义”。请对文中的其他地方该词的翻译再检查核对一下。 的概念作为把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运行方式的关键。在这个方面,比较最近出版的另两部作品极其有意义。其中一部作品是由一个流亡者从广泛的社会民主视角出发写作的,另一部是民主反对派内部的新托洛茨基分子倾向的一个声明。
彼得·乌尔(Petr Uhl)写的《社会主义的禁锢》(Le socialisme emprisonne),阐述了在七七宪章运动中自成一格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少数派的观点,这部著作是1968年后出版的最值得被人们关注的作品(正如下面将要显示的,这本书的法国编辑对这本书和鲁道夫·巴罗所作的比较是带有很大误解的)。正如标题所表明的,一个被“禁锢”在官僚结构中的社会主义的潜能概念是争论的核心。然而,托洛茨基主义的残余没有阻止乌尔去修正转型社会理论的重要方面。虽然乌尔坚持认为官僚还不是完全成熟的统治阶级,但是他强调了官僚统治权力的阶级基础(对劳动力和对象化劳动的垄断控制)以及官僚和普通大众之间存在的阶级对抗。他的反官僚制革命的理想蓝图是将传统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元素与更早一些的元素结合起来。由于即将到来的革命直接指向官僚政治的中心,因而它应该主要是政治的,但是它所带来的后果将引起社会和经济的转变。对代议制民主的狂热的列宁主义批判伴随着非列宁主义的革命组织概念;乌尔假定一个“革命的共同体”,在那里许多“非正式的先锋队”将会出现。虽然对后革命的社会秩序所制定的纲领带有一种强烈的工运中心主义(ouvrieriste)的味道,但是它们也包含着明显的对自然法的参照。自治的原则将被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但这绝没有降低工会的重要性。[乌尔在“自我管理路线系统”“(circuit autogestionnaire)”和“利益防御路线保护系统”“(circuit de defense des interets)”之间作出了区分]。
总之,这种被忽略和被逐出的主题总体说来达到了马克思遗产的一大部分。事实上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连续性的生产模式,且连续的列表可能大体上也包含着其他现代模式。但是除了这种狭义的定义外,马克思使用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资本主义概念。从第二种观点来看,资本主义世界与所有先前的社会生产方式不同,它的出现被视为空前的历史决裂,即与传统世界的基本模式的断裂。资本主义更加革命性的形象明显取决于人类学的前提: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表现为全球的转变,影响了人与自然、人与其他人的整个复杂关系。最后,这种人类学的语境认为文化解读——包括特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能够比传统生产模式理论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尽管在锡克和乌尔之间存在着尖锐对立,他们分析的主要缺点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官僚统治的理论。虽然对东欧社会的解读一般都不能省掉官僚统治的概念,但是它表明的只是部分的和衍生出来的方面,而不是苏联制度的具体历史的特殊性(differentia specifica)。为了阐明这一理论的解释力的局限性,只要想起现实的社会主义的一些明显特征就够了。最起码,通常与官僚统治相关的结构上的保守主义与后革命国家并非不相容,但是就长期来看,扩张的和变化的动态制度掩盖了这种保守主义,斯大林模式自上而下的改革制度只是最显著的例证。苏联意识形态的内容和作用都不可还原为官僚制合理性原则。最后但也很重要的是:没有官僚统治的理论能够解释在苏联体制内政党的独特地位。
六、新列宁主义和倒置的列宁主义
1. 东德的改革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持异议者与上述讨论的其他国家相比明显是更无力的。[注] 适当地来说,恩斯特·布洛赫的著作不属于东欧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布洛赫对马克思的非正统的解读在他定居在前民主德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从长远看他不能与政党共存;决裂是在1961年最终完成,布洛赫的生涯与东欧其他地区没有平行线。另外,东德也吹嘘了这个独特案例,一个从前的异端继续发展成一种官方学说的可输出版本:Wolfgang Harich, Kommunismus ohne Wachstum, Hamburg 1975。 造成这种状况的最显著原因便是分裂国家的具体情况和党内产生的“受困心态”;在所有的可能性中,他们的影响力也解释了反对派在发展中的这种较为正统的特性。东德至今创作的仅有的主要作品是鲁道夫·巴罗的《东欧的抉择》(The Alternative in Eastern Europe )。[注] 写于1972—1976年间,1976年首次在西德出版;英文版于1978年在伦敦出版。西方的反应参见U. Wolter (ed.), Rudolf Bahro: Critical Responses, New York 1980 and AndrewArato’s review of this book in Telos, no. 48, also Andreas Wildt “TotalitarianState Capitalism”, in Telos, no. 41。 这本书在某些西方左派的圈子中获得广泛欢迎并不是其理论功绩的一个可靠标志:即便粗略查看巴罗的观点也会显示出,他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批判在很多方面都表现为东欧最能体现传统派观念的思想。
巴罗的事业被恰当地描述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一种重新调整。他的修正被纳入对更加基本的宗旨的维护。目的是在普遍的革命模式下为东欧社会的改革计划奠定基础——在一种普遍的人性内涵和一种世界范围的策略外延的双重意义上都是如此。可以用下面的话总结出20世纪的一种乐观主义的基本观点:随着俄国和中国革命的爆发,拉丁美洲、非洲和印度的革命进程也在不断向前推进,人类找到了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为了与马克思保持一致,巴罗首先在社会劳动领域确定了革命解放的任务。更准确地说:生产者的自由联合将战胜且替代劳动者的社会组织的异化和对抗形式。但是巴罗不再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是通往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可行路径。在他看来,劳动分工而不是传统的阶级关系模式,日益决定了东欧的晚期资本主义与后革命社会之间的内部冲突。与先前的阶级或阶级同盟的对抗不同,目前基本的替代选择趋向于采取人类学方向和文化方向的形式——这一形式“不像先前对理论那样将个体划分为稳定的社会团体”。巴罗将它们还原为利益的二分(dichotomy of interests)。补偿性的利益是对早期社会限制和阻碍无数人的生长、发展和自我确证的方式所作出的不可避免的反应,相应地需要与替代满足相符。有助于解放的利益适应人类活动各个维度上个性的生长、分化与自我实现。“臣属性”是巴罗对盛行的符合补偿性利益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术语指称,只有通过文化革命才有可能克服臣属性,这种文化革命将改变“大众生活的主观形式”,并且确立有助于解放的利益的首要地位。
(2)农业价格和补贴政策。包括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格、农产品直接补贴、产品售空计划和期权合约补贴。从1995年开始,巴西政府就减少了对农业的补贴和价格支持力度,增加产品售空计划和期权合约补贴[13]。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防止农村人口迅速向大城市流动;另一方面可以减少政府收购农产品的储备成本,同时保持巴西农业的综合竞争力,不断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对于本斯和吉什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伪质子(proton pseudos)在于把资本主义发展等同于现代化。他们坚持不可通约的多元化的现代化的类型和道路。苏联道路最典型特征是废除组织的形式自主权,且建立“权力和管理的全球等级制度”。这既蕴含市场的边缘化(不是市场的完全消失——还留有市场的残余)也蕴含着民主机制的缺乏,民主机制将允许不一致利益的体制化。本斯和吉什没有将民主的缺乏归因于市场的消失,新的政治组织原则解释了市场作用的巨大削弱,也解释了完全废除市场的不可能性以及周期性的但必然前后不一致的企图,即企图至少在更加合理的经济制度内恢复一些市场机制。
由于巴罗将苏联模式社会的发展视为“通往工业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并且认为它的历史必然性是理所应当的,因而他被迫把斯大林主义政权——或者至少是其决定性特征——归于他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捷径”中。然而,他认为斯大林的积极成就仅仅是对信仰的声明。而且,回顾历史的合理性使他无法准确判断目前社会危机的症状。他对国家主义复兴的态度,同对要求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工会的态度一样,都是犹豫不决且模棱两可的,他一会儿承认这些情况的“客观必然性”,一会儿又将它们视为复归倾向的表达。
然而,在目前的环境下,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巴罗的“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剖析”。在没有阐述可能会抵制文化革命的社会力量的情况下,他对文化革命的规划是无法完成的。因为巴罗的概念框架既排除了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排除了新的阶级社会的理论,所以他不得不去寻求解释后革命时代的不平等和统治形式进行的其他途径。为了这一目的,他利用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两个相对发展不发达的方面:对劳动分工的批判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批判理论。二者是相互联系的,但并不是同时共存的。
对于巴罗来说,劳动分工是最基本的统治结构,是阶级社会的“基本起点”。在这方面,他同意早期马克思的观点。但是虽然如此仍旧有一个新的转变: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本身与作为迈向更深刻的决裂的第一步,综合劳动之间的分化——即涉及与社会总体的直接关系的协作活动——以及那些被禁止这样一种直接关系的人的附属性的和特殊的劳动力相比,这一分工本身就显得不那么重要。正如巴罗所看到的,在后革命社会中这种模式的毫无争议的优势地位不应该被误认为是新的阶级结构:它只是证明了统治的一般基础结构能够比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废除存在得更久。
但是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批判来说,批判劳动分工明显是不充分的基础。如果人们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废除未触及很多传统劳动分工,那么对于基础结构是怎样产生一个完全控制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领域的体制这一问题就不那么容易理解。巴罗试图用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填补这个空隙。更确切地说:借助这种理论的两种不同版本。
首先要与劳动分工批判紧密联系起来。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和社会完全从属于国家——以“原始社会最终的父权时期和亚洲的阶级社会之间的连接杆”为特征——源于在综合和从属活动之间的最初分离。但是为什么这种结构应该在“原始社会主义”社会被重新生产出来?如果经济和社会的原始“分层”是由低水平的技术和文化发展所造成的,那么它也不能在现代条件下实现相同的具体功能。目前还未能发现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后资本主义的转变应当以相反的规则重复这种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模式——除非亚细亚的复合体有它自己的自我再生产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巴罗转向了另一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不是将这一概念解读为原始社会和文明社会的“连接杆”,而是理解为占统治地位的非西方的阶级社会模式。从这个角度看,亚细亚形态代表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径,而不是完全的停滞;正如巴罗指出的,亚细亚模式生成了抽象劳动和商品交往的具体形式。顺理成章下一步应当是去分析作为传统和现代的一种具体综合的苏联模式的社会。换句话说:如果这些社会的亚细亚背景已经产生了建构性的影响,那么它就共同决定了现代的最终模式,就像欧洲过去的特性形成了最初通往工业社会的道路。然而巴罗欠缺这种考虑。关于东欧社会的短期问题,巴罗的提议没有超出改革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在与布鲁斯的对比中(参见本文第三部分),一方面,他的观点由更雄心勃勃的理论计划所支持;另一方面,他的观点更依赖于布拉格之春的经历和对类似事件可能更大规模再次发生的期盼(他甚至考虑到“苏联的杜布切克”的可能性)。说到底,而后十年的事件并没有使这一期盼得以实现。鉴于导致了捷克斯洛伐克出现改革运动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以及1968年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外采取的防止类似于布拉格之春的事件反复的措施,巴罗的期盼似乎难以成真了。
2.如果从巴罗对十月革命的回顾性辩护和他对指导文化革命的新先锋的依赖来讲,有足够的理由去将他描述为一名新列宁主义者,倒置的列宁主义似乎是标示乔治·康拉德(Gyorgy Konrad)与伊万·塞勒尼(Ivan Szelenyi)观点的最合适的标签。在他们著作《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上的知识分子》(The Intellectuals on the Road to Class Power )一书中——在很多方面都可以说成是巴罗《抉择》的准确对立面——列宁主义的先锋被理解为新的统治阶级的胚胎。由知识分子统治并以“科学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论证合法性的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思想,比苏联模式出现得更早。康拉德和塞勒尼将巴枯宁视为先驱;更恰当的例证是扬·马察斯基(Jan Waclaw Machajski)的著作,他将自己对第二国际的批判拓展到对社会主义的一般性批判,指责社会主义是“新的知识分子宗教”和“有知识的资本家”的阶级政策的烟雾弹。但是,这种相似性不应该被夸大:对于马察斯基来说,核心要点是占有了资本家阶级并不意味着占有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而且,它为先前的资产阶级的从属部分,即知识分子,提供了新的机会,为了保护和扩大自己的特权,这些知识分子控制了工人阶级运动。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占有文明的社会”。在康拉德和塞勒尼看来,只有在东欧“知识分子才相对早地企图为阶级权力这类的事物而奋斗”。在选取这条路径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则充当不在场的或瘫痪的资产阶级的替代物,而不是充当资产阶级秩序的最终防御者,结果是现代化的非资产阶级和非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东欧的道路被描述为“捷径”的话,那只是因为由胜利的革命精英创造的“理性分配”的制度,是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替换。
总之,康拉德和塞勒尼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是第一个知识分子能够“聚集成一个阶级”并且成为占支配性的社会力量的社会。它是“第一个专业知识来自社会的潜意识,并且在社会主义初期结束时,变为越来越公开地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合法原则的社会制度”。这种对现状的理解,在东欧持不同政见者当中相当少见,是以对过去的特定解读和对将来的确切预期为前提的。东欧知识分子长期分裂为官僚和革命者,两种模式的布尔什维克式综合以及当下政治精英和管理阶层间的激烈竞争都被视为权力和知识之间关系的长期转变的插曲,这种转变是长期的但绝不是顺利的和连续的。因此与意识形态和专门知识都利用知识资源并诉诸知识标准的事实相比,二者之间的冲突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虽然在理性的——增长导向的——再分配中显现自身的阶级权力,“没有被知识分子整体所实践,而是被知识分子中更少的一部分——国家和政党官僚所实践,我们将称这些人为统治或管理精英”,统治精英的专制主义现在逐渐让位给一个“不平等的联盟”和对技术官僚的一种“合理妥协”。如今对于权力的斗争本质上是占支配地位的阶级之间的斗争。
这种解读的合理性取决于三个前提:阶级的潜在概念,使得从“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角度书写历史成为可能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以及对东欧当下和可预见的发展进行的评估。最根本的是阶级的概念。康拉德和塞勒尼将它们的论点建立在对马克思的如下解读上:马克思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财产所有权为人们对剩余产品的控制提供了合理性依据。因此,他正确地宣称资本的所有权是基本的因素,决定了这类社会的结构。那么,阶级结构的核心是使处理剩余产品的权利合法化。以这种方式,马克思阶级理论的两个维度毫无道理地合并了。对于马克思来说,阶级关系的基础是叠加在人对自然的首次占有基础上的二次占有,并且使其从属于拥有特权的少数派的控制和利益;部分发达的阶级关系从更复杂的一些关系中区分出来,且私有制绝不是阶级统治的唯一可能的表达。合法化的程序,以特殊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转化为核心,服从于他们的内部构成和他们与阶级结构的关系的历史变化。在私有制中经济和意识形态两种维度在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是一种特别的现象;对经济制度所带来的合法性功能的直接设想是传统资本主义的特质。
康拉德和塞勒尼对韦伯的解读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相似的合并迹象。在韦伯看来,多种形式下的合法性统治是结构化的社会存在构建的先决条件,然而,阶级的概念指的是这些社会存在之中的权力的分配。康拉德和塞勒尼用历史的差异来代替结构上的差异:阶级的概念被用来去描述适用于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合法性统治类型。因而,在假定阶级关系和合法权威的对等之后,他们可以在其特殊的合法性统治模式基础上继续去确定现实的社会主义中的统治阶级。即使表面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具体有效要求不被重视,以明显的权力合理性为真正本质的更为根本的要求也会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地,合法性被视为所有权:它建立在对资源的垄断基础之上,指包括思想和技术在内的专业知识。
在新统治阶级的形象被描绘出来后,仍然要展示出新统治阶级如何结束了知识分子的发展与演化。整个进程明显按照源于韦伯关于理念与利益的问题的视角来分析,但是进行了高度简化的修整。出发点是对知识分子的遗传存在(geneticbeing)和类存在(generic being)的区分,即区分知识分子的历史决定性和作为超越意义的承受者的角色。随着知识分子“将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提升到超越的价值的高度”,两极之间的张力逐渐消失,这种被利益所合并的理念在由使再分配权力最大化的利益所激发的合理再分配的思想体系中达到顶峰。理念与利益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被反映在相应内部观念的修正上。知识分子的两种根本任务——文化取向的构建与专业知识的积累——之间的差别,可以演变成一种“目的和技术的矛盾”;最稳定的综合是苏联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里文化和技术的元素并入整个再分配控制的理念中。
通过比较这个概念及其传统原型可以看到这个概念的有限特性。根据韦伯可知,理性化过程涉及利益和理念,理性化过程导致它们之间关系更为复杂且不断变化,而不是一方为另一方所吸收;随着各种“生活秩序”之间的差异变得更突出,且更加充分地被表达,综合性构建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虽然知识分子在理性化的进程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正是它的多维度使得他们不可能在阶级基础之上联合起来。
江苏油田高邮凹陷位于苏北盆地南部东台坳陷中部,南为通扬隆起,北接柘垛低凸起与建湖隆起相连,东起白驹凹陷,东南靠吴堡低凸起与溱潼凹陷相连,西接菱塘桥低凸起与金湖凹陷相隔,东西长约100km,南北宽约25~30km,面积达2 670km2,呈北东向长条形展布,新生界地层沉积厚达7km,是苏北盆地沉降最深的一个凹陷。高邮凹陷构造单元可划分为南断阶、深洼带和北斜坡3个部分[4](图1)。
在关于东欧的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解读来说,很难找寻由精英和技术官僚所带来的“权力的联合实施”的任何证据。康拉德和塞勒尼对这一问题的思索是对匈牙利模式高度乐观的推断。更不必说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近期历史并没有确证他们的假设。甚至在匈牙利,卡达尔政权的让步缺乏真正的权力下放。并且作者自己对最近事件的描述清晰地传递了一种与他们更为乐观的理论的不一致的信息:统治精英的反击使得技术统治论激进化,并使得它更愿意和工人阶级的运动联合起来;反过来,这也为“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新的机会,他们的任务是去说清楚这种冲突的阶级特性。
目前,众多学者已经从分子水平对移植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机制进行探究,RIRI主要从促进肾脏炎性反应、增加组织内的氧化应激、激活细胞的凋亡通路及内质网应激这几个方面对移植肾脏造成损害。近年来,硫化氢的广泛作用已得到共识,它自身是生物体内生的气体分子递质,具有多种物理及化学特性,对肝脏、心肌、肺脏、脑及肾的IRI均具有保护作用[26-28],值得注意的是硫化氢具有毒性,故研究中一般采用低浓度的硫氢化钠(NaHS)的生理盐水溶液提供外源性硫化氢,由于硫氢化钠在常温下比较稳定,操作人员佩戴口罩及安全防护眼镜,并穿防护服、戴手套,在通风的操作台小心操作即可避免硫化氢对研究人员的损害。
七、布达佩斯学派
1.科拉科夫斯基对修正主义与改革的共产主义之间关系的解释既不适用于南斯拉夫的情况也不适用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另一个反例是20世纪60到70年代期间匈牙利形成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布达佩斯学派——当在广泛意义上使用这一名称时,这个标签指的是一个相对多样化的团体,仅仅在致力于社会主义批判上是一致的,但是如第二部分所示,这一学派也与更加具体的哲学立场有关——既不是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副产品,也不是它的补充延伸。另一方面,1956年的革命最初没有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对派普遍更直接地与1956、1968和1970年的事件相关)。对1956年革命及其启示的重新挖掘来得较迟,且与其他修正主义有关联。
1956年苏联的干预结束了改革的共产主义和革命的进程。20世纪60年代早期卡达尔政权采取的让步策略不是改革的共产主义的新版本(在上面第五部分定义的意义上),如果将它描述为赫鲁晓夫主义的一种非常稳定的变体可能更有道理。1963—1968年间,让步政策可以演变成一种真正的改革的共产主义的希望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存在于领导阶层的实用主义革新和社会主义反对派更加激进的理念之间的鸿沟从没有被填平。由局部和目光短浅的改革所引发的批判,不亚于由这种制度根本上的保守主义所引起的批判。而且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上述关于结构改革的最终幻想消失了。
此外,作为一个整体的布达佩斯学派与改革的共产主义有着部分的和暂时性的亲缘关系。这种关系最明显地体现在安德拉什·赫格居什(Andras Hegedus)的著作中。尽管1968年之后呈现了一种明显更为悲观的论调,他的作品与我们上面讨论的(布鲁斯、巴罗)改革的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型属于一类。正如他已经看到的,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财产所有制形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终结创造了一般利益的客观化的可能性。这个决定性步骤的进一步结果是更高程度的社会流动。然而,社会主义结构优越性不能一劳永逸;为了充分实现新社会的潜力,必须首先达到一定程度的成熟性和稳定性。1966—1967年,赫格居什推论出,后斯大林主义时代的改变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更加接近这个历史的转折点。特别是,自我批评的制度化现在不但可能而且是必要的(因此,社会学的新作用也是如此)。社会主义的自我分析被发现集中于官僚制问题和反击它过度膨胀的方式。对于赫格居什来说,官僚制现象比早期马克思主义批判已经实现的东西要更复杂和模棱两可。它的终极源头一定会在社会管理从“强制执行财产权和私有权的功能”的分离中找到,但是其发展也受“所有权实践”(占有)与潜在的财产权的“必要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分离所影响。因此,官僚制——特别是在现代条件下——体现了相对自主的权力形式和财产的派生形式,且这种结合在社会主义社会变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的官僚关系根植于行政和管理上的结构限制。进一步必不可少的是对官僚制的一种社会主义批判,官僚组织的客观必然性和合理性也不能被否认。从一种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来看,可以想象官僚制的完全废除;在社会主义发展的给定阶段,最实际的策略是逐渐引入社会控制新形式,旨在控制和限制官僚组织的异化趋势。在赫格居什看来,这样的措施应该由“行政和管理的人道化”的调节性观念来引导。他坚持这一问题的自相矛盾性:“最优化和人道化之间的真正矛盾”是可能的,效率的必要性可能与那些民主化发生矛盾。
1976年,赫格居什为他文章的英译版写了一篇附言,承认“社会主义的自我分析和自我批判没有坚持自身”,但是他将改革共产主义的失败归因于不利的国际环境,并且表达希望将来的“群众运动”可以开启新的视角。他避开了对改革而言内部的结构性障碍问题。
近代以来,西方人把军队开进亚洲,导致东亚政府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苦苦挣扎,甚至需要跨越语言的藩篱互相交流,自从维多利亚女王派去的部队抢走了京巴狗洛蒂,西方已经史无前例地主宰了地球。几乎全世界都同意西方主宰世界的事实,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方而非东方。
然而,一些关于这些障碍的观点在早期的论文《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替代选择》(Modernization and Alternatives of Social Progress )中被提出,这篇文章是赫格居什和玛丽亚·马尔库什(Maria Markus)于1972年所写,并被选出用于谴责党内对匈牙利社会学中的“反马克思主义趋势”的制裁决议。在区分现代化的类别的过程中,该文提出的问题在之后的布达佩斯学派的文章中日益得到凸显。布达佩斯学派将现代化的国家主义模式——苏联和它的影响范围内所采用的模式——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的“主流”模式进行了对比。他们将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描述为对抗性和单方面依赖的一种混合。这种国家主义模式通过拒绝“主流”模式而确定并证明了自己的合理性,但是它的发展目标和策略违背了与先进资本主义的模仿和寄生关系。这种不对称因苏联体制未能充分地意识到从全面增长到集中增长的过渡而进一步加剧。从官方的角度来看,这导致对“主流”模式的新的借用,总之,就是经济改革的非政治化的概念。在更加广泛的社会范围内,最典型的应对危机的策略是以源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多重价值标准的名义对国家主义模式的更为明确的拒斥。尤其是,“重占有的消费模式” 影响日益加大,且掩盖了改变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计划。对于布达佩斯学派而言,摆脱恶性循环的“第三条道路”将把人道化的价值目标(在自我实现和对需要的自主解释这一意义上)和更动态的经济中的那些部分联系起来。关于可能更重视这种替代性选择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相关需要的问题,他们的结论反而不那么清楚。
如果赫格居什比匈牙利反对派的其他理论家更接近改革的共产主义的观点,那么G.本斯(G.Bence)和J.吉什(J.Kis)代表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对东欧社会的分析是基于对1968年之后事态的非常悲观的评价基础上的。他们认为东欧社会既是后斯大林主义又是后改良主义:统治阶级现在获得了一种内在的统一和灵活性,这种灵活性既排除了回归到不加选择的恐怖的可能性,也消除了可以为更加激进的转变计划铺路的内在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他们围绕着这种诊断建立的更一般的理论被简化为两个基本主题:东欧社会代表了一种非资本主义类型的现代性,且在马克思的意义上,它们仍然可以被视为阶级社会,即使他们内部的阶级关系没有以资本和雇佣劳动那样的方式显现自身。
巴罗对列宁主义所作的贡献同样值得提及。虽然他为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权力作辩护,认为这是合理并且成功的方案,但是他乐意承认自己的解读包括了比列宁更深层的脱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构想。对于巴罗来说,俄国革命是“通往工业社会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开端,是一场有其自身逻辑和动力的非西方社会的革命性变革。在不可想象的情况下,这一过程走了捷径,或者通过在资本主义腹地的革命,它本质上的困境自行抵消。东西方社会解放运动的集中爆发只可能作为长期未完成的历史迂回的结果而发生(列宁最后的著作已经开始意识到这一状况,但是他从没有抛弃1917年的“社会主义的幻想”)。并且如果未来的文化革命仍旧是由一个先锋所领导的话,那么后者一定会被设想为“剩余意识”的化身,即没有为社会经济秩序再生产所完全吸收的精神力量。因此,它存在的理由完全不同于党派中的传统列宁主义概念,是无所不包的科学教义的唯一贮藏所。
尽管这些社会拥有单一的组织化的等级制度,本斯和吉什不想抛弃阶级分析的原则。但是他们的方法不同于以上提到的新统治阶级理论。他们不想探索特定团体(官僚阶级或知识分子)向统治阶级的转化,而是从基本的阶级关系的定义着手,然后继续将阶级的作用当作集体活动者。并且,他们区分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概念的两个维度,即社会的维度和历史的维度:前者指的是一切非原始社会的共同特性,即不平等地使用和控制生产资料和生产结果;后者更明确地使用由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历史创造的生产资料和生产结果,即阶级能够合理有序地表达基于它们社会经济状况的利益。在东欧的社会形态中,第二种要素的缺乏像第一种要素的加剧一样明显:非常有限的少数派对管理和指导功能近乎完全的垄断导致了冲突周期性的爆发,但是没有走向公开的和制度化的冲突。阶级分化的加深和阶级冲突的封闭是相同的潜在原因的互补结果:在全球等级制度下政治和经济力量的融合阻止了附属阶级自治组织的出现和统治阶级内部部分利益的公开表达。
本斯和吉什认为,阶级分析是可以合理地应用于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部分。其他方面都是过时的、误导性的或者只是边际相关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对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组织没有直接的影响。鉴于阶级关系的新结构,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不能再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进行解释。对于这个问题,本斯和吉什没有说太多,并且他们的一些观察似乎具有高度误导性(例如他们不理会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新的统治阶级用作“历史偶然性”导致的结果)。他们最不接受对马克思的人类学解读,他们谴责这种解读,因为对马克思的人类学解读是“抽象的激进主义”且这种解读拒绝正视一个新的阶级社会的现实。
分析: 双子叶植物过量吸收生长素类似物后,形成层的细胞分生能力加强,产生肿胀,破坏了韧皮部的运输功能,使植物因有机物运输受阻而死。同时,这还破坏了植物正常的代谢,使植物呼吸作用加强,但不会产生ATP,造成植物细胞的损伤并浪费大量能量[5]。正常的生长素则容易被植物代谢掉,不会产生此危害。单子叶植物因能迅速使人工生长素类似物失活,所以除草剂也不会对单子叶植物产生效果。
应当承认,马克思著作的这个方面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相比,没有得到那么系统的发展,且它对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的影响非常有限。它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批判的重要性在其与布达佩斯学派第三个分支相联系的部分中充分显现出来:费伦茨·费赫尔(FerencFeher)、阿格妮丝·赫勒和乔治·马尔库什详细阐述的“对需要的专政”的理论。在下面的部分,我将首先总结这个理论的要点(第2点、第3点),然后讨论一些未知结论和开放性问题(第4点)。
2.对需要的专政理论是多股想法的综合。不只是其他当下方法的综合,它将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的讨论与20世纪70年代结构性分析联系了起来。这个理论使用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概念,但既不同于康拉德和塞勒尼的理解,也不同于官僚统治理论的理解。最后但也很重要的是,它在专注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矛盾的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极权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之间搭建了桥梁。第一点和最后一点紧密相关;人类学基础有助于克服极权主义的狭隘概念(将它与普遍的恐惧和持久的意识形态活动等同起来)和对马克思生产范式的经济主义的扭曲。
为了去追溯这一理论的起源,有必要简要地回忆一下布达佩斯学派最初的观点(参见上述第二部分)。如果我们从个体作者之间的差异中寻找,两个基本的原则将凸显出来。一方面,有人提出人的模式强调要包括社会和历史的决定性因素。尝试排除或消解它们的“人的本质”的概念不能被接受。另一方面,需要理论有助于避免超社会化和历史化人的概念的陷阱。需要不被视为人类行为的自然基础,但是它们至少是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交叉点。马克思关于“人的能力的自由发展”的思想将扎根于需要的领域,采取这种方法,经验个体的自主性将得到保护。
之后对于这种人类学计划的各种修正都有一个共同的要点:他们勾画出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概念。首先,一个多元的转向是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更为批判性的态度的逻辑结果。马克思的人的概念的早期重建与解放了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计划分不开;现在通过对东欧经验的不抱幻想的再评价,我们得出一种结论,即一种非常不同的但同样是非资本主义的选择已经盛行了。在一些方面,它可以被视为对马克思思想的一种倒置——既不是一种简单的变形,也不是一种完全异化的计划——并且,就其本身而言,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传统。因此,后者充当了相互冲突的人类学观点的战场。但是对新的多元主义来说也有更积极的一面。马克思自由发展的价值观本身是多元化的;生活形式的多元化变成了人的本质的自我实现的完整部分。因此,再阐述人类学的设想对于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仍然至关重要。制度的反多元化逻辑现在被视为最有异议的特性之一。
很多家长会觉得被欺负就打回去,是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粗暴”是够粗暴的,但真的简单和有效么?我们设想一下自己如果被“欺负”了会如何。
对需要的专政的理论最明显、最公开的退步特性集中于个体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层面,苏联制度已经设计了其自身解决一般现代问题的办法,即将一种内在具有社会性的产品与劳动活动的高度差异化的和个体化的消费与选择联系起来的乍看起来矛盾的必要条件。答案在于行政集中化的生产的一种二元结合,这种生产的唯一主题(原则上)是统一的权力机构和原子化的消费机构,这种行政集中化的生产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连同劳动力的“出售”)由成千上万的独立家庭承担着。在社会生产领域内,个体的自主性部分被取消,部分通过传播中立化。政治制度适应相应的政治人的转变;虽然公民再次被还原为一个主体,但他所处的条件与传统统治的条件存在重大的差别。这个发生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程被最恰当地描述为“去启蒙”和“潜在自由个体的毁灭”;对需要的专政的逻辑与道德和理性的自律不相容。所有领域的共性在于“无所不包的家长式统治”;同个体相比,社会制度采取了家长式权威的形式。
HE染色结果(图7,表2)显示,正常对照组肾组织中,肾小球及周围肾小管结构正常且清晰,细胞外基质均匀,无病变现象。与正常对照组相比,GM模型组小鼠肾小管管腔出血,肾小管空泡变性,上皮细胞脱落和变性坏死,肾小球皱缩,肾小管坏死程度等级显著升高(P<0.05)。与GM模型组相比,SVPr给药组小鼠肾组织病理变化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Ridit分析显示,SVPr 200 mg·kg-1组和阳性药组小鼠肾小管坏死程度等级显著降低(P<0.05),但均未恢复至正常水平。
3.然而,社会化的形式仅仅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方面。对于其制度原则的重构而言,最合适的起点是区分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结构。虽然这种分析将表明对需要的专政没有像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样采取子系统区分的模式,但是这种三分法——也显著存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近来译本中——仍然有某种分析的价值。
(1)在马克思的生产范式中,需要和生产活动的相互作用至关重要。当一个社会权力机构直接承担协调它们的任务,整个社会生产的复合体都需要进行相应修正。最重要的是,生产的取向和关系融合了更加广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机制。因此,生产的组织不再体现在一种相对自主的经济结构中。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在社会背景下占有自然——仍然是理解社会总体的关键,但是在与传统资本主义相联系的意义上,“经济的优先性”被这种制度的逻辑所逐出。
经济决定论的相对性适用于分析目标和制度。将现实的社会主义描述为适应经济目标的需要,与资本主义类似,或者甚至比资本主义更极端具有误导性。合理的构想既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也不是“以消费为代价的积累”。累积的生产扩张总是从属于一种社会方面决定性的目标功能,并且在东欧社会——与传统资本主义相反——不再可以单纯从经济角度来界定:“……在权力机构的全球化倾向下,物质资料(作为‘使用价值’)的量的最大化”构成了控制国家经济活动的目标函数。
尝试将对需要的专政还原为一种新的财产形式的各种努力导致了相同的结果。财产关系部分脱节了,部分被包含在控制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更加广泛的权力之下。控制生产组织的权力被扩散——虽然不平等——贯穿于管理的官僚机构中;机构核心保留了关于全部社会剩余产品的分配的基本决策,即党的领导阶层,且这里经济考量最终隶属于“国家利益”,正如中央政治权力所界定的那样。与其说生产目标由新的财产形式决定,不如说由一种财产功能上的等价物决定。换句话说:如果财产观念完全可适用于这些社会,我们仅仅可以谈论与这种权力机构的一些或所有成员的群体或集体财产相反的机构共同财产。
最终,对需要的专政在任何一种词义上都不是“计划经济”。经济的官僚管理建立在“完整的约束性秩序制度”基础上,这反过来是机构内部竞争与讨价还价的结果。因此,“计划经济”有它的体制偏好,但是它也有其内在的缺陷。为了满足经济合理性的最低要求,这个制度被迫创造成功的市场替代品。它仍然依赖于分段的、“非价格的”消费品和劳动力市场。其长期的困境导致周期性的经济改革试验,在不危及“国家利益”的最终主导地位的条件下,这些改革试验将给予市场机制更大的发挥空间。最后也很重要的是,它不能在缺失两种“补偿性的经济”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存在高度分歧的私人企业和活动复合体,以及基于机构内部“个人非正式的互助关系”的“等价交换和互惠服务”。
(2)“统一的命令制度”以社会的再政治化为前提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苏联模式是对国家与社会的典型的现代分离的一种否定。理论的寓意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前现代政治社会研究的概念是适用的(例如,正如苏联官方学说中所遵从的,存在着对专制国家和“政党主权”原则的重要类比);另一方面,动态的现代社会的“分层”需要新的权力机制,而传统的政治理论无法说明。
社会的再政治化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治精英任意而无限制的独裁。这个制度有它自己的制度条件,且在经济领域表现最为明显。不仅政治领导阶层,尽管付出了艰苦努力,仍无力改变东欧经济的一些最明显的“消极结构现象”;在更普遍的意义上,新的“统治阶级”明显不能使整个经济体从属于它自己的利益和特权:它同时保护和防御了制度安排,这种制度安排创造了对于“利润”分享来说最不舒服的条件。换句话说,权力的实施及其目标的执行是由机构而非由团体执行的,机构的运作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由其成员个体或附加利益所决定。对需要的专政理论不认为利益的概念有同样的解释权力,就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通常做的那样(缺乏表达和实现它们的社会机制,利益不能与在多元社会里一样发挥相同的作用),但是由于涉及利益的动态发展,因而我们认为机构决定一般利益的独有的权力忽略了更加具体的、物质的利益。这个制度通过抢占一般利益而不是转换特殊利益来运行。这就说明了政党统治的必要性,这种政党统治是对需要的专政的政治表达。
关于新政治制度的思想更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1月至8月之间发生的事件成为对这个制度公开讨论的核心热点。此次入侵是一个转折点——大部分讨论目前只是出于历史兴趣,但是与20世纪70年代的后改良主义异端的一些根本联系也不应该被忽视。由于改革的共产主义者致力于社会力量的政治解放,所以这一进程呈现出真正的多元化倾向,正如在运动中一些理论家公开阐述的那样,这一进程也体现出他们试图改变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的努力。在这个意义上,兹德涅克·姆林纳(Zdenek Mlynar)早期提出的纲领性阐述是在表达一种真正的趋势:一方面,必须承认不仅‘社会整体’能够被赋予独立的政治机构的地位,而且这一地位也必定被赋予个体成员、社会团体和阶层、公共利益团体以及也很重要的作为个体的每个公民。另一方面,即使本应在形式和内容上更加民主,但对新路线的官方解释仍旧致力于“政党的领导作用”。回顾一下,便不难发现这种联合明显站不住脚;至于1968年虽有争论提出要保卫这一政治制度,但对于一个外部人来说,要区分出战略性的保卫措施在哪里结束以及机构的自我防御从哪里开始是十分困难的。
(3)对于对需要的专政来说,意识形态的集权化与政治专制相比同样是根本性的。由于其无所不包的抱负,机构的权力只有通过普遍的解释才能发挥作用。意识形态因此扮演了比在非极权主义现代社会中更主要的角色。当人们考虑这个体系的起源时,意识形态的作用就更加清晰地显示了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对资本主义及其矛盾的反映”,它利用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扩张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意识形态和更加分散的文化取向。更清楚地描绘意识形态的核心属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虽然对需要的专政的逻辑反驳了社会主义解放的目的,但是不可否认,它与一些更矛盾的社会主义思想模式密切相关,例如一种关于教育的专政的雅各宾主义思想,技术统治论的国家主义的圣西门主义遗产,或者对需要进行专制管理的巴布瑞安(Babourian)计划。在这个意义上,对新的统治制度的批判一定包括对社会主义的一种自我批判。
更远一些的背景是对现代化的一般渴望,一些发展迟缓的地区尤其强烈,在那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被视为更公平发展的障碍。这种“消极的工业化乌托邦”,即对内在于工业社会的发展中但受具体的历史形式所限制的趋势的推断,也为对需要的专政开辟了道路。完全中央集权的社会和完全受控制的劳动力的愿景在新社会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更容易实现。
迄今为止,意识形态的成分似乎非常明显地指出了对需要的专政的系统和结构。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转变,这是如此的激进,以至于传统意识形态概念的有效性还存有疑问。我们应当注意这个变化的两个方面:首先,政权的意识形态因素越来越趋向于通过外在限制而不是动机和说服而发挥作用。只要意识形态对于定义社会上的实施原则和宗旨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信用的侵蚀就绝不能决定性地决定它的地位。其次,意识形态垄断的确立改变了意识形态自身的特征,各种意识形态完全是相互矛盾的,它们总是走入市场,它们也总是并存的。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国家的学说,一种全面的、排他性的世界观,而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对科学地位的要求服务于双重目的:科学的标准是轮流被用来证明整个学说的合理性,并为修正具体的教条进行辩护。
(4)最后,对需要的专政的社会结构——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因素的具体的总体——必须被简要地说明。尤其是,需要回答的关键性问题如下:这个制度是新阶级社会吗,或者它应该被描述为一种“无阶级”的统治形式吗?乍看起来第一个替代性选择的理由是明显的:如果阶级关系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占有社会剩余产品,也包括后者对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界限的划分,并决定了剩余产品使用,对需要的专政明显属于这个范畴。“需要的强制非难”和对剩余产品分配的完全控制表明了一种特别激进的阶级划分形式。它的社会后果指向相同的结论;机构和工人之间的深层对抗无疑是东欧社会最明显的特征。不过,如果存在着迫不得已的原因来拒绝或至少限制东欧社会的阶级分析,它们一定在某些方面与反动的社会团体的行为模式有关,在某些方面与被其他结构化原则所扰乱的阶级模式有关。
马克思的阶级概念,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分析中所使用的那样,不仅假定“围绕着剩余产品的处理和占有的利益存在互相敌对的关系”,也假定反对派群体有能力表达他们的利益并成立自己的组织。东欧社会的生产者不具备这样的可能性。对需要的专政一定程度上使工人原子化,一定程度上按照完全不同于阶级社会的方式缓和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尤其是,其危机导致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公开冲突。但是严格说来,机构也不是扮演着阶级的角色:虽然毫无疑问其内在的同质性比斯大林时期更强,但它是一个共同的实体,而不是利益一致的个体的集合。这种社会团体……建立在存在于个体之上的明确的有组织团体(社团)的领先性基础上的……它应该被视为独特的(sui generis)统治团体,不能与统治阶级相混淆。
机构和全体居民的对抗性分裂不是苏联式社会的仅有的构成性原则。另有两者干扰了苏联模式社会并且影响了社会冲突的模式:在这些社会的流行形象中,“政府主导的同质化”最明确地被描述为“权力的金字塔”,同时也呈现为一种客观趋势,并且劳动的社会分工导致了城乡阶层,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各领域手工业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总之,上述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对需要的专政使得阶级关系的某些方面极端化,并且抑制和废止了其他方面。
4. 在这篇论文上述提到的所有概念中,对需要的专政理论对我来说似乎是进一步讨论东欧问题的最有前景的起点。接下来的评论集中于它的一些要点。
(1)上面已经提到,研究极端主义现象的人类学方法,为东欧社会的分析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妥善性现在可以从两个维度得到检验: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对抗以及着眼于得出更普遍的马克思的人和社会的形象的含义。在后者的转变中,高度的连续性比经济和社会必然的再概念化更加明显。但是需要和对象化理论不是唯一可想到的区分框架。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 包含了一些批判现实的社会主义的非常具有提示性的线索,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它的理论潜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科西克的实践的关系概念(在它与布达佩斯学派的人类学之间存在着一些反差,我们在第二部分已经指出了)包含相应的极权主义概念的缩影(in nuce),这种极权主义概念被理解为人类语境的同质化和破坏的对立统一。
巴斯克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艺术身份的论述很有价值,一方面他为马克思曾提出的“任何工作都可以且应该具有一定创造性或艺术性成分”的观点进行了辩护,且这一观点对于发展一种社会主义工作哲学至关重要,另一方面他为马克思提出的“人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的观点进行了辩护,而这种观点隐含着一个美学和审美经验的概念,且该概念比最传统的那些概念要丰富得多。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更好地探索这些观点的潜在含义,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的马克思主义美学领域中,走出一条新的研究之路。
(2)从另一个角度看,对需要的专政理论需要诉诸更加普遍的现代性理论来完成。虽然与东欧的其他地方相比,匈牙利反对派对这一主题的研究更加深刻(他们的分析与哈贝马斯的作为发展起点的现代性概念之间存在着某些连结点),但现代性理论是一个长期的规划,且至今可以明确的只是其裸露在外的轮廓。并且,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完成的必要的基础性步骤之一,是运用马克思资本主义发展理论的解释基点。正如对本斯和吉什的评论中提到的(第七部分第1个点),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时代及其在历史中的位置的解读一直徘徊在部分概念和整体概念之间。资本主义的双重形象——作为生产模式的形象和作为历史宇宙的形象——被反映在马克思作品的矛盾性和不一致之中,从价值理论到革命理论。然而,甚至总体性概念的全面重建至多将充当现代性理论的踏脚石。
尽管如此,马克思著作的这个方面对于现实的社会主义批判是十分重要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费赫尔、赫勒和马尔库什特别排斥这个概念(他们还排斥转型社会理论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正如他们已经令人信服地展示出来的那样,将苏联模式社会还原为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的解读不能解释新制度的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在这方面需要作出一个告诫。国家资本主义理论只是在后革命社会的结构与资本的自我超越趋势之间建立联系的众多企图之一。当这些解释策略植根于资本主义的总体性概念而非部分的概念时,这些解释策略更胜一筹。正如卡斯托里亚迪斯(Castoriadis)的著作所展示的,这个立场的逻辑可能导致逐渐抛弃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体系。
(3)对需要的专政理论主要针对苏联模式的自我延续的逻辑。它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说明新社会是一个连续的且自我繁殖的制度,而不是一个过渡的或离经叛道的现象。这个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其逻辑对多样的历史环境的必然适应没有得到广泛讨论。在目前讨论的语境下,对这种制度某些方面的选择性强调不会招致反对。但是在更基础的意义上,起源和结构的分离不能在方法论基础上简单地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如说,问题在于是否新社会也无法体现起源和结构之间的新关系。在一些方面,对需要的专政是与过去空前激进的决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前资本主义背景下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国际化和积极再生产。这种无法否认的连续性已使得一些批评家将苏联制度解读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专制政治的新变体。费赫尔、赫勒和马尔库什认为这些观点与新社会本质上的现代性不相容。假如前资本主义的祖先从未建立一种充分的解释,然而应当注意到的是,最近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在很多方面已经修正了最初的问题,并使它更接近于历史现实。具体的生产模式概念趋向于为一种更一般的社会类型让路,较少依赖于发展程度和环境状况。在某种程度上,亚细亚形态的广义概念与资本主义的总体概念相匹配;它包含了不同的发展路线和历史阶段(由于其全部缺陷,魏特夫在这个方面的东方专制政治理论比他的批评者大多愿意承认得更为有趣)。在这种语境下,专制国家更极端的形式似乎经常出现在亚细亚文明的边缘或中间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俄国的历史就是恰当的例子。
(4)最后,关于苏联社会运行的独特的制度逻辑需要更进一步说明。当然,这些形态不是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后资本主义特征的一个“杂集”,而是不能通过解释来消除的体系的特殊融合。[注] 我从最近的出版物著作《融合的社会》(The Syneretic Society ,New York 1980)中借用了这个术语,作者为菲利普·加西亚·卡萨尔斯(Felipe Garcia Casals)(这是东欧作者的笔名;他对专制领导权的持久性和后斯大林时代的超工业化的强调暗示了俄国的背景)。作者认为,“融合的社会”不仅是一个转型的社会,而且它是走向一种生产模式的过渡模式。“从这点出发,文章指出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不同流派采取了不同于帕森斯模式的(Parsons’model)差异化路线。在这里,它没有体现在功能明确的元素的繁殖上,而是体现在功能的融合上——因此,元素与元素之间是不连贯的。”(p.55)然而,作者在这点上的有趣建议被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法的传统版本所削弱;这反过来使得斯大林主义看起来像是对历史的长期违背。它在上述的三种经济体制的结合与“行政集中的生产和原子化的消费”[注] Casals, op. cit. , repeatedly uses this expression. 的二元论中显现自身。在政治领域,政党自主权是与无所不包的国家机构和不明显但最终或许是更具决定性的社会军国主义化结合在一起的。在意识形态现象中,普遍的教条与民族主义流派的共生揭示了一种相似的模式;这在苏联体现得最为明显,但是尽管在“人民民主”中国家主义扮演更具破坏性的角色,但是如果完全没有“人民民主”,国家主义合法化制度也不能发挥作用。
① 本文来源:Perspectives and Problems of Critical Marxism in Eastern Europe(Part Two),Thesis Eleven,Nos.5/6 1982.(215-245)。这是将在爱奥迪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鲍姆和奥尔斯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的故事》(Storia del Marxismo)第四卷中一篇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感谢朱利奥·艾奥迪编辑允许本文的出版。《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卷的英文版已经由Harvester 出版社(1982)出版了。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发表在《论提纲十一条》(Thesis Eleven )第四期,研究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和批判性替代方案的性质,并评价了波兰马克思主义和南斯拉夫对批判性选择事业的贡献。本文是对东欧批判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两部分研究的第二部分。
[收稿日期] 2019-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理论在东欧的发展与演变研究”(17CKS025)
[译者简介] 杜红艳(1983- ),女,黑龙江林甸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 B5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05-0005-21
〔责任编辑:杜 娟〕
标签:东欧论文;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论文; 捷克的新马克思主义论文; 东德的新马克思主义论文; 布达佩斯学派论文;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