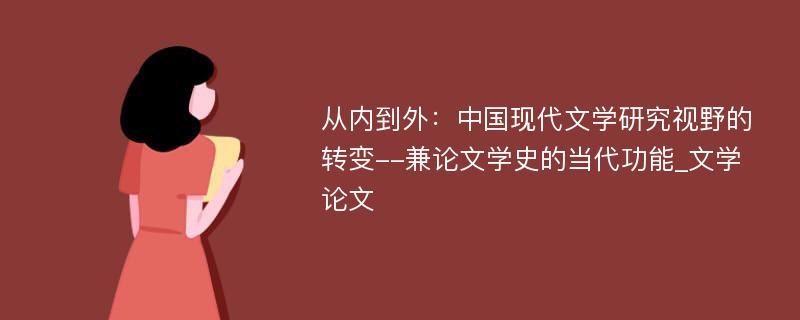
从内向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视野转换——兼谈文学史的当代功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向外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2)05-0114-05
一、由茅盾研究说起
在近20年茅盾研究史上,有两个学术事件令人深思。一是王一川编辑的20世纪中国文 学大师文库,改写了长期以来现代中国文学鲁、郭、茅、巴、老、曹格局,不但将通俗 武侠小说家金庸列入大师行列,更将茅盾逐出大师之伍;二是蓝棣之重评《子夜》,以 审美标准对《子夜》文本重新阐释,颠覆了长期以来《子夜》的经典地位。一石激起千 层浪,两个事件惹恼了众多茅盾研究者不说,而且解构了长期以来有关茅盾及其作品的 镜像世界。
且不论两个学术事件本身的是与非,问题是,茅盾作为文学大师、《子夜》作为经典 作品的观念从何而来?是人们真正全面系统地阅读茅盾作品后得出的结论,还是固有政 治意识形态下现代中国文学教学体系长期灌输的结果?答案显然是明确的。长期以来, 现代中国文学史教材编写系统,以强势话语的姿态将茅盾及其作品封闭起来,割断了思 想活跃的受众与茅盾作品丰富性之间的对话,使大、中、小学生认为他们读到的就是茅 盾最好的作品,从而使真实的茅盾及其作品退隐了。《背影》等作品可以树立朱自清一 流文学家的形象,可是,像《白杨礼赞》、《春蚕》等能充分展现茅盾作为一个作家的 才情和艺术风范吗?茅盾或许不具有郁达夫、徐志摩的潇洒飘逸、哀婉缠绵,但谁能否 认他的艺术天赋和文学才情?那些与文学史正统观念不尽一致的作品,是否更能展现茅 盾作为文学艺术家的资质?众多的问题足以说明,许多人评判茅盾及其作品的标准,并 非建立在求真、求实、系统全面和独立阅读的基础上。今天,我们已明白,不能因为一 个人的政治选择,无视他的卓越的艺术创造,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的艺术创造,美化他的 政治选择。
二、质疑“纯文学论”、“纯审美观”
从另一个角度讲,这两个学术事件的要害在于,它们体现了过去20多年现代中国文学 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术思想:“纯文学论”或曰“纯审美观”。改革开放之后,一批令 人尊敬的学者以“纯文学论”、“纯审美观”为理论和观念的武器,抗衡政治意识形态 对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束缚,为文学和学术的独立开辟了应有的生存空间。在这种理论 看来,一部文学作品存在的根本理由,就是作品蕴含的文学性和审美价值,对于文学作 品的评价,不能依赖文学和审美系统以外的任何标准,最终取决于它自身的文学品质和 审美趣味,取决于文学想像和审美理想的丰富程度。
“纯文学论”、“纯审美观”为人们久闭的心灵打开了一扇自由的大门,为现代中国 文学研究赢得了相对自治的话语系统,众多学者仿佛在此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学术根基。 于是,那些革命色彩浓郁的作家受到了疏远,过去那些与革命保持距离、甚至持不同政 见的作家迅速走红,一些具有解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作品大行其道,过去为正统观念 排斥的许多作家像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迅速成为大师级作家。夏志清的《中国现 代小说史》在近年现代文学史的重构风潮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夏氏对鲁迅、茅盾等作家 的贬低虽不能令内地研究者心悦诚服,可是对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进行的审 美的和艺术的分析阐释,却让人一见倾心。
在“纯文学论”、“纯审美观”的引导下,现代中国文学史经过近20多年的重新书写 ,实质上形成了两套明显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一是现行的政治意识形态所规约的价值 取向;一是“纯文学论”、“纯审美观”的评判坐标,由此形成了近20年现代中国文学 史批评的一个奇特现象。一方面,那些与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取向保持一致的作家作品, 尽管在艺术和审美品位上受到责难,但因为是革命和国家政治意识形态自身重要的历史 文化资源,其品评的重点就被放在作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功能上,突出作品的实用价值 ;另一方面,对于政治上没有光荣履历但写出了优秀作品的作家,就强调作品的审美性 、艺术性、超越性和永恒性,突出展现作品的内在价值,强调作品对文学艺术发展的贡 献。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评判系统并存,不能不说是近20年现代中国文学述史结构上的 一大特色。人们一面以文学史价值为理由,为那些在历史上产生影响但又不为现时代所 青睐的作家作品开脱,一面又以文学作品的内在审美价值为武器,论证那些为革命的政 治意识形态洪流所淹没的作家作品的合理性。
文学史价值和文学审美价值的一分为二、并行不悖,可谓是学人们为解决自身困境提 出的一个折衷的理论方案和述史模式。在过去的20多年中,可以说它功莫大焉,然而, 今天却成为阻碍学术发展的一个观念的牢笼。究其原因,“纯文学论”、“纯审美观” 并非严密周备、内涵确凿的实质性概念,而是一个描述性概念,是在与政治意识形态相 对立的语境中产生的抗衡性概念,其立论的基础是艺术性、审美性等经验色彩浓厚的元 话语,过于强调这一点很容易滑入纯形式主义的泥沼。事实上,随着社会和文学观念的 变化与发展,对流行的“纯文学论”、“纯审美观”观念的反思和质疑,已经进入了学 术视野。经过近20年的努力,学术界已经基本建立了相对自立的学术话语系统,“纯文 学论”、“纯审美观”所指涉、所反对的对立物已成强弩之末,难以简单粗暴地干涉学 术系统的运转和循环;学术的自身机制也不再允许自己只负有单一的功能,它所产生的 意义和能量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语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纯文学论”等对政治意识形 态话语霸权的抗议性和批判性,已开始淡化,其纯形式主义的偏执凸显了出来。长此下 去,很难使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适应当今社会文化语境的巨大变化,难以随着时代的变 化建立学术、文学与社会的新关系,难以克服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越来越边缘化的倾向 。
进入21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在累积了20世纪90年代思想精神问题的基础上,又孕育出 许多新的复杂矛盾,产生了许多过去不曾有过的尖锐问题。当社会各个层面在复杂的社 会现实面前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碰撞时,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对当前思想学术界 的影响却在削弱,它的介入社会的主动性降低了。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味坚持“纯文学 论”、“纯审美观”的理论思维,很难与新的社会思想状况沟通,与社会现实进行精神 的互动,更不必说以崭新的学术成果和思想效力参与当前的社会变革了。
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正处于自身发展上的“滞涨”阶段,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 能力减退,庞大的科研教学队伍、每年不计其数的研究论文和创新成果呈反比例增长。 面对这些,除了准确勘定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在社会系统中的价值定位,建构合理的学术 与社会的对话关系之外,对自身的反思更体现为学科系统新陈代谢的内源性动力,故对 “纯文学论”、“纯审美观”的合理批判与重新建构,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文学定义的现代界说
对“纯文学论”、“纯审美观”的合理批判与“什么是文学”的问题有着密切关联。 什么是文学?文学是什么性质的行为?它有什么作用?文学在人类众多活动中的地位如何? 把文学区别于人类其它精神产品或其它实践的特征是什么?……伊格尔顿就提出:“‘ 文学’的意思是什么?它是否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形式的著作区分开来?文学批评的最终目 的是什么?它提供什么样的(常常含蓄和看不见的)思想意识价值?”[1]所以,文学的定 义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是否是鉴定文学的标准,也不在于明确一个无论是共时状态还 是历时状态都能接受的内涵,而在于要将其作为理论和方法论导向的工具,来阐明文学 的基本风貌并参与社会文明的进程。
关于文学的内涵和本质,比较富有成果的讨论基本围绕着两个标准进行。其一,通过 与某一设定现实的关系来界定文学性;其二,瞄准语言的某些特性,甚至语言的某种结 构来界定。据此,学者们提出的定义大致有五种:第一种是形式主义定义,认为文学科 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是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也即“文学即 新颖化”。第二种是功用主义定义,即文学文本通过语言的表现方式,把自己从生产时 间及现实环境中分离出来,把文本语言试图完成的实际行为变成一种文学手法,并置身 于一系列文本与文学手法的背景中。第三种是结构主义定义,认为按传统和文学背景的 规范,融合语言结构和修辞结构而建立起统一的功能性的相互依存关系,应为文学特征 的标志。第四种是文学本体论定义,认为文学语言的参照物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幻想 中的人和事,是对非虚构性严肃语言行为的虚构性摹仿。第五种定义涉及文学的社会文 化环境,认为社会的首肯即文学,该社会的作家、学者、教育家、出版家及普通民众所 认可的即文学。
当然,这五类文学定义从不同角度解释和描述了文学的部分特征,并不能令人十分满 意。人们寻求“文学性”的完整内涵,不亚于对“人性”进行定义的难度,这或许因为 文学的永恒主题就是它的不可知性吧。事实上在19世纪末以前,“文学”还不具有现代 的含义,虽然文学作品的创作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总体上还只是意味着“文章”、甚 至“书本知识”,文学研究也还不曾成为独立的社会活动。直到在科学、道德、艺术的 学科建制日趋完备的近代,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定义问题才浮出水面。据卡勒的说法:“ 在莱辛自1759年起发表的《关于当代文学的通讯》一书中,‘文学’一词才包含了现代 意义的萌芽,指现代的文学生产。史达尔夫人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则 真正标志着现代意义的确立。”[2]他又说:“提出问题的目的,并非一味追求‘区分 ’本身,而是通过分离出文学的‘特质’,推广有效的研究方法,加深对文学本体的理 解,从而摒弃不利于理解文学本质的方法。”[3]显然,在追寻文学定义的背后,隐藏 着现代价值观念和知识系统的建构过程。对于“文学”的理解和描述,依赖于所处时代 的价值判断标准、知识构成、思想意识状况以及流行的常识与惯例。任何文学作品以及 对它的评价,都取决于“阅读”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个人趣味。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 有关“文学”的定义,取得所有时代所有人的认可;也还没有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被所 有时代所有人判定为是文学的典范和标本。关于“文学”的判定、描述、阐释和想像以 及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和评价,都始终处在历时性的演绎和共时性的建构过程中。
四、域外文学史观流变一瞥
关于何为文学史的观念的建构,也是一个历史演绎过程。下面以德国现代文学史形态 的建构过程为例,作些分析描述。
第一个对文学史提出特殊要求的是赫尔德,他强调文学的反思精神、理论和历史意识 的重要性,要求文学史在保持总体形态的同时首先体现出一种启迪精神,应当为人们的 “自由与精神振奋”指明道路,为促进“民族自豪感”作出贡献。他提出了文学史写作 的意义和功用问题。赫尔德关于“个性”和“主体性”的设想,表达了建构一种“新的 内心世界”的愿望,并与政治、社会领域联系起来。在他那里,文学艺术不仅是促进人 类不断进步和幸福的手段,而且成了资产阶级自我完善意识的体现和目的。
施莱格尔兄弟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文学史写作的先躯。他们把目光转向文艺的审美维 度,认为文艺的历史只是一种狭隘的自我完善的精神史,文学史研究的重心首先是审美 的基本原则和文学批评问题。如果说施莱格尔兄弟突出了审美判断和艺术的价值标准, 那么在资产阶级上升阶段,强调文学史写作现实功能的要求很快压倒了它。文学艺术越 来越滑入政治和社会的巨轮之下,这方面,格尔维努斯是一个代表。他认为,在文学史 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各时代的目标和思想内涵的演变,他反对浪漫派将文学审美化的 倾向,强调人的自我完善和知识应当与实践相结合,应指导人的行动,增进民族意识。 他不仅向过去的文学提出了政治评价的标准,而且向文学史写作本身提出了同样的要求 ,认为文学史几乎是一部“时代史”,文学史写作应肩负起让全民族了解它当前的价值 、重新振作自信心并对未来鼓起勇气的任务。
19世纪后半叶,上述这种分歧出现了时代变体。一种是置文学史宗旨于不顾,热衷于 细节考证的实证主义文学史写作方法;另一种是把文学解释为整个历史精髓所在的审美 历史主义。代表人物分别是谢勒尔和兰克。这时的文学史写作,并没有完全放弃意义和 价值判断,而是把注意力从总体联系转向具体分析,试图建立一种新的意义结构。实证 主义的长处体现在语言学和文本批评中,细致性和认真性毋庸置疑,但把注意力集中在 孤立的现象考证的狂热,明显妨碍了文学史著述与历史联系的简明扼要的归纳,丧失了 宏观的把握能力和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辨析。实证主义的理论缺陷,却成为审美历史主义 的优势。兰克所代表的学派把文学史看作由某些“思想”所统治的相对封闭的整体,文 学史家应当在内心投入和有意识认同的过程中,找到把握和理解这种“思想”的途径。 这种把历史看作是一种“现实精神之物”的观点,带来了文学史研究中越来越严重的审 美化倾向。由于把历史解释为人类精神的展开和自我呈现,文学史有流于专门的文化史 写作的危险。
狄尔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展了带有浓厚心理学色彩的阐释学。他认为解释是一 种个人的艺术,其完美程度取决于解释者的天才,这种天才建筑在解释者与作家的亲和 力上,通过对作家生命的深入体验而得到增强。在他的继承者那里,认识过程中的个人 主观因素愈来愈明显,像在格奥尔格学派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学史写作中,作者的独特个 性与才华被突出出来,超时代、超历史的价值和“本质”受到高度赞扬,而作家与时代 环境的联系却被割断。他们相信,艺术创造了一个“更高的第二世界”,认为艺术不是 对生活的摹仿,而是“生活本身的形式”,文学史的写作也就成了一种创造性的和再创 造的活动。如果说实证主义者因过于沉迷于作品与外部世界关系的考证,丧失了准确把 握作品艺术世界的能力,那么精神史学派则往往陷入自我观念的世界而不能自拔。
为弥补这一不足,精神史学派内部出现了注重艺术作品形式结构的研究方向,试图从 风格和形式中发现作品与一个时代的精神和心灵气质的内在联系。这导致了“二战”后 “文本批评”学派的崛起,文本阐释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越来越突出,意在“寻找超时代 有效并在历史流变中长存的东西”。这种文学史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直到20世纪60年 代都处于主流地位。总起来看,精神史文学理论仅对“真正的文学性”感兴趣,拒绝对 文学与社会的历史联系作出解释。放弃了描述文学与政治、经济、心理等社会现象互动 的总体把握,也就丧失了通过解释和研究将过去的经验运用于今天的目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文学社会史”的主张重新抬头。人们纷纷指摘过去文学史意识 的危机,要求建立一种“肩负起解放使命的文学科学”,“为社会启蒙和变革服务”, 赫尔德、施莱格尔兄弟和格尔维努斯提出的问题又得到人们的再认识。之后,意识形态 批判、历史主义、社会史和唯物主义方法被广泛采用,认为,新型文学史的写作首先必 须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历史不仅是自我完成的精神史,也不仅是琐碎的考证和纯形式 的建构,还应起到普遍启蒙、甚至指导人们行动的作用,是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力 量。文学史的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连续性,为人们提供了自我意识的基础和价值判断的参 照系,使人们更清醒地评价和改造现存的世界,因此人们普遍认识到,“美学观察与历 史分析的鸿沟必须填平,文学史是文学与历史的统一;各个文学品种与文本都应当受到 足够的重视,但同时又必须把它们放到广泛的社会关联系统中去。”[4]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德国现代文学史观念的流变,并非是独有的和特殊的区域性现 象,而是全球性文学史观念流变的一个缩影,体现了人文学科视野中文学史塑造的诸多 共同特征。从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诗学批评开始,中经符号学理论、英美新批评、结 构主义、精神心理分析与原型批评、语言学研究,直到解构主义理论与批评,这个历史 阶段的主导潮流,是对文本作形式主义和修辞学式的“内部”研究。但是,从70年代开 始,这种关于文本“内部”的研究逐渐受到人们质疑,人们越来越关注文学与外部世界 的联系,文学阐释学、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 、少数民族话语、同性恋理论、新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和方法的崛起,表明西 方的文学研究经过大半个世纪以文学内部为中心的研究后,开始全面转向文学与外部世 界关系的重新探索。这种由内向外的视野转移,已经成为一种强势潮流。正如米勒所指 出的:“自1979年以来,文学研究的兴趣中心已发生大规模的转移:从对文学作修辞学 式的‘内部’研究,转为研究文学的‘外部’联系,确定它在心理学、历史或社会学背 景中的位置。换言之,文学研究的兴趣已由解读(即集中注意研究语言本身及其性质和 能力)转移到各种形式的阐释学解释上(即注意语言同上帝、自然、社会、历史等被看作 是语言之外的事物的关系)。”[5]
五、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视野转换趋向
在近20年全球性文学研究由内向外视野转移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学研究却出现了一个 时间差:极为注重“向内转”,注重作品的审美、艺术分析,注重作品语言风格、叙事 模式、结构张力、技巧手法等现象形态,注重作家的自我意识、生命体验和艺术感受, 而相对忽视作家作品的社会属性和历史意识,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文学研究视为一个相对 封闭、自足的本体存在。这种纯文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就是相信文学作品有超越时空的 艺术永恒性,相信文学作品有不依赖于任何外在事物的、独立的审美本性,而文学史的 任务,就是要揭示、保存和传播这种审美本性和艺术永恒性。这种思潮的盛行,有着历 史的使命,是对此前一元政治意识形态控制下的僵化学术史的反拨,是谋求自身发展的 一种补偿性措施。但是,当产生和支持它的社会语境发生变化后,当它的学术纠偏功能 基本完成以后,再拘泥于和沉醉于“纯文学论”“纯审美观”之中,已无异于坐井观天 ,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如果说一元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可以窒息学术的生命,那么“ 纯文学论”、“纯审美观”的偏执,亦足以使文学艺术沦为精神贵族的专利品。因此, 重新调整文学史观念系统的价值坐标,检测、更换理论思维和方法的武器,是当前现代 中国文学研究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的必要措施。
中国现代文学是脱离了古典观念的中国人在追求现代人生梦想和社会理想的过程中, 在现代价值理念的导引下,运用现代汉语的审美形式发出的心灵的歌哭与吟唱。“现代 ”是一个不断告别过去、迈向未来的过程,是一个已经开始、尚未终结的进行时状态, 因此文学的生产与研究,也是一种开放行为。现代中国文学曾经和正在创造一个五光十 色、斑斓多姿的生活体验世界和艺术想像空间,这个空间将为过去、现在和将来提供丰 富的生存经验、生命智慧和精神支点。因此,应当有这样一种文学史意识:接受过去是 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在,创造未来。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不但要放弃为某种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狭隘理念,而且要摒弃关于 文学超越历史的思路,防止自我封闭和自足的偏执。应该避免让文学史简单地适应现代 口味的倾向,避免把过去的问题现代化,无论它的借口是政治的还是艺术的。文学史写 作是一种既要求倾向性和投入的活动,又是要求与对象保持距离的对话活动。我们所描 述和阐释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叙事技巧和所选择材料的产物,这种追溯与说明,始终 受自身认识论视野的制约,研究者的诚实在于,不隐瞒自己的学术兴趣、政治倾向和价 值追求,由读者去判断结论的真与伪、虚与实,抛弃那种在研究中抹煞独特、力求全面 的客观理想,才能获得从某一视角出发,探寻和追问历史意义的自由。
我们的研究,应当坚持视作品或文学行为的产品为研究核心;应当从历史与审美相关 性中去理解作品;应当在分析文学与社会依存关系的同时,重视它作为人类独立精神形 式的自主性;应当把作家作品放到历史传统的发展链条中,把它们同前后时代的文学联 系起来……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人创造文化,又被文化所创造,人是文化的主体,又是 文化的对象。文化体现为各种各样的符号,“文学既是文化的声音,又是文化的信息。 它既是一种强大的促进力量,又是一种文化资本。它是一种既要求读者理解,又可以把 读者引入关于意义的问题中去的作品。”[6]因此,必须尊重这样一个事实:文学作品 作为审美感知的对象,始终要经受人们的阐释和评价,惟有如此,它才能得到审美的现 实化。审美感知与接受始终和价值评价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如果仅 用现实尺度衡量文学作品,忽视作品及结构的历史性,或者仅仅是还原和复制历史而忽 视文学作品的精神指向,都无法全面、系统、合理地进行文学史建构。因为在当前,正 如绍伊尔所论述的:不仅文学被看作是一种社会产物,文学史被视为社会史的一部分, 而且文学的审美评价也发生了根本变化,美学本身也成为一种受历史条件制约的艺术观 。判断“美”的标准不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只有在历史这面镜子中,一种审美现 象才能获得其价值[7]。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任务,当然不是把价值判断作为最终目 的,而是要引导人们在批判性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历史的和审美的思考。如果能达到这 一目的,一种新型的文学史视野也就建立起来了。WW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艺术价值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当代作家论文; 艺术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纯文学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子夜论文; 茅盾论文; 审美观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