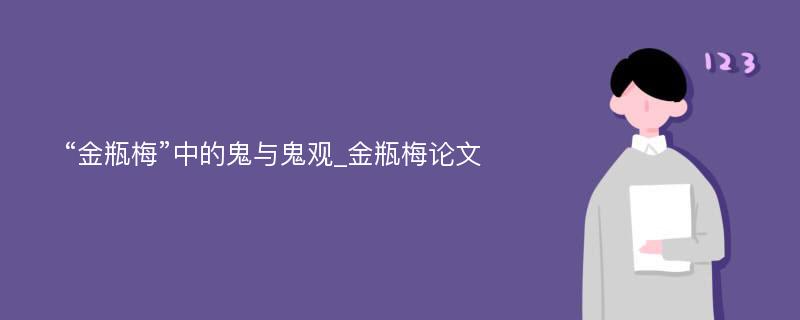
《金瓶梅》求助鬼神观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金瓶梅论文,鬼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古代中国,民间(民众、世俗)佛教和民间(民众、世俗)道教,与民间信仰几乎难以区分。许多佛教徒和道教徒也相信术数。还有很多人自称什么宗教都不信,却参与民间信仰活动,相信术数。由此推断,具有民间信仰和相信术数的人数,比正式皈依佛教、道教的人数还要多,这一点大概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事实表明,民间信仰和术数在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地位虽然远远低于宗教,不过其对民众影响的广泛性却令经典(教团)佛教和经典(教团)道教自愧不如。故而,中国古代文学特别是长篇小说,往往将民间信仰、术数,与宗教一起描写,一起求助。这样的作品数量很大。信手拈来,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不胜枚举。用余国藩先生的话说,叫作“富有宗教主义的作品,俯身可拾”[1]。这类世俗作品的数量虽未精确统计过,但林林总总,若汇辑起来,必将是洋洋大观。
民间信仰和术数的信仰核心和“理论”基础也是鬼神观,与宗教相通。许多术数虽然没有将超自然、越社会的力量偶像化,但其宣扬的神秘性也是一种“神”,所谓玄妙莫测谓之神,故也可以将之通俗地概括为鬼神观。中国古代文学象对待宗教那样,也向民间信仰和术数求助鬼神观,就不是什么天方夜谭的事。我们在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向宗教求助鬼神观的问题时,应当将民间信仰和术数结合起来一并探讨。这里仅以分析《金瓶梅》为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
世俗文学作品《金瓶梅》在引入宗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鬼神观时,采取了直接阐述和融入两种方式。
《金瓶梅》不少地方象一位宗教教职人员向信徒传教一样,喋喋不休地宣扬讲解鬼神观,甚至直接引用佛道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有关典籍。这种直接阐述的方式一般用于夹议、卷首及回头、回末诗词中[2],而频繁地出现夹议、卷首及回头、回末诗词,正是词话和章回小说的特点。鬼神观会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影响人的政治态度、人生态度和道德观念。换句话说,鬼神观只有同人生哲学和政治观点结合在一起,才对人的上述方面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也是这样,鬼神观只有同故事情节结合起来,才能对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手法发生较大的作用。否则,它就几乎仅限于直接阐述的作用,仅限于配合故事情节作一些评论、解释、提示、总结和调节节奏的作用,真正对加强作品主题思想和增强艺术表现能力发挥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这点儿作用可以放到融入方式中一并考察。
《金瓶梅》将宗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鬼神观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和人物塑造之中,最突出的是融入了民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经典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的业力即神灵,为内在神。业报轮回的主体相当于灵魂,即鬼。尽管佛教界内不少学者反复强调佛教是无神论的宗教,我们仍可以称经典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为鬼神观。至于民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满是鬼神形象,称之为鬼神观当更无异议。围绕着因果报应说,《金瓶梅》还虚构了普静禅师屡显异行,潘天师祭星坛引来地府勾批,吴神仙等相面、占卜、测字、查黑书均应验不爽,李桂姐等踏发禁厌奏效、木偶回背灵应以及人死投胎、亡人托梦、鬼魂显灵等情节。通过这些情节,融入了佛道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神迹观、神灵观。总之,融入了鬼神观。
十八世纪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G·E·莱辛曾将欧洲文坛在文艺作品中引入鬼魂的手法称为“运用迷信”[3]。他为什么使用“运用”一词呢?因为欧洲文学不仅求助鬼魂,同时也根据作品的需要对之进行改造。《金瓶梅》求助因果报应说和其它鬼神观时,也要根据主题思想和创作手法的需要,对它们进行了加工、改造,使其有些“走样”。鲁迅先生早已指出,《金瓶梅》引入的佛法不纯[4]。鲁迅主要是说《金瓶梅》引入了民间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与经典佛教相比增加了不少民间信仰的内容,同时也是指出《金瓶梅》作者加进了一些自己的东西。看不到后一种“走样”或“不纯”,就会将融入鬼神观看成直接阐述鬼神观,把世俗作品等同于宗教作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应当看到,融入鬼神观是为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服务的,融入从实质上讲主要是一种写作方法,一种文学手段。是以宗教之石,攻作品之玉。而不是相反,不是用文学去宣传宗教。故而,莱辛使用“运用”一词是非常准确的。本文仿效之,将中国古代文学融入鬼神观的作法称为“运用鬼神观”或简称“鬼神手法”。
《金瓶梅》的鬼神手法遭到过批评,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书中的因果报应说。严厉者斥之为“符合反动统治的宗教鸦片”、“思想毒素”、“思想糟粕”、“最黑暗的内容”等等,温和者指摘其为全书的“缺点”、“无稽之谈”。笔者在撰写《论〈金瓶梅词话〉中的佛道教描写》一文时,也只看到因果报应说在书中的消极作用。
所谓业报、轮回和善因乐果、恶因苦果、善趣、恶趣等内容,是佛教对人的命运的一种解释。它强调人的思想和言行决定自己的命运,鼓励人们行善,恐吓人们不要作恶。这些内容即是鬼神观,也是人生哲学。但主要是鬼神观,人生哲学的内容尚属淡薄和抽象。因为没有明确世间具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即没有明确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时究竟何为善,何为恶。只有加进世间具体的伦理道德标准,因果报应说才对人的思想产生较大的作用。用一种比喻来说,业报轮回说只是一辆车,善恶标准才是这辆车运载的货物。这辆车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运载的货物不同。这辆车是否有价值,主要看它是否运来了对人有价值的货物。所以佛教自己称因果报应说为世间法。用通俗的话讲,因果报应说,是一种针对现世的道德说教。因此,评价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主要应当看它在某个社会,某一时期究竟宣扬了什么样的道德。具体到评价文学作品融入的佛教因果报应说,第一要看作品宣扬的道德内容,第二要看因果报应说对作品宣扬的道德内容服务得是否成功。总之一句话,要作具体分析,一读到中国古代文学作品融入了因果报应说,运用了鬼神观,便拍案斥责,或不屑一顾,这些作法失之简单化。
《金瓶梅》一书,主要宣扬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因此,评价《金瓶梅》融入的因果报应说,首先应当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毫无疑问,在封建社会,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道德也居统治地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就是封建社会的道德的全部。应当看到,封建道德不能与封建社会的道德画等号。须知在封建社会中,农民阶级也有自己的道德观,用以协调本阶级的内部关系。还应当看到,居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封建道德,即儒家道德,亦非伸手不见五指,漆黑一团。因为,除了只维护大地主阶级狭隘利益的腐朽的纲常名教外,封建道德中还有一部分进步的道德规范,另有一部分道德规范制约着人与社会的最基本关系。腐朽的纲常名教,是封建道德中的糟粕,可称之为封建性糟粕。而进步的道德规范属于封建道德中的民主性精华。制约人与社会最基本关系的道德规范为维护全社会的共同利益所必需,任何社会均不可缺少,属于社会公德。封建道德中的民主性精华和社会公德,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与遏制封建统治阶级的虚伪与残暴,稳固社会基本伦理秩序,保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从而对社会发挥一定的积极与进步作用。对于这种作用,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给予肯定,而不应不分青红皂白,一见到封建道德,即当头一棒。当然,平时我们在抨击封建道德中的封建性糟粕时,习惯于简略地称之为封建道德。在不会引起误会时,这种简称与当头一棒不是一回事,无可厚非。
下面展示一下《金瓶梅》的现实主义情节表现了明代的哪些道德规范。
有学者称《金瓶梅》为“黑色小说”,高度评价它“黑得美、黑得好、黑得深刻”,“审丑力是独一无二的”[5]。笔者觉得《金瓶梅》尚不是完全的“黑色小说”,但“黑色情节”确乎不少,将高度评价移用于“黑色情节”更为准确。《金瓶梅》用现实主义“黑色情节”,暴露并抨击了西门庆对损人利己的不义之财的贪求,暴露和抨击了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春梅、陈经济等人损人利己的情欲和损害自己身体的纵欲,同时对受损害的弱者寄以同情。被西门庆、潘金莲害命的武大郎,被西门庆、李瓶儿气死的花子虚,因西门庆贪赃枉法而沉冤不得昭雪的苗天秀,被西门庆奸母和愚弄的林三官,被西门庆迫害的来旺儿和他惨死的妻子宋惠莲,受西门庆玩弄蹂躏的众女性、男性,被潘金莲、春梅、虐待的孙雪娥,被经济摧残而死的西门大姐等,均是受损害的弱者。
儒家道德谴责损人利己的恶行,称之为“不仁”。孔子答复樊迟问仁曰:“爱人”(《论语·颜渊篇》)。孔子答仲弓问仁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仁”正是《金瓶梅》现实主义“黑色情节”所包含的道德规范的核心,也是封建道德民主性精华的核心。张岱年先生将发端于孔子的古代仁爱学说(仁),称为“古代人道主义”,说:“这种人道主义不是革命的理论,但也不是反动的思想。这种学说批判暴虐的苛政,作为一舆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6]《金瓶梅》的现实主义“黑色情节”正是制造这样的舆论。
前面之所以说《金瓶梅》不是完全的“黑色小说”,是因为在“黑色情节”掩盖下,表现正当的人性要求,肯定进步的思想,也是该书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不显山,不显水,但不可或缺。一些学者已经揭示,《金瓶梅》中有一部分现实主义情节描写并肯定了西门庆对利(货、财)的正当追求,描写并肯定了西门庆及其妻妾对情欲的正当要求。比如西门庆诚然是书中天字第一号反面人物,罪大恶极,但《金瓶梅》在谴责西门庆投机倒把、倾轧并吞的超经济剥削和荒淫无耻的性掠夺、性霸占行为的同时,描写他的经济活动中也有一部分是合法的、积极进取的,家庭生活中也有一部分是正常的、感情真挚的。根据《金瓶梅》的描写,潘金莲虽然自私自利,狡诈狠毒,害死武大郎,又纵欲无度,是一个心灵丑恶的人物,但她有时正常的感情得不到满足,精神和肉体均受西门庆的摧残,处于玩偶地位,也值得同情。李瓶儿虽然对花子虚之死负有道义责任,欺侮过蒋竹山,应受一定的谴责,但她背叛只知狎妓的丈夫花子虚,投奔西门庆,却是追求正当幸福的行为。进入西门庆府门之后,她受西门庆蹂躏和潘金莲折磨,变成悲剧人物。现实主义的这种写法是真的,也是深刻的。[7]
晚明文学受以李贽为代表的思想解放运行的影响,在一些观念上冲破了封建道德(糟粕部分)的束缚。《金瓶梅》中的这种写法与这一反叛大潮相呼应。[8]。
孔子虽“罕言利”,但没有否定利,明李贽更提出行仁义为功利的观点,充分肯定功利。其曰:“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藏书》卷32《德业儒臣后论》)。《金瓶梅》描写并肯定对利的正当追求,体现了需家伦理道德中进步的义利观,与明代进步思想家的义利观相通。
孔子重德甚于重色,但不主张禁欲,而是主张以礼驭情。他删定《诗经》,留下许多篇热烈的爱情诗篇。李贽批评受宋明理学守节思想束缚的妇女是“徒失佳偶,空负良缘”(《藏书》卷37《司马相如传》),称赞自由结合的男女“可师可法,可敬可羡”(《焚书》卷4《杂述·红拂》)。《金瓶梅》描写并肯定了人对情欲的正当要求,体现了儒家道德中进步的情欲观,与明代进步思想家的情欲观相通。
由于现实主义情节对财色二字既有否定,又有肯定。因此,现实主义情节对同一个人物往往既无情地暴露与抨击其恶行,又深切地关怀与同情其痛苦,并肯定其正当行为。故而,现实主义情节并不把西门庆五人之死完全归因于贪财与好色,而是写出了诸如官场斗争、社会纠分、家庭矛盾、庸医误人、养生不慎和缺乏知识等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和偶然因素。从而,把五人之死置于大的时代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和封建制度的腐朽。《金瓶梅》的作者主观上并没有深刻揭示这样重大主题的意识。但由于他的许多情节忠实于现实主义的写法,遂使作品客观的思想意义超出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思想水平。
因果报应说以及其它鬼神观为《金瓶梅》现实主义情节宣扬的道德规范服务,只成功了一半,成功在“黑色情节”上。
在《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合谋毒死了武大郎,并轻而易举地逃避了法律的追究。作者施耐庵挥动如椽大笔,驱使武大郎的幽灵向武松哭诉冤情,恳请武松为自己报仇雪恨,导致西门庆和潘金莲成为武松的刀下之鬼,受到正义的惩罚。《金瓶梅》继承《水浒传》这一鬼神手法,加以发展,先安排武大郎和花子虚一起显灵索命,使西门庆惊恐万状,连病带吓而死。又描述武大郎再次显灵,指点武松手刃潘金莲。无论怎样变动,在《金瓶梅》中西门庆和潘金莲二人均逃不出因果报应的恢恢天网,被迫吞下自己种下的苦果。
《金瓶梅》“青出于兰而胜于兰”,鬼神手法对西门庆的惩罚远远重于《水浒传》。表现为虚构爱子官哥儿竟是花子虚转世,然后夭折。虚构西门庆命相克妻,导致爱妾李瓶儿早逝。西门庆生前即已遭到这两次沉重的精神打击。又虚构孝哥儿竟是西门庆本人转世,后在吴月娘因果之梦中被云理守一剑砍死。虽经吴月娘敬佛好善扭转了一些恶报,孝哥儿免于一死,终被普静禅师度化为僧出家而去。西门庆死后落得个家业凋零、断子绝孙的凄凉下场。这种惩罚带有浓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色彩。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这种身后的报应是比死更令人不寒而栗的事。李瓶儿、春梅、陈经济也先后不得好死,也被涂上一层因果报应的色彩,尤以李瓶儿之死被涂的色彩为重。
以上鬼神手法将西门庆等五人之死描写为恶报,加强了现实主义情节对不仁行为的道德审判。尤其是把西门庆和潘金莲之死描写为恶报,使他们为被害死者偿了命,满足读者的愿望。这些与现实主义情节宣扬的道德观念相一致,对完成作品的主题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必须指出,《金瓶梅》的鬼神手法以不得好死的结局严惩西门庆等人,在完成作品主题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缺陷,失败了一半。
鬼神手法对李瓶儿的恶报畸重。不仅让她遭丧子之痛,被病魔熬煎,最终被花子虚告在阴间,命丧黄泉,而且报及来世。宣布她来世为女儿时,“艰难不能度日”,耽搁大龄(按:以明代标准),难以出嫁,好不容易出嫁一富翁,却与夫主年龄相差悬殊,无乐趣可言。刚活到42岁,即“得气而终”(《金瓶梅》第62回)。李瓶儿并不象潘金莲那样有杀人之罪,以害死花子虚为罪由惩罚她是不公正的。她确有好色贪淫之处,但罚不至于此。春梅和陈经济同样如此。这种畸重的恶报,将他们对财富和情欲的正当要求也否定了。
西门庆和潘金莲都有直接的血债,西门庆还有贪赃枉法、霸占妇女、偷税漏税等罪行。按照封建社会的律法,均应处以死刑。鬼神手法以恶死来严惩二人,对潘金莲说是罪罚相当,西门庆是死有余辜。但他们的罪恶不能仅仅由个人的道德来解释。特别是西门庆。西门庆摧残和蹂躏妇女的恶行自然与贪财好色有密切联系,但二者终究不是一回事。如果西门庆不是官僚、富商和地主三位一体的又有钱、又有权、又有势的恶霸,如果没有封建主义的官僚集权制、一夫多妻制、奴仆制和娼妓制度的保护和撑腰,仅仅贪财好色,西门庆怎么能够妻妾成群?怎么敢私用酷刑?怎么能把那样众多的妻妾、婢仆、他人之妻和妓女都霸占为自己的性奴隶?累累恶行,触目惊心。与帮闲应伯爵等人对比一下就会更加明了。尽管这群帮闲无不是贪财好色之徒,但他们绝无造出西门庆式的重罪累恶的能力和胆量。
至于另外几人受恶报而死。更非本人贪财好色之过,因果报应更为不公。孙雪娥受虐待并延伸到最后被逼上吊而死。西门大姐遭丈夫冷落、拳打脚踢,最后也含恨而亡。她们之死是封建大家庭内部激烈矛盾的结果。因果报应说没有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去暴露西门庆的罪恶和解释孙雪娥、西门大姐的死因,所以到底没有表示出对被摧残和柔躏的妇女们的深切同情。
《金瓶梅》的鬼神手法把上述诸人之死畸重地、仅仅地或错误地归结为贪财好色之恶报,实际是否定一切追求“财”、“色”的活动,所获得的效果是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简单化了。《金瓶梅》的鬼神手法虽然对完成作品的主题思想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没有从社会制度的角度去暴露罪恶,在义利观和情欲观上没有冲破封建道德(糟粕部分)的束缚,没有达到现实主义情节反映生活的深度和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同时还宣扬了天命论和出世思想等,对全书的主题也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并存。鬼神手法绝对否定财色,否定了现实主义情节所表现的进步的义利观和情欲观,违背了现实主义情节,这是其一半失败的根源。
其实因果报应说并不一定犯简单化的错误。本来在佛教的因果报应说中,一个人的善业和恶业是可以相互折抵的。这样的说教意在鼓励做了恶事的人弃恶从善,不要丧失对来世的信心。警戒作了善事的人不要半途而废。按照佛教因果报应说,《金瓶梅》现实主义情节所描写和肯定的对利和情的正当追求,属于自他俱利的善业。即使将之列入自利不损他的言行,也属于善业一类,不属非善非恶或难判善恶的“无记业”,也应获善报。《金瓶梅》的鬼神手法没有这样作,说明作者受一切皆空的思想影响很深,说明绝对否定财色正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在。它反映了作者的思想水平。
二
所谓借用鬼神观的外壳,是指文学作品仅借用鬼神观的具有超自然、超社会的性质的神学形式和鬼神形象,而抛弃其宗教内核。所谓抛弃宗教内核,是说抽掉鬼神观自我宣扬的主宰世界和人类的能力,使其丧失被崇拜的资格,使其由居高临下的主宰者下降为作者可以随心所欲裁剪的布料;或原封不动的借用,或在借用的基础上加以增减、组合,再造新形式和新形象。
我国历代鬼神志怪、传奇神魔类文学中不乏借用鬼神观外壳的作品。借用鬼神观外壳的古代小说,以《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最为脍炙人口。学者们曾争论《西游记》到底扬佛还是扬道,各执一端,相持不下。一些学者也曾批评《封神演义》充满了佛道二教争斗的情节,考证书的阐教和截教究竟是道教的哪两个派别。有人批评《聊斋志异》宣扬了鬼神迷信。笔者认为,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即用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去读《西游记》,应该说该书无所谓扬佛或扬道的问题。因为书中的佛、道二教的许多鬼神观形式和形象只是外壳,而且被裁剪过,不代表佛、道二教的本质内容。如果以破译隐喻或密码的方式去读《西游记》,已超出了文学艺术的范围,则另当别论。[9]。《封神演义》和《聊斋志异》也是这样。这三部传世之作当然都使用了一些鬼神手法,但大部分超自然、超现实的情节,都是在借用宗教、民间信仰和术数的鬼神观的外壳的基础上,加以增减、组合,再造新形式和新形象。批评者们把空壳误认为有内核的实体。有知识的佛道教徒是不会出现这样的误解的。他们反而会觉得这种仅借用外壳的方式,对佛道教有失恭敬。
借用鬼神观外壳也是对鬼神观的运用。人们极容易把这种方法与前面分析鬼神手法相混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再宣扬对鬼神观的崇拜,因而应当将它与前面分析的宣扬对鬼神观的崇拜的鬼神手法区别开来。为了区别于融入鬼神观的方法,笔者不再将这种方法称为鬼神手法,而决定命名为“新神话”手法。因其形式及实质均与远古神话相同,故可称为“神话”。但这类神话与远古神话在创作年代和创作方式方面差异很大。它们不是人类幼年时期自发的集体创作,而是人类成年时期主动的个人创作,所以应冠以“新”字,以示差异。当然,编制新神话不一定非要借用鬼神观的外壳不可,也可以完全重新创造新形式和新形象。但本文所分析的新神话手法,特指借用鬼神观的外壳编造新神话的手法。
《金瓶梅》虚构吴月娘在永福寺作因果之梦,在梦中经历了西门庆家庭原应遭到的最后恶报。这个梦对于全局的整个情节来说,纯属“节外生枝”。但这一“枝”形象化地展现了吴月娘和孝哥儿最终结局的另一种可能性,为吴月娘母子的实际结局作铺垫,表现了善有善报的思想。从在书中所处的位置看,这个梦是不折不扣的因果之梦。但是,这个梦本身是借用超自然的梦中经历的形式,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编织了一个孤儿寡母遭遇忘恩负义之徒强暴的故事。
梦中经历并不是《金瓶梅》的创造。佛教《杂宝藏经》卷2的《娑罗那经丘为恶生王所苦恼缘》早已宣扬有关梦中经历的神迹观和灵魂观。借用梦中经历的形式,即借用这种神迹观和灵魂观的外壳,编织新神话,也不是自《金瓶梅》始。唐沈既济著传奇小说《枕中记》,主人公卢生头枕吕翁所授青瓷枕昼寝,作黄梁美梦,梦中经历一世荣华富贵。鲁迅已指出这一故事与《搜神记》中焦湖庙祝以玉枕使杨林入梦事大旨相同。后汤显祖依据《枕中记》改编《邯郸记》传奇,将吕翁改为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其事遂大显于世[10]。唐代另一位作家李公佐著传奇小说《南柯太守传》,主人公淳于棼酒醉后梦入槐树中的蚂蚁国,是为南柯一梦。吴月娘的因果之梦虽然情节简单,但亦不失为一个新神话故事。
一些学者在批评《金瓶梅》的鬼神手法时,将新神话手法也混同在内。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区分鬼神手法和新神话手法。这种区分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在今天也还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笔者认为,如果说对鬼神手法在文学作品的作用应当具体分析的话,那么,对新神话手法就更应该这样作。因为新神话手法只借用鬼神观的外壳,我们应当分析借用这种外壳包裹的内容是好还是坏,包裹得是否精致。黄梁和南柯二梦暴露封建社会官场黑暗与险恶。二梦想象奇特,故事生动,广为流传,深受喜爱。《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这三部新神话小说的内容,从总体来说,都是健康的,进步的,积极向上的。这一点业已经受了历史的检验。有人指出,不同阶级的鬼神戏是不同阶级的戏剧鬼神观的体现。统治阶级用表现迷信思想的鬼神戏,麻痹人民的反抗意志。被压迫者则反其道而用之,常常把鬼神当作武器,进行反抗。被压迫者的鬼神戏,以鬼神为外壳,表现人间生活的内容。[11]。这里所说被压迫者的鬼神戏,当属于“新神话”,其作用显然是积极的。
吴月娘的因果之梦,以吴月娘母子在梦中遭遇的恶报和梦醒后所获善报,直接和间接地继续揭露、谴责西门庆生前的恶行。特别是揭露了帮闲、次要人物云理守忘恩负义、乘人之危、手辣心黑的丑恶嘴脸。虽然是一个小插曲,也向腐败的封建官僚制度狠狠地戳了一刀。这个新神话为完成全书的主题作出了贡献。
借用鬼神观外壳的新神话,有时也难免融入一些鬼神观。鬼神手法和新神话手法在同一部作品中混合使用,鬼神手法中也掺进一点儿新神话手法,新神话手法中也沾染一点儿鬼神手法,这些均不罕见。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复杂。黄梁和南柯二梦不免流露出人生如梦的思想。《西游记》中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封神演义》中正义与非正义双方的英雄们相继一一战死,最后皆按照封神榜上早已确定的位置归位成神。《聊斋志异》一些故事也流露出宿命论思想。吴月娘因果之梦的故事也有些宿命论思想,正是这种情况。
三
艺术创作离不开虚构。《金瓶梅》运用鬼神手法和新神话手法,虚构超现实、超自然的故事情节,增加起伏跌宕,制造戏剧性,塑造人物性格,也有成功之处。
《金瓶梅》叙述潘金莲暴尸街头后,托梦于春梅,哭诉凄凉。此梦引来春梅义葬潘金莲于永福寺,又为春梅日后于永福寺重会吴月娘埋下了伏笔。普静禅师先后两次神秘地出场,均使吴月娘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这些均是鬼神手法对故事情节作出贡献的例子。
书中虚构李瓶儿阴魂三次托梦给西门庆。后两次托梦中,李瓶儿殷殷切切,千叮万嘱,提醒西门庆提防花子虚鬼魂暗害。李瓶儿对西门庆的耿耿忠心和似水柔情,跃然纸上,也有一些李慧娘鬼魂搭救裴舜卿(明·周朝俊《红梅记》)的影子。西门庆也毫不嫌弃李瓶儿已成血污之鬼,与她抱头作长恨之哭。这种表现生死不渝的情节,进一步刻画了李瓶儿痴情、善良的一面,刻画了西门庆的复杂性格,表现他对玩弄的女人也有动真情的时候。花子虚、武大郎两个鬼魂显灵,向仇人索命,就多少显示了一些妓女霍小玉鬼魂向负情郎李益复仇(唐·蒋防《霍小玉传》)的味道。
吴月娘的因果之梦,进一步刻画了吴月娘看重名节、刚强不屈的性格。
《金瓶梅》的鬼神手法也给刻画人物性格造成很大威胁。由于《金瓶梅》现实主义情节如实描写,并无讳饰”,所以它展示了人物性格的丰满、复杂、多层次和多色调。它打破了“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传统思想和脸谱化写法,使人物形象更加逼近现实。因此,现实主义情节对同一个人物往往既无情地暴露与抨击其恶行,又深切地关怀与同情其痛苦,并肯定其正当行为。但鬼神手法绝对否定财色,对西门庆等人一律报以恶死,使人物出现了脸谱化的趋势。由于现实主义情节的描写非常成功,脸谱化的趋势终于未能奏效。
《金瓶梅》运用鬼神手法刻画人物性格也出现了画蛇添足的纰漏。如第12回现实主义情节描写潘金莲因被西门庆冷落,正当的情欲得不到满足,郁闷不乐。鬼神手法将这种心态解释为李桂姐踏发禁厌所致。现实主义情节描写西门庆不久从李桂姐的青楼回到潘金莲身边。这实在是西门庆狎妓暂时腻味儿了,回家来换换口味,而鬼神手法将这种回归解释为潘金莲使用木偶回背木禁厌西门庆产生的效果。这两种解释均违背了现实主义情节,冲淡了对西门庆玩弄妇女的劣行的谴责。幸好这种败笔仅是白壁微瑕,在《金瓶梅》中数量极少,力量很弱,没有对全书造成致命损害。
《金瓶梅》突破了《水浒传》单线发展的艺术结构,采取“千百人总合一传”的新写法,为《红楼梦》网状结构的创新开辟了道路。作者运用多种手法精心编织合传。鬼神手法为诸手法之一,颇具匠心,令评点奇才张竹坡击节赞叹不已。
书末叙述普静禅师在永福寺荐拔亡魂,虚构西门庆等亡魂前来悔罪并一一投胎而去的情节,为千人之传最后作一简要总结,收束全书,画了一条漂漂亮亮的“豹尾”。张竹坡评点说:“且于幻影中,将一部中有名人物,花开豆爆出来的,复一一烟消火灭了去。盖生离死别,各人传中皆自有结,此方是一总大结束”[12]。
这一结尾,产生了“千流归海”的效果,增强了形象性,避免了公文式的枯燥乏味。
为了这一结尾,书中用鬼神手法预埋伏笔,叙述普静禅师于泰山同吴月娘约定,十五年后收孝哥儿为徒。此外,现实主义情节也多处描写吴月娘信佛礼僧。全书结尾时,普静禅师如约前来收徒,为收徒而荐拔亡魂,情节发展显得非常自然。故张竹坡赞曰:
此部书总妙在千里伏脉,不肯作易安之笔、没笋之物也,是故妙绝群书[13]。
《金瓶梅》结构严谨,鬼神手法有功焉。
鬼神手法的结构作用尚不止于有力的结尾和细致的前后照应,还表现在使书中的层次显得清晰。
《金瓶梅》故事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自第1回至第29回,叙述西门庆纳妾发财、家道兴旺的过程。张竹坡将其概括为“虽讲财,却单讲色”[14]。第二阶段自第30回至第46回,叙述西门庆加官联姻、权势鼎盛时期的日常生活。张竹坡将其概括为“虽亦讲色,却单讲财”[15]。第三阶段自第47回至第79回,叙述西门庆亡子丧妻、本人殒命的过程。张竹坡称第79回“总结‘财色’二字利害”,“乃一部大书之眼”[16]。第四阶段自第80回至第100回,叙述西门庆家道中衰,一败涂地。
作者在四阶段的三个衔接处,插入吴神仙、龟卦老妇为西门庆及妻妾们占卜的情节。明代市民阶层打卦问卜是极其普遍的事,富豪西门庆一年占卜几次是不足为奇的。但作者有意写这几次占卜十分灵,通过卦词断语,简要复述了上一阶段的内容,即占卜所宣扬的“熟知过去”,提示下一阶段的情节发展,即占卜所宣扬的“洞察未来”。这种复述和提示的作法,不仅是词话表演的需要,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一次次理清脉络,使“千人合传”层次分明。四阶段的三个衔接处,尤其是前两个衔接处,作者用鬼神手法写占卜,就象画竹画出了竹节一样。
在一些次要关节处,作者也使用了这种手法。如陈经济穷途潦倒之时,水月寺叶头陀为他相面,揭露他荒淫的过去,分毫不爽,又预言他将时来运转,但最终落于凶险。相面后陈经济很快即进入守备府,摇身一变,成为贵戚,与昨日判若两人。最后又成为刀下鬼。相面的断语皆一一应验了。这一鬼神手法的运用,使后21回里代替死去的西门庆上升为新的男主角的陈经济,后半生前后两阶段的戏剧性转折更为突出,前后两部分文字更富层次感。
四
有人批评《金瓶梅》的地狱和鬼魂的形象阴森恐怖,不适于采用。《金瓶梅》中出现地狱和鬼魂形象,是使用以因果报应说为主的鬼神手法和新神话手法不可避免的现象。中外许多文学名著运用地狱和鬼魂形式的程度远远超过《金瓶梅》。可以说,如果不运用地狱和鬼魂的恐怖形式,这些文学名著绝对写不出来。这些名著都没有因为运用了地狱和鬼魂的恐怖形式,而被取消在文学史上应有的一席之地。
中国古典名著如清张南庄著《何典》,完全虚构鬼界众鬼故事,讽刺了封建社会世态人情的鄙薄,故鲁迅称赞该书“谈鬼物正象人间,用新典一如古典”[17]。鲁迅先生对《何典》的称赞,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先后为王品青的《痴华鬘》、刘半农的《何典》点校本题记,一直喜爱绍兴戏剧的两个鬼,即无常和女吊的艺术形象[18]。《聊斋志异》卷10《席方平》一则,写席方平为其父伸冤,亲赴冥界投讼。不想冥界官场腐败如同阳世,“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19]。席方平偏偏拒不行贿,遂在地狱受尽酷刑。文学史家们赞扬这一故事无情地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官吏贪赃枉法的可耻行径,也歌颂了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外国名著如成书于公元二世纪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意大利文学巨匠但丁的代表作《神曲》(全书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部)、英国诗人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英国诗人弥尔顿晚年创作的三部长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波兰诗人密茨凯维奇的诗剧《先人祭》等。“先人祭”是波兰民间为超度先辈的亡魂而举行的一种仪式,与佛教的荐拔仪式类似,人民通过这种活动寄托自己的感情。文学史家的翻译家们异口同声地推崇这些名著,郑重地向中国读者推荐。对这些外国名著,即使在“前十七年”和“文革十年”,也很少有人指摘书中的地狱和鬼魂形象阴森恐怖,不适于采用。为什么要独独批评《金瓶梅》出现了地狱和鬼魂形象呢?
在古国古代,由于宗教、民间信仰和术数影响广泛,加之统治阶级几乎没有为文学艺术创作圈定有关鬼神的禁区,更由于地狱和鬼神形象富于想象,可以借他们之口说出人们想说而不敢直接说的话,故地狱和鬼魂形象为人民群众所熟悉,为他们喜闻乐见。有一些鬼甚至“活”在人民心中。如颖叔考(《伐子都》)和李慧娘的鬼魂被视为正义和复仇的象征。钟馗(《钟馗嫁妹》等)被视为保护人民的鬼王,它立誓要铲平天下的不平,专治恶鬼。这些鬼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受到人民的同情与喜爱,人民不会抛弃他们。表现之一即表演这些鬼故事的戏曲长盛不衰。这种正常现象在左的年代却遭到批判。为此,六十年代,廖沫沙特意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为戏剧《李慧娘》辩护。他也是在为中国古代文学使用鬼神手法和新神话手法辩护。
其实,阴森恐怖的形象、现象、事件等等,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中,不足为奇。人类不可能杜绝所有的恐怖,人的一生大概都会或多或少地经历恐怖。地狱和鬼魂形象是人对现实世界的恐怖心理异化的产物。只要认清这些形象不过是人为的虚构,我们完全可以作到面对它们时不恐怖。即使有些恐怖,也未必是坏事。它可以烘托故事情节所需要的环境和气氛,可以激发人们的想象力。关键不在于恐怖还是不恐怖,而在于地狱和鬼魂形象给作品带来了什么样的作用。近年来,贵州傩戏颇引人注目。傩戏源于傩舞,傩舞源于巫舞。傩戏的内容多为请神驱邪和武将厮杀,所戴面具形同牛鬼蛇神,恐怖之极,却极具审美价值。傩戏也早已从宗教性向娱乐性转化,傩戏演出成为民俗活动,深受群众喜爱。傩戏对我们是很好的启发。总之,地狱和鬼魂形象对《金瓶梅》既产生了积极作用,也带来了消极影响,我们应当分别给予肯定和批判。但无论肯定还是批判,都不是以恐怖与否为依据。
本文开头部分提到的德国剧作家、文艺理论家莱辛曾用寓言、箴言诗无情地讽刺和抨击当时一些教会的腐败和虚伪,并同汉堡牧师葛茨就宗教问题进行论战。正是他挺身而出,为鬼魂形象出现在法国悲剧中大声辩护说:
当然,整个古代是相信过鬼魂的。古代剧作家有权运用这种迷信[20]!我们也应当尊重《金瓶梅》作者和我国古代其他作家们的权利,对作品中的鬼神手法和新神话手法进行客观的、历史的、深入的分析。
注释:
[1]余国藩:《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玄道”》,李奭学译。见《文学与宗教》,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7年9月30日第1版,第291页。
[2]参阅魏子云:《因果·宿命·改写问题——〈金瓶梅〉原貌探索》,见《中外文学月刊[台]》,1985年13卷9期。
[3]参阅莱辛著《汉堡剧评》第11篇,张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19篇《明之人情小说(上)》。《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第9卷,第185页。
[5]宁宗一:《小说观念的更新与〈金瓶梅〉的价值》,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第62页。
[6]张岱年:《仁爱学说评析》,见《孔子研究》1986年第2期,第37页。
[7]参阅马美信:《〈金瓶梅词语〉的时代特征》,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
[8]参阅卢兴苍:《十六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故事——〈金瓶梅〉主题研究》,见杜维沫、刘辉编《金瓶梅研究集》。
[9](明)谢肇浙《五杂俎》认为《西游记》乃“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清)汪澹漪《西游证道书》、陈士斌《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和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均将《西游记》断成丘处机所著的一本纯而又纯的内丹术书。今人王国光在《西游记别论》(学林出版社,1990年)中认为内丹术是《西游记》主要内容之一。另可参阅余国藩著、李奭学译《宗教与中国文学——论〈西游记〉的“玄道”》,见第一届国际文学与宗教会议论文集《文学与宗教》,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第19页。
[10]鲁迅:《〈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83页。
[11]参阅欧阳友微:《戏剧鬼神观》,见《戏剧春秋》1991年第4期。
[12]《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34页。齐鲁书社,1987年11月第版。
[13]《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33—34页。
[14]《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667页。
[15]《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667页。
[16]《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第1269页。
[17]鲁讯:《〈何典〉题记》,见《鲁讯全集》第7卷,第296页。
[18]参阅:《鲁讯全集》第2卷《无常》,第6卷《女吊》。
[19](清)蒲松龄:《聊斋志异》卷10《席方平》,见张友鹤辑校《全校全注今译本聊斋志异》,第13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4月新1版。
[20]莱辛:《汉保剧评》第11篇,第59页。
标签:金瓶梅论文; 西门庆论文; 李瓶儿论文; 文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西游记论文; 水浒传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描写手法论文; 封神演义论文; 神话论文; 民间信仰论文; 佛教论文; 因果报应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