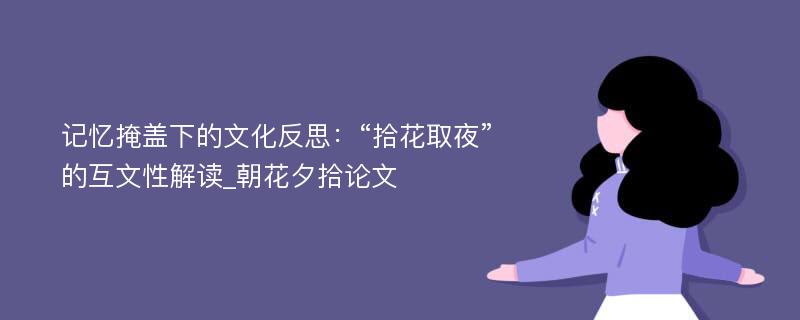
记忆遮蔽下的文化反思——《朝花夕拾》的互文性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朝花夕拾论文,记忆论文,文化论文,互文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批评的重要理论,强调文本与文本间的关系及其所构成的话语空间,它反对自我封闭的文本观,主张将文本置于一个由文学、文化及其他文本所构成的开放体系中予以关照,从而获得对文本存在的多重影响的认识和意义确认。这一理论给予我们一种启示:即在解读一个作家的作品时,应将文本置于一张由诸多文本织成的网中,在文本的互涉对照中认识其同质性或异质性,并在相关性的寻绎中去理解作品的意蕴和内涵。《朝花夕拾》作为鲁迅的一本回忆性散文集,记叙了令他难以忘怀的人与事,是鲁迅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生活的追忆。鲁迅在小引中写道:“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我们往往很轻易地就认同了这一记忆的文本,而又往往轻易地忽视了《朝花夕拾》中文本间的指涉。《朝花夕拾》的文本不是一个自足的封闭文本,而是以回忆与现实的交织,叙述与随感的交融,引用与考据的互释,形成了一种相互映射、彼此关联的开放性对话关系。但鲁迅的娓娓回忆巧妙地遮蔽了《朝花夕拾》文本的异质,同时也遮蔽了记忆外衣下的文化反思内核。
一
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认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① 在他看来,任何文本都是一种互文,每一个文本都包含了其他文本涉及的因素,其意义是在与其他文本交互参照、交互指涉的过程中产生的。《朝花夕拾》的文本意义不仅在于鲁迅对儿时生活的反顾中所体现的浓浓情谊,以及他所构筑的从晚清到民国初年的历史空间,还在于它在不同文本指涉中显示的文化思索。
从创作动机而言,《朝花夕拾》与《故事新编》存在着显著的互文指涉。《故事新编》的开卷之作《补天》本是源于对弗洛伊德的文学缘起理论的一种解释,但在写作中途,鲁迅从报刊上看到封建卫道士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指责,因不耻“伪君子”之行为,笔锋一转,在女娲的两腿间出现了一个穿着古衣冠的小丈夫,由神话传说的阐释转向现实的影射与讽刺,从此奠定了《故事新编》文本的整体讽喻风格。《朝花夕拾》的缘起则与当时现代评论派对鲁迅“仇猫”的攻讦有关,引发了鲁迅对孩提时代的回忆(《狗·猫·鼠》),由此促成了《朝花夕拾》对童年与青少年生活的反顾。两部作品的相关性就在于其创作均因现实而起,1926年的鲁迅试图“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将自己埋于古书之中,“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花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② 但寻“闲静”而不得,现实迫使他在反顾中折返现实。所不同的是,《故事新编》对古代传说的拾取,掺杂着现代人、事、物的“戏说”,重在借古讽今;《朝花夕拾》对儿时生活的拾取,融进了诸多典籍、风俗、传说、掌故,带有明显的思辨色彩。
《朝花夕拾》在整体上是一个记忆文本,而“回忆不是对充满童心的天真、原始人等东西的记忆,也不是对黄金时代的追忆(这个时代从未存在过)。回忆作为认识的功能毋宁说是一种综合,是把在歪曲的人性和扭曲的自然中所能发现的那些支离破碎的东西重新组合在一起。”③ 从此意义上说,回忆不是对过去事物的简单复制,它所追忆的内容是有所选择且重新组合的,同时也必然糅合了回忆者当下的情感及个人经验。因而,《朝花夕拾》的追忆,不纯然是对童年及青少年时代生活片断的简单连缀,而是鲁迅以现时的视角对过往世界的重新审视,是过去与现在、历史与现实的交织所呈现的思想之光。《狗·猫·鼠》中“慢慢折磨弱者”、“媚态”的猫性,《阿长与山海经》中阿长“懂得许多规矩”和“女人的神力”,《父亲的病》中的中医处方,《二十四孝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传统教育,《无常》、《五猖会》的民俗文化,《琐记》中雷电学堂的“螃蟹态度”和“关帝庙”等等,无不体现了鲁迅对封建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行为方式、传统习惯和文化心理定势的反思。
《朝花夕拾》所包含的十篇作品,以及《小引》和《后记》,其本身即构成了一个极有意味的互文体系。《小引》为我们开启了进入《朝花夕拾》文本世界的一扇窗子,《后记》让我们探寻到《朝花夕拾》文本所指涉的历史与文化的背景,而十篇作品的文本相互独立又相互映射,共同织成了一张历史与现实、回顾与刺时相交错的生命成长和情感思想之网。从第一篇《狗·猫·鼠》到最后一篇《范爱农》,各个文本的叙述或零碎或完整,或独立或藕断丝连,在不断的互文中清晰地勾画出鲁迅的童年生活——家道中落——出走异地——日本求学——弃医从文——故乡从教的成长历程,而文本的叙述又总是伴随着鲁迅现时眼光的审视,伴随着鲁迅对成长历程的思索。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细述了一段在百草园嬉戏和三味书屋学习的儿时生活,百草园在童年鲁迅眼中是一个乐园,有菜畦、皂荚树、桑葚,有鸣蝉、黄蜂、叫天子、油蛉、蟋蟀,有传说中的人形的何首乌、美女蛇、可堆雪人、捕鸟;即使在严肃、古板、枯燥的三味书屋,也有“爬上花坛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在教室偷偷“画画儿”的乐趣。然而在饶有趣味的回顾中,却隐藏着鲁迅对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特点之关系的思考,体现了鲁迅对传统教育的反思。如果再将此文本与《藤野先生》文本相对照,两个文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指涉关系。同样是回忆学生时代,同样是记叙老师事迹,其中有一个相类似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前一文本写“我”去问私塾先生“怪哉”是什么?先生说“不知道”,“似乎很不高兴,脸上还有怒色了。”后一文本写“我”的讲义被藤野先生“用红笔添改过了”,“一一订正”且当面辅导。针对学生的疑问,两位先生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前者被动且不容质疑,后者主动且务求理解准确,两者在互文中形成了特定的指涉意义,鲁迅在此所要记叙的已不仅是两位先生的行状,而隐约传达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反思倾向:相对于已走上革新之路的日本教育而言,中国封建教育缺乏的正是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从而揭露了传统文化漠视个人权利、禁锢人们思想的封闭性与落后性。
在《朝花夕拾》的互文体系中,形象的互文也是一大特色。阿长是文本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形象,《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五猖会》均有所刻划,其中又以《阿长与山海经》最为详尽,五个文本共同指向了一个纯朴而粗俗、严肃而可笑、善良而略带狡猾的乡下保姆形象。由于《朝花夕拾》中母亲的缺席,加上阿长的特殊身份,我们几乎可以认定阿长即是文本中对“母性”的一个补充,阿长的懂许多规矩,阿长的“长毛”“美女蛇”传说,阿长的送《山海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开启了童年时期鲁迅的懵懂心智,鲁迅对之是充满浓浓眷意的,“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而另一方面,阿长的迷信,阿长的关于“女人的神力”,又折射出了落后的封建文化因子在中国女性身上所烙下的深刻印记。与之相对应的是父亲形象的刻画,父亲形象主要集中在《五猖会》和《父亲的病》中,《五猖会》中的父亲有些不近人情,在看五猖会前叫“我”背书,以至自己高兴的心境荡然无存;而《父亲的病》中,父亲的两次“沉思”和“摇头”,则写出了父亲颇具人情的一面,父亲知道自己的病已医无可医,不想给日趋艰难的家境添乱,也于“前世的事”无关,只是静静地等待死亡的降临,两个文本形象表面上的矛盾最终统一于肩负家庭重任的“父性”责任上。鲁迅对阿长与父亲的刻画,其实是对人背后的文化的解剖,无论是阿长还是父亲,都背负着传统文化负面因子的沉重十字架。《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可以看作是这两个形象的杂文性互文:“中国的男女,大抵未老先衰,甚至不到二十岁,早已老态可掬,待到真实衰老,便更须别人扶持。”④ 几千年来所沿袭的封建文化和庸陋习俗过早地扼杀了中国男女的生机,鲁迅的思考是感伤而沉重的。
互文性理论在肯定文本间涉的异质性价值的同时,也关注文本间涉的同质性。《朝花夕拾》的所有文本中,有一个关键点是不可忽视的,那就是对人性“恶”的一面的揭示。对人性“恶”的感受几乎贯穿于鲁迅童年到青年生活的始终。如果说《狗·猫·鼠》、《阿长与山海经》里阿长踩死隐鼠说成是被猫所吃,还是一种善意的欺骗,但已给童年时代的鲁迅蒙上了心灵的阴影;而《琐记》中衍太太的搬弄是非,竟成了少年鲁迅逃异地的一个触动点;到了《藤野先生》干事检查讲义怀疑泄题,则让青年时代的鲁迅痛彻地感受到:“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至此,鲁迅对封建礼教、传统教育的反思,提升到对人性的反思高度,由个人的痛楚上升为整个民族的痛苦。回忆原本是为了寻求心灵的慰藉,最后却成了历史的陈述与文化的反顾,这一点也许是为鲁迅自己所始料未及的。
二
在互文理论看来,由于作者在创作他的作品(此在文本)之前,他所涉及的其他作品(他写文本)对他的创作动机、艺术思维等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与改造。《朝花夕拾》的各个文本就大量地吸纳了古籍、传说、时人的评论等“他写文本”,并通过引用、借用、转述、拼贴等技法,对“他写文本”进行改造和重新阐述,从而体现出新的意义指向。如《狗·猫·鼠》中,现代评论派的“鲁迅仇猫”指责、覃哈特博士《自然史底国民童话》的“猫狗成仇”童话、祖母说的“猫是老虎师父”的故事、床头“老鼠成亲”的贴花等等,打破了各自独立的封闭系统,各种关于狗、猫、鼠的他文本相映成趣,既客观地说明了作者之所以仇猫的缘由,表达了对现代评论派无端指责的愤懑,也藉此引发了诸多智性的思考。
引用,作为修辞学上的一个概念,是指有意引用现成的语句以表达自己的观点。互文理论将之引进文学创作与批评,并作为主要的互文手法之一。“引用总是体现了作者及其所读书籍的关系,也体现了插入引用后所产生的双重表述。”⑤ 很显然,引用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对现成语句的复述,不是自闭的、机械的重复,而是经由作者阅读并渗透着作者阅读体验的重新创造。《朝花夕拾》各文本中所引用的“他写文本”较为驳杂,概括起来有三大类:一是时人的言论,如《狗·猫·鼠》对现代评论派陈西滢等人“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不好惹”、“阴险的暗示”等言辞的引用;二是古籍内容的概要复述,如《二十四孝图》讲述“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之事;三是传说、掌故的转述,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转述阿长的美女蛇的故事,《无常》转述无常的唱词等等。第一类为直接引用,一字不改地取之于他文本,二三类为间接引用,即用自己的话语转述他文本的话语,这些引用将作者的阅读与写作两种活动汇聚于一体,呈现出双重表述的意义指向。一方面,透露出了文本写作的背景或动机等相关信息,如“负有指导青年责任的前辈”(《狗·猫·鼠》)、“跳到半天空,骂得体无完肤,——还不肯罢休”(《二十四孝图》)、“绍兴师爷”(《无常》)等等,看似信手拈来的引用,透露出了《朝花夕拾》的写作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有关等信息;另一方面,体现了作者对所阅读文本(他写文本)的理解和创造,使“他写文本”为我所用,并服务于“此在文本”的写作。鲁迅在《朝花夕拾》中对“名人”或“教授”言论的引用,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讽刺的目的,而在复述典籍故事梗概、转述传说故事时,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智性的思考和深沉的反思,这一点又恰恰是《朝花夕拾》文本中呈现最多的。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美女蛇的传说,“结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无常》中对无常的唱词的引用,是为了刻画一个鬼而情的形象,而乡下人“凡有鬼神,大概总要给他们一对一对地配起来。无常也不在例外。所以,一个是漂亮的女人,只是很有些村妇样,大家都称她无常嫂。”这一叙述颇有意味,民俗文化中的无常是人情化的,也是有妻子与儿子的,并不像《玉历钞传》所刻画的那样了无生气,体现了鲁迅的独特思考,正统的封建文化往往漠视人情,缺乏人性关照。《二十四孝图》在转述了“老莱娱亲”的故事后,鲁迅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典籍“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其批判矛头直指封建道统文化。
《朝花夕拾》还有一个重要的互文手法——拼贴,与引用相比,拼贴较完整地将多个“他写文本”并列于“此在文本”中,以突出其片断的同质或互异的特色。《二十四孝图》叙“郭巨埋儿”事,先后拼贴了两个相关的“他写文本”,一是南宋师觉授《孝子传》:“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巨谓妻曰,贫乏不能供母,子又分母之食。盍埋此子?”二是西汉刘向《孝子传》:鲁迅先叙述“巨家是富的,他都给了两弟;孩子是才生的,并没有到三岁。”后直接粘贴了文中原句,“及掘坑二尺,得黄金一釜,上云:天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二文本并列互存,显然不只是简单的事相罗列和同异比照,而自有作者的深意。如果刘向的文本是这个故事的初始版本,由于其年代较早,叙述的可信度也更高;师觉授的文本晚于刘向的文本,由于在流传过程中经过诸多人为的改造,在叙述上会与前文本产生一定程度的背离。而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前人的文本讲“孝”,至少没有以扼杀生命为代价,而后人的文本讲“孝”,却已漠视生命,以剥夺他人的生命来求得所谓的“孝道”,传统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就是在这种可怕的变异中一代代承继了下来,民族的生命力就这样一次次被扼杀,尽管鲁迅并未言明,但互文的意义已昭然若揭。
这种由拼贴而形成的文化反思在《后记》中的呈现更为显著。在探究《朝花夕拾》的文本意义时,我们往往比较重视十个记忆性文本,而只是臆断地将《后记》作为鲁迅搜集考据相关资料的补充性文本,从而忽视了《后记》应有的价值。事实上,《后记》是《朝花夕拾》写作中鲁迅耗时最长的,“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恰恰说明了这决不是一种“闲笔”,而应该作为《朝花夕拾》文本整体性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鲁迅自己也认为:“我本来并不准备做什么后记,只想寻几张旧画像来做插图,不料目的不达,便变成一面比较,剪贴,一面乱发议论了。”《后记》对相关资料的拼贴,正是互文性的集中体现,其拼贴手法也是耐人寻味的,除了文本的拼贴外,还拼贴了大量的图画,营造出图文并茂的效果。
如“老莱娱亲”,鲁迅就将三种不同的版本拼贴在一起。一是“陈村何云梯”的《百孝图》,“画的是‘取水上堂诈跌卧地作婴儿啼’这一段。也带出‘双亲开口笑’来。”二是“直北李锡彤”的《二十四孝图诗合刊》,“画的是‘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这一段;手里捏着‘摇咕咚’,就是‘婴儿戏’这三个字的点题。”三是吴友如画的,“合两事为一”。另外,鲁迅还粘贴了《百孝图》中的一段文字:“……莱子又有弄雏娱亲之事:尝弄雏于双亲之侧,欲亲之喜。(原注:《高士传》)”这种拼贴并不像一般文本那样构成一个连续性的叙事,而是将一个个断续的文字片段和图片文本相并列,文本间隙间的空白产生了相互指涉的互文张力,“拼贴边缘的空白就说明了这一点:它们将两种陈述分开,使得读者不得不暂停下阅读,把目光投射向另一个空间,另一种方式的话语。”⑥ 一方面扩张了文本的历史厚重感,另一方面也增强了反思与批判的力度,由前两个文本的各述一事,到第三个文本的合二为一,揭示了封建礼教逐步完善并进而走向极端的形成过程。而对原注《高士传》中一段文字的考据,无疑是鲁迅对这一形成过程的历史与文化的追问:“我想,这‘雏’未必一定是小禽鸟。孩子们喜欢弄来玩耍的,用泥和绸或布做成的人形,日本也叫Hina,写作‘雏’。他们那里往往存留中国的古语;而老莱子在父母面前弄孩子的玩具,也比弄小禽鸟更自然。所以英语的Doll,即我们现在称为‘洋囡囡’或‘泥人儿’,而文字上只好写作‘傀儡’的,说不定古人就称‘雏’,后来中绝,便只残存于日本了。”如果鲁迅的推测是合理的,那么“弄雏娱亲”中“雏”非但不是“小孩”,甚至连“小禽鸟”都不是,后人的曲解或许是无意的,但为了所谓的道德礼教有意的曲解,则是荒谬而不可原谅的,传统文化正是在这一次次符合道统观念的曲解中异化成了禁锢民族思想的工具。鲁迅在解构历史文本的同时,也颠覆了其中积淀着的观念。从此意义上说,《后记》的意图或许就在于试图纠正十个回忆性文本的叙述指向,在于执著地补充《朝花夕拾》文本的文化反思特质。
三
《朝花夕拾》的互文性还表现在它自身的文体样式上,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文体中,散文体式的互文性是最为显著的。因为散文的文体规则总体上是松弛的,不严格的,其他文体的不同写作方式均可介入散文的文本创作,这种文体边缘性为互文性的构成提供了方便。鲁迅在《小引》中指出《朝花夕拾》的“文体大概很杂乱”,正是对文本中各种不同写作方式的确认。由于每一种写作都有自己的语义潜势,都指向特定的意义表达,因而《朝花夕拾》的文本所杂陈的记叙与抒情、幽默与讽刺、引用与考据等等,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由叙述文本、批判文本、考据文本组成的多层次的立体的文本空间。
叙述文本是《朝花夕拾》的显性文本存在,其语义指向是对人、事、物的记叙。鲁迅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⑦ 它真实地记录了鲁迅从幼年到青年时期的经历和感受,展现了清末民国初期的生活画面。在娓娓而谈的叙述中,体现了对保姆、对师长、对好友的深切怀念,“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阿长与山海经》)“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藤野先生》)“他死后一无所有,遗下一个幼女和他的夫人。……现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儿景况如何?倘在上学,中学已该毕业了罢。”(《范爱农》)其真切之情令人动容。显然,往事叙述和情感抒发的生动与真切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朝花夕拾》的隐性文本意义。
如果说叙述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叙述的抒情的美文,那么,《朝花夕拾》的议论、讽刺、幽默则呈现出了批判性的杂文特色,《狗·猫·鼠》是其中最具杂文体式特征的文本。由于现实环境的纷扰,鲁迅在往事的追忆中,往往借题发挥,不时将笔触指向现实世界,“绅士们”的言行、社会的陋俗、传统的痼疾等等,无一不在其讽刺之列,闪现着社会批判的锋芒。这一批判性文本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不露声色的讽刺,如《无常》一文在叙述了无常颇具人情的故事后,顺带对“名人”、“教授”进行了讽刺:“这样看来,无常是和我们平辈的,无怪他不摆教授先生的架子。”《二十四孝图》描述站在云中的雷公雷母时,顺笔写道:“不但‘跳到半天空’是触犯天条的,即使半语不合,一念偶差,也都得受相当的报应。……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然而究竟很有比阳间更好的处所:无所谓‘绅士’,也没有‘流言’。”《琐记》中写雷电学堂高年级的学生“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可见螃蟹态度,在中国也颇普遍。”在讽刺中达到了批判的目的。二是因压抑不住的激愤,直笔批判的对象。如《二十四孝图》一开篇,就喊出:“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得到一种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因这最恶的心,应该堕入地狱,也将决不改悔,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妨害白话者。”愤慨之情溢之于言表。三是反思性批判。如《父亲的病》针对庸医的药方,议论道:“似乎昆虫也要贞节,续弦或再醮,连做药资格也丧失了。”对传统医学提出了质疑,进行了讽刺。《二十四孝图》由传统儿童启蒙读物,引发了一段融往事与现时、历史与现实于一炉的深沉思索:“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的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但回忆起我和我的同窗小友的童年,却不能不以为他幸福,给我们的永逝的韶光一个悲哀的吊唁。我们那时有什么可看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地翻开第一叶,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在沉痛的回顾中,在中外儿童读物的比较中,对传统启蒙读物、传统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正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文化和蒙昧主义教育在虐杀儿童的爱美天性的过程中,形成了落后的思想意识、文化观念和伦理道德,塑造了麻木不仁、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
除叙述文本和批判文本外,《朝花夕拾》还置入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体式,如《二十四孝图》列举了日本小田海僊所叙老莱子之事,“行年七十,言不称老,常著五色斑斓之衣,为婴儿戏于亲侧。又常取水上堂,诈跌仆地,作婴儿啼,以娱亲意。”又列举了师觉授《孝子传》,“老莱子……常著斑斓之衣,为亲取饮,上堂脚跌,恐伤父母之心,僵仆为婴儿啼。”并注明为“《太平御览》四百十三引”,得出后者“较之今说,似稍近人情”的学理思辨结论。而《后记》简直就是一篇严谨的考据性学术论文,对“马虎子”应作“麻胡子”的考证,对“老莱娱亲”、“曹女投江觅父”、“无常”的不同版本的对比研究,且“或作或辍地几乎做了两个月”,其治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然而,鲁迅并不是单纯地为考证而考证,其间总是伴随着自己的思索,“在礼义之邦里,连一个年幼——呜呼,‘娥年十四’而已——的死孝女要和死父亲一同浮出,也有这么艰难!”“人说,讽刺和冷嘲只隔一张纸,我以为有趣和肉麻也一样。”这些议论显示了鲁迅对封建礼教和腐朽文化进行反思的考据意图。很显然,在《后记》中,鲁迅更感兴趣的和重点关注的是历史文本的阅读与解析,是文本间隙中所难以觉察到的历史和文化的内涵。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文体的界限被彻底粉碎,《朝花夕拾》才真正成为了一个开放的文本体系,叙述、批评、反思达到了相互装饰、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的目的。
可见,《朝花夕拾》的三层文本空间为我们提供了三种形态的话语资源:叙述话语、批评话语和反思话语,与之相对应的是作者的三种身份:回忆者鲁迅、革命者鲁迅和思想者鲁迅。通过这种多元话语、多重身份共存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朝花夕拾》的意义指向和价值旨归是复杂多元的,《小引》所确定的《朝花夕拾》的叙述指向,标识着鲁迅在文本中是作为一个回忆者身份而出现的,但由于回忆的心境不断地被现实世界的“纷扰”所打破,在文本创作过程中,鲁迅又自觉或不自觉地修正着自己的叙述,以议论和抒情传达着自己的好恶感,显示出战斗的锋芒,凸显了具有强烈现实批判精神的革命者姿态。如果说批判基于否定,倒不如说更是一种反思,《后记》无疑是这一反思倾向的极好注解,它标识了鲁迅作为一个思想者,对以古代典籍为代表的传统历史和文化所作的历时向度和文本意蕴的深度思考,回忆者鲁迅最终被革命者鲁迅和思想者鲁迅所替代。
《朝花夕拾》的文本形式是有意味的,它披着回忆的外衣,指涉着现实的世相,隐含着的却是沉重的反思,时空的腾挪与个人的情绪因为互文而统一于理性的思考中,对个人生命经历的微观反顾延伸到对历史、文化的宏观考察。一方面它试图在片断的连缀中建构着一个完整的生活轨迹,另一方面,它又因视角的不断转换和“他写文本”的经常插入而消解着原有的构想。《小引》强调的回忆与《后记》呈示的考据,构成了一种矛盾的互释,但正是这种文本层叠和时空穿梭的微妙编织所形成的思想之网,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寻“闲静”而不得,进而折返现实的躁动心灵,也给我们理解《朝花夕拾》的文本意义留下了互文的想象空间。
注释:
① 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947页。
②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342页。
③ 马尔库塞著,李小兵译:《审美之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④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
⑤⑥ 蒂费纳·萨莫瓦约著,邵炜译:《互文性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97页。
⑦ 鲁迅:《朝花夕拾·小引》,《鲁迅全集》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30页。
标签:朝花夕拾论文; 互文性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论文; 阿长与山海经论文; 二十四孝图论文; 读书论文; 故事新编论文; 鲁迅论文; 父亲的病论文; 小引论文; 鲁迅中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