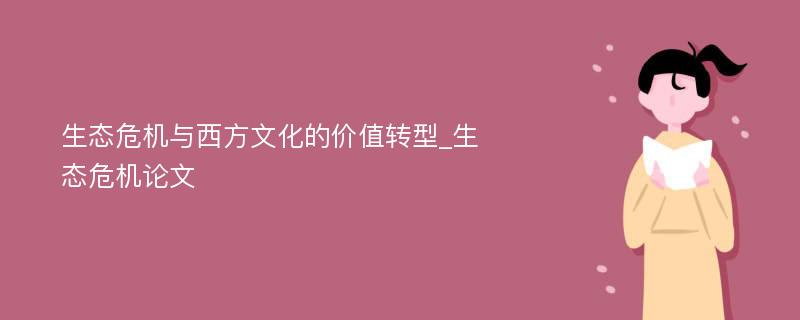
生态危机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文化论文,危机论文,生态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和自然的矛盾自有人类社会起就一直存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环境危机或生态危机最早出现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并且在本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世界范围的工业化而变为全球性的问题。其结果不仅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也把别的物种甚至整个生态系统推到了濒危的边缘。因此,反思危机的根源,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谋求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从6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对生态危机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人们由开始把环境危机归咎为人口、经济、技术等因素,进而认为生态危机是整个西方文明的危机,对危机根源的认识要求首先对西方近代以来的自然观和传统的伦理学乃至宗教神学作出全方位的深刻的检讨。相应地,解决危机的办法也由重视经济、技术的改进,到了倡导整个文化的自然观、价值观念的变革。伴随着环境运动的发展,这些观点和思想在西方社会获得了很大的可见性,并对当代西方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追溯这一认识演变过程,对西方生态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达成一定的理解,对于我们应当有借鉴的意义。
1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环境问题已经是世界发达国家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各种公害事件频频出现,如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水俣病等。70年代以后,环境问题在范围上变得更广,在危害程度上变得更深,沙漠化、酸雨、臭氧层的破坏、全球性气候变暖和物种多样性的减少等,这些严重关系人类和其他生物存亡的现象已触目皆是。
由于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发生在科学技术取得巨大进步、全球经济有了长足发展的时期,因此人们自然从人口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行为的失当等方面去理解环境问题,由此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例如,生态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在他1968年的文章《公共牧场的悲剧》中认为污染问题是人口膨胀的结果。他说,一个孤独的美国拓荒者怎么处置他的废物关系并不大,但随着人口变得稠密,自然的生化过程就会变得不堪重负。因此,自由生育将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1〕在1974年提出的颇受非议的“救生船伦理”(a life-boat ethic)中,哈丁认为发达国家的援助应当给予那些愿意控制人口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就像翻船事故中救生船应先给予那些有力气自救的人一样。
70年代后,从比较综合的角度来理解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有罗马俱乐部的米都斯(D.Meadows)等人在《增长的极限》(1972 年)中所提出来的思想。他们指出人口、食品、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是以指数规律增长的,而地球的承受能力和产出能力是有限的,如果上述五方面的增长不受限制的话,那么在不远的将来,人类的经济增长将达到地球的极限。他们因此提倡一种零增长的模式来避免人类社会的穷途末日。
另外有些学者从经济和技术的角度入手分析环境问题,但是他们看到了在技术和经济背后有着更深层的原因造成了环境和生态的破坏,而经济和技术只不过是这些因素的结果而已。
美国生态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在他1972年的著作《封闭的圈子》中把环境污染的原因归结为新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他指出,从美国的历史上看,大部分污染问题的出现或恶化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这段时间正是战前科学上的理论突破急剧转化为技术,并在工农业生产上广泛应用的时候。在讨论了农用化肥、农药、洗涤剂、化纤产品、内燃机汽车的环境后果之后,康芒纳认为,支配生产的许多技术都是和生态相冲突的,因为技术在解决问题时只考虑一个局部的环节,而生态是个无穷的循环。而且,更为本质的是,“这些污染问题不是产生于新技术中某些小小的欠缺,而正是源于技术在达到既定目标方面的成功”〔2〕,例如,塑料正是因为不易生物降解才对人有用。 由此看来,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即技术是被设计来解决单一的、分离的问题的,而且人们相信,针对每一问题都存在解决办法,这已经是技术社会的一个普遍信念。康芒纳认为技术的这种缺陷来自于其科学基础。现代科学的最重要的方法是还原论,即认为复杂的系统只有被打碎成为分离的组成部分才能得到理解,整体性质是其部分性质的总和。这种还原论的偏见还往往使科学不去关心实际的生活问题,如环境退化等。康芒纳认为以还原论的方法去分析生态系统这样复杂的自然系统是无能为力的,而一种相反的方法,即杜博斯(ReneDubos)等人主张的整体论(holism), 在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关系方面倒是取得了出色的效果。〔3〕可见, 康芒纳已经把生态危机的原因追溯到了现代科学的方法论缺陷,这是对危机认识的一种深化。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 )在《小的是美好的》(1973年)一书中对于西方经济学的环境后果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批评。他 指出,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经济效率、经济增长等已经成了人们最关心的事情,任何反对经济发展的人都会被视为破坏分子或傻瓜。但是,经济学的评价却是一种片面的评价,因为除此之外还有社会的、美学的、道德的或政治的评价。经济学评价的片面性首先在于它只计算事物的市场价值,而不考虑事物自身的、内在的价值,这样,无价的物品标上价格后,就成了没有个性的东西,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经济学上的成功意味着买卖中的获利,而环境的损害是不在经济学考虑范围内的。舒马赫认为,经济学应该了解超经济学(meta-economics),即考虑经济学之外的意义,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比如,商品在质上的区别,即相对于环境的重要性。另外,经济学是受形而上学的影响的,现代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孕育了现代西方经济学,而另一种文化则会有不同的经济学,比如“佛教经济学”。总之,文化价值的目标决定了什么是“经济的”行为。如果我们的目标是追求获利,我们就会用机器代替人力,并采用更高的技术手段;如果我们把人的幸福和自我实现当作目标,我们就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让更多的人能参加创造性的劳动。舒马赫主张后者,并为此提出“中间技术”的概念。在他看来,人们应当因地制宜地采用一种介于先进技术和传统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来安排生产,因为这种技术对资金和人员的要求都比较低,而且是一种能把人的双手和大脑结合起来的具有“人性”的技术,能够适应生态学的规律。舒马赫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入手,但是他认为起支配作用的东西是经济学后面的哲学和价值,因此,他把教育视为最大的资源,因为他认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授价值观念,传播如何对待生活”〔4〕。
2
在康芒纳和舒马赫那里,我们看到,从技术和经济的角度来审视生态危机,最终会涉及这两者背后的科学和文化价值观念。事实上,在六七十年代以后的西方环境主义运动中,从西方社会文化的深层寻找环境危机的原因已形成一种强大的趋势。因为生态危机只不过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的一种表现,而人们如何对待自然,最终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当代环境问题和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植根于代表自然观和价值观的传统哲学、伦理学以及宗教之中。
近代自然观的特征是机械论,它以机器的模型去理解物质和整个宇宙。它把物质看成是由部分(原子)构成的,而原子的运动是由外部力的相互作用引起的,这些运动服从牛顿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各个部分运动的总和就构成整体,就如机器的零件构成一架机器一样。甚至动物和人的身体也是机器,只不过比平常的机器复杂、精密而已。这种机械论的自然观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物,并且和笛卡儿等西方近代哲学家的思想密不可分。和有机论的自然观相比,它的生态学后果是很严重的。
女性主义科学史家、生态学家卡洛琳·默琼特(Carolyn Merchant)在其1992年的著作《激进生态学——探索一个可生活的世界》中认为近代机械科学及其世界观是造成今日生态危机的原因。她认为古代东西方文化及美洲人民都把地球看作一位活的、对人类行为有反应的母亲。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把宇宙概念化为一个活的机体,有着身体、灵魂和精神,把地球设想成一个有着呼吸、循环、生殖和排泄系统的滋养万物的母亲。大多数民族和地球的关系是一种我—你(I—You)伦理的关系,人们在小河上筑堤、砍倒一棵树或挖一个矿井之前需要乞求神灵息怒。但在过去的三百年中,西方的机械科学和资本主义却把自然视为死的、惰性的、可从外部操纵、可为利益而剥削的东西。“自然之死”使得对它的支配变得合法化。殖民地式的榨取资源伴之以工业污染和消耗,把整个地球推向了生态毁灭的边缘。〔5 〕卡洛琳·默琼特的观点代表了许多生态学者的看法:近代科学把自然只看成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因而人和自然的关系只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同他的对象之间的关系,一种我—它(I—It)关系,人对自然的分解和利用并不存在道 德上的禁忌。
不仅如此,近代自然科学本身还被看成是“支配自然”这一意识形态的产物,也就是说,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认识论本身是为了“控制自然”这一目的服务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在其《自然的控制》(1972年)一书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莱斯反对把环境问题看作是一个经济代价问题,他认为“把环境质量问题归属于无所不包的经济核算问题,那就会成为落入陷阱的牺牲品。按照这种思路,结果是完全把自然的一切置于为了满足人的需要的纯粹的对象的地位。这一过程就是那个更深困局的根源,而环境的衰退只是这种困局的一个征兆。”〔6〕这个困局就是“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 因此,他也反对把环境问题归咎于科学技术本身,他认为“现代科学仅仅是控制自然(the domination of nature)这一逐渐广为人知的更大谋划的有利工具”。
卡洛琳·默琼特在她较早的著作《自然之死:妇女、生态和科学革命》(1980年)中详尽讨论了近代科学革命中“机器的隐喻”(the
machine metaphor)和“统治自然”(dominion of nature)的观念的联系。默琼特指出,在西方历史上,自然一直被赋予女性的形象,被看作是有机的,而科学革命受当时社会的、理智的因素的影响,则充满了男性中心色彩,因而,压迫自然和压迫妇女成了一个合而为一的过程。这一过程是由一种“机械秩序”(mechanical order)的出现而完成的。默琼特说:“在有机世界中,秩序意味着每一个部分在更大的整体中的功能,是由其性质决定的,而权力则是通过社会的或宇宙论的等级结构从上到下而扩散的。在机械的世界中,秩序被重新定义为每一部分在一个由理性决定的规律系统中的可预测的行为,而权力则来自于在一个已被世俗化的世界里积极的、直接的干预。秩序和权力一起构成了控制。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理性控制是通过这种新的机器隐喻而实现的。”〔7〕默琼特是站在女性主义和生态学的角度重新审查科学革命和它所支持的机械论自然观的。
对近代自然观的批评必然要求有一种符合生态学原则的新的自然观来取代它。这种替代性的自然观是和机械论相对的整体论(holism),它本身是生态学的产物,并且也从量子力学、相对论、系统论和混沌理论等当代科学中受到启发,而不只是对前科学的有机论的简单回归。它包含这样一些要点:1.每一样东西都和另外的东西相联系。如果把一样东西从生态系统中移走,必定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2.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生态系统具有协同作用,子系统的效应不是简单的线性叠加;3.知识依赖于处境。在整体论中,每一部分的意义都依赖于它和整体的关系;4.过程优先于部分。生态系统是一个开放的、有物质和能量交换的系统,这个稳态的系统与其说是由部分构成的,不如说是由过程构成的;5.人与非人自然的统一。在整体论中,人和其它自然物都属于同一个有机的宇宙系统,不存在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8〕另外, 在这种新的范式中,认识不再是为了控制,而是意味着了解、参与和交流(understanding,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cation)。
3
对生态危机的反思也深刻地触及了西方的传统宗教。因为,自从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 年)中论证新教基督教对于西欧理性化资本主义的诞生所起的正面作用之后,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K.Merton)又论证了清教伦理为17世纪英国科学的体制化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认可(1938年)。因此,基督教与西方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的关联在西方学术界受到普遍承认。而且,虽然现代的西方人生活在一个后基督教时代,但基督教文化中所形成的对自然的态度对他们仍然有着很大的影响。因而,生态危机的原因也必须追溯到基督教。
和前述生态学对近代自然观和批评相联系,基督教主要在这样几个方面受到责难:基督教对自然的所谓“去神圣化”(desacralization ),使得机械论的自然观成为可能;对自然的征服直接来自《圣经》中上帝的命令;基督教神学的二元论教导使人只关心灵魂得救,而忽略肉体和世界,等等。
批评基督教的既有教内的人士,又有教外的人士,其中著名的有美国风景建筑师麦克哈格(Ian McHarg)、环境史学家纳什(RoderickNash)、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及中世纪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T.White,Jr.),而以林恩·怀特1967年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的影响最大。
林恩·怀特的文章旨在理解造成西方生态危机的原因以及摆脱危机的办法。怀特指出每种生物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环境,但是以人对环境的影响最大,而自从19世纪中叶科学和技术“联姻”之后,这种后果也越来越严重。针对人们提出的具体的缓解措施,怀特认为,“除非我们考虑根本的东西,否则,我们特定的措施可能会产生比我们计划要弥补的更严重的缺陷。”〔9 〕这更根本的东西在怀特看来既是要以某种历史的深度来审视那些在背后支持着科学和技术的“预设”(presupp-ositions)。怀特发现,欧洲科学和技术的重大进步应该溯源到中世纪早期,而这种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对自然的实践手段的变化与当时的理智模式(intellectual pattern)即基督教思想是和谐一致的。
怀特首先指出,从教义上看,与别的古代文化不同,基督教从犹太教那里继承的创世故事,把人作为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人虽然是用泥土做的,但他却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所以,人通过命名所有的动物而建立了对它们的统治,而物质的创造物除了服务于人以外就没有别的意义。而且,早在2世纪,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和爱任纽(Irenaeus)认为亚当预表着道成肉身的基督(第二亚当)的形象,人在很大程度上和上帝一样,享有对自然的超越性。怀特认为,基督教不仅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二元论,而且还坚持认为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剥削自然是上帝的旨意。所以,“尤其是西方形式的基督教是世界上所见到过的人类中心色彩最强的宗教”〔10〕。
怀特认为,在实践的层次上,这样的教导必然造成对自然的冷漠和无情。在古代,每一棵树、每一处泉水、每一条小溪、每一座山都有自己的“地方神”(genius loci)即守护神,人们在砍树、 采矿和筑坝之前都需乞求神灵的息怒。基督教由于反对偶像崇拜而禁止将自然赋予神性,随着基督教摧毁了这些异教的万物有灵论,对于剥削自然的禁令也就消除了,因此,人们可以不惮为满足自己微小的奇想而利用自然。
怀特相信正是对自然的这种看法产生了近代科学。在基督教的传统中,上帝给人的启示通过两种媒介,一是《圣经》,一是自然。由于上帝创造自然,所以自然体现了造物主的思想。为了更好地理解上帝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宗教研究构成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在早期教会以及后来的东方教会中,自然主要是一个上帝通过它向人说话的象征系统:蚂蚁是对懒汉的布道,火焰象征着灵魂的渴望,等等。这种关于自然的观点主要是艺术性的,而非科学性的。所以,尽管东方教会保存了许多古希腊的文献,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却很难在这种气氛中发展。而13世纪之后,西方的自然神学却沿着一条不同的路子走下去。它不再是试图从自然物中理解神和人的交流,而是变成通过发现他的创造物的运作方式而理解上帝的心思。所以,从彩虹的研究中得到的是光学知识,而非洪水之后上帝和挪亚立约的见证。西方科学形成期的科学家们从自然神学中汲取的养分使人们有理由相信“近代西方科学产生于基督教神学的母体”。因此,就基督教神学和近代科学的关系,以及科学、技术的联合对于生态环境的后果而言,基督教对我们时代的生态危机应负有巨大的罪责(bears a huge burden of guilt)〔11〕。
在追溯了“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之后,林恩·怀特又提出了自己对解决危机的见解。首先他对认为只要使用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就能避免生态灾难的观点表示怀疑。其理由是,科学技术是从基督教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看法中成长起来的,如果不改变这种至今仍有大量信众并影响着社会文化的宗教,那么真正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用怀特的话说,“除非我们找到一种新宗教,或者重新思考我们的旧宗教,否则,更多的科学和更多的技术将不会使我们摆脱目前的生态危机。”〔12〕
林恩·怀特的文章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在西方生态运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把生态危机的原因引到了作为西方文化传统核心的基督教上,对基督教的生态学批评使很多的基督教学者重新思考在基督教信仰中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他们必须重新考虑《圣经》的教义和神学,重新审视基督教的历史,以便回应和反驳怀特的责难,其结果是掀起了一场生态神学(eco-theology)的浪潮,使得生态思考成为当代基督教思想中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生态神学的效果是双向的,一方面,它试图发掘基督教神学和历史传统中的生态学思想的资源,使基督教绿色化;另一方面,它又以独特的神学立场为人们关心自然提供理论基础,并且通过教会对信徒的影响而在环境运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还有一些人不相信基督教能够提供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基础,从而在别的宗教中寻找生态保护的思想资源,其中最受重视的有美洲印第安人的万物有灵论、东方文化如中国的道教、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日本的神道和禅宗等。由于这些东方宗教的输入,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一场具有很强生态意识的准宗教运动,即所谓的“新时代运动”(New Age Movement)。这一运动信仰超自然的力量,倡导以原始方法增进人对生命的体认,开拓自身的潜在力量。它的思想和实践都很庞杂,没有严格统一的规格,大致说来常常包括这样一些:环境保护、性别平等、素食主义、瑜伽、冥想、超觉静坐、各类传统和非传统的灵修生命、气功、自然疗法、草药、古代文明和知识的复兴等。〔13〕而把自然对象包括人重新赋予神性是新时代运动的最基本的特征,这一点常常被称为自然的“再着魅”(re-enchantment),是对基督教和近代科学对自然的“去魅”(disenchantment)的一种反动。这样,人对自然的关系不再是冷冰冰的控制和被控制的关系,而是一种有交流的内在的生命关系。因此,新时代运动在这一点上和激进的环境主义是一致的,以至于有人将绿色运动同新时代运动相等同。〔14〕
现在,从宗教信仰出发的环保思想和实践已被广泛地称为“灵性生态学”(spiritual ecology), 成了当代生态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4
环境危机还对西方传统的伦理学提出了重大的挑战。传统的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中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以及集体与集体之间的行为规范,认为道德主体只限于人类。而当生态危机促使人们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人对自然如何行动才合适的时候,人们已开始把道德考虑的范围扩大到动植物和人类环境,这种以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伦理学就是环境伦理学,它在70年代的出现是伦理学的一个突破。按纳什的看法,“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应被视为由伦理学调节和约束的道德问题,这一观念的出现是最近的理智史上最超乎寻常的发展之一。”〔15〕
但是在环境伦理学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仅仅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待环境和资源,从人类利益考虑,认为保护自然是对的,滥用自然是错的。这是本世纪初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出发点,也是某些人道主义者反对虐待动物的理由。这样的环境伦理学虽把环境考虑在道德抉择的范围之内,但其范畴和立场并没有超出传统的伦理学。另一种观点不同于旧的功利主义的资源保护主张,它认为自然具有内在的价值,而不只是工具价值,因而至少具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保护动物不是出于人类的私利,而是由于它们自身的权利。虽然自然物没有能力要求这种权利,但我们人类可作它们的道德代理人,有责任表达和捍卫它们的权利。这种思想的环境伦理学通常被称为“生物中心主义”(biocentri-sm)、“生态平等主义”(ecological egalitarianism)。而与此相 对的前一种思想则被称为“人类中心论”(anthropocentrism),因为它认为人是所有价值的尺度。纳什认为正是这种不同,标志着美国本世纪初的资源保护运动和六七十年代的环境主义运动的区别。
卡洛琳·默琼特也按照伦理主体不同把伦理学划分为自我中心或个人中心伦理学(egocentric ethics)、人类中心伦理学(homocentricor anthropocentric
ethics)和生态中心伦理学(ecocentric eth-ics)。个人中心伦理学基于个人的权利,认为凡对个人为善的对社会 也有益,因此个体的利益高于社会的利益。在生态方面,个人只要不影响其他个人,就可以榨取和使用自然资源以增进自己的利益。默琼特认为,个人中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把个人视为隔离的、但是平等的社会原子,植根于17世纪机械论科学中,反映了机械主义的世界观;人类中心伦理学以社会为基础,如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和穆勒所主张的一个社会必须以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行动原则。人类中心伦理学和哲学基础有机械论的(牛顿科学),又有整体论(达尔文理论);生态中心伦理学以宇宙或生态系统为基础,整个环境,包括非生命元素如岩石和矿物,和动植物一起,都被赋予了内在价值。它从生态学中寻求解决伦理困境的指导,其目标是维持自然的均衡,保持生态系统的统一、稳定、多样性与和谐。在生态中心伦理学中,所有东西不管有无生命,都和人类一样享有道德可考虑性(moral considerability)。 生态中心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以生态学原则为基础的整体论。在这样一种生态中心伦理框架中,人们可以提出“岩石拥有权利吗?”这一类的问题。而在纳什看来,其回答显然是肯定的:“我们可以设想岩石同人类一样,拥有在其自身中并属于其自身的权利(rights in and of themselves)。因此,受到保护的是岩石的利益,而不是人类在岩石中的利益。”〔16〕
生态中心伦理学一方面建立在现代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圈内一切生命处于平等、共生的关系之中的基础上,另一方面也从西方基督教传统以及与其有密切关系的自然神论、泛神论、超验主义等思想中吸取了丰富的养分。 对这种生态伦理学有过重要影响的思想家包括梭罗(HenryDavid Thoureau,1817—1862)、缪尔(John Muir,1838—1914)、史怀泽(Albert Schweizter,1875—1965),以及以提出“大地伦理” (the land ethnic)著称的、 被誉为环境伦理学之父的美国生态学家阿尔多·列奥波德(Aldo Leopold,1887—1948)。
生态伦理学现在已经为许多环境主义者所认可,被当作判断人对环境的行为是否正当的价值基础:如列奥波德在《大地伦理》中所说的,“一件事情当它倾向于保持生物群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和美时就是对的,反之则是错的”。和传统伦理学相比,生态中心伦理学的激进之处表现在它对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激烈批判上,有人(如Paul W.Taylor)甚至认为,在某些情况下扼杀一朵野花的错误比另外一些情况下杀死一个人的错误还要大。由此可见生态中心伦理学和传统伦理学差别之大。
以上我们看到,对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认识已经深入到了西方文明的核心,生态学也因为提供了批判传统的哲学、宗教和伦理的价值基础,而被称为一种“颠覆性的科学”(a subversive science)。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生态原则为指导的整体论、环境伦理学以及所谓的“灵性生态学”并不是孤立的,它们正在融合成为一种“深层生态学”(DeepEcology),试图“超越一种有限的、零碎的、 浅层的对待环境的方法,尝试表达一种综合的、宗教和哲学的世界观”〔17〕。
当然,这种深层生态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除了它内部主张的不统一、甚至矛盾(比如同属“灵性生态学”的基督教生态神学就和新时代运动格格不入),它在科学技术和生态破坏的关系的看法上有失偏颇之外,它还需面对如何协调其激进的生态中心观点和基于“合理的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s)的主流环境运动的问题,等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人们对解决生态危机的迫切要求,这些观点和见解也影响越来越广,发挥越来越大的规范作用,并且逐渐地成为当代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与此相伴随的环境和生态问题也非常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观在我国受到了越来越高度的重视。我们在经济、技术的层面上重视环境问题的同时,还应加强思想和意识层面的环境和生态教育,应该研究和利用已经受到西方生态运动重视的我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在这方面,西方对于生态危机的反思无疑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注释:
〔1〕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Science,162(1968):pp1234—1238.
〔2〕Barry Commoner,The Closing Circle:Nature, Man andTechnology,Alfred A.Knopf,Inc.,1972,p 185.
〔3〕Ibid,p190.
〔4〕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0页。
〔5〕〔8〕Carolyn Merchant,Radical Ecology: The SearchFor a Livable World,Routledge,Chapman & Hall,Inc., 1992,pp41—42、76—78.
〔6〕W·莱斯著、岳长龄等译:《控制自然》,重庆出版社,1993年,第3页。
〔7〕Carolyn Merchant, The Death of Nature: Women,Ecology and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Harper & Row,1980,pp192—193.
〔9〕〔10〕〔11〕〔12〕Lynn White,"The Historical Rootsof Our Ecologic Crisis",in Ian Barbour ed. Western Man andEnvironmental Ethics:Attitudes Towards Nature and Technology,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93,p18、25、27、28.
〔13〕〔14〕郑建生:《另类绿色手册——新纪元初析及绿色运动》,香港卓越书楼1995年,第58、56页。
〔15〕Roderick F.Nash,The Rights of Nature: A Historyof Environmental Ethics,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4.
〔16〕Roderick Nash,"Do Rocks Have Rights? " The CenterMagazine (Nov/Dec 1977),p10.
〔17〕Bill Devall,George Sessions,Deep Ecology: LivingAs If Nature Mattered,Peregrine Smith Books,1985,p65.
标签:生态危机论文; 伦理学论文; 自然观论文; 基督教论文; 生态环境论文; 生态文化论文; 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生态学论文; 科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