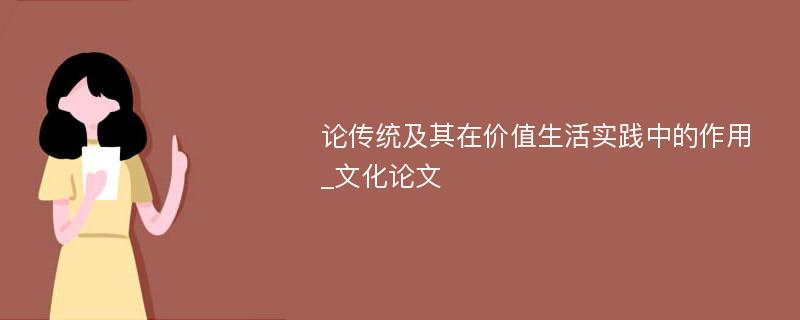
论传统及其在价值生活实践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用论文,传统论文,价值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1)03-0001-05
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以创新、创造为旨趣,以变革世界、完善自己为目标。但这种创新、创造并不能“凭空”进行,它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必然会遭遇人们面对的各种文化或文明的历史传统。如何理性看待历史传统,充分发挥传统的积极作用,避免消极作用,是当代人经常会遇到的一个时代课题。
一、传统是传承到“现在”的“过去”
“传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历来存在着许多含混、模糊的见解。择其要者,有人认为,传统就是生活在“过去”的“古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成果;也有人把传统等同于有些年头的文化形式,特别是以文字、书本形式存在的圣贤之言、祖宗之法、文献典籍;持这类观点者坚持,传统意味着曾经的光荣与梦想以及历史的前车之鉴和经验教训,“尊重传统”意味着怀旧、向古人致敬,“弘扬传统”意味着崇古复古。很明显,这类将传统静止、凝固化的理解倾向保守。与之相反,有些“进步主义者”则视传统为“过去的东西”甚至“死了的东西”,斥之为“陈旧、落后、保守”,认为传统阻碍将科学和理性运用于人类事务,阻碍现代化和人自身的发展,因而对传统不屑一顾,亟欲破之去之而后快……实际上,这两类迥然相异的看法都曲解了传统。它们共同的问题在于,是用形而上学孤立、静止、凝固、僵死的观点理解和解释传统,而不是运用辩证法、深入人们自身及其价值生活实践审视传统,并且忽视了传统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流变性。
从词源上说,“传统”的拉丁文是traditum,英文是tradition,其本意系指从过去延续、传承到现在的事物。从结构上看,传统是极其丰富、复杂、多面的,既包括实存性的内容,也包括价值性的内容。希尔斯指出:“传统——代代相传的事物——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惯例和制度。”[1]16当然,人们经常所指的传统,更常见的是在人们具体的历史的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且世代相传的制度、思想、观点、习俗等文化内容和形式。也就是说,传统主要体现为活生生的“文化价值之流”——在历史长河中流动着的文化和价值。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对文化传统和传统不加区分。
传统是动态的,具有流变性,是流传到现在“活着的”过去。过去已死的人类创造,无论是实存性的还是价值性的,因为已经死亡,没有传承下来,在现实社会中已经不具有影响力和支配力,因而我们不再称之为传统。这一点十分简单,但却十分关键。否则,讨论传统就如同在故纸堆、博物馆中流连,甚至类似于在荒郊野外掘墓考古了。因此,尽管不同的人可能对传统的具体表现会从不同方面加以理解和归纳,无论如何不能偏离如下关键之点——传统是把人们的过去和现在相联系、连接起来的那些社会文化因素和方式。
可以说,传统就是人们价值生活实践中面临的一种丰富复杂的历史联系——“过去”与“现在”之间的联系:传统是传承到“现在”的“过去”,是过去形成的、但仍然“活”在“现在”、具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那些历史因素。具体说来,这可以进一步从如下一些方面加以阐释:
首先,从时间上看,传统源自已经逝去的人类历史。大凡传统,总有一个历史的积淀、“传承”过程,是历史地形成和积淀下来、经历了一定传播和承继过程的因素。人们当下的价值生活实践的内容和形式,由于未经时间风雨的洗礼,没有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称不上传统。即使是现时代勃兴的那些时髦的、时尚的潮流、风气等,无论如何普及流行,无论如何蔚然成风,也称不上传统。
其次,传统实质上与当代人并不“相隔”。传统源自历史,流传至今,“活”在当代人现实的价值生活实践之中。当然,时间和历史是无情的,它必然会淘汰许多传统,遗忘许多传统。就算是古代圣贤的经典训诫,就算是封建帝王的“金科玉律”,就算是英雄人物的行事方式,只要没有被时间和历史承认,没有真正流传下来“活”在当代人的心中,它们就不再成为传统。也就是说,它们“失传”了,从历史中默默地消失了。同时,就算有些内容是后来的、外来的,时间并不太长,但如果它融入了当代人的价值生活实践,改造了民族文化和人们的社会心理,那么也会成为传统的新鲜血液,成为传统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传统并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不断吐故纳新中充实和改变着自己的内涵,在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中不断“流变”、“生成”。
再次,传统往往具有自身的历史连续性和内在发展逻辑。只有在发展中,传统才能得以保持、流传、发扬光大。但传统的历史“传承”(包括消亡、复活或弘扬等)过程并不是随心所欲、毫无规律的。在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下面,无形中似乎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因素——诸如“血脉”、“道统”、“灵魂”、“精神”——制约着传统的“流变”、生成。正是“血脉”、“道统”、“灵魂”、“精神”等内在要素,将历史发展中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聚合、融贯在一起,将传统展现为一种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多样性的统一,变化中的“不变”。
最后,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传统“流变”、“生成”的核心实际上是人,特别是当代人的价值生活实践。从方法上看,发现传统并发挥传统的作用,必须以“现在”为坐标,以当代人为对象,而不是局限于既往的过去,发思古之幽情,厚古薄今。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尽管多少有些偏颇,却具有一种“片面的深刻性”:把握历史传统,必须从当代人自己的现实出发,而不是从古人出发;必须以对当代人自己的认识为参照,从现在追溯过去,而不是脱离现实,按照主观意愿有选择地回顾、剪裁。可见,传统源自“过去”,却不是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古董”,更不是沉睡发霉的历史文化典籍;“传统的本质是真正的现在;传统是通过对现代人的制约和支配而获得自己的规定性的。”[2]传统是以“现在”为坐标、向“过去”追溯、向“未来”开掘所发现的文化联系;或者说,是由过去的人们创造的,内化在当代人身上,在当代人“现在”的价值生活实践中“显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也正因为如此,“古已有之”的东西,如果已经没有生命力,已经死去,就不再是传统;只有在现实社会中仍然“活着”并发挥作用的既往存在,才是真正现实而非虚幻的传统。至于解释传统、弘扬传统、变革传统、创新传统,更是只能以“现在”为坐标,以“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活动”为依托[3]105-108。
二、传统与当代人的价值生活实践的互动
如何对待这些“活着的”历史因素?如何看待传统在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中的作用?历来也存在争议。我们认为,分析的焦点在于是否立足于当代人的价值生活实践,是否真正理解和尊重当代人的权力和责任。
人是文化的动物,也是历史的产物。我们也可以说,任何人本身都是一定文化传统的产物和体现。人们从历史走来,绝不可能割断与历史、文化的关系,绝不可能抛弃、脱离、割断自己的传统,非历史地展开自己的价值生活实践。希尔斯指出:“没有传统,人类便不能生存,即使他们司空见惯地不满于他们的传统。”[1]429虽然具体的传统因素可能断裂、可能消失、可能死亡,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与任何传统因素相联系,区别只在于谁的、什么样的传统。
传统是传承到“现在”的“过去”,是活跃在“现在”的历史因素,是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的既在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4]585传统已经深深地烙印在深层文化结构之中,成为人们活动的历史条件之有机组成部分。每一代人、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从零开始”凭空从事新的价值创造,而总是生活在某种既定的文化传统中,总是在前人的创造成果的基础上,从既定的历史条件出发进行创造。
传统是有力量、有韧性的,它通过内化到人的内心,顽强地塑造、提升、变革人自身。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中的人,不论其对本民族的传统态度如何,由于他孕育、成长于这一传统母体之中,因而都不可能是外在于这一传统的人。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4]585咀嚼历史我们发现,即使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都不可能反对一切传统,与一切传统彻底决裂。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往往与传统保守主义者一样,身上带有深深的传统的烙印,有时甚至比后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有时他们会以最具传统特色的方式反传统。这实际上说明,传统本身是深沉的、多面的,有着坚韧的性格和“不同的面孔”。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常常两极相通,呈现为同一个硬币的两面[3]107。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如果利用得当的话,传统甚至可以成为资本,即布迪厄所谓“文化资本”的一部分。“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5],参与具体的历史的价值生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传统不仅可以凝聚社会或组织成员,为发展与创造营造良好氛围,而且可以直接提供思想资源,给予人们启迪性的灵感。许多文化创意产品和产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就是例证。
当然,上述过程都不是传统的单向的作用,而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也正是在这一互动过程中,旧的传统才被“大浪淘沙”,“优良传统”才被发扬光大,新的传统才开始酝酿形成,人们的价值生活实践才获得了进步的阶梯。
立足自身的价值生活实践评估传统、利用传统、改造传统、为传统贡献新的资源,既是每一代人的权力,也是每一代人的责任。实际上,每一代人不仅身处传统之中,而且在自身的价值生活实践中,评估、消化着自己的传统,筛选、改变着自己的传统并根据新的时代背景和生活境遇,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和价值。人是文化和价值的主体。而人是由世代相续、前仆后继的无数个人构成的,没有一代代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重新反思、选择、消化和改造,传统就会沦为僵死、固定的东西,不可能“活着”、“传承”下去,更不可能发扬光大。这正如希尔斯指出的:“传统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着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类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传统。”[1]19
当然,面向未来的价值生活实践,我们绝不应该一味固守既定的传统,沉迷在具有历史惰性的文化传统中而不能自拔。科学、理性地对待传统的态度是,立足当代人自身及其价值生活实践,高扬人们自身现实的权力和责任:既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有自尊自立自强的意识,敢于肯定和弘扬传统中一切合理、精华性的内涵,并将之发扬光大;又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有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敢于否定和扬弃传统中一切落后、糟粕性的内容。特别是要在反思过去和现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确立、改造优秀文化传统,并在创造性的价值生活实践中,创造更合乎时代特征、更合乎实际情况、更具想象力的新传统。这种创造活动本身,也就是在塑造“未来的传统”。
三、保守主义及其对价值生活实践的影响
在历史与现实中,人们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往往存在许多误区。这令社会和个人都付出了许多代价。其中最常见的误区,是单纯用美化了的“过去”解释历史传统,对传统持单纯讴歌、全面肯定的保守主义态度。
或许有人会辩解,几乎所有文化传统都具有保守性。这种保守性几乎用不着刻意灌输、培养,它似乎是所有文化传统与生俱来的“天然”惰性。咀嚼历史与现实,我们确实不难发现,文化传统愈是源远流长就愈是博大精深,愈是成熟发达就愈是影响深远,它的保守惰性就愈强,相应的守旧势力就愈强大,愈加根深蒂固。当浸淫在这种文化传统中的人们不够清醒、自觉时,就愈是容易背上沉重的“历史包袱”。这可以从如下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盲目乐观,骄傲自满,夜郎自大,让缺乏理性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文化优越感随意泛滥。例如,中华五千年文明在历史上就曾经滋长出“中央之国”、“唯我独尊”、“天下第一”的心态,有些人曾经表现出一种“无知的傲慢”或“虚骄”。他们认为,中华帝国不但无须向其他民族学习(典型的如乾隆皇帝所谓“天朝之大,无所不有,无需与尔等夷狄互通往来”),而且负有普及自己的文化价值观、教化“四夷”之责。“用夏变夷”被认为是常理,而“用夷变夏”则是当然的大逆不道。今天强势的美国或西方,借助其现代化成就和科技、经济、军事上的领先,向全世界渗透、推广其政治模式、文化价值观念,表现出的是同样盲目的“无知的傲慢”,是同样缺乏理性论证和实践检验的文化优越感。
其次,与盲目乐观的文化优越感相联系,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自我封闭、自我美化、孤芳自赏。在落伍挨打的近代中国,有些人顽固地坚持: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中国均“古已有之”。如早就“发明了”足球,早就有了电子计算机(算盘),早就提出了系统论……现在和未来需要的一切,过去无不齐备,只待发掘。在黄遵宪“泰西之学,其源流皆生于墨子”之中,在孙中山“外国现在最重要的东西,都是中国从前发明”的论断中,在当今的各种“传统复兴论”(“儒家复兴说”、“道家复兴说”等)中,都能看到这种心态的某种反映。
再次,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甚至“尊祖法宗”,“向后看齐”,复古倒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先师孔子就是典型的崇古复古派。孔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已逝的周朝一切都是那样美好,令人心向往之,值得效法;至于周朝,则是从更古老的尧舜“二代”承继而来……孔子愤世嫉俗地指责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主张“从周”,以周礼作为治世的规范和标准,“克己复礼”。自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孟儒学成为万世经典,“尊祖法宗”、“向后看齐”、复古倒退蔚然成风。近代以来,虽然国运不济、落后挨打、屡遭劫难,但复古守旧之声仍不绝于耳:“中国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旧”,因此正确的选择只能是“宜考旧,勿厌旧;宜知新,勿骛新。”由是可见此风之盛,传统保守主义之顽固!
第四,封闭保守,盲目排外,拒斥其他文化传统、甚至新的时代潮流。胡适指出,文化的这种保守性,既能对内抵抗各种新奇之风气的兴起,对外则能抗拒外来文化思潮的侵袭。在历史与现实中,即使是那些希望变革、创新之士,为了减少阻力,往往也需要抬出老祖宗“托古改制”、暗度陈仓。马克思曾经对此有所论述:“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闻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他们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4]585历史上类似的事例屡见不鲜、不胜枚举。例如,王安石变法时,一再推崇孟子及其仁政学说,提倡所谓“法先王之意”、“法先王之政”,利用复古招牌来推行新政;近代康有为更是用心良苦,为了变法维新、堵住守旧派们的嘴,他费尽心力对儒学经典进行考证,创作了长篇《孔子改制考》,将孔子描绘成“托古改制”的先师,以所谓儒学真谛作为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武器[3]195-196。
应该说,保守主义所体现的强烈的民族主体意识、自尊感和自信心,有其合理性和积极意义。然而,这种观点却站不住脚。例如,保守主义对传统存在误读,它往往热衷于从古代文献典籍中寻找“优良传统”,似乎越“古”、越“老”、越“旧”就越有资格代表传统;它往往只看到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甚至片面、绝对地夸大这一部分,对其中消极的糟粕估计不足,甚至视而不见。究其实质,保守主义态度的失误在于其“向后看”的视角和思维方式。一根筋式地回头“向后看”,看见的只能是逝去的古人和成堆的古籍,坚持的只能是历史退步观和“死人的支配权”[1]32。这种复古主义把价值选择的方向和标准定位于过去,把主体的权力和责任都赋予前人和古人,在盲目推崇、刻意美化既往存在的同时,忽视或者否定了当代人的权力和责任。这种迷信“过去”、厚古薄今、崇古非今的态度造成了严重的“主体自我迷失”,令当代人迷失在虚幻灿烂的历史辉煌之中,失去了批判的理性和前进的方向。
四、虚无主义及其对价值生活实践的影响
与保守主义针锋相对,对待文化传统的另一个误区是全面贬斥、全盘否定、彻底摒弃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在价值生活实践中,这种观点视自身的传统为落后之本甚至万恶之源,认定他人的文化传统才是优越的,才具有普适价值,才值得学习和效法。在方法上,它不耐烦对自己及其价值生活实践进行认真反省、分析,更对独立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缺乏信心,而是希望“走捷径”,借助“向外看”,发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借助从外“进口”,“取人之所‘有’,以补己之所‘无’”。在历史与现实中,这类人为数还真不少,如有些人“言必称希腊”,动辄“西方如何如何”;有些人盲目崇外,感觉“月亮也是外国的圆”;有些人见到外国的东西就欣喜“拿来”,生吞活剥,毫无批判地硬搬和模仿;更有一些人自觉、公开地主张“殖民地论”、“全盘西化论”。
“全盘西化论”是典型的彻底的不折不扣的虚无主义。中国的“全盘西化论”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五四运动以后更是屡生波澜。在落后而被动挨打,痛感文化传统的落伍并进一步提出“打倒孔家店”、倡导“民主”、“科学”与现代文明的同时,有些人将西方文化视为唯一先进的文化,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唯一楷模,从而采取了一种极端肯定(西方)的方式。其代表人物可推胡适和陈序经,尽管他们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胡适在《独立评论》第142号的《编辑后记》中认为,“现在的人说‘折中’,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文明。”陈序经在《独立评论》第160号《全盘西化的辩护》一文中,更是情绪激烈地宣称:“百分之一百的全盘西化”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国文化的一条更为完善、更少危险的出路。当今的全盘西化论者更为大胆“热烈”,毫不隐晦,有人干脆提出,既然美国经济最发达、政治最“民主”、文化最先进,是当今世界文明的样板,不妨去“傍美国这个大款”。
应该说,落后的文化传统确实应该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同时,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虚心向先进文化学习和借鉴,并真正咀嚼消化,补充和完善自己。只有这样,才可能少走弯路、少受挫折,才可能创新自我,甚至实现跨越式发展。但是,历史虚无主义却走入彻底否定传统的极端,落入与保守主义相对峙的另一个误区。
首先,文化是“人化”与“化人”的统一,任何文化传统都是与相应的人民直接同一的。文化传统是相应人民的“根”,是其“精神的家园”,是“活”在他们身上的文化因子,是积淀在其灵魂深处的文化精髓。正因为如此,文化传统不是孤立的,不是想回避就可回避的,不是想摆脱就可摆脱的,也不是想割断就能割断的。越是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越是如此。实质的差别只在于是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正确发挥传统的作用,还是因盲动与无所作为,文化传统沦为“纠缠着人们头脑的梦魇”。
其次,人们特有的文化传统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环境、前提条件,都是适应其自身环境、条件的产物。在某一社会中成功的文化传统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社会,不能简单地加以认定,更不能强制性地推广。不加分析的“拿来主义”,很可能造成水土不服,“橘化为枳”,导致自身文化传统加速衰亡;同时,又可能如“邯郸学步”,不仅未得异域文化传统的精髓,反而丧失了自身的“国粹”和发展根基。
再次,历史虚无主义过于迷信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其他文化传统之所长,不能客观评估自己的文化传统及其价值。它甚至断章取义,把自己文化传统中那些陈旧、过时、糟粕性的内容视为全部,甚至加以夸大,并以此为据断定它落后腐朽、一无是处,现实中所需要的一切皆需依靠“进口”。问题是,虽然科学技术、物资设备、生产工艺、生活方式等大多可以“进口”,诸如语言文字、社会关系、信念信仰、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文化传统如何全面依靠进口?[3]233-236
第四,还有人宣称“不破不立”。凡传统都是陈旧落后的,只有彻底否定传统,才能创新和发展。如“全盘西化论”,太平天国砸孔子牌位,“文革”彻底“破四旧”等,都是典型情形。但事实证明,这种实质上的只“破”不“立”,结果只能导致“传统的断裂”、文化的危机以及人们自身的漂浮无根。毕竟,创造传统、开创人们自己的未来,比单纯“打倒”、“扫除”、破坏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也重要得多。
此外,还应该重点指出的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失误根源在于单纯“向外看”的价值视角和思维方式。它淡化、弱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悬置”、放弃了自己的权力与责任,是缺少自尊、自立、自信、自强意识的表现,甚至是彻底的无耻的投降主义。这同样表明了传统虚无主义者“主体自我的迷失”。迷失自我,放弃自己的权力、责任和义务,不加分析地迷信他人,不加批评地盲从他人,既不可能建立健全自己的主体意识,也不可能做出恰当的价值评价与选择,更不可能通过自身的价值生活实践创造性地发展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收稿日期:2011-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