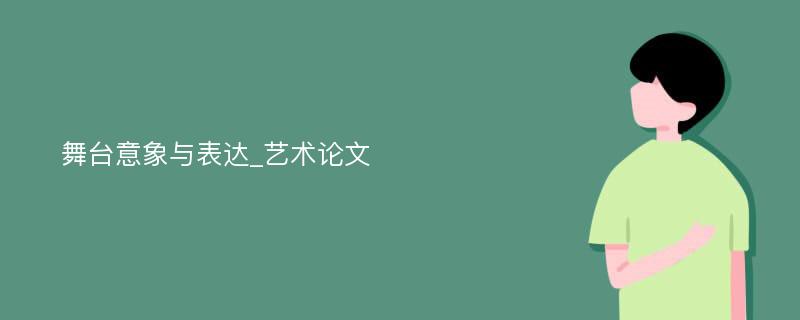
舞台意象与表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象论文,舞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象征、意象、表现
所有的艺术都具有象征性。但并非所有的象征都具有艺术性。
关于象征,黑格尔写道:
象征一般是直接呈现于感性观照的一种现成的外在事物,对这种外在事物并不直接就它本身来看,而是就它所暗示的一种较广泛较普遍的意义来看。
……
它是一种在外表形状上就已暗示要表达的那种思想内容的符号。同时,象征所要使人意识到的却不应是它本身那样一个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①
如果这个表达“思想内容”的“符号”仅是以缺乏有机整体感的机械式组合和推理印证的方式,暗示某个涵义单一明确的、具有“科学抽象”性质的理性观念,那么这个象征就是非艺术性的。
真正可以称为“艺术”的象征,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因为正如苏珊·朗格所说:
作品的情感就是作品的思想。就象论述的内容就是推理的概念一样,艺术品的内容就是情感的非推理式概念,它通过形式——我们看到的外表直接表现出来。②
当那个“感性的外在事物”成为人的思想情感的象征符号时,它便构成了“审美意象”。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一书中论述道:
至于审美意象,我所指的是由想象力所形成的一种形象显现。在这种形象的显现里面,可以使人想起许多思想,然而,又没有任何明确的思想或概念,与之完全相适应。因此,语言就永远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达它,使之变得完全明白易懂。这就很清楚了,审美意象是和理性观念相对称的。③
现代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对审美意象也作出了与康德非常接近的描述:
意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具有活力。……它是一种在一刹那间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感情的集合体。④
克罗齐更是明白无误地指出:
情感是有意象的情感,意象是可以感觉到的意象。……没有意象的情感是盲目的情感,没有情感的意象是空洞的意象。⑤
而苏珊·朗格则直接使用“情感意象”⑥这一概念来表示“意象”作为艺术象征乃是主观情感与客观物象的有机统一的整体。
这里所说的“情感”或“理性与情感的集合体”,都是指所谓“审美情感”,它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具体体验到的诸如“喜怒哀乐”等实际的情感,而是一种具有普遍性和实质性的人类情感,是一种“对情感的理解”,是“人类从一种特殊的角度观看世界的方式”⑦,它本身就已内在地包括着理性内容。而那些“审美意象”、“情感意象”等概念表述,实际上均是“意象”的同义语。
从这样的“意象”定义做逻辑推论,我所说的“舞台意象”就应该是指:在戏剧演出中(而非仅在剧作文本中),以综合性的舞台视听形象为感性形式(而非仅是文学性的语言文字),以涵义丰富深刻的诗化情感和人生哲理为隐喻对象(而非仅是日常的喜怒哀乐表达和浅显的道德伦理说教),所共同构成的象征性的舞台艺术形象。“舞台意象”可以是再现性的。谭霈生老师在《戏剧本体论纲》中,论及了这种再现性的艺术象征:
戏剧作品中的“模仿”(再现)性动作也可能具有象征性。我们针对这种因素运用“象征”这一概念,只是意味着:当形体动作、对话、静止动作作为人的活动的自然形态的模仿时,它们不仅传达了人物在特定情境中具体的心理内容,而且这种心理内容又具有审美的普遍性。它们本身构成一种具象,其内涵又是对具象的超越。不过,这种超越,并不是对实在的自然形态的超越,而是具象的内在意义对具象个性价值的超越。⑧
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茶馆》(焦菊隐导演)为例。具有高度逼真的再现性形象的“裕泰茶馆”,既如实呈现出具体现实的旧北京大茶馆内形形色色的生活气氛和人物形态,也通过这个百年老字号的兴衰和演变,隐喻了中国社会历史从近代的兴衰和演变,既表达了处在这历史兴衰中的人物情感的复杂历程,也反映了创作者主观意识中对这社会演变的情感态度,可以说这个“裕泰茶馆”和王利发、常四爷、秦二爷等人物本身已经构成了再现性的舞台意象。其中最富情绪感染力的“送葬”场面。三个垂老的人物形象,模仿送葬队伍行进的调度图形,满台飘撒的白色纸钱,凄惨悲凉的喊魂之声,既是人物在为自己送葬,也是在为一个行将结束的旧时代送葬,既有人物的生命意义随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无可挽回地逝去的深刻悲哀,也有从这近乎残忍的人物自我调侃中透出的创作者以历史眼光所发出的带泪的欣喜,因为这“送葬”毕竟同时预示着一种“新生”,旧时代的被葬送之后必然是新时代的诞生,旧人生的被终结之后必然是新人生的开端。《茶馆》中的“送葬”场面可以说是极为精彩的舞台意象创造,但是在这个场面中,人物行为和人物语言,戏剧时空的意义,乃至所有的舞台视听形象的综合,都并没有超越现实生活的自然形态,其象征性的情感内容仅限定在“具象的内在意义对具象个性价值的超越”这一层面上,因而它是典型的再现性舞台意象。
当舞台意象创造具有了“表现”的美学特征时,它才能成为“表现性的舞台意象”。谭霈生老师在《戏剧本体论纲》中接着论述了这种表现性的艺术象征:
在戏剧中还有另一种象征。当具象已经是对人的活动的自然形态的超越时,我们就可能进入表现的领域。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创作主体对人的生命活动的体验,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已经升华为具体存在的超越,切近自然形态的具体形象已经难于传达这种体验和感受,就可能闯进“只有情感才能进入的不可模仿的世界”,从而走向抽象领域的象征的道路。……戏剧艺术向我们显示的是我们内部生活的各种形式,而我们对一个人的内心生活的洞察,只有藉助于感官直觉(视、听)。主体传达内心生活,固然可以藉助自身的语言、形体动作、姿态、手势等等;但是,当这种方式已经不能准确无误地传达最隐秘、最深层的内心生活,或者当主体并不想把它们形诸于外的时候,甚至当主体自身都不能意识到这种内心生活的具体内容时,剧作家只有藉助超越自然形态的方式去表现这种内心生活,这就出现了另一种象征——表现性的象征。⑨
“艺术使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⑩而以“超越自然形态的方式”感性形象直接表达这种潜隐在人的精神深处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情感活动,即是所谓“表现”。谭霈生老师对此做了进一说明:
如果说再现的对象是客观化的世界,那么,表现的对象则是为创作主体内心体验过的世界。后者也可能是变了形的,它是不能复制、不可模仿的,也就是说,它是用传统的写实性的语言所难于再现的。(11)
那么,“表现性的舞台意象”就可以理解为:为了对诗化情感和人生哲理进行直接、深刻、强烈的表达,以不受生活表象局限的、不顾现实逻辑制约的、非再现性的视听艺术手段创造的舞台意象。
契诃夫的《樱桃园》,显然具有不容置疑的象征意味,但按过去的理解,那却是隐含在自然、流畅、合情合理的生活表象之下的象征,是一种将“明显的生活现实和深蕴的诗意概括”完美结合的“现实主义象征”(前苏联著名契诃夫专家叶尔米洛夫教授语)(12),因而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艺术家通常都是以再现性的舞台意象创造来演出《樱桃园》的。
然而随着对《樱桃园》象征性涵义的理解的深入,特别是随着将那种沙俄时代封建贵族对旧生活的依恋、怀念、挽留直至不得不与之告别的伤感情绪,推广为人类在不停变幻、更叠、发展着的生活现状面前的普遍性的矛盾情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在演出《樱桃园》时突破严格的现实逻辑,改变传统的再现性风格,而且人们越来越多地将“樱桃园”处理成具有情感涵义的直观性舞台形象,使其成为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性的背景”。因为只有超越了具体历史时代、具体生活氛围和具体人物形象的自然形态,那种蕴含其中的深刻而复杂的隐秘情感才能更强烈地被现代人所理解、所感受,才能更直接地与现代人的相近似的人生体验相沟通。
我一九九三年底曾在莫斯科观看了小剧院演出的《樱桃园》,这个忠实于俄罗斯现实主义演剧传统甚至多少显得有些保守的老资格剧院,一反过去仅仅将“樱桃园”当作环境性形象的处理,用盛开着雪白花朵的樱桃树枝构成一道道侧幕和檐幕,将剧中人物的生活包裹于其中。在第一幕,刚从巴黎赶回来的柳薄芙·安得列耶夫娜和加耶夫·瓦里雅一起伫立在观众面前,眺望窗外久违了的樱桃园,柳薄芙·安得列耶夫娜在静谧朦胧的气氛中充满诗情地回忆她“纯洁而快活的童年”、赞美开满白花的“我的樱桃园”,而此时灯光悄悄地将现实中的生活环境隐去,同时将周围的樱桃树枝突显出来,沉浸在曙色之中显得分外美丽的樱花层层环绕着她们,作一种心理内容的外化,它让我们直接“看见”了人物情感中的“樱桃园”,直接“看见”了他们心中的精神支撑。虽然在这台《樱桃园》中开满樱花的树枝仍然更多地是一种装饰性结构,并没有在演出进程中充分体现其内涵的情感意义,但它毕竟已经在这一时刻让“樱桃园”这个舞台意象具有了一些“表现”的意味。
在圣·彼得堡托夫斯托诺格夫大话剧院(原列宁格勒高尔基大话剧院)看到的另一个《樱桃园》,则在“表现”的路子上走得远得多。演出者明确地追求舞台假定性效果,他们置剧情环境室内室外的区别于不顾,在整个演区范围里“栽种”了十几棵樱桃树,人们在这些树托间穿行,情感冲突依着这些树展开,这些造型逼真的树显然让人觉得它们绝不仅仅是外部环境,“樱桃园”作为朗涅芙斯卡娅及其亲人的精神家园的象征,被这样处理成了一个直观的感性形象。第三幕,当商人罗巴辛为买下了樱桃园而得意不已时,他大幅度地在樱桃树之间走动,也在那些象樱桃树一样呆立不走动的人们之间走动,他激动得近乎狂暴地说着他的大段台词,全然没有了在此之前的卑怯和谦恭。他从内到外地成了这片“樱桃园”的主人,而朗涅芙斯卡娅也从内到外地失去了这片“樱桃园”,于是第四幕开幕时那些樱桃树便荡然无存了,就象柳波芙的空荡荡的内心一样。当大家收拾好行李准备最后离开时,朗涅芙斯卡娅恋恋不舍地说:“我得在这儿再坐一分钟。”每个人便都席地而坐,好象就坐在原先有树的那些地方,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不动,不说话,也没有任何声音,空空的舞台上充满了诗的意境,这是一个告别仪式,但它更象一个凭吊仪式,“樱桃园”旧日的主人们此时极为复杂的情感活动,在这几十秒中得到了传统演出所难以达到的鲜明而强烈的外化,“樱桃园”作为表现性舞台意象也在此时被最终创造完成。
而在我看到的另一个《樱桃园》的演出录象中,“樱桃园”已经完全脱离了它自身的自然形态,雪白的樱花被演绎成了高度假定的白色舞台形象,白色的布景,白色的家具,白色的长裙,白色的西装,白色的遮阳伞,白色的文明棍,舞台上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的东西全都成了白色。看不见一点点“樱桃园”的影子而它却又无处不在,它已经成为体现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乃至渗透进每一个情感角落里的名副其实的“精神背景”了,同时它也从一个再现性的“现实主义象征”彻底变成了一个“表现性舞台意象”。
从《樱桃园》的舞台意象由再现走向表现的嬗变中,以及从无数的表现性戏剧演出创造中,我们也许已经看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表现性舞台意象的创造总是在“心理时空”概念下所建构的“组合型戏剧演出时空系统”中进行的。这个基本事实的真正意义在于,“假定性”演剧观念的确立和“假定性手法”的运用,是在戏剧演出中进行“表现性舞台意象”创造的必要条件。
(二) 哲理、诗情、美的形式
徐晓钟老师在对《桑树坪纪事》的演出作艺术总结时,专门谈到了舞台意象创造中的“表现”及“表现的原则”:
“表现”的原则追求用非写实的或远离生活形态的形式,直接外化形象的心理潜意识及创作者的主观感受和理念,而且往往不理睬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我认为真正的“表现”原则和“表现”的美,只存在于饱涵哲理、饱涵诗的激情和意境并找到美的形式的那些瞬间。如果失去其中的某个因素,往往出现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有时成为创作者某种理念的冷漠的图解,甚至只是一些“美妙”的形式的“游戏”。(13)
徐晓钟老师为“表现”的原则明确了三个要素:哲理,诗情,美的形式。其中“哲理”和“诗情”,可以看作是一回事,是浑然一体的“诗情哲理”,因为没有“诗情”的“理”是干巴巴的理性概念,不算是“哲理”,没有“哲理”的“情”则是随处可见的日常情感,谈不上“诗情”。这浑然一体的“诗情哲理”,就是所谓创作主体对人的生命活动的体验和对客观世界的感受,就是所谓潜隐在人的精神深处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情感活动,就是所谓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无法用语言概念准确表达的“审美情感”;而“美的形式”,则是为了对这生命体验,对这包含着理性内容的“审美情感”作象征性表达而创造出的具体、感性的符号形式,而且这符号形式是非写实的或远离生活形态的,并富于舞台视听觉的形式美感。
在“表现”的原则具体体现时,在进行将“诗情哲理”和“美的形式”融为一体的舞台意象创造时,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即徐晓钟老师所说的“不理睬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假定性”演剧观念的确立和“假定性手法”的运用,就意味着超越“环境时空”的限制而进入可供创造想象自由驰骋的“心理时空”。
看看《桑树坪纪事》中的那些堪称经典的舞台意象创造,无一不是在“不理睬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的“心理时空”层面上进行的。当疯子福林被怀着阴暗心理和残忍动机的无聊村民所挑唆,当着众人强行扒下自己媳妇的裤子时,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应该是:青女遭受侮辱后的无地自容和悲痛欲绝,村民们或愤慨或窃喜或怒斥无赖或安慰青女或因习以为常而无动于衷等各种情绪反应,然后是乐极生悲的不欢而散。而实际演出却在福林示威般举着青女的裤子喊着“我的婆姨!钱买下的!妹子换下的!”并愤然离去之后,随即将舞台逻辑由写实转向了表现:在沉重且震摄人心的主题音乐中,围成一团的村民慢慢散开,原先青女倒卧的地方出人意料地倒卧着一尊虽残破却洁白的中国古代仕女雕像,众村民面向她虔诚下跪,他们此时已由具体的人物变成了抽象的歌队,他们代表着桑树坪的良知,也代表演出创造者的良知,他们为几千年来深受落后、愚昧、野蛮的摧残戗害的中国妇女乃至整个中华民族而悲哀、而痛悔、而深深地反省、而默默地呐喊。在另一条情节线索中,小麦客榆娃与桑树坪的年青寡妇彩芳偷偷幽会,相约共同去追寻他们所憧憬的幸福生活,一个美丽的梦幻几乎就在产生的同时便立刻被村长带来“捉奸”的村民手中的火把和棍棒所破灭,彩芳忍痛扶送被毒打致伤的榆娃离开桑树坪,就在两人难舍难分之际,前面曾多次出现的麦客行列再次随着主题音乐出现在缓缓旋转的舞台上,他们没有人招呼榆娃,没有人安慰榆娃,没有人搀榆娃,只是肩背重负深埋着头默默地走着,榆娃渐渐融进了他们的行列,没有回顾彩芳,没有挥泪告别,也只是肩背重负深埋着头默默地走着,他的因伤痛而显得踉跄不稳的脚步渐渐变得和众麦客一样扎实有力,于是我们从这非现实的然而充满情感意味的舞台图景中看到了我们整个民族的历史形象:忍辱负重,坚韧不拔,迈着艰难沉重的步履,在这块贫瘠落后的黄土地上缓缓前行,从古走到今。与“青女石象”和“麦客出村”相比,“杀牛”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县上成立革委会,“脑系们”为吃喝庆祝而明令桑树坪人杀掉他们的老牛“豁子”,对于以农耕为生的人来说,这头唯一的耕牛不仅是他们的劳作伙伴,更是他们相依为命的生存伙伴,他们爱惜它,但是这个可能是充满血腥且惨不忍睹的现实场面却以近似民间舞狮的非现实形式呈现出来:音乐是悲壮的,灯光是血红的,由两个演员披着“牛皮”套着“牛头”扮演的“豁子”,在围着它作棍打石砸慢动作的村民中间躲避、翻滚、哭号,它匍匐着爬向老饲养员寻求保护,它直立哀鸣以示它的大惑不解,可是那些桑树坪人不为所动,仍然不停地打杀着,他们象是在进行又一场“围猎”,他们曾这样“围猎”过榆娃和彩芳,“围猎”过福林和青女,“围猎”过月娃,“围猎”过外乡人王志科,“围猎”过……可是他们又无时无刻不在被另一种更巨大、更残忍、更罪恶的力量所“围猎”、所打杀、所戗害,当他们向那颗硕大的牛头跪拜祭奠时,他们分明是在祭奠自己!《桑树坪纪事》的演出,在以上这些时刻都达到了“诗情哲理”和“美的形式”的完满统一,实现了对最富于理性震撼力和情绪感染力的“表现性舞台意象”的创造。其实“桑树坪”本身就是一个饱涵诗情、饱涵哲理的整体舞台意象,它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历史的艰难脚步和沉痛情感,它也是演出创造者所有的激情和沉思的形象总括。
“不理睬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对于表现性舞台意象的创造是不可或缺的,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前提,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当创造者自身没有激情和沉思时,当演出内涵中缺乏诗情和哲理时,“假定性手法”的使用便失去了价值意义,表现性舞台意象当然也就无从产生。试想当初徐晓钟老师如若没有从《桑树坪纪事》中看到“小桑树坪”和“大桑树坪”的关系,如若没有从桑树坪人的生存状态中看到那种“围猎”与被“围猎”的关系,如若没有感受到他们“盲目而麻木地相互角逐和厮杀,制造着别人的也制造着自己的惨剧,……所谓相互残害,实质上也是自戗”(14)的沉重悲哀,如若没有对生活在当代的“桑树坪人”仍然“用自己瘦骨嶙峋的脊背负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负”(14)(15)引起深刻共鸣,如若没有激发出“希望通过李金斗和他的村民的命运,引发人们对五千年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反思”(16)的神圣责任,我们便不会在舞台上看到诸如“捉奸”、“青女石象”、“麦客出村”、“杀牛”、“围猎”等一系列给人留下极深印象的场面处理,“桑树坪”也不会最终由一系列表现性舞台意象合成一个整体的舞台意象。没有诗情为内涵,没有哲理做底蕴,“假定性手法”既使能制造出某些貌似精彩的舞台形式,也只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无皮之毛,构不成舞台意象,更谈不上表现性,充其量也就是有些“好看不中用”的最表浅层面的观赏效果而已。
另一方面,蕴含在演出之中的诗性哲理要迸发出艺术感染力和思想震撼力,必须有一个适当的表达方式,有一个相应的承载体,这就是徐晓钟老师所说的要找到一个“美的形式”。事实上,徐晓钟老师在《桑树坪纪事》的导演构思阶段,在形容心中汹涌如潮的诗情,在概括令人坐立不安的演出哲理的同时,已经开始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意识到、看到、听到这个“美的形式”,当然那时它还是模糊的,不确定的,甚至是幼稚的,但它却隐含着生发未来演出艺术形象的巨大的潜在可能性,徐晓钟老师把它叫作“形象种子”,并说明“它是一个演出的形象化的种子”。(17)我认为“形象种子”和“舞台意象”之间具有直接而有机的联系,“形象种子”可以说是“舞台意象”的雏形或胚胎,如果“形象种子”在演出创造过程中没有被掩盖在“戏剧冲突、情节的表层的写实的逻辑”之中,如果它能破土而出,将它所蕴含着的诗情哲理和潜在的形象可能性给以充分的释放,就将直接导致表现性舞台意象的形成。《桑树坪纪事》中那一系列精彩的舞台意象创造,实际上就都是从“围猎”这颗“形象种子”生发出来的。
这个将诗情哲理给以直观表达,将“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给以感性呈现的“美的形式”,总是非写实性或远离生活形态的,它常常是将那抽象的感性内容转而寄托在一些原本并无直接逻辑联系的具体事物上。譬如生活在桑树坪这块贫瘠土地上的农民们原本并不以打猎为生,而舞台上却总在“围猎”,其实那只是一种生存状态和一种情感体验的象征;又如《樱桃园》人们对象征着旧日生活的“樱桃园”的依赖、怀念之情转化为无所不在的、变形夸张的白色布景环境、白色服装道具;再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把几块普通的卡车车厢板处理成红军女战士的精神形象,不仅一直伴随着她们与德寇殊死搏斗,而且在她们牺牲之后作为她们的墓碑代替她们在音乐中不停旋转,等等。在一个具有美的造型形象,尤其是能够引起美的联想的事物上寄托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隐喻某种诗情哲理,是表现性舞台意象创造中最为常见的表达方式。关于艺术家之所以在创作中使用象征性手法的理由,黑格尔曾经讲了三点:“第一个理由是强化效果”,第二个理由就是为了“把自己和自己的情绪转化为美的形象”;“第三,隐喻的表达方式也可以起于想象力的恣肆奔放,不愿按惯常形状去描绘事物或不用形象而只简单地直陈意义,于是到处搜寻一种相关联的可供观照的具体形象。因此,隐喻也可以起于主体任意配搭的巧智,为着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出相关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一起。”(18)徐晓钟老师也认为创造“诗化的意象”应该“在破除现实幻觉的同时,给观众创造诗意的联想意境的幻觉,……不在舞台上创造现实生活的幻觉,而是通过某种象征形象的催化,在观众的心理视觉和艺术通感中创造出再生的饱含哲理的诗化形象……”(19)
也许红绸子的色彩和质感,太容易让人联想到鲜血的流淌和跃动,所以它经常被用来创造象征鲜血的舞台意象。徐晓钟老师在排演《马克白斯》时,曾把马克白斯自身的理性判断与生命冲动的巨大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巨大悲剧概括为:“一个‘巨人’在鲜血的激流和旋涡中蹚涉并被卷没”(20),并由这个“形象种子”演绎出了一块宴会中的红绸桌布,马克白斯在幻觉中与班柯的鬼魂搏斗,就拿它权作武器,血红的桌布在他周围翻飞,在他身上缠裹,在他脚下践踏,当众人散去,马克白斯安静下来,在夫人的陪伴下精疲力竭,神情恍惚地消失在幽暗的舞台深处时,那块红桌布就象他们的影子,长长地、久久地拖弋在他们的身后。查丽芳在《死水微澜》中时常舞弄一条红绸子,它曾烘托过邓么姑和蔡兴顺婚礼的喜庆气氛,在邓么姑和罗德生深夜幽会中,它又成了那积蓄已久压抑已久,而今突然迸发的强烈的情欲的外化;当邓么姑为保护罗德生而遭受毒打时,它则表现了一种染满血色的惨烈和悲壮;全剧的结尾处,它再次被用于邓么姑的婚礼,但此时新郎和伴娘们都变成“教民”了,至此,这条红绸子完成了对邓么姑的命运的总括,实现了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精神实质的象征。我在排演《浴血美人》(原名《艾丝倍塔》)时,也用了一幅巨大的红绸子象征鲜血,它被用来衬托艾丝倍塔每一次用鲜血涂脸、用鲜血沐浴的残酷而血腥的行为,它时而象幽灵在艾丝倍身边缓缓飘过,时而象地毯铺垫在艾丝倍塔脚下,时而象血幕在艾丝倍塔背后映出白衣少女的身影,时而象血河滚动流淌在艾丝蓓塔与白衣少女之间,它可以将艾丝倍塔整个笼罩于其中,它甚至还曾直接笼罩在观众头上。王贵在《血染的风采》中也用一块翻舞的红绸子表现士兵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宫晓东在《无声的嘹亮》中甚至直接从每个战士的伤口“流”出一块红绸子。以红绸子象征鲜血在国外的演出中也时常能见到,托夫斯托诺格夫导演的《马的故事》,在最后将老马杀死时就用了一条从演员胸口飘落的红绸带表示鲜血的涌出,德国布来梅“摩克斯”剧团演出的《蓝胡子》,一个年轻姑娘被人用手杖击头后,便倒在一块红绸子上以示流血而死,而柏林德意志剧院演出的《丹东之死》,为了渲染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和流血的气氛,干脆让演出自始至终在完全由红绸构成的舞台布景中进行。
“美的形式”可以被创造成无数种具体形态,也有无数种具有美感的事物可以被用来象征艺术情感,这里的“红绸子现象”只是“表现性舞台意象”创造中较为显而易见的一个例证。红绸子频繁有效而且各具特点地在舞台上创造了诸多“鲜血意象”,其中有悲哀、有惨烈、有残忍、有优美,它竟然可以把差异如此之大的人生体验都分别予以容纳,其实可以说它也同时创造了“生命意象”,因为“鲜血”总是和“生命”密切相关的。“红绸子现象”非常典型而且集中地体现了戏剧演出艺术创造“表现性舞台意象”的一种模式:以某种与表面戏剧冲突并无直接联系、原本没有具体意义、然而却潜含着某种视听美质的客观事物,作为对创作主体所感受到的情感内容和生命意识进行直观外化的感性形式的物质基础,这“事物”可以是象红绸子这样的舞台道具,也可以是对布景形象的变化处理,还可以是对舞台技术设备诸如灯光、转台的潜力挖掘,更可以直接发挥演员自身的形体表现力,将这些原本无确定涵义的舞台造型因素,与戏剧演出中的情感意蕴建立非写实逻辑的但却谐调有机的联系,以形成黑格尔所说的戏剧演出的“精神性的布景”(21)或者叫作“精神背景”并利用其间形成的情感转移和创造想象,达到“美的形式”对“诗性哲理”进行直观表达的艺术目的。
(三) 舞台意象创造中的另一种“美”
在一个具有美的造型形象,尤其是能够引起美的联想的事物上寄托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隐喻某种诗情哲理,这种“把自己和自己的情绪转化为美的形象”的表达方式,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十分吻合。中国古典文学就有这样的明显特点,不论是欣喜之情还是愁苦之情,均能将之体现在“美”的形象中,而且这“美”的形象还可能出自同一事物。例如同是桃花,《诗经》中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被用来形容姑娘的娇艳,也是在渲染欢乐喜庆的婚嫁气氛;在唐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仍旧笑春风。”中,重游故地却不见故人,桃花又成了这种怅然若失的淡淡忧伤的写照;而在林黛玉的《葬花辞》中,那“花谢花飞飞满天”的桃花的“美”,却表达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无限悲伤的人生感怀。将种种情感体验都通过桃花来表达,与将种种诗情哲理均寓于红绸之内有异曲同工之妙,以桃花表情,是所谓“情景合一”,以红绸喻血,是所谓“在似与不似之间”,两者都可以说是“写意”。
然而在戏剧演出中,在表现性舞台意象的创造中,还可能出现另一种“美”。
我们仍以舞台上的“鲜血意象”的创造为例。
仍然是《马克白斯》,德国海德堡剧院在一九八八年柏林戏剧节上以近乎舞剧的方式演出此剧,但他们却没有象我们通常那样把“鲜血意象”通过舞蹈场面隐在“红桌布”式的概括性形象中去引发联想,在这个演出中大量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血。开演伊始,舞台后部一扇巨大的铁门轰然开启,从黝黑的门洞里走出一个黑衣黑帽的黑人,拎着一只铁桶径直走一台前,几乎在观众的鼻子跟前将满满一桶血淋淋的猪或牛的内脏倒进乐池,心肺落地噼啪有声,所有观众都好象立刻嗅到了血腥味,这个动作以后还重复了多次;马克白斯遇三女巫时,三个女巫一副在西方街头常见的“朋克”打扮,她们围着马克白斯狂舞,用一块白布将马克白斯象婴儿一样起来,然后撩起衣服露出橡胶做的乳房让马克白斯吸吮,而乳房中流出的却不是奶而是血,血水染红了马克白斯的脸颊,染红了他的衣服,也染红了那块白布,于是,女巫把“嗜血的念头”注入了马克白斯的灵魂;马克白斯与班柯跳了一段表现争夺权利的舞蹈之后,又在同一个浴盆中由三女巫为他们洗澡,洗完后她们把浴盆推到台前,而倒进乐池的又是一盆鲜红的血水;马克白斯和夫人为祝贺获得权利而一同跳舞嬉戏,夫人突然掉进了乐池,当她爬上来时,脚上沾满了鲜血,她想擦,擦不掉,要抹,抹不尽,欲走,脚不敢沾地,最后就连站着也如“立”针毡;马克白斯夫人在灵魂的自我折磨中精神失常,她的双手突然变成两只张着大嘴的蛇头,她惊恐、躲避、挣扎、求救,但还是被蛇咬住了脖子—她自己掐住了自己,眼看着大量的鲜血不断流出,流遍了全身,流到了台板上,她挣扎着倒在血泊中……
有着“沉默的哲学家”称号的阿根廷哑剧艺术家比内托,直接把日常生活“浸泡”在鲜血里,用以表达他对“人”,对“人生”的看法:
他表现一个人,不停地重复以下这些动作:醒来、穿衣、穿鞋、漱口、洗脸、吃饭、出门、微笑、握手、打电话、抄文件、争论不休、数钞票、挤车、回家、晚餐、看报、漱口、洗脸、脱鞋、脱衣、入眠、醒来、穿衣、穿鞋、漱口、洗脸……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个人一天枯燥又奔忙的生活,越重复越快,满身大汗,面容憔悴,疲于奔命,苦于应付,强颜欢笑,直到他突然一抹身,“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当他再挣扎着站起来,转身面向观众时,从他的嘴角淌下敫红的鲜血!那鲜红的血沿着颈、胸,一直流到全身,在这鲜血淋漓中,他仍重复着穿衣、穿鞋、漱口、洗脸、早饭、出门、寒喧、握手、打电话……最后,他所表现的这个形象,累死在舞台上,躺在血泊中。”(22)
这种在舞台上直接用实实在在的鲜血来创造非写实性的“鲜血意象”,可以一直追溯到“残酷戏剧”的创始人,充满反叛精神的安托宁·阿尔托那里:
一九二七年,阿尔托演出的《喷血》一剧中有人的四肢和石头房子的碎片从舞台上端落下,借以象征文明的崩溃。用来表达人类反叛的则是,一个妓女咬破上帝的手腕,接着喷射出大量的血,溅满舞台。(23)
同为“残酷戏剧”的倡导者彼得·布鲁克于一九六三年再次排演《喷血》,仍然是“一只巨大的‘上帝之手’从空而降,喷出鲜血。”(24)他一九六五年为英国伦敦奥德维由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排演的著名的《马拉·萨德》,在那些精神病人扮演的戏中戏里有一个断头台处决的情景,演到铡刀落处,大量的鲜血喷涌而出,直流进舞台布景中的浴室水沟里。非常有意思的是,彼得·布鲁克原先也曾是“红绸现象”的制造者,在他的早期作品《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中,“布鲁克曾用红色缎带作为流血的象征”(25)。
这里的“喷血现象”,在表现性舞台意象的创造和“假定性手法”的使用上,显出一种与“红绸现象”截然不同的理解和感悟。
从直观表象上看,“红绸现象”直接使用“假定性手法”创造表现性的舞台意象,它的感性形式本身就是非现实逻辑的,是通过创造联想从“戏剧冲突、情节的表层的写实逻辑”中生发、延伸出来的,然而它又鲜明而彻底地超越了现实事物的自然形态,因此它具有显而易见的表现性功能,它为传达演出所蕴含的诗情哲理而存在的价值意义也是一目了然的。同时它的形象造型是抽象性的符号,它的色彩、线条、律动、音乐、演员形体动作、舞蹈化场而等,本身就具有非自然状态的形式美感,因而也就同时具有某种观赏价值。而“喷血现象”则不然,它似乎没有经过寻找象征性舞台形式的过程,没有黑格尔所说的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之中”找到“一种相关联的可供观照的具体形象”,“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料地结合在一起”的那种“任意配搭的巧智”。它直接将表面情节冲突中产生的事物按其原始形态和自然特性呈现在观众面前,它的舞台形象没有符号化的变形,没有寓言式的隐喻,如同海明威说在他的《老人与海》中“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一样,在这里鲜血就是鲜血。它当然是“假”的,但它“逼真”之极,它不但是暗红的颜色,粘稠的质感,它甚至令人觉得有血腥的气味,它简直就与真正的鲜血没有区别,因此它也就十分容易被认为是“自然主义”的演剧方法。
但是,海明威笔下的“大海”绝不仅仅指一片自然景物,“老人”也绝不仅仅指一个生活实象,老人与海的搏斗,最深刻、最强烈地表现了海明威所感悟的生活底蕴和人生精神,作为一件艺术品,《老人与海》的具体表象既保持了自然形态,同时也构成了诗情哲理的载体,它没有把事物的表面形态引伸转化成一种简约的、写意的象征符号,它是把事物的表面艺术形态本身当作了象征符号,这是所谓“本体象征”,是一种与“自然主义”南辕北辙的艺术观念和创造方法。从把事物表面形态本身当作象征符号这一点来看,“喷血现象”也可以说是一种“本体象征”,但它却要具有更明显的假定性质和更强烈的主观色彩,那实实在在的“血”的形象并不激起人们对其它事物的联想,它直接地、不可抗拒地将观众引入对它的超现实性的、抽象的情感内涵的读解。
“喷血现象”对现实逻辑的超越是整体性的。这种舞台意象的具体形象与戏剧情节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表面的逻辑联系,例如马克白斯在女巫“唆使”下弑君篡权完全可能浑身沾满鲜血,极度劳累的确会导致人口吐鲜血,人被打伤、被杀害、被咬破不可避免要流出鲜血,但是这形象与情节的内在关系却是非现实性的,或者说这鲜血的流淌与导致流血的动作之间的关系是非现实性的。依照现实逻辑,涂满马克白斯全身的鲜血不应该是从被吸吮的乳房中流出的,人不可能一边口中不停喷涌鲜血一边持续日复一日的生活动作,妓女当然更咬不到“上帝的手”。在这里,戏剧的情节、环境、人物之间的关系、动作的内在动机,都超越了现实逻辑,就是说整个戏剧情境的设置本身就是非现实性的,这决定了在此情境中出现的一切事物都具有非现实的意味,无论它的表象是自然形态的抑或是经过变形、转义、美化处理的,它都直接传达了一种超越自然形态的主观情感。
“喷血现象”对现实逻辑的整体超越还在于,它的舞台意象的表象部分是“大规模”的。一个自然形态的事物,如果其在数量、体积、力度等方面都明显超出了现实逻辑所能容忍的规模,它就直接越过自己的具体形态而异化为某种抽象观念的载体,这就是所谓“规模效应”,如希区柯克的电影《鸟》,观众在开始时还能认为鸟对人类的袭击只是自然现象,可当那充满威胁感的黑鸟多到无所不在时,观众便不由自主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超自然力量和神秘灾难的巨大恐怖。在比内托表演的哑剧中,那从口中喷涌而出的“鲜血”,的确大大超过了人在实际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大大超过了现实逻辑所能允许的规模,假如人只在嘴角上挂一些血迹而持续日常活动,尚可用生活逻辑加以解释,如果鲜血不断地涌出,浸透了衣服,染红了地板,而那人却仍然在血泊中“寒喧、握手、打电话”,这就逼迫观众不能不去追问其中蕴含的象征意义,不能不去思考其中反映的普遍人生。
“喷血现象”显而易见地带有“残酷戏剧”的印记,这部分地因为它的始作俑者正是“残酷戏剧”的发起人阿尔托。阿尔托的“残酷戏剧”强调戏剧演出对人的感觉器官的直接而强烈的震撼效果,他认为“我们的敏感性已经磨损到如此地步,以致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戏剧来使我们——神经和心灵——猛醒。”而戏剧演出“能够以物质的形式在舞台上表现和表达一切。它们首先针对的是感觉,而不像话语那样首先针对精神。”所以,在他看来一出真正的戏剧应该“扰乱感官的安宁,释放被压抑的下意识,促进潜在的反叛”。他不仅在舞台上为了冲击观众的感官而制造“喷血现象”,而且常在理论阐述中提到“血”,他用“血”描绘瘟疫景象:“从尸体喷出的血流成小河,浓稠、恶臭、呈恐慌和鸦片的颜色。在血河中走过一些古怪的人……”,他用“血”形容残酷戏剧:“强烈而紧凑的情节仿佛具有抒情性,它在诗人和观众的脑中同样唤起超自然的形象,带血的形象,形象的血喷。”他甚至预言“我们不久该用真正的流血来表现这种残酷了。”但是他并不是把对观众的感官冲击当作目的,而只是把这作为通向观众的理性接受的途径,他认为:“观众最初是通过感官来思想的,而普通心理剧则首先着眼于观众的理解力,这是十分荒谬的。……躯体和精神,感官与智力是无法分开的,何况在戏剧这个范畴,器官在不断地疲乏,必须用猛烈的震撼才通能使我们的理解力复苏。”他指出:“暴力和鲜血服务于思想的强烈性。”并作了如下结论:
有人认为残酷就是血腥的严酷,就是毫无意义地、漠然地制造肉体痛苦,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残酷首先是清醒的,这是一种严格的导向,对必然性的顺从。没意识,没有专注的意识,就没有残酷。是意识赋予一切生命行动以血的颜色,因为,显然,生命总意味着某人的死亡。(26)
在马丁·艾思林眼里,阿尔托的“残酷戏剧”是这样一种戏剧:
以中世纪黑死病那样的瘟疫的令人战栗的恐怖,及其毁灭性的全部冲击力,向观众猛扑过去,在它所袭击的人群中引起彻底的剧变,肉体上、精神上和 道德上的剧变。(27)
无论是用“本体象征”、“规模效应”抑或是用“残酷戏剧”来解释“喷血现象”,都离不开它的一个最明显同时也最具实质性的特征:不利用一个经过变形处理的、远离自然形态的、具有抽象的形式美感的符号系统作中介,仅以自身的具体形象为符号,以超出现实逻辑的巨大的感性冲击力,直接传达主观的诗情哲理,它要求于观众的,也是对极为具象化的形式表象直接观照之中的理解和感悟,它从高度具象的感性形式直接通向高度抽象的审美情感。
这显然是对戏剧演出的假定性本质的更为深刻的体认,在这样的假定性的概念之下,许多我们原本认为不便或不宜出现在舞台上的事物,都有可能于戏剧演出中显示“表现的原则”的巨大而独特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德国汉堡塔利亚剧院演出的德国历史剧《尼伯龙根》,为表现古代战争的宏伟壮观,用五、六个汽油桶在台上燃起熊熊大火,剧中的英雄独坐在被火光映得彤红的平台上,那大火便成了他的汹涌激情和人格力量的外化。
德国鲁尔区米海姆剧院在一九八八年柏林戏剧节上演出的《死无葬身之地》,几个被俘的抵抗运动战士始终被泡在近一尺深的水里,他们在水里忍受酷刑带来的肉体痛苦,他们在水里争论自己行为的意义,他们把脆弱的弗朗索瓦溺死在水里,他们在水里静等着死亡的来临。这水大大强化了他们的境遇的残 酷感,也大大强化了他们的心态的紧张感,更把演出内涵直接引向了“在境遇中选择生命的意义”这个存在主义的人生命题。
德国汉堡德意志剧院在同一戏剧节上演出的表现主义前驱弗兰克·魏德金的著名作品《露露》,为了揭示“性”中所蕴含的人性的瑰丽和人性的丑恶,为了通过“性”来表现生命的张扬和生命的枯萎,便让扮演露露的女演员在三分之二的演出时间里完全坦露她的并不丰满美艳的身体,而且演出始终令观众席一片通明,以消除在黑暗中“窥淫”的色情感,导演显然试图采取一种近乎残酷的方式,迫使观众直面在艺术中所呈现的同样残酷但却最真实不过的生命本质。
还有《阿麦迪或脱身术》中的那具不断膨胀而且长满蘑菇的“尸体”,以及尤奈斯库堆在舞台上多得让人无处立足的“椅子”……
与利用红绸暗喻鲜血,假借桃花表达感情的“美的形式”相比,那血、火、水、人体以及尸体、椅子,的确缺乏赏心悦目的美感。这样的艺术语言对具象外观不加以修饰,甚至刻意强调其自然的形态和质感,它们是刺目的、威胁性的、狞厉的甚至是丑陋的,但是它们在通过强烈的视听冲击给人以感官刺激的同时,也实现了对情感的震慑和理性的惊厥,它们在狞厉、丑陋的表象外观之中蕴含着抽象的美质,因而可以说它们具有一种“狞厉的美”,“丑陋的美”。如果我们不把“美的形式”仅仅理解为“优美”的话,那么类似“喷血现象”这样从高度具象直通高度抽象的演出处理,因为它们同时具有舞台视听形象和饱满而强烈的诗情哲理,并且“不理睬戏剧冲突、情节表层的写实的逻辑”,我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认为它们已经构成了“表现性舞台意象”,而要对这样的舞台意象进行创造,更是须臾离不得“假定性手法”。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0页。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下同。
②⑥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第52、98页。第12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③康德:《判断力批判》第四十九节。转引自《西方文论选》上卷,第563-5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蒋孔阳译。
④《现代西方文论选》第25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
⑤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第233-234页。外国文学出版1983年版。
⑦布洛克:《美学新解》第165、15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⑧⑨(11)(13)谭霈生:《戏剧本体论纲》。《剧作家》八九年第一期第68页。70页。
⑩卡西尔:《人论》第189、18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12)转引自童道明:《他山集》,第16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3年版。
(14)(15)(16)(19)徐晓钟:《在兼容与结合中嬗变——话剧〈桑树坪纪事〉实验报告》,见《徐晓钟导演艺术研究》第407、408页、406页、409页、413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1年版。
(17)徐晓钟:《导演基础知识》,见《戏剧艺术讲座》第126页,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1983年内部出版。
(18)黑格尔:《美学》,第二卷,第130-132页。
(20)徐晓钟:《马克白斯初探》,《戏剧学习》1981年第2期。
(21)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第304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2)转引自高鉴的《戏剧的世界》,第80-81页。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3)(24)(25)J·L·斯泰恩:《现代戏剧的理论与实践》(二),第156页、167页、159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版。
(26)以上阿尔托的言论分别引自《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第80页、第33页、第22页、第18页、第78页、第84页、第81页、第79页、第100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