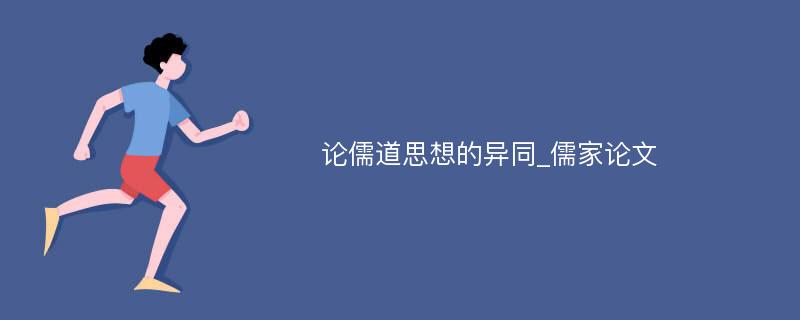
略论儒道两家境界哲学的异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道论文,异同论文,两家论文,境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1999)01—0049—53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儒家的创始人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为己”是通过道德的自我修养完成人格的自我塑造,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为人”则是通过知识的积累,以学识渊博取悦于人。孔子是推崇古之学者的。他认为学习不只是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提高精神境界。所以他提出要“志于道”(《论语·述而》),“朝闻道,夕可死矣。”(《论语·里仁》)道家的鼻祖老子指出为学与为道的区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48章)为学的目的是获得更多的知识,知识需要积累,积累越多越丰富,为道的目的是提高人的心灵境界,境界的提高有待于私欲的减少。老子是提倡“为道”的。儒道两家都提倡“学道”,以提高心灵境界为哲学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都可以说是境界哲学,但两家所追求的终极境界并不相同。
儒家哲学是一种伦理哲学,它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宗法社会,为了维持宗法社会的秩序而必须建立一套伦理道德规范。它认为人是社会中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等道德本性,能够自觉按照伦理道德规范行事,履行道德义务,并在道德践履中完成人格的自我塑造,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即仁义境界。孟子认为人天生便具有仁义礼智四德,四德之中,仁义为主而仁又为四德之本。仁不仅为最高的道德本质,也是人格完成的最高境界,是儒家哲学所追求的终极境界。只有圣人才能达到这种境界,所以仁者与圣人同为儒家标榜的理想人格,连孔子也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达到最高境界的人行事必是出于义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又云:“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仁义境界是儒家所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
道家哲学是宇宙自然本位论的哲学,在它那儿,宇宙是一个莽莽苍苍,浑然一体的原始天地,人只不过是其中一物而已,是自然界一分子,他与鸟兽虫鱼,花草树木本无区别。但人却常常以人自居,给自己套上仁义道德的枷锁,把自己与其他物类区别开来,变成宇宙中异己分子。故与儒家大讲仁义相反,道家是鄙视仁义的,老子说过:“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他认为最高境界应是道的境界,道的境界即自然境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所以人应忘掉仁义道德,恢复自然本性,回归天地自然,自同于宇宙大全。他说:“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老子》二十八章)教人“抟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十章)要人返朴还淳,回到婴儿时的无知无欲的自然状态。庄子则赞美浑沌之无知,在《应帝王》中对浑沌之死深为惋惜。他认为道的境界便是无知无欲,无思无虑,无处无服,无从无道的自然无为境界。如《庄子·知北游》中说:“知谓无为谓曰:‘予欲有问乎若:何思何虑则知道?何处何服则安道?何从何道则得道?’三问而无为谓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以之言也,问乎狂屈,狂屈曰:‘唉,予知之,将语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问,反于帝宫,见黄帝而问焉,黄帝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则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知问黄帝曰:‘我与若知之,彼与彼不知也,其熟是耶?’黄帝曰:‘彼无为谓真是也,狂屈似之,我与汝终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这里黄帝虽然说出了道的境界,却没有明白“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的道理,所以他没有达到道的境界。无为虽什么也没有说,但无为遵循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的原则,知而不言,他的境界就是道的境界即自然境界,它是道家哲学的终极境界。
儒道两家所追求的终极境界虽不相同,但两家境界哲学却有相通之处,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道两家都把审美境界作为人生的理想境界
孔子自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说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颜之乐是由道德自律进入到道德自由自觉状态而获得的一种美感体验,他们所达到的境界不仅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而且是审自由境界。李泽厚、刘纲纪在《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指出:“仁学的最高境界不是别的而是自由的境界,审美的境界,也就是孔子自论和夸赞颜回‘不改其乐’的人生境界。”审美自由境界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论语·先进》记载:孔子让弟子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回答都不能令孔子满意,轮到曾点:“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雾,泳而归。”孔子听了,方才满意,喟然叹曰:“吾与点也”。曾点的志向是投身于自然,超然物外,忘世自乐,悠然自适。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曾点之学,盖有以见人欲尽去,天理流行……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曾点由道德修养的自由自觉状态进入到一种审美自由的境界,这就是曾点自己描述的“风乎舞雾”的境界,这正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生境界,故得到孔子的首肯。
庄子以寓言的形式描述了道家理想的人生境界。《逍遥游》中大鹏自由地飞翔,飞翔的自由象征精神在无限宇宙时空中自由遨游,超乎对待,来去自如,无滞无碍,逍遥自在。他追求的是实现了超乎对待的绝对自由的境界,所以他笔下的神人是“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逍遥游》)真人是“翛然而往,翛然而来。”当然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这种绝对自由的逍遥也只能是在精神领域内,在虚幻的审美的人生境界中才可能实现。
把审美境界作为理想的人生境界主要还体现为儒道两家都提倡一种快乐的人生哲学。
孔子认为道德修养的最后完成是达到超道德的审美境界即乐的境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提倡安贫乐道,乐天安命,认为只要心中充满仁义道德即使外界条件如何不利、物质生活十分贫乏亦不影响内心的和乐,如他自称饭蔬食饮水而乐在其中,夸颜回身居陋巷而不改其乐。孟子以为乐是对人性的自我认识与自我完成,仁义之人自然有乐。“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期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章句上》)并认为以家族伦理为基础的道德体验才是乐的内在依据,父子之亲是人之大伦也是乐之所在。他提出,“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所不俯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尽心上》)三乐之中,第一乐便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孟子还指出“乐”是具万理于一心之中,反身而诚,则万理毕现,达到浑然与万物同体,上下与天地同流的超道德的美学境界。“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矣。”(《孟子·尽心上》)
在儒家哲学中,乐不只是一种积极性的情感体验或乐观主义生活态度,它还是一种既具道德而又超道德的美感体验,是由道德的自我充实,人性的自我完成所达到的一种超道德的美学境界。
而在道家,“乐”不仅仅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超然物外,旷达洒脱,而且是一种实现了绝对自由,无往而不适的逍遥境界,它既是一种审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了与道冥合,与物同体,与天地变化齐一的超越的本体境界。
庄子在濠梁上看见“鲦鱼从容出游”,便说这是鱼之乐。因为“鲦鱼从容出游”能使人联想到一种从容自适、自由自在的快乐人生,这也正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所描述的大鹏自由飞翔的逍遥境界。庄子认为他所说的“乐”与儒家所说的“乐”有所不同。儒家所说的“乐”指的是“人乐”,是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由道德的自我充实产生的内心和乐,而他所说的是“天乐”。“与天和谐,谓之天乐”。“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故知天乐者:其动也天,其静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服万物,言以虚静推于天下,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是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自然界和谐相生中体会到与道冥合,与天合一的超道德超伦理的终极愉悦,是实现了精神上的超升和心灵自由的生命愉悦,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快乐。“无言而心悦”(《庄子·天运》),不仅无法言说,甚至身处其中却感觉不到,但这是最大的快乐:“至乐无乐”(《庄子·至乐》),因为它超越了一般喜怒哀乐等日常的情感体验,不是一般的感性快乐或理性愉悦,而是涌动于生命底层,萌发于心灵深处的愉悦,是超感官的终极愉悦。庄子又称之为:“忘适之适”,“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庄子·达生篇》)这是实现了物我两忘,浑然一体,我自同于宇宙大全,回归生命之所,自我性灵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产生的精神上的快适,是一种超情感超理性的生命体验,是属审美而又超审美的本体体验。
儒道两家虽然所说的“乐”的含义并不相同,但两家“乐”的精神却是一致的,都体现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和谐的热爱。
虽然儒家为了维护宗法社会的等级秩序而要求个体循规蹈矩,严格遵循伦理道德规范而不能越雷池一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体的自由,但他们也不愿意个体生命因受到压抑而痛苦不堪。他们向往“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道德自由境界。故他们把伦理道德观念看成是人生来就具有的,道德品质是人的社会本性,化外在的伦理道德规范为内在的心理欲求,使个体生命能量在无压抑的状态下获得最大的释放,个体任性而行,随心所欲而不会违反道德规范,自由自在,无往不适。
道家对自由表现出强烈的渴望和热烈的追求,他们把社会看成是囚禁个体生命的牢笼,把仁义道德看成是人性的枷锁。现实生活的黑暗与种种不自由使他们非常重视个体人格的独立和精神上的自由,主张打破枷锁,冲出牢笼,回归自然,恢复天性,把自己融于大自然之中,与天相合,与物玄同,于大化流行中尽情畅游生命的快乐与自由。庄子在《大宗师》中抨击那种为了虚假的仁义道德而牺牲个体生命的“适人之适”,提倡“自适其适”,认为实现了个体精神上的解放和心灵的自由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他理想的人生境界是实现了绝对自由的逍遥境界。他所说的“天乐”、“至乐”、“忘适之适”是摆脱了一切束缚,身心获得彻底解放,精神上实现了绝对自由的生命愉悦。
当然,自由的含义在儒道两家哲学中并不相同,儒家向往的是伦理道德自由,道家追求的是个体精神上的绝对自由。
对和谐的热爱也是儒道两家快乐哲学所体现的主要精神。
儒家推行礼乐制度,主张“克己复礼”。最终还是为了调谐人际关系,实现社会人生的和谐。“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礼的作用就是为了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用庄子的话说就是要实现“人和”,只有在和谐的人际关系中才能获得身心的愉悦即“人乐”。当然儒家对和谐的追求并不止于“人和”。《中庸》:“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是宇宙的根本秩序与法则,宇宙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自然界和谐相生,人类社会的活动不仅不能破坏自然界的和谐,还要效法自然和谐的法则实现人际和谐,在自然与人和谐统一中享受和谐的人生,实现天地人一体,宇宙自然社会人生和谐统一的整体境界,这也就是曾点所描述的“风乎舞雾”、“泳而归”的审美人生境界。
道家对和谐的热爱与追求却表现为与社会的冲突。他们是社会的叛逆者,认为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很难实现真正的和谐,社会人际的和谐往往是人为的,虚假的,既不自然也不自由。因此他们把目光投向宇宙自然,从天地之和中求得心灵的安慰,与儒家追求“人和”相对,他们以实现“天和”为最高旨归。“夫明白于天地之德者,此之谓大本大宗,与天和者,所以均调天下者,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庄子·天道》)均调天下只是实现了人际和谐,个体在社会中能够感受到与人相处的乐处,却未能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不能与物同乐,在宇宙中他还是一个异己分子,并未能获得完全彻底的快乐。只有当人类与自然万物融为一体,自同于宇宙大全,与天同和,与物同乐时才是实现了真正的和谐,获得了终极的生命愉悦。
二、儒道两家境界哲学都具有深沉的宇宙意识和浓郁的生命情调
儒家在强调人是社会中的人,是社会一分子的同时,还意识到人也是自然界之一物,是宇宙之公民。作为社会一分子,人要尽人伦尽人职;作为宇宙之公民,人要尽天伦尽天职。孟子认为以人在宇宙中地位而言,人又称“天民”,“天民”具有“天位”与“天职”,居“天位”便要尽“天职”,所以要尽心知性以知天,存心养性以事天。知天事天是人作为宇宙公民应尽的义务。《中庸》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作为宇宙之公民,人不仅要“尽人之性”,还要“尽物之性”,担负起“参天地赞化育”的任务,实现人与整个自然和宇宙的同一,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与儒家相比,道家表现出更为深沉的宇宙意识。道家是宇宙自然本位论的哲学,不管是老子还是庄子,都是立足于宇宙自然,把人看成是宇宙之一分子,天地间一物,认为人应自觉融入自然,与万物为一体,自同于宇宙大全,让自我意识消匿于宇宙意识中。庄子更是站在宇宙的高度上俯视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面对广大无限之宇宙慨叹人类何其渺小,否定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与盲目的优越感。同时又觉得人作为宇宙一分子,应有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精神境界,有一种与宇宙同体的超越意识。
儒家在强调人的道德本性时并不否定人的生命感性。承认食色情欲为人的自然生理需求,强调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与抒发,重视感性,爱惜肉体,并能由珍惜一己之生命出发推及宇宙间一切生命形式,把一片仁心爱意普施到宇宙间一切生物身上。《孟子·尽心上》:“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体现出泛爱生生的思想。另外,儒家虽满口仁义道德却并不板起面孔来训斥,而是让人在活泼泼的感性生命中去自己领悟,故在儒家道德宇宙中却流荡着无限生机,洋溢着无穷无尽的生趣。如《中庸》云:“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鸢飞鱼跃,生意盎然,生趣滔滔。儒家哲学便是在活泼泼的生命形态中察视内在的生理,寻找人类伦理道德的客观依据,具有浓郁的生命情调。道家较之儒家更加注重人的自然生命,老子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老子》三章)之论。庄子在《养生主》中提出“养生之方”,在《庚桑楚》中又借老子之口说出“卫生之经”,在《达生篇》中提出要畅游生命。对生命的重视与爱情在道家文化哲学中具有普遍影响,从老子提出要“实腹”、“强骨”,回归生命之本根,庄子要尽情畅游生命,到道教的修炼养生活动,生命问题成为道家文化哲学关注的中心,道家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便是一种生命哲学。而道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个体回归生命之所,实现与宇宙生命合一的生命境界。
三、儒道两家境界哲学都强调超越自我,都属于自我超越的哲学
儒家认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实现,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孔子在总结他一生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实现了自我超越。孟子认为个体人格的完成经过了六个层次:“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这也是一个不断地超越,不断地自我提升的过程。善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信则是真实的自我存在,美是自我存在的充实,大则是对善与美的发扬广大,圣能化育天下,神是圣而不可测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了与天地同其在,与宇宙同其大的“天人合一”境界,是实现了自我超越,达到普遍和无限的终极境界。“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孟子·尽心上》)
道家老子提出:“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主张超越感性自我,实现“真我”。“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老子·十六章》)提出要恢复自然本性,回归生命之本根,实现人的本体存在,达到“与道同体”的自我超越的本体境界。庄子认为达到道的境界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庄子·大宗师》篇中就记叙了这个过程:“吾犹守而告之,参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先要把天下置之身外,既而要去除物欲之累,进而要置生死于度外。然后才能豁然开朗,随遇而安,洞见大道,达到与道同体,无古无今,不生不死的永恒的本体境界。
儒道都强调自我超越的过程,儒家指的是道德本体的超越,人格境界的提升,道家境界的提升,道家则是个体精神上的超越。儒家是要使自己成为道德主体进入道德自由境界,道家则要实现本体之我进入永恒的本体境界。但两种超越之间亦有相通之处,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1.超越有限,实现无限与永恒。儒道两家都认识到个体生命的有限。儒家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论语·子罕》)的生命叹息,时间像流水般流逝,生命是如此短暂!道家有“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却(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庄子·天下》)的感叹。大化流行,冥漠无迹,人如尘埃,随其翻转,生命何其有限!如何使这有限之生命具有无限与永恒的意义?儒道两家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儒家认为肉体生命虽然短暂,道德生命却是永恒的,提倡为了道德理想的实现,可以舍弃有限的生命形式,杀身成仁,舍身取义。道家认为个体生命虽然有限,宇宙生命却是无限,提出要“归根复命”,回归生命之所,把自己的生命与宇宙大生命融为一体,投身于生生不息的大化洪流之中,从而实现无限与永恒。殊途同归,儒道两家都超越了有限而实现了无限与永恒。
2.超越有形,进入无形。儒道两家都主张超越感性自我。儒家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他们主张克制感官欲求,屏除形体之“我”,把自己变成道德的化身,实现仁的境界,从而超越了有形的物质界而进入无形的道德宇宙。道家老子提出“少私寡欲”,庄子提出了“心斋”、“坐忘”、“吾丧我”的境界,主张限制形体感官之欲,忘记形体之“我”的存在,泯灭自我意识,恢复“我”的本然状态,成为大道之化身,从而超越了有形之现象界而进入无形的本体界。
3.超越小我而成就大我。儒道两家都主张超越一己之小我而成就宇宙之大我,超越有私之小我而成为主宰之大我。儒家孟子提出要“居天下之广居,至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孟子·滕文公下》),主张人不仅要成为自己的主宰,还要成为社会的主宰,宇宙的主宰。他的人格理想是做一个不为贫贱所移,富贵所淫,威武所屈,浩然之气,充满全身,充塞天地的“大丈夫”。而他所谓的“大丈夫”便是一个超越食色、生死等形体之私,一己之限,实现了与宇宙精神相交通,与天地相合一的“大我”形象。道家庄子认为,人应有“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豪迈气概与主人翁精神。他的人格理想是“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庄子·天下》),“上与造物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同上),“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洹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庄子·齐物论》)是超越相对之我而实现绝对之我,超越形体之我而成为宇宙精神化身的“大我”形象。
综上所述,儒道两家都以提升心灵境界为哲学的根本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儒道两家都是境界哲学,但两家所追求的终极境界并不相同,这使他们常处于一种相互抗衡的状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的两大主干。但儒道两家境界哲学亦有许多相同相通之处,这使他们又能互补,共同支撑着中国人的心灵。
收稿日期:1998-03-18
标签:儒家论文; 孟子·尽心上论文; 儒道论文; 国学论文; 道家论文; 孟子思想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孔子论文; 孟子论文; 老子论文; 读书论文; 论语·述而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