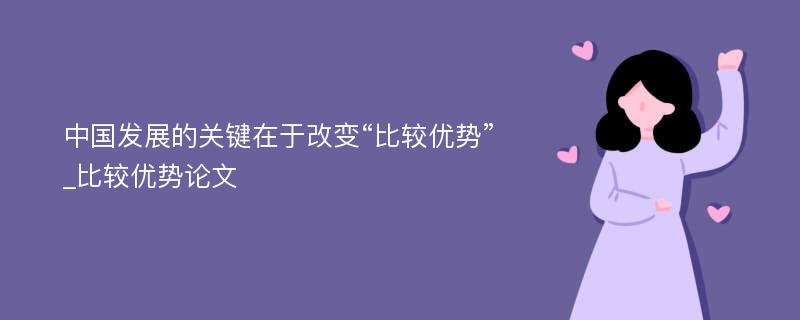
中国的发展关键在于改变“比较优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关键在于论文,中国论文,比较优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最近十来年,“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盛行于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宏观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东部沿海的经济发展成就被认为是“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的应用效果,在这个经济理论的引导下,东南沿海地区利用了“中国劳动力价格较低的比较优势”,逐步占领了纺织服装、轻工产品、家用电器等国际市场。中国经济目前也因为这个理论转型为外向型,国际贸易的总量增长用GDP发展论的眼光来看还是令人欣喜的,然而高速发展的GDP并没有带来高速增长的GNP,大量的劳动民众已经对带不来收入增长的经济增长感觉失望,同时,过高的外向型经济比重已经开始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
其实,“比较优势”理论不过是一个商人的生意理论,而我们却在该经济理论的教导下,不是围绕着增强综合国力水平而发展,而是以最大限度增大国库收入的“赚钱路线”为中心。中华古谚说:“国之上下交相言利,国之危矣。”这个“交相言利”的理论就来源于“比较优势”理论,在这个表面华丽的理论诱导下,我们忘记了中华古训“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的立国之本,而是整天比较来比较去,寻找赚钱的机会,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混同于公司的经营发展。
“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的三个误导
“比较优势”理论是一个时髦的西方经济学词汇,其含义并不深奥,用中国俗话来说就是“因势利导”。无可厚非,这是一种很明智的方法。对于一个企业发展,采用“因势利导——比较优势”发展自己的深厚技术优势或者廉价的人力优势,比如依托技术资源雄厚的大学发展高科技企业,依托资源丰富的山区发展绿色农业等等,用这个“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企业发展都是很有用的。但是对整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世界级大国而言,片面强调“比较优势”就是理论用错了对象,最起码也是没把中国看成一个“具有多产业的集团公司”。国际关系的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很多产业发展不是取决于基础条件而是取决于战略需要,中国能不需要先进的航空产业吗?能不需要先进的机床产业吗?能不需要先进的通信产业吗?
首先,“比较优势”发展理论所引申出来的一个说辞是所谓的“国际大分工”。然而,这个“国际大分工”到底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则语焉不详。如果说“国际大分工”是先天的,那么今天的美国不应该成为发达国家,以色列、日本更不应该成为发达国家,而最发达的国家应该还是老牌工业国家英国和法国;如果“国际大分工”是后天的,那么“比较优势”理论又为什么反对“赶超”,反对“自主”?这个“国际大分工”根本就不可以自圆其说,是一种很荒唐的经济学说法,由于以讹传讹年代久远,已经不可考察当年的出处,但是现在依然误导着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前一个阶段龙永图和何光远争辩“自主品牌”也是这个问题,龙先生的理论依据就是“国际大分工”理论,说根据国际大分工的原则世界上就只需要“六大三小”这几个大型的国际汽车企业,中国汽车不需要搞什么自主品牌。事实若真如此,我们就不禁要问上一句了:最近几年韩国现代汽车的成就是从哪里出来的?韩国现代相对于美国通用怎么进行“国际大分工”?
再说说这个“比较优势”发展理论的另一面——“反对赶超”的问题。中国上世纪的“超英赶美”到底是为了中国的战略需要还是“好大喜功”?当年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非常险恶,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不断在中国周围发动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和“一五”、“二五”计划成功完成的鼓舞下,为了让中国保持更可靠的独立自主,才提出“超英赶美”的经济口号和实行了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可以说,“赶超战略”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而在于“赶超战略”的效果和“赶超战略”的国家安全意义。而这个“反对赶超”的经济理论,其结论却是引导中国经济建设削弱自己的尖端科技投入,削弱自己的战略支柱产业投入,削弱自己的民族产业,运十下马、“中华之星”搁置的惨痛教训就是这个理论滥觞的结果。
最后,从中国战略产业发展的视野,来论证“企业自生”理论的不合理。在民族产业经济学者看来,企业的利润不管是来自垄断的市场还是来自自由的市场,企业本身都不仅仅是资本利润的制造工具,每个企业的产品都有它特定的“社会使命”。食品公司是给社会创造饮食的,家电企业是给社会创造娱乐的家用电器,军工厂是给国家提供国防安全的产品。在一定条件下,企业的社会职能还可以延伸为国家职能,了解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工业史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卢作孚先生的民生公司在1938年进行宜昌三峡大抢运,中国的抗战历史就可能要改写,这是企业发挥国家职能的最好案例,也是对那些“经济是经济、政治是政治”言论的最好批判。君不见,企业的国家职能在日本工业企业中尤其明显,日本没有任何军工企业,军工生产线都是在民营企业中和民品生产线混用的,而且经常是在亏损状态中为国家职能而保养维护着,三菱公司在这方面做得尤其充分。企业自生也好,他生也好,归根结底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利润决定自己的生存,企业自身的社会职能也能决定自己的生存,难道美国和日本就是纯粹的“自由、开放和竞争的市场”吗?事实上,美国、日本、欧盟都在对它们所需要的企业进行大额补贴,并由此引致国际争端不断。
关键在于改变比较优势
西方主流经济学论证各国实行自由贸易的好处,主要的理由就是它能够使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出口自己的相对生产率比较高的产品,或者出口产品密集地使用本国相对丰富的资源。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必定使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相对价格较低,从而在国际贸易中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没有贸易壁垒的自由贸易会让这种优势充分发挥出来,结果,各国都仅出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自己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使各国的福利都达到最大。
统计表明,各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大体上合乎“比较优势”学说,这只能证明当代世界各国在国际贸易中都已经大体上发挥了它们的比较优势,却并不能证明发挥比较优势会导致成功的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少数落后国家成功地发展了经济,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获得快速的经济增长,其经济发展并不成功。这些经济增长比较慢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证明,简单地发挥“比较优势”并不是成功地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
当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的经验都证明,富国之所以人均收入极大地高于穷国,主要是由于富国平均每人掌握的科学技术水平极大地高于穷国,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均掌握的科学技术快速增加。将这一原理应用于说明国际贸易结构,就可以看到,虽然富国与穷国都在国际贸易中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但富国之所以富,就在于它生产并出口的是技术密集产品,而穷国之所以穷,就在于它只能生产并出口技术含量比较低的产品。
由此可知,一个国家持续的高速经济增长必定也伴随着其比较优势的内容变化,成功的经济发展必定是一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从技术含量低的产品变为技术密集型产品。这已经为二战后日本,韩国等地区的高速经济增长历史所证实。它们在高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支柱产业都经历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技术含量低的纺织业经过钢铁、造船或日用百货、计算机而变为汽车或集成电路等高度技术密集的产业。
成功的经济发展的关键不是简单地发挥比较优势,而是改变比较优势,将低技术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转变为生产高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这样转变比较优势的速度越快,经济发展和增长的速度就越高。为了尽快地完成这种比较优势的改变,就必须大力开展学习和自主的研发,以便尽快增加和提高本国所掌握的技术。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话说,这就是“加快技术进步”。
为了尽快增加和提高我国所掌握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就需要保护我国高技术的幼稚产业,以适当的贸易壁垒来阻止外国高技术含量产品的进口,将国内的市场留给我国的高技术产品。这样的保护措施虽然可能通过许多途径妨碍本国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出口,并且导致一国的比较优势不能得到完全的发挥。但是,这样做有助于加快我国的技术进步,进而促进我国的“产业升级”。
现在的经济发达国家在由落后变为先进的过程中,都曾经对能提高本国技术水平的产业大力实行贸易保护。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韩国也在实现高速经济增长的时期大力保护了本国的关键产业。这样的保护并不妨碍我们观察到上述的事实:这些国家的进出口结构仍然大体上合乎古典比较优势学说的预言,出口相对生产率高的产品,进口相对生产率低的产品。因为对本国高技术产业的保护只是减少了本国没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的进口,这些国家出口的基本上还是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的还是外国有极强的比较优势的产品,只不过这些国家的进出口规模小了一些,对外贸易依存度低了一些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