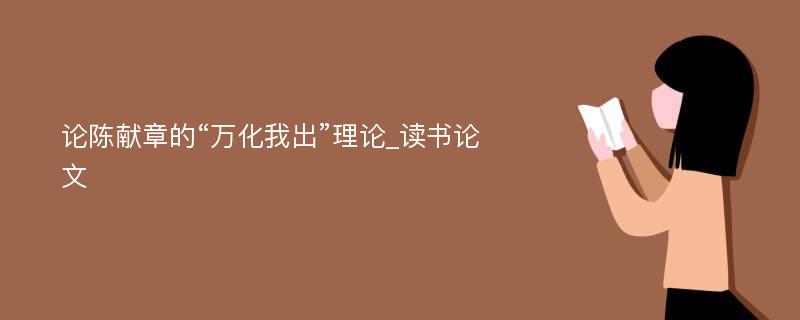
简论陈献章的“万化我出”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简论陈献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摘要] 陈献章提出的“万化我出”说,上承朱熹、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构成宋明理学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他认为,心是与道相对而言的主体,心虽离不开身,但具有至上性、主动性。人借助于心与道相通。基此,他提出天人一气、天人一理、天人合德、天人同体等命题,阐发儒家的天人合一观。他认为,天人合一的关键在于人,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陈献章的人学思想强调自我,强调在道的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任何人都有进入与道同体境界的机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市民倾向。
[关键词] 天 人 心 道
陈献章,字公甫,号石斋,广东新会县白沙村人,世称白沙先生或白沙子。他是一位有思想原创力的哲学家。陈献章自述:“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阳。”[①]他师从朱子,又走出理学,上承陆九渊,下启王阳明,成为明代心学的开山。人们根据陈献章的“万化我出”说,常常把他同陆九渊、王阳明相提并论,其实,他的“万化我出”说既不同于陆九渊的“心即理”,也不同于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表达了他关于天、人以及天人关系的独到见解。
一
陈献章看来,人的存在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从物质存在的意义上看,人是物质的存在物,这就是人的身体。人的身体作为万物中的一物,同其他事物相比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仅从物质存在的意义上看,人与动物并没有什么两样。“人具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着一大块骨头。”[②]倘若“凡百所为,一信血气”,这样的人称之为禽兽亦未尝不可,因为在他的身上并没有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质。从陈献章的“禽兽说”可以看出,他不同意仅从物质存在的角度看待人。
从陈献章的“天道自然”论的角度看,肉体意义上的人,可以说天人同质或天人一气,即天人都是气的表现形态。他指出:“元气之在天地,犹其在人之身。”[③]元气构成“耳目聪明”的生理机制,因而对个性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影响。陈献章认为,气禀仅构成人的形而下的方面,而不是形而上的方面,故而他并没有用很多精力去研究。
从精神存在的意义上去看,人是意识的主体,这就是人的心,或者称为自我意识。在宋明理学中,理学家最关心的哲学范畴之一就是心,而分歧最大的也是心。关于心的看法,大体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朱熹一派的看法,认为心不属于形而上的范围,而属于形而下的器。陈淳在《北溪字义》中解释说:“心只似个器一般,里面贮的物便是性。”陆九渊一派认为,心就是理,心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声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④]。
陈献章关于心的看法,既不同于朱熹一派,也不同于陆九渊一派。他综合两派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他没有完全把心看成形而上的本体,因为在他看来,本体只能是作为客体的道,而不能是作为主体的心。所以,他没有接受陆九渊“心即理”的提法。他强调心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具体的心,并非抽象的心,身与心有着密切的联系。“此心一到,精神俱到。”换句话是说,心作为精神主体,必须以身体为生理机制才能发挥作用。心离不开身,心不能单独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心是形而下的。在这里,他肯定身心的一致性,部分地接受了朱熹一派“心只似个器一般”的观点。不过,他不赞成只把心看成性的存储器的看法,因为这种看法似乎对心的认识能力作了限制,没有充分估计到心的能动性和至上性。他没有对心的认识能力作任何限制,是其与朱熹理学一派的一个明显区别。
在处理身与心的关系时,他一方面承认身与心的一致性,另一方面却强调心的主导作用,认为心“寓于形而为之主”。心虽然要通过身体得以表现,但它却是支配者,心的认识能力不受身的限制。正是因为它不受身的限制,方显出它的可贵,使人获得异于禽兽的特质。在他看来,心是独立的、主动的。强调人的能动作用,这是陈献章人学思想的特色之一。
正因为心的认识能力是不受身体限制的,可以以任何客体为认识对象,当然也可以以天道为认识对象。心既是一身的主宰者,又是能够接受天道的主体。在陈献章看来,心就是构成主体与客体相互联系的通道,能够使人达到与天道同一的形而上境界。他说:“心之大用,初无不该。”又说:“高明之至,无物不覆,反求诸身,把柄在手。”[⑤]“高明”是指天道,意思是天道无所不在;“把柄”是指心,意思是只要发挥心的作用便能把握天道,使之由自在之物化为为我之物。在陈献章看来,心虽然不是陆九渊说的那种形而上的本体,但它却是人进入形上境界的根据。通过发挥心的作用,就可以使人超越身体的限制,把自己从万物中的一物提升到形而上的本体存在。
归结起来,陈献章关于心的看法包括以下几个具体观点。第一,心以身体为生理机制,心离不开身。第二,心是人的主宰,他称心为“神气”,强调“神气人所资”。心就是人资以为生的神气,没有了心,人就不能成其为人,失掉了作为人的价值。人正是因为有了心,才把自己同其它动物区别开来。第三,心的作用有至上性。心虽是方寸之地,却具有无限的容量。它是人所认识道、体验道、把握道的唯一途径,是人之所以能够“道化”即进入形上境界的根据。第四,心具有主动性。道是自在的、被动的客体,“天道至无心”,天道不以人心为转移,也不会自动地进入人心。人要认识、体验、把握天道,必须反求诸己,使把柄在手。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陈献章虽不否认人的物质存在(身),但更看重人的精神存在(心)。他把心看成与客体的天道相对而言的主体。
二
陈献章立足上述心学理论,进一步讨论了天人关系问题。他接受儒家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并且作了四点发挥,提出一组命题。
(一)天人一气。陈献章认为,天和人都以气为物质基础,人的身体来自气,天地万物也都来自气。在他看来,这是不证自明的事实,故而并没有用多少笔墨详加说明。
(二)天人一理。他在《天人之际》一诗中写道:“天人一理通,感应良可畏。千载陨石书,春秋所以示。客星犯帝座,他夜因无事。谁言匹夫微,而能动天地。”他在诗中明确肯定天人一理相通,都遵循着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正因为天人一气相贯、一理相通,故而可以互相感应。其实陈献章的天人感应思想主要来自董仲舒的影响,并非是他的发明,也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首诗中并不怎么注重天与人的感应关系,而着重强调的是天人一理。并且得出“匹夫动天地”的新结论,这就使他的天人合一观有了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不同的新内容。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中的“人”特指封建皇帝,宣扬君权神授的帝王思想;而陈献章的天人一理说中的“人”是指平民百姓,表达的是平民意识,旨在唤起人的责任感。他所说的“天”是一种自然的运行变化过程,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这同董仲舒把天视为万物的主宰者的看法显然有本质区别。陈献章提出天人一理的命题,无非是说天地万物与人都遵循着最一般的规律,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考,只不过披上了一层天人感应的外衣罢了。
按照陈献章的看法,既然天人一理,那么,人就应当取法乎天,遵循于理。他在《程乡县儒学记》中写道:“夫子太极也,而人有不具太极而生者乎?”在宋明理学中,太极常常被当作天理的同义语,陈献章沿袭了这种用法。他指出:既然为人师表的孔夫子都把太极奉为圭臬,我们普通人还能离开太极而生存吗?陈献章虽然沿用了理、太极、天理一类的理学用语,但赋予其不同的含义。在朱熹哲学中天理被赋予伦理规范的含义。朱熹在提出“宇宙之间,一理而已”的命题之后,立即从中引申出“其张之为三纲,其纪之为五常”的伦理规范。陈献章的“天人一理”思想同朱熹“宇宙一理”的观点类似,但他没有给天理涂上伦理色彩。他心目中的天理,只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流行变化过程,同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同他的“天道自然”的本体论是一致的。在陈献章哲学中,天道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自在之物,他在《次韵张东海》一诗中写道:“道超形气元无一,人与乾坤本是三。”天道并不直接地干预人事。朱熹的天人一理说给人一种紧张、敬畏的感觉,陈献章的天人一理说并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只给人一种精神上的归依感。陈献章说:“神理为天地万物主本,长在不灭。人不知此,虚生浪死,与草木一耳。”[⑥]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没有“天理”意识,就等于虚度一生,同草本没有什么区别;只有确立“天人一理”的观念,才算获得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在这里,他把天理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终极归宿,而没有视为社会伦理规范的形而上学依据。
(三)天人合德。这是陈献章从主体方面对“天人一理”原则的引申和发挥。“天人合德”的提法,初见于《易传·文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孟子·尽心上》也有“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在天矣”的说法,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陈献章接受了儒家的这些传统的思想,对天人合德的观念表示认同。在他看来,“天人合德”中的所谓“德”,就是儒家一向重视的“诚”的心境。他在《无后论》中写道:“此心存则一,一则诚;不存则惑,惑则伪。”这就是说,心是把天与人贯通起来的中介,正是通过心把天与人合而为一;对于人来说,天人合德就是造就一种“诚”的心境,而不是“伪”的心境。他所说的“伪”是指言行不一,即表面上表示拥护天人一理的原则,而骨子里却加以拒斥。对于这种伪善的态度,陈献章十分厌恶。他指出,“诚”是开万世的根本,而“伪”是丧家邦的祸根。只有立足于诚,才会有宽广的胸怀和坦荡的心境。“盖有此诚,斯有此物;则有此物,必有此诚”[⑦]。“诚”是人所拥有的最完满的心境,也可以说是人心的全部内容;人们拥有了“诚”的心境,才可以自觉地参与天地间万物大化流行的过程,担负起“开万世”的重任。只有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有道君子。“诚”是天地万物发生发展真实无妄的根本道理,也是人认同这一道理的最佳心境。
“诚”是儒学的主要范畴之一,可以从主体与客体两方面理解。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⑧]他从客体的角度界定诚,把诚视为天道的同义语。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⑨]他从主体心态的角度界定诚,强调诚是心性修养达到的最佳心境。《中庸》则把这两种用法综合起来,写道:“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理学家周敦颐、程氏兄弟乃至朱熹一般都从客体角度理解诚,认为诚的意思就是无妄。朱熹在《中庸注》中写道:“读者,真实无妄之谓。”无妄意即无虚妄、真实无误的意思,于是,诚变成了凸显天道实在性的修饰语。
陈献章对诚的理解与宋代理学家们有所不同,他不是从客体的角度而是从主体的角度界定诚,强调诚是人们认同于天道的心境。陈献章认为人们在天道面前,应当抱着一心一意、真诚归依的心态,而不应当抱着虚与委蛇的伪善心态。在陈献章哲学中,诚主要同人道相联系,而不是同天道相联系。他倡导真诚的人道是有感而发的。在他生活的时代,儒学已不再是读书人的真诚信仰。大多数儒生读书只是为了猎取功名,一旦金榜题名,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把儒学讲的道理抛到九霄云外。对于他们来说,儒家的道理完全是外在的,并未真正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毫无真诚可言。正是针对儒学的这种工具化倾向,陈献章才大声呼唤天人合德,呼唤人们对于天道的真诚信仰,抨击那种伪君子式的人生态度,要求重新建立起“诚”的心境,做一个真诚的儒者。陈献章对“诚”的另一种新的理解是顺其自然,这同他的“天道自然”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在他看来,天道至诚无妄,天自然成其为天,地自然成其为地,万物自然成其为万物,没有半点矫揉造作;人取法至诚无妄的天道,就应当养成至诚无妄的心境,顺应天道行事,不要受到个人私欲的干扰。他说:“圣道至无意。比其形于功业者,神妙莫测,不复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⑩]这里所说的“至无意”就是放弃个人狭隘的功利目标,顺应自然,一切以天道为归宗的意思。在他的心目中,“至无意”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拥有“诚”的心境的尺度。一个人一旦养成“至无意”的心态,他便成为自己内心世界的主宰者,而不再成为功名利禄的奴隶。他主张“以自然为宗”,以道为安身立命之地、为精神家园,体会人生的真谛,真诚圆满地度过一生,绝不要自己欺骗自己。
(四)天人同体。陈献章在《致湛民泽》的信中明确提出“人与天地同体”的命题。这是他从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角度对“天人一理”的发挥与引申,也是他所追求的最高的得道境界。他在《题吴瑞卿采芳园记后》写道:“随时屈信(伸),与道翱翔,固吾儒也。”他指出,儒家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天人同体、与道翱翔的境界。天人同体的意思是实现天道与人道的统一,这里的“体”是指作为终极本体的自然之道,他主张以道为基础实现人与道的统一,实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按照他的“天道自然”本体论观点,天地变化,草木蕃时,是万物的自然;随时屈伸,与道翱翔,是人的自然。站在道的立场上看,这两方面是同一的,所以说“天人同体”。
陈献章指出,天人同体是人的道化,而不是道的人化。换句话说,天人同体是人追求道的过程,因为只有人才具有主动性、能动性,才可以设立追求的目标;而道作为客体来说是被动的,当然不会主动地追求与人同体。他在《认真子诗集序》中说:“夫道以天为至,言诣乎天曰至言,人诣乎天曰至人。必有至人能立至言。”他在文章中经常使用“得之”、“会此”、“凑泊吻合”等字眼描述人主动追求与道同体的心路历程。为什么说天人同体是人的道化而不是道的人化呢?因为道在陈献章的哲学中是自然的本体或实体,具有自在性,天自己成其为天,地自己成其为地,每一事物都是自然的存在,并不受外力的干预,“宇宙内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动自静,自阖自辟,自舒自卷;甲不问乙供,乙不待甲赐”(11)。也就是说,天道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在之物,当然不可能自动地实现人化。与天道相对而言,人具有主动性,有能力将天道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不过天道由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后,并不意味着天道服从人,仍旧是人服从天道。他在《与林郡博书》中指出,人得道之后,进入“往古来今,四方上下,一齐穿纽,一齐收拾”的境界,但在这种境界中仍需遵循“色色信他本来,何用尔脚劳手攘”的顺道自然的原则。换句话说,人们进入天人同体的得道境界后,并没有取得支配一切的权利,只不过是达到了顺道自然的自觉而已。进入天人同体境界中的人有那些特征呢?陈献章指出,第一,在这种境界中的人摆脱了名缰利锁的束缚,真正获得了超越感。他在《随笔》中这样形容得道之人:“断除嗜欲想,永撤天机障。身在万物中,心在万物上。”“嗜欲想”是指小我的私欲。私欲是妨碍人进入天人同体境界的最大障碍,只有除掉了这个障碍,才能进入得道境界,获得心灵的解放。进入天人同体境界的人,身体虽然仍为万物中之一物,但他的心已超越万物之上,他既世间而出世间,有一种类似宗教的体验,与佛教中讲的“得证真如”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在写给太虚和尚的信中说:“太虚师真无累于外物,无累于形骸矣。儒与释不同,其无累同也。”(12)他以儒家的方式实现了对小我的超越,获得心灵的宁静,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
第二,在这种境界中的人真正有了自我意识,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陈献章在《论前辈言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上篇中指出,对于得道之人来说,“天道之始,吾之始也,而吾之道无所增;天地之终,吾之终也,而吾之道无所损。”他有了真正的自我意识,真正成为认识道、体验道、掌握道的主体。这种人与天道为一,精神上不再受任何限制,遗世独立,真正获得了精神自由。陈献章写道:“天地无穷年,无穷吾亦在。独立无朋俦,谁为自然配?”(13)]得道之人首先必须是独立的主体,然后才说得上得道。掌握了道,掌握了自然,也就是掌握了自由。在这里,他接触到“自由就是掌握必然”的辩证法。陈献章用诗的语言描绘精神上的自由,如“江门洗足上庐山,放脚一踏云霞穿。大行不加穷亦全,尧舜与我都自然。”(14)诗中所描绘的境界,正是达到天人同体的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境界。
第三,在这种境界中的人真正体味到形而上的意义,充分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陈献章在《与林郡博》的信中这样形容与天同体的人:“此理干涉至大,无内外,无始终,无一处不到,无一息不运,会此则天地我立,万化在我,而宇宙在我矣。”这里的“我”显然不是人的肉体,而是人的精神、人的心。人心作为主体来说,本来是同作为客体的道相对而言的;但进入了天人同体的境界后,主体与客体已经完全统一起来了:人通过心从道那里获得了形而上的本质,从而成为道的自觉的体现者。在陈献章哲学中,道是宇宙万物的实体和发展演化的自然过程,具有无限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得道之人已成为道的化身,他将道的无限性、普遍性和永恒性充分地体现于一身之微中。对于得道之人来说,他的精神世界与道已合而为一,不再有主体和客体的分别。
三
一些研究者抓住陈献章“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一类的话,把他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者,这是一种误解。因为陈献章在这里不是描述客观事实,而是描述天人同体的精神境界。在对天人同体境界的描述中,他似乎把天道、万化、宇宙都归结为我,其实并没有因此而取消道的本体地位。他是在肯定天地道立、万化道出、宇宙在道的前提下说这番话的;这些话只适用于那些得道之人,并不是一般性的判断。其意思无非是说,对于得道之人来说,他的精神主体已取得了与道同等的意义。因此,对于他来讲,可以说“天地道立,万化道出,宇宙在道”,也可以说“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得道之人只是体味到道的形而上意义而已,并不意味着他的心就是宇宙的本原。由此看来,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对于陈献章来说并不合适。
陈献章在处理道与心的关系问题时,同陆九渊、王阳明是有区别的,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一类的命题。他始终把道的实在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基本点,并没有把道同心直接等同起来。他承认道与心具有同一性,但在他的哲学体系中,这种同一性是在克服了道与心的对立之后实现的。道与心的第一层关系是道心分立。道是本体,同时也是客体;心为主体,心是道的一部分,心从属于道。第二层关系是心追求道。道虽然具有实在性,但没有能动性;只有心才具有能动性,只有心才可以使人获得求道的能力。第三层关系是道心合一。道与心完全地溶为一体,不再有主体与客体的分别:我心即是天道,天道即是我心。但这是心经过长期涵养之后实现的,况且并不是任何人都能进入这种境界。陈献章关于道心关系的看法,显然比陆九渊“心即理”的粗疏之见精致得多,深刻得多。他在承认道的客观实在性的前提下,阐扬心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之教无疑具有启迪作用。
综上所述,陈献章提出“天人一气”、“天人合德”、“天人同体”一组命题,以独到的方法对天人合一观念作了新解释。在这组命题中,天人一气是基础,天人一理是核心,天人合德是最佳的心境,而天人同体是最高的道境。这组命题论说的重点是人,而不是天,因为天与人能否合一,关键取决于人。陈献章的人学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第一,他强调自我,强调在道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只要认真涵养心性,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得道境界,从而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市民倾向。第二,他肯定心是人掌握道的根本,认为万化道出可以转化为万化我出,对心的主体性作了充分的肯定。他承认道的实在性,但没有凸显道的绝地性和权威性,尤其是没有把道同封建伦理规范相联系。他强调人有求道、掌握道的自由,把人从封建伦理的大网中突出出来,因而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
注释:
①②③⑤⑥⑦⑩(11)(12)(13)(14)《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79、61、107、278、234、57、57、242、225、309、315页。
④《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3页。
⑧《孟子·离娄上》。
⑨《荀子·不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