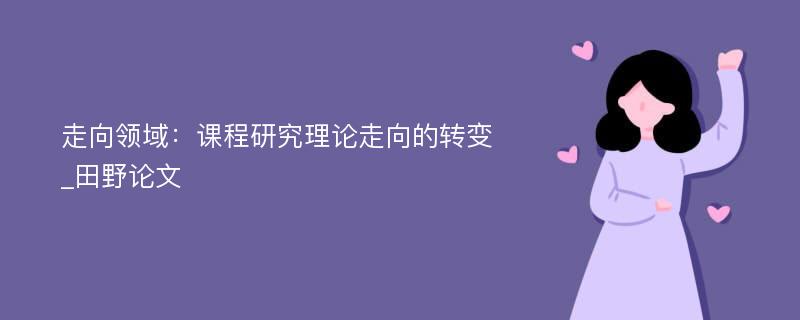
走进“田野”:课程研究理论化趋向的改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田野论文,课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学中有田野文化与书斋文化的区分,也即是基层文化与高层文化、俗文化与雅文化的区分,不断地消除这两种文化的隔离,实现田野与书斋、基层与高层、俗与雅的文化架构,是文化演进的必然。中国自古有“礼失反求诸野”的传统,这种传统的文化意义表明:高层雅文化如果发生某种失落,就需要到基层民间的俗文化中去寻求。本文以走进“田野”为题,讨论课程研究理论化趋向的改造,虽然主要讨论走进课程实践的问题,但是希望对它的理解能比课程实践更宽泛,因为课程问题在其现实性上只能是个宽泛的文化问题。
毛泽东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天天念的理论和实际联系,在许多同志中间是个糊涂观念。认为:“他们天天讲‘联系’,实际上却是讲‘隔离’,因为他们并不去联系”①。教育理论与教育之间的联系和隔离问题可能是最令人尴尬的,因为它们简直就像是两个文化圈里的事,自说自话的理论,自行其事的实践,而且各自心照不宣。
一
有关课程及课程研究的理论,可谓学科壁垒森严,它可以毫不理会课程与教学的实践,自成一套书斋里的范式或观念。由于制度化规定而不得不学些理论的实践者们,逐渐习惯了这种由理论霸权支持着的文化隔离,往往会很宽容地不多苛求理论接受实践检验。
我们的课程研究中原创的理论不多,拿来的理论则从一开始就失落了它们赖以存活的实践。这让书斋里的研究变得简单也轻松,只需要就理论研究理论,甚至是各色理论只要词语相同或相近,就可以通过比较判断进行拼装组合,就可以得出研究“定论”。这些定论到底定在哪里恐怕也是个糊涂观念,既撇开了产生它的实践基础,也未曾栽进借鉴它的泥土地里,它只能是书斋里的想当然的定论。譬如,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现过多种课程理论,它们必定都有其复杂的文化基础,但如果简单地把它们概括为几种僵化的类型,就可以造出许多“定论”来。从课程目的论的角度分类,可以把课程类型依照社会、学科、人本的不同取向来分析;从课程发展的角度分类,则可以找到学科、活动、结构的线索来分析;从课程样式的角度分类,还可以归结成学科、活动、综合、核心的类型来分析。事实上哪种分类都还能变着说法研究并且创新,只要不以此时此地的实践来检验,也无须尊重彼时彼地课程实际上曾经发挥了怎样的文化发展功能,书斋里的研究观点就能层出不穷。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只要类型分定了,各类型的特征功能以及优劣褒贬也就清晰可辨,课程的历史一下子就明朗起来,也说不清课程真是像这般切割整齐的样子发展过来的,还是研究者们主观武断地削课程之“足”来适自己的理论之“履”的?但是定论总给人一种深刻印象:以往的人类智慧都是僵滞分割的,他们设置课程要满足社会需要,断然不会想到个人,他们划分学科尊重科学体系,断然想不到应用时学科要综合等等,唯有研究者慧眼识历史,把各种是非曲直尽收书斋,课程才得以完美无暇。活生生的课程真是这样的吗?
再譬如,课程研究的研究,这也被称为元研究,显然是更高层次的研究,由于它的田野就是低一层次研究的书斋,这与课程实践隔离得就更远。尤其是有了库恩的“范式”,古今中外文化历史研究,当然也包括课程研究之“足”,终于都有“履”可适了。原来,课程研究走过的道路都是由一组观念、价值和规则所“支配的”,研究者们研究的行为、解释资料的方法,以及看待问题的方式,必定是在某种范式里,而且迄今为止的课程研究,概而言之主要有三大范式:知识中心的课程研究、儿童中心的课程研究、社会中心的课程研究。人们凡研究课程,必定是步入其中的某一种范式,而且特征必定清晰,因此人们就必然各自从自己的出发点出发来着重解决课程某一侧面的问题,都有不同的适应范围,也都有不同方面的局限性。有了这样假设的前提,课程研究的研究也就可以居高临下地统整三大范式,得出一系列重要结论,诸如无论是从课程的整体目标还是从受教育者本身的发展来说,课程都包含着学术本身、学生需要和社会要求这三个基本要素等等。同样令人困惑不解的是,研究者概括的研究范式,特征总那么清晰,那么准确,而且范式与范式间总那么泾渭分明,而如果想在课程实践中试图找到哪怕稍有相似的例证又几乎绝无可能。即使依照研究者提示的案例去寻找,即使找到的只是理论或文字描述的实践,也总会让人失望。譬如,没有比杜威的课程研究更该符合儿童中心范式的,但杜威研究的课程明明极符合当时的社会要求,他明明是要培养儿童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而他给儿童设计的问题恐怕也不违背社会主题。课程实践中,真有那么清晰的研究范式的证明吗?
课程研究以及课程研究的研究,如果不是基于“田野”源于实践的原创性研究,只是书斋里的制做,其结果就很值得推敲,改造的思路可能需要进行某种必要的选择:要么去寻求研究结果的课程实践,要么去考察研究者的研究实践,不能想当然地采择些理论来进行简单组合;如果研究要用来指导或启迪我们的课程研究,那就必须先沉到我们的课程实践中花一番体验的功夫,唯有切己体验才会把实践中的课程实实在在地弄清楚,诸如影响课程发展的各种因素,它们对课程到底影响如何,这只靠文本靠宣言靠理论解释是全然无用的;如果只是翻译介绍外国理论资料,这也是极有参考价值的,但这不能替代用以指导课程实践的课程研究,否则就会弄成外国理论乱点中国实践的尴尬来。
二
课程研究中的教条主义,从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理论繁荣与实践贫困共存的不和谐状况。许多研究者执迷于课程理论,不能真实地进入课程与教学的生活界域,就像花树栽不进泥土地。从实践者的立场来看,这样的研究者似乎也不懂得有的放矢,只能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或者“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①。
课程研究执迷于理念界域里的情形,的确比较普遍。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那种教育理论依赖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乃至把它们由理论基础变成基础理论的状况,就清楚地体现于课程理论。尽管不能说课程理论的领地,已由教育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瓜分,但是课程理论研究的确没有“似乎是如梦初醒,对这种教育理论初始的热情因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学科’与教育实践的脱节而冷却下来”。我们的课程理论似乎尚未觉悟到“实际的教育问题并不能从学术性学科的狭隘范围内得到解决”,也不会去关心在世界范围内,“所设想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合作实质上从未顺利地进行过”②,只是有些盲目地认为,只有充斥了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课程研究才是有品位的学术或科学,这样,课程实践、课程生活、课程田野,就在某些研究者那里显得极为生疏甚至是荒芜了。
可能施瓦布、斯腾豪斯等人倡导的“实践”观,应当可以给我们提供些启示。施瓦布主张课程理论是一种实践科学,并且对实践进行了规定性解释:“我说的‘实践’并不是庸俗管理者和一般人所认为的门外汉似的实践性,对这些人来说,实践意味着通过熟悉的手段极容易达到熟悉的目的。我指的是一种综合科学,它对学术界来说很生疏,与理论上的学科有很大差异。它是一门关注选择和行动的科学,对比起来,理论上的学科关注的是知识”②。可以认为,施瓦布理解的课程理论是在课程的实践层面,动态的选择与行动层面,是实施中的课程,是教学的课程或课程的教学,这与关注知识的课程理论不同。走进田野的改造思路正是基于关注课程在实践中的选择和行动提出来的,这既可以了解既有的选择和行动,又可以把握新课程遭遇的新的选择和行动,因此与关注知识的课程理论不同,而后者是可以不走进田野而只在书斋里拼装的。应当清楚的问题在于,课程理论与课程生活之间的冲突其实很少是在知识层面,这恰恰是新课程改革中人们培训教师摆脱不了“内容教育学”框限的失误所在,冲突更多是在选择与行动方面,是在教学方面,这正是本人主张课程改革中的教学问题,比之制定课程标准和编教材有着百倍艰难的道理③。
课程理论研究者跌落到课程观念世界的情形,与徐继存教授对教学论研究者的忠告颇为相似:“从一种即使是正确的教学思想或理论出发,以思想或理论剪裁教学现实,用思想或理论规范教学现实,都将使我们难以避免教条主义的巢臼,造成唐吉柯德式的历史闹剧”,因为“陷入自我构造的教学观念世界的教学论研究者,就会有意或无意地遗忘了教学生活世界,就容易把教学论研究当成了一种纯粹知识的追求,而不是当作一种知情意相统一的智慧探索活动”。②时下的课程理论几乎当然地在从思想和理论出发,剪裁课程现实,规范课程现实,并且用简单的省略了主语的短语“课程实施”替代了教学,这使得唐吉柯德都理直气壮了许多,而教学生活却更多了些与课程的隔膜。
走进田野的课程研究因此首先要走进课程生活,走进学校、教师群体、学生群体中去体验课程,去获得课程的体验。课程在实践中的命运与书斋里严密的理论化设想是完全不同的,不理解这里的差异只能说是理论的悲哀。进一步说,走进田野的课程研究还应走进教学生活,这是最直接的课程体验,课程研究者必须研究教学、践行教学,他“首先应该是这样一个优秀的教学践行者;而要做一个优秀的践行者,就必须是一个教学生活的体验者”②。就此可以认为,走进田野是种从最基层文化起始的选择,非此就会弄成“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钦差大臣’满天飞”①的模样,实践者只能敬而远之。
三
鉴于原创理论不多,我们的课程研究必然需要开放视野借鉴吸收外国理论精华。但是,即使是外国的理论改造外国的实践也还有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他们懂得“不能像改造工厂里的工艺流程一样改造教育的实践(学校课程和学习方法,教学法风格和教学材料)”④,那么外国的课程理论改造中国的课程和教学竟会是轻松的吗?如果我们自己的理论,实践、民族文化特色得不到充分关照,课程研究岂不只能削足适履,而不是量体裁衣吗?弄不好还可能落得个邯郸学步的结果。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实际的理论教学是“谬种流传,误人不浅”①,他还批判理论研究者说:“许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是他们对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上”①。诚然,这里所提到的谬种流传误人不浅的或空洞的理论,未必就是外国的,但外国的理论作为研究外国的实践的某种结果未必适合中国,如果是原汁原味地译介进来供人借鉴固然无可厚非,如果不研究中国的实际就试图凌驾或指令中国的实际,的确会误人不浅。
课程研究中的一个明显趋向即是对今天中国的课程和昨天中国的课程一概无兴趣。于是,任何发达国家的课程研究都是中国的楷模,理论研究者们仿佛在给中国的课程实践者举办外国课程理论展览。但理论却是经过了一番书斋研究的,严格说来是跨时空剪裁的,所以更像是美不胜收的“插花艺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根、把枝叶也一起呈现出来。既是食洋不化的理论,当然没有人会理会中国的水土,但插花虽美可是无本之木,理论研究者的热情可佳却是无源之水,即使是良种恐怕也不易流传吧?不幸的是,有人却硬是要灌输要指令移栽,更不幸的是邯郸人要学步,是采用把黑发染成金发的办法来学课程理论,断然没想过过些时日黑发还会长出来。
说课程研究一点也不关照实践,这也不客观,我们许多人还是各国蜻蜓点水地考察过一番的,因此我们的课程研究中不仅有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理论比较研究,还有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的比较研究,甚至有外国看到的、拍摄下来的实践的比较研究。但是,这些比较研究中有几个明显的误区值得关注:其一,有些研究忽视了“教育问题是如此复杂,以至它容不得半点简单化和僵化。预测措施和革新的效果比进行其他活动更为艰难。经常会出现意想不到或与预期相反的结果”④,所以竟然对于尽人皆知的影响课程发展的诸因素熟视无睹,像社会发展基础、学科发展水平、人的发展需求、文化传统差异等,如果进行比较研究,其复杂与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所以,许多比较研究只能说是比较对照并且予以描述性概括,其实是没有什么“研究”的。其二,比较研究中接触到的一些深层次文化界域里的问题,有明显的历史唯心论印痕。仿佛中国的问题至今也还是该由孔子承担责任,外国的发达仿佛没有历史过程。否定中国的课程换上美国或其他国的课程,仿佛就像铲了中国的树种上美国或其他国的草一样简单。对此,我们有必要重温198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课程改革的会议上突出强调的一种看法:“必须承认,有步骤、有组织地制定教学规划并不意味着搞出一套理想化和脱离现实的标准……我们寻求的解决办法只能在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的实力、财力和物力,尤其是时间条件所限定的范围内得到。力量越有限便越应该从中获最大效益。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面临着尖锐的问题……”④。其三,亦步亦趋地模仿外国实践并照猫画虎地研究改造中国实践的情况也是误区之一。盖大楼、购设备、学技术甚至科学管理(不是更高层次的文化管理)都有可行性,可行是因为简单,即令财力不支也依然可能通过巧立名目滥收费来应对,甚至就“弃软件、上硬件”搞定形式主义。但是课程与教学的模式与方法也这样照抄照搬,定然行不通,这不仅因为“形质的文明易,精神的文明难”,而且把中国的教师和学生都折腾成外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以及全套的教学模样,岂不真要重演邯郸学步的故事?况且,那些赴外国考察过的研究者还不止仅去过“邯郸”。其四,外国的理论从来也不等于外国的实践,他们也有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譬如美国始于杜威的许多课程与教学的理论,通过研究者的比之理论本身更为繁荣的研究,已经和正在以一种早已由美国人的实践检验过的普遍真理的模样被中国人学习,但是至今“在美国大多数学校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情况却很少见到。相反,美国初、中等教育都极力向学生灌输并让他们掌握大量的实际教材,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脱离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兴趣的”②。
课程研究趋向改造因此必须下到基层文化田野里寻根,即寻求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或特色,在这样的根本上嫁接或借鉴异质文化精华,或者就在多元的异质文化精华的启示之下,从自己的根本上生长出中国特色的新文化来。课程研究是因为它与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都息息相关才必须这样改造的,而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价值观的不确定性、它所导致的各社会内部规范和价值系统的多样化、以及许多惯例的规范和价值观的相对性等等,也迫使它必须这样改造。由于“新的行为模式在中青年中正在扩展:暴力、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和权力、色情变态、不承担任何义务的性爱等等。这些行为模式有的已经从发达国家传播到经济上不太先进的社会,并且动摇了这些社会的所有社会结构”,对于中国的课程研究乃至课程改革教学改革而言,撇开自己无与伦比的优秀文化根本,特别是伦理的和道德的许多人类精华理念,盲目地崇洋媚外是不智的,而选择“努力在复兴其最深远文化价值观的基础上”④的前提才是妥当的。
四
课程研究不能走进田野还体现于一种形式主义的趋向,这种趋向不切实际地拔高起点、忽视普适性还获得了某些基层研究者的盲目认同,研究成果也以一种形式主义的形式在附庸理论风雅,这样的研究陷入自欺欺人的状况会十分必然,甚至弄成“皇帝的新衣”,人人都清楚又都不愿意像那讲真话的孩子似的“愚昧”,所以就理论与实践继续隔离。
拔高起点的研究经常是要与国际接轨的,自近代以来,我们盲目接轨而不果的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当年我们新学堂试办没多久,乡间私塾还兴旺着的时候,就曾经跟着杜威搞活动课程改革过;解放后大一统地效仿前苏联;60年代丢下前苏联又接着老解放区的办法改;近年来改革开放信息流畅,所以外国有什么我们就饥不择食地学什么。譬如,这几年比较时髦的是后现代课程,建构主义的课程等等,笔者并非狭隘到认为后现代课程一定要现代化以后才能“课程”,也不以为理论界尚无定论的建构主义课程我们就不能研究,但研究并且还煞有介事地在实验学校里操作起来,成功起来,这就令人不安了。其实有些基层学校搞人本化课程的成功就这样令人不安,全世界几无成功案例,怎能在丝毫不影响应试竞争的中国学校里成功呢?至少,这类实验研究,在我国目前教育田野里的成活率不应该太高。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几经坎坷之后,得以在赞科夫的实验教学论体系中得到很好的应用,这样的一种发展理念其实很适合我们的课程研究,它无疑重视发展,甚至用“高难度”这样令人误解的词语来阐释发展教学的原则,但由于发展区是“最近的”,也即是可及的,这就比同时代的许多想当然的课程与教学理论更实际,赞科夫的实验能延续15年并拓展到1281个教学班,正反映了它实际、富有成效而且十分艰难。相比之下,拔高的研究远离教育田野,或者像是田野边缘的诗意的过客,如果这样的研究多了,也就强化了文化隔离。
课程研究的形式主义趋向忽视了普适性,也辜负了教育实践者的真诚渴望。由于学校在竞争中成长,连同教师和学生也缘于一种并不公平的竞争,加剧了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平衡,而课程研究,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层层筛选之后的享有优势教育资源的学校和教师及学生的话(当然这种适应未必不虚假,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优势资源学校适应研究者,它们在硬件设施与国际接轨之后,会试图像购置硬件那样提升“软件”,于是在学校各类文本及科研项目名堂上竭力追逐“前沿”。而学校的同一扇橱窗里出现的某些“前沿”理念,与陈腐的譬如应试竞争的信息所呈现的理念,滑稽地并列不悖,是为“未必不虚假”的证明),那么对于被排斥在外的欠发达地区的薄弱学校而言,就只能是些自说自话的书斋梦呓了。笔者很为那些奔波于真田野里的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研究所感动,他们的研究让中国农民的生活发生着质的改变,而课程研究走进教育田野,研究一些教师们面对的、疑难的、渴望改变的问题,或者就与实践者们一起进行自发的教学问题研究,让农村学校里的课程与教学也发生些质的改变究竟是不能?还是不为?陶行知先生当年不就是这样践行过的吗?
课程研究的形式主义趋向实际上得以张扬,是在研究与实践之间,邓小平同志告诫的“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⑤,往往正是在这个环节上发生的。严格论起来,说这里发生了课程研究的问题,不如说是发生了“不研究”的问题,而任何课程理论以及决策或策略本应该在这里得到最充分“研究”的。趋向失误体现为两种情况:其一,“许多人是做实际工作的,他们也不注意客观情况的研究,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①,前述未必不虚假的证明就属这种情况,基层许多课程研究,如时下热点的校本课程开发,综合活动课组织,研究性学习课的盲目模仿等等。即令热情可佳,但不花一番心血研究实际基础,甚至凑几个教师“培训”十天半月就开发起课程来,这与大跃进时代每村派几个代表“培训”几天,回村就垒起土炉炼起钢来有什么两样?其二,“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反对本本主义》中的这段话,对于“不研究”的课程状况可谓批判得十分贴切,只不过实践中的“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也有个未必不虚假的问题而已。正因为虚假,才把形式主义弄成了“皇帝的新衣”一样,只不过有些“不研究”课程的基层管理者经常是不穿这“新衣”的,他们会以观望态度直接怠工,还会依着旧思维驾驭新课程。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课程研究及其成果还有个形式的形式主义问题。这是学科壁垒还是学术壁垒或者兼而有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书斋与田野之间划了太深的鸿沟,而且是课程这样一个与全社会都息息相关的问题领域。这还不是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病历像天书”病人看不懂的问题,而是医学研究及其成果主治医师看不懂的问题。对此,或许提高教师的专业化素养是具有根本性的策略,然而这策略恰恰需要研究者走进田野,或者,至少先迈出书斋看看田野。“为了在研究者、决策者和教育者之间建立持续而有效的联系,不仅需要认清各种障碍,而且需要消除那些随时都能制造困难的因素”,我们的课程研究及其成果的形式真有必要成为障碍、制造阅读困难吗?或者,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章还需要译成白话文?但许多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确“没有考虑读者公众中的差异,这一事实已带来许多困难”。坦率地说,我们不该回避那些“更令人头痛的事实”:“有些研究者使用精心考虑过的词汇只是为了掩饰作品的空洞或论证的薄弱”④。
空洞或薄弱正是课程研究理论化趋向的必然结果,对于研究者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还未曾真正在第一线实践过课程与教学的研究者来说,太需要走进田野、躬耕于田野去寻求充实和厚重了。课程和教学及其变革与发展都在教育生活里,不只是那些占尽资源优势的教育生活,还有那些黄土坡上的深山沟里的教育生活,那里不仅是研究者智慧的源泉,更重要的是教育的道德、情感、良心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