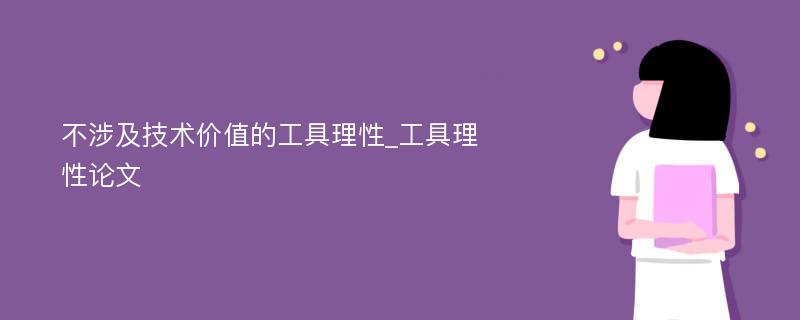
Technocracy———种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论文,价值论文,工具论文,Technocracy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语义学看Technocracy
对于Technocracy, 我国学界把它译为“科技治国论”(高铦先生等译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技术统治论”(赵国畸先生等译的《当代美国的技术统治论思潮》)、 “专家政治论”(商务印书馆于1984年出版的《英华大词典》)、“技术主义”(香港版的《牛津英汉百科大辞典》和梁实秋主编的《远东英汉大辞典》)。
上述译法自然表达了Technocracy这个英名的某些语义, 但并未揭示出它的深层内涵和基本精神。因而有以偏概全、以末充本之嫌。这种译法不仅影响学界和社会对Technocracy的理解和接受, 而且招致并误导了对Technocracy 的来自学界内外的非理性批判,因而危及Technocracy这种工具理性在我国学界内外的生存和发展。
Technocracy是由Techno-这个前缀和-cracy 这一后缀所构成。Techno-源于希腊语,原为“艺术”、“技艺”之意,现为“技术”之意;-cracy较为复杂,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语义:(1)作为一种社会力量或权力及其存在的合法性;(2 )优先权或权威性的存在;(3)一种国家体制或政府管理体制;(4)某一社会集团对社会的统治或控制等(注:参见 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G.&C.Merriam Company,1977.)。
根据-cracy的几种语义,Technocracy有如下几种意义:(1 )认为技术在社会中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2 )与推动社会发展的其他力量相比,技术是最重要的力量,因而应该获得优先发展权或对其他力量的先决权;(3 )一种以技术为原则调配工业及经济资源并管理全社会的政府管理体制;(4)在高度发达的“工艺社会”里, 由技术专家治理社会(注:参见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Volume 21,Encyclopedia Britannica,Inc.,1966.)。
Technocracy的四种语义并不是并列的, 它的基本语义是:技术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先决作用;社会应给予技术以优先发展权。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Technocracy 是一种追求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的技术化的学说。至于社会是否由专家管理或技术统治,只是Technocracy 的次要语义,并不表征Technocracy的本质特征,也不是区别Technocracy与非Technocracy的最高判据。
根据分析,可以把Technocracy译为科技兴国论, 因为科技兴国论这个中名能够恰当地表达Technocracy 中依靠技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给技术以优先发展权的基本语义,体现Technocracy 所内含的追求社会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社会化这一基本精神。
就追求社会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社会化而言, 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是一种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 它本身并不表达任何特定的阶级意志或制度偏好。它只是在诉说人类社会发展到“技术时代”的历史要求和客观理性。
我们不同意把Technocracy 译为科技治国论。 科技治国论突现了Technocracy中所蕴涵的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语义, 但却冲淡甚至消解了Technocracy 中所承载的经济社会发展应给科学技术以优先发展权的语义。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优先推进科技进步,是一对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对称范畴,而科技治国论这种译法至少在字面上破坏了这对范畴的对称与守恒,造成“语义破缺”和“语境失衡”。
同样,我们亦不同意把Technocracy译为技术统治论。 上述分析表明,Technocracy是一种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 而技术统治论至少在字面上把Technocracy 这种工具理性提升为一种表征某一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这就把Technocracy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异化语境, 原本是追求某种目的的工具,却被当成这种目的本身。
同科技治国论、技术统治论等译法一样,专家治国论、专家政治论等译法也都存在着与科技治国论、技术统治论等译法相同或相近的问题,只看到了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却没有看到经济社会发展对技术的反作用。此外,专家治国论和专家政治论还有其特有的弊端,即过分强调某种社会过程的主观因素,而忽视了经济基础的本原性力量和社会活动的体制化效应。至于技术主义、技术主义社会学等译法,虽然表达了Technocracy所负载的工具理性和中性价值, 但却难以体现技术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是难以体现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和社会给技术以优先发展权这种特定语义。
另外,在日本和东南亚的著述中,技术立国论较为常见。一般而论,谈技术立国似无不可,但是,技术立国论的用法有技术决定论之嫌。尽管技术对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然而,认为技术可以取代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技术进步可以等同社会进步,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难以服人的。
二、从语源学看Technocracy
Technocracy 首先是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位发明家和工程师W·H·史密斯在1919年创造的新词儿。他在该年2月、3月和5 月发表在《工业管理》杂志上的三篇文章用了这个词。史密斯在这些文章中指出,他创造Technocracy 这个词是为了表达理性化的工业民主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发展历程。本世纪30年代初, 霍华德·斯科特(1890 —1970,曾经是世界产业工人联盟研究部主任)在1932—1933年把它推广开来。但他对这个词的解释却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制度学派的创始人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凡勃伦认为,经济现象根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原理, 代表商人利益的价格体系(systemof price)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或低效,因此,价格体系应被工业体系所取代,即按照技术原则而不是按照商人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调控经济与社会运行。
当这个词通过斯科特在全美推广开来的时候,它的创始人史密斯却摒弃了它。史密斯认为,斯科特对该词的用法把技术和专制溶为一体就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技术人员的统治”;而他的原意是“人民通过他们的公仆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史密斯在他的《由创始人所解释的科技治国论》(旧金山, 1933 年)一书中一再重申Technocracy 这个词是作为一种工具理性而存在而不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斯科特与史密斯确实有分歧,斯科特突出了Technocracy 一词中的主观意向(注:参见史密斯和斯科特关于Technocracy 一词赋义的争论,请参见J ·乔治·弗里德里曼编的《拥护和反对科技治国论:一次专题讨论会》,纽约,1933年。)。
1932 年秋天, 正值美国大萧条之时, 许多人都把希望寄托在Technocracy这种乐观理论之上。一时间,无数个倡导Technocracy的组织在全国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在1933年这类组织像它们迅速诞生那样迅速地收缩,到了1936年,这类组织所剩无几。由斯科特本人领导的Technocracy组织吸收了一些这类中小组织,虽不景气,却生存下来。 当然,Technocracy作为一种社会建制之所以能够生存下来, 有两个原因:一是科学管理的奠基人弗里德里克·W·泰罗把Technocracy应用于实际的工业管理实践,
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
从而赢得了社会对Technocracy的理解和接受; 二是后来的美国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他的厂商理论分析中证明了“生产者主权论”等有关经营决策权从资本占有者手中转移到管理者和技术者手中的结论。
当然,这个词在斯科特时期和泰勒时期就招致了批判,有人批评它具有把人类社会异化为物的潜在可能性,有人怀疑用技术原则解决整个社会管理特别是政治问题的可能性。 这些批评和怀疑一度使Technocracy跌入低潮。
到了60—70年代,Technocracy 由于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而获得新生。贝尔(Dasniel Bell)等人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以知识为中轴的社会, 这个社会是实现了技术化和知识化了的社会, 也就是实现了Technocracy的社会。与此同时,这个词由英、美、法、 德等古典发达的工业国家传播到在二战前后崛起的新兴工业国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经历了贸易立国阶段之后,迅速走上了技术立国之路。
在80 年代, 世界性的改革浪潮使技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Technocracy这个词又从新兴的工业国家迅速传播到发展中国家。 在我国,它被赋予科技兴国这一内涵。
90年代特别是1995年以来,知识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识,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机械工业出版社1997年版,第1页。),是建立在知识的创造、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知识的使用等之上的经济。可以想象,科技兴国将主导世界主流。
从语源学的角度看,我们至少明确如下问题:
第一,Technocracy这个在20世纪初创造的新词, 在它诞生期便被赋予若干具有相关关系的语义群。
但是,
随着历史的发展,Technocracy的基本语义逐渐确定在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 而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必须给科学技术以优先发展权这两大原则之间,即社会的技术化与技术的社会化之间。而社会应由专家来管理,只是一种极限情况,它已经游离于Technocracy的基本内核, 变成一种“边缘语义”。
第二,随着历史的变迁,Technocracy 逐渐由少数技术专家的理性信念演变成为社会各个阶层以至整个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社会性思潮,即从个人意识和小群体意识变成社会意识和历史意识,最近演化为全球意识。
第三,Technocracy这个词的语义, 它在初创时只是为解决某种特定的社会问题(工业管理的合理性问题)而存在,但在自身的演变过程中,Technocracy 的语义从追求工业管理的合理性深化到追求经济管理的合理性,又从追求经济管理的合理性泛化到追求社会管理的合理性。这就使Technocracy 的语义空间经历了工业领域—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嬗变,即从一种工业观上升为经济观,再上升为社会观、历史观和世界观。
第四, 随着Technocracy 基本语义的定型和语义空间的拓广,Technocracy开始从一个国家扩散到另一个国家, 从一种社会制度传播到另一种社会制度,从一种文明氛围渗透到另一种文明氛围,从一种发展梯度跃迁到另一种发展梯度,从一种价值目标转移到另一种价值目标。
三、从学说史看科技兴国论
Technocracy这个词是在20世纪初创立的, 但是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想,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可谓源远流长。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在人类历史上率先提出了“智慧即美德”的哲学信念,首次昭示了知识对人类自身及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的学生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家的最高判据就是尊崇知识、以理性为原则,其具体体现就是最高统治者应该熟知哲学,或哲学家(真正的智者)出任最高统治者。柏拉图因其上述主张被公认为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之远祖(注:参见柏拉图:《理想国》, 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欧洲中世纪,哲学和科学都成为神学的婢女, Technocracy受到贬抑,甚至受到迫害。中世纪是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 思想发展史中的最黑暗时期。但这并不否认像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神学大师曾以“双重真理”的名分给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以一席之地; 也并不否认像库萨的尼古拉、伽利略和布鲁诺等思想家为了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的合法地位而上下求索。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造就了一大批像达·芬奇、蒙田、弗兰西斯·培根那样的“思想巨人”。他们高举“知识就是力量”的旗帜,用以批判宗教神学对人性的无视和对历史进步的窒息。达·芬奇一生都在为他的科学技术得到社会认可并付诸实施而奋斗,培根在他的晚年设想了一个以科技机构为中心、以智者为最高统治者的理想社会。
近代以来的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及稍后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启蒙主义都包含着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思想。 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或启蒙主义,都坚信人自身及其外在世界都是一架按照固定程序运转的机器。经验主义侧重于证明外部世界的机械性,理性主义侧重于证明主观世界的机械性,计算机和数理逻辑的奠基人大卫·休谟试图把人这架机器同外在世界这架大机器对接起来,他在《关于自然的对话》一书中确信自然界的创造者必定是一个工程师。既然人和外在世界都具有机械性,那么人类社会在本质上也是技术性的。洛克的《政府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都在力图证明人类社会的理性本原和技术属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叫做奥古斯丁·库尔诺的数学家,因首次把数学应用于经济学而闻名。然而,他的历史功绩却主要地不在于此,而在于他论证了一个技术文明的兴起。他看到了历史由生存向理性发展的总趋势,他预见到一个“史后”的机械化时代,因为普遍理性化必然导致社会的技术化。
理性革命带来了科学革命,科学革命带来了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带来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又带来了政治革命。然而这一伟大的历史循环却率先发生在英国,与它条件相近的法国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头。这是一个正直的学者所不能容忍的,于是,一个叫圣西门的乌托邦创立者大声疾呼:学者和实业家“真正是法国社会之花,因为他们是最能生产的法国人,是制造最重要产品的法国人,是管理最有益于民族的工作并使民族在科学、美术和手工业方面取得丰硕成果的法国人。”(注:《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36页。)因其上述主张,圣西门被尊为科技兴国论之父。
圣西门之后,他的思想分化为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学生孔德把他的思想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实证主义哲学,成为现代科学主义的本源。孔德的科学社会学是现代科技兴国论的理论来源之一。另一方面是卡尔·马克思在社会主义思想上的探索。像圣西门一样,马克思“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但与圣西门不同的是,马克思看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异化问题,即技术把人异化为物的社会后果。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的技术化与资本的反社会化已经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让科学忠告资本退位”。
在马克思之后,社会主义的实践者继续高举技术进步的旗帜。列宁率先提出“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斯大林甚至提出“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中国人民经过极其痛苦的探索,终于由邓小平做出世纪性的结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此,中国人民在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走上了科教兴国的正确道路。
与此同时,西方思想家继续追求技术社会的意义。凡勃伦在他的《工程师与价格体系》一书中论证了商人控制的价格体系与技术人员控制的工业体系之间的矛盾以及工业体系取代价格体系的合理性。“若美国会出现像苏维埃那样的革命机会,那它必定是技术人员的苏维埃。”(注:Thorstein Veblen,The Engineers and the Price System,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1983,P.128.)加尔布雷思在他的《新工业国》《丰裕社会》和《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等一系列著述中论述了资本的两权分离以后生产者包括生产的管理者控制权力的经济原因。丹尼尔·贝尔和阿尔温·托夫勒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三次浪潮》和《未来的冲击》以及《权力的转移》等著述中论证了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以知识为中轴的社会,在后工业社会中,产业结构知识化了,阶级结构知识化了,整个社会结构也知识化了。
从科教兴国论或Technocracy的学说史,我们不难发现:
第一,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普适于任何时代。 古代有古代的Technocracy,近代有近代的Technocracy, 现代有现代的Technocracy。而且,时代越发展,Technocracy的功能就越大。
第二,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普适于任何社会制度, 奴隶社会有Technocracy(如柏拉图),封建社会有Technocracy(如托马斯·阿奎那和库萨的尼古拉),资本主义社会有Technocracy(如培根、 库尔诺、休谟等),社会主义社会也有自己的Technocracy(如圣西门、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第三,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可普适于任何阶级或社会集团,贵族阶级可以利用Technocracy,封建主阶级可以利用Technocracy,新兴资产阶级可以利用Technocracy,工人阶级可以利用Technocracy,知识阶层(管理阶层和技术阶层)可以利用Technocracy。
第四,科技兴国论或Technocracy普适于任何社会发展样态。 发达工业社会可以拥有Technocracy,新兴工业社会可以拥有Technocracy,发展中的工业社会可以拥有Technocracy, 前工业社会或非工业社会也都可以拥有自己的Technocracy。
科技兴国论是一种价值无涉的工具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