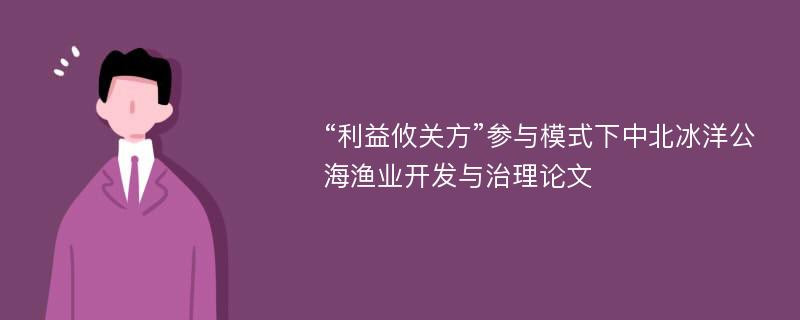
“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下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
王玫黎,武俊松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重庆 401120)
摘要 :中北冰洋开发前景的日益显现使得北极地区成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尤其是中北冰洋核心区域即北极公海地区海冰的消融使得北冰洋鱼类资源向北转移,核心海域鱼类资源的开发与治理成为各国争夺的目标,加快构建完整的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的国际法律体系和组建新型管理模式的呼声愈发强烈。对当前中北冰洋公海渔业治理所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并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治理模式进行梳理,提出相应的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新模式,有利于加快推动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步伐,提高中国应对北极问题的能力,共建北极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 :利益攸关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治理
2017年11月30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六轮北冰洋公海渔业谈判大会上,中国、冰岛、日本、韩国、欧盟同原北极五国即美国、俄罗斯、加拿大、丹麦、挪威一致通过了《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协定》(以下简称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协定》),《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协定》的签订标志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开发与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也是世界跨区域国家一同应对北极问题的合作典范。国际社会之所以高度关注北极事务以及北极未来的发展走向,主要是北冰洋海域冰层的解冻将会释放很大的潜在既得利益,当前北极航道的开通与试行正演化为一种可能,其背后不仅仅涉及航道运输的经济利益,更多的还是军事战略利益。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升高,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前景尤为可观,即使当前中北冰洋公海地区仍被大面积的冰层所覆盖,渔业商业开发尚不可能,但北极五国早已察觉只有抢先制定北极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规约,才能将开发权与管理权紧紧握在本国手中,排除域外国家的介入,独享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可得利益。考虑到北冰洋的整体性与不可分割性,单方面将北极域外国家排除在外,难以达到维护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开发与有效管理的效果,还会加剧传统远洋捕捞大国与北极国家之间的矛盾,制造不必要的纷争。因中北冰洋公海区域作为人类共同的财富,该区域渔业资源的开发与管理需要世界各国的参与。
一、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开发的必要性
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开发主要考虑到北极地区对全球的气候环境、海洋安全、生物多样性具有关键的影响作用,北冰洋附近拥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渔场之一即巴伦支海和挪威海,随着中北冰洋核心海域逐渐演变为季节性无冰海区,北极周边国家单方主义捕捞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势必会产生恶性竞争的趋势,加剧中北冰洋公海地区渔业资源的枯竭,这不仅是对中北冰洋地区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也会对全球生物多样性和生物链产生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能源消费结构不断优化,与2015年相比,2030年煤、油比重分别下降15.2%和5.6%,天然气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分别上升8.0%和12.8%[4-5]。
1.2 观察指标 在观察期间的每年12月,抽取患者透析前空腹静脉血,检测血红蛋白(HGB)、血浆白蛋白(Alb)及甲状旁腺素(PTH);按照Daugirdas尿素单室模型公式计算尿素清除指数(KT/V)。比较导管组与内瘘组透析患者的HGB、Alb、KT/V及PTH差异;比较观察期间两组患者HGB、Alb、KT/V及PTH的变化情况。
(一 )“暖温期 ”时代下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开发的潜在威胁
北冰洋是一个近似地中海的半封闭海域,与南极大陆相比不存在大面积的陆地,相反由大面积的冰层海域和十分分散的诸多岛屿构成,北冰洋是四大洋中最小和最浅的大洋,同时北冰洋拥有八个附属海。中北冰洋海域拥有着丰富的渔业资源,巴伦支海、挪威海和格陵兰海是世界著名的渔场,近年的捕鱼量约占世界的8%~10%。[1]尽管中北冰洋的渔业资源都在边缘附属海域生存,但由于地球当前正处于“暖温期”时代,加上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口基数的增加,科技水平的提高使得温室气体不断地被排放并积聚在大气层中,致使地球大气层内部的热量无法向外扩散,造成北冰洋冰川、冰层融化,而中北冰洋的渔业资源却存在大量的高度洄游性鱼类种群,气候环境的变化必然使得鱼类种群向纬度更高的海域游动,这就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商业开发提供了可能性。
1995年10月31日,世界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粮农组织)一致通过了《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以下简称《守则》)。该《守则》确定适用于所有渔业的养护、管理和开发的非强制性的原则和标准,[15]致力于解决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和跨界鱼类种群在公海被非管制捕捞的问题,旨在能够促进海洋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该《守则》第7条渔业管理中第7.1.4款就规定了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应当包括对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渔业或资源拥有实际利益的国家的代表。[16]这里的“实际利益国家”其实就是指一些传统的远洋捕捞大国以及与中北冰洋事务存在相关联系的国家,该规则为了进一步维护相关实际利益国家的权利,还提出了这些国家应当成为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的成员或参加者通过相关的合作共享渔业开发的利益,共担养护与管理渔业资源的义务。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模式是当今区域渔业委员会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吸引不同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更有助于从整体上维护海洋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当前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商业开发尚无法实行,但未来不久就会成为一种现实。当前国际社会应当未雨绸缪,及早论证、分析、制定可行的具有国际法约束力的统一性国际法律文件,组建利益攸关方参与的中北冰洋公海区域渔业开发与管理组织。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针对公海生物资源的养护和管理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公约第118条规定各国在公海要进行养护和管理生物资源方面的合作。虽然公约未对北极做出专门的安排,但考虑到北极是由整个北冰洋和诸多岛礁构成,所以应当适用公约有关公海方面的规定。从社会学的集体行动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看,中北冰洋公海的渔业开发与管理仅靠某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或北极国家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作为一项集体行动,并非是单方面的作为,在集体行动的过程中,由国际社会共同创造出公共物品,由此产生的成本由集体行动的成员互摊、利益共享,但难免会出现“搭便车”的窘境,[7]这就需要制定统一的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公约来约束各国的行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适合作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指导性原则,北极和北冰洋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需要人类以及整个国际社会的守护,而不是某几个国家的私物。
(二 )“全球化 ”时代下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开发的相互依赖
当前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工作仍然由北极五国制定的一系列临时安排措施加以调整,但其弊端也日益显现。尽管北极五国近年来不断地扩大其他国家参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事务的范围,但其目的基本都是为了获得国际社会对其制定的临时措施与安排的承认。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挑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组织的缺失。北极五国之间的利益错综复杂,难以就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组织的组建达成一致的意见。2018年是伊卢利萨特宣言签署十周年,原本定于在此次会议中签署有关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协议,由于俄罗斯与签署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导致该项议程未被列入会议。从北极五国外部来看,北极五国之所以避而不谈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组织主要是想将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事务纳入五国的内部事务范畴,这样其他国家或者国际社会如果想要参与该事务,就只能按照北极五国的程序进行申请。根据世界公海区域大部分都组建了相应的区域性渔业组织的惯例,因而构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组织是当前最为重要的事情。第二,北冰洋沿岸国家主张利益的严重分歧性,除上述北极五国内部的政治利益存在很多矛盾外,北冰洋沿岸国家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关注点也不同,尤其明显地体现在各个国家的国内渔业政策上面,对于美国、俄罗斯而言,两国更加注重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事务的掌控权,通过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事务的管理谋求对整个北极事务的主动权;而加拿大则主张渔业经济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观念;以冰岛、挪威为主的国家则倾向加大对中北冰洋公海的渔业开发,渔业产业在北欧国家为支柱性产业同时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种群在未来大部分将会是从大西洋边缘海域渔场浮游过去的,因而北欧国家更为看重公海渔业的开发潜力。[8]基于各国之间渔业政策的相互冲突,就难以达成统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北冰洋渔业开发与管理的国际公约。第三,中北冰洋公海地区海底状况以及潜在鱼类种群和数量的数据并不完整。当然这并不属于国际法上的问题,但一般国际条约中都会将其作为专门的一章加以规定,要求各国之间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共享数据。该事实问题是开展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和管理的前提,对该区域渔业资源过多过低的估计都会影响到是否应当对该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开发与管理,所以北极五国要打开中北冰洋事务的大门,协同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国家共同开展相关的科学调查活动,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提供准确的数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称作是一部“综合性海洋宪章”,[2]但其并未单独针对北极或北冰洋公海地区渔业开发和治理做出相关规定,与南极完善的国际法律体系相比还存在诸多的问题。目前针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开发与治理存在两种分歧:一种是虽然《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未专门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做出适当的安排,但中北冰洋作为世界四大洋之一,理应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公海生物资源的相关法律规定。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北极五国主张通过制定并采取适当的临时措施来防止未来中北冰洋可能会出现的不管制渔业捕捞现象,同时承认东北大西洋渔业委员会对大西洋一侧中北冰洋公海地区有关渔业资源的管理与养护,这些适当的临时措施适用于中北冰洋公海地区。[3]美国的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中北冰洋公海适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将北极域外国家参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事务排除在外。北极五国虽然对外一致强调五国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享有专属的开发权与管理权,但北极五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除了涉及北冰洋岛屿归属、海域划界问题之外,北极五国针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开发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五国之间有关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政策也存在很大的差异,相互之间并不认同。这种情势极易引发北极五国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进行单方主义的捕获活动,碎片化的渔业政策有可能将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推向枯竭殆尽的窘境。
江上,舟来船往,汽笛声声;入夜,航标灯忽明忽暗,星辰一样闪烁。没有多少瞌睡,总爱于江边逗留。我们家在二号码头附近,铁质栈桥倾斜地伸向江中,铁腥气在夜里散发得更加浓郁,鲁莽地钻入鼻腔,掺杂着江水的气息,醇厚而浓俨。江水哗哗,一波一波涌向水泥石阶,复而退后,循环往复,像极了平庸又琐碎的日子。月光洒在江上,江水澄亮,似碎钻、纯银,一齐倾倒于江中。那样的月夜,坐在江边,置身失真的美里,却写不出一首诗来——好急啊。生命里横亘无数失语时刻,急也急不来的,唯有回忆。
二、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治理的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调整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法律依据,该公约的第116条规定了所有国家均享有在公海捕鱼的权利,依据公约的规定,中北冰洋公海区域的渔业资源自然允许世界各国国民在履行一定义务的前提下前往中北冰洋公海范围从事捕鱼活动。公约第118条也要求各国在公海要进行生物资源方面养护和管理的合作,在适当的情形下建立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组织。该公约的两个条款即赋予了远洋捕捞国家以及与北极存在相关利益的国家参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和管理事务的权利。诚然,引入利益攸关方参与的模式是建立在中北冰洋公海应当存在一个区域性渔业开发和管理组织的前提下,但北极五国认为中北冰洋公海当前仍未全部融化,渔业商业开发尚不具备条件,但又要防止未来有可能存在的不管制捕捞活动,于是倾向于通过一系列的临时安排以代替组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组织。笔者认为北极五国的行为其实就是想把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事务的权利握在五国手中,避免国际社会的干预,但这种临时的安排真的有利于中北冰洋渔业资源的开发与养护吗?且不说北极五国的这种行为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19条第1款的违反,北极五国也未意识到引入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重要性,参考其他国际区域性渔业组织,都有大量的国际组织和利益攸关方的参与,所以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和管理需要引入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平衡世界各国在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中的利益问题。
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国一般性辩论演讲中首次提出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面对全球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世界各国需要以负责任的精神同舟共济、协调行动。[4]之所以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开发与管理在“全球化”时代下具有相互依赖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从自然层面来看,北极及北冰洋对地球的气候环境以及沿海国领土安全、海洋生物具有牵连性的影响。毋庸置疑的是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以核心海域冰层的融化为前提,据华盛顿大学消息,以往的潜艇和现代卫星显示,1975年至2012年间,北冰洋中央区的海冰平均厚度减少了65%,9月份冰层最薄,冰层厚度减少了85%。2018年3月27日,美国气象学会的《气候杂志》发表题为《北极海冰损失的季节性和区域性表现》的文章,指出了北冰洋目前正处于快速的季节性无冰状态,北极海冰连续4年达最低值。[5]虽然中北冰洋公海区域将会出现大面积的无冰状态,有助于开展商业渔业捕捞工作,但中北冰洋海冰的快速消失将对部分沿海国的领土产生淹没的负面效应,北冰洋大量的岛礁或许将从地图中消失,重要的是作为调节地球气候的作用力将会明显减弱或消失,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是建立在以上负面效应的背景中的。因而,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涉及诸多因素。根据德国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海洋与基地研究所(AWI)的海洋生物学家的调查发现,北极海冰下存在大量的极地鳕鱼,该鱼类种群是北极海豹、鲸鱼的主要食物来源,[6]因此,这种鳕鱼是北极动物生态链中的重要环节,一旦商业过度开发将会对整个北极的生物系统造成不可估量的毁坏。
三、预防中北冰洋不管制公海渔业的治理模式
(一)北极五国协同治理模式
北极五国协同治理模式是由美国、加拿大、俄罗斯、丹麦和挪威通过一系列的临时安排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进行开发和管理,将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排除在外,或仅仅在某些重要的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事务中以邀请的方式使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会谈,当然他们仅仅有临时参与权和建议权,并不享有任何实质性权利,至于哪些国家可以真正地参与相关的会谈这不取决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该决定权往往在于北极五国。2008年的伊卢利萨特宣言的签订标志着北极五国在北冰洋管理领导地位的正式确立。从2010年开始,北极五国历届年会主题都是关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问题,2014年北极五国针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达成一系列的临时安排,除了组建中北冰洋公海区域性渔业开发与管理的组织,还通过一系列的中北冰洋公海渔业会议试图向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推广北极五国制定的临时安排,已达到排斥他国和国际组织涉入的目的。[9]在伊卢利萨特宣言实施十周年之际,2018年5月,北极五国携手原住民及其他国家举行会议,讨论的内容包括北极理事会之前未涉及的议题——加强安全政策合作的框架等,原本定于在此次会议进行北极渔业协议的签署,但由于北极五国内部的政治局势致使该协议未被纳入议程。[10]北极五国协同治理的模式虽然在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事务方面取得很多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北极五国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得该模式也难以有更为光明的前途,也可以理解为北极五国协同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将沦为美国与俄罗斯之间争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权与管理权的工具。
(二)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
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是指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组织不应仅仅包括北极五国或北冰洋沿岸国家,该组织框架结构应当是开放、包容的体系制度,传统的远洋捕捞大国以及热衷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均可通过一定的申请程序加入该组织中。或者给予这些国家或国际组织参加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事务的提案权,发表自己的见解和看法,使该组织的运行过程更加科学、公正、透明。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将会拓宽用于开发和管理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资金途径,鉴于当前中北冰洋公海区域仍被巨大的冰盖所覆盖,中北冰洋海域的鱼类种群以及具体的鱼类数量仍是无法确定的,北极五国以及传统远洋捕捞大国所掌握的数据也存在相互冲突和不完整性,构建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区域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组织将会重新整合各国之间的渔业数据,进行统一的科研调查。以2009年11月14日在新西兰签订的《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公约》为依据成立的南太平洋区域渔业管理组织(以下简称SPRFMO)为例,SPRFMO共包括十二个缔约国,其中就包括欧盟、丹麦(代表法罗群岛)以及俄罗斯,以上三个国家和组织均非南太平洋沿岸国家,但依旧将其纳入SPRFMO的公约之内,欧盟方面认为欧盟的加入,使得该协议填补了全球公海渔业管理方面最后一个空白点,SPRFMO的生效将确保澳大利亚西部至南美洲海域的渔业捕捞活动被纳入国际公认的法则之中。[11]欧盟、丹麦以及俄罗斯的加入将会促进南太平洋区域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多边水产品国际贸易和非法捕捞问题的解决。地中海渔业开发与治理也有利益攸关方的参与,地中海渔业一般委员会(以下简称GFCM)除了地中海沿岸国为其成员外,还将传统远洋捕捞大国日本、韩国纳进该组织之中,同时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等国际组织也参与其中,[12]为其提供科学研究数据和资金支持。
四、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法律依据
(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北冰洋公海渔业治理至今还未签订一份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国际公约,也未形成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究其原因是其背后涉及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利益。从北极五国的角度来分析,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成员国,其并不受该公约的约束,而俄罗斯自二战结束以来就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虽然1991年《阿拉木图宣言》标志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就此丧失了与美国相比肩的优势,但俄罗斯并未失去与美国继续争夺世界霸主地位的决心。现如今北极航道正成为现实,该航道的开通运行带来的不仅仅是巨大的经济利益,其军事战略利益也不言而喻,因而美俄为了提前掌控北极的局势使得两国的关系就更加不稳定。除此之外北极五国经济发展的差距还很大,国内的支柱产业也不同,挪威和丹麦两个国家对捕鱼产业十分依赖,主张加快对中北冰洋渔业的开发,而美国、加拿大则更为注重中北冰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因而五国的渔业政策的侧重点就存在不同,因而解决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所面临的挑战任重而道远。
重新爬上床,却横竖睡不着了,身子翻来覆去,心情也变得烦躁起来。越不想去听客厅的动静,耳朵却偏偏侧起来听。于是又听见小母鸡说,咯咯咯,他们可真逗。老母鸡忙不迭地回应,咯咯答,谁说不是呢?
(二)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
1995年8月4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关于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会议上通过了《联合国鱼类种群协定》(以下简称UNFSA),北极五国即美国、俄罗斯、加拿大、挪威、丹麦均是UNFSA的成员国,同时北极理事会成员、永久观察员和正式观察员也基本为UNFSA的成员国。[注] 北极理事会成员:美国、俄罗斯、加拿大、芬兰、丹麦、冰岛、挪威(均为UNFSA成员国);北极理事会永久观察员: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荷兰、波兰(均为UNFSA成员国);北极理事会正式观察员:韩国、日本、中国、意大利、印度、新加坡(新加坡非UNFSA成员国)。 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来看,美国并不是该公约的成员国,而美国当前在北极事务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单独依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难以对美国加以约束,但UNFSA几乎是囊括了整个北极沿岸国以及积极参与北极事务的国家,至少北极五国是UNFSA的成员方。UNFSA第三部分专章规定了关于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国际合作机制,第8条第3款中就提到对有关渔业真正感兴趣的国家可成为这种组织的成员或这种安排的参与方,这种组织或安排的参加条件不应使这些国家无法成为成员或参加。[13]该条款实际就赋予了传统远洋国家和利益攸关方参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和管理的权利。UNFSA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鱼类种群内容的具体规定,因而这两个公约有些条款是具有一致性的,比如在公海捕鱼的国家应当直接或通过适当的分区域或区域渔业管理组织或安排,就特殊鱼类种群进行合作。[14]所以笔者认为UNFSA的相关条款为构建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区域渔业开发与管理组织提供了法律依据,北极五国应当依照UNFSA的规定加快推进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进程。
(三)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
传统观念认为,患者出院后即终止了服务,实际上,患者出院后仍需要很高的照护需求。近年来,此种护理模式在临床上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延续性护理通常指医院到家庭的延续,包括经由医院制定的出院计划、转诊、患者回归家庭或社区后的特续性随访与指导。
五、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潜在优势
“利益攸关方”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的外交谈判专家罗伯特·佐利克针对中美关系提出,旨在美国应当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中国。按照马克思的哲学原理,世界的一切事务都是普遍联系的,这也为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哲学基础。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应当分为两种类型: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和不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17]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一般涉及对北极事务享有实际管辖权和治理权的内部成员国(北极五国或八国的内部成员国),而不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则包含中国、日本、韩国、欧洲诸国等对北极事务不享有实际的决策权、管理权的国家,但北极事务的整体进展对其他国家会产生较大影响力。本文主要围绕第二种模式即不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模式,笔者认为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潜在优势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
第一,在顶层设计上构建利益攸关方监督组织制度。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针对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开发与治理等北极事务,从之前由北极五国到北极八国再到现如今中国、日本、韩国、欧盟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参与,很容易给外界造成一种北极沿岸国家对北极事务治理权和管理权松动的假象。深入地剖析整个事件的进程,不难发现这也许是北极沿岸国家缓解国际社会对北极事务过度关注的一种计策。因为目前为止中国、韩国、日本、欧盟对北极事务享有的仅仅是表达权、建议权,不享有真正的决策权、表决权,但中、日、韩、欧等利益攸关方可以借此把形式上的表达权、建议权逐步转变为相应的监督权,相比直接获取决策权和管理权要更为简便,更加为北极沿岸国所认可。利益攸关方监督组织制度的创设将敦促北极沿岸国家积极履行国际义务与责任,推动北极事务获得更好的解决。
第二,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能够打破集体行动上的逻辑困境。根据新政治经济学中的相关理论可以将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解释为国际性的公共产品,因为从国际法的角度公海的资源属于全人类共同的遗产,而并非属于某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国际公共产品包括所有利益跨越边界、时代和人口组成的产品。[18]国际公共产品涉及公海航行自由、环境保护、资源开发等等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19]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由国际社会的成员共同支持,同样由国际社会成员共同享用,但在供给的过程中难免会因国家利益的考量而出现集体行动的困境,出现“搭便车”的怪象。美国学者奥尔森提出个人理性不是实现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其原因是理性的个人在实现集体目标时往往具有搭便车的倾向。[20]具体来说,在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过程中,国家的主权和管辖权与海洋资源制度的矛盾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矛盾造成了集体行动的困境。[21]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的引入相对于传统北极五国或八国而言将会是对其北极事务的治理权和管理权的一种“潜在外在威胁”,域外国家的介入将促使传统北极沿岸国处理北极事务更加积极、慎重、科学,同时利益攸关方也将会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的支持。除此之外,利益攸关方参与模式更具有制衡的作用,平衡传统北极沿岸国家之间的失衡状态,由不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促进参与北极事务集体选择的利益攸关方更好地与传统大国斡旋。
六、“利益攸关方”中国参与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治理的事务
2018年1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的北极政策》,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对北极事务的高度关注,该白皮书指出中国是北极事务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中国是“近北极国家”之一,北极的自然状况及其变化对中国的气候系统和生态环境有着重要的影响,关系到中国众多领域的经济利益。[22]中国作为世界负责任的大国之一,有义务也有责任对人类共同的财富——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开发与治理加以重视。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应向国际社会宣扬“共商、共建、共享以及共筑北极命运共同体”的先进理念,让更多关心中北冰洋公海渔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能够加入其中。其次,中国还可以同其他利益攸关方以及国际组织共同推进组建区域或分区域渔业组织或安排的进程,加强对相关区域渔业组织的研究论证分析,力争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提供一个理想的组织运行框架。再次,中北冰洋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与管理固然重要,但自然具有整体性,各国都应当重视中北冰洋的环境保护,海洋是鱼群的生存环境,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开发要严格遵守相关国际环境公约的规定,当前可以先行组建中北冰洋公海渔业开发与管理基金委员会,主要用于针对中北冰洋公海的科研调查、鱼类种群的养护、海洋环境的保护等。作为中北冰洋利益攸关方的中国要加大对国内有关北极事务方面人才的培养以及北极科考的投入,这样才能打破北极五国对中北冰洋的控制。
[参考文献 ]
[1]刘慧荣,董跃.海洋法视角下的北极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
[2]韩成梁,潘抱成.国际法教程[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3]唐建业.北冰洋公海生物资源养护:沿岸五国主张的法律分析[J].太平洋学报,2016,(1).
[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5]全球变化研究信息中心(Information Center for Global Change Studies)[EB/OL].http://www.globalchange.ac.cn.
[6]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国际处,中国极地研究中心极地信息中心.国外极地考察信息汇编[J].2015,(28).
[7]赵鼎新.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J].社会学研究,2006,(1).
[8]邹磊磊,张侠,邓贝西.北极公海渔业管理制度初探[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
[9]邹磊磊,黄硕琳.试论北冰洋公海渔业管理中北极5国的“领导者”地位[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10]极地与海洋门户.《伊卢利萨特宣言》发表十周年之际,北极国家代表将齐聚格陵兰[EB/OL].http://www.polaroceanportal.com/article/2083.
[11]李励年.欧盟签署南太平洋公海渔业管理协议——称协议填补了全球公海渔业管理上最后一个空白点[J].现代渔业信息,2010,(10).
[12]李聆群.南海渔业合作:来自地中海渔业合作治理的启示[J].东南亚研究,2017,(4).
[13]《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第8条第3款[A].崔利锋,黄硕林.国际渔业条约和文件选编[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4]《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第8条第1款[A].崔利锋,黄硕林.国际渔业条约和文件选编[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5]《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序言[A].崔利锋,黄硕林.国际渔业条约和文件选编[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6]《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第七条[A].崔利锋,黄硕林.国际渔业条约和文件选编[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5.
[17]张宇. 共同治理模式下利益攸关方监管体制构建[J].财会通讯,2009,(5).
[18]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7).关于全球(国际)公共产品的阐述参见张宇燕,李增刚《国际关系的新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9]庞珣.国际公共产品中集体行动困境的克服[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7).
[20]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M].陈郁,郭宇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1]王琪,等.公共治理视域下海洋环境管理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全文)[EB/OL]. http://www.scio.gov.cn/zfbps/32832/Document/1618203/1618203.htm.
High Seas Fishery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in the Middle Arctic Ocean under the “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 Model
WANG Mei-li, WU Jun-s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the Arctic Ocean becoming more and more obvious, the Arctic reg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Especially, the melting of sea ice in the Arctic high seas, the core area of the Arctic Ocean, has caused the Arctic fish resources to move northward,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fish resources in the core sea area become the goal contended by all countries. Therefore, the call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plete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ies and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management model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stro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management of high seas fisheries in the middle Arctic Ocean, and sorts out the related management models of high seas fisheries resources. Then a new model is put forward, so as to speed up the pac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Arctic affairs, improve its ability to deal with Arctic problems, and jointly build the Arctic destiny community.
Key words :stakeholders; the middle Arctic Ocean; the high seas; fisheries; Arctic Pole
中图分类号 :D8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2-0045-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7XGJ003)
作者简介 :
王玫黎(1964—),女,四川成都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公法、海商法研究。
武俊松(1993—),男,河北沧州人,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海洋法、国际法研究。
〔责任编辑 :阮凤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