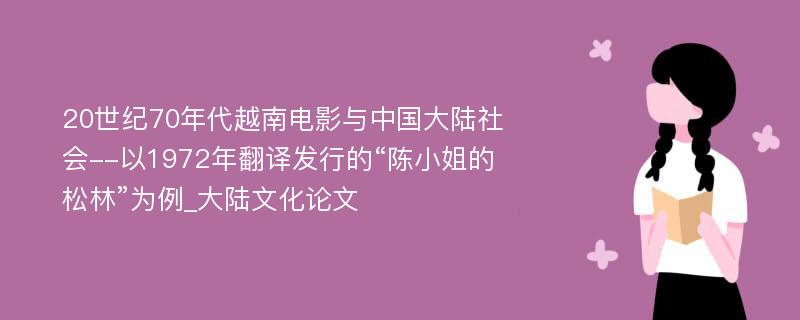
越南电影与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社会——以1972年译制公映的《琛姑娘的松林》①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松林论文,越南论文,为例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姑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4)02-0120-07 尽管越南是一个电影小国,但在1959年之后,尤其是“文革”时期,越南电影不仅成为中国大陆社会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当时的亿万观众保持了长达二十年的历史共时性依存,就像朝鲜电影与中国大陆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关系那样,血浓于水、荣辱与共、万众一心、同仇敌忾。 从现在为数不多的资料看,1951年,中国大陆就与越南联合拍摄了一部名为《战斗中的越南》的长纪录片(张寥林、阮月眉联合导演)[1],而越南出产的第一部故事片《同一条江》(1959)在次年即由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后在大陆公映。从译制的时间和数量上看,大陆20世纪60年代(1960~1965)译制的越南电影有9部,即《同一条江》《阿甫夫妇》《中线炮火》《纪念品》《白烟》《金童》《义静烈火》《年轻的战士》《浮村》。20世纪70年代(1970~1974)也有9部译制后公映,即《森林之火》《前方在召唤》《战斗在继续》《阿福》《回故乡之路》《琛姑娘的松林》《山村女教师》《小火车站》《火》②。 这些越南电影的密集和反复放映主要集中在“文革”时期,对大陆社会产生重大影响也基本是在这一时期。原因是“‘文革’十年浩劫特别是前五年文艺百花凋零,在人们听八个样板戏听得耳朵眼儿起茧子的情况下,进口公映上述国家的一些影片也算是来点儿花样,禁锢的铁幕还留下一丝缝隙,譬如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有《海岸风雷》《宁死不屈》《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等,同志加兄弟的越南有《阿福》《回故乡的路》《琛姑娘的松林》等。还有两部苏联老影片《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一九一八》放映率更高,与国产老电影‘三战一队’享受同等待遇——只有你不想看的时候,没有你看不到的时候”[2]。 单就这18部越南影片而言,其主题、题材和内容大致可以用三个“争”来概括,那就是战争、抗争、斗争。“战争”指的是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包括顺带提及的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者的光荣历史。“抗争”表现为对因为战争造成的恶劣的生活环境、生存环境、生产环境的抗争。“斗争”则是越南人民和敌对势力,包括本国敌对势力、反对势力、落后势力之间的斗争,包括思想和意识层面的对立和交锋。 鉴于中国大陆和越南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这些影片在整体上成为大陆模块化政治思想教育样本的同时,又成为官方引导民众认识外部世界——外国历史和社会现实的宣教平台。换言之,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一样,1979年前进入大陆的越南电影,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以特定的方式,印证、影响了中国大陆民众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人生观以及与之相应的艺术观和审美观。1967年出品、1972年译制的《琛姑娘的松林》正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一、越南电影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电影的简单比较 越南电影的三“争”特色整体上正好对应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思潮和官方口号。譬如,“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七亿人民,不斗行吗”等等。这既是毛泽东“斗争哲学”的典型体现,也是贯彻、体现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社会现实方方面面,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当中的人生指导思想理念。“人定胜天”讲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置方式,“亲不亲,阶级分”,用于对待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矛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文革”时期的大陆电影中只有“好人”和“坏人”之分(如果有“中间派”,那一定是糊涂虫,不是敌人利用了,就是后来被“我们”争取过来、改过自新了的。这样的社会心态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的价值评判和取舍标准并延续多年)。面对矛盾和分歧,只有一种解决方法即斗争解决。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如果从主人公成长历史的角度分析,这些越南电影还可以粗略地归为两类。第一类是男人版,以《回故乡之路》(1971)为代表,影片写一个越共战士孤身一人和强大的美军斗智斗勇。这个故事相当感人,其内在的张力不亚于英、美同年拍摄的《墨菲的战争》(Murphy's War,1971),后者讲的是一个人独自对抗强大的德国潜艇,最终大获全胜。第二类是女人版,代表作就是《琛姑娘的松林》。事实上,这个影片的主题是女主人公的心路历程和微妙的心理刻画,只是后半部分的情节被生硬地归位于主题先行的叙述模式。 虽然同属于亚洲电影和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也都曾经在历史上拥有同一个文化宗主国,但越南电影和同时期引进大陆的朝鲜电影却有着很大的不同。近现代的朝鲜,其历史和文化在传统上受到了中华文化约束,又接受了日本的殖民改造,因此,朝鲜电影就难免对威权形象的无条件尊崇。这也是为什么朝鲜的大量影片在具有明显的东方悲情主义色彩和基调的同时,又能非常轻松地与中国大陆“文革”时期的艺术形态和社会心态,以及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个人崇拜的社会基础融洽一体、无缝对接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进入近现代的越南,由于受到以法国为代表的欧洲文化的长期侵入,其中华文化的接受、浸透和熏染,更多地成为其本土文化的背景性存在,继之而来的是更为现代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洗礼。虽然这些洗礼都不乏血与火的暴力媒介,但不能否认的是,越南的历史和文化在近现代逐渐脱离了单一品质的继承性质。尤其是越南战争期间,东西方政治势力和文化潮流成为第二种形式的多元介入。因此,在越南的电影中,也相对缺乏朝鲜式狂热的个人崇拜;或者说,电影中类似的痕迹虽很明显,但远不能与中国大陆和朝鲜电影相比。譬如,如果按照朝鲜电影的逻辑,《琛姑娘的松林》会这样处理军车因为大弹坑不能前行的问题——领导过来说:“胡志明伯伯教导我们说,我们一定能打败美帝国主义”。 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时期,同属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如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的电影也几乎同时在中国大陆反复公映。将此时期的越南电影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两国的电影相比就会发现,两者的差异更大。除去历史和文化的不同,亚洲与欧洲、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这两个不同的文明圈和文化层,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电影本体理念上的根本性不同。换言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两国电影的电影理念和表现手法更为成熟、圆润,越南电影就显得稍稚嫩一些。不过,如果单就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而言,最为出色的当属越南电影。 如果说,“文革”时期进入中国大陆的朝鲜电影,不过是外国版的“样板戏”,那么,格调、色彩稍有不同的越南电影恰好弥补了中国大陆在电影文化上的一个空白。这种弥补的特殊历史情境和客观前提是: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向上彻底斩断了本土传统文化的延续;向外基本隔绝了与西方文化的良性互动和现代文明的共时性渗透;对内则以“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抑制了正常人伦的常态表达。因此,从一个细微的角度上讲,越南电影《琛姑娘的松林》里的人情、伦理,乃至隐约存在的爱情心理刻画,以及富有东方色彩的视听语言表述方式,至少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反哺式的滋养或弥补。 二、《琛姑娘的松林》的文化特色与中国大陆社会的读解语境 《琛姑娘的松林》除了故事的主题思想,譬如对战争环境的强调、无处不在的党的领导以及干群关系的主次位置,与当时的中国大陆电影多有对接之处外,其他的就显得有点“另类”。譬如一个情节很简单的单线故事,却被处理得情绪丰满、摇曳多姿,相对于当时的中国大陆电影,绝对胜出一筹,故笔者视其为越南电影“女人版”的代表作。 1.女性信息以及人物形象。 即使是普通观众,也能感受到这个片子的与众不同。譬如表现女主人公的镜头特别地“贴”,近景、特写、空镜和长镜头都是,但最重要的是,导演从镜头的运动性当中体现出来的情感性。“贴”的结果是让人们发现,这些镜头是会说话的,表情达意极为到位。其实琛姑娘和年轻的军车司机之间只有一种似有还无、隐约可见的情感传递,但就是这些东西打动了观众。因为这些情景散发出无比强烈的、女性独有的情感信息。而且,客观镜头和主观镜头交叠在一起,层层铺开。前者指的是观众的角度,后者的重点是影片前半段中几个年轻男性军人的视角,其中包含了很多性审视和性审美的意识。 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影片放映的20世纪70年代是中国大陆一个特定的时间。这个“特定”有如下几层意思:第一,观众大多处在青壮年时期,而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比例更大③[3]。第二,“文革”期间民众能看到的、能够表达情感,尤其是有关女性信息的电影几乎没有,涉及性信息的镜头少之又少。第三,那时候大陆“样板戏”和“样板电影”也少有女人出现。如果有,她首先是战士,其次是女战士,最后才是和男人一样的革命者,而且不近男色,内心充满的除了“民族仇”就是“阶级恨”。 譬如单就女主人公来说,现代京剧《海港》(1972)中的方海珍是中年单身女,《龙江颂》(1972)里的江水英也是单身女中年,《杜鹃山》(1974)里的柯湘还是;《沙家浜》(1971)中的阿庆嫂倒是已婚了,但名义上的丈夫压根儿就没出现过,除了名字。电影版的《红色娘子军》(1960)中男女主人公的情感戏已经被工作上的上下级关系替代;到了“文革”,无论是芭蕾舞剧版(1970),还是现代京剧版(1972),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个人情感,只剩下宏大叙事的阶级感情在支撑。《智取威虎山》(1970)干脆把原作《林海雪原》(1960)中的女主人公直接删除。甚至母子间的情感也有嫌疑,因为1974年翻拍1955年的《平原游击队》时,竟把原作中男主人公的母亲换成了没有血缘关系的革命大娘。这方面做得最彻底的是《奇袭白虎团》(1972),基本是男人戏,出现的大娘大嫂一概是朝鲜人④。 所以,《琛姑娘的松林》中有关女主人公的镜头和情感表达,与其说表现出一个勇敢的越南少女的独特魅力,倒不如说在那一段特定时空内弥散出沁人心脾的性气息和性信息。而其他的男性人物形象,又是从不同侧面、以不同形式衬托、强化了这种气息和信息的存在与质感。譬如琛的父亲,他和女儿之间的父女关系比较特殊,因为这个家庭缺少妻子(母亲),而兼父母功能于一身的这个男人形象显然比单一功能的父亲形象更能打动人心。影片中那段着力渲染的两棵松树成长的闪回,正是父女相依为命的典型象征。这两棵树既是父亲和女儿守望家庭的根基,也是父亲为女儿出嫁能做出的最后贡献。这不是树的故事,是血浓于水的亲情写照。 琛姑娘的形象还体现于其他三个年轻男性司机的审视之中,来自主客观镜头叠加后的反映,表达的是情感、心理和行为意识。在第一个男司机眼里,琛姑娘体现更多的是活泼、可爱,还有点小顽皮,譬如一方面用树枝为人家遮荫,另一方面又开玩笑地把人家的炉子端走了。第二个男司机更年轻些,他对琛姑娘的情感就比较复杂一些,譬如看到琛姑娘后,几次三番地梳理自己的头发——没人能够否认他对琛姑娘的好感和微妙感觉。影片情感线索的重点是第三个年轻男性,即在琛姑娘的指导下冒着敌机轰炸赶往前线送弹药的军车司机。这两人之间的镜头最多,也最为丰富、细腻。 从一开始的拒斥,到两人生死同一的危险经历,很少有人会忽略其中隐约的情感痕迹,或者说朦胧的爱情心理体现。即使是译制片,也没有删掉这处最“给力”的台词:当琛姑娘的父亲捐献出的两棵松树成为军车安全通过的桥梁后,这个年轻人激动地与老人拥抱,说“大伯,我应该叫您爸爸”。影片当然有歌颂越南人民战斗友谊的意图和基调,但在这里,当年电影院里几乎所有的观众都将之视为这是一对年轻人从此缔结良缘的证据,虽然世俗,但却最激动人心。 2.电影主题思想和时代背景的对应。 所谓主题的对应,指的是以《琛姑娘的松林》为代表的这批越南电影对应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现实。当时弥漫于中国大陆的是全民性的战争意识,因为最高领袖一再“教导”和“号召”人民,要“备战、备荒”,“提高警惕,保卫祖国”,“要准备打仗”,“不是小打,而是大打”,而“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琛姑娘的松林》属于战争题材,主要情节和所有的人物都围绕抢修军运公路,几乎没有表现日常生活的镜头。换言之,所谓的生活或生存其实就是战争生活或战争背景下的生存,而这种一切为了满足前线战事的需要、为战争胜利奉献一切的状态,正好对应于中国大陆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心态,即全民一体的战争意识和战争动员。 这种浓郁的战争意识首先表现为对民众牺牲精神的描述,譬如琛姑娘一家,父女二人都是民兵,女儿负责保障公路运输,父亲负责在关键时刻把准备盖新房的木料捐出来抢修桥梁。谁都知道,这房子不是父亲为自己盖的,是准备留给女儿的。所以他才对女儿说,“我不怕炸弹,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好好成长,有了好房子住,我死了就安心了!……有了房子,我就不操心了”。问题是,动员父亲捐献大树抢修桥梁以保证军火运输的,恰恰是他自己的女儿琛姑娘。此情此景,如此这般的行为意识当时的中国大陆观众实在是太熟悉了: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提倡的牺牲小我、奉献大我,牺牲自己、奉献国家和集体的精神吗? 而且,这种牺牲还不仅仅是财产上的、肉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和亲情上的。譬如,当美军飞机轰炸人民军的军车时,父亲和女儿都争着冲上去为军车指导安全路线;当抢修桥梁发现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时,抢着上去排除险情的还是父亲和女儿。这种争和抢意味着,无论是谁“有”了这个机会,一旦发生意外,都是对亲情伦理最大的和最痛苦的伤害:女儿上去了,对父亲来说,也许就会失去女儿;反过来,失去了父亲,对女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这个家庭本来只有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但影片恰恰要把这种非此即彼的伦理抉择残酷地呈献给观众,事实上是以此来教育民众。 其次是时代背景的对应,这主要表现为爱国主义即民族抗争精神的彰显。一般来说,爱国主义的定义和含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特定的表述,内涵和外延均有所不同。此处的爱国主义主要是指面对外国侵略时的民族抗争精神。在这一点上,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和越南有着共同的理解、一致的行为意识。对越南来说,正处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大陆而言,对外,北面有昔日的“苏联老大哥”陈兵百万、虎视眈眈;东面是“美帝”支持和操纵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蒋匪帮”,敌意不减当年;南面,是“美帝”引燃的“印度支那”战火火势正酣。而内部环境,国家政治正处于混乱状态,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民生艰难。因此,越南电影的全民抗争、保家卫国、争取国家和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思想主题,正好符合大陆用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大政方针。 就影响中国大陆社会的、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而言,朝鲜电影与越南电影一样,主题思想上也符合中国大陆的宣教口径,但越南电影的愚忠精神和个人崇拜意识相对淡薄。至少,不是每部越南电影都动不动会弄出一段“想起领袖教导”的画面而让人们泪流满面、又哭又笑;至少,《琛姑娘的松林》就没有类似的“菩萨心肠”和“霹雳手段”互为表里,进而触及观众的灵魂和泪腺。就这一点来说,《琛姑娘的松林》与当时中国大陆的电影是不对应的,但她却像闷热的房间里突然间吹进的一股清风,虽然力量不大,但足以让人清醒一时、舒心片刻。 因此这个片子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在大陆公映的越南电影的一个样本,因为即使外行也能感觉到影片的镜头具有韵律之美,既富有东方魅力也符合东方审美标准。尤其是影片开始时那几组镜头组合,譬如俯拍的琛姑娘苗条的身影,特写光着的两只脚。黑白影片恰恰最能表达色彩,少女黑色的服装,白色的沙子,阴影和光亮,色调饱满,魅力无限。 从1960年中国大陆译制公映第一部越南生产的电影,到1979年中、越两国爆发武装冲突、兵戎相见,二十年间的中、越两国的电影交流曾经呈现出一股单向度的热潮。相对于当时节奏拖沓、动辄哭天喊地的朝鲜电影,有时让人莫名其妙、有时又让人感觉惊险得喘不上气来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以及不无压抑的苏联电影,文化血缘更接近中国的越南电影如《琛姑娘的松林》,整体节奏把握得舒缓有致、细而不乱。譬如抢修桥梁时间紧迫的时候,一点都不突兀地加入了一段舒缓的闪回,交代那两棵树和一家人共同命运的由来。与其说这是对当年艰苦岁月的回忆,不如说是对家庭幸福时光的一种追述:两棵树长大了,中间的吊床上女儿静静安睡,妻子在旁边的破瓦罐上炒着松子。正是有了这层铺垫,父亲的决绝在迎合主题思想的同时,更从情感上印证了父女同心的真理。什么叫亲人?就是同心同德同感觉。 即使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大陆与举国战火纷飞的越南有着相通相近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但两边的电影制作理念却有很大的不同。就《琛姑娘的松林》而言,影片是以个人的视角和感受来见证时代,或者说是以小见大,《回故乡之路》也是如此。它们对个体和个体命运的描述详尽备至,这就意味着对全体的把握尽在掌握之中。这使人联想起苏联的《第四十一》《雁南飞》《一个人的遭遇》《伊万的遭遇》以及《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即使史诗般壮阔如《静静的顿河》,它的镜头也始终聚焦于男女主人公的情感世界,继而深入人性的层面。 可惜这些属于苏联“解冻时期”的优秀成果,大陆普通民众几乎无从看到,对电影的认知依然被滞留于斯大林时代的政治雾霾中。当时的大陆电影热衷崇“大”、崇“高”,其实依然局限于崇“假”、崇“空”。因为,“高”和“大”的角度实际上是基于对个体的忽略、对历史的清除,进而消弭现场感、真实感和艺术审美感受。譬如现在再看“文革”时代的电影,基本上是见“事”不见“人”,“事”都是大事:“两条路线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可是活生生的人呢?没有了人,电影也就只能是傻大黑粗的品相。 这样的制作理念和审美标准实际上也影响到了对当时外国影片的译制,这体现在配音上。譬如尽管《琛姑娘的松林》情感如此丰富、表达如此细腻,但对中国大陆观众来说,很难从声音上感受到这一点。即使是少女琛姑娘——情窦初开、还处于懵懂状态的小姑娘家,配音听上去也是尖、硬、生、狠的成年女声。其实,1949年后的译制片都可以看作是中国大陆的二度创作,所以,《琛姑娘的松林》的配音有明显的“文革”特征。 在20世纪70年代译制公映的那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应该说每一个国家的电影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以《琛姑娘的松林》为代表的越南电影,貌似失之于“单纯”的线性描述,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线索纷繁,情节线索设置比较精巧,拍摄、表现手法相对成熟。譬如阿尔巴尼亚电影《第八个是铜像》,用的是倒叙,非线性闪回构成其叙事客体;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的紧张惊险,不乏源自性心理的推动;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将世俗人情和宗教情结编织交集。这些都和越南电影的“单纯”不同,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现实主义依然魅力不朽的表现。因为越南电影的“单纯”能与朴素的表达和复杂的内涵奇妙地结合起来,其反映战争中人的特殊状态的主题思想正与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相吻合。 对中国电影而言,现实主义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不可或缺须臾的,但1949年后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大陆电影,根本没有现实主义的容身之地,只有意识形态上的“八股主义”盛行。就这个意义上说,朝鲜电影也有类似的傻大黑粗特征。“傻”指的是充斥影片始终的个人崇拜与宗教式的狂热和迷信;“大”,指的是见事不见人、见人不见情的所谓宏大叙事;颠倒黑白的“阴谋文艺”是谓“黑”,粗暴灌输的艺术手法的是谓“粗”。从这一点上说,越南电影尤其是《琛姑娘的松林》具有切实的但又不对应于接受语境的指导意义。 凡是经历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陆民众,只要看过哪怕一部越南影片,绝大多数都很难忘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越南电影与许多人的生命共同成长并就此融入历史时空。人的生命之所以是至高无上的,就因为每个人只有一次。这些越南电影曾经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以一个特定的即单向度传播的方式进入了其曾经的文化母国,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观众群体,尤其是“文革”时期,电影的观众动辄数以亿计。他们在相似的战争状态下,有着和越南电影一致的全民战争意识,而这种意识不仅与他们当时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息息相关,而且也延伸至今,譬如老父亲为孩子操心的住房问题:“辛苦倒没啥……我就是希望你能够好好成长,有了好房子住,我死了就安心了”,用过去那个时代的话说就是“中越人民心连心呢”。 收稿日期:2013-12-20 注释: ①《琛姑娘的松林》(又名《琛姑娘的森林》),故事片,黑白,越南民主共和国河内电影制片厂1967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72年译制,VCD时长:63分31秒。导演:海宁;配音导演:徐雁;琛——赵文瑜,琛父——郭振清,阿虎——马静图,阿贝——徐雁,司机——郑万玉。 ②这些影片的相关信息如下:《同一条江》,导演:阮鸿仪、范好民,1959年出品,上海电影译制厂1960年译制;《阿甫夫妇》,导演:梅禄,河内电影制片厂1961年出品,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62年译制;《中线炮火》,长春电影制片厂1962年译制;《纪念品》,导演:阮鸿仪、苑民,1960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62年译制;《白烟》,导演:阮翻利、黎少,1963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63年译制;《金童》,长春电影制片厂1964年译制;《义静烈火》,越南人民军电影团1964年出品,八一电影制片厂1964年译制;《年轻的战士》,河内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译制;《浮村》,导演:陈武、辉成,1964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65年译制;《森林之火》,河内电影制片厂1966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70年译制;《前方在召唤》,河内电影制片厂1969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72年译制;《战斗在继续》,长春电影制片厂1971年译制;《阿福》,河内电影制片厂1969年出品,八一电影厂1971年译制;《回故乡之路》,越南河内电影制片厂1971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72年译制,1973年上映;《琛姑娘的松林》,河内电影制片厂1967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72年译制;《山村女教师》,河内电影制片厂1969年出品,北京电影译制厂1973年译制;《小火车站》,北京电影译制厂1973年译制;《火》,导演:胡利奥科尔,河内电影制片厂1964年出品,长春电影制片厂1974年译制。(以上片目收集整理:钟端梧) ③能够查阅到的数据表明,1964年的大陆总人口约7亿,其中15~29岁的青少年占23.51%(见参考文献[3]),几乎占全体社会成员的四分之一。而从1963年开始,大陆人口出生率猛增,这意味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十几岁的青少年在总人口的比重愈加庞大。 ④说到性信息,《沙家浜》倒是有所传达,那就是刁德一的弟弟刁小三对一个年轻姑娘说的一句台词:“抢东西?我还要抢人呐!”这句话给无数观众无比丰富的想象,“抢人”是什么意思?比照现在的词,那就是要对女方“非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