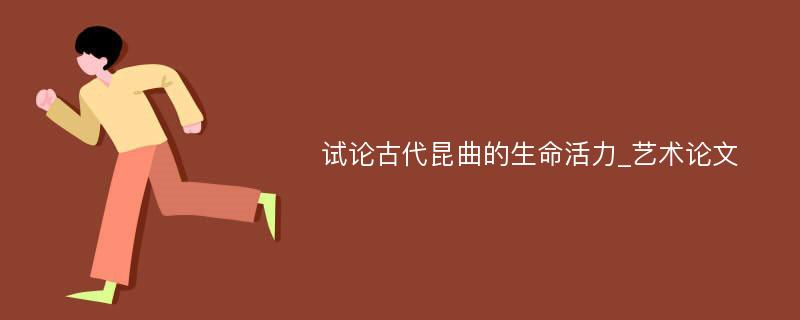
探寻古老昆剧的生命活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昆剧论文,古老论文,活力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戏曲的历史来看,在清代“花部”与“雅部”之争的过程中,最终是以花部成为剧坛霸主而雅部变为其附庸而告终的。但是,作为雅部的昆曲在戏曲史上的辉煌业绩是不能忘却的,它虽然在这种竞争中败下阵来,但并没有消失,因为它毕竟有着几百年的历史积淀,除了顽强地与花部并存着,同时,其精髓部分还被诸多声腔取为己用,并加以发展和创新。
当然,近代昆曲的发展,可以说也是举步维艰的。这主要是因为它继续沉浸在唱曲的角度,一味地对文学价值的追求和热衷于一声一韵的敲打之中。她是文人雅士工余饭后的案头之曲,长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独守清高,成为一种名副其实的、曲高和寡的“高雅艺术”。其实,昆曲的高雅实在应该是一种精神,不应该仅是一种形式,因而忘记了自己载歌载舞、“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的戏曲本色,失去了维系自身生命的根本。在这一点上,对于昆曲而言,可以说到了必须返朴归真的关键时刻了。
一、昆之曲,昆之命脉
就昆曲而言,有两种情况:其一,欣赏其华丽词藻和优雅旋律,喜欢几人围案而坐,观谱拥笛,细细品味。这更多地是诉诸于人们的听觉。但是,这种情况的不足是仅占人口总数的万分之一;其二,是作为综合艺术形式在台上演给人们看的。面对着成百或上千的观众,或在大舞台、或在小舞台上粉墨登场。这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双向接受以及由二者综合而形成的一种审美通感。后者应是真正意义上的戏曲审美功能,而清唱只能算是一种附加值产品。当然,清唱的形式也有她自己的功能:唱的人越多,越表明其曲子受欢迎的程度;她是戏曲这种以曲为先导的演剧形式吸引和培养观众的最佳方式。但当她作为一种舞台演出艺术的时候,截然不同于案头的清唱形式,甚至两者的性质、对象也不一样。一个是演给别人看的,是以娱乐对方为主;另一个则是唱给自己听的,是借曲子来抒发一种自我情感,是以娱乐自我为主的。由此可知,舞台演出的戏曲(昆曲)更需有一种自觉意识,一种随时代进步的意识,因为舞台演出永远是时代精神的反映,折射出时代的气息。而作为一种自娱和消遣的清唱曲调,至少是不能称之为完整的舞台艺术的。
中国人看戏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那就是注重欣赏她的技艺和审视其精神内涵,而相对轻视故事的戏剧性。纵观历史,不论是宋金杂剧、或是在她之前的被王国维称之为古剧的非纯正剧,表演上都特别强调技艺表现。一种艺术形式之所以能流行发展,和观赏者的喜爱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直接关系。过去的观众欣赏昆曲的什么我们暂不去考证,而今天的观众前来看昆曲,你让他们看什么?是武打?是身段?是词曲?还是故事情节?或许是让其仅仅目睹一下名角的风采?……在这一点上,昆曲艺术作为一种历史与现实的综合体,似应明确:其一,什么是昆曲艺术最独特的本质;其二,究竟是什么东西能使现代观众获得审美享受。从戏与曲的文字学意义来考究,昆曲应该最符合“以歌舞演故事”这一概念,因为她是在曲的基础上加以舞蹈而形成的一种戏剧,所以她最符合戏曲的定义。而且,越是仔细深入研究昆曲,便越是感到“曲”在昆曲艺术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曲”是昆曲的个性所在,也是它区别于其它戏曲种类的根本所在。从这个角度出发,“昆剧团”的称谓似乎有些欠妥,应该叫做“昆曲剧团”,才较为接近它的本质特征。但不管怎么说,这种颇具传统遗风、民族风韵的曲式,如能很好地揉进时代的艺术精神内涵,她在抒情、叙事方面给人的审美震憾力,当是不可低估的。
由此可见,故事的曲折性在戏曲中并不占主导地位。故事仅是一个载体,能引起观众兴趣的是载体里包含的内容,而内容必须通过能使他们获得审美享受的技艺——唱、做、念、打——得以体现。当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对于塑造鲜明的人物性格而言,观众们有了新的期望值,这就要求今天的唱、做、念、打不仅仅是建立在一个完整故事框架中的技艺表演,而且要达到两个目的:首先以直观的技艺来满足观众表层的审美需要,再通过技艺的表演展现性格,以达到创造鲜明人物性格之目的。所以,与其通过发挥独特技艺去征服观众,不如说在此基础上以创造出鲜明的人物个性来征服观众。在现代戏曲中,这两者早已密不可分:通过技艺表现性格;通过性格展现技艺。这是戏曲作为表演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也是区别于电影、电视和话剧的根本所在。
在戏曲中,技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形体的技巧表现;二、声音的曲调表现。这两者既相互配合又各有侧重,只有这两者配合好了才能真正体现以歌舞演故事的本质。就戏曲而言,以歌舞演故事,就是通过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塑造提供给演员一个施展技艺的机会。
当然,作为昆曲最本质的艺术表现形式“曲”,是一种曲牌体的音乐形式,与作为“腔”的板腔体相去甚远。曲的流畅性和连贯性为舞蹈表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依托,而板腔体就不太适合于舞蹈。也许正因为如此,运用板腔体的剧种在唱腔上有了极大发展,也才有了今天的流派之说。可以说是流派支撑了板腔体的弘扬和发展,观众对京剧和诸多地方戏曲的热爱主要是建立在以唱腔为依托的流派上。而昆曲似乎就没有这种传统,有的只是词、曲的派别,注重的是剧作中词的雅丽、文采、意趣、本色和曲的合律依腔、按字模声以及顺应时事、崇尚自然。演唱不能因人而异,必须遵循已有的词曲格式和旋律。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对昆曲来说,何人演唱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词的内容和曲的旋律,但它又不是清唱,作为戏曲它须以歌舞演故事,所以又要以舞姿来配合词曲的演唱,表现一段情节,完成一个故事。由此,曲在昆曲中既是词演唱的载体,又是舞表演的依托。正因为这样,昆曲成为一种曲调多而念白少的剧种,它始终以曲为先导来载歌载舞。
自然,昆曲的这些特点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也许历代的创作者更注重于词、曲内部结构的变化和调整,而没有意识到曲对于昆曲在其整体艺术结构中的绝对地位。今天,当我们来重新审视昆曲的时候,是到了该把“曲”提到重要位置的时候了。面对今天的昆曲,一定要充分发挥曲牌音乐旋律强的特点来结构一个戏,甚至可以适当削减打击乐而用曲牌音乐的节奏来引导舞台表演。
二、昆之舞,昆之神韵
沈达人在《中国戏曲通论》中写道:“从诗歌、音乐、舞蹈与戏曲形态的关系来看,戏曲实际上是一种有规范的歌舞型戏剧体诗,这是戏曲的最本质的艺术品格。也因此,戏曲才具有了自己的一系列艺术表现的特点。这一系列艺术表现特点,一般认为是戏曲形态所拥有的节奏性、虚拟性、程式性。”作为歌舞型的戏剧体诗,舞的份量不言而喻。可以说,在戏曲舞台上是无动不舞,角色除声音之外的任何形体动作都包含着节奏性、虚拟性、程式性。演员除了通过包含这三性的动作来完成角色有目的的行动,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三性来体现戏曲的艺术品格。自然,这是对戏曲的总体概念而言,落实到昆曲艺术,其实她对舞蹈的依附更是情有独钟,在以舞蹈表现人物的行为、思想方面昆曲也要优于其它戏曲种类。从总体而论,昆曲的对白要少于其它戏曲种类,思想、情感的表达更多地是靠曲的演唱,再加上曲的节奏和韵律感强,舞台上的演唱必需伴以优美的舞姿与其配合,方能使歌与舞这两者互为交融,相得益彰。
在中国艺术史上,舞蹈的历史很长,而舞蹈作为戏曲的组合成分则是经过了漫长的阶段。舞蹈能进入戏曲,正是由于曲的原因。曲调由坐着的叙事体演唱形式发展到站着的代言体演唱形式的过程中,需要动作给予配合和表达,这种动作不以再现生活中的真实行为为目的,而是伴随着曲调的旋律、节奏,变生活的动作为舞蹈化的动作,这种舞蹈化的动作在表现生活的过程中,必然呈现为一种虚拟的、写意的表现方式,当这种方式形成一种有机的模式以后,也就成了程式。
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中,早期诸多形成戏曲的艺术种类,如果它是一种要开口演唱的形式,一般都是演唱曲。虽然我们谁也说不出、也没有人听过那些曲子,但史料和文献的记录却相当丰富。戏曲就是在那些有唱曲而无舞、有舞而无唱曲或在叙事体形式唱与舞分而治之的演进中,逐渐形成了在代言体的基础上集唱、舞于一身,并最终完成表现人物的戏曲艺术的。
可以这么说,离开了表现人物行动的这种集虚拟、写意,有鲜明的节奏和韵律感的舞蹈,也就谈不上戏曲。而昆曲由于先天具备了音乐曲调上的优势,就更能在舞蹈的表现上和舞与曲的相互衬托上得以强化、发展。这既是昆曲自身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
当昆曲艺术发展到今天,似乎在这方面还显得有些不足。先拿昆曲的武戏来说吧。记得台湾的魏子云先生在他的一篇名为《昆曲的艺术魅力》的文章中写到:“皮簧戏(京剧)中的武戏,十之九都是由昆曲(剧)原样掠过来的。换言之,今之皮簧戏中的武戏,十之九都是昆曲的原本,不但武打,歌也是唱的昆曲。再说,皮簧戏中采用的牌子曲,也十之九都是昆曲的。”魏先生的这段回顾很好地表明了昆曲固有的对舞蹈的包容力,但也闹出了如魏先生讲的以下这个笑话:“有一次,一位德国留学生用怀疑的语气问我:‘昆曲没有武戏吗?’我很吃惊,反问她:‘此问从何而起?’她说是一位专家告诉她的:‘只有京剧才有武戏。昆曲是文人的产物,怎会有武戏?’她这一问几乎把我问愣了”。
魏先生的这个小故事虽然很普通,但它反映出昆曲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其实,不光是武戏,昆曲的文戏也并没有得到人们充分的认识,总认为这种典雅的文词、雅致的曲调所构成的昆曲应该是文文诌诌、慢条斯理、一唱三叹,并以能品味其词意和曲韵为上,所以戏曲文本一直都有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的区别,演唱也有清工(清唱)、戏工(登场演出)之分。但问题的实质是载歌载舞乃昆曲的本质,在曲调的引导下,歌声与舞蹈齐头并进,两者是密不可分地共同完成整个艺术展现过程。与其说是看词听曲,不如说是看一段别具神韵的歌舞表演,在一段段流畅、舒展,或婀娜多姿,或神采飘逸的舞蹈中,伴随着俊词雅乐,人们欣赏到的是那集文辞、音乐、声腔、舞蹈为一体的昆曲艺术。
著名京昆大师俞振飞先生,如果当年仅仅热衷于清唱而不正式“下海”登台演出,便绝没有后日之辉煌成就。他曾在《振飞曲谱》的序言中写到:“然而,清曲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它不如‘戏工’的紧密结合演出,与舞台形象产生距离,这是不符合唱曲艺术的正确而严格的要求的。”也正因为他在戏曲舞台上创造了一大批鲜明的艺术形象,使他成为了昆坛的一代宗师。这难道仅仅得益于他的“俞家唱”的美名吗?不,,是他细腻高雅的表演风格、儒雅秀逸的风度,是唐明皇、李太白、建文帝、柳梦梅、许仙、裴少俊这诸多鲜明的舞台艺术形象,构建了他艺术的丰碑。
正因为这样,我们也许能明白昆曲的唱,乃舞之唱;舞,乃唱之舞。特别是今天的“昆剧”更应如此。今天的昆曲应属于舞台上的昆曲。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区分案头昆曲与场上昆曲的实质,也有助于我们今天在继承和发展昆曲艺术时注意观念和意识的解放。正如沈达人先生在前面所提书中所说:“戏曲实际是上一种有规范的歌舞型戏剧体诗。”其实,昆曲最符合这个原则。所以,衡量一出戏曲是不是真正的戏曲,除了唱腔以外,就要看她能否以节奏性、虚拟性、程式性这三者为表演艺术的轴心,这是戏曲艺术的本质所在;也是戏曲的美学原则。对于以“舞”为第一创作原则的戏曲艺术而言,昆曲艺术更是其当之无愧的母体。
舞乃戏曲之魂,离开了舞也就无法谈论戏曲,这在以往的改编和创新的戏曲中(包括昆曲)已得到印证。那些试图革新的创作者们以为只要抓住了“曲”(与唱腔同概念),也就抓住了戏曲的根。于是,在注重人物的心理体验的同时,用唱腔和写实的方式来再现戏曲艺术,其结果当然不尽人意。因为他们不了解戏曲中的“曲”,既是唱之曲,更是舞之曲,既是唱带舞,也是舞带唱。
外国人把京剧翻译为“北京歌剧”(PIKING OPERA),其症结就在于只注意了曲,忽略了舞。其实,严格意义上的歌剧概念是没有舞蹈的。歌剧只是一种用不同形式、不同旋律的歌曲,再加上写实的行为方式来再现故事情节的,观众欣赏其艺术,第一着眼点在于歌声,第二在于故事情节,他们从来都没指望在歌剧中去看舞蹈,也没指望去看载歌载舞。戏曲是一种舞歌结合,并以节奏、虚拟、程式三大原则为其轴心的表演形式,与歌剧的表现形式相去甚远。对于昆曲也是一样的道理。目前,对昆曲有两种流行译法:Kun Opera、KunJu Theatre。后一种或许更好一些,因为它没有把昆曲界定在歌剧的概念中,承认这是一种叫作昆曲的戏剧。自然,这种界定也有弊端,戏剧可以涵盖昆曲,但戏剧的概念并不能完全解释昆曲。昆曲自有有别于戏剧的特点,这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
三、昆之“俗”,昆之本性
说到昆曲,今天的人们总爱称其为高雅艺术,但在本质上,也就是在具体的表现形式上,昆曲实在应是“俗”的艺术。现今有一种观点认为,词的雅、词的美是昆曲的第一特征,是她最大的艺术特点,并认为宁可少些观众,也不能丢掉这份高雅。毋庸否认,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文学)的源远流长,为戏曲的成熟作了很好的铺垫,也使戏曲艺术在以后的发展中,得益于文学的滋养颇多。但对于昆曲,这种滋养更多地体现在曲辞上,并不体现在其整体上。因此,绝不能因为文字的深奥或格律的严谨就以为是高雅,其实,昆曲真正意义上的雅在于她由通俗的曲、飘逸的舞、文采的词共同构建而升华出来的一种审美情趣的雅,并非单是文词的雅。它虽求文词具有文采,但绝对应该是通俗本色。关于这一点,戏曲史上的大家们早有论述。当然,我们在这里讲的俗是针对昆曲的文词不宜过雅而言的。因此这里的“俗”是有引号的“俗”,而非俚俗的照搬。即便是俚俗的东西,由于文人的参与及其对戏曲文本文字的提炼,也渐渐地变得雅致了。
可以这样说,整个戏曲艺术并不以表现文学为目的。而昆曲要表现的也是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载歌载舞的“舞蹈”、赏心悦耳的“曲”,以及由这两者综合而成的舞台表现形式,观众要感受的就是这种综合而成的审美通感,观众欣赏的不完全是文辞的义,更多的是负载这些文辞的曲之味。当然,由于文学性不断地强化,这种属于民间艺术的戏曲,在结构上、故事情节的完整性上、文字记录的规范性上、演唱韵律的丰富性上都得到了提高,使得她既进得宫墙又入得祠堂,既典雅又通俗。可以这样说:昆曲是一种由俗而不鄙的内容与细腻的歌舞形式相结合的高品味戏曲艺术。它自身文学性的丰富不是仅仅为了表达文字的优美,而是为了使剧本结构更加完整,演唱更加富有韵律,旋律感更强。它是作用于舞台演出的,不是纯文学的,它始终都应界定为一种“俗”的艺术。如果说我们能通过它的形式感觉到它高品味的话,那也是通过“俗”的形式来实现的。在这方面,历史已为我们储存了众多范例。
就拿我们都知道的,在北曲和南曲形成以前最为流行的诸宫调来说吧:它虽然具有相当的文采,但听来和读来确是十分通俗的。诸宫调在宋元时期即已是相当成熟、流行甚广的讲唱文学,她的文词已超越了里巷歌谣的那种鄙俗,显得更有文采、更加完整。但她也决不是雕章琢句、晦涩难懂的。据宋代王灼《碧鸡漫志》等书记载,诸宫调的唱法是北宋民间艺人孔三传创造的,非常通俗,一时为世人所倾倒。有了这种传统,加上元代的戏曲大家辈出,尽管北杂剧在结构上非常呆板,但文词的内容还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尽管杂剧有时也进宫廷演出,但他们更多的时候还是在瓦肆勾栏中为市民演出,基本上走的是一条生存于民间、服务于民间的道路。
南戏更是俗的代表,这种在市井俚俗小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由于不采取北杂剧的格式,形式上显得灵活多变,因此具有较强的活力,深受民众的欢迎。今天的昆曲虽走到了剧本文字上的另一个极致,可当我们沿着昆曲的母体向上溯源时,我们看到了它的源头是十分的纯净,十分的质朴。吴国钦先生就认为像《张协状元》这样的南戏不仅唱词口语化,而且情节也是通俗化,有许多插科打诨的段子:“如张协与贫女在破庙结婚时,没有桌子摆设,呆小二便用两手撑地,用背部做桌子。这时新郎新娘开怀对饮,呆小二却叫起来:‘做桌底腰屈又头低,有酒把一盏与桌子吃!’贫女问:‘小二在何处说话?’呆小二说:‘在桌子下!”这种穿插既让观众看到精彩的技艺表演,又使场上气氛轻松。整个剧本看来粗糙些,但朴素无华,这正是初期民间戏曲剧本的特色。
就象当年“北曲不谐南耳”一样,北曲虽然在结构上更加完整,文本上更有文采,但它完全把自己固定在一个近似僵化的形式之中,脱离了时代的需求和观众的需求,最终被结构不太整饬、也少文采的南戏所取代。这里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南戏符合戏曲艺术最根本的原则:贴近生活、贴近观众。而当高则诚的《琵琶记》问世后,又使南戏在结构和文采上跨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具有一种“俗而不媚,雅而不涩”的风格,也使作者成为一代剧坛的魁首。
后来的昆曲艺术由于过分强化词语的典雅,消弥了通俗的精神而带来的一种晦涩,是当初那些创作者所始料不及的,成了阻碍昆曲发展的一大障碍。因为看戏的过程本应是一个创作者与欣赏者之间的顺畅的交流过程,这中间要越通顺越好。如果大家都带着字典和听人解释才能看得懂,那真正是进了博物馆,变成一种看历史、看文物的过程了;同时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这种艺术在形式的结构上、表现的方式上也存在着问题。实践表明,无论何种艺术,特别是象戏曲艺术这种扎根于民间的大众化的通俗艺术,如果让观赏者无法理解,看不懂,无异于作茧自缚。
四、昆之新,昆之再生
当然,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如果用更加宏观的眼光来看今天的昆曲,它的问题所在并不仅仅是文词的典雅,还有诸多方面,正象有的人指出的那样:是文采有余而感发人心不足。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缺乏自身本体艺术特点的准确定位,没有找到一个已然存在的、真正属于它自身的艺术特性,而这种特性又是昆曲发展、特别是区别于其它艺术种类的首要问题。
自身的独特个性对艺术种类的弘扬是十分重要的,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忽略它,有时甚至视而不见,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前人留下的那点遗产,有时甚至可能是误传的东西。通常总在内容上作文章而不在形式上开拓。必须指出,这样说并不是要提倡形式主义,而是希望能顺应戏曲形式美这一艺术特征的需要,特别是昆曲的曲带舞的需要。要知道戏曲艺术从总体而言是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艺术,如此,才有了反复吟唱和反复观看的客观需求。近年来一些昆曲界的有识之士也力求在寻找新的突破点,但似乎收效甚微。相对而言,上海昆剧团在这方面迈的步子更大些、收效也较丰厚些。这其中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可获得的经验却是宝贵的。譬如,他们演出的《上灵山》,虽有诸多可议之处,还算不上是一出成功之作,但它的创作初衷却非常可贵:那就是力求使昆曲更加歌舞化,更加有旋律感,更加轻快,更加通俗,真正做到曲舞结合,舞为先导,逢动必舞。当然此剧在如何把握昆曲之特长与革新意识之结合方面尚有诸多值得讨论的地方,但它给了人们一个信息:昆曲艺术,只要把握好了载歌载舞、通俗易懂这个总的原则,还是会受到人们欢迎的。
最近上海昆剧团又接连排演了两个新戏。两者都力求创新,但由于编导的艺术出发点不一样,导致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出现,而其中相对被观众看好的《夕鹤》一剧,恰恰就是在如何使昆曲舞蹈化上做得好些。看得出,编导们在力求使其整体上展现出一种歌舞化的风格方面是下了功夫的。如果说《上灵山》在舞蹈化方面的探索较多地用现代舞蹈来演故事,还在台上为热闹而舞蹈的话,那么《夕鹤》已具有一种寻找艺术自身本质的觉醒。而另一出《一捧雪》,虽然也是新编戏,但由于它的编导更忠实于传统的、广义的戏曲艺术观,没有在如何把曲牌旋律溶进人物的行为中进行新的探讨,较多地在内容上作文章,因而基本上是一出遵循传统创作方法的新编老戏,没有显现出昆曲应有的歌舞化倾向,所以除了唱的是曲牌以外,在直观上与其它戏曲无多大差异之处。
艺术的魅力建立在艺术自身精神、品格的深入开掘、切实把握和被人们理解的前提下,只有当它们形成一种合力时,魅力才能显现。尽管传统的昆曲已是一位“老美人”,但她是来于民间、根植于民间的艺术形式,并经过几百年的锤炼而绵延至今的,这本身已显示出她旺盛的生命力,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昆曲艺术精神、品格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