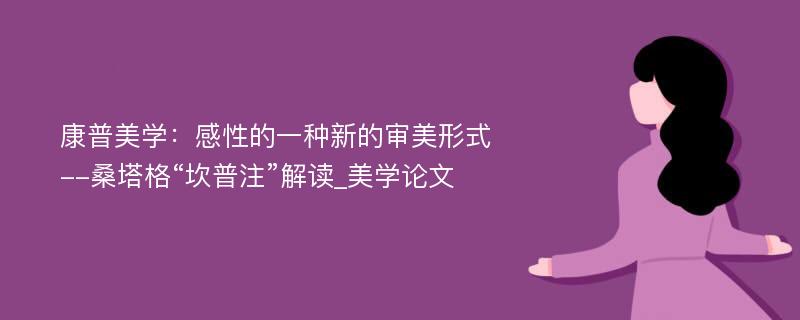
坎普美学:一种新感受力美学形态——解读桑塔格《关于“坎普”的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感受力论文,札记论文,形态论文,桑塔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9)04—0246—05
1964年12月11日,《时代》杂志刊登了桑塔格《关于“坎普”的札记》的主要内容,文中趣味(taste)一词用了黑体,在它之后是用引号引起来的坎普(camp)一词。这一纸檄文并不是在弄出点轻微响动后,就悄然躺在历史的角落中了,它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从局限于文人圈的《党派评论》跃至拥有巨大发行量的通俗杂志《时代》,从狭窄的纽约文人群奔向了浩瀚的大众。像桑塔格所期待的那样,“坎普”成为更多、更广的人关注、讨论甚至争论的热点问题,而她也荣膺“坎普皇后”。无怪乎威廉·菲利浦斯和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她是因为此文的写作而“一夜成名”的[1]。
《关于“坎普”的札记》不是一篇线索清晰、结构严密的论文,它由序言和58则“札记”组成,没有明确的层次分化、没有严谨的逻辑,前后论述常常重复、叠加又矛盾重重、悖论不断,甚至有些含混不清的地方。可见,桑塔格对“坎普”并不是毫不含糊地维护,这兴许就是她既为“坎普”所吸引又为它所伤害的表现。这种矛盾性和怀疑性也体现了桑塔格早期文章的批评功能:在纷繁复杂的辩证性中揭示对象的本来面貌。
桑塔格不是“坎普”的命名者,只是尝试描述“坎普”的冒险者,她不仅在茫茫的文化海洋中发现了“坎普”,而且发现了“坎普”与当下文化意味深长的关系,从而引起人们对于诸如感受力、文化趣味、文化等级秩序的分化、审美价值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和定位,推动了一些新趣味和价值的传播和接受。
用桑塔格的话来说,“坎普”是一种现代感受力,一种生动的感受力,“不是那种我们所熟知的对字面意义以及象征意义的层层叠叠、错落有致的构织,而是作为某物或任何物的意指的物与作为纯粹人工制品的物之间的差异。”[2]坎普同样是一种对失败的严肃性以及体验的戏剧化的感受力,它拒绝传统严肃性的那种和谐,又拒绝全然与情感极端状态认同的那种危险做法。”[2](P.334)更确切地说,“坎普”是一种新的感受力,一种现代的审美方式,一种新的文化趣味。桑塔格确信,“坎普是唯美主义的某种形式。它是把世界看作审美现象的一种方式。”[2](P.322)在王尔德那里,“生活模仿艺术”,这是对资产阶级传统美学的解构,颠覆了美的本体论地位及以此为基础的价值体系。以王尔德、佩特、戈蒂耶等人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追求艺术的非功利性,提出“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他们看来,艺术无须(也不应该)带有某种政治的或道德的训诫,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本身,即艺术的审美性。艺术既然是超功利的,那也就是说,艺术和艺术之外的功利世界是绝缘的,他们把艺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现象秩序,一种特殊的材料秩序,即一个同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封闭系统。这种特殊的现象秩序和材料秩序就是文学艺术的语言形式本身,即语言形式本身的审美功能。于是,追求形式技巧的雕琢和规整也就必然成为唯美主义的艺术理想。[3]坎普是唯美主义精神浸染的结果,或者说,坎普是新的文化和时代语境下的“唯美主义”运动的拓展。但是与王尔德等唯美主义者不同的是,桑塔格所维护的坎普不是采用奇装异服来显示自己的贵族精神和对“生活就是艺术”的理解,而是显示出对于传统艺术、新艺术、“非艺术”、“反艺术”,甚至生活的碎片和细节等等强大的感受能力和独特的审美趣味。在她那里,从非崇高的艺术中也可以找到趣味,“非艺术”、“反艺术”也存在艺术的价值。趣味和美无处不在,只要你善于去发现,即便是刀、叉、勺也散发着灼灼的艺术光芒。作为一个具有高贵审美能力和强大感受力的精英知识分子,她的职责不仅是继承、传播旧有的趣味和价值,还应该去不断发现、开掘新的趣味和价值,旧与新不是势不两立、非此即彼的,新是对旧的补充和发展。于是在她的努力下,感受力的层级、艺术的空间、美学的能力都不断地拓展、延伸,成为滋养意识和道德能力的养料。桑塔格的坎普感受力更进一步强调了唯美主义的那种解构功能,不但彻底抛弃了资产阶级传统美学追问“美是什么”的价值体系,更重要的是,它在颠覆艺术等级秩序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审美趣味,这一趣味是与当时风起云涌的文化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成为构建与当下时代相宜的新感受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关于“坎普”的札记》一文中,桑塔格尝试着勾勒了“坎普”的大致轮廓,将“坎普美学”正式地纳入新感受力美学的范畴。
首先,坎普是那种“纯粹审美的感受力”,强调“技巧”、“风格”,坚持“在审美层面上体验世界”,它“体现了‘风格’对‘内容’、‘美学’对‘道德’的胜利”,体现了“反讽对悲剧的胜利”[2](P.334)。这种特征从其诞生伊始就一直延续着,与唯美主义的追求一脉相承。“这种方式,即坎普的方式,不是就美感而言,而是就运用技巧、风格化的程度而言。”[2](P.322)坎普艺术作品“常常是装饰性的艺术,不惜以内容为代价来突出质地、感性表面和风格。”[2](P.323)一切“坎普”的物或者人,都包含了大量的技巧因素,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为“坎普”。“坎普”是一种以特别的风格表达出来的世界观:它充满着对夸张之物、“非本来”(off)的热爱。可以说,追求“非本来”、追求脱离是坎普的基本结构。桑塔格认为最彻底、最典型的坎普风格体现在新艺术当中:例如照明设施被制作成了开花植物的形状,起居室被制作成了名副其实的岩洞,赫克特·基玛把巴黎地铁的入口设计成了铁铸兰花柄的形状……[2](P.324)它们都处于非本来、非本身的“另一种状态”中。她还进一步指出:“作为一种对人的趣味,坎普尤其对那些十分纤弱以及极度夸张的人物感兴趣。女性化的男子或者男性化的女子肯定是坎普感受力的最伟大的意象之一。”[2](P.324)可以这么说,坎普在它身上寻找“非他”的因素,并且醉心地迷恋这种“非他”的因素。因此,拉斐尔前派的绘画和诗歌中的那种孱弱、纤细、柔软的人形;被雕刻在灯具和烟灰缸上的新艺术出版物和招贴画中那些单薄、平滑、缺乏性感的身体,格丽泰·嘉宝绝色美貌背后的那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男性化的闲散感觉等等都成了这种意象的典型代表。[2](P.325)
其次,坎普是对失败的严肃性的感受力,“在质朴或纯粹的坎普中,基本的因素是严肃,一种失败的严肃”[2](P.329)。桑塔格分析了高级文化的严肃性:那种达到原初效果,实现它背后意图的严肃性,即是高级文化的万神殿——真、美、庄严。这是评判高级文化的基准。接着,她分析了先锋文化的严肃性,一种以痛苦、残酷和错乱为标志的严肃性。博希、萨德、兰波、雅里、卡夫卡、阿尔托这些20世纪伟大的作家都实践了这种严肃性,他们强调这样一个原则:要创造出一部过去意义上的作品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指艺术中的作品,还是指生活中的作品,只有“碎片”是可能的。他们揭示了人类状况的另一种真相或者人之为人的另一种体验,也可以说,他们展现了另一种令人信服的感受力。[2](P.334)坎普所拥有的严肃性是不同的。如桑塔格所言,“坎普的关键之处在于废黜严肃。坎普是玩笑性的,是反严肃的。更确切地说,坎普与‘严肃’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关系。”[2](P.328)她所说的被坎普罢黜的“严肃”是高级文化和先锋文化所垂青的那种严肃,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严肃,它确立了与高级文化、先锋文化不同的价值评判标准。严肃是坎普的绝对态度,也即是说坎普艺术家在参与创作的态度上是严肃的,她举例说:新艺术的艺匠把盘绕的蛇雕刻在自己制作的灯具上,不是图好玩,也不是为取悦他人,而是认为它具有真正的东方情调;巴斯比·贝克利为30年代早期华纳兄弟影业公司的那些音乐剧设计的数字标题,比如《第四十二街》、《一九三三年的淘金者》、《一九三五年的……》、《一九三七年的……》等等并不是有意为了逗乐。[2](P.328)只是“坎普”是反悲剧的,因为悲剧将自己深深地卷入某种事态当中,成为参与者、介入者;而“坎普”提出一种喜剧色彩的世界观,它不那么投入事态的体验,参与事态的进行,而是维持一种不动声色、超然事外的体验状态,作为旁观者出现。因而,坎普面对的是一种失败的严肃,虽然它严肃地规划自身,但是它崇尚铺张、崇尚戏剧化,它不能成就高级文化中那种严肃的成功、也不能达到先锋艺术中那种道德激情与审美激情之间的张力,它太过了。在坎普那里,传统美学的严肃价值落空了:历史的绝对价值、人性的追求、理念的至高无上地位、理想、自由、真善美都失却其原有的意义。但是那并不是因为“坎普”刻意去摧毁、刻意去放逐这些崇高的价值。而是其努力追求之后的结果是这些严肃价值的落空,于是它只能在技巧、形式、风格、戏剧性中去寻找新的价值,而这些因素是诉诸感受力的。于是它建立起一种以新感受力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从而逃离了虚无主义的陷阱。“当然,并非所有失败的严肃都可以作为坎普而获得救赎。只有那些适当地混合了夸张、奇异、狂热以及天真的因素的严肃,才能算作坎普。”[2](P.329)
再次,坎普是体验的戏剧化的感受力,是被平庸所胁迫的艺技表演。“那种传统的超越一本正经的严肃性的手段——如反讽、讥讽——在当今显得软弱无力,不适合于为文化所浸透并滋养着当代的感受力的媒介。坎普引入了一种新的标准:作为理想的技巧,即戏剧性。”[2](P.335)王尔德曾经宣称“不是艺术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对于唯美主义者来说,“生活即是艺术”,整个世界都可以被看做审美现象,这是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种努力。而桑塔格在谈论坎普时说:“坎普在引号中看待一切事物。例如这不是一只灯,而是一只‘灯’;这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女人’。从物和人中感知坎普,就是去理解其角色扮演的状态。它是生活是戏剧这一隐喻在感受力中的最远的延伸。”[2](P.325)桑塔格显然挪用了“生活即艺术”的观点,将它改装为“生活即戏剧”,而坎普正是这一隐喻在感受力领域最远的延伸。坎普感兴趣的是扮演、是夸饰、是浮在真实躯体之上的面具、是一袭华丽奢靡的袍子,它混淆了现实和景观、生活和戏剧。更确切地说,在坎普感受力的观照中,没有现实,只有景观;没有生活,只有戏剧。“坎普”是那种连贯的、狂热的方式展示的铺张,它来自于一种不可遏制、也无法控制的感受力,它喧嚣、奔涌,它激情四射、非同寻常。桑塔格宣称:“没有激情,人们就只能得到伪坎普——即仅仅是装饰性的、四平八稳的东西,一句话,是花哨。”[2](P.330)因此,“一件作品可以接近坎普,但无意成为坎普,因为它已经达到了效果。”[2](P.330)她认为爱森斯坦的影片很少是“坎普”,因为他的影片尽管也有铺张,却没有多余,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如果它们多一些离谱,可能就能成为伟大的“坎普”。“固定的性格”是“坎普”感受力体验戏剧化的一个关键因素,换言之,坎普感受力体验的戏剧化是那种持续的存在、反复和重叠。
第四,“坎普”趣味提倡一种艺术民主的原则,它“反感惯常的审美评判的那种好-坏标准。坎普并不变易事物。它不去争辩那些看起来好的事物其实是坏的,或者看起来是坏的事物其实是好的。它要做的是为艺术(以及生活)提供一套不同的——补充性的——标准。”[2](P.333)在桑塔格看来,王尔德的许多态度显露了某种更为现代的东西:当王尔德表示他志在“配得上”他的青花瓷器或声称一个球形门把手能与一幅油画一样令人赞叹时,他道出了“坎普”感受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对一切物品等量齐观。当他宣称领结、别在钮孔里的花、椅子的重要性时,他已经是在提前实践“坎普”的民主精神。[2](P.336)在传统价值体系当中,艺术趣味有严格的等级区分,真、善、美被奉为高级文化的准则,而与高级文化趣味相左的艺术都被排除在高雅、严肃、经典的门槛之外,贴上了低级、媚俗、黄色、淫秽、颓废等标签。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的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依然秉持这种观念,其代表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和麦克唐纳都捍卫着精英文化的阵营,贬斥大众文化、媚俗文化。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在《先锋派与庸俗艺术》中写道:“一般来说,在有先锋派的地方,我们总会发现一个‘后卫’。确实如此,它就站在先锋派的大门口,这第二种新的文化现象出现在西方工业国家:德国人给它起了个绝妙的名字——Kitsch(庸俗艺术,或译媚俗)。它包括流行的商业性的艺术和带有彩色照片的文学,杂志封面,插图,广告,通俗黄色小说,喜剧,艾莱的音乐,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等。基于某种理由,这个巨大的怪物始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4]在该文中他进一步指出:“庸俗艺术把真正文化所贬斥和程式化了的形象用做原材料,助长和培育了这种迟钝感觉,这正是它可以获利的源泉。庸俗艺术是程式化和机械的,是虚假的快乐体验和感官愉悦。虽然庸俗艺术依据样式而有所变化,却始终保持着同一性。它是我们时代生活中一切虚假事物的缩影。庸俗艺术宣称除了金钱之外,对消费者无所要求,甚至不费时间。”[4](P.194-195)不难看出,第一代纽约知识分子以保守的精英姿态对抗着不断出现的新的艺术形式和文化现象,坚持以“内在价值”和“终极价值”为文化的旨归,对庸俗艺术、流行文化充满了厌恶、排斥。桑塔格也赞赏先锋文化,但是她突破了格林伯格这种狭隘的先锋概念——隶属于高级文化的先锋概念。在她的理解中,先锋是一种以反叛和创新的姿态出现的新艺术,在其所倡导的审美趣味没有被接受并普遍化之前,它可能被看做“另类”、“边缘”、“怪异”、“反艺术”、“非艺术”,甚至媚俗之作。坎普实际上就是要颠覆这种传统艺术观念中文化等级秩序的严格划分,消弭高雅文化与低级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先锋艺术与媚俗作品的绝对化距离,批判一元的、非此即彼的评判价值,建构一种新的品味、欣赏的方式,而不是去指手画脚地评判,它所依据的便是一种新的感受力——与当时文化艺术、社会状况相适应的感受力。这种新感受力是纯粹审美的,它拉平了身体与心灵、观念与现实、内在状态与外在状态的界限。于是在这种感受力的反应当中,身体的地位得到了恢复,而心灵的激情仍然备受重视,人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完满的状态来创作艺术和感受艺术。“坎普”致力于敞开新的感受力,致力于彰显这种新感受力的价值,发现一种新的对世界的审美方式并打开一片新的审美空间。于是,坎普为流行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甚至一些庸俗文化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它可以在坏趣味中品味好的趣味,也可以在好趣味中品味坏趣味,关键的是鉴赏者本身的感受能力。
最后,“坎普”是大众文化时代的纨绔作风(dandyism),“坎普趣味从其本性上说只可能存在于富裕社会,存在于那些能体验到富裕的精神机能障碍的社会或者圈子”[2](P.337),“超然,这是精英的特权;正如十九世纪的纨绔子在文化方面是贵族的替代者,坎普是现代的纨绔作风。坎普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这个大众文化的时代,怎么成为一个纨绔子。”[2](P.336)纨绔子在欧洲社会中所代表的主要是贵族阶层,特别是那些艺术家或具有艺术家风度的小群体。欧洲的纨绔子,在19世纪具有相当复杂的社会含义。他们是游离于主流社会的人,拒斥资产阶级的主流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具有相当的思想修养和艺术追求。他们反抗资产阶级的工具理性和现代性,具有强烈的唯美主义倾向。[5]桑塔格指出,“坎普”是与同性恋文化相适应的,坎普趣味扮演着同性恋“自我身份合法化”的工具角色,他们通过提升自己的美学感受力来将自己内置于现代社会当中。但是坎普并不仅仅是同性恋趣味,它是“贵族趣味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标志着一种以更加武断和真诚的方式来坚持纨绔作风的姿态。“纨绔子受了优裕的教养;他的姿态要么倨傲,要么厌倦。他寻求那些稀有的、未被大众趣味糟蹋的感觉……他献身于‘优雅趣味’。”[2](P.336)“坎普鉴赏家发现了更巧妙的乐趣。他的乐趣不在拉丁诗歌、稀有的酒类和天鹅绒上衣上,而在那些最通俗、最常见的乐趣上,在大众的艺术上。仅仅是利用,并不糟蹋他的乐趣的对象,因为他学会了一种稀有的方式来拥有它们。坎普——大众文化时代的纨绔作风——不在独一无二之物与大量生产之物之间进行区分。坎普趣味超越了对复制品的厌恶。”[2](P.336)也就是说,在文化过剩、富裕的社会中,坎普提供了一种贵族趣味幸存的形式。坎普可以看作对于精英姿态和精英意识的讽刺性、智性的维护。不能将坎普等同于大众文化,但是它的确与大众文化、流行文化、通俗文化、甚至媚俗文化紧密相关。马泰·卡林内斯库评论说:“如果先锋派和坎普时尚可以求助于那些显然同最确定无疑的媚俗艺术相联系的形式与技巧,媚俗艺术反过来也可以通过模仿先锋主义的外表而获益。”[6]我们抛却媚俗艺术对高级文化、先锋、坎普的模仿和利用暂且不论,但坎普的确与大众文化有着微妙的关系,它超越了对于“灵韵”的崇拜,对本雅明所言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抱以宽容和吸纳的态度。传记家利亚姆·肯尼迪认为,坎普可以说是一只美学透镜,我们通过它可以审视大众文化,它提供了在“大众艺术”中获得快感的可能,并且通过设置趣味的屏障来将快感从“大众艺术”中分离出来。可以说,它是一只不带色的美学透镜,拒绝把文化的歧视性带入观看的过程。[7]它假定了一种趣味民主,但是坎普这种民主是以保护它自身的“贵族趣味”的方式进行的。在这里它为桑塔格自己提供了一个对待大众文化的比喻:只有在它恢复为艺术作品的时候,她才准备好去为它庆祝。她的方法是要“大度”(一个她在描述新感受力挑战高级文化的时候经常使用的有效的词)和包容,将多种多样的经验纳入美学审视的范畴。这并不妨碍她对于那种密闭的现代观念真诚地、愤怒地挑战,这种现代观念鄙视大众、鄙视泥泞,鄙视街区。桑塔格避开这些鄙视,因为她的目的是重新审视现代主义和大众文化之间早已建立起来的那种辩证性的关系,并促进一种新的批评意识的产生。[7](P.35)通过坎普,桑塔格仍然维护了一种精英知识分子的姿态,坎普精神中那种根植于历史焦虑中的自我意识所显露的被动性、分离性、反道德性,表明了一种从社会经验中自我保护性的撤退,也表明了一种对大众文化的客体和风格世故性地使用和占有。正如王秋海博士在他关于桑塔格形式美学的论著中所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断定,桑塔格在60年代已经深切感受到了后现代主义艺术以拼贴、并置、仿象(simulacrum)等手法强烈消解现代主义追求终极理念和创立个性化的风格烙印努力的倾向,她在与这种大众流行艺术认同的同时,却也不希望看到现代主义精英艺术的旁落,因此祈求以“矫饰”① 在大众文化中重构风格,保持艺术的先锋性,并调和精英艺术和后现代艺术的对立性。”[8]
如果说,以王尔德等人为代表的唯美主义解构了古典美学的价值体系,消解了“理念”的宰制地位,批判性地发展了康德美学,使“纯粹美”从艺术中析出来,艺术从高高在上的万神殿重新回到生活当中,褪去了环绕在其周围的神圣光环。从而艺术成为生活的准则,艺术向生活敞开。那么桑塔格的坎普美学将唯美主义的行动又推进了一步,她为削平生活和艺术的界限找寻了支点——新感受力。在这个支点的支持下,我们才得以穿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摆脱对媚俗文化、流行文化不假思索的排斥,在它们当中找到在高级文化和先锋文化中同样存在只是不同程度、不同类型、不同质量的“快感”、“感动力”和“审美体验”。
也可以说,《关于“坎普”的札记》为“文化过剩的”美国社会,为经济发展、复制技术所带来的商业文化空前的繁荣提供了一种世故的回应。它超越了20世纪40、5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写作中所惯常的那种文化等级秩序的严格区分,也回应了更早一些时候批评界对于大众生产所带来的文化变迁的忧虑中的一些问题,引进了一种新的艺术和批评的多元主义和折中主义原则。[7](P.35)是桑塔格等知识精英面对无法抵挡的大众文化浪潮,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性反应,它既机智地回避了与文化主潮的无谓对抗,又巧妙地捍卫了精英的立场和趣味。
注释:
① 矫饰,也就是英语的camp,王予霞、王秋海等国内研究桑塔格的学者将其翻译为“矫饰”,但是camp这个词在文化领域的含义极其丰富和含混,不是直译为“矫饰”可以涵盖的,所以《反对阐释》的中译本采取音译法,将其直接译为“坎普”。笔者在文章其他地方均遵循该译法。
收稿日期:2008-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