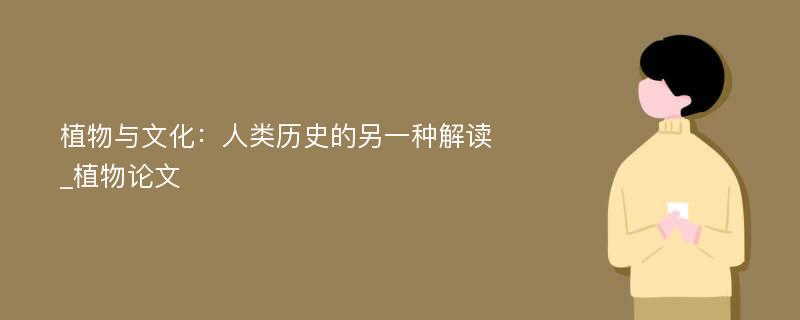
植物与文化:人类历史的又一种解读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论文,植物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Q9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12)01-0001-07
一、植物关乎人类历史的进程
当代植物分类学家确认,世界上生息着50多万种高等植物。民族学家则断言,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曾经成功的驯化和运用过上万种植物。可是,在当今的国际粮食市场上,大规模流通的粮食作物却不到10种。这显然是一个令人既惊讶,又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怪现象。围绕这一难题的解答,至今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只有这几种农作物才符合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也是人类能够靠得住的食物,可以长久依赖的食物。也有人认为,人口的爆炸迫使人类不得不利用现代技术、现代的生物技术,集中依赖这几种有限的植物维持生存,否则就无法养活数十亿的人口。还有的人认为,现代社会替代传统社会是一个不能逆转的历史进程,只有这几种植物最适合工业化的现代农业栽培和种植。上述人群之间,不同认识和理解差异的并存,只要考虑到人类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就会感到不足为怪,但历史进程本身应当有它的规律。之所以感到历史的进程复杂得难以捉摸,恰好证明人类没有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机制和规律。有幸的是,当代民族学的研究由于同时关注到文化的功能,又关注到文化与所处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而还注意到了文化的进化与历史演进的联动关系,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去解读植物与人类历史进程的关系开始变得可能。
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得以延续的根基在于它能够养活自己的成员,而养活这些成员最最关键的是要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食物需求正是民族学家理解文化功能的核心内容。食物从哪儿来,主要是靠植物替我们去生产,而文化的功能正体现为它能够有效的组织社会成员去推动植物的规模性、连续性栽培和收割,从而为相关社会提供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而文化的进化最终都会落实到对植物的驯化、种植与利用,而对植物驯化、种植和利用的变迁也因此而必然推动相关社会的历史发展。有鉴于此,从植物与文化的视角出发,渴望成为解读人类历史过程的一把钥匙。
这把钥匙的不可替代作用与传统历史文本写作的方式存在着一对一的匹配关系。长期以来,前人编纂历史的目的都是总结治国平天下的经验与教训,以至于前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人是地球上的万物之灵,因而对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很自然的会聚焦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精英人物的贡献,而较少关注支撑历史演进的文化这个根基,更会对支撑文化的植物这个根基的根基不屑一顾。结果,能够传到今天的史料文本记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记录精英人物活动的内容汗牛充栋,而规约社会进程的文化则无人提及。特定文化驯化、栽培和利用植物的具体过程则无人问津。我们现在所能够看到的文本史料是一种残缺的史料,看不到历史演进根基的史料。历史演化的规律复杂得让人难以捉摸,其实仅是一种假象。关键在于,我们对现存文本史料的解读较少触及历史演进的根基,因而历史才显得如此的复杂。如果反过来,我们能够从植物与文化入手,去解读现存的历史文本,发掘其间能够揭示根基与表现关系的信息,掌握历史的规律必将成为可能。
年鉴学派的前辈们由于能够从不同程度的认识和了解民族学分析思路和结论,他们也才注意到无论任何一种人类社会其构成要素在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其延续的时间有长有短,而波及的空间也有广有窄。只要将这样的构成要素区分为长时段、中时段和短时段,那么史料文本记载的残缺、扭曲、关系错乱等都能够因此而得以理顺。将他们的理解稍加延伸,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靠地质史上的自然选择汰选出来的当代现存植物,其物种包括他们的生物属性必然具有超长期稳定延续的潜力。只要它们进入人类及其文化的圈子里,那么它们就肯定是长时段的社会历史要素。换言之即为,今天我们吃的大米,其生物属性与我们祖先数千年前吃的大米的生物属性并无二致。历史文本中,对大米生物属性有关的社会文化事实,不管其间的关系多么远,即令史料文本未加记载,或者是记载有误,立足于今天对大米属性的认识,今天的历史研究都可以补缺,都可以匡正,并连带可以澄清与此相关的各种历史文化事实的真相。民族文化则显然属于中时段的历史要素。凭借文本史料对民族文化不同时段的事实的零星提示,借助民族学的文化整合分析方法,我们也能够对文本记载的残缺和偏颇做出令人信服的推测和复原。有鉴于此,只要将民族学、生态学作为两套工具去参与历史科学的研究,那么我们就可以极大的丰富史学研究的内涵,给历史研究另辟蹊径。利用现存的文本史料,揭示其背后隐含的历史演化规律和具体的历史过程。这里仅以几种与中国历史的发展紧密关联的植物为例,对文本史料、民族文化田野调查和特定植物生物属性的科学认识,将三者有效结合,那么很多历史上悬而未解的历史难题都可以得到逐一破解。当然,本文仅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只要能够持之以恒,历史的解读自然就可以翻开新的一页。
二、从葛藤到玉米的悲、喜剧
葛藤是一大类豆科藤蔓植物的总称。这种植物的生物特异性在于,它可以在我国17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荒山区广泛种植,而不与其他粮食作物争地。种植的投入少,但单位面积产量却并不低,而且不需要仓储、也不需要保鲜,可以随时随地取用。同时,它还是一种具有综合利用价值的植物。地下的块根富含淀粉,可以作为粮食食用,也可以做饲料使用。藤蔓的韧皮富含纤维是优质的纺织材料。叶子可以作为饲料,而花儿则是优良的蜜源植物,整株植物还是理想的观赏植物。在历史上,它曾经是我国好几个民族的主粮。在汉族的历史典籍中,早就对它有所记载。《诗经》中提到过葛制品的使用,而《吕氏春秋》则提到过以葛为姓氏的人群。可是,这种植物对中国历史进程所发挥的作用,史料记载却十分残缺和凌乱,因为在前人看来,葛类植物的种植和利用无关治国平天下的宏伟目标,以至于葛的真实历史价值长期隐而不显,直到清代的乾嘉之际,由于一次特殊的战争,葛在历史上的特殊作用才有幸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同时,它是以一个配角的身份,被或隐或现地提及而已。
清代的乾嘉之际,在湘、鄂、渝、黔四省边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苗民大动乱。当然,就在同一时期,全国还爆发了其他十多起大规模的动乱,而朝廷对付其他的起义都是通过擒贼先擒王的手段,轻而易举的将动乱平息,唯独对湘、鄂、渝、黔四省边区的苗民动乱却多年征战,但收效甚微。其原因在于传统的平叛手段总是希望通过经济封锁的办法使叛乱者的后勤补给不支的情况下,不战自溃。这一有效的手段在对付苗民的动乱时,却无法收到预期的成效。尔后,几经波折,军事长官才注意到这儿的苗民其食品构成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可以仰仗满山遍野半驯化的葛根和蕨根为食,不要说是围上几个月了,就算是围上几年他们也不会饿死。据此,清军调整了战术手段,不再实施大范围的封锁,而是化整为零。十几个或几十个士兵组成一个小组,各组之间相互策应,深入苗疆腹地,只要见到苗民露脸就一面追赶一面放枪,迫使苗民躲回山洞之中,无法挖掘葛根和蕨根充饥。结果,不到两个月,再辅以离间手段,原先看似无可奈何的苗民很快就俯首就缚。苗民间各集团的争斗随之而加剧,动乱也就很快被平息了。清人严如熤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战争获胜的关键做了他力所能及的揭示。然而,由于严如熤本人的立场观点是站在清廷的立场出谋献策,而不是从植物与文化的视角总结这一次生态战争的成败关键,因而他的《苗防备览》长期被后人所误读。误以为是苗民社会发展落后,被清廷所征服是无从规避的历史命运,而没有看清这是一场跨文化的生态之战。
苗疆平定后,清廷当然不会容忍苗民继续以葛根和蕨根为主食,因为这样的粮食产品无法在无比广阔的内地市场流通,被征服的苗民也就无法为朝廷提供税赋。这将意味着苗民还将继续成为朝廷的“化外”之民。可行的对策只能是施以“德政”支持苗疆的社会生产发展,这样的话,就既可以施惠于民,朝廷的教化也能够轻而易举的深入苗疆腹地。具体的做法也很简单,那就是由地方官出面,在苗区推广玉米、烟叶、马铃薯、红薯等外来作物的种植。这些作物对苗民而言,不仅新奇美味,而且可以在整个内地市场广泛流通,从中可以获取现金收入。加之,社会的安定又加快了这一技术更新的推进,以至于到了道光中期陆续编修的凤凰、永绥、乾城等地方志都明确地记载,玉米已经成了无可争议的主粮,当地各民族的主粮一半以上仰仗于玉米,现金收入则主要仰仗于烟叶。也就是说,整个农作物的结构几乎翻了个底朝天。葛藤和蕨根当地苗民虽然还在继续食用,但原先生长葛藤和蕨根的最好耕地现在已经改种了政府所推广的外来农作物。这些农作物在种植时,都是把葛和蕨类植物作为“杂草”去加以清除,只需持续种植玉米10年以上,那么就不可能再自然而然的长出葛和蕨类植物来了。更可怕之处还在于,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葛和蕨类植物的生长带急剧萎缩,只有到了灾荒年景,人们才会想到用葛和蕨类来度荒。这一转型,对朝廷而言是正中下怀,对苗民而言也只有感恩戴德之份。然而,始料不及的悲剧却在于生态环境快速恶化。
玉米等外来作物都是高秆直立作物,它们的原生地是中美洲季节性干旱的回归带,而苗疆腹地虽说距离回归带不远,但却极度潮湿,暴雨频率极高。再加上地质、地貌结构的高山与深谷相间,坡陡、土薄,在大面积种植玉米等高秆作物后,而且还要频繁除草。一方面降低底层大气的湿度,另一方面还要借此控制虫害的蔓延。玉米的产量虽然有了保障,但却给重力和地表径流的复合侵蚀大开方便之门。在道光以后的数十年时间里,山区的水土流失愈演愈烈,旱灾的爆发频度也逐年加大,种植玉米的效益越来越低。可是,到了这个时候,随着苗民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国内市场的拖动,已经无法放弃玉米的种植了。于是,为了给玉米保产,就得不断地与水土流失做抗争,抗争付出的代价与玉米的生产几乎持平。这样一来,推广玉米种植的所有经济成效也就丧失殆尽。原先的喜剧,而今却转换为了悲剧。不过,这一悲剧的受害者是苗民,而清廷则可以置身事外。
如果不澄清这一历史递变的实质关键所在,今天要想推动上述苗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肯定会显得无路可走,因为就短期的意愿而言,当地苗民也习惯于种植玉米,他们也开始恐惧,葛藤虽然对控制水土流失有再多的好处,但却当不了饭吃。这样的积习如果不做历史的回顾,肯定无法加以逆转,眼前的扶贫和生态建设也就不可能找到出路,但如果从植物与文化的视角入手,那么成败却只在一念之转。时下,当地苗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早就习惯于进城打工,他们的现金收入早就不仰仗于玉米了。他们的食物结构也已经和都市人逐步趋同,都是以大米为主食,种植玉米主要是喂养牲口之用。然而,在植物资源无比丰富的苗疆腹地,绝无离开了玉米就无法喂养牲口的道理。其中,历史上长期食用的葛藤本身就是最好的饲料,而且是可以复合喂养牛、羊、猪、鸡等的高产饲料。我们的扶贫当局只需以历史为鉴,帮助他们在观念上转过弯,形式上做一个创新性的回归,只需要扩大葛藤的种植面积,畜牧业、农业等都可以获得新生,生态建设、水土流失的根治也可以以逸待劳。加之,葛藤还可以支撑特种的纺织业、食品工业,甚至是能源产业。要做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三者兼备,并不是一件难事,而且无需再做深层次的论证去说服持有异议者,因为当地200多年来的历史就是最好的验证。
三、玉米和马铃薯的引进驱动了彝族大迁徙
对近300年来彝族社会的巨变,有两位学者分别做出了两项相互衔接的研究结论。先是方国瑜在编撰《彝族简史》时,明确地指出在近300年来,生息在凉山地区的大量彝族居民陆续迁出了大小凉山地区,向西展拓定居。凭借他们强大的武装力量,迫使原先生息在安宁河,及其以西地带的不少民族,如傈僳族、怒族、纳西族等民族也缓慢地向西迁徙,抵达滇西的横断山区,重新定居了下来。同时,他还明确指出这次规模巨大的民族迁徙与彝族社会的巨变有关联。其后,秦和平则进一步指出玉米和马铃薯在清初引进凉山地区后,由于这两种作物需要定居种植,加上这两种作物的生长季较长,定居的时间还不能够太短。这就使得彝族居民的定居时间相对延长。与此同时,财富的积累得以加快并进而导致农业劳动力的紧缺,最终使得此前已有的储养奴隶的社会惯例得以放大,俘虏汉族等其他民族当“娃子”,推动了彝族社会的巨变。奴隶储养的规模迅速彭大,彝族社会也变得军事实力日趋增长。向西展拓生息地也就在所难免了。可是,这两种外来作物为何会发生这么大的社会推动力,它与这两种作物的生物属性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关联性,却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在此之前的彝族和其他狄羌系统的民族相似,他们都是靠农牧兼营的生计方式生产食品,并围绕这一生计方式,及其所处环境的需要去建构自己的文化。这样建构起来的民族文化可以维持数千年之久,其中必然隐含着可以确保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特殊原因,而这样的特殊原因为何会在玉米和马铃薯的冲击下失效,则是解读这一段历史过程的关键。查阅相关的史料后很容易注意到,彝族的传统粮食作物是至今他们仍然在食用的当地特色农作物,燕麦、荞子和圆根。早年的彝族选种这三种农作物为主粮,除了这三种作物对当地的自然与生态环境具有极高的适应能力外,更关键的还在于,这三种农作物可以和游动放牧实现高效的结合。一方面,燕麦和荞子的生长季极短,从播种到收割只需要经历大致60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将畜群驱赶到高海拔地带放牧的时段刚好可以完成从种植到收割的整个农事工作。至于圆根。由于它是一种越冬农作物,只需要将种子播撒在羊粪堆上,不再进行任何的田间投入就可以安心等待来年的收割,也就是来年牲畜回到高海拔区段时,再去慢慢地收割。因此,三种农作物都可以做到农、牧两不误。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农业和畜牧业往往是冤家对头,大片的牧场只要有一些部分开辟成农田,那么牲畜偷食农作物,农田隔断了牲畜的放牧路线就会不断地引发冲突。可是,在彝族地区,由于农、牧的搭配照顾到了上述三种农作物的属性,同时又照顾到了畜群是往返于高海拔到低海拔之间的垂直放牧,因而农、牧两业才得以相安无事。这样的作物种植方式,既可以评价为不同凡响的创新,也可以理解为是特定自然与生态环境对彝族文化的模塑。然而,最为关键的是,文化与植物的这种制衡关系具有很强的可持续延伸能力,可以规避当地不断爆发的各种自然灾害,而农业和畜牧业产品始终可以保持稳定,农、牧业生态系统也可以自然更新,而不会表现出蜕变。随着玉米和马铃薯的引进,无论这两种外来作物产量再高,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也具有一定的适应能力,但它们肯定会打乱彝族原有的生计方式。
马铃薯的食用部分是地下的块茎,但在彝族分布区海拔偏高,地温必然偏低,在3000米以上的高海拔区段,地底下还存在着永久冻土层。要确保马铃薯能够在当地正常生长,并且获得高产和稳产,那么就必须要与气温偏低展开抗争。实际的调查表明,在凉山州,马铃薯产量最高的盐源县,一亩地的马铃薯种薯用量高达2000斤,而其产量却也高得诱人,亩产可以达到13000斤左右。即令是按照4斤马铃薯折算成1斤大米,其亩产量也远高于超级杂交稻的实验产量。不过,更大的劳动力投入也令人吃惊。每产1斤马铃薯,需要投入2~3斤干厩肥。干厩肥是经过暴晒脱水后的厩肥。如果按照体积计算,产出1个体积的马铃薯需要使用6倍体积的干厩肥,而且得将干厩肥垫在地上,将马铃薯的薯块种植在干厩肥上,而不能将其种植在土壤中。也就是说,马铃薯种薯块的整块种植,得必须整块种植,而且得包在干厩肥之中。这样一来,厩肥的搬运量就更大了,而由此结算出来的劳动力投入显然比种植水稻要高得多。这将意味着在高产马铃薯的诱惑下,要大规模种植马铃薯并确保其稳产和高产,必须投入巨额的劳动力。这一需求直接干扰了农牧兼营的农事节令。要种植好马铃薯必然要影响到牲畜的游动放牧,彝族的传统文化又是将牲畜看得比粮食更重,简直是将牲畜作为财富的象征去对待,因而这一来自外来植物的冲击,会使得彝族居民在传统与现实之间难以做到两全其美。要将牲畜作为财富的象征就得拒绝马铃薯,而要追求马铃薯的高产就得放弃对牲畜的钟爱。后来的解决办法,从文化与植物的关系而言,确实是做到了两全其美。当然,从族际关系而言,却有欠公平,那就是必须俘虏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替彝族从事他们认为是低贱的农耕劳作。奴隶拥有量的膨胀,就此种下了种子。
玉米也是如此。玉米种植需要不少于120天的无霜期,而且需要气候相对干爽,还必须有微风才有助于玉米完成授粉。偏巧,彝族的生息地不是每一个地方都适合玉米的种植,玉米只能够呈现为带状,在河谷坡面大规模种植。海拔再高一点,玉米就不能够顺利结实,而再低一点,河谷焚风导致的季节性干旱又会影响到玉米的正常生长。这样一来,玉米的种植带一旦规模化,就必然阻断彝族进行垂直放牧的通道。这就注定了玉米在彝族地区,在规模种植的状况下,必须设置围栏,以免遭逢农、牧难以兼顾的困境。然而,更难以绕开的纷扰却来自于玉米的生长期太长,而且生长期又全部处在一年中气温最高的夏季。这对垂直放牧的影响更大。
单从产量高,杆蒿可以做饲料着眼,引进玉米经济上十分划算,理当十分欢迎。可是,对于彝族的传统文化而言,却远远不是这么简单。由于玉米的生长期太长,必然会干扰游牧的经营,在一个地方的定居时间就不得不延长,这对于牲畜的抓膘和饲草资源的均衡消费极为不利。玉米的种植地又是从牧场改造而来,偏巧彝族的生息地恰好位于面向海洋的青藏高原东南缘,大气湿度极高,生物多样性水平也因之而较高。这不比在内陆干旱地带种植玉米。要确保玉米高产,除草必然成为劳动力最大的投入生产项目。这样的劳动力投入更会干扰对畜群的照看,而玉米的收割也会派生出劳动力配置的艰难。在如此潮湿的地带种植玉米,如何避免玉米因发霉出芽成了玉米收割中的难题。为此,玉米的收割不仅要及时,而且还要进行不断地晾晒。这样一来,要想种植好玉米,劳动力会变得极为缺乏,因而玉米种植规模一旦扩大,劳动力的需求就会驱动彝族社会大量抓人当“娃子”。这一作用的后果跟马铃薯的引进一样,几乎是在无意中刺激了奴隶拥有量的飞速增长。一方面,增强了彝族社区的武装实力,增加了彝族社区的财富。另一方面,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甚至引发与汉族地区的对立。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影响则是玉米和马铃薯的引入刺激了彝族传统阶层的大分化。彝族传统社会原有的黑彝、白彝、安家娃子、锅庄娃子在此前通过畜群的规模放牧,黑彝可以将地位较低的其他三个阶层牢牢的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但玉米和马铃薯引种过后,地位较低的阶层只要拥有一片土地就可以自立谋生,摆脱黑彝控制的倾向就会越来越强。近年来,对凉山州西部各县的调查表明,在这些地区与藏族、纳西族杂居的彝族,大部分都不是黑彝阶层。他们定居到木里、盐源等地时,都是与当地的藏族结盟,甚至是得到了当地藏族的荫庇才得以顺利定居。可是,他们自己在不久以后,又可以拥有不少的奴隶。这种情况直到民主改革后才宣告终结,而这一历史过程恰好可以印证玉米和马铃薯的引进确实起到了冲击传统社会结构的作用。
两种外来作物的引进,引发了彝族社会历史的重大变故。在其他民族中,虽然也有不少实例,但像彝族迁徙那样引发牵连式的社会大变动却不多见,因为这场社会变迁并不仅仅局限于彝族。它事实上牵动了周边好几个民族的族际关系都发生了巨变,而且很多巨变在历史文本中是以另外的面目出现,很少提及与彝族社会变动的关系。有鉴于此,剖析这两种外来作物与彝族文化的制衡互动,确实可以发挥重新认识历史文本的作用。作物引进据此绝对不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农业生产的技术“微调”。在近300年的彝族历史中,农业技术的“微调”事实上引发了一场历史文化的巨变,环境景观、生产组织、生活习俗、社会结构、科学技术,乃至是价值观和伦理观等,都发生了不容忽视的大调整。玉米和马铃薯作为植物物种而言虽然微不足道,但它们的后续影响却关乎整个地区的历史进程。这就是历史文本解读中的以小喻大。
四、桄榔木历史地位的沧桑
到了今天,葛藤不再是苗族等相关民族的主食了,燕麦粉也成了彝族老人才能够享用的奢侈营养品,但是这两种植物曾经辉煌的历史却在今天的民族文化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痕迹。为了调节口味,乡民们偶尔还会挖掘葛根食用,而在彝族地区则会用加工燕麦面的工艺去加工玉米。历史的记忆在文化中总是留下可资识别的痕迹,成为已经被遗忘历史的见证。前些年,我们在贵州的麻山地区做田野调查,惊讶地发现当地的苗族对玉米的加工并行着三套不同的工艺:一是将玉米磨碎,多次反复蒸煮,做成玉米饭。这儿所采用的工艺与汉族煮米饭相似。二是将玉米磨成很细的粉末,混入糯米浆蒸成饼食用。这套工艺与很多民族做糍粑极为相似。三是用磨得极细的玉米粉在锅中直接加热,然后陆续少量加入水,使玉米粉充分膨胀熟透,接着再把它团成玉米团,用植物叶子包裹起来,像粽子那样做干粮用。这一套工艺加工程序最多,最费时,也最费事,但从玉米自身的生物属性而言,做这样的加工实际意义并不大。像磨成这样细了的玉米粉直接和水后,无论是蒸,还是烤都可以充分熟透。后来,在调查后期,我们进而还注意到他们用这第三种办法去加工很多我们还不熟悉的植物,天星米、葛根、蕨根等。上述植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的粒度非常小,加工成细粉非常简单,而采用这样的工艺去加工上述三种植物最符合它的生物属性。于是,我们先是推测当地的居民在古代曾经以天星米、葛根或蕨根做主粮,而这种加工办法仅是一个历史的记忆。可是,在调查结束后,我们与湘西地区加工葛根食品工艺做对比后发现,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差异,因为在麻山的加工工艺中,并没有包含将淀粉提纯的技术操作环节。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想到,这第三种加工办法肯定还有早已遗忘了的加工对象。在查阅宋代以前,南方地区特有的植物后,我们猛然发现这第三种加工办法其实很有可能是用来加工桄榔粉的,桄榔木退出食品圈后,才转而用该套工艺去加工其他新启用的其他植物。
桄榔木见诸汉文典籍的记载为时甚早。《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就有如下的记载,“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桄桹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这一记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明确指出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曾经用桄榔木做过主粮。可是,在继续查阅其后的典籍后还发现这种植物虽然被几十种历史典籍同时提到,而且是以较大的篇幅进行记载,但作为食品运用的记载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的递减,到了宋人所作的《桂海虞衡志》和《岭外代答》则仅仅是记载这种植物的外形和它特意的生物属性,对其作用则仅仅提及它是一种很好的观赏植物,大多种植在庙宇、祠堂等地作为配置风景之用。桄榔木遭遇的这一历史轨迹,虽然延续的时间很长,但过程与葛藤在苗疆受到的遭遇却如出一辙。退出食品圈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这种植物制成的食品无法长期保鲜和储备,更难以长途运输,特别是无法与内地的消费习惯相接轨,因而任何一个中央王朝都不可能将这种植物的产品作为税收的对象,朝廷必然需要置换掉这样的作物,完全是出于国家施政的需要,而不是这种植物的产量低或它的食用价值低,更不是它没有生态价值。
有关如何食用桄榔木,汉文典籍的记载虽然缺乏系统,而且十分残缺,但只要细心研读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资料,还是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比如,一株桄榔木能够产出的食物比之于习见的任何一种农作物批量都要大,一株树龄达到10年的桄榔木只要没有开花儿,从它那庞大的树干中,能够提取的淀粉就高达数百斤,因而收割一株桄榔木,一个村寨的乡民几乎等于过一次隆重的节日。砍的时候要集中全寨子人力,而砍伐下来后大家又可以共同分享十来天。魏晋南北朝时代直到唐代的历史典籍中,无论是《异物志》、《南方草木状》、《临海异物志》、《广志》等都都曾提到这种过节式的收割情景。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想到,《后汉书》说这些地区最为贫困的真实含义。文中所提到的“最贫”并不等于经常饿肚子,而是说这些新设置的郡县无法按照中原的习惯征收赋税,因而财政收入小得可怜。以这些资料提供的信息为依据,再反观桄榔木面的生物属性,我们总会感到文本史料的信息虽然不多,但是十分管用。
桄榔木树心的淀粉,由于在分子结构上支链很多,加热遇水后很容易容融胀,因而在加工时只需要将取出的桄榔粉加少许的水就很容易做成饼饵,但是如果要长期保持,那么就必须得提纯为淀粉,并充分脱水才行。可是,这样的加工未免太费事,对燃料的消耗太大,而这正是这种粮食作物无法成为庞大帝国税收来源的原因所在。然而,要支撑一个微型化的政权却又十分合适。明白了这一点,就很容易解读为何中央王朝在岭南的广大地区不会遇到强大政权抵抗的历史原因所在。
弄清了桄榔木充当粮食作物的利弊得失后,长期以来历史上很多未解之谜就可以迎刃而解了。两汉时代,一度在桄榔木的主产区设置过边郡,但三国以后,中央政权就已经退出了这一地区,隋唐虽然实现了全国的再次统一,但对桄榔木的主产区的经营也远远不及两汉时代。最后,南召政权成了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者。只要对比相关正史的记载,都会发现一个似乎存在,但却不十分分明的天然界限。西南夷的北部地区很容易形成势力强大的政权,而且可以和中原王朝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但西南夷的南部地区,中央王朝却难以建立直接的联系。同时,西南夷的南部和北部地区也经常发生冲突。如果将这样的差异在今天的实测地图上加以复原,那么就可以发现其间大致存在着一个模糊的界限,界限以北是农牧兼营的氐羌系统民族的生息地,而界限以南则是以桄榔木为主食的百越系统各民族的生息地。从生态背景看,前者是温带森林和高山疏树草地生态系统,而后者则是亚热带常绿阔叶丛林生态系统。两者政治地位的逆转,则与水稻在这一地区的普遍种植相关联。自从《新唐书》和《旧唐书》明确记载在南方的百越民族中已经推广“秧稻”种植起,相关时期的汉文典籍对桄榔木食用价值的记载就淡出了历史典籍,而作为观赏植物的记载却成了有关桄榔木记载的主流,足证从桄榔木到水稻的历史转换,与百越民族在中央王朝中地位的提升恰好合拍。一种植物的地位的转换,总是牵连着相关民族政治地位的变革,也牵连着整个文化结构与内涵的重构。只要遵循这一线索,看似十分残缺的历史文本,要恢复其真实的历史过程,也不一定是一件难事。
五、汉族政治中心东移南下背后的农作物更替
弄清了主种农作物演替对少数民族历史进程的影响后,反观汉族自己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发现相似的历史演进轨迹。历史文本的正面记载,虽然没有正面提及汉族历史上主种作物的演替,但只要注意到泰勒的“文化残留”理论,我们仍然可以从汉文典籍中提取足够的信息,能够支持汉族主种农作物演替的探讨,只不过需要研究者多一份关注、多一点耐心罢了。
二十四节气的编排、七十二候的配置,这是今天每一个汉族居民都不会陌生的汉文化标志,但却很少有人细究这些节气和名称背后的农作物,及其相关的汉文化特质。举例说,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和芒种,如果不是从汉字的字源做探讨就很容易误解,误以为小满是雨水多了,但是请不要忘记小满之前还有谷雨和雨水两个节气名称。作为一套节气用语,在逻辑上不应当有这样的分歧,因为这种用词习惯的分歧会直接导致理解上的逻辑混乱。再说芒种这个节气的用字是谷芒的“芒”,而不是忙碌的“忙”,这同样不可思议。明明到了春种大忙季节,哪儿可以看到谷芒呢?总之,这二十四个节气的名称和今天以水稻为主种作物的现实很难合拍。七十二候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我国南方的稻米主种区在冬天都不会出现冰冻封河的景象,但七十二候中却有“鱼负冰”的物候名称。这同样不得其解,但是如果与今天的生态学和物候学为依据,去逐一审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名称内涵,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目前通行的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是以黄河下游所处的温带湿地和森林生态系统为描述对象,而制定出来的。查阅了《晋书·天文志》后还可以提供这样的信息,二十四节气首见于蔡邕的著述,蔡邕的原书虽然失传,但是可以确定今本二十四节气的定型是在三国时期,而七十二候的定型则更晚。与此同时,若进而考虑到黄河下游最适合种植的作物是冬小麦,那么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和芒种,其真实的含义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小满的实质不是指“江河水满”,而是指“冬小麦开始壮浆”,而芒种则是指冬小麦进入了蜡熟期,可以开始收割了。如果进一步的核对史料,从汉代到唐代的汉文典籍总会留下很多若隐若现的信息,都直接或间接的与冬小麦耕作有关。把这样的信息叠加起来,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水稻支配中国历史进程之前,冬小麦也曾主导过中国数百年之久的历史进程。
可是,从冬小麦出发,仍然无法理解先秦典籍留下来的史料。一个最简单的实例正在于作为国家象征的社稷坛,绝对不会有人将它叫做“社麦坛”或“社稻坛”,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追问这个“稷”是什么东西,居然会成为国家的象征。答案其实也不难找到。只要我们细细品味《诗经》中有关农耕的记载,答案就在其中。在《诗经》中多次提到在原上进行耕作。众所周知,在今天的人看来,黄土高原台面荒凉而贫瘠,咱们的祖先为什么要在这样的地方去种植粮食,但如果考虑到稷这种粮食作物的生物属性后,就不难理解相关的史料了。其原因在于,稷、粟、黍这一组农作物的原产地正是在我国内陆的干旱地带,其原生种正好来源禾本科的牧草。这类植物不怕旱,而怕水涝,以至于到了南北朝时期,黄河下游的居民要再种植这种作物时,就得起陇,将种子播种在陇上,为的是怕土壤过分潮湿会窒息这些植物的根系。《齐民要术》“区种法”项内,可以对其细节提供了详实的记载。如果将先秦和两汉的典籍中,涉及到农事活动的零星资料汇集起来,我们还可以进而发现汉族历史上客观存在过以稷、粟为主食的历史时期。出于称谓的简洁,我们不妨将这个汉族历史上的远古时代,称为“主稷时代”;将两汉以后直到宋代以前的时代,称之为“主麦时代”;而将宋代以后到今天的时期,称之为“主稻时代”。值得一提的是,汉族历史也像少数民族历史那样,主种作物的更替也会导致生活方式的更替,甚至是地方政权的更替,就连过的节日也会发生巨变。“寒食节”和“人日”在唐人的诗歌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但今天已经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圈,而“端午节”和“清明节”在今天的汉族生活中却变得比唐代更为重要了。原因其实很简单,主种作物一旦改变,生产组织、生活习惯、技术要领都得做出相应的调整,最终会影响到观念的彻底改变。
众所周知,唐代以前的汉族居民在居住环境中,非常忌讳“卑湿”,居民的住房都要修筑在台阶上,务使住房高出地表。江河沿岸湿地生态系统总是被朝廷封禁起来,仅作为猎场使用。显然,这样的地区是没有人居住的。可是,到了宋代以后,居民住房开始临河而建,西湖美景,美就美在与水、河、柳相伴。这就说明宋代以后,出于开垦稻田的需要,居民为了便于耕作,临水而居势在必然。这样的选择与此前汉族所认为的,居处环境的优劣观发生了一个大大的逆转。原先的所弃之地,今天却成了争夺的宝地。
以水稻为主种作物,虽然发端于长江下游,但水稻一旦成为国家的依赖,立国的根基,那么它就必然具有很大的张力。在汉族的历史上就表现为,继“苏湖熟天下足”之后,紧接着发生的是“湖广熟而天下足”的新局面,而接下去,珠江下游的“基塘农耕”又成了引领中国农耕的稻田种植模式。这三地在稻田耕作的技术又互有区别,同样会引发相关地区社会结构的新一轮调整,因而立足于水稻的生物属性,很多看似不可思议的历史信息最终都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解答。
六、结语
对若干种曾经主宰过历史进程的植物做一番回顾,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需要解决的关键难题在于,为何如此众多的植物到了今天只剩下有限的几种在左右着人类的生存。这是人类自己犯傻,还是另有原因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仍然无法把握人类历史的进程。要系统的回答这一难题,当然远非易事,但提供一个不成熟的猜测却是我们希望能够尽力做到的事情。我们认为,民族文化的建构本身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确保食物来源的富足,同时又要减低食物供给的风险,那么最好是食用尽可能多的植物物种。远古时代的人类就是这样过日子的,但这样的选择也有它致命的弊端,食用的植物物种越多,需要配套的技术和社会制度保障就会越复杂,人与人之间组成的社会规模就会越来越小,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离心倾向就会很大。食物虽然有了保障,但是要对付其他强势群体,最佳的活路莫过于逃跑。贵州苗族在反抗清廷时,就曾经立下一个格言,“我们打不赢朝廷,但是我们可以躲得赢朝廷”。后来的历史却证明,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躲过朝廷。由此看来,单一的食物充沛还不能够确保一种文化能够长治久安,它还必须考虑与其他民族周旋,特别是与那些强悍的、高度组织化的民族进行周旋。于是,对食用植物的选择还得适可而止。除了考虑吃饱肚子外,还需要进而考虑形成的食品容不容易存储,容不容易运输,容不易容易加工,保鲜是否容易等。然而,只要做出这样的选择,文化的演变又得走上另一条道路,主要依赖的植物就应当物种越少越好,因为这样选择后,有利于社会组织的划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也得到了极大提高。总而言之,可以支持起一个个庞大的政权。然而,其弊端也是十分明显。这显然是一种反生态的选择。植物物种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生物属性必然有其适应的范围,不可能所在皆适。大规模的种植和使用某几种有限的植物,最终都会导致在不适宜的地方强制种植这些有限的植物物种。这既违反了相关植物的生物属性,又与生物多样性的维护背道而驰,还与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相左。最终会使得人们的生活方式越来越单调,无意中种下了不胜枚举的生态隐患,自然与生态灾害的成灾和频率都会不断的攀升。这确实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也是支配人类历史进程的不解死结。不管是哪一个民族,都得在两者之间走钢丝,而这一走钢丝的摇摆过程则构成了挥之不去、隐而不显的历史轨迹。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在这两者之间摇摆,而且派生了一系列令人啼笑皆非的社会事实。当年古代百越各民族天天都能够吃到的桄榔木,今天却成了政府需要出钱去保护的珍惜濒危物种。当年,支撑了汉族先民走向中央集权的粟和稷,在我国现行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被贬称为“小杂粮”。农业经济学家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作为“小杂粮”的稷,当年却是皇权的象征,江山的标志。诸如此类的现象,不仅是历史研究的素材,更是今天的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必须认真思考的大事。历史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可以发挥此前想都不敢想的重大作用。
注释:
①本文是笔者于2011年11月在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讲座系列第68讲上的主讲内容,由李银艳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在刊发前,笔者已经做了认真审读,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