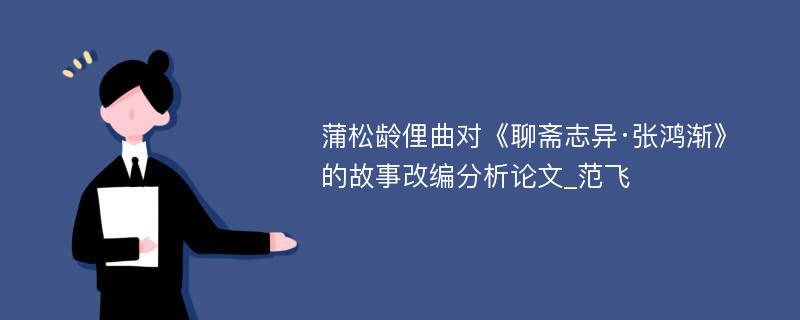
摘要:蒲松龄晚年时期创作了大量的通俗俚曲,其中有七篇俚曲是由相应的《聊斋志异》篇目再次创作而来。蒲松龄这些俚曲的创作,不仅使小说的故事情节得以丰富和完善,而且在艺术手法和主题思想上也发生了变化。根据《聊斋志异·张鸿渐》改编而来的俚曲《富贵神仙》和《磨难曲》正是这些俚曲中的代表作。本文则是从艺术构思和思想变化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两部俚曲对小说的故事改编。
关键词:张鸿渐;蒲松龄俚曲;富贵神仙;磨难曲
蒲松龄毕其一生之力创作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聊斋志异》,除此之外,他又巧妙地运用山东淄川方言创作了大量的聊斋俚曲,不仅展现出其非凡的语言才能,而且也成为蒲松龄文学作品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蒲松龄的众多俚曲中,有七种是根据其小说《聊斋志异》的故事改编而来。其中又以小说《张鸿渐》为故事蓝本改编而来的《富贵神仙》和《磨难曲》成就最为突出。
小说写的是张鸿渐因为代笔创词控告卢龙县令赵某贪暴而被迫离家出逃,路上偶遇狐仙舜华与其结为夫妻。后因离家三年,思家心切,在舜华的帮助下回到妻子身边,不料被恶少李甲发现,意欲告官,张鸿渐“忿火中烧”,“把刀直出,剁甲中颅”,因不想连累妻子,遂投案自首。在押往京师的路上,再次得到了狐仙舜华的帮助,在太原设馆教书十年。后来,张鸿渐在许家认出了刚刚考取孝廉的儿子,父子二人抱头痛哭,最终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小说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不仅揭露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还穿插了张鸿渐与狐女舜华浪漫的爱情故事,是一篇“聊斋味”非常浓厚的作品。
作为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蒲松龄对科举制度一直抱之以希望,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即使这样,也并没有使蒲松龄对科举考试失去信心。在那个时代,唯有参加科举考试,金榜题名,才能改变读书人穷苦的生活状态,才能光宗耀祖,实现“快活浑如在天边外,荣华不似居人世间”的富贵美梦。蒲松龄俨然意识到科举考试才是改变穷苦书生命运的最有效途径,因此,他的这种思想在小说《张鸿渐》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小说中张鸿渐逃亡在外,流离失所,受尽磨难,直到儿子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故事才发生了转机,以家人团聚的圆满结局收尾。从《聊斋志异》的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情节,这与蒲松龄对科举考试的执迷密不可分。
其次,纵观整篇小说,张鸿渐与狐妖舜华的这段爱情故事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赞扬了狐妖善良聪慧的美好品质。但作者对现实社会黑暗面的揭露并不够深刻,小说对知县赵某贪暴、范生杖毙的描写只是一笔带过而已,并没有进行细致入微地刻画。虽然后面还写了恶少李甲的蛮横霸道,表现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但仍然缺乏广阔的社会背景,其描写力度远远不如后来的两部俚曲,全篇唯美的人狐之恋反而为人所津津乐道。
面对官场的腐败、官吏的残暴、百姓的凄惨,身处在黑暗社会中的蒲松龄却异常的清醒,基于这样的社会现实,他再次执笔,对小说《张鸿渐》进行了二次创作,将其改编为俚曲《富贵神仙》,以期达到“破村农之谜,醒市媪之梦”[1]的目的,代民立言,希望可以通过俚曲的传播改变人心,移风易俗。
俚曲《富贵神仙》较之于小说,故事情节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只是弱化了张鸿渐和狐仙舜华的情感纠葛,而大大加强了作品对现实主义的描写和对黑暗社会的讽刺与揭露。小说中对卢龙县令的刻画并没有着过多的笔墨,只用了“被杖毙”三个字来描写县令的贪暴不仁,《富贵神仙》则写的是卢龙知县“老马”,“异常的残酷”,“作弄的财尽民穷”,老百姓“叫苦连天”。俚曲中写范秀才因交了七分钱粮而请求宽限时,马知县大怒,认为这是在“梗”他的“行令”,便“丢下六支签”,将范秀才活生生打死。相比于小说,俚曲交代了范秀才命丧黄泉的起因,同时也将知县丑恶残暴的一面进行更加细致的刻画。
在结构上,小说《张鸿渐》以单线故事情节展开,全篇围绕主人公张鸿渐的个人遭遇进行描写,而对其他方面涉及很少。《富贵神仙》则从两条线索写张鸿渐的苦难,一条是他自己的磨难历程。张鸿渐因代笔创词而被迫走上背井离乡的逃亡之路,如果从矛盾的角度来看,矛盾的一方张鸿渐贯穿整个故事始终,而作为矛盾的另一方则在不断地变化中。矛盾的对立面不仅有卢龙知县,还有在逃亡过程中不幸患上重病,唯一的代步工具驴子又被人牵走,一路上忍饥挨饿,再加上怒杀李鸭子等等,这一系列磨难的承受者,都由张鸿渐一人来完成。最后张鸿渐参加科举,和儿子相认,一家人得以团聚,享受后半世的荣华富贵,这也印证了“楔子”中“这人原是一个才子,他下半世的荣华可尽观”的预言。
另一条线索是妻子方氏在家的悲惨遭遇,作为夫妻双方,妻子所承受的苦难,也加重了张鸿渐的心灵负担,所以这也是张鸿渐磨难的另外一个来源。张鸿渐逃亡在外,妻子被知县收押在监,与儿子保儿在监狱忍受了四年痛苦的光阴。张鸿渐杀死李鸭子之后,方氏又要独自一人忍受李母的侮辱谩骂。作为一个女子在操持家务、维持生计之外,还要督促儿子的学业,使其成才。这背后都由一个女子来承担,其艰难痛苦可想而知。
最后父子相认,家人团聚,两条线索合归一处,皆大欢喜。俚曲的结尾又增加了八仙为张鸿渐庆寿的情节,整个故事就在这样的欢乐氛围中以大团圆式的结局落下帷幕。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但是,如果从对现实批判的角度讲,全篇只是向读者描写了张鸿渐个人的穷通遭遇,表达了人生须是由磨难而富贵的道理,而缺少了对当时广阔的社会环境背景的展示,因此,对现实社会批判的力度与后来的《磨难曲》相比远远不够。
康熙四十二年(1703)前后蒲松龄的家乡山东淄川发生了罕见的灾荒。当时的贵州道监察御史刘明偀反映:“比年以来,烽烟不断,赤地千里,由畿南以及山东,比比皆然。”[2]蒲松龄作为这场灾荒的亲历者,目睹了在天灾下封建官吏的惨无人道和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状况,使他对社会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痛心疾首。因此,他再次将《富贵神仙》进行了艺术加工,改编成共有三十六回的《磨难曲》,在故事情节上较《富贵神仙》又有了进一步的完善,而且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艺术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被看做是蒲松龄俚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磨难曲》较小说和《富贵神仙》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
首先,作品向读者展示的不再是张鸿渐个人的“磨难”,而是将这种“磨难”放在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环境背景下来描写,从而揭示了磨难的普遍性,且对造成磨难的原因也有了更加深刻地揭露。《磨难曲》的开场,作者就极尽笔力用了整整两回向读者描绘了一幅天灾人祸下老百姓衣食无告、颠沛流离的社会众生图。卢龙县遭遇大旱,麦子颗粒无收,新种的谷子又被蝗虫吃个精光,老百姓不得已背井离乡,踏上出逃的道路。对于如此严重的灾荒,“下头知县不肯报,上头大官不肯言”,以至于老百姓发出“怎么就大小官吏,都没有摊着一个爱民的”的感叹。就连皇上发的“漕米百万石”,最后也都“赈济”给了衙役县官,即使这样,这些官吏仍然欲壑难填,为了一己之私全然不顾百姓的生命安危,甚至视生命如草芥,将欠粮请求宽限的范秀才活活打死,又不知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惨死在县令马某的杖下。
张鸿渐带领秀才们告到北直总督,总督受贿,反而诬陷秀才们把持官府,问罪充军,发配辽阳,中途幸而被三山大王仁义所救。后来张鸿渐父子金榜题名,步入仕途。但俚曲至此并未结束,作者还有意写了当时朝廷大臣的昏庸。面对北兵犯境,掌管重兵的杨藩却按兵不动,坐视不管等等。刻画了一幅上至朝廷权奸,下至县官、衙役,无不贪赃枉法、上下其手、鱼肉百姓的官场丑陋图,将官场的黑暗与残酷又进行了一次辛辣的暴露和抨击,并且揭示了劳苦大众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根本原因,从而更加强化了作品的政治批判意义。
其次,在艺术构思上,《磨难曲》在《富贵神仙》双条线索叙事的基础上,演变为多条线索共同叙事,尤其是除了保留《富贵神仙》张鸿渐和妻子方氏这两条线索之外,还增加了三山大王仁义这条线索,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磨难曲》也比前两部作品有了很大的提高。
作品中仁义是位义军领袖。他有着与梁山好汉一样的经历,落草山林,占山为王,他痛恨贪官污吏,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着“只爱雄兵百万,遍天下寻杀贪官,开刀先诛杀了严世藩。一匹马扫清那金銮殿,奸臣杀尽,解甲归山”的雄心壮志,显然和《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如出一辙。
他是一方百姓的“保护神”。当他看到众秀才被押往辽阳充军时,便杀了解子,救出秀才,并给他们银子,开了酒店,丰衣足食。他嫉恶如仇,曾发出“只杀赃吏与贪官”的誓言,当北兵对老百姓进行猖狂的杀戮抢掠时,他带兵杀到了兵营。北兵头领听说仁义杀到,弃甲曳兵而走,狼狈不堪。正是在仁义的保护下,附近的百姓才得以安全的生活。仁义虽然是个山贼,却被当地的老百姓奉为救苦救难的“活菩萨”,而本应该为百姓服务的朝廷大臣却和贼兵并无二致,因此,对仁义形象的塑造,在这部作品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作者结尾为仁义安排了一个圆满的结局。张鸿渐奉朝廷之命向仁义招安,三山大王最终归顺朝廷,又因抗敌有功被御封为“忠义侯”,成为抵御北兵入侵的民族英雄。这样的结局安排避免了仁义像梁山好汉们一样的下场,同时也反映出此时蒲松龄对农民起义态度上的变化。蒲松龄曾在《聊斋志异》的一些作品中,丑化农民起义军,认为是“左道无济,止取灭亡”,将李自成义军称之为“闯贼”等等,都表达了蒲松龄对农民起义军持反对的态度。而在《磨难曲》中却可以欣喜地看到他对三山大王的赞赏和颂扬,由对农民起义军的反对到支持,甚至出现在作品中成为人民群众救苦救难的民族英雄,这不得不说明晚年时期蒲松龄的思想发生的巨大变化。在那个世态炎凉、暗无天日的时代里,当蒲松龄认识到参加科举之路行不通时,所以只能将自己的希望和理想寄托在像仁义这样的人民英雄身上。
何满子在《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中这样评价俚曲:“小说和戏曲相比,正像一具二度刻或浅浮雕变成了立体的、饱含着动势的雕塑,而它又被安设在一个一个烘托得宜的背景之前。”[3]由小说《张鸿渐》改编而来的两种蒲松龄俚曲正是这样,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生动,而且每一次的改编又会注入蒲松龄对现实社会新的思考和关照,也让读者对当时社会官场的丑陋、政治的黑暗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朱一玄.聊斋志异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283.
[2]佚名.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28.
[3]何满子.蒲松龄与聊斋志异.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42.
作者简介:范飞(1993年—),男,黑龙江大庆人,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作者:范飞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3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5/22
标签:俚曲论文; 聊斋志异论文; 富贵论文; 鸿渐论文; 磨难论文; 蒲松龄论文; 仁义论文; 《知识-力量》3月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