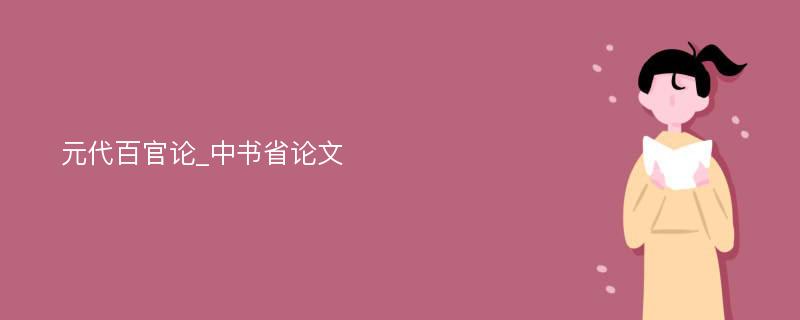
元代的百官集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百官论文,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蒙古国时期(公元1206—1259年),由蒙古贵族,包括“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注:《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朝会》,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参加的忽里台(又译“大朝会”)是议决国家大事的最高形式。推选大汗、出征外国、发布法令、向诸王和功臣分封领地与臣民等事务都必须在忽里台上议决。如1229年的忽里台上窝阔台被立为大汗,蒙哥在1257年的忽里台上宣布伐宋。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城召开忽里台,宣布即大汗位,开始按中原王朝体制的框架构建政府机构。同年七月,立燕京行中书省,设丞相、平章、参政主领省事;建左右司为幕府,司置郎官参佐机务和掌管左右两房诸掾属及所司文牍事宜。此外又置架阁库官、奏事官等各色省属掾吏。这时候的燕京行中书省实际上承担了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此后在燕京行中书省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机构,充实和调整人选,建立了以中书省和左右两部为主要机构的全新的行政中枢。新的行政中枢又一度再分为中书省和行中书省两部分,但两省于中统四年以燕京为大都之前已合并为中书省(注:姚大力:《从“大断事官”制到中书省——论元初中枢机构的体制演变》, 《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忽必烈即位后,大蒙古国时期的忽里台制度予以保留,且为后代皇帝承继,但就其作用而言,不再是中央决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中统和至元初年,燕京行中书省和中书省的省内议事,即“堂议”制度是当时朝廷定策的主要模式。据王恽《中堂事记》,参加堂议的主要是各位相臣,忽必烈郊祀之前常常会关照他们认真议事,“凡内外之务,比还,悉裁定以闻”。议事时诸相“圆坐都省”,议定结果向皇帝奏报,皇帝批准实施,向全国颁诏执行。议事范围则有选官、民政、钞法、军事、立制、省规等军国大政。
随着六部、枢密院、御史台、翰林兼国史院、集贤院等机构的陆续设置和地方行政体制的逐步完备,元朝政治决策体系中议事方式相应多样化。大致说来,元代有这样几种主要议事方式:
第一、忽里台。元朝新皇帝即位,重大事务的决定,依然举行蒙古宗王贵族和朝廷大臣一同参加的忽里台大会;但其功能和意义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大蒙古国时期的最高决策层次地位丧失而蜕化为形式上的军国大事议决会议。第二、省议,即中书省宰相集体讨论时政。元代中书省宰相每日都要共同议事,制定各种政策措施,报请皇帝批准。第三、院议,枢密院官员商议某些军务的决策会议。第四、台议,御史台官员议事方式。第五、六部和其他机构内部议事,所商决的内容多是各机构职权范围内的事务。第六、地方官员聚会议事。元代地方官员每日需在衙门相聚,讨论有关财赋、刑狱、治安、农桑等方面问题。第七、百官集议,指遇有重大军国政务,召集朝廷大臣共同讨论商议,最后由皇帝裁断的决策制度。第八、廷议。元代不存在皇帝定期上朝听政的朝会制度,但天子仍有不定期地接见百官讨论政事之举,文献中多称之为“廷议”或“朝议”(注:杨国藩在《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专列一节介绍元代的十种议事形式,见该书第131—149页;但分类不够明确,对它们的作用分析也有问题,所举例证多引自《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更是不妥,故本文不从其说。)。
显然,上述几种议事方式在元代决策体系中所起的作用不尽相同。如前所述,忽里台只是形式上的军国大事议决会议,重要决策往往在皇帝与各中央官员内定后拿到忽里台上宣布,与会者即使有反对意见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平等讨论,只能表示服从(注:萧功秦:《论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辑,1983年; 又见白钢主编,陈高华、 史卫民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 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第42—43页。)。省议所议事项,偏于一般行政,议定的结果由宰相入宫向皇帝奏禀,皇帝据此下达旨意。廷议由于是天子在场主持,议定的结果具有决定性,除非皇帝有所变更,其他人不得更改;不过这种议事方式没有制度化,因而作用必定有限。只有百官集议才一度成为中央决策系统中的最高层次。
百官集议是指遇有重大和复杂的军国政务,君主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指示中央政府相关机构的主要官员进行讨论(少数情况下可由宰相召集),议论所提方案和群臣意见上奏君主,供后者作决策时的参考。大多数问题经过一次这样的会议就可以决定下来,而有些问题则需要反复辩论,多次会议,需较长时间才能决定方案。中国古代的集议制度形成于秦汉时期,以后历代多有沿袭。元代时人关于百官集议制的论述,我们只见到王恽的一篇《论百官集议事状》,收入他的《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六。张帆在《元代宰相制度研究》一书中认为:“王恽虽然引经据典地追溯到汉制,但他关于百官集议的一套设想,实际上是直接源于金制的。”笔者以为王恽文中“汉故事”基本符合史实,就集议这一方式而言,金制实际上是汉制的一脉沿袭。张帆继续说:“根据史料记载来看,元代很早就开始推行百官集议制度,或许与王恽的上言不无关系。”(注: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第117页。)按, 王恽此文作于他任监察御史之后(王恽至元五年受职),但元代集议制度至晚在中统四年枢密院设立之后就有记载。如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十月,“太庙成,丞相安童、伯颜言‘祖宗世数、尊谥庙号、增祀四世、各庙神主、配享功臣、法服祭器等事,皆宜定议。’命平章政事赵璧等集群臣议,定为八室”(注:《元史》卷六《世祖纪》三,中华书局1976年点校本(下引此书不再注版本)。)。当然这一时期(中统和至元年初)集议制度尚不健全。
事实上,元代由于不存在朝会制度,忽里台对一般国务也不再具有决策功能;特别是元代前半叶,没有一个机构具有独揽一切政务的大权,中统年间作为决策主要模式的堂议制度就随着中央各主要机构的相继设置自然而然地发展为百官集议制。百官集议制的推行似乎与某个人的上言关系不大;与其说采用集议制是忽必烈行汉法的一项内容,倒不如说之前的堂议制是他所接受的一项中原制度模式。我们可注意到,元代中后期,由于中书省权力的膨胀,百官集议制流于形式,在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也相应下降。
二
元代集议的议事过程,陈高华、史卫民认为:“凡要决断国家之事,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先各自召集本部官员,商量有关事宜,提出方案和措施,然后三大机构的主要官员,聚在一起,讨论方案的可行性,把意见上报给皇帝。”(注:《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第53—54页。)需要用这种方式议事的情况其实比较少。院、台有自行上奏军务和台内事务的权力,他们所提的方案和措施若一时定不下来,一般也需要由皇帝下诏,令与中书省官员共议。倒是一些次一级机构,像六部、宗正府等,在遇到棘手问题时可上呈中书省,由宰相召集官员集议处理。如延祐六年(公元1319年)正月,“帝御嘉禧殿,谓札鲁忽赤买闾曰:‘札鲁忽赤人命所系,其详阅狱辞。事无大小,必谋诸同僚。疑不能决者,与省、台臣集议以闻。’”(注:《元史》卷二六《仁宗纪》三。)
同历代百官集议制类似,元代的这种议事方式一般也包括下诏、议事和上奏三个过程。议事的主题和基调多由皇帝决定,其信息来源主要有中央高级官员的奏事、臣民的上书陈言、近侍信臣的个人意见以及皇帝自己的意愿等。需要指出的是,元代有不少次集议,特别是世祖朝,皇帝在下诏举行之前就有了自己的主张。这种情况下召开的集议,与其说是寻求决策的参考意见,不如说是为了寻求对自己政策的支持和参与。至元五年,“宰执传旨,命公(张德辉)议御史台条例。公奏曰:‘御史,执法官。今法令未明,何据而行?此事行之不易,又难中止,陛下宜慎思之。’后数日,复召公曰:‘朕虑之已熟,卿当力行。’对曰:‘若必欲行之,乞立宗正府,……’上良久曰:‘可徐行之。’”(注:《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之四《宣慰张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仔细玩味这段话,笔者以为忽必烈在令集议之前就已“熟虑”了。再如,至元中期,忽必烈“诏廷臣杂议”立门下省,在诏议之前他就有“锐欲行之”的意旨(注:事见姚燧《牧庵集》卷一○五《董文忠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皇帝下令集议之前的倾向性初衷有时会因群臣的意见而加以修改甚至全盘放弃,但有时也会不顾集议结果而执意行之。忽必烈多次诏令集议伐日事宜,反对者甚众,但他并不改变自己的原先决定。
元代百官集议大多由皇帝下诏举行,不过有时候宰相也可召集一些官员讨论政务,商议的结果经宰相上报皇帝,由皇帝作最终定夺。元朝大部分奏章、上疏须先经过中书省,中书省有权决定是否继续上呈,即便是实封言事,也时有被中书省扣压情况发生。这自然给宰相弄权提供了方便,但若所有的公文奏札都交给皇帝处理,不用说不恤政务或对理政兴趣不大的皇帝,就是勤政如忽必烈者也对此颇为厌倦发烦而乐于将权力下放,先由中书省省议或召集相关官员议论“孰是孰否,可行者行之”(注:《元史》卷一七三《崔彧传》。)但是宰相决定的集议,议事范围只限于一些“便民利物”之事,和省议对象差不多,而不能和皇帝诏令举行的集议内容相提并论。即便是权臣专决时期,依权臣意旨举行的讨论有关国家前途的重大政务的集议,事先一般也需经过皇帝首肯。元后期脱脱任中书右丞相时主持的四次重要集议,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的议开金口河、十年的议变钞、次年的议治河、十二年的议募江南人耕种京畿地,都是经过皇帝同意而举行的(注:事见《元史》卷四二《顺帝纪五》、卷六六《河渠志三》、卷九七《食货志五》、卷一三八《脱脱传》、卷一八五《吕思诚传》、卷一八七《贾鲁传》等。)。只有在皇位空缺或内乱等特殊情形下,宰相才可自行召集集议,商讨军国重事,包括皇位继承等大问题。成宗、泰定帝去世后,新皇帝未登基之前都有过这样的集议。
百官集议一般由中书省宰相主持,议事地点多在中书省都堂,史籍中有时也记作“中书”、“中书堂”。文献中有时也有“集议廷中”的说法,依常理论之,由宰相主持的会议在朝堂中进行的可能性不大。史料作者或者记载有误,错以为“廷臣集议”就在廷中进行;或者把集议和廷议弄混。《松雪斋文集》附录杨载《赵孟頫行状》中记载:“诏集百官于刑部议法。公(赵孟頫)适立左右,上命公往共议。”据此则集议也曾在都堂以外举行,不过类似记载极为少见。另外,世祖和武宗两朝,曾三度设立尚书省,最初目的都是为了理财,但一经设立就尽揽中书行政,后者反而形如虚设。世祖朝有尚书省宰相参加和主持百官集议的记载,如至元八年六月敕枢密院“干钱粮者”与尚书省共议(注:事见《元史》卷七《世祖纪》四。)。二十四年十一月集议弭盗,桑哥(尚书平章)、玉速帖木儿(御史大夫)、叶李(尚书左丞)皆有陈辞,中书右丞相安童则很可能没有参加,这次集议估计为桑哥所主持(注:事见《元史》卷一四《世祖纪》十一。)。到第三次立尚书省时,集议少有记载。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十月,御史台臣奏罢常平仓、禁行铜钱、弛拘民间铜器、续酒禁等事之后,“有旨:‘其与省臣议之。’”(注:《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此处省臣无疑是指尚书省官员。尚书省是否遵旨集议,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即便举行,仅仅“俯焉食禄”的中书省宰相也是无权主持的。
同历代百官集议一样,元代百官集议的出席人员也因具体情况不同而有多有少,范围也有大有小。前面提到的王恽《论百官集议事状》一文中,建议“五品以上官集议阙下”;事实上一些品秩不高甚至不入官品者有时也可入议,他们的意见有时还特别被看重。如至治年间,宋文瓒任右司都事,这是一个七品的宰相僚属官职。“湖广行省平章忽刺歹咨言广西岑世雄及黄圣许之子谋叛,请调兵四万讨之。时中书参政马来,忽刺歹之侄也,与参议王某同主允其请,集议于中书政事堂。右丞相拜住公曰:‘是事属右司,宋都事首署案牍,其先言。’”宋文瓒陈述反对意见,“邀功生事,非国家之福也”。丞相纳其言,后“广西果不反”(注:刘基:《诚意伯文集》卷六《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四部丛刊初编》本。)。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决策方式,集议参加官员的类型相对固定。据张帆考订,经常性的出席人员有宰相和宰相以外的中书省官员(包括宰相的僚属和六部长贰)、枢密院官员、御史台官员、翰林国史院儒臣和集贤院儒臣等五大机构主要人员(注:《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118—121页。)。另外,在集议某些具体问题时,五部门以外的中央有关机构官员和一些老臣、儒者也得以出席。如讨论祭祀、舆服等属太常礼仪院职掌范围内事务时,太常官得参加集议。不过,只有分掌行政、军政和监察的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官员才是百官集议上的主角,他们的意见直接关系到集议的结果。两院儒臣在集议上的意见最终能否被采纳完全取决于宰相,一般说来他们在集议上扮演的只是陪客的角色。至于那些老臣儒者在集议中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他们自己本人更是无法保证的。揭傒斯就曾有过牢骚:“使揭傒斯有一得之献,诸公用其言而天下蒙其利,虽死于此无恨;不然,何益之有!”(注: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六《揭傒斯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本。)
元代通过百官集议而后决策的事情很多,不同时期集议的议事范围也有所变化。大致说来,集议所议事务有这样几种类型。第一是军事与征伐事项;第二是钞法、赋役、理财等经济事项,这两类集议均以世祖朝为多。第三是官员人事管理方面和制度机构之置废的事项。人事管理方面的集议,几乎每一年都有,相对而言,至元、大德以后,举行得较少;世祖朝,曾举行过数次有关机构设置和政区区划等问题的集议,世祖以后,制度机构之建立和变更不再成为统治者需认真对待的问题,这方面的集议也就很少见到。第四是典礼方面的事项。终元一朝,每帝在位期间都有讨论祭祀事务的集议;中原王朝群臣集议给帝、后以及其他显贵上尊号、封号之制,成宗之后诸帝也多乐意继承。第五是灾异赈济等急务。元代遇有灾异,常常召集百官泛论急务,有些官员就利用这样的集议场合借题发挥,批评时政(注:例见《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此外,所谓急务还包括一些需立刻处理的具体问题,如致和元年(公元1328年)三月,“集议修海岸”(注:《元史》卷三○《泰定帝纪》二。)。元中后期的集议,大多讨论后面两种类型的事务。总的说来,元代百官集议内容多为征伐、理财、立制、典礼等军国重事和一些较复杂、难以独断的事情,而像造作工役、钱粮出入、一般的人事除拟等日常事务多不在其列。
自中书省建立以后,元代对中央和地方官员的要求也日益严格,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官府常守之制”,当时称为“公规”。比如圆座、署押、掌印、上下行文等都有相应的礼仪规定和一定的程序与格式。百官集议是不定期举行的,参加的人员也不固定,它是否需要遵守或怎样遵守这些公规,史料中很少记载,尚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参加集议的官员如果意见一致,问题好办;但在人多会议场合,为各自利害和责任问题,政见不合以至互相攻讦则更是常事。对后一种情况,元代前期和后期的处理方法大为不同。元代前期集议中的不同政见需上报皇帝,由皇帝召集争论各方在御前就施政方略等陈述己见,辩论是非;皇帝根据他们申述的理由判别对错,决定最后方案。史籍中把这种制度称之为“廷辩”或“廷对”。当然,元代廷辩制度并非仅仅为解决集议时官员意见分歧而定,凡政见不同或官员间彼此弹劾告讦,皇帝都可以通过廷辩加以调解和处理;而允许被指责为有不轨行为的官员在御前廷辩,则同廉希宪的建议不无关系,事见《元史·廉希宪传》。张帆认为史籍中多把皇帝在内廷召集官员讨论政务称之为“廷辩”(注:《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122页。)。但据笔者检索, 史料中称内廷会议为“廷议”者居多,有时也称“朝议”,但称“廷辩”者似乎不多,不知张帆此论何据。
从武宗朝起,廷辩很少见于记载,百官集议的采用频率也明显减少,且所议内容的重要程度不可与前期的“军国重事”相提并论,而多是些关于典礼的议论或对于天灾等急务的泛泛而谈。元代中期,皇帝基本上仍然保持着朝廷的最终决策权。有关这一时期百官集议的史料多为片言只语,我们难以对此作出较为详细的考订。大概这一时期因集议内容多为典礼和弭灾之论,群臣一般也不大有什么异议;不过皇帝仍然可以否决集议结果。《元史·张珪传》记: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六月,车驾在上都,“先是,帝以灾异,诏百官集议”;张珪等与留守大都的院、台、翰林、集贤等机构官员集议后赴上都向皇帝上奏了篇洋洋数千言的集议意见。皇帝的答复是“不从”;张珪再进谏,“帝终不能从”。
元代后期,权臣迭出。燕铁木儿“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注:《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伯颜专权,“省、台、院官皆出其门下”(注:《元史》卷一三八《伯颜传》。)。脱脱就任中书省右丞相之前,极少集议记载。脱脱任相后,百官集议形式上恢复了世祖时的定制,主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而又复杂的政务;但与前期不同的是,丞相可左右集议的结果并将此上奏皇帝。从前文提及的脱脱所主持的四次集议中,可以看出,参加集议的官员尽管会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议事的结果全由丞相一人作主,然后再将这种带有权相主观意志的所谓议事结果上奏皇帝,政见不同者根本没有御前廷辩的权力和机会。这样的集议场合,百官只有附和其议才能坐稳自己的位置,否则就很可能受到排挤和贬黜。又《元史·张翥传》记载,张翥以翰林侍读学士兼国子祭酒,“尝奉旨诣中书,集议时政。众论蜂起,翥独默然。丞相搠思监曰:‘张先生平日好论事,今一语不出何耶?’翥对曰:‘诸人之议,皆是也。但事势有缓急,施行有先后,在丞相所决耳。’搠思监善之。明日,除集贤学士”。这个事例能说明同样的问题。
三
如果我们能对元代的百官集议作一些个案分析,无疑会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诸如投下利益、省台冲突、官僚机构间缺乏相互制衡、上层内部倾轧、中央与地方权力矛盾、汉人之地位变化以及自然灾害等影响元代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有关集议的原始史料多语焉不详且过于分散,可资利用的前人研究成果也不是很多,这一工作目前看来相当困难。不过,从前面的叙述中,可明显地看到,元代百官集议作用的大小和中书省地位以及皇权强弱的变化有关,下面对这两方面再作些补充论述。
世祖朝设立了理政、统军、监察三大机构,但它们各有所掌,中书省当时仅仅只是一个以理财为主的机关。没有一个机构能够独自决断征伐、立制等军国大事,同时又没有制度化的朝会或御前会议,由中统年间的堂议发展而来的集议制度就成为中央决策系统中的最高层次。集议的长处在于集合朝廷精英的大部分,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集思广益,从而为政府的最终定夺提供依据。世祖曾经对此深有感触:“大猎而后见善射,集议而后知能言”(注:《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成宗承其祖余荫,两朝政治延续性至为鲜明,乃至人们常以“至元、大德之政”相并称。
到武宗在位时,“稽厥庙谟,无一不与世祖皇帝时异”(注: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上时政书》,[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尽管时人的这一议论有所偏激,但朝廷制诏变更不常,“朝出而夕改,于事甫行而止者随至”(注:张养浩:《归田类稿》卷二《上时政书》,[清]乾隆五十五年周氏刊本。)的事常有发生,中书省正常的行政职能遭到严重破坏。出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也为了补中书省机构的不能正常工作,元廷另立尚书省。世祖时为解决财政困难,也曾设立过尚书省,但当时这一机构尚不敢过分弄权,而武宗时尚书省则借助于管理国家财政收入来抬高自己,侵犯其他机构职权,从而真正做到“总治百司”。至大年间所设尚书省随着仁宗的登基而被铲除,但其职权则为以后的中书省所继承。武宗朝尚书省的短暂设立,是元朝中书省地位抬高的关键一步。此后,中书省凌驾于其他机构之上,包括御史台。
从武宗朝设立尚书省开始,元朝的决策更多依靠尚书、中书的决断,百官集议则很少举行,且多为关于典礼和灾异等急务的泛泛而谈。元代前期,官员上疏奏事所陈内容大多要经省、院、台等官员集议后再实行,而元中期则多直接下中书省处理。文宗朝起,中书省又开始为威胁皇权的权臣控制,国家政令实多出自这些“独秉国钧”者,连流于形式的集议都很少见有记载。脱脱拜相后集议多少恢复了一些往日的作用,但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大臣专决的烙印。至正十四年,脱脱被解除兵权,此后,元朝各级机构瘫痪,集议基本上不再进行。
和中书省地位上升相适应,同时对集议的作用有重要影响的是元朝皇权的不断削弱。每一个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都有一个加强皇权的过程,元朝的这一过程最早开始于成吉思汗的千户百户分封,最终完成于忽必烈朝。大蒙古国时大汗和蒙古贵族集团间存在着微妙的权力平衡,忽必烈利用中原财赋为后盾,采纳汉人谋士的建议,通过一系列集权措施,同时也加强了皇权,最终彻底打破了大蒙古国时期的这种平衡。世祖时期的集议,其范围、基调、议程、参加人员实际上都受到皇帝的控制。参加集议的官员只能在皇帝规定的事项范围内就事论事,或者揣摩上意,或者为皇帝初衷寻找法理上的根据;尽管有皇帝接受群臣意见而放弃原先初衷的情况发生,但毕竟这样的事情较少,至少制度上存在着集议会被皇帝利用的漏洞。
台臣参加集议,一方面说明世祖朝没有能够独断大事的机构,另一方面也是皇帝用来牵制宰相、控制集议的手段。元前期皇权至高无上的力量在集议上的最集中体现则是皇帝对集议结果有无可置疑的最终裁决权。集议的结果皇帝可以不予理睬,集议上难以平息的争论任何官员,包括中书省丞相都无权加以调解而必须在皇帝面前廷辩,由皇帝作最后的决定。元代皇权在世祖朝达到顶峰,成宗继承了这笔遗产;虽说在位后期因身体不好,政事委于他人,不过总的而言,皇权并未受到什么威胁。成宗对集议的结果仍然可予以断然否定,丞相并不能左右集议结论。
元代皇权的削弱是从武宗朝开始的。这位在大德年间与西北藩王的几次硬仗中战功卓著的蒙古君王对中原王朝式政治实在不在行。随着尚书(中书)省地位的上升,加上元中期诸帝的私人目的,如仁宗欲背毁武仁授受之盟约而改立己子为储君,泰定帝欲保住自己皇位等,元中期的皇权被权(大)臣分割。集议虽继续举行,但结果多是些不关痛痒的议论;皇帝尽管保持着最终决定权,偶尔也会否定集议的结果,但廷辩则极少见于记载。如前所述,文宗朝开始,皇权受到威胁;燕铁木儿和伯颜两权臣得势期间,集议极少举行。脱脱任相后,尽管其权势不与皇权冲突,国家政令仍多出自丞相之意而非出自九五之尊。对比世祖朝,阿合马、卢世荣等受宠幸之臣有所建议尚须让群臣集议商讨。如阿合马意中书、尚书两省合一,拜安童为三公,“有诏会议”,因王磐反对,“其议遂沮”(注:《元史》卷一六○《王磐传》。),就是一例。阿合马可以弄权迁调与自己相抗之人,但不能作主集议结果。而在元末,军国大事全由权臣拍板,皇帝最终裁决权也名存实亡。
标签:中书省论文; 元史论文; 尚书省论文; 忽必烈论文; 元朝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元朝论文; 丞相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尚书令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晋朝论文; 南宋论文; 东汉论文; 隋朝论文; 唐朝论文; 西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