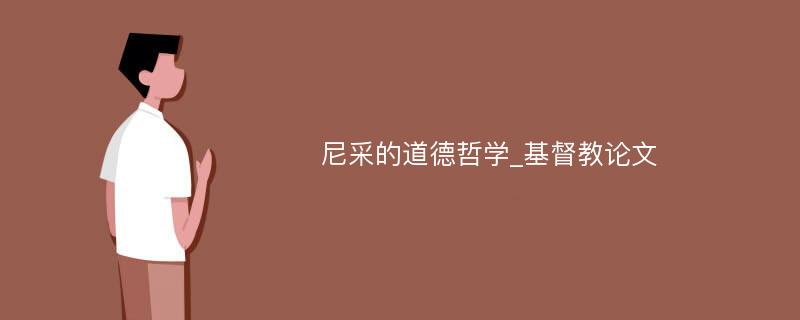
尼采的道德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道德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尼采(1844—1900)哲学中,艺术哲学和道德哲学占据重要的地位。艺术哲学是核心,道德哲学是其延伸。尼采的道德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1887年所写的《论道德的谱系》和1888年所写的《偶像的黄昏或怎样用铁锤作哲学思考》两本书中,在《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及其他著作里也有颇多的论述。而贯穿于尼采的艺术哲学和道德哲学甚至全部哲学中的精神,乃是狄奥尼索斯精神。尼采在自传中谈到《论道德的谱系》时颇为自得和满意,并指出了它的基本精神:“就表现、目的和意想不到的技巧而言,构成道德谱系的三篇论文,也许是曾经所写过的东西中最精彩的。你们知道,狄奥尼索斯也是黑暗之神。在每篇论文中,开始的时候,都是故意地把人导入迷途;它是冷漠的、科学的、甚至反常的,故意惹人注意的,故意缄默的。渐渐地,气氛变得比较不平静;偶然间,有一道闪电:以从遥远地方发出来单调的隆隆之声,唤起对那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事实之注意——直到最后,遇到一个强烈的进行速度,于此,一切东西都是热烈地奋力向前。最后,在每一情形下,在可怕的霹雳声中,透过浓浓的乌云, 又可以看见一个新的事实(truth——译为真理尚好——引者注)。”〔1〕贯穿于尼采哲学中的狄奥尼索斯精神乃是真、善、美的统一,如果说超人的本质是狄奥尼索斯精神,那么超人就是真、善、美的具体表现。这里美是核心,它包容着真和善,真和善是美的体现。
在尼采的道德哲学中,反基督教道德是出发点和基础,他的一切道德理论,皆来源于此出发点和基础。尼采从心理根源上探讨了基督教道德的起源和本质。他说,基督教把怜悯当作美德,所以它是怜悯的宗教;又说,基督教产生于憎恨心理,所以它是仇视人的宗教。这两种说法表现上看来不一致,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问题是基督教对谁而言是怜悯的宗教,对谁而言是憎恨的宗教。对于基督徒、教士、神学家而言,它是怜悯的宗教,因为他们把怜悯当作美德。而怜悯是敌视生命的表现:因为怜悯背离了人生机勃勃的情绪,使人抑郁、痛苦,使人生活的力量和生命的活力耗费和消失;怜悯与优胜劣汰背道而驰,它阻碍发展,阻碍淘汰,它保存行将毁灭的东西,为那些被剥夺了继续生存权以及为生活所淘汰的人作辩护,由于它使各种失败的人继续存在,因而赋予生命本身以黯淡和可疑的一面;怜悯也是虚无主义的,因为它阻碍了那些旨在保全生命和提高生命价值的本能,它增加了不幸并保有了一切不幸的东西,因此是助长颓废的主要工具,它教人相信虚无,虽然它不直接用虚无这个词,但它所说的上帝、天国、来生就是虚无。怜悯是一种病态的道德,它使人失去力量、健康,陷入死亡的危险。所以基督教的怜悯道德是否定、毒害、谋杀生命的。
基督教对于强者、超人、具有高贵价值的人却是憎恨的宗教。因为基督教颠倒了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它把使生命高尚化、提高生命价值、肯定生命、证明生命意义而使其壮丽的东西都当作假的、恶的、丑的;即使那些持科学见解的人也被拒斥于所谓“正当人”的行列之外,被视为“上帝的敌人”,被视为真理的蔑视者和“被迷惑者”,被视为贱类。所以尼采说基督教的道德没有一点真实性:除了想象的原因(“上帝”、“灵魂”、“自我”、“精神”、“自由意志”和“不自由意志”)以外,什么也没有;除了想象的结果(“罪恶”、“赎罪”、“神恩”“惩罚”、“赦罪”)以外,也是什么都没有。基督教也是一种想象的心理学,除非自我误解,除了借助宗教道德特质的象征语言如“悔改”、“良心的痛苦”、“魔鬼的诱惑”、“上帝的显现”等以解释那些适意的或不适意的一般感情以外,一无所有。基督教道德还是一种想象的目的论。它宣扬的“上帝之国”、“最后审判”、“永恒生命”是真正的虚构的承诺。尼采指出,这个纯粹虚构的世界是远逊于梦幻世界的,因为后者反映现实,而前者捏造现实,剥夺现实的价值而且否定现实。因此,基督教道德以虚构的上帝、虚构的原罪、虚构的神恩、虚构的地狱、虚构的魔鬼、虚构的末日审判,表明它的道德是仇视自然的,仇视人类的,仇视生命的。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揭露了基督教道德的反自然的本质,那就是它切除、阉割、根除人的激情、欲望和生命。“教会用不折不扣的切除来克服激情:它的策略,它的‘治疗’是阉割。它从来不问:‘怎样使欲望升华、美化、圣化?’——它在任何时代都把纪律的重点放在根除(根除感性、骄傲、支配欲、占有欲、复仇欲)。——但是从根本上推残激情就意味着从根本上推残生命;教会的实践是与生命为敌”;“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而且,它们声称上帝洞察‘人心’,它们否定生命的最深最高的欲望,把上帝当作生命的敌人,给上帝逗乐的圣人是地道的阉人,……‘上帝的疆域’在哪里开始,生命便在哪里结束。”〔2〕在《论道德的谱系》中, 尼采称基督教道德的体现者教士是最凶恶的敌人,因为他们最无能,而从无能中生长出的仇恨既暴烈又可怕,既最富有才智又最为狠毒。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是来自于这些教士、这些基督教道德的捍卫者。而基督教道德是奴隶的道德,他们的价值观念是弱者的价值观念,是强者的价值观念的颠倒。在他们看来,不报复的无能便是“善良”,卑贱的怯懦便是“谦卑”,向仇恨的对象屈服便是顺从;爱自己的敌人便是宽恕,不反抗压迫便是忍耐。总之,“基督教道德是一种最有害的虚伪意志,是使人类腐化的真正巫婆。它不是那种激怒着我的错误;它不是在基督教道德笼罩下一种长久不断的‘善意’、熏陶、庄重,以及精神上勇气的缺乏;它是人性(nature)的欠缺,它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实,即凡是非自然的东西,都被接受而作为道德的最高荣誉,都是悬诸人类之前以作为无上命令的法则。”〔3〕
除了批判基督教道德之外,尼采更为深刻地批判了传统的市俗道德和近代伦理学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功利主义目的论,并特别批判了康德的义务论道德学说。康德义务论的伦理学,是与近代西方伦理学中功利主义目的论相对立的。其出发点是善的意志。所谓善的意志,就是对于来源于理性的道德律令的绝对服从,或者说强制“我”、命令“我”,“我”也认为必须为尽义务而尽义务的意志就是善的意志。因此,康德主张人应按绝对命令行事。所谓绝对命令就是出于善的意志的人所特有的具有强制性的行为准则,它是无条件的,不讲功利,不考虑效果的道德原则。它具有普遍的立法形式、人是目的、意志自律的特点。按照这些原则行事的行为叫道德行为。例如,忍辱负重、宁死不屈、为尽义务而尽义务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与绝对命令相反的道德原则,也就是讲功利、讲效果,讲条件的以人为工具的道德原则叫假言命令。按假言命令行事的行为,无道德意义。例如,商人做买卖,做到童叟无欺,不卖高价,这种行为是为了达到一种效果,所以无道德意义。康德认为,道德的根源不在人性,例如,爱憎、幸福等等,恰恰相反,道德之所以道德,正在于它经常是自觉地牺牲幸福、爱憎、生命,不顾利害、效果,不屈服于自然的需要、欲求和愿望,不等同于动物性的求生本能或任何享乐愉快,而以牺牲人作为感性血肉的存在显示出来、令人钦佩、令人仰慕和敬畏。牺牲自己的肉体生命,既不是为了精神上的名誉、快乐或满足,也不是为上帝的恩宠或报答,它只是为了服从或执行所“应当”服从或执行的道德律令而已。在这里,任何经验的喜怒哀乐、利益、欲望、效果、功利都应摒弃。这是康德义务论伦理学的核心思想。在尼采看来,康德的这种伦理学思想实质上与基督教伦理思想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新教伦理的基本主张乃不是义务,便是罪恶。这种伦理是反对生命,反对强力意志和欲望,因而是狡猾的神学。尼采还批评了康德的美德和善良意志说。他指出,美德必定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是我们最需要的自我表现和自卫,任何其他种类的美德只是一种危险。而康德的美德仅仅是一种概念和情感,其“善良意志”的普通有效性又否定了个人存在,因此,康德伦理思想是一种空想和没落的表现,是生命最后的衰竭。这是道德的非自然化,即所谓理想化。
道德的非自然化,是道德的非历史化、非现实化,它必然要导致对上帝的设定。“康德以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狂热贯穿了整个18世纪;他完全处在历史之外;对他那个时代的现实不屑一顾,譬如革命,未受到希腊哲学的触动;他是义务概念的幻想家,感觉论者,带着教条主义恶习的神秘嗜好”;“我们世纪出现了向康德的回潮,也就是向18世纪的回潮。因为,人们想为自己重新谋求信奉旧的理想和旧的热衷的权利。——也就是说,‘设定界限’的认识论,准许任意设定理性的彼岸。”〔4〕
尼采口口声声要否定道德,要求人们置身于道德之外,有时甚至自称是一个反道德论者,以致有的学者说尼采是反道德主义者。其实,尼采只是反基督教道德,反非自然主义道德,反对群畜、弱者的道德,而主张非基督教道德、自然主义道德、强者或超人道德。尼采强调说:“道德中的每一种自然主义,也就是每一种健康的道德,都是受生命本能支配的——生命的任何要求都用‘应该’和‘不应该’的一定规范来贯彻,生命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和敌对事物都藉此来清除。相反,反自然的道德,也就是几乎每一种迄今为止被倡导、推崇、鼓吹的道德,都是反对生命本能的,它们是对生命本能的隐蔽的或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谴责。”〔5〕
自然主义道德,是尊重生命的道德,强者的道德,超人的道德。它要求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首先是对道德价值本身进行重估,也就是说,我们究竟需不需要道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道德?对现存的道德我们应作如何评价?我们根据什么给予一种道德价值以较高的评价?根据什么给予一种道德价值以较低的评价甚至否定它?尼采说:“让我们来宣布这一新的挑战:我们要批判道德的价值,必须对道德价值本身的价值提出疑问——为此还需要认识这些道德价值产生、发展和拖延的条件和环境,认识作为结果、作为症候、作为面具、作为伪善、作为疾病、作为误解而存在的道德,同认识作为原因、作为医药、作为兴奋剂、作为抑制物、作为毒药而存在的道德。”〔6 〕基于存在着不同的道德价值体系,尼采确定了对它们肯定或否定的标准:凡是使人类处于危险、诱惑、麻痹、甚至牺牲的道德就应加以否定。根据这一标准,尼采认为,从根本上说,“反道德”一词,有两种否定含义。第一,否定以往被称为最高者那种形态的人——即善良的、仁慈的、宽厚的人;第二,否定普遍承认所谓道德本身的那种道德——颓废的道德,也就是基督教道德。“我认为第二种否定更具有决定性,因为,一般说来,我早就觉得,高估善良和仁慈的价值是颓废的结果,是柔弱的象征,是不适于一种高扬而肯定的生命。否定和灭绝是肯定态度的条件。”〔7〕
不仅要重估一切价值体系,而且要重估具体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评价。首先要超越传统道德的善与恶,好与坏的观念。传统道德将善与好与不自私相联,恶与坏与自私相联。并且善与好是由主体行为的得益者来评价的,而不是来源于道德主体本身的创造性行为。道德史家们在这两对价值观念的起源和本质的论述上是拙劣的,违背历史的。他们宣称,最初,不自私的行为受到这些行为对象们,也就是这些行为得益者们的赞许,并且被称之为好,后来这种赞许的起源被遗忘了,不自私的行为由于总是习惯地被当作好的来称赞,因此也就干脆被当作好的来感受——似乎它们自身就是什么好的一样。在尼采看来,善与好的价值判断,并不是来源于善行的人,其实它起源于那些好人或善者本身,是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自我评价。那些处于高贵等级的、拥有强力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善与好的本质也不是“不自私”,而是显示人类力量感的行为,显示人类意志力的行为,显示人类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变失败为胜利,变痛苦为幸福,在悲剧中显示崇高的行为。这是善与好的本质。因此,“‘好’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根本没有必要和‘不自私’的行为相关联:那是道德谱系学家们的偏见。事实上,只是在贵族的价值判断衰落的时候,‘自私’和‘不自私’的这种全面对立才越来越强加于人的良知,——用我的话说,群体本能终于用言辞(而且用多数的言辞)得到表述。”〔8〕恶与坏也不能等同于自私。 尼采指出,从德文词上来分析,它本来是称谓那些简朴的、普通的人的贬义词。因为德文的坏(schlecht)和简朴(schlicht)是通用的。作为道德行为评价的恶与坏,乃是那些群畜、基督徒、卑贱者的怯懦、柔弱、无能、乞怜、妥协,而这正是基督教宣称的奴隶道德。基督教道德颠倒了善与好,恶与坏的价值判断。在强者、超人看来是善和好,在基督教看来是恶与坏。“在地球上,所有反对‘高贵者’、‘有力者’、‘主人’、‘权力拥有者’的行动都不能和犹太人在这方面的所为同日而语:犹太人,那个教士化的人民,深知只需重新评定他们的敌人和压迫者的价值,也就是说,以一种最富有才智的行动而使自己得到补偿。这正适合于教士化的人民,这个有着最深沉的教士化报复心理的人民。”〔9〕
道德哲学中另外两个重要范畴是“负罪”和“良心谴责”,道德史家对这两个范畴的起源和本质也作了歪曲。好象自主的主体对上帝、对他人本来就是有罪的,理应受惩罚。而“良心谴责”表明个人没有尽义务,有过失,而进行自我责备。尼采说,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他指出,一个自主的个体,对他自己来说是平等的,他是超道德习俗的个体,摆脱了一切道德习俗的约束;同时,他又是一个自由的个体,他有权力去统治自然、环境和一切弱者;自由也意味着负责任,负责任是他的权力和特权,甚至是他的本身,也就是所谓良心。这种人,是不应该有“负罪”和“良心谴责”的概念的。但是后来由于习俗形成了,理性发展了,耻辱感产生了,人类社会才有“负罪”、“良心谴责”的概念的。“理性,严厉,控制感情,所有这些意味着深思熟虑的暗淡的东西,所有这些人类的特权和珍品,它们的代价有多高啊!在这些‘好东西’背后有多少血和恐怖啊!”〔10〕
“负罪”这个道德范畴起源于经济学和法学的“负债”,它反映的本来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一种法律和经济关系。如果债务人不尽还债的义务,债权人就有权要求施以惩罚,作为不尽还债义务的回报。“欠债要还债”,这本来与行为主体的道德不道德毫无关系。但是,当人性发展到高级阶段,负债的概念进入到道德领域就变成了“负罪”的概念。法律上负罪,应受刑事责任,要受法律惩罚;道德上的犯罪称之为道德过失,它的惩罚形式是舆论谴责和良心谴责。从本质上说,它们都是用制造一种痛苦抵偿一种损失,这是法律正义感和道德正义感的由来。尼采指出,正是在这里人会起疑心,也正是在这里发现了冷酷、残忍和疼痛。为了让人相信他关于还债的诺言,为了显示他许诺的真诚,同时也为了牢记还债是自己的义务,债务人通过契约授权债权人在债务人还不清债务时用他尚拥有的能支配的东西抵债。例如,使债务人卖身为奴,甚至出卖他的妻子。而在宗教势力强大、宗教意识浓厚的环境下,债务人甚至要转让他的后世幸福,他的灵魂得救的机会,乃至死后的安宁。例如,古埃及人很重视死后的安宁,但若债务人死前未还清债,那么债权人可以进行鞭尸,甚至从尸体上割肉还债。尼采说,道德观念正是起源于这种经济关系和习俗。“在这个义务与权利的领域里出现了一批道德概念,如‘负罪’、‘良心’、‘义务’、‘义务的神圣’等等,它们的萌发就像地上所有伟大事物的萌发一样,基本上是长期用血浇灌的。”〔11〕
“良心”本来是自主的主体负责任的本能,它如何变成了良心谴责、良心忏悔、自我惩罚、自我残忍呢?传统的道德史家说,这是由于惩罚引起人们的负罪感,这种负罪感反馈到主体自身就产生了“良心谴责”。尼采指出,这是歪曲心理,歪曲现实,歪曲历史。因为,罪犯和囚徒中绝少有人因惩罚而真心忏悔,甚至有人因惩罚而产生逆反心理,变得坚强残酷、负于反抗。即使在起到正常作用情况下,惩罚也只是驯服人的手段,而不是改进人、完善人的手段。“良心谴责”起源于外在环境的种种压力,起源于自己生存意志的软弱和这种软弱表现出的对外界压力的不敢反抗和对自我的残忍。尼采指出,人有一种适应的本能、求生存的本能、求满足的本能,这种本能有时要表现为残忍,当这种残忍本能不能再向外发泄时,便回过头来对自己发泄。他说,这是发泄本能内向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人的“灵魂”,随之产生良心谴责。“整个的内在世界本来是像夹在两层皮中间那么薄,而现在,当人的外向发泄受到了限制的时候,那个内在世界就相应地向所有的方向发展,从而有了深度、宽度和高度。那么被国家组织用来保护自己免受古老的自由本能侵害的可怕屏障(惩罚是这个屏障最主要的部分),使得野蛮的、自由的、漫游着的人的所有那些本能都转而反对人自己。仇恨、残暴、迫害欲、突袭欲、猎奇欲、破坏欲,所有这一切都反过来对准这些本能的拥有者自己:这就是‘良心谴责’的起源。”〔12〕尼采认为,传统道德中的“良心谴责”是极其有害的,它使人患上了最严重、最可怕的疾病,人为了人而受苦,人为了自身而受苦,这是人的自我价值的贬低、推残和否定。特别严重的是“负罪”和“良心谴责”这两个范畴被道德化以后,还和宗教学说结合起来。上帝成了人类的债权人,人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欠了债的,有罪的,因为有罪,人们会感到内疚、忏悔,要进行良心谴责。最后使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因为债务是无法还清的,所以赎罪也是徒劳的,从而形成了罪孽无法赎清的思想,即“永恒的惩罚”的观念。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上帝面前人人有罪。但是物极必反,事情走向了反面。因为债务人毕竟是债权人上帝创造的,债务人的债是欠他的创造者的。上帝创造了债务人,创造了他们无法还清的债。他只得以自己的牺牲来替债务人还债。上帝的自我牺牲体现了他对人类的爱。最后,尼采满腔愤怒地谴责了“良心谴责”,“正是这个进行良心谴责的人以其倒退的残酷抓住了宗教假说,从而使他自我折磨加剧到可怕的程度。对上帝负债的想法变成了他的刑具;他在上帝身上抓到了最终与他的真实的、未脱尽的动物本能相对立的东西。”“这种动物本能,为的是把它们当作对上帝负债的证据。当作仇恨上帝、拒绝上帝、反叛‘主’、反叛‘父’、反叛始祖和造物主的证据。他把自己置于‘上帝’和‘魔鬼’的对立之中。他对一切都掷以否定:否定自我、否定自然、否定他自身的自然性和真实性。他把从自身挖出来的东西当作一种肯定,一种可能的、真实的、主动的东西,当作上帝、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刑罚,当作彼岸世界,当作永恒的折磨,当作地狱,当作永无止境的惩罚和无法估算的债务。这种心灵残酷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意志错乱。”〔13〕
在道德哲学中,还有一个禁欲主义理想问题,也就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做一个圣洁的基督徒,是不是要否定人的一切欲望。基督教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经过马丁·路德、伽尔文改革后的基督教即新教,包括英国的清教徒,都宣扬禁欲主义,以至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认为新教的禁欲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力。但是,教会本身所提倡的禁欲主义是什么呢?它如何产生?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有什么危害?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对这些问题作了下述回答。
禁欲主义就是用道德理想去扼杀人的本能欲望。例如,人人要饮食男女,人人有七情六欲。但是,在基督教看来,人们满足这些欲望的追求,都是罪恶,需要禁止。所以,禁欲主义反映了道德与本能的对立,否定本能,宣扬虚伪的道德;反映了性欲与贞操的对立,压抑性欲,吹捧贞操;反映了意志与理性的对立,否定意志,高扬理性;宣扬了动物和天使的对立,否定了人这种高等动物的生的本能,宣扬了天使这种精灵的圣洁;反映了人的自我肯定和自我否定的对立,否定生命本身,肯定来生幸福;宣扬了善与恶的对立,禁欲是善,欲望是恶。总之,反映了与上帝的对立,否定人,肯定上帝。所以,禁欲主义理想反映的是教会的意志,僧侣的信念,甚至反映了他们的权力和利益。正因此,在尼采看来,禁欲主义理想乃是生命的自我保护和自我本能的败落表现,是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病态表现。因为现实的生命受到折磨,他又不能积极的反抗,因此就采取消极反抗,欲望既然达不到,甚至欲望是罪恶,不如禁止一切欲望,追求虚无缥缈的永恒生命。所以禁欲主义理想,是人摆脱折磨的工具。它之所以有力,并不是象基督教所说,它背后有上帝这个精神支柱,而是因为直到现在,它是唯一的理想,没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它,而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
禁欲主义理想有三个重要口号:乐于贫穷,慎行谦卑和严守贞操;它的战斗旗帜是“胜利孕育在垂死的挣扎中”,它在这个旗帜上看到了光明、福祉和最后胜利。对于禁欲主义者来说,十字架、利益、绝妙是三位一体的。所以,禁欲主义理想被教士和哲学家道德化了。他们把它作为一种药方,其效用就是把病人变得无害;让病入膏肓的人去推残自己,并且把类似患者的丑恶本能全部利用起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控制、自我征服。它不仅不能治病,反而置人于死地。因此,必须对它进行批判否定。
尼采对基督教道德、对在西方有着长远历史影响的功利主义道德和义务论道德的批判,虽然有其合理因素,但对之实施全盘否定则是错误的。基督教道德固然有许多消极的东西,但是,它所提倡的博爱、善良、慈悲、诚实等精神,至今仍然是许多西方人恪守的价值观念,并且成为维系西方家庭和社会伦理的纽带和保持社会稳定安宁的力量。尼采对于西方功利主义道德和义务论道德的基本精神的理解也是片面的。功利主义道德是一种幸福论,他提倡的是个人幸福和他人幸福的协调,物质幸福和精神幸福的统一,甚至在必要时牺牲个人幸福维护社会进步,并强调精神幸福高于物质幸福,这正是人和动物之区别。康德提倡的义务论道德虽然有其抽象性、非历史性,但他所强调的意志自律,人是目的与尼采的主张并不矛盾。至于尼采提倡的强者、超人道德,强调个体、肉体、意志的崇高,强调权力、精神、欲望的支配力量,强调更新善、恶、好坏观念,强调重估一切价值,这种怀疑、批判和否定传统的精神是值得称赞的,但走到极端就难免陷入虚无主义。从虚无主义那里,我们是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
尼采的哲学思想和道德思想在近代中国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陈独秀都曾介绍过尼采的思想。他们试图用尼采思想来反对封建礼教, 鼓吹个性解放和人性复归。 尤其是鲁迅, 他在1907年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介绍了尼采对旧文化的批判,对近代文明的抨击和对未来文化的展望。特别是鲁迅痛感旧中国国民性的软弱、卑劣、落后,想用尼采的“权力意志”、“超人”来改造国民性,重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但1949年以后尼采在中国的命运是令人遗憾的,由于受到前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尼采曾被当作死狗批判,说他是主观唯心主义者、战争狂人、法西斯主义者。后来,到70年代和80年代,在部分青年中又出现了“尼采热”,尼采又成了盲目崇拜的对象。这一褒一贬,一誉一谤,皆是人为的,都不是从研究尼采的著作和本来思想出发的,而是出于某种需要和主观臆断。我们主张应从客观的历史背景出发,在深入研究尼采原著的基础上,对尼采的思想作公正的分析和批判。
1996年6月初稿 1997年6月修改
注释:
〔1〕〔3〕〔7〕尼采《瞧!这个人》,中国和平出版社1986 年版,第94、14、110页。
〔2〕〔5〕尼采《偶像的黄昏》,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2、35、35页。
〔4〕尼采《权力意志》, 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3页。
〔6〕〔8〕〔9〕〔10〕〔11〕〔12〕〔13〕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6、12、18、42、45、63、70、71页。
标签:基督教论文; 尼采论文; 道德论文; 道德批判论文; 文化论文; 禁欲主义论文; 康德哲学论文; 哲学家论文; 存在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