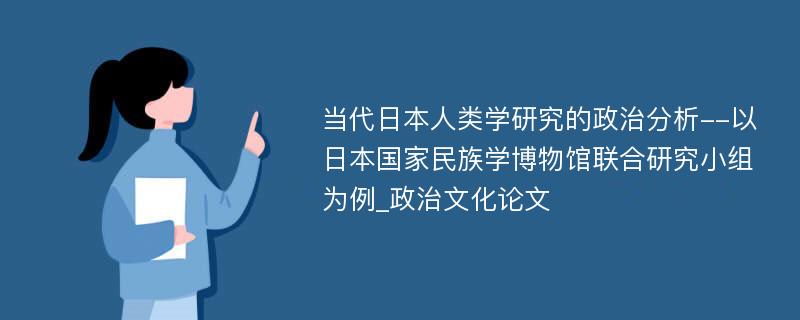
当代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一个共同研究课题组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民族学论文,人类学论文,为例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试图通过近年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梳理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的历史脉络,并从研究的主体、研究对象、选题、民族志的写作方法以及与其他学科学术对话的角度,揭示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的特点、近年的变化及其原因。
2004年10月,由笔者发起的“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再构筑:革命的实践与表象”(Social Change and Reconstruction in China:Focusing on Practice and Representation of Revolution)现当代中国研究课题组,在日本的人类学研究中心、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以下简称“日本民博”)正式组建。
“革命”是揭示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新中国诞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建立,已有的社会结构、法律制度、道德伦理、宗教信仰受到革命的巨大冲击。社会主义革命从理念变成了现实,并被意识形态化、制度化,通过日常的生活实践在中国社会扎下了根,从而形成了另一个文化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诸种制度、话语和象征在日常生活、旅游、艺术、民间信仰等领域被重新构筑、表象和消费[1]1-15。
日本民博“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再构筑:革命的实践与表象”课题组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课题组每个成员在中国基层社会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考察社会主义革命所产生的诸种制度与已有传统之间的断层和延续性,并从个人、家族、地域社会等角度阐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意义和本质。我们的研究方法不是把焦点放在少数政治家或思想史上,而是从话语(discourse)、表象(representation)、民众的实践(practice)等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革命理念是如何被意识形态化、制度化的;个人、家族、地域社会等是如何把国家的理念和制度内在化的;为了回应激剧的变革,人们又是如何有策略地调整亲族组织、婚丧嫁娶、民间信仰的。这种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和表象直接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在日本为首创,不仅为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界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也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
一、以“革命的实践和表象”为切入点的共同研究
(一)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共同研究
“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再构筑:革命的实践与表象”(代表:韩敏,2004-2006年度)课题是日本民博共同研究的一部分,而研究是日本民博展览、教育、研究的三大功能中最为重要的功能。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创建于1974年,1977年11月正式对外开放。民博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是日本最大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机构,研究对象和范围几乎包括了世界七大洲。民博也是文部科学省指定的大学共同利用机构,因此,民博的专职研究人员通常要与馆外研究者就某个课题进行共同研究。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共同研究课题组共有43个,笔者主持的“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再构筑:革命的实践与表象”是其中的一个。
除本课题组外,日本民博自建馆以来到2006年度为止,关于中国的共同研究课题组共有8个:“中国少数民族的基础研究”(代表:佐佐木高明,1984-1985年度)、“以满族为核心的中国东北的文化复合——满洲文化对周边民族的影响”(代表:烟中幸子,1986-1987年度)、“汉族的地域性及其认同——以中国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整理和分析”(代表:竹村卓二,1987-1989年度)、“中国大陆少数民族的汉化的诸侧面——以仪礼为中心的整理与分析”(代表:竹村卓二,1991-1993年度)、“中国大陆诸民族的移动和民族性——以华南地区为中心的整理和分析”(代表:冢田诚之,1994-1996年度)、“中国大陆诸民族的移动及文化动态——以周边地区为中心”(代表:冢田诚之,1997-1999年度)、“中国民族表象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以南部地区为中心”(代表:长谷川清,2000-2002年度)、“中国民族表象的政治性——以南部地区为中心的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代表:冢田诚之,2003-2005年度)。
从以上课题可以看出,日本民博对以及在日本的中国研究有三大特点:(1)以民族学为研究方法的民族性(ethnicity)研究。(2)对汉族、少数民族的两分法研究手法[2]170-173。竹村卓二组织的两次共同研究探讨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少数民族的汉化以及民族界限等问题。(3)研究对象以少数民族为主,而且除了烟中幸子组织的满族研究外,其余的基本都是对南部少数民族的研究。近年来,长谷川清和冢田诚之主持的课题组脱离了历来对民族性、民族界限的分析框架,开始了对民族表象的政治性的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3]。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关于“少数民族和法制度的比较研究”的共同研究(代表:横山广子,1998-2000年度)。该课题组以法律制度为切入点,对中国的国家法规及地方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行政管理,泰国、尼泊尔、印度、越南、缅甸、俄罗斯、立陶宛的民族法,菲律宾、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地的原住民以及国际机构对民族和民族法的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4]。
(二)以革命的实践和表象为研究对象
“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再构筑:革命的实践与表象”的共同研究始于2004年10月,由日本民博的4名学者以及来自日本19所大学的20名学者构成。他们主要来自人类学领域,也有一些来自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学、民族音乐学等领域的学者。值得一提的是,课题组中有10名是在中国直接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并在改革开放后赴日留学,现已在日本大学执教的华籍学者。而课题组的一些日本学者也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日本间接地受到过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些来自不同学科领域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日本民博对中国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为期两年半的讨论。
在使用汉字的中国和日本,“革命”一词有三种涵义。在古汉语中,“革命”是一个动宾词组,“革”是动词,“命”是天命。古汉语中的“革命”表示革天之命,也就是说,革命意味着改朝换代,是天子因接受了天命而即位的意思,或者说,天子的更换是因为天命的改变。现代汉语和现代日语中的“革命”已经脱离了古汉语的意思,它是英语revolution的对应词,而英语的revolution是从拉丁文的revolutio(旋转、变动)转变来的。现代意义的“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革命”是指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根本改变。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就属此类。广义的“革命”是指事物由一种状态激剧地转变成另一种状态。它可以用来指在经济、文化、艺术、语言、风俗习惯等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动。英国的产业革命、中国的文化大革命、IT革命就属此类。本课题组经过讨论,决定把“革命”一词定位在现代意义的广义上,并把辛亥革命也放入课题组的研究范围之内①。
在考察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被动员的中国革命时,实践和表象是两个有效的概念和工具。这里所说的表象是指象征,或者说是象征性地表示或代表某个事物。具体来说,表象是通过语言、旗帜、服装或发型等象征对已有的实际存在进行意义生成的行为。社会学者涂尔干(Durkheim)曾指出,几乎所有的社会生活皆由表象(representation)构成[5]21。他还认为,表象分为个人表象(individual representation)和集体表象(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两类。集体表象是某个集团的成员所共有的知识和感情的象征,它既包括旗帜等表现为物质形式的象征物,也包括人们看待世界和决定人们看待世界方法的基本概念,如神话、信仰和意识形态等。而个人表象则与集体表象不同,它意味着每个个人的经验。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表象都是指通过图像、符号等形象标志对已有的现实进行意义生成的行为,而且在这种表象行为中往往含有与个人或集体的主张和利益等有关的政治因素。本共同研究课题组中的文革时期军便服的流行,现在有关唐装、汉服的流行和争议,灵魂拯救实践中的冥界观的表象,婚葬礼仪中的宗族表象,英雄、模范、领袖人物的表象和象征意义,革命艺术中的女性形象以及现当代电影中的革命表象等讨论,就属于个人表象和集体表象的范畴。
共同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实践。实践有两层含意:一是指行为,作为理念的对应词。二是指人对社会和社会关系的认识和改造。课题组从不同的理论维度对现代中国社会发生的葬礼革命、学英雄模范的制度化、样板戏的京剧革命、曲艺作家的创作等社会实践进行了剖析[6-9]。
笔者把以下21个研究报告分为三个主题:(1)宣传、言说、服饰、电影中的革命表象;(2)革命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制度、文化/礼仪的重构;(3)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下的革命记忆与社会转型。希望通过这三个主题来探讨当代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中政治分析的现状和特点。
二、从宣传、言说、服饰、电影来看革命的表象
如上文所述,本课题组把“革命”定位在表示社会领域的巨变这个现代意义的广义上,并将包括1911年辛亥革命在内中国百年的社会巨变纳入本课题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且我们把中国的百年“革命”看做是不同于西方和日本的另一个现代化过程[10]2-4。
课题组首先注意到了社会主义革命理念的表象和实践,并通过个案分析探索了国家言说的内在化、新中国妇女形象的塑造、英雄人物的产生和宣传的过程。例如,聂莉莉在其研究报告中,以焦裕禄和雷锋两个英雄模范人物为案例,阐述了学习和选举英雄模范人物是革命初期红军时代以来一直延续至今的党和政府进行大众动员的主要方法。焦裕禄和雷锋两个人物具体体现了“为人民服务”的言说。对他们的学习运动是通过毛泽东等领导人物的题词、报纸的宣传、宣传画/邮票的发行以及电影宣传等方式展开的,并且通过每年各级选举的“学雷锋先进个人/集体”和“表彰焦裕禄式的好干部”的表彰大会而制度化。“为人民服务”言说中的“人民”成了“无产阶级”、“劳苦大众”、“祖国”和“国家”的同义词,可以任意替换,是除去了社会属性和具体性的政治概念。作者试图通过考察模范英雄人物制度化的途径及其效果来分析革命实践的过程[10]6-7。
“宣传”(propaganda)作为社会动员的重要手段,在当代中国得到了充分发挥。因此,研究中国式的“宣传”技巧和效应是揭示20世纪中国革命的有效概念。牧阳一在日本民博共同研究的课题报告中利用大量的宣传画、图片等资料,对建国后“宣传”中的女性表象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了革命中国的妇女表象与前苏联的妇女表象的相似性,并指出这种抹杀了女性性别的表现手法源于以男性为规范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53-73。
武田雅也则通过对大量的雷锋照片、宣传画、连环画、小人书、漫画等宣传工具的比较,指出了英雄人物雷锋表象的时代变化。他揭示了革命宣传与雷锋表象的关联性,并从文化论的角度分析了“傻子雷锋”与古典神话系谱中的“愚者”、六朝时代《世说新语》中的奇人或怪人、现代文学中的阿Q之间的相似性,指出了革命英雄与传统英雄在叙述方法上的连续性。在道德沙漠化的今天,“雷锋”的意义已经从对共产党的绝对忠诚、对敌人的仇恨转变成“助人为乐”。在市场经济的中国,“雷锋精神”似乎象征着买卖的公正性和诚实性[1]131-154。
服饰与革命表象是课题组关注的另一个侧面。汪晓华对“文革”期间的军便服成为国民服装的原因和普及程度进行了分析。通过与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制度对服饰文化(如中山装)的影响进行比较,作者指出了文革军便服的流行与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关系(如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并认为当代中国服装是政治理念和政权的正统性、权威性的视觉表象。作者从1999年到2001年在北京、沈阳、武汉三个城市对36岁到72岁的知识分子、干部、工人、退休人员共250人进行了个人访谈和民意测验。调查的内容包括个人拥有军便服的件数、对军便服的认识、穿着场合、穿着的心情或感觉等。从她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中可以看出,北京、武汉、沈阳三大城市的军便服普及程度存在差异,而这种差异似乎与当代革命的中心地带、红卫兵势力的强弱、造反派武斗的程度等有关[1]75-106。
周星回顾了近现代服装史的百年演变之后,用“制服社会”的概念来解释文革时期的中国社会以及服装意识和军便服的普及原因。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服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多重性,首先是西装在城市的普及,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也穿上了西装。同时,中山装在国家领导层中仍具有正统的象征意义。在部分农村地区,中山装作为革命的记忆仍继续存在。周星利用互联网上的争论和信息,着力对唐装、汉服和汉服运动的状况和实质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近年民众在服饰上的新追求和争议既有来自对欧美国际社会的意识,对东亚社会的和服、韩服等国民服装的意识,也有来自中国国内少数民族的影响。大众文化的国际化现象(韩国的《大长今》、日本的《大奥》和中国的《汉武大帝》等电视剧的影响)也是促使人们希望确立民族服装的要素之一。周星指出了对唐装、汉服和汉服运动的研究意义,并展望了从文化认同、文化自觉(费孝通)、寻根的民族主义(加加美光行)、构筑主义、社会心理学的流行论和大众文化论等角度进行研究的可能性[1]437-474。
西泽治彦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的当代电影,并用人类学的文化解释方法对中国电影的社会、文化背景和习俗进行了分析。在课题报告中,他运用了象征手法和文化解释的方法对中国电影中的文革描述进行了分析。他列举了《牧马人》、《芙蓉镇》、《蓝色风筝》、《活着》、《霸王别姬》、《孩子王》、《太阳少年》等电影,对导演、革命的内容事项、文革发生的舞台、文革电影的登场人物进行了分类。通过对居委会和街道干部的观察,他指出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委员会是城市政治动员的工具。从电影的主题方面看,中国电影的文革描写表达了伤感、仇恨和怀旧等情绪,同时也是对人性的反思和对社会结构的质疑[1]107-130。
三、革命过程中民间的社会制度、文化/礼仪的重构
(一)对宗族理念和形态的动态研究
日本学者对中国亲族制度的研究始于二战前,它一直是日本人类学者中国研究的主线,并且成果丰厚。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日本学者受19世纪以来欧美近代学术的影响,把血缘和亲族关系看做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社会结合,认为亲族和家族是一种后进性,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他们把这种以血缘为核心的中国社会和以地缘为核心的日本社会进行了对比,在这种比较背后可以看到一种社会发展阶段论的图式——以地缘为核心的社会结合比以血缘为核心的社会结合更进步[11]59-65。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亲族制度仍然是日本人类学界主要的关注对象。但是,与二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日本学者不同,新一代学者更注重亲族制度和观念在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中的变化和作用[12-13]、香港城市的宗亲会[14]、亲族制度中的女性角色和姻亲网络[15]等,并用历史的连续性来说明父系继嗣原则的延续和改革开放以后的宗族复兴[16-17]。此外,社会主义革命与改革开放以来亲族制度的变化、延续和重构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赴日留学学者的主要考察对象[18-24]。
在本课题组中,有两篇是来自在日华籍学者的汉族亲族制度的报告。秦兆雄以湖北汉族农村村落为例,从个人的辈分、性别和年龄的角度考察了家族、亲族和宗族的原理、范围和形态。同时通过对人民公社集体化的毛泽东时代与改革开放以后的家族和宗族的理念、组织和实践的比较,指出在毛泽东时代,联合家族、父权和儒教伦理仍然存在;宗族组织虽然受到了破坏,但是宗族内部的辈分等秩序和宗族意识仍然存在,并起着一定的作用。他用上门女婿改姓归宗的现象证明了以上的看法。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自由化和个人主义的兴起导致了提早分家、联合家族和直系家族的解体以及老人抚养等问题。他的结论是:在毛泽东时代,家族和宗族受到的冲击主要是来自国家的政治影响;而改革开放以后,家族和宗族受到的是经济自由化、少子化和个人主义的影响;后者对家族和宗族的影响远远大于前者[1]313-342。
潘宏立分析了福建南部石狮市农村的婚礼和葬礼仪式中的宗族、祖先和神灵的表象后得出结论:建国以后,虽然受到国家的控制和影响,但民间的婚礼、葬礼等通过礼仪的基干部分——礼仪的基本顺序、个人与宗族以及祖先的关系、人与神灵的关系、神灵的作用和秩序等基本要素仍然得到维持。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基于节约农地、环保和科学精神,在闽南农村地区进行了殡葬改革。随着土葬转为火葬,“点主仪式”也从坟地移到了火葬场②。
(二)丧葬、灵魂拯救和改良风俗
长期从事汉族丧葬文化研究的何彬在本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对20世纪初至今北京八宝山等地的葬礼、埋葬法、墓地和祭祀进行了民俗学的实证研究。她指出由于政府使用了行政手段,北京的丧葬民俗发生了巨变。民众为了灵活地适应社会和政治环境以及都市现代化的变化,巧妙地导入传统的生活习俗,重构自己在城市的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都市社会的新民俗。她还指出,从都市型的葬礼中可以看到,在汉族的深层意识中依然存在着传统的灵魂观和冥界观念。在火葬普及的现在,骨灰盒成了死者居住的家,而汉族原有的“灵肉一体”的灵魂观在火葬普及后的今天变成了“灵骨一体”[1]183-213。
田村和彦以陕西省中部地区的公墓产业和殡葬改革为事例,揭示了关于“死”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以及民间知识的延续。他的特点是在考察殡葬改革的实践中,没有使用常见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国家—民众的对抗模式,而是注重考察了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存在的推进者、代理者(agent)——公墓服务中心和经营性的公墓事务所的作用。这种对国家和民众之间的回路的分析视角为殡葬改革的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方法[1]215-250。
谢荔援用了法国文化人类学家丹·斯佩伯关于文化表象中“公共表象”(public representation)、心理表象(mental representation)的概念③,对20世纪90年代四川地区宗教设施的雕刻、壁画、劝善书等展示冥界观念的公共表象与村落死者礼仪的灵魂救赎观念的个人心理表象进行了考察。她还对操作葬礼的宗教职能集团“坛”的存在及其功能进行了分析,并通过对宗教职能集团的礼仪和在家信徒朝圣的考察,揭示了公共表象与个人心理表象的连锁关系。同时,她指出了改革开放后冥界信仰文化的连续性,并对复兴后的灵魂拯救的礼仪实践中基于因果关系的“劝善惩恶”、“孝”、“和”的家族伦理观念进行了重新评价[1]251-276。
在广西从事壮族研究的冢田诚之使用了历史学的文献分析方法,对广西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政权下的文化政策、法规以及社会动员方式的异同点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和比较。他列举了大量关于婚俗、男女对歌、起居卫生、信仰、服饰的规定和改革实践的记述,得出如下结论:两个政府对壮族实行的风俗改良都是以政府的尺度来衡量的,并且都以婚俗和迷信为主要的改良对象,并展开了卫生运动。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虽然在社会体制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两者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对改良风俗的规制和实践上却差异不大。另外,比起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政府的风俗改良,30年代国民党政府实施改良政策的对象范围似乎更广、规模似乎更大。他指出,今天我们看到的壮族风俗习惯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被改造过的[1]157-182。
(三)文艺中的国家和革命
在中国汉族农村地区长期从事曲艺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井口淳子,通过对河北滦县乐亭大鼓的文本、河北曲艺作家韩起祥和高荣远的个人生活史以及他们的创作实践、陕西米脂杨家沟村的自编歌的文本分析,揭示了在北方农村曲艺说唱中的革命实践和革命记忆。近年,她在牛津大学查阅的四百余册中文的现代曲艺文本皆为大陆作品。而在没有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台湾地区,曲艺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曲目上。她指出中国大陆的革命给传统的曲艺不仅增添了时代的新内容,也为大陆的现代曲艺创作开拓了地方叙述(local narrative)的可能性[1]29-51。
薛罗军从民族音乐学的角度,对文革时期的语录歌、知青歌、样板戏进行了分析,并重点探讨了样板戏音乐的民族性和现代性问题。他还分析了近年在中国出现的样板戏音乐的复归现象,如红色经典音乐会,样板戏的CD、DVD、乐谱和明信片的流通,指出了对样板戏音乐的认同存在着年龄层的差异④。
长期在云南白族等地区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横山广子在1949年后社会主义民族政策、文化政策的框架下,讨论了传统民族(ethnic)音乐的现代性与作为国民文化的音乐的关系,并通过对1984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的实证分析,考察了“民族音乐”、“民族舞蹈”以及“原生态”等概念⑤。
徐素娟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政府在甘肃省莲花山的花儿和花儿会这一多民族的民间文艺形式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她通过对花儿的语境分析(context)以及对“掌柜的”(sponsor)这个群体的存在及其对花儿影响的分析,揭示了花儿在建国后是如何在政府的介入下被重构的过程。政府通过充当花儿的“掌柜的”参与民间活动,把花儿作为可以利用的文化资源;同时政府的现代化政策、革命的概念等也通过花儿被民间文化所吸收,成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在花儿和花儿会中可以看到民间和国家领域的并存[1]399-435。
四、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下的革命记忆与社会转型
笔者在前言中已提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和全球化的今天,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制度和历史仍在日常的生活实践、旅游、艺术、民间信仰等领域被重新构筑、表象和消费。
东美晴用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对上海人旅游景点的选择和旅游心理进行了调查,并侧重考察了以革命表象为消费对象的人群及其旅游动机。她指出,与选择海南岛的度假旅游、云南的民族旅游的游客相比,选择革命圣地的游客仍算少数。而对革命圣地感兴趣的游客主要集中在40岁左右这个年龄层。她用戴维斯的怀旧(nostalgia)概念[25]解释了这个年龄层的游客心理[1]345-365。
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今天,作为革命中国符号的毛泽东在政府的言说、国家媒介、民间记忆、旅游等活动中具有怎样的象征意义已经开始受到在日学者的关注。韩敏在共同研究的报告中,以2003年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政府、民间团体及个人在韶山举行的各种纪念、祭拜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为例,用涂尔干的集体表象、个人表象的概念以及维克多·特纳的象征概念[26],对毛泽东的多重象征意义进行了考察。她对表象的主体进行了分类,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韶山当地人、外地的农民、工人或职员、公务员及学生,并把由这些主体展示出的象征意义及其口述进行分类整理,揭示了毛泽东意义的多重性与职业、阶层、年龄的关联性。她还指出,政府主办的诞辰庆典的舞台表述了国家的记忆,演绎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延续性[1]367-397。
深尾叶子以自传的方式折射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日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影响,以及20世纪70年代经济高速成长中的日本人对现代化的困惑。改革开放以后,深尾开始在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尤其是在对陕北黄土高原榆林地区的调查过程中,她注重与当地人的互动,参与了对当地生态文化的保护,并通过“黄土高原生态文化恢复中心”和“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网络”的建立,观察并参与了另一个革命——绿色革命的实践[1]475-509。
对东亚的民俗知识、共同体的整合性和风水素有研究的渡边欣雄在共同研究报告中,首先整理了英美与日本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共同体论研究(community studies)的理论脉络,提出了共同体论的三大特征:首先是共同体的内部性,即相对于国家制度的邻居关系、亲属关系等“基础的地域社会”的要素。其次是共同体与外部的联系,即以“基础的地域社会”为核心的人和物质的移动与交流的范围,如通学圈、通勤圈、婚姻圈和购物圈等。再次是把共同体作为国家行政单位的视角。他重申了共同体论的理论框架对中国研究的有效性,并以北京东城区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进行的社区重建为例,分析了社区的类型、选举制度、管理运营机制、社区与家庭关系、社区的福利以及社区中的现代胡同民俗⑥。
佐佐木卫长期以来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凝聚力。日本近代化的研究证明,以“家”为规范的日本式结构是引发社会移动的能量,同时也规定了社会移动的形式。佐佐木卫援用了这个命题,讨论了中国社会“差序格局”的现代意义。他以河北农村、青岛市崂山区为例,指出了在土地、住宅、义务教育、就职、福利、生活保障等方面存在的“本地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以及“本地人”与外地人、定居者和移动者之间的“差序格局”。他分析了青岛市崂山区出现的三类社区。第一类社区为单位型社区,主要由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职员和有关人员居住。单位以优惠价格将房屋卖给单位员工。社区内有幼儿园、小学、超市和邮局等生活服务设施。第二类为新建的高级公寓型社区,公寓按市场价格出售,居住者多为私营企业的老板和管理阶层。社区内有医院、学校、饭店、健身设备。第三类为单位的旧房屋改建的公寓,已脱离单位管理,租借给外来的流动人员。这样的公寓面积狭小,而且没有空调设备。第一类、第二类社区为定居者的生活空间,第三类社区多为流动者的生活空间。作者的结论是,“本地人”、“外地人”的差序格局不仅存在于农村,在城市的社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也普遍存在。在全球化的中国社会,差序格局是人口移动的源泉,也规制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的方向⑦。
五、结语
以上笔者从三个主题,通过21个研究报告介绍了日本民博关于中国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这些虽然不能反映日本人类学界中国研究中政治人类学的全貌,但它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人类学界研究的特点和动向。
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同欧美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相比,其最大特点是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继承了东洋史的学术传统,是中国学(sinology)式的研究。中国社会人类学研究的先辈末成道男先生在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就读时,首先阅读的是滋贺秀三、仁井田升、牧野巽等东洋史先辈的研究文献[27]220。对中国的研究,日本人比西方早,而且研究的积累也多,研究也更详细。日本东洋史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仅是供日本学者享用的遗产,而且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国学者享用的共同财产。黄宗智(1985)的华北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7]29。
悠久的学术传统是一笔财富,但无形中也会对后学形成一定的束缚。已故人类学者王崧兴先生在21年前曾对日本的汉人社会研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和期待:“日本的人类学研究终于已经走出了汉族研究、中国研究的第一步,即研究危险性最小的家族、宗族和村落。是否能再进一步,有勇气研究世界观和宇宙观,突破日本中国学的厚墙呢?这是个未知数,也是一个期待。”[27]228王崧兴先生的疑问和期待如今已成为现实。日本人类学的中国研究不仅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宇宙观进行了研究,还直接把20世纪中国革命的表象和实践作为研究对象。如本文涉及的政治动员方法,英雄模范人物的形成和制度化,服装、红色旅游、毛泽东的多重意义,戏剧、曲艺和电影中的革命表象,城市社区的重构等都是富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课题。
日本的中国研究在研究课题方面发生变化有很多原因。其中,国际环境和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按照上田信的说法,可以把日本的中国学者大致划分为三代。第一代学者是战前在中国有考察经验的一代。第二代是战后没能到中国考察的学者。他们把中国研究作为批判日本的原动力,期待从中国找到非西方式现代化的模式。第三代是改革开放后可以到中国调查的一代[27]221。中国的门户开放、中国社会自身的变化、中日之间学术交流、世界人类学的动向改善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条件,并影响了他们的研究视野。此外,笔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给日本学者带来了在中国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新契机,同时,日本严谨、实证的学术气氛也吸引了许多中国青年。中国的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日本式的人类学熏陶,并逐渐成为日本学术共同体的一部分。中国研究的仙人会以及日本民博的共同研究课题组就是很好的例子。仙人会是研究中国以及周边地区的人类学、民俗学、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会,“于1981年5月召开了第1次研究会,并一直持续到现在”[27]9。仙人会主要由大学生和青年学者构成,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经参与过这个组织。在那里,中日青年学人和学者共同切磋,互通情报,互相取长补短。“仙人会在为在日本执教和研究的中国人类学者提供学术交流和知识刺激的场所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28]17这些曾是留学生的中国学者在日本人类学界被称为“留学生组”,他们和日本学者的关系既是“研究同行”,又是“良性的竞争对手”[29]164。“留学生组”学者的出现不仅给日本的中国研究带来了量的变化,也提供了崭新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角度。日本人类学的研究重镇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新近出现的“中国的社会变化及再构筑:革命的实践与表象”课题组就是一例。这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于2009年3月由东京风响社出版后,在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日本的中国人类学研究在研究主体、课题、问题意识等方面正在发生变化,笔者对日本民博的一个中国共同研究课题组的政治分析的综述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希望本文能够成为读者了解日本人类学中国研究的一个契机,并为今后的学术交流提供一个参考。
[收稿日期]2008-12-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09-05-19
注释:
①渡边欣雄和濑川昌久在笔者筹划共同研究的初期,就曾建议把辛亥革命也作为本课题组的考察对象。在此,对两位学者表示感谢。
②参见潘宏立“通過儀礼·宗族·国家——福建省南部農村の現地調查から”,国立民族学博物館“中国の社会变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共同研究会研究報告,2005年。
③公共表象是指公众共有的信号、发言、文本、绘画等表象。心理表象是指仅仅属于个人的信念、意图和爱好的表象。参见ダン·スペルベル“表象は感染する”,東京:新曜社,2001。
④参见薛羅軍“よみがえりつつある革命模範劇の音樂”,国立民族学博物館“中国の社会变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共同研究会研究報告,2005年。
⑤参见横山廣子“中華华人民共和国における民族音樂·民族舞踊というカテゴリ一に関する一考察——革命の表象と実践をめぐって”,国立民族学博物館“中国の社会变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共同研究会研究報告,2007年。
⑥参见渡邊欣雄“Sociological Anthropology としてのCommunity Study——北京社区建設の事例”,国立民族学博物館“中国の社会变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共同研究会研究報告,2007年。
⑦参见佐佐木衛“现代中国にわげるグロ一バル化と構造転換”,国立民族学博物館“中国の社会变化と再構築:革命の実践と表象”共同研究会研究報告,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