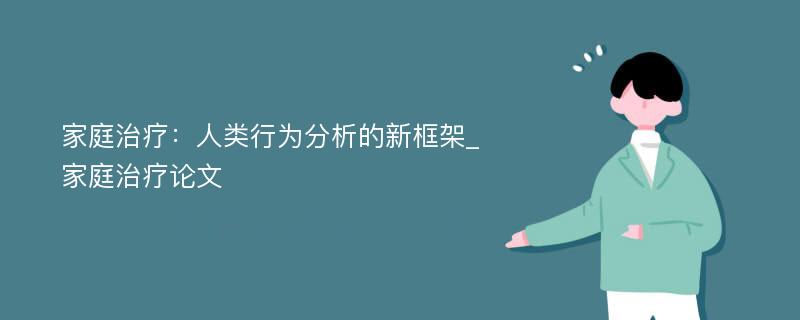
家庭治疗:一种分析人类行为的新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治疗论文,框架论文,人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8)01-0105-05
一、心理治疗:从个体治疗到家庭治疗
现代心理治疗的历史是从个体心理治疗开始的,从个体心理治疗到家庭治疗走过了漫长的50年。
尽管个体心理治疗各流派的治疗理论和技术不同,但它们都有几个共同点:其一,将心理疾病看做是个体和个体心理作用的产物,治疗者的工作完全集中在对个体的诊断、分析和干预上。如精神动力学的治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内心世界,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人格重组的过程;[1]456行为主义治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行为模式,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采用学习原理增加适应性行为,减少问题行为;人本主义治疗关注的核心是个体人格改变的进程,治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来访者自身的潜能,促进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接纳;认知治疗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个体的信念系统,治疗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将一个人消极的自我陈述改变为具有建设性的、积极的陈述方式,从而改善个体的情绪和行为。其二,个体心理治疗认为,最好的治疗方式是在治疗者与当事人之间建立私密的关系,在治疗时特别强调一对一治疗关系的形成,将治疗师和来访者的关系隔离出来,把有压力的环境因素排除在治疗室之外,并且坚持认为和来访者的亲属接触会干扰治疗师。如弗洛伊德只关心个人内心世界的心理冲突和做深层的人格分析,即使沙利文,虽然他认为自我是个体与环境互动的产物,但受到个人、线性因果关系机械论的影响,还是将“人际关系中的自我”转化成“重要关系人的内化作用”。这就预示着个体心理治疗把一种本是相互影响的结果内射化,在现实的建构中,不再包含与重要关系人的持续互动。其三,个体心理治疗,除了人本主义治疗,都从心理病理学的角度去了解人,努力寻求精神病理症状为什么会发生的原因,然后再对疾病进行治疗。治疗的目的是消除这些疾病,就像动外科手术把疾患割除一样,但疾病的消除往往并不意味着健康的恢复。在治疗的过程中,治疗师关注的是症状,病人体会到的第一件事也是只有他的症状才能使他得到治疗师的关注,其结果是使得疾病越来越突出,治疗的路也越走越窄[2]8。
随着心理治疗实践的发展,人们开始认识到,大多数的人类行为都是互动性的,有些问题,存在于个人的心理状态,却展现于与他人的互动之中,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帮助人们改变他与其他人的互动方式,家庭治疗应运而生。
家庭治疗,和个体心理治疗一样,都是心理治疗的途径以及了解人类行为的方式,但是家庭治疗是对个体心理治疗的一次革命,它挑战了“以个体为整个心理范畴的中心”的基本信念,将所存在的问题或症状从个体转向了关系[3],并且通过家庭或更大的机构在内的系统的改变,进而处理和消除个体所存在的问题或症状。
目前,家庭治疗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渗透到了成人精神分裂症、心身症状、成瘾、抑郁、焦虑、婚姻压力、性功能障碍等许多领域,有人甚至将它称之为心理治疗的“第四势力”。美国婚姻和家庭治疗协会的成员数也已经超过18000人。1978年,斯卢兹科(Sluzki)就曾指出,到目前为止家庭治疗是行为科学上主要的认识论革命[4]366。积极心理治疗大师佩塞施基安也认为,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家庭治疗看成一种特殊的治疗安排,而是把它解释为一种特殊的思想方法,一种公正地对待人的社会性方法[3]7。
一位个体心理治疗的治疗师会这样告诉来访者:“改变自己,自己努力,这样你就会成长。”但家庭治疗师则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描述:只有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有了改变,家庭成员才会有所改变。因此,家庭治疗给出的信息是这样的,“帮助其他人改变,当你和他互动时,你自己才能改变,而且能让在同一系统中的你们两个都改变。”[6]110
二、家庭治疗: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关系
作为一种分析人类行为的新框架,家庭治疗代表了心理治疗的一个新领域和新方向,它的“新”,在概念、诊断和具体介入技术等整个治疗过程中都有体现。
1.从家庭人际关系背景中寻找心理行为障碍的原因
家庭治疗反对内省观,强调人际观。它的第一个基本假设认为,人是其所在环境的产物,个人的心理问题不单纯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与其所处的环境有关,人格和心理的各种障碍是不良人际互动的结果。
每个人都需要经过人际的相互作用,才逐渐成为一个“社会人”,除了遗传和生物学的疾病过程外,心理和人格的健康成长取决于良好人际的相互作用。家庭治疗师认为,家庭是个人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人际活动场景,家庭不仅是一群由共享特定物理、心理空间的个体组成的集合体,也是一个具有独特性质的自然社会系统。家庭会形成一组规则,里面布满了对成员角色的分配和要求,有一个组织化的权力结构,形成外显和内隐的沟通模式,并发展出协商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方法,以有效执行各种不同的任务。家庭成员在家庭系统层次上产生的各种关系是深刻而多层次的,并对每个家庭成员的成长和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经验形成了个人心理的整个深层结构。人类的经验包括归属感和自我感两部分,能够将这两部分加以混合和调配的主要场所就是家庭,作为个人认同感的孕育母体,在任何文化中,人们自我感大部分都是由家庭塑造完成的。
家庭治疗采用系统论观点,把个体心理治疗所强调个人的观点扩大到研究个人在其主要组织如婚姻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本质[7]。家庭治疗虽然不否定个人内在心理的重要性,但它不是以个人的心理为着眼点,个人的心理结构、潜意识的冲突、个人行为的动机和信念系统不是家庭治疗分析的主要焦点,而是将个人问题放大,放在更大的人际关系层面上,聚焦于家庭的结构与规则,家庭的交流与沟通,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角色与情感,家庭的生命周期,家庭的功能、问题与适应等,思考家庭中的人际关系是怎样或至少部分地造成症状问题。家庭治疗把个人行为视作发生在家庭社会系统中,是整个家庭反复交互作用的结果,即家庭成员的症状行为不单单是个人内在正反力量相抵抗的结果,而是家庭人际间挣扎的产物,是目前发生在家庭系统中有缺陷的互动过程的呈现,那个“病人”只是一个“带症状者”(identified patient,IP),他真正表达的是家庭的失衡或功能不良。
在治疗实践中,家庭治疗认为,家庭成员症状的意义和功能是家庭变得不平衡并企图调试或重建平衡的信号,家庭维持着其成员的症状,而这些症状反过来又维持着成员之间的关系模式。如,萨提尔(Viginia Satir)主张被困扰的病人,其“症状”事实上可能代表他对于家庭所做的反应,并且尝试吸收和缓和“家庭痛苦”,结果导致成长的扭曲[8]。米纽钦(Salvador Minichin)认为,症状行为是对处于压力下的家庭组织所做的反应,尽管家庭努力把问题设定在某位家庭成员身上,但所有家庭成员其实都一样“具有症状”[9]。沃兹拉维克(Watzlawick)、威克兰德(Weakland)和费舍(Fisch)则认为,症状或问题是因为家庭不断重复使用同一种没有作用且只有收到反效果的解决方法而引起的[10]。虽然他们对症状产生的原因阐述不一,但对症状的目的以及从家庭环境的人际背景中寻找心理行为障碍的原因这一点,他们的观点却是完全一致的。
2.从家庭生命周期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寻找个体心理行为障碍的原因
家庭治疗强调了家庭作为有机体的概念,认为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功能和结构层面上产生了持续的变动。这种变动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家庭将经历有次序的、渐进的、连续的、可预期的家庭生命周期的转变过程。根据杜瓦尔(Duvall)的观点,一般的核心家庭在它的生命周期中将经历几个重要的共同转折点,如离开家庭成为单身年轻人,通过婚姻建立一对一的夫妻关系,孩子的出生,有青少年的家庭,孩子离开家庭,父母亲成为祖父母,晚年家庭生活等,在不同的家庭发展阶段中,各世代间的互动可能同时发生,家庭中每一代的发展都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大部分家庭的发展会出现各种并存的转折期。
其次,一些突发重大事件的出现,家庭经历重大的转折期,如重要家庭成员的突然去世,父母的离异,再婚,突然的家庭经济困境,残障儿的出现等。这些事件的出现,家庭的连续的可预期的进程遭到破坏,对家庭系统产生重要的影响。
第三,一个人与周围的环境总是互相影响的,家庭生活本身和它所在的社会环境中的许多外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广大的社区和社会的生活形态、文化类型和突发事件都会对家庭产生重要的影响。
家庭是一个随着时间而不断前进的系统,在每个阶段中,家庭依赖家庭任务的完成才能继续发展下去,前一期的家庭特征也会被传递到下一个阶段,如果特殊任务没有完成或被阻碍、干扰的话,那么发展就会因此耽搁或停滞不前,而且这些困难也会带进下一阶段的家庭发展中。
家庭生命周期的概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架构以研究家庭发展可预期和不可预期的阶段。家庭治疗认为,当家庭进入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一方面,家庭需要重组以适应成员的成长和改变,并支持成员致力于个人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随着家庭的转变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协助家庭任务的完成。
家庭治疗认为个人的生命周期发生于家庭生命周期之中,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他们以家庭生命周期为背景,分析个体的同一性和个体的发展。如策略式家庭治疗认为,个人症状是家庭生命周期正常历程被干扰的结果[11]213,症状的出现是家庭无法进展到下一阶段的信号;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个人症状往往被视为一种征兆,不是“家庭功能失常”,而是家庭在面对某一段生命周期的转换无法重新调整其结构以适应变化的征兆;鲍文(Bowen)等其他以心理动力为导向的家庭治疗师认为,家庭发展和个人成长一样,会在早期阶段变得固着或停滞,固着的结果是家庭中个人以症状的形式表现出来。巴赫尔(Barnhill)和朗哥(Longo)认为,家庭和个人一样,也会固着或停滞在某个阶段,无法在适当的时机做出必要的转变,同样和个人一样,在压力下,家庭还可能会退化到先前已经度过的生命周期阶段的转折点。在他们的概念中,出现在任何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的症状,都是目前家庭生活任务没有达成的证据[12]33。
虽然家庭治疗各个流派在运用家庭生命周期概念时的着眼点不同,但他们都强调以家庭生命周期为背景,从家庭发展的互动关系中寻找个体心理行为障碍的原因,都认为一个家庭必须不断地成长,家庭的规则、角色、结构、观念和互动模式必须有灵活性,才能使其内部成员保持健康成长。
三、家庭治疗:处置对象、目标与成效
虽然家庭治疗认为,个人的心理问题是存在于家庭关系中,是家庭问题的表现,但现代家庭治疗已经不再强调家庭是个人问题的“罪魁祸首”,而更重视家庭是解决与家庭相关联的个人问题的“治疗所”。对家庭治疗师来说,家庭是一个整体,当这个系统中的一个或更多成员出现问题,处置的对象应是整个家庭。
家庭的本质包含家庭的结构、发展与功能几个层次。家庭治疗主张通过家庭或比家庭更大的系统的改变,来处理和消除家庭成员的症状。具体包括:协助建立适宜的家庭结构,以便发挥家庭功能;促进良好的家庭关系,免除家庭人际冲突;促进合适的家庭沟通,维持家庭交流的成效;协助家庭顺利地度过家庭发展的阶段,以助于家庭完成发展任务;协助家庭成员间建立适当的联结,提供适宜的情感支持;协助建立家庭规范,促使家庭生活形成有效的预期与方向等。
在这些共同的基本目标之外,不同家庭治疗流派在具体的治疗目标上还是有些差异的。结构式家庭治疗认为,家庭治疗师必须通过家庭内各次系统的发展以及亲子关系中阶层和教养方式等家庭结构的改变,来协助家庭重构家庭的整体性发展和个体的自主性;策略式家庭治疗认为,家庭治疗师必须改变家庭的信念系统,帮助家庭找出新的解决方法来面对原来的问题,对于那些在家庭生命周期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的家庭,在治疗过程中,家庭治疗师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帮助它重回正轨,家庭治疗的主要目标就是从生命周期中寻找以使问题正常化的信息,重建家庭发展的动力;心理动力式家庭治疗师的目标是,通过协助家庭克服未能化解的伤痛,脱离家庭发展上的困境;米兰(Milan)学派家庭治疗会探索家庭史的细节,以寻觅可发展各家庭成员的“正向解读”的信息,并首创运用家庭仪式以促进家庭生命周期各阶段的转换;叙事式家庭治疗则强调解构家庭无意义的叙事以重构更有意义的新叙事。
除了在概念、处置对象和治疗目标发展外,家庭治疗的成效问题也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为此,研究人员进行了很多实证研究。
1963年,哈利(Haley)发现,在14个精神分裂症的年轻人中,经过家庭治疗,只有3个人再次住院,住院期在2-4年,有一个人自杀。1974年,沃兹拉维克、威克兰德和费舍的一个研究发现,在家庭治疗3个月后随访了97个家庭,他们的治疗长度平均为7次,40%的报告说症状完全缓解,32%有相当程度的缓解,28%没有改变[13]659。1978年,格曼(Gurman)和科尼斯肯(Kniskern)考察了14个比较研究(家庭治疗和其他方法)发现,在10个比较研究中,家庭治疗都优于其他方法,在其余的4个研究中,家庭治疗的效果与其他方法相当,在大约2/3的个案中家庭治疗都起到了治疗效果,家庭治疗案例的整体改善率为73%[14]。托德(Todd)和斯坦顿(Stanton)于1983年以及格曼于1986年的研究也都证实,家庭治疗能在短期治疗中产生了积极的效果(1-20个疗程),且短期或限时的家庭治疗与长期治疗一样有效果[15]。1975年,米纽钦的报告发现,通过结构式家庭治疗,糖尿病和慢性哮喘病等心身症的改善率为90%[16]。1978年,米纽钦,罗斯曼(Bernice Rosman)和贝克尔(Lester Baker)报告,在对53例厌食症患者及其家庭的治疗中,改善或治愈率为86%[17]。亚历山大(James Alexander)及其助手在犹他大学运用“功能性”家庭治疗,对青少年犯罪家庭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用这种方法进行治疗的家庭在交流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与其他治疗方法相比,显示出较低的重犯率(26%),其他如患者中心治疗法的重犯率为47%,动力—折中治疗法的重犯率为73%[18]。1989年,斯扎普尼克(Szapocanik)和柯蒂斯(Kurtines)对西班牙药物滥用青少年进行结构式治疗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建立在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基础上,但结合了部分策略治疗,然后把它和用家庭治疗方法对一个来访者做治疗的所谓一人家庭治疗进行了比较,有76个西班牙药物滥用青少年随机进入两组进行家庭治疗,然后使用父母对青少年行为评定、青少年心理功能的评定、家庭成员对家庭功能的报告等指标对个体和家庭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在两组治疗中,儿童的心理都有改善,但是只有在前者中,家庭的功能才有改善。1991年,卡阿(Cart)在对米兰系统家庭治疗综述中发现,在10个研究中,米兰学派的家庭治疗中症状有改善的在66%-75%[19]661。
尽管至今仍然存在着对家庭治疗概念和方法上的质疑,但这些精心设计的研究都证实了家庭治疗的成效。作为一种分析人类行为的新框架,家庭治疗拓展了我们理解人类行为的概念体系,使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更好地理解人类行为的意义,并在此过程中,显示出它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
收稿日期:2006-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