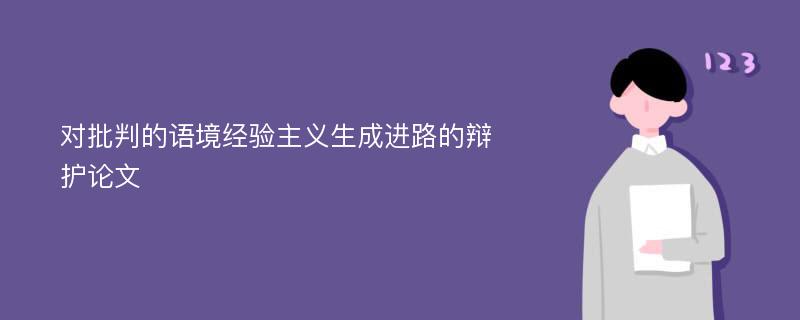
·哲学专题讨论·
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数据与语境 ——第十七届《哲学分析》论坛专题研讨之一
编者按: 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和《知识的命运》两部著作中提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是当代引人瞩目的科学哲学理论之一。本期专题围绕“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选编了四篇文章:复旦大学黄翔教授的《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生成进路的辩护》,塔林理工大学彼特·穆尔塞普教授的《作为一种实在论的批判语境经验主义》,中国社会科学院孟强研究员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CCE的几点思考》,以及朗基诺教授对以上三位作者质疑的回应。黄翔认为,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强弱两个版本,弱版本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强版本则引起较多争议,但通过引入当代认知科学中生成进路的强版本辩护策略,可以为CCE强版本做辩护。穆尔塞普认为CCE将社会和规范方面融入对科学的理解中,实践实在论也使文化和规范方面在理解科学时发挥重要作用。孟强认为,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是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的哲学研究的第三条道路。朗基诺在回应中指出,理性和社会二分是对知识概念的误解导致的,而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规范来自科学自身的形象。与认知科学中的生成主义进路相比,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更注重思考科学探究的过程,它关注的是作为公共知识的科学。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和实践实在论都拒绝“上帝之眼”的可能性,但在形而上学和规范性问题上两者依然存在差别。
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生成进路的辩护
黄 翔
摘 要: 海伦·朗基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可被理解为两个版本。弱版本认为在科学实践中社会性因素必然地参与到知识论过程中。强版本则坚持一些社会性因素是科学实践中知识论过程的构成性成分。弱版本被大多数学者接受,强版本则引起许多争议。这两个版本之间存在着论证上的鸿沟,而该鸿沟是学界质疑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的主要原因。当代认知科学中的具身进路也存在着类似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生成理论对强版本具身进路的辩护策略可以被借用来处理批判语境主义的强弱版本之间的鸿沟。两种对应强弱版本鸿沟策略的相似性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意味着生成进路所提供的资源可为批判语境主义提供更好的辩 护。
关键词: 批判语境主义;海伦·朗基诺;生成进路;具身认知
海伦·朗基诺(Helen Longino)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和《知识的命运》两部著作中提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是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科学哲学理论之一。一方面,它继承了20世纪上半叶传统科学哲学理论对一般性问题的系统和深入的分析与探求,没有像历史主义和自然主义转向之后诸多科学哲学研究那样,在专注于真实的科学实践的具体细节的同时却丧失了对一般性问题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它在看似难以相容的规范性科学哲学与注重社会性因素的科学元勘之间,尝试着找到兼容两者的中间道路。中间道路的建立需要消解一系列根深蒂固的理论二分,这种消解具有很大难度。朗基诺的理论在同类尝试中相当成功。① 其他的中间道路的尝试的一些典型例子包括哈金提倡的新实验主义(Ian Hacking,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Introductory Topics in the Philosophy of Natural Sci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巴拉德的能动实在论(Karen Barad,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Quanta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her and Meaning,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7),张 硕 夏 的 多 元主义前提下的行动实在论(Hasok Chang,Is Water H2O?——Evidence,Realism and Pluralism,Dordrecht,Heidelberg,New York and London:Springer,2012),巴尔德的科学仪器哲学(Davis Baird,Thing Knowledge: 然而,对朗基诺的理论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质疑。本文的目的是深入地分析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些质疑。本文第一部分区分了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强、弱两个版本,并指出许多质疑针对的是强版本,而朗基诺对强版本的辩护有待进一步加强。第二部分引入当代认知科学中生成进路的强版本辩护策略,并在第三部分中论证该辩护策略可被借用来加强朗基诺对强版本的辩 护。
一、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两个版本
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以下简称“CCE”)由三个基本概念组成。“经验主义”一词继承了传统经验主义知识论的基本思想,即对外在世界的知识不可避免地依赖感觉经验。朗基诺坚持经验充足性是辩护科学理论应该遵循的知识论标准。② 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93—94. 经验充足性(empirical adequacy)是范·弗拉森提出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是一个理论是经验充足的当该理论在面对某一观察现象时,能够找到一个模型,使得该观察现象成为该模型的所指(Bas 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p.12)。不难看出,经验充足性是比对世界的正确表征更弱的标准,因为满足后者也就满足了前者,而反之则不成立。范·弗拉森认为经验充足性是科学更为可行的目标。朗基诺对经验充足性的坚持只是出于知识论的考虑,并不意味着她因此而坚持范·弗拉森的反实在论立场。本次论坛中穆尔塞普(Peeter Müürsepp)的论文展示了CCE可以支持某种版本的科学实在论。 CCE与传统经验主义知识论的不同之处则由语境和批评这两个概念表达出来。加入语境概念是因为,在朗基诺看来,科学实践过程中知识的产生与辩护不可避免地受社会性因素制约,从而造成不同研究传统在不同背景条件下,对同样的研究对象会形成不同的认知视角,而不同的认知视角会对同样的研究对象给出多元化的认知内容。CCE中另一个概念即批评性的加入,是为了保证具有语境主义和多元主义特征的科学知识不会丧失客观性。朗基诺提出,一个科学共同体只有满足以下四个规范,即CCE规范(CCE norms),才能有能力捍卫科学的客观 性。
(1) 进行公共交流与批评的公开渠道(venues),如会议、论坛、学术期刊 等。A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Instruments,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Joseph Rouse How Scientific Practices Matter:Reclaiming Philosophical Naturalis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以及本文讨论中会涉及的所罗门的社会经验主义(Miriam Soloman Social Empiricis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1)等。
GA系列五轴联动万能加工中心该产品具有设计紧凑、铣削性能卓越、可见性高以及工作区操作方便等优点,加工效率高且维护简单,拥有独一无二的机床理念:卧式主轴使得Z轴行程路径达到最长,可实现最佳的排屑效果;3个直线轴的独特布置,将导轨与加工点之间的距离降至最小,使机床具有极大的稳定性;“隧道”概念使用了超长工具旋转和加工最大组件的理论基础,使得上述操作的过程中不会发生碰撞;3个直线轴和2个旋转轴,可实现五面加工和五轴联动加工。
(2) 对批评意见予以吸收和回应(uptake)。
(3) 进行交流与相互批评的各方共有某些公开的标准(public standards)。
(ASC-2) 具有语境主义和多元主义特征的科学实践需要解决客观性理想的问 题。
这四个约束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规范与经验充足性这个传统知识论规范结合在一起,构成了CCE的知识论规范性的大致轮廓。在这个轮廓中,对科学实践的社会性研究和知识论研究不必相互隔离甚至相互对立,而是必然地结合在一起形成对科学知识更为透彻的理 解。
(ASC-3) 只要具有语境主义和多元主义特征的科学实践中的科学共同体遵循CCE规范,它们将能够解决客观性理想的问 题。
(CCEw)社会性因素必然地参与到知识的产出、知识的内容形成和知识的辩护过程中。② 知识的产出、知识的内容和知识的辩护分别对应朗基诺区分的知识生产实践(knowledge-productive practices)、知识的内容(content)和知道过程(knowing)。知识生产实践是指从旁观者的视角来看知识的产生或制造过程。知识的内容是从知识所涉及的对象来谈论知识。知道过程是从认知主体的视角来看获取知识的认知过程。朗基诺正确地指出,由于传统知识论与对科学的社会学研究都未能区分与知识相关的这三种含义,从而在相互讨论中引起了许多歧义(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p.82—85)。
在这个版本中,社会性因素对科学实践中的知识论过程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是因为这些因素构成了某一特定的知识产出、知识内容的形成或知识辩护事件得以发生的语境或条件。在这里,社会性因素与知识论因素尽管相互影响却拥有不同的功能,用来说明科学的不同方面。更具体地讲,社会性因素指的是形成知识论或认知事件发生语境的外在影响因素,而知识论或认知因素则构成认知主体的内在过程。当该过程遵循我们所接受的知识论或认知原则、规范或标准时,我们便会认为相应的认知主体是理性 的。
春季是鸡病高发期的养鸡过程。春季常见的鸡病主要有以下几种:新城疫、大肠杆菌病、呼吸道疾病等。其中,传染性鸡病对养鸡业危害极大,将导致大量的鸡病。在处理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困难,严重影响养鸡的经济效益。
朗基诺的一些表述可以被看成是对CCEw的支持。比如,《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在开始的部分就宣称,该书是为了发展出一种新的科学推理和科学知识的理论,该理论“可以使我们认识到科学争论既涉及了社会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也涉及了更为典型化的科学证据与逻辑问题”。换言之,该书的目的在于“通过分析科学推理的种种方面,来展示社会性价值在科学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③ 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3. 。不难看出这个目的与CCEw兼容,因为如果社会性价值是科学知识产出、知识内容的形成与知识辩护中难以避免的因素,那么它们的确在科学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此书的第三章中朗基诺给出了对CCEw的论证。其论证策略大致如下:在科学研究中,只有依赖某些背景知识才能做出某一事态(a state of affairs)是否能够成为某一假说的证据的判断,而背景知识不可避免地被社会性价值渗透;因此,社会性意识形态和价值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制约着科学家们对数据与假说之间的证据关系的理解,换言之,它们必然地参与到知识的产出、知识的内容形成和知识的辩护过程 中。
Case study on stability of cutting side slope and Its control measures ZHOU Zhi-guo FU Bi-chang ZHOU Zhi-bin(60)
[亚当斯和埃扎瓦]对延展心灵的刻画预设一个事先形成的、装备了内在心灵表征的认知主体,该主体与独立于内在表征的外在世界发生因果互动。因此,[对延展认知的质疑所提出的]问题就变成了说明该认知主体如何将环境成分装置在认知装置中的问题。而实用主义者[即生成主义者]则会质疑为什么要预设认知主体要独立于环境,或者仅与环境发生因果关系。在实用主义者看来,有机体与环境并不是仅仅通过因果关系相关联的两个事物,而是相互构成了一种有机体—环境的关系。一个有机体并不是与环境耦合之前的一个认知能动者,环境是造成该有机体成为有机体的本质性的和构成性的成分。更为具体地说,有机体的认知能力是在与环境中所具有的结构相互耦合(相互调和或操纵)中转化形成的。① Shaun Gallagher,Enactivist Interventions——Rethinking the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60.
(CCEs)社会性因素是知识的产出、知识的内容形成和知识的辩护过程中的构成性因素(constituents)或扮演着构成性(constitutive)角 色。
强版本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上面提到的CCE的四个规范。这四个规范都是针对科学共同体的社会性规范,而正是这些社会性规范担负起保护科学知识的客观性的知识论任务,因此成为科学实践中的知识论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它们本身也是知识论规范,是科学知识产生和辩护过程中的构成性因素。朗基诺区分了两种价值:一是构成性价值(constitutive value),另一个是语境价值(contextual value)。构成性价值是指那些建立在对科学目的的理解之上的价值,如真、预测、说明力、简单性等。这些价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科学实践和科学方法接受原则的构成性资源。而语境价值则是指属于科学实践环境中的个人、社会和文化价值。① 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4. CCEs意味着一些语境价值在特定的实践要求中可以成为构成性价值。CCE的四个规范就是这种情况。它们是规范科学共同体行为的社会性规范,但是,朗基诺指出一个科学共同体如果遵循CCE规范,那么它将会比不遵循CCE规范的科学共同体拥有更多的资源捍卫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因而,CCE规范也是构成性规 范。
许多学者接受CCEw却难以完全认同CCEs。例如,在一份对CCE最早的书评中,富兰克林(Allan Franklin)表示:“朗基诺正确地强调并展示了社会和文化价值渗入到研究资助与探求的决策中。但她举出这些价值进入到辩护语境的例子并没有说服我。”② Allan Franklin,“Review on Helen Longino’ 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The British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3,No.2,1992,p.285. 在对《知识的命运》的书评中,杜普雷(John Dupré)高度认同朗基诺对社会因素渗入科学研究中的知识论过程的论证,然而,对CCE规范则坚持认为它们是社会学而非知识论规范。③ John Dupré,“Reconciling Lion and Lamb?”,Metascience,2003,Vol.12,No.1,p.226. 这些学者的态度并不令人惊奇,因为CCEs要强于CCEw,接受CCEs意味着接受CCEw,但反之则不必然。因而,朗基诺给出的支持CCEw的论据,即证据关系的价值渗透,并不能成为支持CCEs的直接论据。朗基诺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的第四章中,给出了支持CCEs的论据,其结构大致如下:如果支持CCEw论据成立,即如果使得某一事态成为证据的过程必然地相对于不同的背景知识,而背景知识又一定具有社会性和多元化的特征,那么,我们就会面临着如此理解的科学如何能够满足对客观性理想(the ideal of objectivity)的追求问题,因为“如果没有决定或修正背景知识的绝对的和非随意的手段,我们看起来就不具备阻挡主观性影响方式”① 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61.② 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2. 。然而,一个科学共同体完全可以通过CCE规范所规定的批判性过程,以非随意或客观的方式对背景知识进行辩护、修正或扬弃。CCE规范的确是社会性规范,但由于它们是维护科学知识客观性的必要资源,因而应当被看作为知识的产出、知识的内容形成和知识的辩护过程中的构成性因 素。
对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最主要的质疑,大多是围绕着辩护CCEs的论据展开的。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不妨将这个论据更为清晰地重构于 下:
(D4) 一些学者接受(ASC-2),但对(ASC-3)持保留态度,因为他们尽管认为社会性因素是达成科学客观性理想的必要资源,但并不同意CCE规范是唯一或最好的路径。③ 朗基诺在《知识的命运》第六章中讨论了三个例子:所罗门的社会经验主义(Miriam Solomon,Social Empiricism,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2001)、劳斯的科学实践哲学(Joseph Rouse,Knowledge and Power: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7;Engaging Science,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和富勒的社会知识论(Steve Fuller,Social Epistemology,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8;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Its Discontents,2nd edition,New York London:The Guilford Press,1993)。
(ASC-1) 如果CCEw正确,那么具有语境主义和多元主义特征的科学实践将面临如何满足客观性理想的问 题。
按:“悖與”字,涵芬楼、三家本原作“荐興”。“悖與”形近误录。《尔雅》:“荐,再也。”“荐興”谓再兴盛也。
(4) 相互交流与批评的各方拥有适当平等的(tempered equality)认知权威。① 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pp.76—79;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2,pp.129—132.两书对四个规范的描述略有不同。
本文首先要指出的是,一位读者可从朗基诺的CCE中读出强弱两个版本,而这两个版本的差异引发了对CCE的一系列重要的质疑。我们先看弱版 本:
具身认知中生成进路的基本观点是心灵与身体及相关环境是相互生成的。③ 生成进路的早期文献见Francisco J. Varela,Evan Thompson and Eleanor Rosch,The Embodied Mind——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revised edition 2016(first edition in 1991),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当代进展除后面引述的加拉格的研究外,还可参见Richard Menary(ed.),Radical Enactivism——Intentionality,Phenomenology and Narrative,Amsterdam/Philadelphia: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2006;Daniel D. Hutto and Erik Myin,Radicalizing Enactivism——Basic Minds without Content,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2013。 从这个观点出发,ECs以及延展认知是很自然的结果。加拉格回应上述对ECs质疑的基本策略是否定内在心灵和与特定心灵相应的身体与环境是事先给定的(pregiven),坚持心灵内容和认知功能与使其成为可能的身体(包扩大脑)和环境是相互生成的(mutually enacted)。相互生成性的概念为ECs和延展认知提供了新的本体论资源,以理解为什么一部分身体和环境因素可被当作心灵和认知的构成性部分。加拉格指 出:
(ASC-4) 遵循CCE规范的科学实践是一种强版本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s。
(结论)追求客观性理想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应坚持强版本CCEs。
在《知识的命运》中,朗基诺对ASC进行了更为精致化的处理。首先,她区分了知识的三种含义,即知识生产实践、知识内容和知道过程。更为宽广的知识概念避免了只关注知识结果的传统知识论而忽视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认知主体、社会条件和历史性语境的局面。其次,朗基诺指出,一个阻碍我们接受CCEs及其论据ASC的重要原因是合理性—社会性二分,根据这个二分,知识论过程不能同时既是认知合理的又是社会性的。一旦我们抛弃这个错误的二分,我们就会找到将社会性说明资源引入科学的知识论中的合适的方式。②更为一般性地,朗基诺希望对二分的抛弃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具有社会性和多元性的科学实践可以通过CCE规范,而不仅是依赖经验证据对理论的支持关系,来建立知识的客观性。然而,朗基诺的工作并没有打消学者们对CCEs的质疑,这些质疑集中在ASC上。不难看出(ASC-1)和(ASC-4)并不具有争议性,它们表述了两个事实。质疑主要来自(ASC-2)和(ASC-3),以及与其相关的各种组合。我们大致可将这些质疑分为四 类。
(D1) 一些具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学者直接否认(ASC-2),认为对客观性理想的追求是现代社会人为制造出来的幻觉。③ 这些学者包括朗基诺在《知识的命运》第二章中讨论的一些使用社会学资源来研究科学的学者。在哲学领域里罗蒂可以归为此类。本次论坛中孟强的论文持有类似的观点。
我是临时工,他是领导。我月薪2000,他月入20万,我们人均收入10.1万;我的宿舍10平方米,他的别墅290平方米,我们人均住房面积150平方米;我一餐8元,他一餐8万,我们人均每餐消费4万;我有80元的单车,他有80万的奥迪,我们人均40万的座驾;我是光棍,他有1个老婆9个二奶,我们人均5个女人——谁还敢说中国人不幸福?——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
(D2) 一些学者如基切尔(Philip Kitcher)和戈德曼(Alvin Goldman)等承认科学应当追求客观性理想,即承认(ASC-2),但反对(ASC-3),因为他们坚持使用方法论个人主义而不寻求社会性资源来达成客观性理想。① Philip Kitcher,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Science without Legend,Objectivity without Illusions,New York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Alvin Goldman,“Psychological,Social and Epistemic Factors in the Theory of Science”,in PAS 1994:Proceeding of the 1994 Biennial Meeting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Philosophy of Science Association,pp.277—286;Alvin Goldman Knowledge in a Social Worl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9.
(D3) 一些学者接受(ASC-2),但对(ASC-3)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为CCE规范存在缺陷,难以说明科学史案例,或难以对应当下的科学实践。② 如戈德曼认为宗教思想也能满足CCE规范(Alvin Goldman,“Knowledge and Social Norms”,Science,New Series,Vol.296,No.5576,2002,pp.2148—2149);所罗门认为科学革命时期的许多科学研究并不遵 循CCE规 范(Miriam Solomon and 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of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005,Vol.36,No.2,pp.211—222);品托认为CCE规范难以对应科学的商品化和私人化倾向(Manuela Fernandez Pinto,“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Globalized Privatization:Uncovering Some Limitations of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7,No.1,pp.10—17);本次论坛中罗琳(Kristina Rolin)和英特曼(Kristen Intemann)的论文分别质疑不加修正的CCE规范难以对应科学异议和科学多样性的复杂情况。
现阶段,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迎来新一波消费浪潮,从而致使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主流观念更侧重于提升经济效益,致使缺乏政工工作的重视程度与扶持力度。而事业单位出于其主要由国有资产创立,主要一定公益性质,因此单位经济效益并非为首要运营目的,然而现阶段少部分事业单位实际运营情况为,事业单位管理层与大多数员工较为重视取得经济效益方向的各项成绩,在事业单位长期运行过程中,实际发展方向与预期有所偏差,然而,良好有序开展的政工工作帮助事业单位明确、引导了正确发展方向,并推进了事业单位整体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对CCEs的论据,Argument for CCEs,以下简称“ASC”)
这些对ASC的质疑直接削弱了人们对强版本CCEs的信心。朗基诺对这些质疑也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过回应。然而,其回应基本上是零散与局部性的,即使在对合理性—社会性二分的批判的帮助下,也不足以驱散这四种质疑。本文将使用当代认知科学的资源,提出一个统一和更为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些质 疑。
以15个蛋白为研究对象,分析这15个蛋白的互作网络,除了上述的15个蛋白外,还有另外12个蛋白共计27个蛋白一起构成了蛋白互作网络,具体见图1。
二、具身认知的两个版本
当代认知科学的一个重要进路是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以下简称“EC”)。它的基本立场是,认知不能仅通过大脑中心灵运作与功能来刻画与理解,还需要加入大脑和环境因素。④ 具身认知有许多研究成果,全景式的展示可参见Lawrence Shapiro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Embodied Cognitio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Taylor and Francis Group,2014。 与我们所讨论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类似,具身进路也有强弱两个版本,其弱版本 是:
(ECw) 一部分身体(包括大脑)与环境参与了心灵的形成与运 作。
而强版本则坚 持:
(ECs) 一部分身体(包括大脑)与环境是心灵的形成与运作的构成性因 素。
强版本比弱版本更具有争议性,ECs蕴含着ECw,反之则不存在蕴含关系。两者都承认认知过程依赖身体与环境,但对如何理解依赖关系则有不同的看法。弱版本ECw首先预设了内在心灵与外在身体及环境之间清晰的划分,并认为心灵对身体与环境的依赖是一种因果依赖关系。按照亚当斯(Frederick Adams)和埃扎瓦(Kenneth Aizawa)的说法,ECw“坚持认知过程是在受身体和环境因果影响的意义上依赖于身体和环境”,而强版本ECs则试图“从认知过程与脑—身体—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中挤压出它们之间的构成性关系”。① Frederick Adams and Kenneth Aizawa,The Bounds of Cognition,Malden,MA:Blackwell Publishing,2008,p.175. ECs的一个典型代表是延展认知理论。② Andy Clark,Supersizing the Mind,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Richard Menary(ed.)The Extended Mind,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The MIT Press,2010. 该理论坚持认知过程并非只发生在大脑之中,而是跨越了大脑、身体和环境,延展到一旦缺少就难以使特定的认知功能得以进行的身体与环境资源,比如,帮助人们进行数学验算的纸笔,帮助人们记忆的笔记本,引起视觉运动视差的头与身体运动等。亚当斯和埃扎瓦指出,以延展认知理论为代表的ECs会面临一系列质疑。例如,ECs难以解释大脑内认知与跨越大脑的认知在本体论地位与说明力上的差别;ECs试图从大脑之外的某些因素与某一特定的认知过程具有耦合性的因果关系的事实中,推出我们可以把这些大脑之外的因素当作该认知过程的构成性因素的推理难以成立;ECs难以建立认知的标志等。如何对应这些质疑是ECs的重要任务。本文对此不拟深究,而是拈出生成进路中加拉格(Shuan Gallagher)对ECs辩护策略,以便在后面借用于我们对CCEs的辩 护。
我住院期间,老秦不仅照顾我,还照顾我家。我家大门坏了,不挡风。他看见了,不管爸妈同不同意,就把门拆了重做。那个门本来很宽,按说也不用那么宽,进人又不进牛。我心想,要是把门口挡起来一部分就好了。结果,老秦修好后,我一看门口果然被挡起来一部分,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成我肚里的虫啦!剩下的部分,他做了个推拉门,安上了玻璃,美观又暖和。门修好了,他又去我家的地里打禾,就是割稻谷,干得顺脖子淌汗。天擦黑了,他什么也不说就走了。第二天他又回来接着干,直到把禾收完。
选取我院2014年2月~2016年6月收治的KOA患者9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45例。两组一般资料经统计学处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然而,CCE也有其强版 本:
如果心灵、身体(包括大脑)和环境相互生成而构成人们的认知,那么,亚当斯和埃扎瓦所提出的对ECs的质疑也就自然消解了。首先,大脑内认知与跨越大脑的认知在本体论层面上是相互生成和互不可缺的,因而不存在亚当斯和埃扎瓦所以为的事先给定的差别。其次,相互生成关系使我们可以从大脑之外的某些因素与某一特定的认知过程具有耦合性的因果关系的事实中,推出这些大脑之外的因素是认知过程的构成性因素。再次,对ECs来说,认知的标志并不是认知生成之前事先给定的,而是心灵、身体(包括大脑)和环境相互生成的具体过程中产生或涌现出来 的。
三、对CCEs生成进路的辩护
上述生成进路对具身认知的强版本ECs的辩护策略也可以被借用来为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的强版本CCEs进行辩护。从生成进路的视角出发,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因素和科学家们在研究中的认知过程不应被看成是事先给定的,而是相互生成的。将规范性的社会因素和科学家们的认知过程看成是事先给定的,科学实践就展现为如下景象:一方面,科学家们采用合理的科学方法获取为真的信念,尽管有时社会性因素会引诱他们偏离正确的方法;另一方面,相关的社会性因素遵循着由社会团体所采纳的社会性规范。换言之,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维度和知识论维度分别由不同的本体论资源来说明。在这个景象中,作为个体的科学家被当作事先形成的理性能动者,他通过与外在世界的因果互动获取内在表征。对该理性能动者的认知过程的理解独立于社会、文化、技术和物质环境,尽管该认知过程可受到这些环境的影响。因而,在讨论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因素与科学知识的产生与辩护中的知识论维度之间的关系时,问题就变成了如何将科学家们的认知过程嵌入社会性的语境和背景知识 中。
而当我们将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因素和科学家们的认知过程看作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互相生成的,科学实践的景象就发生了重要改变: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因素被理解为由科学家们设计、建构、应用和修改的规范性资源;科学家们则来自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背景,他们迫切地需要相互交流与讨论,而这些交流与讨论的方式需要遵循特定的社会性规范才能保证其有效与明智;同时,正是因为以不同的方式积极参与设计、建构、应用和修改相应的规范性资源的进程,科学家们才被看作是负责任的、有能力的和有潜力的。用加拉格的话说,我们不应预设科学家们在认知和知识维度上独立于环境,或与环境仅产生因果联系。在生成主义者看来,作为认知主体的科学家与社会环境不是两个仅通过因果关系相关联的相互独立的事物,而是相互构成了一个科学家—社会环境的关系。科学家并不是一个在与特定的社会环境相互耦合之前就已经给定的认知主体,社会环境是使得科学家成为科学家的本质性的和构成性的成分。更为具体地说,科学家的认知能力是在与特定社会环境中所具有的结构相互耦合(相互调和或操纵)中转化形成 的。
否定科学实践中的社会因素和个体科学家是事先给定的生成主义策略要强于朗基诺对合理性—社会性二分的否定,这是因为前者蕴含着后者,而反之则不成立。换言之,坚持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规范与知识论规范的相互生成的特征意味着社会性规范不应该与知识论规范互不兼容,但是社会性规范与知识论规范的兼容性并不意味着两者相互生成。因此,生成进路为强版本的批判的语境经验主义CCEs提供了更强的辩护资源,这可以从它如何为ASC提供帮助上看出 来。
在第一节中,我们看到有四种对ASC的质疑。第一种质疑D1认为科学无需坚持(ASC-2),即对客观性理想的追求。朗基诺通过对合理性—社会性二分的否定部分地回应了D1。她指出,正是因为一些学者错误地以为合理性规范与社会性规范互不兼容,在承认科学的社会性特征之后,转而放弃对客观性理想的追求。一旦否定合理性—社会性的错误二分,这些学者放弃客观性理想的理由就不成立了。朗基诺的这个观察是正确的,尤其是对科学元勘中极端相对主义立场形成了十分有效的批评。但D1否定对客观性理想的追求还有其更为深刻的、来自后现代主义的理由。根据这个理由,客观性理想是一种现代主义的幻觉,对其幼稚的理想主义的追求注定失败,而且之前的所有追求也都未成功。对这个更深刻的理由,对合理性—社会性二分的否定难以处理,而生成进路则能够给出有效的回应。生成进路可以回应说:即便之前追求客观性理想的尝试因为过于简单化或理想化而未能成功,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的追求就一定失败;如果科学家们的认知能力与科学实践环境中的社会、物质和技术等因素相互生成,那么,我们有理由期望未来对客观性理想的追求会更加适用,也更加现实。生成进路要求我们放弃脱离科学实践的先验原则来追求客观性标准,从科学史的经验与教训中,从科学实践的社会、物质和技术等资源中寻求更为适用、更为现实的客观性标准。这种自然主义而非先验主义的方式,提供给科学工作者们尽管可错但却可靠的增进客观性的手段,其中包括CCE规范。这些手段并不能保证排除一切主观性因素的干扰,宣称一旦应用这些手段,就可正确无误地获得客观性。但如果一个科学团体应用这些手段,与不应用这些手段相比,该团体会更加接近客观性。① 这就是为什么朗基诺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讨论CCE规范的一节中使用“客观性的程度”(Objectivity by Degrees)作为标题(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p.76)。
D2的支持者如基切尔和戈德曼等赞同对客观性理想的追求,但坚持使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而不是社会性资源来获取科学的客观性。基切尔和戈德曼都承认社会性因素不可避免地参与到科学实践的过程中,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支持弱版本CCEw。但他们所采纳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反对强版本CCEs。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可以从不同角度予以质疑。比如,所罗门(Miriam Solomon)指出科学合理性不能还原到科学家个人的推理过程中,因为科学合理性的一些重要部分只能用群体为单位进行说明。② Miriam Solomon,Social Empiricism,chap.7. 所罗门的研究成果与生成进路很是契合,可以当成支持生成进路的一个具体案例。朗基诺对基切尔和戈德曼的方法论个人主义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提出了质疑,其中一些观察不乏真知灼见,在一些方面可以得到生成进路的支持与加强。比如,朗基诺指出,正是由于合理性—社会性二分的预设,戈德曼把社会性推理规则(如数量论题等)看成是科学家个人与其他个人进行因果互动后的结果,也使得基切尔把携带特定内容的集体状态看成是可以因果地由个人及其信念来定义的结果。③ 所谓“数量论题”(The Number Thesis)是指科学家更容易接受被数量更多的同侪支持的观点。 而一旦我们否定了合理性—社会性二分,就可以直接把社会性推理规则或携带内容的集体状态看成是构成性的认知能力与状态。④ Helen Longino,The Fate of Knowledge,p.47,p.54. 生成进路则为为什么把社会性推理规则或携带内容的集团状态看成是构成性认知能力与状态提供了说明,这是因为科学研究中的认知资源与社会性因素是相互生成的。又如,基切尔认为批判语境主义CCE所持有的社会方法论不应与个人主义不兼容,因为要预设能够执行CCE规范能力的认知主体。⑤ Philip Kitcher,“The Third Way:Reflections on Helen Longino’s The Fate of Knowledge”,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9,No.6,2002,pp.551—552。与此类似,比德尔也认为朗基诺把科学家们看作类似密尔的政治自由主义社会中的个人,因而无法避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Justin B. Biddle,“Advocates or Unencumbered Selves?On the Role of Mill’s Political Liberalism in Longino’s Contextual Empiricism”,Philosophy of Science,Vol.76,No.5,2009,p.613)。 对基切尔的这个观察,朗基诺指出CCE并没有取消科学家个人的概念,但仍需要避免方法论个人主义,这是因为在科学实践中,科学家们并不是“知识论层面上自我充足的个人”(epistemically self-sufficient individuals),而是不可避免地拥有社会性。① Helen Longino,“Reply to Philip Kitcher”,Philosophy of Science,Vol.69,No.6,2002,p.574. 生成进路则为为什么科学家们不是知识论层面上自我充足的个人提供了更为深层的论证。从生成进路的视角出发,科学家们不是独立于环境的、事先给定的认知能动者,他们在与环境的因果互动后获取了相应于外在世界的内在的心灵内容。科学家们是与相应的社会、物质和技术环境相互生成的结果。他们所拥有的对外在事物的心灵内容,是知识论规范和社会性规范共同运作下的产物。其中知识论规范制约着科学家们对经验证据的使用,社会性规范制约着他们之间有效的批评互动实践。因此,在CCE中科学家的概念并不预设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是持有强版本CCEs的立场。总之,生成进路可以联合所罗门的论据,为CCEs提供比朗基诺建立在对合理性—社会性二分的否定之上的论据更为有力的辩 护。
D3的支持者质疑CCE规范难以在科学史中找到足够的支持证据,或者难以对应当下的科学实践。比如,所罗门指出在科学革命中,CCE规范没有起作用。朗基诺曾说过,在科学革命初期出现的以真理持有者自居的女巫追捕者们未能遵循CCE规范,因为他们拒绝通过公开批评的渠道来听取女巫们对世界的不同看法,因此,他们在迫害女巫的运动中无法获得对相关事件的正确知识。然而,所罗门认为当时的女巫追捕者们有许多是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遵循着当时科学界共有的规范,不缺乏追求真理的真诚。如果他们被CCE规范排除在知识范围之外,那么大多数科学革命时代的科学家也都会被排除在知识范围之外。② Miriam Solomon and Alan Richardson,“A Critical Context fo Longino’s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36,No.2,2005,pp.213—216. 再如,品托(Manuela Fernandez Pinto)认为,当代科学日益受到商业化和利益私人化的侵蚀,这种情况使得要求公共性和公开性的CCE规范变得越发地难以应用。③ Manuela Fernandez Pinto,“Philosophy of Science for Globalized Privatization:Uncovering some Limitations of Critical Contextual Empiricism”,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47,No.1,2014,pp.10—17. 对于这类质疑的各种具体案例,朗基诺试图在技术层面上分别找到消解策略。而生成进路则可以对这类质疑予以更为一般性的回 应。
采用孟加拉红培养基[18],分别接种10-5、10-6、10-7、10-8 四个稀释梯度的悬浮液,将接种好的培养皿于30 ℃培养24 h后进行酵母菌计数。计数时选取培养基上湿润、光滑、不透明、大而厚的菌落进行酵母菌计数。
1)陕南柑橘、秦岭北麓猕猴桃幼园和渭北南部红提葡萄园、渭北北部和陕北苹果幼园,都要在树干基部培堆高30 cm左右的土堆,避免根际受冻。
从生成进路的视角出发,CCE规范并不是科学客观性的充分必要条件,并不因为一些历史中的反例和当代实践中的困难而失去其规范性。在生成进路看来,CCE规范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建立在理想德性(ideal virtues)之上的规范。④ 这里的“理想”(ideal)一词,并不是指完美的、与现实不符的虚构,而是近于韦伯的理想型(ideal type)概念中的理想,该理想是人们在考察诸多(社会)现象时,对其中某些而非全部特征或样式形成的观念化和理论化的分析结构[Max Weber,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Science(1903—17),edited by Edward A. Schils and Henry A. Finch,New York:Free Press,1997,p.90]。因而,这里的“理想”一词并没有脱离现实的意思,而是指现实中已经发生过的,并因此证明了可以在现实中更为大量、更有规律地发生的可能性。 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使用各种理想德性表达自己对世界的规范性想法。比如,我们都能够以某种方式持有对什么是好大学应该具有的理想德性的理解,尽管我们的理解或多或少会有所不同。因而,我们会说大学经商或过多的商业化不是一个好大学应该做的,而注重培养教学和研究水准则是好大学应该做的。QS和《泰晤士报》大学排名标准也是由某些理想德性如学术声誉、研究质量、国际化程度等构成的。建立在理想德性之上的规范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理想德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历史性的,即理想德性是历史生成的产物。不同的历史时代对同一事物的理想德性会对应于当时的需要而有所不同。中世纪大学的理想德性更加注重神学目的和对古典文化的保护和传播功能,20世纪初期我国的大学则强调为国家民族储才的功能,而今日的大学则更强调学术水准的培养。二是理想德性不是事先给定的,而是人们为了获取更好的存在和实践状态而主动建构的产物。人们之所以对事物形成理想德性,是因为面对现实中的缺陷与困境,人们从历史教训和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事物拥有特定的理想德性作为行动的目标来规范未来的行为,以期改善现实状况。科学家们正是看到社会性的、多元的当代科学实践需要通过加强公共性、宽容性和交流性来增进科学客观性,才形成了CCE规范中的理想德性,并希望通过提倡CCE规范来提高科学实践的质量与效 果。
具有历史性和主动建构性特征的理想德性不必完全与历史事实和现实实践相符,就像许多大学并不能完全符合人们对好大学的期盼那样。许多大学达不到好大学的标准,并不意味着规范好大学标准的理想德性不成立。同样,历史和现实实践中的一些事实与CCE规范不相符,并不意味着CCE规范不成立。科学革命过程中的确有许多事件并不符合CCE规范,但这并不奇怪,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对好科学的标准与今日的标准自然不会完全相同。与所罗门的指责相反,我们其实可以从科学革命给予的经验教训中更好地理解坚持CCE规范中的理想德性的重要性。比如,伽利略花费许多精力争取与经院哲学家们公开、平等地讨论的机会与权力。① Mario Biagioli,Galileo Courtier:The Practice of Science in the Culture Absolut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又如,霍布斯在与波义耳对真空泵实验的争议中,要求更为公开和更为广泛的实验见证者,以及对不同意见者更为宽容的态度。② Steven Shapin and Simon Schaffer,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Hobbes,Boyle,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 对于日益严重的商业化和私人化对科学事业的影响,的确会使得CCE规范的运作更具有挑战性。但这个挑战并不意味着CCE规范的失败,从生成进路的角度看,它反而展示了CCE规范的重要性与急迫性。科学家正是要运用CCE规范来减少商业化和私人化对科学事业的消极影响,而CCE规范是对应这种消极影响的,也许不是唯一的但一定是最为重要的资源。实际上,朗基诺在《作为社会知识的科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CCE规范时,也正是要对应科学中的商业化问题。① Helen Longino,Science as Social Knowledge:Values and Objectivity in Scientific Inquiry, pp.86—89.
缅甸琥珀主要产自克钦邦密支那到德乃一带的康胡盆地[2],是缅甸北部与印度接壤的沼泽地带。矿区位于塔奈西南角20公里处,由达罗盆地和新平阳盆地组成的康胡河谷这个方向上第一座海拔250m的一座叫Noije Bum山上[3]。缅甸琥珀是被发现和利用最早的白垩纪琥珀,早在2000多年就进行开采作为工艺品。
以上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建立在理想德性之上的规范,特别是CCE规范是无法被批评的,而只是意味着它们不应像充分必要条件那样,通过简单地寻找反例就可以被推翻。批评理想德性的基本方法是检查遵循和拥有这些德性是否能够有助于达成提倡这些德性时的目的。因此,批评CCE规范的基本方法是检查一个遵循和拥有CCE规范的科学团体是否比不遵循或不拥有该规范的科学团体更有可能接近科学客观性理想。在这个意义上,D4形成了对CCE规范的严肃的批评。D4的支持者认为,存在着其他社会性资源去达成客观性理想,比如所罗门指出的以社会为单位的科学推理结构,劳斯所提倡的规范性科学实践,富勒所倡导的社会知识论等。在CCE与这些进路之间如何进行对比、评价和选择是十分复杂的工作,因篇幅限制无法在本文中展开。但从生成进路的视角看,这些进路与CCE并不一定是不兼容的。这些进路中的一些资源,如社会性推理结构、科学实践中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等,都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刻画和理解CCE中社会性因素与知识论和认知因素之间的相互生成的关系。② 例如,本次论坛中王不凡的论文就试图将技能性知识加入到CCE中。
四、结论
从上一节的分析可以看出,生成进路对强版本ECs的辩护策略一旦被借用过来为CCEs辩护,就将成为一个比朗基诺原始辩护更为有效的辩护资源。这一借用从方法论层面上展开,其有效性是在辩护的效果上建立起来的,并未对该辩护策略为什么会有效给予更多的说明。要想获取这个说明就需要在本体论层面展开生成进路对CCE的支持。本文无法进行深入的本体论层面上的探讨,但生成进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CCE的支持是更为基本的。如果心灵、身体和环境是相互生成的,我们就有理由坚持在科学实践过程中,知识论和认知过程不是如传统知识论认为的那样是纯粹内在的,而是多元的和社会性的,因为它们是来自不同理论、实践、物质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在与社会和环境的互动中展开的。因此,生成进路在本体论层面上对CCE的支持是下一步亟待发掘的课 题。
目前,中国正处在高速城镇化的进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民因城镇化失去了土地而成为失地农民。据估计,到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预计将超过1个亿。[1]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尽管在土地被征用的过程中会获得一定额度的安置补偿款,但是“仅仅依靠安置补偿款无法保障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2]。要解决长远生计,对于那些尚在劳动年龄段的失地农民而言,最好要能以非农就业方式重新就业。
中图分类号: B8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47(2019)01-0004-13
作者简介: 黄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科学院科技哲学创新团队成 员。
基金项目: 本文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作为一种自然化科学哲学的历史知识论研究”(项目编号:18BZX041)资助。
(责任编辑:肖志 珂)
标签:批判语境主义论文; 海伦·朗基诺论文; 生成进路论文; 具身认知论文;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