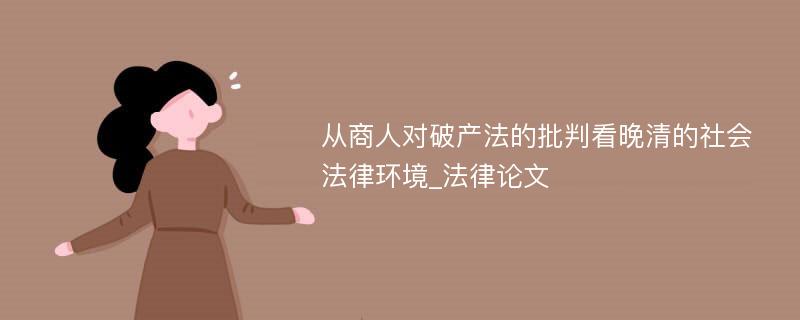
从商人对《破产律》的批评看清末的社会法律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对论文,批评论文,环境论文,法律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6)02—0120—07
一、《破产律》的颁布
中国社会在清末以前,由于商业不够发达,加之政府的重农抑商政策,未见有关破产法律的规定。长期以来,对欠债不还者,在法律上实行“以刑代偿”或债务奴役,如《唐律》规定,对“负债违契不偿”者,除规定赔偿外,还要处以笞杖刑,甚至徒刑;同时,《唐律》还允许债权人对违契不偿者,可强制扣押其财物,或令债务人及其户内男口,以劳役代偿债务,即“役身折酬”;直至清代,“役身折酬”制度才被禁止①。总之,在古代社会,由于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上并未产生对破产制度的需求,债务人即便不能清偿债务,在实践中也无破产的规定;以刑代偿、以劳役抵债和以其他财物抵偿钱债,为历来通行的做法;私债必偿、父债子还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为传统法律、伦理观念以及民间习惯公认的准则,不存在破产免债的概念。
鸦片战争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一批新式工商企业。这些新式企业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和影响下,越过工场手工业阶段“仿西国公司之例”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企业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较为复杂,要求有相应的法律来加以调整。但当时通行的《大清律例》“成于三百年前,主为刑法之规定,而户婚、田土等类关于民法者极少;至商法则全无规定,间有如市廛法、牙行法、度量衡法等亦止为国家对于商人之禁令,非商人对于商人之平衡。民间钱债交涉向视为细故,官置不理;商民涉讼官无可援之例,其判决例案多出于任意”[1]。处理此类案件无一定章,随意性很强。随着国际国内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和商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商人因经营失败,资本亏折,不能清偿债务的个案日益增多;虚设公司行铺、卖空倒骗之案也一再发生,有的甚至“朝集股本,暮既卷逃;昨方下货,今已移匿栈单房契,轻赉远遁。于是倒盘贬价,弊端百出,贻害无穷”[2](1483页)。各地倒骗现象猖獗,却无相应的法律来加以调整处治。
针对此情况,刑部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十月间议定“奸商倒骗定例治罪专条”,申明“如有侵蚀倒闭商民各款,立即拘拿监禁,分别查封寓所资财及原籍家产,仍押令家属勒限两个月完竣”;根据其诓骗钱财的数目及还债情况,治罪专条自枷杖以至军流极之永远监禁不等,分别予以严惩[2](1484页)。 但倒骗之事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随着商情变幻,倒骗之局愈出愈奇,如光绪三十一年四月(1905年5月),商部有如此奏折:“现今市面日紧,各省人心风俗日益离散,奸商倒欠之案愈出愈奇。……嗣后遇有商人词讼,乘公讯为理直。……并查照光绪二十五年刑部议复两浙总督奸商倒骗定例治罪成案办理。”[3] 总之当时每每此类个案发生时,因无破产法规可资依据,多由商人团体协议清理,或由地方官吏强制执行。而破产情形多种多样,有确实是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的,也有奸商诈称亏损,倒骗财产的,处理颇为困难。因此,颁布出台有关法律法规来清除因破产所生之时弊,取缔破产者的诈亏倒骗行为,成为当时的紧要大事之一。
清末的“新政”为商法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环境。光绪廿九年(1903)三月,清政府要求载振、袁世凯、伍廷芳等“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4]。很快在当年七月设立商部,成为清政府制定商事法及相关法律的主要机构之一;廿九年十二月即1904年1月, 颁布《钦定大清商律》,包括《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此后,清政府又颁布实施《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事法规;光绪卅二年(1906)四月颁布《破产律》,补续《钦定大清商律》的内容。《破产律》共有9节69条。第一节呈报破产; 第二节选举董事;第三节债主会议;第四节清算账目;第五节处分财产;第六节有心倒骗;第七节清偿展期;第八节呈报销案;第九节附则②。条文虽少, 但从呈报破产到债权清偿及破产终结等重要的破产过程都予以涵盖。虽然从清政府的立法意图看,似有意仅适用于商人,视《破产律》为商律的补充,但是以单行法的形式颁布,并且鉴于“今中国民法尚未订定,其有虽非商人破产之案,除依臣家本、臣廷芳编订之诉讼法办理外,其余未赅载者,应准地方官比照本律办理”[5],对商人和非商人均适用,“凡虽非商人,有因债务牵累自愿破产者,亦可呈明地方官请照本律办理”(第8条)。
二、商人的批评意见
在《破产律》颁布之前,已经出台了如《公司律》之类的一系列商事法规。这些律令出台后,受到当时商民的批评,其中最主要的批评集中在相关法律法规缺乏对中国商事习惯的调查与融合,不合中国固有商业习惯等等。商部也逐渐认识到:要制订适合中国社会的商事法令,光靠从外国移植是无法奏效的。在此后修制商事法令法规时,商部开始比较重视商会的意见,并请商会协助调查全国各地商人的商业习惯等。在颁布1906年《破产律》时,商部官员即指出:臣等“调查东西各国破产律,及各埠商会条陈、商人习惯,参酌考订,成商律之破产一门”[5]。但是,《破产律》颁布后却受到来自于商界更为激烈的批评,从1906年6月开始,上海、镇江、宁波、汉口等城市的钱业商人,纷纷指驳该律,并通过当时的商部顾问官张謇和上海商会向商部反映意见,认为该律是窒碍难行的法律,请求暂缓施行。综合商人们的意见,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商人们认为该律照搬外国律令,不合中国实际情况、民商事惯例处颇多,不妥当之处也随处可见。如第45条有“破产之商不得涉及其兄弟伯叔暨妻并代人经理之财产”的规定,商人们认为,“此条杂于西律不能行诸中国。考西商财产多系注册,其间有父子夫妇不同产而兄弟伯叔侄无论矣;其分授子女之时必由律师签字以为佐证方能作准。今中国商人财产素无注册之例,且多有兄弟伯叔子侄合数世而同居者;至夫妻同室共产尤为常事。……苟破产者托名寄户其中夫产妻产又何法以办之耶”?因此该条规定并不适合当时以家族为本位的中国社会,除非“必有清查财产法而后破产法可行之无阻也”[6]。又如第27条规定“该商与人买卖借放之事,虽已订立契约尚未交货付银,经呈报破产均应作废”,商人们认为该条有违商家之通例,历来商人做买卖,“但问契据之有无,不计银货之交否,此商家之通例而货殖之特权也”,如果呈报破产契据即作废,则奸商“恃有此律乘百物腾贵之际,为孤注一掷之谋,月初订约,月底为期延至下旬市情暴著,意中则万金可致,算失则一钱不名”,呈报作废之言对于工于倒骗者来说,不仅有违传统商业重契约的惯例,而且为他们倒骗欺诈提供了可乘之机,“其为败坏商务岂待言之”[7]。
(二)商人们认为该律有关规定对债务人惩罚不力,忽略了债权人利益;某些条款流于形式。如《破产律》第48条规定,“倒闭之商若将财产偿还各债后实系净绝无余,并无寄顿藏匿情弊,应由董事向各债主声明,准于未摊分以前在财产项下酌提该商赡家之费,约敷两年用度以示体恤”。商人们认为此条体恤倒闭之商“恩至而义尽”,而且“该商破产之时此外有无寄顿隐匿仓促之间实不容易查察”,尚有漏洞可钻;而债权人不仅于破产时“同受其亏,今于变产项下不论其成数之多寡又复抽提赡家之费”,使其“更受亏难言矣”。因而他们认为体恤倒闭之商“可以有此办法,不可有此条例,更岂能限以约敷二年之期哉”[6]。又如第66条规定,“倒闭之商如查明情节实有可原,且变产之数足敷各债主至少十分之五,可准其免还余债,由商会移请地方官销案”。商人们认为“今如定例还债至十分之五准可免还余债,然则放款者大有寒心,相率裹足,凡一倒闭坐失一半之血本”,因此他们认为这些规定对债务人处理过于宽大,忽略了债权人利益,从而有欠公允,不利于商业的发展[6]。
(三)商人们认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相当不完善。就当时清政府颁布的有关民商事法律来看,仅有诸如《商人通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公司律》、《奖励公司章程》等内容,无相应的民事法律规定;而当时各国民法中之债权编财产编,多有法律之规定,而且“条绪多端”,都是为了求得财产之安全,促进经济的发展;当时有人就指出“在今日民法未立、权债未定”之时,“则疑破产律之不适于用者,亦固其所”[8]。从上述商人关于第45条的指驳中,即可看出中国当时有关清查财产法律之缺失,在社会财产尚无律师签字作证、银行支付、官厅登记诸办法的情况下,“一旦因商破产则其家之财产何从分别”,往往个人财产虽夫妻父子不能确知虚实,“盖必有清查财产法而后破产法可行之无阻也”[8];对有关担保法之规定也很不足,“担保有对人对物二种,债权法中之担保债务属于对人担保。吾国虽有其习惯而全属放任,此对人担保之不足恃也;物权法中之留卖权、先取特权、质权、抵当权等,属于对物担保。吾国既无留卖权与先取特权,仅有所谓质与抵当者,亦不知其所利用此对物担保之不足恃也。对于人如此,对于物如彼,以是吾国诈伪倒骗之案愈出愈奇,而社会之财产遂不能处于稳固万全之地位”[8]。
三、从商人的批评意见看当时的社会法律环境
第一,法律与传统习惯的关系问题。在清末《破产律》中,既有参照外国法律的方面,也有注重传统商业习惯的方面。从其体系来看,更多的是借鉴了日本1890年的破产立法体例。与日本1890年破产法相似,《破产律》没有分为实体、程序、罚则诸篇,而是不作区分,笼统分为9节。从其内容来看,有借鉴外国的,也有结合本国实际的,如关于破产机关,当时日本及欧洲各国都规定破产事件属法院管辖,由法院宣告破产是为通例,而清末《破产律》第1条和第8条规定,商会是破产机关之一,商人、非商人破产均需呈报商会及地方官,商会及地方官查明属实后将该商破产宣告于众;在《破产律》第三节“债主会议”各条(第17至24条)中,将负责“清理破产一切事宜”各项手续事务几乎都交给了商会主持。这是《破产律》的一大特色,也是考虑到当时中国商会势力比较强盛的结果。因此这获得了国民政府法律顾问法国学者爱师嘉拉的称叹:“该律虽尽量吸收欧美法律观念,同时且不离开中国固有习惯,尤以其保持商会实业之任务为最著”。[9](839页) 这是《破产律》注重中国固有商情的重要方面。
但从上述商民之异议及从商部官员的有关回复,我们可以看出外来法律与传统习惯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与矛盾。当《破产律》颁布后受到商人们的指驳批评时,商部回复曰“本部厘定此律,本为便商起见”,在编纂起草法律时,先征求了各商会及商务议员的意见,然后陆续汇齐,“始行参照起草,故此律大半均系采自各处条陈”,只有那些“虽为中国习尚而按之法理未甚允协者则酌量参用各国成例,以期补偏救弊”。他们认为,总的来说,该律“全体沿袭中国习惯者居多,采用外国条文者甚少”,并认为“各国法律虽称精美”,但“中国商民程度未齐,国家法律只能引之渐进”,否则将“致蹈过高难行之弊”[10]。由此可见,清政府在修订该律时,应该是注意了协调外国法律与本国法律传统习惯,考虑到了外来法律本土化的问题。
但是,从商人的反对意见来看,《破产律》似乎并未像商部官员所说的“全体沿袭中国习惯者居多,采用外国条文者甚少”。对此商部官员认为,中国疆域广大,行业众多,因而“不能仅凭一业之意见,一隅之风气遽为更张。此为一定不易之理;凡事难于图始,中国向无此律明文,商民骤见以为转受束缚,不能与向日习惯并行。其实立法本有深意,若沿用稍久亦即习为固然。征之各国立法之初,大率如是”[10]。从这段话来看,商民长期处于无商法的状态下,商业经营活动主要靠长期约定俗成的经商习惯及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来调节;在商法初定之时,如果商法与长期运用的习惯有异,商民当然有“以为转受束缚”的感受了,这确实也是对当时社会经济现实的真实写照;而当时作为参与经济立法工作的官员,面对纷繁复杂的各行业与各地区不同的商业习惯,不仅基本上罕能理解,而且对于西方法律的基本精神与原则也恐怕只是处于一知半解的认知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外来法律与本国传统习惯始终是相割裂的,不仅表现为立法过程中对外来法律的盲目照搬、排斥传统法律习惯,还表现为在法律具体实施过程中传统习惯排斥外来法律;如何协调好外国法律与本国传统习惯的关系,始终是清末民初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一个难以处理好的问题。
第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的缺失与疏漏。清末的民商立法,其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利权,加强中央集权,维持统治秩序,其实用功利思想是很明显的;因而侧重于纵向法律关系的调整,如制订许多行业法规、社会团体法规、奖励工商业的法规等,而调整平等经济主体之间横向法律关系、调整经济法律主体生产及消费等行为的法律法规却几乎没有,对经济主体如何行为、如何调整相互关系,并不在清政府关注的视野之内。就《破产律》的制定宗旨来看,是为了取缔倒骗,急救时弊。因而不仅关于破产的实体规定较疏漏,而且相关的民法、诉讼法等还未制定,许多关于破产的民事规定也多制定在破产律中,以致内容庞杂,体系混乱。这也是该律具体运作过程中窒碍颇多、引起争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各国的破产法规中,一般总是包含着实体法和程序法两类规范,而处理破产案件所适用的实体法规范,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实体规范,即在破产和非破产案件中均得适用的实体法律规范,例如物权法、债权法、担保法、公司法、合伙法、票据法、保险法、劳动法、税法等等法律中的有关规定;另一类是特殊实体规范,即仅适用于破产案件的实体性规范,如有关破产财产、破产债权、破产抵消权、破产免责等等的有关法律制度和规则[11]。而当时相关法律法规的缺失是很明显的;而即使是已颁商律中也缺乏足够的防范性规定,有诸多疏漏之处,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登记注册制度的不完备。我国几千年来,贱视商业,于商人之监督及保护,一概视为具文。开办某种商业,必须报部领帖,方准开办者,亦只以征收牙税为目的,“而于其一己之信用及公众之利害若何,概不注意”[12](25页);在清末近代工业刚刚起步、近代企业的特点及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所应遵循的规则还未被人们所熟知的情况下,要求所订商法尽可能放松限制,为近代工商业的设立和日常活动提供方便。清末商法适应这一要求,从中国固有商业习惯和各国商法中选取了大量的与商为便的规定。如在1904年颁布的《钦定大清商律》中,关于商业注册,规定一般商业注册与否,听其自便,法律不予以强制;关于商号,规定用本人真名或另起一号,听商人自便,法律不予强制;关于商业账簿,虽规定商人必须设置账簿,但不具体规定应如何记载,且不规定必须受官厅监督,等等;与《公司律》配套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在关于申请注册企业的验资和监督开业等方面也缺乏严格规定。
以上种种,如登记注册制度的不完备,为奸诈之徒日后的倒骗行为提供了机会;而相关民商事法律法规的缺失,又使得司法者在处理有关破产案件时缺少依据。因此有人建议“先编民法,将债权法担保法择要制定,使债权者得确切之信用,债务者无投机之侥幸”[8]。万一事出意外,宣告破产时,执行破产律能有民法之依据。这些不仅反映出清政府立法意图的偏差,立法尚无一定的系统性,而且说明当时的民商立法并未满足人们的实际需要,已经颁行的法律存在着若干漏洞,某些领域尚无法律调整,广大商民的利益得不到切实保护。
第三,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商民的法律观念意识程度、执法情况等所营造出的社会法律环境。20世纪初年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处于由传统转向现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社会结构方面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传统的家族模式依然存在;经济结构方面,自然经济虽已开始解体,但仍具有强大的力量,近代化的工商业经济体系还未形成。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体现在人们的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形态方面,传统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依然存在,缺乏形成近代法律正常存在与发挥作用的社会环境;反映在当时商民的法律观念意识上,其程度是不高的,他们需要先进的民商法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当新颁定的法律打破了旧传统及习惯势力维持下的利益平衡时,他们就无法理解和接受近代先进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某些法律理念和制度。《破产律》从法律上废除了“以刑代偿”、“父债子还”的传统法律观念,首次将西方的破产免责、债权人地位平等等先进的破产法理念和制度引入中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也是商民难以理解和接受的。从上述商民对《破产律》的批评意见来看,不无中肯、合理之处,但也反映出当时商民的法律观念意识程度。如从对第66条规定的反对意见来看,他们认为按照商人通行习惯法,“凡倒闭之商折成归还未了之项,往往邀集亲友书立兴隆字据交债主执掌;约俟倒户光复旧业再行补还”。此举虽也不尽人意,近乎自欺,但终使负曲借此了结,亦合权宜,按照此条要求“十成得五便免归还官案,一销脱身事外,试代债主设想恐非下怀所甘”,因此他们拟请用立兴隆书之习惯做法来销案,略平债主之气而愧奸商之心[13],这显然不是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来解决问题,而是欲以舆论和良心谴责的道德力量来惩戒债务人。当然我们不能通过解读某些片段信息、脱离特定语境而以现代破产理论、精神来衡量当时商人的法律观念意识先进与否,也不能苛求在长期传统法律习惯势力浸染下的商人们能有超前于时代的法律观念意识,但这毕竟是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综观商人们提出的意见,真正从法律角度进行指驳的条文寥寥无几,当时商部官员也这样认为,“虽有一二见到之处,而大半均未免过虑;又其立论无甚根据,并非法律家之言,故本部以为无足重轻”[10]。
执法的无力与偏差。当时的执法者仍狃于积习,对民商事案件的执行不甚重视。在农工商部的一篇咨文中这样说道:“有债务急于待理而各州县衙门届时犹有循例之举,悬牌特书农忙停讯,钱债细故概不准理,实足阻朝廷振兴商业之进步而生刁狡冀侥之私心。查职会自设立以来,统计光绪三十三年分理结钱债讼案八十起,三十四年分七十五起,其未经结者实止过半。……而衙门上下非钱不行,商民视为畏途,亦良有以。又有负欠巨款逃回原籍,债主呈请带账前往候质,商会据情移会地方官传案质明追缴,官亦出票而欠户贿嘱衙役瞒以远出,地方官亦以钱债细故不加深问,遂使商人血本无处追偿”[14]。这说明在《破产律》颁行一段时间后,官府对于钱债之事,仍然视为“细故”;按照规定,物权债权诉讼的结果,必然令败诉者对于胜诉者交付财产,为预防奸诈之徒预先毁损隐匿财产,各国诉讼法有假扣押之规定。而在我国,凡扣押之事,十有九成无效;被侵害权利者,费了许多精神财力,才得以胜诉,而即使胜诉也得不到完全之补偿;并且“豪猾之无制裁也”,在取消了“以刑代偿”之后,对豪猾倒骗者违法行为的制裁却没法执行,致其“藉此以自遁也,其甚者,负债巨万,而逍遥自若,豪奢如故,国法既不执行,社会亦无制裁,舆论亦少讥评”[15]。各地方官对钱债案件的不重视,对民商事案件执法的无力,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商民的积极性,也使得社会上的倒骗现象始终存在,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头。
四、《破产律》之被废止及后续
在《破产律》颁行后不久,先是在1906年7月商部宣布第四十条暂缓实行[16];第二年11月,农工商部又奏:“……嗣经各省商会迭次呈称,中国现时商智尚未大开,商业亦未齐同,恳请暂缓实行各等情。查,修律大臣沈家本等奏颁刑事民事诉讼法各省均未实行,而破产律与诉讼法实属互相关合,自应一律办理,现在宪政编查馆奏明设馆修订法律,特派专员编纂民法、商法诸法典,此项破产律应由臣部咨送法律馆统筹编纂,以免抵触。”[17] 许多论著据此认为该律就此归于废弃。而实际上有些地方,在处理破产案件时,还是在采用。当时大理院在该律废止后,“仍于兼顾商业习惯之中,间或援用其法理,以裁判破产之案件,而由其判决例,遂创立一种不完全之破产制度”[9](840页)。在1912年出版的《各省审判厅判牍》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判牍,如新民地方审判厅审理“亏欠巨额破产还债”案、“合股营业耗欠巨款按股勒追”案,安庆地方审判厅审理“积欠货款无力缴还伺隙潜逃”案等等,均有依据1906年《破产律》之规定所作出的判决。而这些案件判决时间已经是宣统年间了[18];还有如宣统二年十二月(1911年1月)法部在给修订法律大臣的一个咨文中说:“据黑龙江巡抚电称,现行刑律诈欺官私取财门内载,各直省商民开设公司钱铺等项有侵亏倒闭者,计数论罪,数至万两以上者,发新疆当差。查与前颁破产律第六节有心倒骗者科罪仅至三年以下之监禁轻重悬殊。现行刑律暨破产律均系钦颁,遇有此项讼案,应援用何律科断,请部示复等因前来。……本部未便卒复,自应片请贵大臣核明,严复过部,以便转咨该督可也”[19];在民国初年的《大理院判例要旨》序言中这样说道,“前清破产律虽经明文废止,关于商人破产只得适用地方特别倒号之习惯或一般破产条例”[20]。
由此可见,在当时,处理有关破产案件时,有不少仍然采用《破产律》来处理,也有仍采用“奸商倒骗定例治罪专条”以刑代偿的方式,还有不少以民间习惯来解决钱债问题。当然就此时的商业习惯来看,民间破产还债制度因受到商业文明之浸染,比较起古代有关做法来,还是有所变化发展。据民国初年对地方民事习惯的调查,如在湖北一些地区,有所谓“摊账”的做法,“债务人负债过钜,以所有财产摊还,俗谓之摊账”。摊账开始,通常由债务人邀同各债权人到场,提出摊还请求,也可由个别债权人邀集其他债权人共同向债务人要求摊还,还有个别地方摊账须经全体债权人同意。摊还时,债务人“有请求让利还本者,亦有尽产摊还者”;多数地方允许债务人“酌留财产,以资养赡”,将财产酌提十分之一二,以资安家,然后将余产和盘托出,由债权人公议分配;有的地方,则由债权人共同管理财产,双方邀请调停人,三面同算;还有的地方财产由各债权人“公议价目变卖,或公同管理,其清算亦归各债权人作主”。摊账完毕,债务从此了结。在一些地区,还有立“兴隆字为债务停止契约”,其用意是等到“兴隆后,再行偿还之谓”,有些地区“从债务人书立兴隆字之日起,债权人即应将其从前所立借券或票据退还,其利息亦即从书立兴隆字之日起停止”;还有一些地区,“书立兴隆字后,仅于其从前所立借券或票据之上,注明止息,并不退还,但兴隆后有只还本者,亦有稍付利息者”等等做法[21](第一编债权,第六类关于清偿之习惯);天津商会在处理和春号米庄倒闭案件时,“将商所有财产货账归为三行公摊,先交付银二成五,俟十一月内交五厘,共交三成。另立期票一成,四年分还,外写兴隆票一成,大家公允”[22](1080页)。立下兴隆字后,至于以后是否真能兴隆、真有能力还债,确实是不可预期的事情,但这种习惯做法清末民初在民间还是很普遍的,毕竟“终使负曲借此了结”,亦为合权宜之举。
而从倒骗案件的发生来看,却依然严重。如在光绪三十三年,两浙总督咨商部:“上海企业常有买空卖空情事,……前数年此风虽有,尚未长大。上年渐次放大,即有金店倒闭伙伴逃亡,并闻有因此自尽之事。……查买空卖空大干例禁,本道访查得实,亟应严行禁止”[23]。宣统元年,天津商会商董边峋为坑商倒骗案屡屡发生请商部严定律例事禀津商会文中称:“年来倾商之事层见叠出,以致牵碍各行商业倒闭时有所闻……年前营口商号东盛和倾骗各商银洋至数百万两之多,牵碍各行倒闭,东三省商务亦尽为之影响,其案情亦诚重且大矣。”[22](898—899页) 等等。可见从清末到民初,奸商买空卖空,倒骗钱财,始终是工商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一方面说明清政府欲以《破产律》惩治倒骗、急救时弊之目的未能达到,也说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亟需完善、系统的商法来加以调整。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由于传统习惯的根深蒂固,政府立法意图的偏差,商民的法律观念意识程度与执法情况等所营造出的社会法律环境的不健全,制约着包括《破产律》在内的近代商事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这也决定了该《破产律》只能作为清政府正式拟订商法之前的过渡形态,其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也不足为怪。
[收稿日期]2005—09—12
注释:
① 参见李志敏《中国古代民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42页;戴炎辉《中国法制史》,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324—325页;张晋藩《清代民法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② 登载《破产律》全文的载体有: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大清光绪新法令》(商务印书馆宣统二年版)第16册,第十类,实业;《商务官报》1906年第4期、第5期;《东方杂志》第三年(1906年)第7期;《申报》1906年5月30日,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