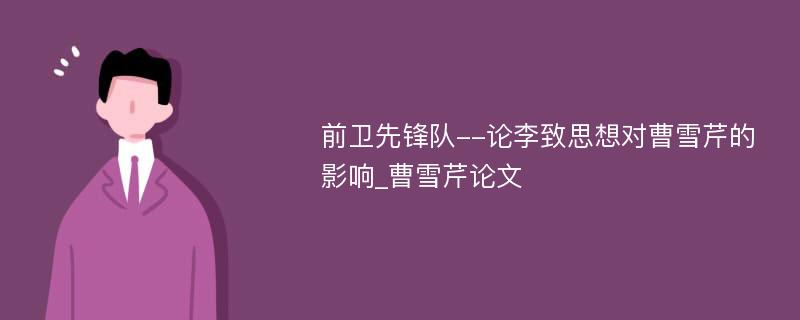
前卫与先锋——论李贽思想对曹雪芹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卫论文,先锋论文,思想论文,李贽论文,曹雪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00)03-0039-04
李贽生于1527年,卒于1602年,而曹雪芹生于1724年,卒于1764(或1763)年。以曹雪芹生年减去李贽卒年,曹雪芹后于李贽122年。李贽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叛逆者,其思想的前卫性是明显的。作为天才的诗人和先锋性的思想家,曹雪芹受到李贽思想的影响应当是毫无疑义的。但曹雪芹生平资料奇缺,要探讨曹雪芹和李贽思想的因缘联系,只能以他留下的残稿《红楼梦》(前八十回《石头记》及专家对八十回后佚稿的研究)作为文本依据。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说过:“从龚自珍等往上追溯,在启蒙思想家中,曹雪芹实在应该列为是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别伟大的一位。”[1]借用冯友兰先生的术语“接着讲”,我们可以说:从曹雪芹往上追溯,李贽是中国思想界“卓立在最前列的特别伟大的一位”。近来,有将“红学”向“新国学”提升的努力,[2]“新国学”的要义,是要为中华民族寻找一种既能承续传统又能衔接未来的民族性精神文化资源。[3]将李贽与曹雪芹之间“启蒙思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是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的。
一“童心说”与“正邪两赋论”
李贽思想学说的一个支拄是“童心说”。“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4]而曹雪芹,则在《红楼梦》的第二回借贾雨村之口提出了“正邪两赋论”。追根溯源,“正邪两赋论”与“童心说”一脉相通。不过其表现形式一个艺术形象化一个哲学概念化而已。“正邪两赋”是与“大仁”和“大恶”正相反对的。“正邪两赋之人”是情痴情种、逸士高人和奇优名倡等“三类人”,即许由、陶潜、阮籍等诗人性情和气质的人,他们最本质的特点应该说就是葆有一颗“绝假纯真”的“童心”。具体到小说中,又衍化为贾宝玉的“意淫”。曹雪芹本人别号梦阮,可见其对阮藉的向往。这也就是李贽所歌颂的“魏、晋诸人标致殊甚”、“真英雄子”[4],欣赏嵇康和阮籍“其人品气骨”“古今所希”[4]“千载之下,犹可想见其人”[4]。而作为“正邪两赋”对立面的“大仁者”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正是儒家“道统”的代表人物,他们与“大恶者”的蚩尤、共工、桀、纣等其实是同一种本质的两种表现形式,具体到小说中,就是贾赦、贾政、贾珍、贾雨村等人物,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失去了“童心”,也就是李贽予以无情鞭鞑的“世俗子”与“假道学”[4],那种“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己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4]。
因此我们可以说,童心说与正邪两赋论,童心与意淫,分别是李贽与曹雪芹的“思想纲领”,从时间先后来说,李贽是“源”而曹雪芹是“流”,其实质是极为接近的,都表现了对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意识形态的叛离、批判倾向。用今天的术语来解读,就是李贽与曹雪芹于历史进程中社会意识形态对人性的“异化”都有极为切肤的痛感,而发出了不屈的呐喊,并从理论层面上举起了新的旗帜,作出勇敢的抗争姿态。
二、“护法裙钗”的妇女观
《红楼梦》第一回开宗明义,曰“风尘怀闺秀”。那段原为脂批后来衍为小说正文的“新书头”说:“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推了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堂堂之须眉,诚不若彼一干裙钗!……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不肖,则一并使其泯灭也。”此后推尊女儿,念念不忘“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把未受男权社会权力话语污染的清净女儿世界作为理想境界来礼赞颂扬,更是全书的基本立足点。《红楼梦》这种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思想立场其实也可以在李贽的著作中找到“先河远影”。《焚书》中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4],就有力地驳斥了封建道学对妇女的贬低和偏见。
李贽承认,妇女在男权社会的压迫性系统中,客观上是受到局限的,“夫妇人不出阃域,而男子则桑弧蓬矢以射四方,见有长短,不待言也”。但他接着指出,不能因此歧视妇女,不能说妇女天生就是“短见者”。“余窃谓欲论见之长短者当如此,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此盖孔圣人所以周流天下,欲庶几一遇而不可得者,今反视之为短见之人,不亦冤乎!”李贽不仅为妇女大声呼冤,而且把杰出妇女比作孔子周游天下欲访不得的圣贤之人,在那个男尊女卑被视作天经地义的时代,实在是非常大胆的,难怪被正统人士视为“异端”了。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对女儿的推崇可以说接过了李贽的思想火炬。特别有趣的是,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见短书》中不仅举出了邑姜、文母这些“圣女”作为女人未必见短的例证,而且特别举出了薛涛这个妓女予以褒扬,同时他又在为文的其他地方赞美卓文君为“善择佳偶”的奇女子,并尊崇《西厢记》等进步文艺作品。无独有偶,《红楼梦》正是一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为女儿鸣不平唱赞歌的“正名”之作,曹雪芹举出的“正邪两赋之人”中也正有“卓文君、红拂、薛涛、崔莺、朝云之流”,第二回通过冷子兴之口把贾府的男人和女人作了对比,说贾家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说到女孩儿,则说“听得个个不错”,又说王熙凤“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深细,竟是个男人万不及一的”,把她的丈夫贾琏比下去了。这些描写是深得李贽思想真谛的,李贽在《初潭集》中盛赞妇女“才智过人,识见绝甚,中间信有克为干城腹心之托者”[5],而反对把国家的败亡归咎于妇女的陈腐之见,说“若使夏不妹喜,吴不西施,亦必立而败亡”[5]。《红楼梦》以极富诗意的笔墨写出《西厢记》、《牡舟亭》在林黛玉和贾宝玉觉醒中的启蒙作用,李贽则高度赞扬“《拜月》、《西厢》,化工也”。而《拜月亭》和《西厢记》之所以能达到“化工”的高境界,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真”,具有“童心”,所谓“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此化工之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耳”[4]。显然,李贽与曹雪芹在妇女观上是惊人的相似的,这种超前的妇女观其哲学根源就是“童心说”和“正邪两赋论”。同时,这种妇女观的形成都有着深厚的生活基础,我们知道曹雪芹所写大观园诸女儿是有其生活原型的,李贽也曾经与女弟子梅澹然等通过当面讨论和通信等形式作思想的交流和探索。
三、圣人糠秕与毁僧谤道
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三足鼎,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既互相补充又互相矛盾的。佛与道在传统意识形态的整合中有其维护现实秩序的辅助作用,但其作为“出世”那一个文化层面的精神意向,也潜藏着对儒家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以后的官方儒学)的某种挑战。同时,作为以政权力量为后盾和支柱的国家意识形态,儒学的权威地位是不可轻视的。即使是像李贽和曹雪芹这样的叛逆者,在表达他们非圣无法的反叛思想时,也不得不采取一些迂回的手法和战术。这是我们在分析李贽和曹雪芹有关儒、佛、道的论说表达时要特别注意的。
李贽与曹雪芹对儒家思想都采取了一种表面上予以尊重而在骨子里反抗排斥的“皮里阳秋”的作法。曹雪芹是写小说的,他的表现更艺术。如在第一回。借石头之口说“上面虽有些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之语,亦非伤时骂世之旨;凡伦常所关之处,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后来写到贾宝玉,“只是父亲叔伯兄弟之中,因孔子是亘古第一人说下的,不可忤慢,只得要听他这句话”,“除明明德外无书”,在字面上维持了一种尊重儒学的假象,另一方面,却通过卓绝的艺术创造,把贾宝玉写成“混世魔王、绛洞花王、遮天大王”,来与封建意识形态的“素王”孔子分庭抗礼。而李贽,由于是写论文、书信等,因而其表达方式在思想的战斗锋芒上表现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当然也有一些“是故圣人在上,万物得所,有由然也”[4]“孔子之道,其难在以天下为家而不有其家,以群贤为命而不以田宅为命,故能为出类拔萃之人,为首出庶物之人,为鲁国之儒一人,天下之儒一人,万世之儒一人也”[4]等表面文章,但对儒学的蔑视、揭露和批判则更加明显突出。他敢于直接指斥儒家大圣人周公是“不仁不智”[4],认为周公也“好名”,而且“无风扬波,无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万世”[4],敢于质疑“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4]“噫!孔尼夫亦一讲道学之人耳,岂知其流弊至此乎!”[4]并针对儒学信徒所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而调侃“怪得羲皇以上圣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4]
李贽对儒学的批判与对“童心说”的肯定互为表里,他说:“夫《六经》、《语》、《孟》,非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人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然则《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4]曹雪芹则以他的生花妙笔写出“禄蠢”与“情种”的形象对立,“禄蠢”也就是失去了“童心”的“假人”,而与“假人”相对立的“真人”就是“正邪两赋之人。”在对传统儒学的态度上,李贽与曹雪芹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
李贽后来出家为僧,但并非世俗意义上的超尘脱俗,而是将佛学中反叛正统的那种思想层面作了特别的发挥。“五十以后,大衰欲死,因得友朋劝诲,翻阅贝经,幸于生死之原窥见斑点。”[4]正如近人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所说,“他的一生,作为士大夫,排击道学,不以孔孟是非为是非,是异儒,但他又不是超世绝俗的佛教徒,是异僧。异端思想、叛逆性格,贯穿在他的行为与作品中。”[23]这与他自幼的思想性格是一脉相承的,“予自幼倔强难化,不信学,不信道,少信仙佛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4]佛学的最大启示是让李贽发现了“我”的存在,进而由“我”的意识产生了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分别表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精神层面是童心说,物质层面则是禅宗的“平常心是道”,即“穿衣吃饭,既是人伦物理”的认识,李贽因此赞美“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4]的“迩言”。因此,李贽的出家为僧与“不信仙佛释”“见僧则恶”是并不矛盾的。他不会赞成佛、道逃离社会现实并与儒学“互补”以维护封建正统秩序的那一个层面,而只突出佛家特别是禅宗与现实对抗的那一个层面。
这种思想立场与曹雪芹极为相似,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既有“毁僧谤道”的层面,也有“参禅”、“悟庄”的层面。如第十九回花袭人劝谏贾宝玉“改邪归正”:“而且背前背后乱说那些混话,凡读书上进的人,你就起了名字叫他‘禄蠢’;又说‘明明德’外无书,都是前人自己不能解圣人之书,便另出己意,混编纂出来的。这些话,怎么怨得老爷不气,不时时打你。叫别人怎么想你!”“再不可毁僧谤道,调脂弄粉。”这清楚点明贾宝玉“不信学,不信道,不信仙佛释”的彻底叛逆特点。第二十一和二十二回则有贾宝玉模仿《庄子·肤筐》悟道及“听曲文宝玉悟禅机”的情节。而据红学探佚学研究,原著佚稿中贾宝玉的结局是出家又还俗,再出家,第一次出家是“情极之毒”,第二次出家则是“情榜证情”。这种故事情节的发展及其所包涵的思想内容正与李贽削发出家而张扬“童心”的“异僧”形象大同小异。从“情极之毒”到“情榜证情”的心路历程,与从“童心”到“异僧”的心路历程有着相似的轨迹,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转化和升华,即凸显佛禅思想中的反叛斗争色彩,使佛禅从逃避现实的“空门”转变为张扬人性、对抗异化的“情教”。
四、“启蒙三圣”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以上数节只是非常简略地比较了李贽与曹雪芹思想精神的某些相似性,更广阔的视野和更细致的研究当然会发现更多的东西。而这一比较特别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地方,是启示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思和创造性转化问题作出进一步思考。在全球一体化已经日趋逼近的今天,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当然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由此产生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大形势、大趋势,如何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不仅能够继续保存,而且能够发扬光大,成为我们的民族性文化资源和精神支柱。这个问题是非常巨大的,也是非常现实的。当然现在已经有各种想法、说法和作法,如思想文化界新国学、新儒学、新道学等等的提倡,政府层面也有纪念黄帝、孔子,支持传统文化研究和京剧艺术等各种举措,但这些尝试和努力显然远远不能适应现实发展的要求,我们现在急切需要一个民族性的文化精神支撑点,“这涉及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审视和切实清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表层的“弘扬传统文化”显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问题。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以“儒道释互补”为基本格局的传统文化毕竟是属于农业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其中固然有许多精华,但也有不少不适合当前时代需要的糟柏,其中的许多内容与今天日新月异的信息社会已经相当隔膜。因此,讲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不能忽视其中的启蒙传统,这种启蒙传统在过去当然不是文化传统的主流,但现在却是特别值得重视的成分。
为此,笔者提出“启蒙三圣”的概念。这“启蒙三圣”就是李贽、曹雪芹和鲁迅。作为封建社会后期思想界的“前卫”与“先锋”,李贽与曹雪芹是两位前赴后继的精神斗士。他们对封建正统的反抗与批判在当时是振聋发馈的,也必然引起整个社会的惊惶与反弹。李贽被迫害而在狱中自杀,其著作也被统治者下令毁版烧书,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叛逆者和殉道者。而曹雪芹,其身后极为萧条,他留下的伟大杰作《红楼梦》被腰斩续貂,从精神实质上被李代桃僵、偷天换日。这其实比李贽所遭受的命运还要悲惨和酷烈。红学中的探佚学正是以恢复《红楼梦》的本来面目和真精神、真艺术为已任的。笔者因此响应周汝昌先生提出的“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说法,并且设想以“人间红学”为具体操作方案作为传统文化复兴和更新的一条出路(当然只是“一条”出路,不是“唯一”出路),也就是以《红楼梦》这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总钥匙”为切入点,来实现传统与现实的对接,因为《红楼梦》同时具有对传统文化继承精华又扬弃糟粕的特点。《红楼梦》一方面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和辉煌,另一方面又有叛逆启蒙的思想闪光。
从叛逆启蒙的层面观照,由曹雪芹往上追溯,是李贽,往下的继承者则是鲁迅,他们都是其所生活时代的“异端”,他们的异端思想未必都有绝对的真理性,但他们的存在昭示了一种“异端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传统的异数,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而从最基本的方面讲,这三个伟人的精神实质血脉流注,前后贯通,他们既生动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粹,又具有特别能与当今时代精神相契合的优点,符合提倡科学、发扬民主,尊重人权、追求原创的世界潮流。在二十一世纪,要发扬中华传统文化,要重新铸造中国人的“国民性”,要寻觅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不应该忘记这一最宝贵最重要的思想传统和精神资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对李贽的精神遗产刮目相看。
〔收稿日期〕2000-0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