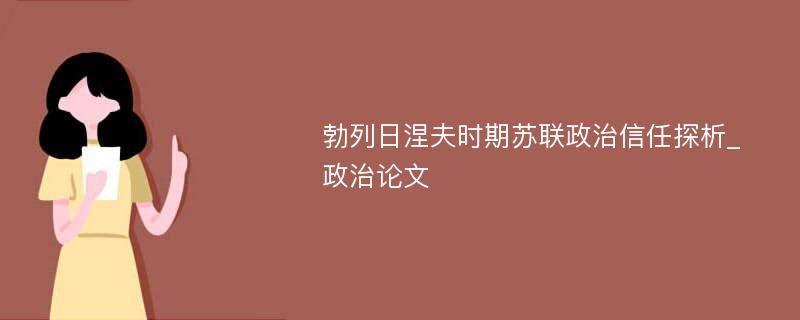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时期论文,状况论文,政治论文,勃列日涅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12-0069-10
所谓政治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的作为将产生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①。它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在最高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政治共同体(国家)的态度;在第二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政治制度以及国家机构的态度;在第三层次上,指的是公民对待作为个体的政府官员的态度。由此出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公民政治信任的状况如何,即反映了公民对国家、政治制度、政府以及政府官员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
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如何呢?在学术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即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以稳定——“停滞”的另一面——而著称于世。笔者也曾撰文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稳定进行过专门的探讨②。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此时的苏联有了稳定是否就意味着有了政治信任呢?恐怕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正相关关系。笔者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虽有社会政治稳定,但是政治信任的状况却并不乐观。简单地说,苏联的这种状况就是:有秩序而无政治信任。
波兰学者彼得·什托姆普卡曾提出诊断一个社会缺乏政治信任的三种指标体系:(1)信任的功能替代品;(2)行为指标;(3)言辞指标③。本文将尝试运用这三种指标体系,来论证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政治信任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的结论。
一、信任的功能替代品
所谓信任的功能替代品(the functional substitutes),按照功能主义的解释就是,“当信任缺失的时候,其所产生的真空状态将被某些提供相似功能并满足对确定性、可预测性、秩序和其他相似的东西的渴求的备选的安排所填充。这些就是信任的功能替代品”④。这就是说,当一个社会缺乏信任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替代品,以发挥本应由信任发挥的功能。由此可见,这种情况,既是社会功能失调的结果,又是对社会功能失调的反应——它对信任功能的缺失起着校正性的作用。这些反应主要有:宿命论、腐败、过度警觉、过分地诉诸诉讼、强迫集中居住、父权化、信任的外部化等⑤。
根据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的实际状况,因其政治信任的缺乏而出现了相应的功能性替代品。它们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苏联民众更多地相信宿命论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美国政治学家乔治·萨拜因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代表了未来的浪潮”、“代表了站在社会进步前列的‘日益崛起’的阶级的呼声”⑥。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所描绘的美好图景的激励之下,在那样一个红色的年代,激发起了俄国广大民众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格·阿·阿尔巴托夫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它激发着民众“要为美好理想的‘每一寸土地’而战斗”的热情⑦。英国学者莫舍·卢因也指出,“在这‘红色’阵营中,不消说许多人都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和热情洋溢的气氛中,而之所以能保持这种气氛,纯粹是由于他们真诚地相信已经建立了较高级的社会制度”⑧。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倾向性”的推动下,苏联作家们以饱满的热情抒发着人们战天斗地的浪漫主义情怀。“全国一片沸腾,热火朝天,在建设,在重新安排’,A·马雷什金在《关于我》一文中这样写道。20世纪30年代就是这样被载入史册的。假如随便翻阅一下当年任何一种报刊、任何一部受欢迎的小说,——你都会受到战斗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灵感的气息的激励。一种投身到全国——从天南到海北——伟大的改天换地的行动中去的激情,占据着作家的心灵。在全国人民热情高涨的气氛中,怀疑论的坚冰正在融化。原来一些宁愿对斗争持超然态度的怀疑论者,想起圣经中创世的神话,便成了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们沉浸在那热气腾腾的日常生活中。”⑨这种情形表明,由于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发之下,无论在思想意识领域,还是在行动领域,人们都已不再相信宗教,不再相信什么上帝和命运等超自然的力量的安排,而是相信可以依靠个人的努力而改变自身和世界。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苏联民众那种战天斗地的热情和激情,一旦遭遇到了严格的计划体制的制度性安排,便不可避免地被浇灭。这是因为,在计划体制下,人似乎失去了一切个性的特征,毫无例外地被看作是整个计划机器的组成部分,被看作是一颗没有任何生气的“螺丝钉”。对此,阿甘别吉扬指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本质上是压缩个人,把他们都变成庞大的国家机器身上的螺丝钉,这样一来,我们无法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无以发挥人的潜力。”⑩这样,苏联民众完全受制于计划体制,听命于国家机器,基本上没有了能动性。这就是说,由于政府掌握着国家的一切经济资源,也就意味着国家绝对地控制了个人的生计问题,苏联民众若想“体面”地生存,就不得不服从社会政治秩序,否则,他的生存就会遇到制度的威胁,他就会陷于衣食无着的境地。通过计划体制的安排,当局便牢牢地把个人控制了起来。对于生活于其中的苏联民众而言,计划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强制制度,更是一种“政治依附”的制度。这样,苏联民众的政治心理在经过了现实的经验之后,又回到了起点,即他们已不再相信个人的努力,因为计划体制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个性发挥的空间(11),他们只好转而去相信上帝、命运等神奇的超自然力量的安排了。
这种情形,在斯大林时期如此,在赫鲁晓夫时期如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是如此。可以看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计划体制并没有得到多少的改变,它仍然发挥着控制个人的功能。当时的一位年轻的俄国人在接受英国记者约翰·摩根的采访时所说的话,即典型地反映了个人受到这种体制的控制和束缚的情况。他说:如果当局“因为讨厌你,而把你解雇了,你在适合自己专长的行业中——比方说艺术界就别想找到别的工作”(12)。因此,迫于生存的压力,人们(至少是大多数人)便不得不服从那种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当然也谈不上什么个性了,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并不由自己来掌握。也正因为如此,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人们渴望着像斯大林那样的铁腕人物的统治。一位青年冶金工人尤里如是说:“你想知道工人们的想法吗?你知道下面这句话吗?‘俄国人需要一个巨灵神那样的人物’。这就是说,俄国人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好躲在他身后,受他庇护。”(13)
2、腐败之风的盛行
一般认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形成了一个队伍庞大的特权阶层(主要是官僚集团)。虽然关于特权阶层的人数没有定论,但是这并不妨碍上述的结论。这个阶层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虽然他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他们在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但在实际上,他们却演变成了人民的主人,他们把手中的权力看作是为自己服务的工具,看作是为自己谋取利益的工具。
就党政官员而言,计划体制的设计本身对于他们在人性上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也就是说,计划体制要求官员都具有崇高的共产主义道德,都具有一心为公的崇高品格,都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度自觉性。然而,无论如何这只能说是一种理想状态下官员的道德标准,在现实社会中可能绝非如此。而且在事实上,由于在计划体制下,党和政府几乎控制着一切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党政官员利用公共权力进行寻租提供了便利条件。实际上,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满足自身的利益,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对此,英国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即指出:“特权阶层正好暗示了勃列日涅夫时期那自私自利官僚体系的弱点所在:也就是无能与腐败的混合体。事实上情况也愈来愈明显,苏联本身的经营,的确在一个走后门、拉关系、照顾自己人等充满了营私舞弊的关系中进行。”(14)
与官员腐败相对应的是民众对官员进行贿赂,在某种程度主,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就是说,官员的腐败直接促使着民众的贿赂,而民众贿赂本身又加剧着官员的腐败。当贿赂成了苏联民众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遇到困难甚至威胁时自我保护的“武器”时,这在实际上意味着民众对体制、对官员的一种不信任。
3、人们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过度警觉
克格勃一向被认为是苏联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得以维持的“党的剑和盾”,克格勃统治是维护“勃列日涅夫稳定”的威慑机制(15)。众所周知,在20世纪70年代,克格勃组织了遍及苏联社会各个角落的密告网,上至红军的总参谋部,下至贫困不堪的村庄。任何一个场合,任何对苏共的统治可能作出批评的集会,都有克格勃在进行着严密的控制和监视。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就认为:克格勃的职责是“监视生活各个领域的意识形态是否健康”(16)。克格勃通过一支无法进行精确统计人数的告密者队伍来刺探民心,以扫除那些确有其事的或虚幻的反苏活动、思想和态度。假如谁有一点点思想“脱轨”的证据,就会迅速招致克格勃的惩治——或被降级、或被解职、或被送入“疯人院”,或被投入牢狱之中。阿·阿夫托尔哈诺夫曾这样说道:如果有谁不按照“中央委员会那些无能之辈和克格勃强盗们那样思考问题,便等于犯了严重的国事罪”(17)。这样,在克格勃及其编织的“带有瘟疫性质”的告密网络的阴影笼罩之下,苏联民众莫不生活在恐惧和互相怀疑之中,而对自身安全的恐惧极大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道德判断力,并使得他们不能也不敢相信其他任何人,甚至在父子之间、夫妻之间也都失去了人世间最可珍贵的“信任”。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之所以出现“夜间人现象”、“厨房文化”现象,恐怕原因就在于人们对政治系统缺乏安全感,对现状和未来都没有稳定合理的预期。这种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对于所有人都不信任的自我保护,是使人们不自觉地互相对立起来的政治控制的最令人沮丧而又最有腐蚀性的后果之一。一个青年人在得知他被一个老朋友向克格勃告发之后愤愤地说道:“除了你的枕头之外任何人都靠不住。”(18)这句话可以说是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过度警觉和不安。
4、政治信任的外部化
在对苏联的政治机构、党政官员、公共产品等的不信任氛围中,人们转向外部社会,并把他们的信任存放在其他的人物、组织或物品之上。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治信任外部化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人们对苏共认识的变化,在他们看来,苏共不再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向苏共中央所作的一份报告就反映了这一点。报告指出:在青年学生中间,“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或者只是当做耳旁风”。他们还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和列宁时期相比较,认为党员“既可能是个醉汉,又可能是个淫棍,也可能是个毫无原则的人。……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方便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至于共青团,在青年学生中也不能“享有必要的威信”。该报告在谈到青年学生对西方的认识时指出:青年人对美国有一种别样的好感和莫名的向往,他们认为,“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人民,因此他们那里没有共产党”,“他们的失业人员比我们的工程师生活还好”。报告还指出:“大学生中任何人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但是它渐渐明显地深入到大学生的思想中去。这一点在许多方面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疏漏造成的。我们对时尚的改变(也许是跳舞,也许是音乐,也许是穿衣)的典型的反应——先是激烈的批评,长时间的了解其习惯,最后甚至超过榜样的盲目模仿。但是采用时髦的风气正赶上批判时期,因此内心想争取什么的青年便为了……发型、胡子、裤子和流行的舞蹈而斗争。并且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要保卫来自大洋彼岸的某些东西,因此它对他们显得非常珍贵”(19)。这种对国外的好感和向往,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看,即意味着对国内的不满和怀疑。
信任的外部化还表现在对外国商品的疯狂迷恋上。法国的白兰地酒、苏格兰威士忌酒、美国香烟、进口巧克力糖、意大利领带、奥地利毛里长筒靴、英国毛纺织品、法国香水、德国短波收音机、日本磁带录音机和立体声收音机,还有外国小汽车等都是人们迷恋的对象。只要不是苏联出产的东西,一件衬衫、一条领带、一个手提包以及随便什么其他小玩意儿,都能得到人们的欢心和渴求。曾于1971-197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的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即指出:“购买进口货是防止吃亏上当的另一个方法,不论普通消费者或特权阶级都是如此。西方商品在苏联市场上虽然为数寥寥,哪怕是东欧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商品也对势利的顾客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即使在苏联本国生产的商品供应还比较充裕时,俄国人也宁愿多出些钱购买进口货”(20)。总之,这种对苏联国内产品的不信任,其实,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对政治、对体制的不信任。
二、行为指标
行为指标是指由社会成员所表现的行为的典型形式,它能够反映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人们实际在做什么,或看上去愿意做什么,或者说就是那些预示着信任缺乏的实际的或意图的典型行为模式。
1、移民
正如彼得·什托姆普卡所指出的那样:“对自己社会的生存能力的普遍不信任的最强有力的信号也许是移民的决定。这是人民在生活条件变得不能忍受,并且看不到改善希望的时候采取‘退出选择’的最清楚的形式”(21)。
那么,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公民移民的情况如何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移民,并不是指国内的流动,而指的是跨越国界尤其是向西方国家的流动。众所周知,由于当时所谓“一球两制”的对立,苏联对自由地向西方国家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是禁止的,因而从移民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信任状况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笔者认为,虽然没有肉体上的移民,但却有“精神的移民”。这一点值得引起我们的关注。例如,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向苏共中央所作的报告中就指出:青年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美国的生活方式”,认同了西方的思想。该报告以文学和音乐为例说道:“青年们认为,西方作家写的东西比我们更好、更有趣。而且他们的作品选题广泛。……西方的歌手和爵士音乐家也很受欢迎。至今一些摇滚乐团的声望还有增无减,并达到最大程度。来自官方的某些‘压制’更加强了新的协会出现的趋势。”(22)赫德里克·史密斯也指出:苏联青年对苏联电台和电视台播放的爱国主义音乐、红军进行曲等十分不满,他们已与“苏联历史相隔绝了”(23)。其实,这种“精神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国内现实的一种无奈和逃避,是对国内政治生活的一种“退出”。
当然,由于没有正常的管道提供移民的机会和途径,因此,也就出现了一些采取非正常途径进行“移民”的事例。苏联高级外交官、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阿·舍甫琴柯在1978年“叛逃”美国,从中即可以看出他为什么坚决“退出”苏联的原因(24)。
值得一提的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一个特殊群体——犹太人。苏联当局对他们采取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政策,允许他们离开苏联。当然,犹太人也乐于离开苏联,因为他们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所以作出了“退出”的选择。据曾任美国驻苏大使的雅各布·比姆回忆说:在1972年,离开苏联的犹太移民每月2000人左右,到了1973年这个数字则增长为3000人左右。而且,尽管这样,犹太人团体还抗议说这个数目太低,不能满足犹太人移民的要求(25)。
2、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中撤退
彼得·什托姆普卡指出:“类似于移民的现象,另一种‘退出’选择是从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中撤退。”(26)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对公共生活的认识及参与程度如何呢?我们知道,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而这种体制惯于对人们发号施令,却根本不会或很少去顾及人们的思想和感情,很少会倾听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反对性的意见),从而造成了他们在公共生活领域的消极态度。彼得·什托姆普卡就指出:“审查制度、教化主义、限制自由表达意见、教条主义或完全的欺骗”只能带来人们政治上的不信任,而“宽容、公开讨论、多元且独立的媒体等防御措施”则有助于产生信任(27)。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属于彼得·什托姆普卡所说的前一种情况,因而人们对公共生活、对政治自然也就失去了兴趣。他们表面上在循规蹈矩地参加官方举行的各种活动,实际上却越来越深地隐退到私人小圈子和家庭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就青年学生对于公共生活的态度发表评论说:“青年中专心致志搞科学的思想很风行,因为科学不管政治危机,可以把他们的生活填得满满的。然而能经得住这条道路的人是很少的,通常过一段时间他们在色情和酗酒这两种麻醉剂的考验中排除了已产生的矛盾。”(28)
或许,有人会以苏联政治生活中民众较高的政治参与程度来反驳这一观点,但是,这种较高的政治参与度是组织动员的结果,是民众被动的政治参与行为。斯基林(H.G.Skilling)即指出:虽然在苏联能够看到民众广泛的政治参与的事实,但是与其说这是他们给政策形成施加影响的活动,不如说是他们对国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服务。因为从根本上说,这种广泛的政治参与是由领导人和党发起的,在较大程度上带有被动色彩(29)。英国学者默文·马修斯从苏联选举中很少有反对票这一现象也看到了苏联民众政治参与的被动性。他指出,在苏联1967年地方选举中,仅有0.6%的合格选民没有投票,但是“严格的投票制度严重妨碍了公开投反对票”。其实,即使是投反对票,也根本不可能影响选举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投反对票的热情。他还通过大量的调查得出结论说:在苏联“社会-政治活动不是很受欢迎的”,“也许大多数调查所透露的对社会政治活动的冷淡和反对,可以看作是说明普通人民中间的冷漠和政治上的反对状况的……指南”(30)。青年人的政治态度历来是社会情绪的风向标,而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青年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冷漠的。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所作的关于青年学生的情绪的报告中就有这样的材料。该报告在谈到苏联大学生的特点时,即把“非政治倾向”列为第一个特点,并指出这是大学生“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特点”,许多学生都倾向于“我可以胡诌几行打油诗,但谁也不会叫我们到参政院广场去”的政治态度(31)。
总之,民众淡漠的政治态度,不愿意参与到政治生活之中,其实是在根本上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政治体制的失望。美国学者悉尼·胡克的话值得深思:“最明智的政策,在民众的漠不关心或敌意面前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即使是那些认为必须由职业上明智的人们或专家们来实行统治的人,要是排斥他们的意见,也得冒自己覆灭的危险。”(32)
3、通过“表达”显示出来的不信任
彼得·什托姆普卡指出:“作为选择,广泛的不信任可以通过选择‘表达’而不是通过选择‘退出’显示出来。那些不想选择移民或选择被动接受的人求助于集体抗议。大量的‘抗议事件’是公共不信任的很好指标”(33)。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借助于“表达”的途径所显示出来的不信任,最为明显的就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不同政见者人数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见表1),他们拥有公开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口号,并进行公开的活动,在苏联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
表1 1967-1971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情况表
年份 1967 1968 1969 1970 1971
组织(个) 502
625
733
709
527
人数(人) 2196 2870 3130 3102 2304
资料来源:[俄]A·B·萨维利耶夫:《1950-1970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治特征》,载《历史问题》(俄罗斯)1998年第4期。
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出现了三个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派别:以萨哈罗夫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派、以罗伊·麦德维杰夫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派和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新斯拉夫派。自由主义派在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影响最大,萨哈罗夫认为,苏联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极端集中或者说极端垄断化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所以,他提出“消灭特权”、“建立民族身份平等的社会”、“取消职位和党内特权”(34)等主张,希求在苏联建立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社会。麦德维杰夫兄弟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对集权统治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积极倡导上,他们通过一系列著作对恐怖统治和个人崇拜等破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行为进行批判,呼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主张政治多元化,实行多党制,要求言论自由。1970年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萨哈罗夫、瓦连京·图尔钦一起写信给苏联领导人,提出了逐步实现国家民主化的15项措施,并指出了民主化进程的两方面威胁:个人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强有力政府”的信徒。索尔仁尼琴在20世纪70年代后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但是也反对学习西方文明,反对苏联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他所推崇的是“俄国式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不是建立在无穷尽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上”(35)。索尔仁尼琴美化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社会,将君主制、东正教、村社看作是最适合俄罗斯社会的东西,主张恢复俄罗斯的古老传统。
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领导人的保守倾向以及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使持不同政见者越来越处于一种思想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排斥革命而寄希望于上层的改革,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勃列日涅夫们的不信任态度。
4、“现世主义”倾向(presentist orientation)
彼得·什托姆普卡指出:“当我们检查人们指向更加遥远的未来的行为模式时,在此我们必须对未来进行某些想象,也可以观察到不信任的存在。如果那种想象是不清晰的或否定性的,我们将会观察到现世主义倾向:只关心眼前的这一刻,忽视任何时间上更遥远的前景。”(36)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对未来的不信任可以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教育方面,党的教育决策首先是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服务,而不是与市场的需要相适应。教育的课程,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课被大学生看作废话,教授这些课程的老师也是大学生最不欢迎的。而大学生读书“第一考虑的是怎样便于升迁和在党政工作方面飞黄腾达”,而不是为了长期的生活做计划(37)。科学研究方面,知识分子都尽量不涉及敏感和紧要的现实问题,致使形成了科学上的不良风气。“科学对社会生活的迫切问题越来越不感兴趣,日益热衷于微小问题、烦琐哲学和教条主义”(38)。日常生活方面,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的热情不在于发展经济,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苏联,而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财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经成为群众性现象。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之风在社会上流行,尤其在青年一代中,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逐渐丧失,追求个人生活的幸福和高收入的职业是青年们第一位的思考。青年们认为:在苏联“建设起来的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社会主义,他们首先要生活,而且要更好地活下去”。38-40%的青年认为“个人幸福”就是生活的意义所在,36%的青年觉得生活“没有意思”(39)。所有这些,都显示出苏联人对未来缺乏信心,因而转向了倾向于获得短期的即时利益的“现世主义”态度。中国有句俗话:“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可以说是这种情况的准确描述。
三、言辞指标
言辞指标指的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直接意见、评价和提议,是对各种类型的不信任的最直接、最清晰的表达(40)。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政治信任状况可从以下两方面来评判:
1、对制度改革的评价
在最一般的水平上,信任的最好指标是对制度改革的评价,包括目前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前景(41)。勃列日涅夫上任伊始即推行以“新经济体制”为中心的经济改革,虽然对高度集中的旧体制进行了冲击并有所突破,但基本上是囿于计划经济的体制内修修补补,并未触动根本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框架。因而在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增长的势头日趋消减,改革也进入了相对停滞的阶段(42)。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大多数苏联知识分子都倾向于认为:“我国的经济似乎已经糟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因为它不遵循价值规律(‘计划体制的唯意志论。”(43)而在政治领域,体制的僵化与腐败已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重要特征,人们看不到任何改革的迹象。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干部队伍超常规的稳定和老人政治现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就废除了赫鲁晓夫推行的干部轮换制,对干部队伍提出了“稳定”的口号以“捍卫干部的权利”,并保证要使干部得到尊重,使干部不用担心什么权力和利益的问题。曾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斯洛夫认为:“干部队伍的稳定是成功的保障”。勃列日涅夫则把这句话看作自己执政的公式,“勃列日涅夫甚至以他领导时期所有地方干部通常没有任何变动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为荣”(44)。俄国学者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甚至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干部队伍比喻作一个“瞌睡王国”(45),而“瞌睡王国”则指干部队伍毫无生机与活力,基本上失去了新陈代谢的功能。正如弗·亚·克留奇科夫指出的那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高级领导层对改革无动于衷和消极等待的态度,像危险的病毒一样出现在社会上,并很快传染开来。不管谁有大胆的设想或有新奇的建议,都不想冒昧地去实现它。大家就这样在原地踏步,在沉默中等待”(46)。
面对经济陷于停滞、政治失去活力的局面,苏联民众怎么会赋予政治信任呢?他们又怎么会对未来持有信心呢?对于“共产主义是什么?”的问题,在当时的乌克兰有一段顺口溜——共产主义就是“有人富,有人穷,有人当老子,有人当小子”,即典型地反映了人们对现实和未来的较为悲观的认识和失望的态度。而且这种对制度的认识,直接影响着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人们已不再关心政治,并具有了非常明显的“非政治倾向”——“我不管什么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只要给我的钱多”(47)。
2、对公共机构和干部的态度
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对公共机构和干部的态度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状况。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首先,对苏共的认识。1968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谈及青年学生对苏共的态度时指出:“对大学生来说,……党对他们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东西的化身”。“学生之间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把党证叫做‘红色的浮子’。”“多数学生群众在许多方面把自己和党对立起来”,同苏共有“抵触的情绪”。大学生对苏共的态度还表现在对列宁态度的变化:“他们不仅嘲笑列宁、捷尔任斯基、克鲁普斯卡娅和其他革命活动家,而且嘲笑对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虔敬态度”。在青年学生中间,“赫赫有名的‘列宁主义中央委员会’这几个词只能引起讥笑或者愤怒”。而在号召青年人珍惜十月革命的成果的时候,“并没有人响应”(48)。
其次,对苏共党的干部的认识。对苏共党干部的认识直接受制于人们对苏共的认识。青年人经常认为“党的领导人对大学生的演说也无助于党的成功,……(敖德萨的)大学生常接触的领导人中很少有演说的才能,大学生们好奇地期待领导人开始演说,但照本宣科且读得结结巴巴使听众的兴趣一落千丈。这种会见只能产生反面的效果,加剧了对党的工作者的藐视。”(49)人们经常认为党的干部言行不一,甚至弄虚作假,以至于使得人们对他们提出的政策、说教、口号等均持不信任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对所号召的东西,对讲坛上讲的东西,对报纸上和教科书中说的东西就开始不那么相信了。”(50)阿·阿夫托尔哈诺夫也指出:“勃列日涅夫想使我们相信,党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然而,党的机关的秘密不仅不能告诉人民,而且也不能告诉自己的党。”(51)
第三,对共青团的认识。共青团在青年学生中也不能“享有必要的威信”。“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的变化几乎没有人发现,这个组织及其活动的存在与否一般说来知道得很少。”“共青团工作并不令人羡慕,它不像党的工作可以飞黄腾达。”(52)
此外,人们对政府机构也表现出不信任的态度。在这里,对苏维埃的认识可见一斑。苏联科学院国家与法研究所的鲍·托波尔宁曾指出:苏维埃代表“习惯于把自己的工作局限于通过决议”,甚至像是“婚礼上的闲人”(53)。对官方的思想则不感兴趣。下面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根据对一个工厂图书馆半年期间的借阅情况的调查,在全部借走的书籍中,政治类的书籍只占了0.5%(54)。
值得一提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上流行着许多的政治笑话。这些笑话本身就是政治信任缺失的例证。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四、结语:有秩序而无信任的政治
通过对上述三个指标系统的描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社会是一个政治信任缺失的病态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以稳定而著称于世,但是,在那稳定的背后却潜伏着政治不信任的暗流,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政治信任犹如软件系统,它的存在方能使社会充满韧性和自由发挥的空间,它保障着社会的稳定而不必过多地依赖于强制力的运用,这样的社会稳定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稳定。而如果政治信任处于缺失的状态,那么,这个社会要想保持住稳定,或许,它只有依赖强制力的发挥。但是,依靠强制力而得来的稳定只能是一种“假稳定”,它是不能持久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主要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指出:“暴力从来就不是解决危机问题的手段”,“违背人民的意志,同时又要他们感到幸福,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他还说:就统治者而言,过多地依靠暴力“往往是自身虚弱和无能的表现,因为他们拿不出比对方(主要指民众——笔者)更好、更富有成果的思想武器。……最终决定斗争胜负的不是武器,而是人的思想”(55)。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之所以出现政治信任的危机,究其实质,也就在于它拿不出能够说服民众的思想,当然也没有能够让民众心服口服的行动。这样的统治是不可能获得民众的信任的,而它为了保持对自己统治有利的政治秩序,也只有依赖强制性的力量去维持一种虚假的稳定。日本学者猪口孝这样说道:“有些统治虽然表面看来十分牢固,宛如形成忠诚的群体,但它也可能会在某一天突然崩溃。”(56)这句话无疑可以看作是苏联命运的写照,因为勃列日涅夫之后的苏联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即遭遇败亡的命运。从勃列日涅夫统治下的苏联的悲剧命运中,不能不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政治信任对于国家治理、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
注释:
①Arthur H.Miller,Ola Listhaug,"Political Parties and Confidence in Government:A Comparison of Norway,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20,No.3(Jul.,1990),pp.357-386.
②郝宇青:《“勃列日涅夫稳定”原因论》,《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
③[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4页。
④⑤[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5、155-158页。
⑥[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册,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96页。
⑦[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20页。
⑧[英]莫舍·卢因:《苏联经济论战中的政治潜流——从布哈林到现代改革派》,倪孝铨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71页。
⑨[苏]阿·梅特钦科:《继往开来——论苏联文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石田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29页。
⑩[苏]阿甘别吉扬:《苏联改革内幕》,常玉田等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11)苏联的计划体制,不仅有大政方针上的总的宏观性领导,还有自成体系的堪称完整而庞大的组织机构,进行着具体而微观的管理。例如,在党的决议中规定生产多少粮食、蔬菜、工业品,开办什么工厂,投资多少,开办多少学校,招收多少学生,是否增加运粮的车皮和存放粮食的库房,干部休养所的归属问题,是否允许出售外国书籍,谁出国买机车问题,甚至是否让某教授出国并拨款给他等十分细小的问题都要经由党中央、政治局来讨论、定夺(参见《列宁文稿》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47页)。这种事无巨细、包揽一切的具体而微观的管理活动,实际上大大压缩了民众的空间。
(12)转引自[美]约翰·巴伦《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全貌》,沈思清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页。
(13)[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56页。
(14)[英]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册,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01页。
(15)郝宇青:《“勃列日涅夫稳定”原因论》,《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
(16)[俄]列昂尼德·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9页。
(17)[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112页。
(18)[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03页。
(19)《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152、153、157页。
(20)(23)[美]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22、365;113页。
(21)(26)[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6、217页。
(22)《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24)[苏]阿·舍甫琴柯:《与莫斯科决裂》,王观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
(25)[美]雅各布·比姆:《出使苏联东欧回忆录》,潘益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0页。
(26)(33)[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0、218页。
(28)(31)《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161-162页。
(29)H.G.Skilling,"Interest Groups and Communist Politics Revisited",World Politics,Oct.1983.
(30)[美]默文·马修斯:《苏俄的阶级与社会》,郑州大学外语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60-267页。
(32)[美]悉尼·胡克:《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金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88页。
(34)郭春生:《社会政治阶层与苏联剧变》,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年版,第205-206页。
(35)[俄]A·B·科罗特尼科夫等:《克里姆林宫私刑——政治局关于作家索尔仁尼琴的秘密文件》,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280页。
(36)[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9页。
(37)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3页。
(38)何瑞翔编译:《苏联著名学者布什坚回顾近20年苏联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88年第6期。
(39)[西德]赫尔穆特·柯尼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态》,《苏联问题译丛》第7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
(40)(41)[波]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程胜利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14、220页。
(42)周尚文等:《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4页。
(43)[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0页。
(44)[俄]B·麦德维杰夫:《保镖》,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25页,B.T.Meдseдeв,ЧeлoвeK эa cnинoй,M.,Pyccлит,1994r.,c .125.
(45)[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93页。
(46)[俄]弗·亚·克留奇科夫:《个人档案——苏联克格勃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狱中自述》,何希泉等译,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第88页。
(47)《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62页。
(48)(49)(52)《国家安全委员会就青年学生的情绪呈苏共中央的报告(1968年11月5日)》,载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152、152-153、153-154页。
(50)[苏]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7-18页。
(51)[苏]阿·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第79页。
(53)[苏]鲍·托波尔宁:《苏维埃国家与人民自治》,《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6期。
(54)[西德]赫尔穆特·柯尼希:《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苏联人民的思想动态》,载《苏联问题译丛》第7辑。
(55)[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6、89页。
(56)[日]猪口孝:《国家与社会》,高增杰译,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标签:政治论文; 移民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