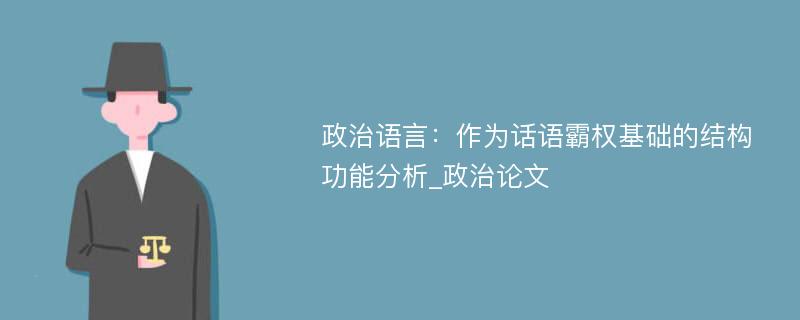
政治语言:作为话语霸权基础的结构——功能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霸权论文,话语论文,语言论文,政治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语言”这一术语,主要用以概括、描述和分析在政治过程中被使用的语言现象。通常,政治语言是政治神话或者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材料,同时也是它们得以生成、存续和传递的手段。就此而言,政治语言演绎为一种权力技术,并成为政治话语霸权的基础。
从政治和语言的二维视角出发,对政治语言的结构和功能分析,在试图解释政治运作的动力因素和理解政治本质的学术努力中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政治语言也成为象征政治学的研究主题之一。(注:Murray Edelman.Political Language:Wouds that.Succeed and Policies that Fail(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7),p.3)本文意图通过对政治语言的结构,要素和类型的分析,关注各类政体及其精英们在主导或垄断社会价值的权威性时,使用了何种语言形式向公众解释和抚慰,这些语言类型具有何种政治意义和功能。
一、语言的结构、隐喻与政治语言
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表明,在意义表达方面,语言具有两种功能:逻辑的和隐喻的。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语言在其形成的原初就预设了两种权力:隐喻的权力和逻辑的权力(即理性的权力)。(注:(德)恩斯特·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53页。)隐喻的意义依赖于情感化的联想,具有任意性,而逻辑的意义依赖于推导,具有确定性。对语言的使用,实质就是对语言的两种权力的行使。
卡西尔的哲学式观察可以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们所借重的语言“能指”、“所指”概念及其关系分析中获得更清晰的阐释。也就是说,只有当语言的能指性与它的所指性保持一致时,语言的逻辑权力才能得到实现。而当语言的所指范围在其能指性上扩大后,这些扩大的意义与其语言原义之间。具有不确定的联系,它相对于本义而言就是“隐喻”,或者说是语言的象征意义。例如,“蛇”这个词作为认知语言所表达的逻辑意义是一类特定的动物。但在《圣经》的伊甸园中,蛇是作为语词的隐喻而被使用的,它是邪恶的象征。在这里,蛇的动物学语境意义被转移为一种道义语境。又如,“红色”一词,其本义指称由人的视觉反应所产生的一种颜色。作为一种象征,它代表激情、血腥,或代表革命、进步等意义,这时就是基于情感式联想的隐喻。因此,要准确获知说话者所表达的是哪一类含义,通常需要将言者所言置于特定的情境,即“语境”之中进行理解。
政治语言,即在特定政治情境中所运用的语言,其意义表达的二重性相当明显。它具有认知性和情感性这两种特性,而基于联想的情感性,话语的特点在于总是缺乏精确定义。因此,政治语言实质上是一种“习得性”语言,它们并不同于日常生活语言。它们通常是由原初表达固定所指的,而现在又由被转移到一个高度情感化的情景中的那些语词所组成。所以,正如莫瑞·埃德尔曼所指出的,在多数情形下,政治语言并不在于客观说明问题,而主要用来转移注意力,准确不是它的基本属性,其根本作用不过是使政治行为神圣化。(注: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p.115.)因而,在对政治语言及其意义的真实性研究中,不仅要了解其字面的、辞典性含义,而且还必需深入研究政治语言特定的表达模式、特定的语言情境以及观察处于不同情景中的听众对这些表达模式的不同回应。
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统治精英主导着、甚至垄断着对政治事件和行为的意义解释权,因而,政治语言实质是精英们惯常使用的语言,它们通常构成了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公共话语。统治精英们通过在语言的本义和隐喻、实质意义和象征意义间的任意互换,通过对同一概念的不同意义的选择,建立专属于己和有利于己的政治话语霸权。以此为自己的统治合法性辩护,而外行的公众则很难弄清其真实含义。这正如米歇尔·福柯所指出的:一切统治,归根结底是语言的统治。话语实际上是统治的根本,语言和话语本身亦即权力。(注:(法)米歇尔·福柯《知识的考掘》王德威译,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第88页。)在这种意义上讲,不懂得政治生活的语言运用方式,我们就无法理解政治,而人们对政治的无知所付出的代价,就是遭受他人和环境的奴役。
二、政治语言的结构、类型和功能,
在政治与语言的二维视角中,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提出和回答如下问题而使政治语言得到分类式描述:(1)谁为了何种目的发出语言?(2)他说了什么?以何种方式?(3)谁是听众?(4)说话内容对听众的影响和效果(回应)是什么?值得注意的是,在确定沟通者的意图、信息的内容、听众的认知以及听众所作出的回应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描述它们的“各种意义”。(注:Harold D.Lasswell,"Key Symbols,Singns and lcons",in Lyman Bryson(ed),Symbols and Values:An lnitial Study.(New York:1954),p,199.)这些意义都是在政治沟通中产生,既可能是逻辑上的本义,也可能是隐喻性的象征。
在研究语言类型和结构所包含的各种可能意义时,必须涉及到语言的多种形式要素。下面的分析将表明这些要素是十分重要的:定义、前提、推论与结论的表述(推理);说话人身份的公开性或秘密性特征和表达的形式与情境(涉及言者的);听众身份的公开性或限制性特征和回应形式与情景(涉及听者的)。这些要素的不同组合,就产生出政治过程中的四种相互区别的语言类型。它们是说服型、法理型、行政型与交易型政治语言。
(一)说服型语言
“说服型语言”是最广泛使用的一种语言。比如,在向公众呼吁对某项政策的态度时,在选举活动中,在立法辩论中,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在基层小组的政治讨论中。在所有这些场合,总是存在一些人试图说服另外一些人。与其他的语言类型相比,这种语言直接地面向欲说服者,而语言的发出者一般是少数人,他们通常是权力者或者是政治活跃分子。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语言所包含的主要术语虽然在其意义上是出奇的不稳定,但在表达的“形式”上却具有极高的稳定性,几乎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人人都可以使用。例如:“民主”、“共产主义”、“人民”、“公共利益”,没有其它语词比它们更清楚地表明,人们在使用这些术语时做出了极不相同的理解。然而,置身于政治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如此热衷使用的这种语言,除了传播混乱的语义之外,一定还会有其它的政治功能。
说服型语言一般由前提、推理和结论构成。前提和推理有时直接表明,更多的时候则是隐含的或被省略。这种语言的基本功用在于诉求公众的支持。诉求的普遍性正是它最明显的形式特征。
在政治过程中,不管言者是否赞成某一项特定的诉求,也不管所使用的术语是如何地模糊,但只要使用了说服型语言,一般就表明公共政策需要大众的支持,以及那些被诉求的公众对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利害关系并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其前提或推论可能具有争议性,但诉求是必须的,公众的回应会对政策形成施加影响的这种假设在事前已被接受。而且公众的每一次认真的回应都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假设。因此,说服型语言的中心意义是普遍参与和理性。即通过在政策制定中强调公众参与和理性,说服型语言意在促进公众对政策的接受,使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得到确认和强化。
但是,很多对于大众的政治诉求其实带有浓厚的情感特征,比如在政治激励和政治规劝行为中。而公众也会更经常、更容易地以情感化方式予以回应。因而,统治精英对说服型语言最精明、最有效的运用。就是把情绪化的诉求隐藏在具体的问题之中,而关键性语词在外观形式上的理性色彩会使这种策略更具可行性。例如,一种革命话语——通常由群体内的精英人物所建构而又被其追随者所普遍使用——就是充满激情的语言,其主要特征是关注话语对于听者在情感上所产生的效果。这种效果并非来自于理性的、逻辑的判断,而是基于情感性的联想。革命话语因为是情感性的,所以它常常成为一种高效的政治炸药,用来摧毁它所攻击的目标。这在雅各宾党人的文告中,在列宁的革命宣传册子中,在红卫兵的口号中都可以窥见一斑。
由此可见,说服型政治语言存在两种子类型,即“理性说服”和“操纵性说服”。理性说服严格遵守逻辑规则,它准确地传播严格、真实的信息。但是,理性说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想类型”,它只能暗藏在关于理想社会的种种观念的核心里。绝大多数的说服都或多或少地具有操纵性的特点。广泛诉诸对象的情感反应的革命话语就是一种操纵性说服,其目的是要听者的思想或行动符合操纵者的主观意图。各类革命精英正是通过运用情感性语言来操纵社会心理并达成他们的政治目标的。罗伯特·达尔就此评论说:“虽然操纵性说服的道德水准被认为远在理性说服之下,但在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论述中,人们常常以伟大的目的为理由来证明本质上坏的手段是合理的。因此,柏拉图为了建立他的理想国的目的而鼓吹操纵性的说服。所有的政治运动,从左到右的,都在步柏拉图的后尘。”(注:(美)罗伯特·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王沪宁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59页。)
(二)法理型语言
宪法、法律、以及司法判决等,是法理型政治语言的主要文本。虽然确定法理型语言意义的简明方法是使用其辞典涵义,但这种语言对于外行的公众和权威者们却存在不同的意义。公众或者很少见过这种语言,或者发现这种语言不易理解,而那些权威的解释者们却很清楚,这种语言的意义在事实上几乎完全是模棱两可的,法律、法规所具有的辞典性涵义与其实际运作几乎毫不相关。(注: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第139页。)但正是这种语言的模棱两可的特性赋予了法官、律师和官僚们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因为根据定义,明确的规则既不需要解释也不需要就其含义进行争论。当官僚、法官和律师们对一项立法指令进行激烈争论时,这种情况正说明法理型语言本身的意义是模棱两可的。
不过,法理型语言的辞典意义对大众却具有两方面的重要功能:第一,它给公众认为存在一个精确的、客观的和可操作的法律定义的假设提供了认知基础;第二,它为有组织的群体证明他们的行为与这种无知的假设相一致提供了语言和词汇。尽管这些词汇的精确定义从来也未曾引起注意。
在结构上,法理型语言一般由概念、定义与命令构成。这些形式构成要素在公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以至于生发出许多关于法律正义的神话。典型的大众回应就是认为法律“十分精确”,因而要求严格依法办事。与之相关的意义就是要保证公众至上和立法至上。法律信念对公众的意义可以被描述为:法规反映了公共意志,它们十分明确清楚并且具有强制执行性;法规由法院与行政机构来贯彻与实施。与此相对应,人们对行政和司法实践行为的批评常常集中在它们违背了大众与立法机关的意志。
在另一方面,法理型语言对于那些专司解释、运用和执行这种语言的立法者、法官、官僚和律师又有什么意义呢?关键之点是,这种语言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在意义上的灵活性即弹性:语言的意义会随着权威者、时间、环境与政治利益的变化而被作出不同的解释。对直接相关的人来说,灵活性、模糊性是他们使用这种语言最有用的特征。而对外行的大众来说,这种变化则被认为是对神话式规则和信条的一种偶然的、应该谴责的背离。(注: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第141页。)
与普通意义上的欺骗相比,这是一种更精妙、也更具重要意义的现象。 如果法律体系仅仅是简单的伪装,那么整个体系就会很快崩塌,并会被另一种更适于表达和解决精英——大众冲突的制度所代替。由于法理型语言的上述两种意义都会得到来自精英和大众中不同群体的强有力支持,因而这种语言就具有实质性的社会功效。反之,法理性语言一旦丧失它的逻辑意义和象征意义,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符号学危机”。
(三)行政型语言
行政性规则、制度和规章的语言风格在很多方面与法律、法规的语言类似。比如,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和定义的精确性就十分显著。但在两个主要的形式要素(语言的创造者和听众)方面,它们之间却有很大差异。
首先要注意的是,行政性语言是由被任命的官僚们所创造和使用的。行政型语言是向特定公众或属员传达命令的一种语言,它要求受众遵守这些指令并马上执行。因此,官僚们强烈的权威意识和潜在的专断性是这种话语的典型特征。
由于权威、专制和武断这些特征渗透于行政话语中,很自然,公众通常以愤怒和幽默等情绪化方式作出回应:嘲笑官僚的行政行话,指责、批评话语中的专制特征。而那些对行政政策不满的人,也往往充分利用大众对官僚的此种普遍反应模式而反向传播自己的目的,而且这种策略一般都很有效。例如,与行政官僚竞争权力的其他“政治人”,如人民的代表们就会加入到对行政的此类攻击中。部分原因在于他们想实现对资源分配的实质性影响,部分原因也在于想证明他们对行政的回应与大众对行政的回应是一致的。作为公众的代表,他们能从这种证明中获得一些收益。在中国,一个有关的例子是,毛泽东利用大众对官僚机构的固有情绪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人民”非常迅速地作出了反应。整个运动持续了十年。
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公众对行政型语言的回应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心理:当把注意力集中到宏观的体制方面时,大众最为关注的是行政官僚们在“主权在民’政治神话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常会认为,行政行为的意义只可能表明官僚们在贯彻大众的意志和执行立法机关的政策。但是当把注意力集中到一项特定行政命令的实施时,大众的另一种反应是:认为自己不得不服从而又没有争论的余地。
(四)交易型语言
交易型政治语言是在政治交易者之间发生的语言,而交易者一般是少数的个人,并多在私下进行交易时使用。因此,这种语言不像前三种语言那样,明显地渗透在政治过程之中。但它却是各种政治过程中一种必要的催化剂。
同说服型语言一样,交易型语言也是要获取对某种政治主张的支持。但这两种语言在运用的场合、涉及的当事人以及它们所传达的意义等方面存在根本区别。首先,交易者提出的是一种交易而不是一种请求;其次,用于交易的价值在性质上是对立的,而不是共享的;第三,交易双方的角色地位相似;第四,交易要尽量避免公众的回应而不是诉求于公众;最后,交易是在对等物的交换中完成,而不是通过某种理性前提建构完成。(注:Robert A.Dahl and Charles E.Lindblom,Politics.Ecomomics,and Welfare,(New York,1953 ),Chaps.10.)
政治交易的实例很多。例如,立法活动中代表们的协商与合作、重大会议前在权力分配上的讨价还价、行政管理中的行贿和受贿,以及在政策偏好相互冲突的政府部门间所进行的谈判、协调活动等等。而内部委员会和跨部门的联合委员会的设立,则表明从制度上正式承认政治交易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因为交易在本质上是秘密的,而且谈判中的实际话语从来都不会正式公之于众,所以它传达意义的重要的形式要素就只有情景:涉及交易的各方当事人和结果。而过程、语言和所有细节都被排除在公众的视线之外。通常,参与者都力求忽略和隐藏他们进行交易的行为,而强调他们保护公众利益的目的。但是,交易语言的意义对于交易者自身而言,几乎不存在模糊性。只有模糊性作为在明确的中心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手段时,它才是有意为之的、被各方认可的和可以容忍的。当然,交易和交易语言中的模糊性必须严格保密。没有大众的反应是模糊性存在的前提条件。
有时候,例如在条约谈判中,强大的公众压力会要求双方当事人宣布一项协议,这时所使用的术语就可能具有模糊性。不过,这时的模糊性语言恰恰证明没有交易或交易失败。在这种情况下,交易者向公众的说明,通常就会换用为说服型或者法理型的语言。
三、政治语言类型的意义与功能比较
将四种语言进行对比分析,一些重要的观点就明显了。 当从说服型语言逐次过渡到交易型语言时,每种语言的意义在听众和说话者之间所产生的差异就会变得越来越小。也就是说,这种过渡是从语言意义几乎完全矛盾的情景过渡到没有差异的情景。与此同时,语言所涉及的听众范围也越来越小。因而,政治语言传达给公众的意义与反映在政治小群体中的意义是不相同的。而且,当政策由明确的意义界定向实质性的价值分配过渡时,公众所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小。(注:Murray Edelman,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5),第149页。)
各种类型的政治语言具有不同的政治功效。简单地讲,说服型语言是为了获得合理性,其主要功能是让公众消除疑虑。法理型语言是为了获得合法性,而行政型语言则是谋求权威性。同法理型语言一样,它具有强制执行性。而交易型语言的本质是秘密性。交易所追求的是避免公众的反应,并避免在公众中出现交易正在发生的清醒意识。
在一种政体中,统治精英通常不止运用一种语言类型。这一事实有助于理解政治分歧和冲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解决。例如,使用说服的和法理的语言,会在社会中产生出“人民”被代表的感觉以及精英正在保卫公众利益的“现象”,其主要作用是向公众传递政治承诺。通过行政的和交易语言的运用,政治小集团获得了实质性的利益。但是行政与交易语言会引起大众的疑虑,因而它们通常与说服的或法理的语言紧密相连。这一事实根容易使公众在政治过程中,低估交易和行政语言这两种公众性程度较低的语言类型的重要性。而过高估计说服和法理语言对资源分配的重要性。
如上所述,交易中所包含的说服型或法理型语言通常是交易未成的信号。但这两种语言的意义通常是模糊不清的。因而,一项宣称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与大众的公意相一致的声明就正表明,公众作为明显的受益者已在事实上遭到排斥,而另一些人却已获得实质性的好处。而且,这项声明也只不过同其它类似的和不断重复的官方话语一样,是在向公众做出的又一次的象征性保证。
一般而言,四种语言类型会同时存在某一政体中,但它们的重要性却会因政体的不同而呈现很大差异,因而政治语言可以成为观察不同政体特性的指示器。理性说服因其道德上的独一无二的地位而得到了民主政体的推崇。公民进行相互的理性说服,自愿地接受讨论结束时所作出的集体决策和产生的义务,这是许多民主思想的理想内涵。法理型语言与理性说服在性质上的一致性也使法治思想成为民主思想的核心。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政治人普遍认同交易型语言的重要性。即认同在既定的游戏规则下,以讨价还价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利益。但大多数集权主义政体则擅长运用行政语言和操纵性说服。因为强调社会的一致和对权力的服从,行政话语的权威和专断属性特别符合集权主义者的胃口,而基于平等精神的讨价还价语言很难有存身之地。集权社会不需要理性说服,因为“服从就是一切”。当然,现代集权主义也喜欢穿上法理语言的外衣,以“人民”、“国家”、“民族”的名义说话,并以此压制对政治的不同意见。这种对法理语言的滥用最易于掩蔽其政体的专制实质。
认识到语言、经历与意义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我们就可以通过对语言的分析来探求政治动力的一个侧面。坦率地说,这个侧面一般是很难被观察到的。对政治语言类型和形式特征的此种分析提醒人们应加强对政治语言和象征策略运用的持续性观察,而不是引导我们简单地、想当然地认为,政策的权威性声明就必然预示了资源分配的真实情形。
由这些语言的意义所结成的社会联系形成了一个政治网络,这个网络也形成了某种修辞学传统和风格。而在其中,语言意义所表达和论及的,则是更具持久性的政治神话。因而,不种形式的政治语言不仅表达着意义,而且,正是意义居于政治解释的中心地位。各类政治语言构成政治神话的建构材料和技术,从而也成为政治话语霸权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