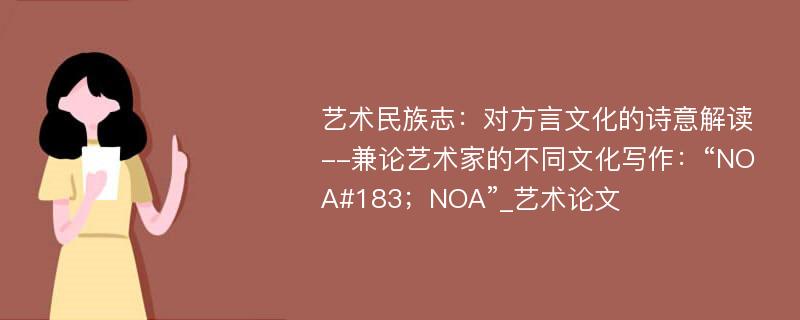
艺术民族志:一种方言性文化的诗学阐释——兼论艺术家的异文化写作:《诺阿#183;诺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异文论文,诗学论文,方言论文,艺术家论文,性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0-03;G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07-0140-06 艺术人类学是以文化研究为基础的人类学分支学科之一,秉承着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的基本研究方法论,注重于研究世界边缘化族群的日常审美和节日仪式。民族艺术是族群文化的鲜活象征,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符号的显现形式。因此,“艺术田野”的民族志写作应兼具文化记录和诗学阐释的双重性。 而现代派艺术家高更,在塔希提岛的异文化写作《诺阿·诺阿》中曾耀亮的某些火种,为艺术家的民族志写作,做出了一些开拓性的尝试。在塔希提岛上,高更与土著居民有两年的生活体验。在此期间,他选择了与土著居民同吃同住的生活方式。在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的过程中,他与当地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比之人类学家在田野点拜土著人为兄弟或父母,高更以更直接的方式成为了当地人:他在这片充斥着平淡、善良与温情的土地上,找到了爱情的归宿,迎娶了一位塔希提新娘。作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他从未停止过艺术创作,更没有停止过对异族文化生活的思考,表明了人类学家的精神气质。他以田野随笔形式写出《诺阿·诺阿》,虽然这本手记没有详细分析异族文化的艺术样式,不能成为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民族志,但是,它与当下热议的人类学诗学和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有着跨越时代的共振;也为艺术家的民族志撰写,以及基于异族文化思考的自身艺术创作提供了可鉴的思路。 一、功能与阐释:民族志写作的转向 Ethnography一词来源于希腊文,词根enthno代表的是人或种族的意思;graphy意指书写。从字面上看,民族志也就是关于特定人或人群的书写。在中国,最早的类似于民族志的记录,见于《史记》的《西蛮夷列传》。其中记载了我国西南(今云南以及贵州、四川西部)地区在秦汉时代的许多部落国家的地理位置和风俗民情,以及同汉王朝的关系,记述了汉朝的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等汉朝官员抚定西南夷的史实,描述了夜郎、滇等先后归附汉王朝,而后变国为郡、设官置吏的过程,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域的不同民族形成一个和睦的多民族国家的必然趋势。而自人类学在西方正式成为一门学科以来,特别是在马林诺夫斯基的倡导下,开创了“田野工作一民族志”的研究范式,民族志成为异文化记录、传播的主要载体,他以《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奠定了现代民族学之文化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论。 在文化研究的宏旨下,人类学者撰写民族志的功能一般有两个。第一,在照相影视技术尚欠发达的20世纪初,人类学家依仗纸和笔,做一种异族社会生活的民族志文本照相。在对个别部落社会文化事实描述的基础上,建立世界各族文化的资料库,以便做进一步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第二,通过民族志的书写过程,研究者对异族文化知识做了更进一步的细化和梳理,从而让自己的观察更加贴近于他者。别林斯基曾说:“民族性是民族特性的烙印,是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的标记。”[1]要描写处于特定场域的民族生活,意味着作家应真实地体验那里的生活状态。因此,民族学研究者都需要在异域完成至少一年的持续观察,确保能够完整观察、记录该群体的社会文化活动,以便尽量科学、客观地描述观察对象。 诚然,经典人类学作为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范畴,其学科性质首要体现在其科学性和实证性。为此,马林诺夫斯基将人类学定义为一种“文化的科学”。但是,知识之于主体的观照总是趋于一种相对性的存在:虽然马林诺夫斯基有着建立精密客观“文化科学”的宏愿,但是民族志的写作,其客观性本身就是有待商榷的。随着马林诺夫斯基的去世,他身前的一些私密的手稿也得以公开。其中一些言论,让人更加质疑所谓“文化科学”的民族志写作。马林诺夫斯基曾写道:“至于民族学,照我看来,土著的生活完全没有兴味和意义,他就像一只狗的生活一样离我那么遥远。”②在此不难看出,“文化功能主义最初包含着作者角色的自我意识,只是被隐抑于客观‘程式’”。[2]马林诺夫斯基以这种态度来观察和分析异文化而写出所谓的“科学民族志”,其科学性和客观性难免让人质疑:潜意识层面的“主体情感的偏好性”与意识层面的“理性科学的客观性”同时存在于民族志写作中。 这种二律悖反,被后来的解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捕捉。格尔茨将田野工作界定为对解释的理解,其著作《文化的解释》写道:“在即将完成的人类学写作文本中,我们称之为资料(data)的实际上是我们对他们及其同胞所做解释的解释……在全部人类学事业的基石之上我们已经在进行阐释,而且更加不妙的是我们在对解释本身进行解释。”[3]他力图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科学性转向为文化解释性。人类学的研究重心由此从族群行为和社会结构的探讨,转向为对文化符号、象征意义和思维方式的研究。他本人深受胡塞尔现象学、伽达默尔阐释学的影响,在其阐释人类学理论辐射下,民族志文本的写作方式也发生了转向:族群文化的本质直观不再是写作的最终目的;相反,民族志写作活动成为一种创作,是解释主体对客体文化现象的交互阐释,从而使文化符号的意义得以生成。此过程尤其突出了主体性的理论倾向。这种主体性范式的显露与当时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话语转向有关:从现象学到阐释学,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等等,这无一不是对主体性话语的理论和现实回应。 因此,人类学家在进行文化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过程中,走人由地方性知识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从而对其文化符号的能指与所指(更多情况下,可能是一种“滑动的能指”,即一个能指对应多个所指)进行主体性阐释。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点,“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被意识到是一种撰写的作品,人类学家的志趣从理性、科学、实证、结构,转向人文、体验、理解、阐释、解构。人类学范式的这个转换使得它在作品的主观性、建构性、话语性及意义创造等方面,越来越将诗学作为民族志写作的一种实验方法。”[4]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家所写的民族志必须让读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异族文化,确信作者到过此地。那么,书写者就会不可避免地运用风格化的语言表述,其文本写作会达到一种文学性倾向。 格尔茨在《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中,分析了列维·施特劳斯、埃文斯·普理查德、马林诺夫斯基、露丝·本尼迪克特这四位身份不同的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作品。他指出:由于以往的经验,所处的社会阶级身份的不同,各人的民族志文本都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化写作倾向。“人类学家究竟在干什么?格尔茨抛开‘他观察,他记录,他分析’的标准答案,响亮地回答:他在写作。既然是‘写作’,那就免不了存在个人性、主观性、文学性的因素了。”[5]乔治·E.马尔库斯也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书中回应道:“获取关于这个世界的精确而自信的知识,唯一的途径在于借助复杂精致的认识论来充分地重视和考虑在解释人类行为时碰到的那种难以应付的矛盾、悖论、反讽以及不确定性。这看来就是不同人文学科中涌现出来的、对我们所界定的当代表述危机之反应的精神实质。”[6] 其实,从根本上说这也是一种从文化本体论(客观、本质、功能)到文化认识论(主观、阐释、意义)的写作转向,即从文化理式的分析到文化叙事之探究的转向。自此,阐释人类学对传统的民族志写作提出了质疑,也不再关心古典人类学关于社会形态进化进行划分的宏大叙事。以此作为背景,格尔茨认为人类学则不应遵循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反对提出普适性的教条律令,转而对具体、个别的社会群体做深入而细致的文化内部分析,以文化深描的方式来揭示其社会行为的意义内涵,他将人类学的学科发展做了一个人文研究的转向,让一门冷冰冰的实验科学有了人文关怀的温暖。[7] 二、拘囿与超越:艺术民族志的方言性诗学建构 这种人文研究转向,为艺术人类学的民族志写作提供了新契机:艺术逃开了理性与科学的拘囿,才能更为感性灵动地呈现于世;也为民族艺术的二度创作提供了新空间,让民族文化以诗学的文本表述和艺术展演的活性形态得以传播和传承。再者,艺术在非理性力量的促使下,往往能产生伟大的作品,这也与原始民族的野性思维和诗性思维有关,高更在塔希提岛上的一系列艺术作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未开化人的诗》《苔拉》等等,无一不表现着异族文化中常见的图式和色彩。 因此,艺术人类学家的创作可以基于两种形态:具体的艺术形态和民族志文本形态。第一种是艺术人类学家提炼异族文化中的活性审美要素,对地方艺术的一种个性化二度创作,其创作形态可还原为之前的艺术形态,也可能被艺术人类学家以自身最为熟悉的艺术语言来重塑,如乐器、歌谱之于音乐家,画作、雕塑之于美术家;第二种便是基于异族文化“阐释之为阐释”的民族志创作,即一种地方性审美文化的个性化文本揭示。前者是纯艺术形态的还原或给予,后者便是研究者对异族艺术形态和文化美学的文本阐释。③艺术原本就是一种情感符号的外化,情感的质素不可能以科学的计量单位来度量。因此,艺术民族志的文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仅仅囿于科学性的记录照相之文本,而是一种关于文化的情感记忆和关于艺术的审美经验表达,那么就必然是一种诗学向度上的阐释和写作。由于民族艺术是带有地方性特征的、一种族群文化的感性显现,所以艺术民族志得以成为方言性文化的阐释性诗学写作。 诚如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在《文艺复兴与自我造型》中所写的: 我在本书中企图实践一种更为文化的(cultural)或人类学的批评(anthropological criticism)——说它是“人类学”的,我们是指类似格尔茨、詹姆斯·布恩、玛丽·道格拉斯、让·杜维格瑙、保罗·拉宾诺、维克多·特纳等人的文化阐释研究(interpretive studies of culture)。上述学者并不同意聚集到一面旗帜之下,其中更少有人分享同一种科学方法。然而,他们确实认同一个信念,即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未加工琢磨的动物”,生活现实并不像它们看上去那样缺少艺术性,而那些特殊的文化及其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一种对于现实的隐喻性把握(metaphorical grasp),并且还认为,人类学阐释工作应当较多地关心某一社会中的成员在经验中所应用的阐释性构造,而不是去研究习俗与机构的制动关系。与此类工作有着亲缘关系的文学批评,因而也必须意识到自己作为阐释者的身份,同时有目的地把文学理解为构成某一特定文化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这种批评的正规目标,无论多么难以实现,应当称之为一种文化诗学(poetics of culture)。[8] 如果说,“诗学的转向”为艺术民族志的文本写作打开了更广阔的方法论空间,那么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缺陷,则形成了艺术民族志写作的第二层拘囿。当下的艺术民族志文本,多是由民族学、人类学出身的学者,基于文化整体观的宏旨下所撰写的。这种写作为民族学交叉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是由于研究者在艺术学、美学方面的知识结构空缺,导致对其所观察艺术本体,即艺术形式层、艺术语言层的分析不甚明了。激进一点来说,“艺术品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作为一个特殊构造的语言事实。这样一来,艺术品成了一个自足的本体,而与外界没有任何联系,只有形式是唯一的存在”。[9] 研究者基于艺术形式本身的分析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就亟不可待地绕到艺术背后来言说文化整体;而在此基础上所写作的艺术民族志难免是隔靴搔痒。如内蒙古的长调,如果仅仅将“长调”作为一种文化仪式,即讲述蒙古族对于草原情怀的歌赞,以一种艺术的仪式来概括其族群的文化全景——这固然是传统人类学对于民族艺术的权威研究方法;但既然研究的对象是艺术,则不能仅仅只谈到艺术他律性的层面;更需要从艺术自律性的层面做分析。就长调而言,它与处于其他文化范式中的音乐有无对比印证的价值?长调的装饰音演唱与西方巴洛克时期的装饰音演唱方式有何区别,此区别中所蕴含的审美精神的差异如何分析?笔者认为,这种差异性既是一种文化本体之间的差异,也是一种艺术本体之于言说方式上的差异。因此,只有在全面把握这种艺术语言的方言性特质之后,才能进一步揭示出其地方性的“族群审美精神”,最后触摸到隐于艺术和美学之后的“文化全景”;即完成一种从艺术语言至审美精神,到文化逻辑的三阶段梯度上升,三个层面绝不能一概而论。 反过来说,一些研究音乐和美术的学者借用人类学的田野方法来研究地方性艺术作品,则收获了较好的成果,如音乐人类学家布鲁诺·内特尔、A.P.梅里亚姆等等。可见,研究者自身的艺术素养对于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至关重要。对于兼具深厚艺术素养和人类学训练的研究者而言,观察异族文化的目的不局限于对客位文化的记录和描写,也是对自身创作的灵性启蒙和既有文化观念的诗意再造。 艺术民族志的文本写作,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拘囿于一种科学和实证的真实,更在于一种情感和艺术的真实。艺术与审美的这种灵动的真实比之实证意义上的确定性更赋于超越的地位。这种灵动的真实需要诗学文本表述,如果忽略了主体的意识和情感,艺术本体的意义也就消解了。笔者在此结合细读高更的塔希提手记《诺阿·诺阿》中的一些段落,来分析艺术人类学家在进行异文化写作的叙述手法和主体审美状态的转变。首先,《诺阿·诺阿》多处运用感情细腻的诗意性语言进行表述: 在绛紫色的地面上,散落着一些长长的树叶。他们拳曲着,呈明黄色;看上去像是遥远的东方哪个国度的文字……一道隐蔽的目光从那上面射入大海的深处。芸芸众生触及了科学之树,犯了罪,犯了胡思乱想的罪,现在已经被大海吞咽。这个盔饰下面也有一个头颅;我觉得它和斯芬克斯有一种说不出的相像之处。你看,那道宽宽的裂缝,不就是它的嘴吗?你看,那嘴角的笑意,不正向埋葬着往事的波涛庄重的投去讥讽与怜悯吗?夜幕完全闭合了,莫雷阿进入了梦乡,寂静包围着我。今天我总算领略到了塔希提岛上夜的寂静。[10] 高更以诗意的语言,言说着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倡导民族志诗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把简化为文本的僵化的文学还原为具体传播情境中丰富而多彩的活的文学。”[11]这种方言性诗学的写作方式,能更加生动地捕捉到特定生态文化机制所建构和维系的审美认同及隐匿其中的审美权利,也提供了对艺术蕴含加以调节和把握的诗学深度和阐释空间。方言性文化的诗学表达,是作者基于“文化他观”到文化自观,从参与观察到观察参与之后的一种文化经验性考察与诗学审美性描述的视域融合,并意指一种文化与人文的回归。文化艺术的方言性与民族志表达的诗学性在此成了文化文本的同一。 从主体上说,异族文化的田野经历也为观者带来了多角度的文化视域和艺术审美观念的重塑: 我的境况一天天好起来,还学会了当地人的话。他们所说的,我差不多都能听得懂。我的邻居们——有三家住得很近,其他远近不等,但为数不少——不把我当外人看待。我的双脚经常和石子碰撞,脚掌长满厚茧,赤脚在土地上走也非常自如了。衣服穿的很少,几乎终年赤身露体,太阳再毒,也不怕晒了。文明慢慢从我身上消退,我的思想也变得单纯了。对邻居们的怨恨所剩无几:相反我开始喜欢他们了。[12] 在此,作者从场内的局外人慢慢向社区的一员进行着身份意识转换。身份意识的转变,也随之带来了审美判断和文化观念从西方中心主义视域的“你们”,转成文化相对论尺度下所称的“我们”。 神像被放到雕刻华美的担架上,由祭师们抬着出了庙门;新国王则由几个首领抬着,走在后面,仍然由阿里奥依簇拥着,向海边前进……老百姓打破了仪式开始以来的沉默,发出响亮的呼喊……国王卧坐在席子上,接受臣民“最后的洗礼”。好几个一丝不挂的男子和妇女在国王周围跳起猥亵的舞蹈,并千方百计地用身体的不同部位触碰国王的身体,使他难以避免受到最不体面的玷污……不过,请允许我谈点不同意见:这些场面并不是无美可谈的。[13] 高更在此达到了一种美学意义上的同情之理解,也就是从主体性的认识论上升到一种主体间性的理解论,他已经完全浸入式地体验到了当地文化的美学意义。即是说,他是从“文化自观”的“内部人”的视角,来审视作为艺术的仪式的美学价值,从而发现其族群内部的文化张力。也只有具有广阔的人类学视野和深厚艺术积淀的研究者才能达到这种方言性诗学的写作范式。 三、从“文本”到“本文”:诗学与生活的间性 诚然,地方艺术的意义和价值并不完全在于其艺术形式的自律性本身,更在于对作品成形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语境的交互阐释。在此阐释过程中进而实现由文本走向文化,从艺术美学走向意识形态,进而揭示出其地方艺术形态的寓言价值和文化意义。对于艺术民族志而言,狭义的诗学是一种浪漫化的文本表述;而从广义上讲,诗学也是一种态度,是艺术人类学家在田野时,所应具有的一种开放的“生话审美”心态和“诗意创造”精神。艺术和诗总是一种关乎生活的隐喻。而方言性的文化幔帐成为艺术和审美生成的独特场域。在此场域中,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二元结构双重叠合,成为一种象征性符号的隐喻,最后衍生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生态系统。因此,生活文化的观察与诗意审美的写作,理应在艺术民族志的文本层次上,形成一种“形式对话”和“阐释共鸣”。进而言之,生活文化的体验与艺术审美的表达,在艺术民族志的写作上是两个共在的向度,即“文化诗性的阐释”和“文化阐释的诗性”。 再者,异族的艺术形态、审美观念和文化逻辑是以日常生活作为前提的;这即是说,其研究必须以族群的现实生活样态和艺术活动作为支撑。以此作为论述的逻辑起点,艺术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应以日常活动审美为基点,日常活动是一个民族与自然世界沟通的媒介和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对内凝聚、对外排拒的一种表现形式,受生活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特定的审美思维方式和观念信仰,并指向一个特有的意义世界,一个包含着真、善、美、用的特殊维度。 田野工作的目的,就是让研究者进入调查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从他们生活中不经意间所表露的无意识细节,如谈话中细微的肢体行为等等,来解释地方性艺术和文化中所存在的“内隐性”。例如: 晚上躺在床上,我俩喜欢没完没了的长谈……在这个女孩的心灵深处,我搜寻着往昔的踪迹……我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地询问,她的回答常常是令人满意的……苔拉按时到教堂去,用嘴唇和手指做着官样的礼拜。但是,她能背出毛利族奥林帕斯诸神的全部名姓;知道他们如何创造世界。[14] 高更惊奇地发现,有些毛利人的信仰是多重的,塔希提的塔阿罗阿神和外来的耶稣基督相安共存。在类似的谈话中,他分析了毛利人关于月亮的文化情节,深入观察了原始居民关于天人意识的宇宙观思考: 有时候,碰对了机会,她就给我上一堂塔希提神学课;毛利人似乎连月光的性质都有所了解。他们设想月亮是和地球大致相同的球体;和地球一样,月亮上也有人居住,也有种种物产。他们用自己的方法测量从地球到月亮的距离。奥拉树(榕树的一种)的种子,是由白鸽从月亮上带到地球上来的。白鸽飞了整整两个月才到达地球的卫星。又过了两个月,终于返回地球。[15] 在此之上,高更进一步挖掘出,月亮与毛利人的信仰及其思维方式有很重要的关系: 在毛利人的“形而上学思辨”里,月亮占有很主要的地位。过去,好几个盛大的节日与月亮有关。阿里奥依帮会的传统记事也常常提到月亮……首先是明确提出了世界的两项基本要素。他们是普遍的、无所不包的,又是唯一的、没有例外的。然后,这两项基本要素又构成一个至高无上的统一体。一个要素是阳性的:灵魂与智慧,塔阿罗阿,等等。另一要素属于阴性,纯粹是物质的,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造物主自身的身体,它就是希娜女神。希娜不仅仅是月亮的名称。还有“空气女神”希娜、“海洋女神”希娜和“内部女神”希娜。不过这个名字仅仅属于空气、水、土地和月亮;太阳和天,光明以及它的帝国,这些都是塔阿罗阿的范围。[16] 从此不难看出:在毛利人的世界里“塔阿罗阿”象征着阳性;而月亮女神“希娜”象征着阴性,并将这两项作为他们文化中最基本的二元对立结构。而且,毛利人将月亮阴晴圆缺的连续变化视为象征世界永恒和生命终结的图式:“毛利人把月亮看成永恒运动的体现,把月亮这个星辰列入永存事物的数目之中。它熄灭是为了重新燃亮,它消亡是为了重生。”[17]由此可见,毛利人颇具哲性和诗性的思维,并内化成他们日常生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常常呈现为一种充满想象和诗意的模式,这即是说原始思维中带有某些诗性思维的要素。人类符号学家卡西尔将这种类似的思维称之为隐喻思维(Metaphorical thinking),认为这种思维不是按照一般的逻辑程序去思考事物,而是先于逻辑的一种概念和表达方法,即呈现出一种形象的直观、模糊的混沌性,喜爱用想象、联想、比喻来思考而缺少逻辑推理的抽象提炼,这中思维方式也正是使其文化生活所具有的诗性特征的关键所在。 这些诗性的要素,也在于原始思维或隐喻思维对生活世界的一种创造性的想象,表征着一种生活场向审美场的互换与同构。人类学家可以通过民族志的写作去把握这个面呈于我们眼前的生活文化,并力求提炼其诗性的意义,进而才能以诗性的文本表述将其呈现于世。作为文化现象的内容是片面的,但意义的阐释空间却为人所敞开。那么艺术民族志的写作就必然是一种方言性文化的诗学阐释。 因此,艺术民族志,旨在以其可考的族群文化艺术现象,展开多维阐释的对话性空间,在对话的过程中完成一种诗学的描述。达到艺术民族志(文本)到文化生活(本文)的互文,即“文化阐释的诗性”与“文化诗性的阐释”的一种间性的互补与互渗的状态。这种互补性和互渗性也进一步说明,艺术和审美不属于实证科学和伦理学的范畴,而是从诗学意义上,对其族群艺术文化符号的一种审美阐释。诚如李泽厚所言:“艺术不是理智所能替代、理解和说明,它有其非观念所能限定界说、非道德所能规范约束的自由天地。这个自由天地恰好导源于生命深处,是与人的生命力量紧密联系着的。”[18]因此,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志写作,并不能贴切地表述异族文化中艺术和美的内隐性。故而,艺术民族志惟有建立在一种诗学阐释的基础上,才能更加贴近其方言性文化中的艺术精神。 ①此处用“方言性”而不用“地方性”来指称民族文化,原因在于:民族艺术与文化符号的象征系统都可视为一种语言的符码,亦即“能指”与“所指”的对应性表达方式。在特定的人文场域中,文化语言和艺术语言的表达有其方言性的意味,而这种方言性不仅仅在于指涉共时性的他律因素,或者一种空间层面的地方性或地域性因素,也在于一种历时性的文化自律性选择,英语中的localism也有方言性的文化含义。 ②原文:As for ethnology:I see the life of the natives as utterly devoid of interest or importance,something as remote from me as the life of a dog.Bronislaw Malinowski,A Diary in the Strict Sense of the Term,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67. ③在此,必须将书写文学与艺术区分开,因为有些民族是无文字的,也就不存在一般意义的文学艺术了,民间传唱的口头诗歌应该列入展演或表演艺术一类,而非异族自身的书写文学。因此,这里的“书写文学”专指艺术人类学家基于异族文化生活所写作的文化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