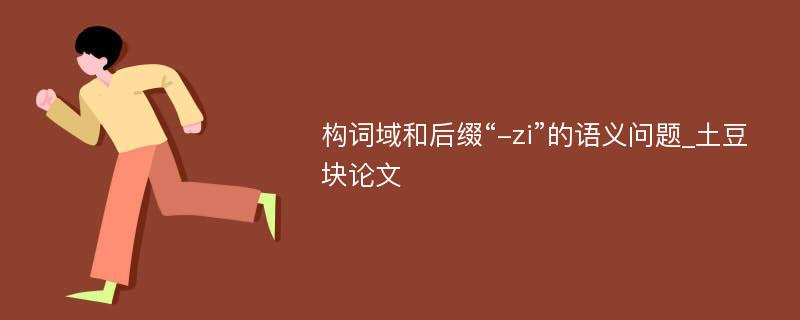
构词域与后缀“—子”的语义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后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子”作为词缀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但有两个问题是有分歧的。一个是“—子”的语义问题,这个问题又包含两个方面:(1)“—子”有没有贬义色彩,(2)“—子”有没有指小功能。另一个分歧是“—子”的鉴别问题,即什么样的“子”是词缀,什么样的不是。本文重点讨论第一个分歧,但第二个分歧也绕不开,不过不做重点。要讨论第一个问题,需要提出一个新的范畴:构词域。
二 构词域
语索是用来构词的,同义语素往往都有构词能力,但在构词活动中又不能随便选取。比如在表示wall这个意义时,汉语有“墙”和“壁”两个同义语素,观察二者的构词结果我们发现二者构词能力差不多(从构词数量上看),但各自适用的领域不同:
墙:墙根儿 墙角儿 墙头儿 墙体 墙裙 墙基 墙面儿 墙皮
壁:壁灯 壁橱 壁柜 壁画 壁虎 壁炉 壁纸 壁钟 壁毯 壁挂
以上材料显示给我们的事实可以作这样的概括:如果要构成与“wall”的自身结构有关的词,选择“墙”;如果要构成与“wall”的附设物有关的词,则倾向于选用“壁”。“墙”和“壁”意义相同,构词能力相近,只是适用的构词领域不同。我们把语素适用的构词领域叫做构词域(word-formation scope),“墙”和“壁”在构词上显示的对立是二者在构词域上的对立。这种对立说白了,就是同义语素在构词时有较为明确的领域分工。为避免孤证立论,我们再举些例子。
在room这个意义上,汉语有“屋”和“室”两个语素,二者构词域上的差异是:构成与房屋结构有关的词语用“屋”,构成与房屋功能有关的词语用“室”:
屋:屋顶 屋地 屋门 屋角 屋脊 里屋 外屋 东屋 西屋 南屋 北屋
室:阅览室 卧室 会议室 实验室 办公室 资料室 手术室 休息室 陈列室
“皮”和“肤”也是一组同义语素,和上举两组同义语素一样,它们也各有自己的构词域:“肤”用于构成与人有关的词,而“皮”则倾向于“非人”构词领域,只有在构成无褒贬色彩的医学名词(植皮、皮炎、牛皮癣、皮疹)时“皮”才可进入表人构词领域①:
皮:羊皮 蛇皮 狗皮 虎皮 树皮 书皮 所料皮 地皮
肤:护肤 润肤 肌肤 肤色
周韧(2006)在讨论“单单式VON型复合词”(如“植树节”)时,认为“如果备选的语素有粘着语素和自由语素,那一般倾向用粘着语素来构造这类复合词”。举例论证说“收银台”“收费站”“收款机”都不能说成“收钱台”“收钱站”“收钱机”,因为“钱”是自由语素,而“银”“费”和“款”都是粘着语素。可是我们也很容易举出“耍钱鬼”“有钱人”“值钱货”“赔钱货”“赚钱术”这样的单单式VON型复合词,这些结构里用的都是自由语素“钱”,并且都不能被粘着语素“银”“费”和“款”替换。有时候自由语素比同义的粘着语素构词能力还强。“国”(自由语素)、“邦”(粘着语素)是同义语素,《论语》中“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邦有道”“邦无道”的“邦”都是“国”的意思,不分本国他国,皆可称邦。进入构词领域,“邦”仅参与构成与友好国家有关的词,涉及不友好国家的词语不用“邦”而用“国”(比较:友邦、敌国)②;构成与国内事务有关的词不用“邦”而用“国”:
邦:友邦 邻邦 城邦 联邦 邦交 邦联
国:国本 国宾 国柄 国策 国产 国营 国耻 国粹 国都 国度 国法
国防 国歌 国故 国号 国花 国画 国徽 国会 国货 国籍 国际
国家 国教 国界 国境 国君 国库 国力 国门 国民 国难 国旗
国情 国庆 国人 国色 国史 国事 国手 国书 国术 国帑 国体
国土 国王 国文 国务 国学 国宴 国药 国医 国音 国有 国语
国乐 国葬 国贼 国债 亡国 与国 王国 开国 外国 异国 当国
报国 岛国 泽国 建国 卖国 窃国 祖国 殉国 爱国 敌国 救国
属国 锁国
所以我们认为,构词时,并不是粘着语素优先,而是同义语素各有各的构词域,语素在各自的构词域中体现自己的构词职能。不仅实义语素间存在构词域上的对立,意义已经虚化的词缀也有这方面的表现,而且尤为突出。比如后缀“—子”与后缀“—者”都能构成表人名词,如“秃子”“执法者”,但“秃子”不能说成“秃者”,“执法者”不能说成“执法子”,二者有严格的构词领域分工。下面我们将对“—子”的构词域进行详尽的描写,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者”是绝对不能进入这些构词域的。
三“—子”的构词域
要讨论词缀“—子”的构词域,先要明了什么样的“子”是词缀,什么样的不是。朱德熙(1982:30)认为,“—子”永远读轻声,并强调指出重读的“子”如“君子、仙子、原子、孔子、鸡子(儿)、五味子”等等都不是后缀;笔者深以为然。但朱先生举例中把“儿子”的“子”当作后缀,赵元任(1979:122)把“儿子”“孙子”中的“子”也看作后缀,任学良(1981:53)把“男子”“女子”“妻子”也看作词缀。我们认为,指称晚辈的“儿子”“孙子”“侄子”“孩子”等词里的“子”虽然也读轻声,但其本义(孩子)的痕迹仍然较为明显。另外,从“孙子—孙女”“侄子—侄女”这种对应来看,这里的“子”似乎还有区分性别的作用。这里的“女”也读轻声,没人建议将其作词缀处理,若不顾系统的一致性将与之对应的“子”处理为词缀,似有不妥。若“孙子”“侄子”的“子”不便看作词缀,也就不好把“儿子”“孩子”的“子”当作词缀。至于“妻子”,原本是联合结构(妻和子),后来在wife意义上使用的“妻子”,是偏义复词,“子”无意义了。但这也改变不了“妻子”的构词类型。“国家”“人物”“窗户”“忘记”“质量”都是偏义复词,这些词中后一个语素已经没有意义了,但任学良(1981:184)仍处理为并列式。至于“男子”“女子”中的“子”语音完足,跟轻声的“—子”不应等同视之。所以本文把“儿子、孙子、侄子、孩子、妻子、男子、女子”这些词看作由两个词根构成的复合词。下面分项给出“—子”的具体构词域。
3.1 构成表人名词
(1)表示有某种缺陷的人
胖子 聋子 哑子 矬子 矮子 秃子 瘦子 瞎子 呆子 疯子 瘸子 傻子 跛子
(2)构成不敬称谓词
骗子油子老婆子 老头子 老毛子 老妈子 丫头片子 汉子 鬼子
小子混子痞子二流子 头子狐媚子 二愣子叫花子
人贩子 小妮子 蛮子赖子贩子厨子(请与“厨师”比较) 探子
戏子卒子地赖子 二五子 光棍子 崽子腿子穷棒子
土包子 二性子(两性人)婊子
(3)亲属称谓名词
小姨子 大姨子 小舅子 大舅子 大伯子 小叔子 大姑子 小姑子 嫂子
婶子 老子 老爷子
(4)专称
小李子 小张子 小金子
3.2 构成表物名词
(1)构成表工具的名词
“—子”附着在一个表示动作的语素上表示完成这个动作所凭借的工具,这是“—子”的最主要、最能产的功能,简称为工具化功能。“—子”的这项构词法可描述为“动作+子=动作所凭依的工具”:
锤子 起子 凿子 锥子 推子 刨子 刷子 垫子 钳子 叉子 扣子 卡子
抹子 托子 架子 夹子 铳子 扳子 坠子 拍子 挡子 钩子 套子 舀子
耙子 剪子 掸子 盖子 铲子 梳子 碾子 绷子 筛子 喷子 罩子 塞子
溜子 锛子 攮子 鞭子 顶子 拢子 抿子 掐子
由于“—子”具有工具化功能,那些本来就指称工具的词语与“—子”同声相应,都可加“—子”,下边的第(2)类就属于这种情况:
(2)构成生产、生活用品、用具名称
刀子勺子 车子坛子 帐子匣子 杠子杆子钎子 环子
轮子炉子 柜子帘子 杯子笼子 盆子缸子盅子 竿子
毡子被子 袍子袜子 褥子毯子 裤子帽子座子 框子
筐子桌子 扇子哨子 瓶子轿子 梆子席子桩子 盒子
匙子盘子 梯子 筏子 棍子棒子 筒子销子 链子 椅子
窗子绳子 梭子笛子 裙子带子 毽子牌子幌子 靶子
筷子楔子 筢子 凳子 碟子管子 罐子 橛子箱子 鞋拔子
耳挖子 簪子 粪箕子 柱子 坛子帐子 网子床子斧子 兜子
袋子帷子 靴子楦子 篮子鞍子 戥子褂子 镊子 钉子
色子 斗子 弓子 模子
材料与工具有相近性,比如它们都可以用“用”作格标(“用柳条编筐”“用钥匙开门”),因此,原本就指称材料的词与“—子”亦同气相求,下边的第3类就属于这种情况:
(3)构成材料名称
坯子 呢子 绸子 绢子 绫子 料子 沙子 椽子 檩子 板子 腻子
(4)构成器官名称
肚子肠子 肘子 爪子 脖子 腿肚子 肺子 脚丫子 嗓子眼皮子
眼珠子 膀子 鼻子 腕子 腰子 脑子身子 眸子胡子须子
根子节子 叶子 皮子 辫子 翎子冠子 脑门子 脑勺子 胰子
(5)构成衣、物部件名称
袖子 里子 面子 纽子 领子 帮子 底子 裤脚子 裤鼻子 大襟子
扣子 耳子 把子 嘴子
(6)构成植物及植物果实名称
苇子 麦子 谷子 豆子 杏子 茄子 枣子 果子 李子 椰子 桃子 栗子
梅子 稗子 蒿子 种子 苗子 秧子 栽子 芽子 竹子 柿子 林子 榛子
柚子
(7)构成动物、昆虫以及寄生虫名称
骡子 狮子 豹子 猴子 獐子 麂子 貉子 狍子 狸子 兔子 驹子 犊子
崽子 羔子 耗子 鸭子 鸽子 鹞子 燕子 蝎子 蛾子 虫子 蝇子 蚊子
虱子
(8)构成肤表麻点状疾病名称
痱子 痦子 麻子 疹子 疖子 痘子
(9)构成珠粒状物名称
弹子 雹子 沙子 珠子 粒子 丸子
(10)构成建筑物名称
院子 园子 围子 寨子 宅子 场子 房子 亭子 台子 屋子 棚子 堂子 地窨子
(11)构成食物名称
饺子 饼子 饭团子 粽子 包子 面条子
(12)构成与金钱有关的名词
金子 银子 款子 锞子 票子 折子
(13)构成与音乐有关的名词
谱子 调子 曲子 段子
(14)构成自然居住区域名称
镇子 屯子 村子 庄子
(15)构成残碎或细碎之物名称
渣子(骨头渣子) 块子(肥肉块子) 碴子(玻璃碴子) 条子(土豆条子) 片子(碎纸片子)
头子(砖头子) 末子(锯末子)面子(药面子)
以上是语料显示的后缀“—子”的构词域,下面以此为基础来讨论“—子”的语义问题。
四“—子”的语义问题
4.1“—子”有没有贬义色彩
如上文所示,“—子”的构词域很复杂,从大的方面看,分为表人、表物两大领域。在表人域里,“—子”尾词的分布是:(1)有缺陷者,(2)不敬称谓,(3)亲属称谓,(4)专称。(1)(2)两类“—子”尾词的贬义性一目了然,不需论证。亲属称谓要分两类:
针对姻亲平辈的称谓:嫂子 小姨子 大姨子 小舅子 大舅子 大伯子 小叔子
大姑子 小姑子
针对长辈的称谓:老子 老爷子 婶子
先说姻亲平辈称谓这类。按照中国的宗法传统,姻亲不比血亲,是较疏远的亲属,在皇族里叫外戚。而且这些姻亲称谓“—子”尾词通常用作背称而不是面称(只有“嫂子”可以作面称)。当面称呼没有叫小姑子、大姨子、大伯子的,都叫妹妹、姐姐、哥哥。跟别人谈到自己的小舅子时,如果小舅子在场,多半会说“这是我内弟”,而不会说“这是我小舅子”。由此可见,姻亲称谓“—子”尾词是称呼者当面不好说出口、被称呼者听了不舒服的一种称谓形式。然而,这种词说它有贬义色彩似乎也还重了点,但说这种称谓缺少点亲敬感,应该没有问题。针对长辈的称谓这类也都不是面称,当面叫“二婶儿”“爸爸”,不会叫“二婶子”“老子”“老爷子”。但说它们有贬义色彩也不太准确。专称这类所以叫专称,是因为它们总是用来称谓特定对象的,语义价值和人名相近,有时还有点儿亲近的色彩(与直呼其名相比),因此这类也不能算有贬义色彩。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由“—子”构成的表人词语除亲属称谓和专称以外,皆有贬义色彩。
褒贬色彩属于语言的主观性问题。纵观表物各类“—子”尾词,它们不像表人“—子”尾词那样有较浓的主观性,它们都属于客观称谓,都是中性的。虽然有些“—子”尾词代表的事物让人不喜欢(痱子、疹子),但这不是词义问题,它们仍是客观的指称形式。这和“苍蝇”“蚊子”不算贬义词是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子”在表物构词域里没有贬义色彩,在表人构词域里除亲属称谓和专称以外的领域里有贬义色彩。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搞清了一个问题:我们不能笼统地说“—子”有没有贬义色彩,只能说在哪个构词域里有没有贬义色彩。吕叔湘(1980:623)指出:“‘子’只有少数含贬义。”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个“少数”说得更具体一些:在“—子”尾词里,表物词居多,表人词占少数,表人的也只有亲属称谓和专称以外的有贬义。刘月华等(2001:38)指出:“‘子’的本义是‘孩子’,作为后缀‘子’没有‘小’或‘轻视’的意思,而只有名词化作用。”这恐怕是只观察了表物的“—子”尾词后得出的结论。
4.2“—子”有没有指小功能
最早提出“—子”有指小功能的是后汉的刘熙。《释名·释形体》中解释“瞳子”的“子”时指出:“子,小称也。”(参见任学良,1981:52)。吕叔湘(1942:11)指出:“‘子’和‘儿’原来都带有‘小’的意味,可是现在已经不很明显,尤其是‘子’字。”王力(1954:265)把“—子”叫“记号”,说它最初的时候像西洋词尾,“因为除了表示名词的词性之外,还带着‘小’的意思;现在‘小’的意思已渐消失,却很像西洋纯粹表示词性的字尾”。太田辰夫(1958/2003:86)指出:“附于大的物体之后的用法,有些在唐代以前也有……到唐代,‘子’就变成为也能附于相当大的东西后面了。如‘车子’‘船子’‘亭子’‘阁子’‘宅子’‘案子’等。”太田辰夫先生的意思我们解读为:“—子”作为词尾,原来有指小功能,唐以后弱化了。任学良(1981:53)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不过,现在词尾‘子’用得太普遍,‘小称’的意义已经不那么显著了。”赵元任(1979:121)表示了鲜明的否定态度:“虽然‘子’的本义是‘孩子’,可是作为后缀却没有指小的意思,或轻松的口吻,只有名词化的作用。”刘月华等(2001:38)的看法与赵元任基本相同。可以说现在已经没有哪位学者明确坚持“—子”可以指小了。
可是在笔者心中一直有一个挥之不去的困惑:人们对粒子的命名何以皆以“X子”(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超子……)称之?③这些词显然不能用任意性来解释,那么是什么东西指导人们用“X子”来命名这些粒子的呢?如果有什么“密码”在暗中起作用,那么这个“密码”是不是“—子”的指小功能?
同时下列事实也使我们不得不谨慎对待学界已有的结论:
(1)在圆木这个聚合中,粗者可为梁,细者可为檩,再细者可为椽,在这个系列里,梁不能子尾化(我们把名词性语素加“—子”构成新的名词叫做子尾化),其余皆能,如檩子、椽子。
(2)在酒具系列里有三个成员:壶、杯、盅。“壶”最大,“杯”次之,“盅”最小。“壶”不能子尾化,“杯”“盅”皆可子尾化,如杯子或酒杯子、盅子或酒盅子。
(3)在印刷品这个聚合里,书最厚,不能子尾化,而本、簿、册都相对薄一些,都可子尾化,如本子、簿子、册子。
(4)在日用容器这个聚合中,大者曰缸,曰桶,小者曰坛,曰罐,曰盆,曰杯,曰瓶。“缸”“桶”皆不能子尾化,“坛”“瓶”“罐”“杯”都可子尾化,如坛子、瓶子、罐子、杯子。
不难看出(1)一(4)是四个语义场,这部分材料显示的语言事实是:在一个语义场里如果有子尾化的事情发生,那一定不是发生在那个大的成员的身上,而是将较小的成员子尾化。这个事实给我们的启示是:“—子”表小发生在语义场中,“—子”能在一个语义场中表小,“—子”尾词的“小”是在同一个语义场中比较出来的。可是我们马上又遇到了麻烦。“世纪、年、月、日、时、分、秒”是一个时间单位场,其中“秒”最小,不能子尾化;“日”比“秒”大得多,却能子尾化(日子)。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观察“—子”尾词所在的语义场。我们发现,一个语义场可分为两个层次:核心和边缘。一个语义场中可及性(accessibility)最高的成员居于核心位置,可及性差的居于边缘位置。就时间单位场来说,“年、月、日”属于可及性最高的核心成员,比如,通常说“某年月日”,说“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年、月、日”是一个最自然的时间单位类聚。在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较少有论分论秒的行为,“日”通常是最小的时间单位。在中国,从前只有年工资、月工资、日工资,小时工资最近几年才有,尚不为一般老百姓所熟知。“—子”尾词是口语词,倘若一个词普通老百姓不太有机会使用它,它便很难口语化,因此也就不能子尾化。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提出自然语义场(简称自然义场)这个概念。
我们通常说的语义场可以叫做特征义场。我们这里提出的自然义场与特征义场不同,它是指在人们语言生活中形成的自然类聚。特征场以语义特征为基础,是理性的产物,是由语言学家归纳出来的;自然义场也有语义特征作基础,但它不是理性的产物,它不是由语言学家划分出来的,而是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在人们心目中沉淀下来的最自然的集合。举例来说,“世纪、年、月、日、时、分、秒、毫秒”是一个特征义场,而“年、月、日”是一个自然义场。“油、盐、酱、醋、味精、料酒……”是特征义场,而“油、盐、酱、醋”是自然义场。“烟、酒、糖、茶”,“鸡、鸭、鹅”,“猪、猫、狗”都是自然义场。自然义场与特征义场的主要区别是:特征场基本上是逻辑的类,自然义场不是逻辑的类,而是生活的类。
自然义场与特征义场的内在联系也是明显的:自然义场是特征义场的一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是特征义场中可及性最高的成员的集合。
就我们目前面对的这个研究对象来说,特征义场帮不上忙,所以我们提出自然义场这个范畴。有了自然义场这个范畴,我们就能解释为什么“秒”比“日”小而“秒”不能子尾化“日”却能子尾化的原因了:子尾化发生在自然义场的较小成员身上,而“秒”不是自然时间单位义场里的成员,所以它不能子尾化,“日”属于自然时间单位义场里的最小成员,所以能子尾化。
我们认为“—子”有指小功能,但现在可以换个思路来讨论大小问题,我们要强调三点:
(一)“小”不应只理解为形体小,这个“小”具有丰富的内涵,它除了表形体小以外,还应包括“短”“细”“薄”“幼”等几个向度。“短”(包括时间短)、“细”“薄”“幼”皆可解释为小:长度小者曰“短”,截面小者曰“细”,厚度小者曰“薄”,年龄小者曰“幼”。“小”为“体”,“短、细、薄”“幼”皆为“用”,是“小”在不同向度上的“用”。物之短者、细者、薄者、幼者和形体小者一样,其称谓形式多可子尾化。
(二)大小不一定是几何、物理上的绝对尺寸,它有时是在同一个语义场中比较出来的。在同一个语义场中,若成员皆小,整个语义场都可以子尾化;若一个语义场中的成员有大有小,如果有子尾化的事情发生在这个语义场里,大者绝对不可子尾化,小者可以子尾化。所以这种“小”有相对的一面。必须清楚这一点,否则我们没办法解释为什么有时绝对尺寸小的不能子尾化,绝对尺寸大的反而能子尾化(比如“屋”比“球”大,可是,“屋”能子尾化为“屋子”,而“球”不能子尾化为“球子”)。特别要强调:这里的语义场指的是自然义场而不是特征义场。
(三)“—子”指小是在特定的构词域里实现的。表人域里的“—子”尾词,不涉及是否指小的问题,“瞎子”“油子”难以大小论,事实上学界在讨论“—子”有无指小功能时,针对的也不是这类语料。由“—子”将动词工具化而产生的工具词(锤子、起子)以及表示材料的不可数的“—子”尾词(棉子、毡子、腻子)也不涉及大小的问题,只有那些自然可数的、原本就是名词加上“—子”以后仍是名词的子尾词才有是否指小的问题。
以上是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其中第二点尤为重要。现在我们重申:“—子”有指小功能。下面将在前边(1)-(4)的基础上继续列举足够多的语言事实来论证我们的观点。
在同一个语义场中,成员皆小,整个语义场都可以子尾化,如(5)-(7):
(5)痱子 痦子 麻子 疹子 疖子 痘子
(6)弹子 雹子 沙子 珠子 粒子 丸子
(7)渣子 块子 碴子 条子 片子(纸片子) 头子(砖头子) 末子(锯末子)
一个语义场中的成员有大有小,如果有子尾化的现象发生在这个义场里,那一定是将小的子尾化,而不会将大的子尾化。下边的(8)-(19)属于这种情况:
(8)就水体这个聚合来说,大者曰洋、曰海、曰江、曰河、曰湖,皆不能子尾化,但这个聚合中比较小的成员都可以子尾化,如池子、(水)坑子。
(9)在家禽这个系列里,鹅最大,不能子尾化,鸡、鸭相对小些,均能子尾化,如小鸡子、鸭子。
(10)在建筑物这个系列里,楼、厦皆大,不能子尾化,房、屋、亭、台相对小些,均能子尾化,如房子、屋子、亭子、台子。
(11)在室内设品这个系列里,“床、炕”最大,不能子尾化,其他如“桌、椅、凳、箱、柜、匣”都相对小些,均能子尾化,如桌子、椅子、凳子、箱子、柜子、匣子。
(12)圆体物系列里,“球”比较大,不能子尾化,“珠、沙、雹”都比较小,都可子尾化,如珠子、沙子、雹子。
(13)若一家有几个儿子,除老大、老四不用“子”称谓,其余皆可:小二子、小三子、小五子、小六子……这个系列里的成员不是同时得名的,除老大外,其余的在得名时都曾经是最小者:老二出生的时候,他就是最小的,故可以叫“小二子”,当老三出生的时候,老三又成为这个系列的最小者,故可称“小三子”,余者类推。在这个系列里老四不能子尾化,不能说“小四子”,这是音系层面的制约,后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14)在行政区单位系列里“省、市、县”为大者,“镇、村、屯”为小者,大者不能子尾化,小者皆能,如镇子、村子、屯子。
(15)在“树”的组成部分这个系列里,“(树)干”相对粗壮,不能子尾化,“根”细,“叶”薄,都可子尾化,如根子、叶子,其他植物,都与“树”的情形相仿。
(16)“宅”的子尾化是唐代开始的,《封氏闻见记》有“此宅子甚好,但无出水处。”古代,天子住的地方称“宫”,达官贵人的住所称“府”(相府、驸马府、尚书府、将军府),虽然有时大官住的地方也称“宅”,如《晏子春秋》:“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辞以近市。”晏子的宅,在贫民区,肯定不是多么可观,否则景公就不会为他更换新宅了。“宅”更多的是指一般百姓住的地方(民宅)。《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这里的“宅”指的是一般百姓的居住处,它比宫和府要小得多;而“院”又是“宅”的一部分。所以“宫”“府”不能子尾化,“宅”“院”都可子尾化,如宅子、院子。“宅”能子尾化还能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在国人的心目中,“房子”与“地”构成不动产,形成一个系列,所谓“田宅”,“田”大“宅”小,故“宅”能子尾化。“田、园”经常并举(田园风光、田园生活、田园荒芜、广置田园),是一个自然义场。“田”大“园”小,“园”在“田”中,故“田”不能子尾化,而“园”能子尾化,如园子。
(17)在人们的观念中,“蛇、蝎”是一个系列(毒虫系列),蛇大,蝎小,故有“蝎子”无“蛇子”。
(18)在野生动物这个聚合中,“象、熊、虎、鹿”个头都较大,无“—子”尾;个头小点儿的,“豹子、麂子、狍子、獐子、猴子、貉子、狸子、兔子、耗子”都有“—子”尾。
(19)“瓜果梨桃”口语中经常并举,属于同一个自然义场。在这个义场中,“瓜”最大,不能子尾化,其余相对小些,皆可子尾化,如果子、梨子、桃子。
以上举例差不多包括了生活常用词的方方面面,应该能够说明一些问题,但是我们也清楚,这样的论证留下了较大的质疑空间。比方,“蚂蚁”乃虫之小者,为什么不能说“蚂蚁子”?老三比老四大,何以老三能说“小三子”,而老四不能说“小四子”?部队编制系列“军—师—旅—团—营—连—排—班”,“班”最小,为什么不能说“班子”?我们在下一节里讨论这些问题。
五制约子尾化的因素
语料显示,一个名词性语素能否子尾化除了受语义场中排位的制约以外,还受很多因素制约。首先,音系制约是一个必须注意的层面。“2+1”节律的动宾结构(种植树)、“1+2”节律的定中结构(技工人)不是好结构,就是音系层面上出了问题,对此学界已经有过很多讨论。④蚂蚁不能说成“蚂蚁子”也是音系制约的结果。“—子”通常选择单音语素,虽然也有“土豆子、豆角子”这样的子尾词,但数量极少。而“土豆块子”“玻璃碴子”“布条子”应分析为:[[土豆][块子]]、[[玻璃][碴子]]、[[布][条子]],“—子”都是附着在单音语素上。我们之所以不把“土豆块子”分析为[[土豆块][子]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土豆块”不能自由运用,它必得和“子”或“儿”一起出现(土豆块儿),二是“把土豆切成块子”“把瘦肉切成条子”“把萝卜切成片子”这种用例的存在说明“块子”“条子”“片子”都是自由的单位。因此我们认为表残碎之物的“渣子、块子、碴子、条子、片子、头子”都是独立的词。而且是一价名词⑤,它们要求的价语通常给它们作定语。由于“—子”有选择单音语素的强烈倾向,“蚂蚁”“臭虫”等虽然小,也不能子尾化。在“鸟类”这个集合里,“雁”“鹤”“鹰”不能子尾化是因为它们在这个集合里属于较大者;“麻雀”小,不能子尾化,是因为它是双音节;“鸽”“燕”形体小,又是单音节,故可子尾化,如鸽子、燕子。
大小的制约是强力制约,因为还没发现在一个语义场中有最大的可以子尾化的情况。音系层面上的制约相对宽一些,因为有双音子尾化的现象(土豆子、豆角子)。如果这两条(既大又非单音节)都占上了,就绝对不能子尾化了。这种情况我们把它看成是大小与节律因素双重作用的结果,(20)-(25)就属于这种情况:
(20)在粮食作物这个系列里,“高粱、玉米”皆身量高大,又不是单音节,不能子尾化,“谷、豆、糜、稻”相对矮小,又是单音节,都可子尾化,如谷子、豆子、糜子、稻子。
(21)在地面交通工具这个系列里,“火车、公交车、旅游车”皆形体庞大,又不是单音节,都不可称“车子”;“轿车、自行车”形体小,可称“车子”。有词典为证,《现代汉语词典》“车子”条:①车(多指小型的)。②自行车。
(22)在昆虫系列里,“蜻蜓、蝴蝶”为大者,又不是单音节,不能子尾化。“虫、蚊、蝇、蜂”为小者,又是单音节,皆能子尾化,如虫子、蚊子、蝇子、蜂子。
(23)交易场所系列里,大者曰商店,曰商场,曰超市,又不是单音节,都无“—子”尾,小者曰铺子,曰摊子,皆有“—子”尾。
(24)吃饭的场所,大者曰饭店,曰酒店,不是单音节,皆无“—子”尾,小者曰馆子,有“—子”尾。
(25)在蔬菜这个系列里,“南瓜、倭瓜、冬瓜、西葫芦、大白菜、大萝卜”形体都较大,又不是单音节,都不能子尾化,而形体小一些的皆可有“—子”尾,如豆角子、茄子、土豆子。
音系层面上除了对直接成分的音节数量有要求外,同音相接也是一个要尽量避免的事。赵元任先生在《语言问题》中讲述过这样一件事:赵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在台湾大学搞语言学讲座,第一讲的题目叫做“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问题”,当时台湾各报都要报道这件事。有几个编辑部打电话询问赵先生题目里是不是多了一个“跟”,赵先生回答说不多。结果第二天刊出后,打过电话的题目没变,没打电话的擅自给删去了一个“跟”。对此司富珍(2005)评论说:“其实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疑问,不是由于问者无知,……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相邻的两个发音和字形都相同的词往往会根据经济性原则进行纯音系的合并。所以有时不合并虽然符合语法,却不符合人们的直觉。”笔者深以为然。就“语言学跟跟语言学有关系的问题”这个表达来说,删去一个“跟”固然可以,司富珍(2005)把此种操作叫做“同音删略”。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把第一个“跟”改为“和”以避免同音相接。我们把这种操作叫做同音规避——换一个同义不同音的。同音相接结构在音系层面发生问题时,如果同音删略行不通,就要实行同音规避操作。比如量词“根”适用于表细长物的名词,“一根绳子”“一根油条”“一根针”,但不能修饰名词“根”(比如树根的根),能说“一条根”不说“一根根”。“一根根”如果删略一个“根”,意思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下只能使用同音规避策略说成“一条根”。用“条”不用“根”是同音规避操作,也是纯音系层面的操作。现在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老四”不能说成“小四子”了。“四”“—子”韵母相同,声母相近(发音部位相同,发音方法相近),听起来读音十分接近,近似于同音相接,又不能同音删略,只好使用同音规避原则,说成“小四儿”。“土豆丝儿”不说成“土豆丝子”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子尾词都是口语色彩很浓的词,书面色彩浓的词不能子尾化,例如“肚”可子尾化(肚子),“腹”不能子尾化(*腹子)。“军—师—旅—团—营—连—排—班”都是色彩上庄重严肃的词,这一系列中无论多小都不能子尾化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到此为止,也不是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结论若作为规则理解,仍有可质疑的地方。在野生动物这个集合里,“狼”小而“豹”大,但可以说“豹子”,不能说“狼子”。“虎”“狮”形体差不多,而“狮”能子尾化(狮子),“虎”就不行。“猫、狗”属于同一系列,“猫”小“狗”大,却都不能子尾化⑥。赵元任先生说得对:“语言究竟是一个社会的自然发展的现象,社会特别常常有很复杂的情形,所以如果事实比理论复杂——如果事实并不规则,那么不能削足适履,把事实硬放在太简单整齐的空架子中。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一直在论证的观点——在同一个聚合中,形体大的不能子尾化,形体小的能子尾化,因而“—子”尾有指小功能——只能说是一种原则或倾向,而不是一种绝对不可违背的规则。如果这种倾向是不可否认的,“—子”尾有指小功能这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
六 结论
句法层面上词有自己的分布规律,词法层面上语素有自己的构词域,语素在构词域内实现自己的构词功能。考察语素的表义特点,构词域是必选视角。透过这个视角将我们观察到的事实概括如下:“子”的构词域分为表人和表物两大领域。在表人域里,子尾词除亲属称谓和专称以外皆有贬义色彩,但五指小功能。在表物域里,“—子”无贬义色彩。至于“—子”有无指小功能,必须在自然义场中考察,我们考察的结论是:若一个自然义场中所有的成员皆小,整个义场都可以子尾化;若一个自然义场的成员有大有小,要么都不子尾化(牛、羊可构成一个自然义场,牛大羊小,但都不子尾化),要么将小的子尾化,而不会将大的子尾化。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子”有指小功能。
注释:
①“脸皮”“肚皮”用的都不是“皮”的本意。“肚皮”不是肚子的皮,“脸皮”也不是脸上的皮,当我们说“脸皮薄”“脸皮厚”的时候,不是真的在讨论脸上的皮,这里用的是“皮”的引申意义,这个意义上的“皮”与“肤”不是同义语素,不能进行对比。同样情况的还有“眼皮”,“眼皮”也不是指眼睛的皮,而是眼球上的覆盖器官。
②“乌托邦”是音译词,不遵循汉语造词法。
③因为“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超子”里的“子”都不读轻声,我们没有把它们当词缀看待;但它们的定位性和类化功能都表明它们基本具备词缀的特点,马庆株(1995)把它记为“—子3”,并认为是准词缀,我们同意他的看法。
④参见冯胜利(1997、2000),端木三(1999),吴为善(2006),周韧(2007)。
⑤关于一价名词,参见袁毓林(1994)。
⑥北大语料库中“狼”“猫”有子尾化形式:
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鲁迅《狂人日记》)
他的眼忽然一亮,象猫子忽然看到老鼠那样。(老舍《四世同堂》)
好像它根本没爱过一只花狸猫,它也根本没有钟情于一只黑猫子!(冯苓植《猫腻》)
这家伙很像猫子,有一个喜欢吃耗子的大缺点。(《安徒生童话故事集》)
但我们觉得,“狼子”“猫子”的语感可接受性不强,所以不认为“狼”“猫”可子尾化。语料库中“熊”“虎”无子尾化用例(语料库中“虎子”很多,但要么指幼虎,要么表示人名),“狮”“豹”“狼”“狸”“兔”有,语料库显示的事实支持我们的观点。
⑦参看赵元任(1980/1999:32-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