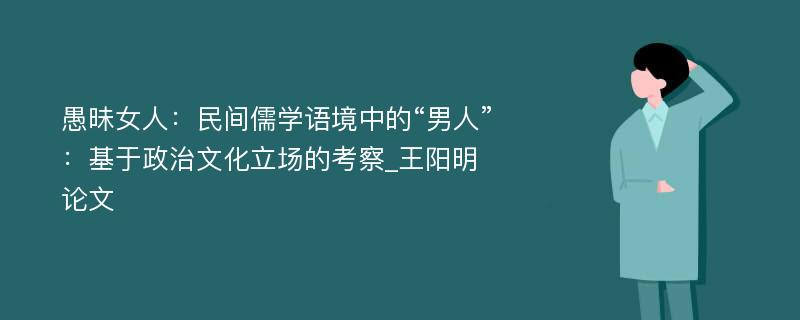
愚夫愚妇: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基于政治文化立场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愚夫愚妇论文,儒学论文,语境论文,平民论文,立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与特征是由儒家文化所给出并限定的,其主要载体是士大夫阶层,但作为社会政治主体的人,理论上包括士大夫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研究儒家观念当中的“人”不能仅仅局限于士大夫阶层,而应该拓展至士大夫外的其他社会阶层,探索他们关于“人”的观念。深入探索和研究包括社会各阶层“人”的观念区别与发展,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政治文化的特质具有特别关键的作用。
有研究者认为,“儒家文化中的人并不涵指独立个体的人,而指依照人伦关系网络组织起来的人类群体”①,“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所能给出的仅仅是人的类主体意识和理性觉醒”②,其结果是,儒家文化中的人“只有社会群体化单向发展的途径,人们的精神归属于道德化的宇宙,他们的血肉之躯归属父母所有,他们的意志和行为被父家长和君权紧紧束缚住。人们越是要成为儒家文化称道的人,就越要泯灭个性,否定自我。沿着儒家的道德不可能导向个人尊严、个性解放、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顺民社会,从而成为君主专制主义生存的最好的文化土壤”③。作为总体的概括与描述,这个结论很有启发性。但是,社会生活中的人是由各阶级、阶层的人共同组成的,他们虽同处于一个社会—文化形态之中,但各自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价值追求以及对于身处的社会—文化形态之感受等等均有所不同。那么,在儒家观念中,除了士大夫群体,其他社会成员、尤其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在政治文化视角下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在与社会发展相伴随的传统政治文化变迁过程中,各个阶层,尤其是普通民众关于“人”的观念与历史实践是否有某种程度的“异动”?这种“异动”对于我们认识传统政治文化又有怎样的意义?这是本文探讨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愚夫愚妇”的思考起点。
一、主流儒家语境与王阳明的转折
“愚夫愚妇”一词的使用,与“匹夫匹妇”、“小民”、“万民”一样,都是一种抽象的群体指称,泛指未经教化之男女众人。宣朝庆在研究泰州学派时解释说,“旧解‘夫妇’为愚夫愚妇,此愚陋之夫妇不必为夫妻,可泛指一般未经教化之男女,也就是明代平民阶层中的农工商诸人”④。
文献中“愚夫愚妇”一词较早见于《墨子》。《墨子·兼爱下》有云:“以为当其于此也,天下无愚夫愚妇,虽非兼之,人必寄托之于兼之有是也。”联系上下文,此间所云“愚夫愚妇”盖指“万民”。在《礼记》中,以“夫妇”来指称“小民”群体。如其《中庸》篇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郑氏注:“夫妇谓匹夫匹妇之所知所行。”孔颖达《正义》:“此一节论夫子虽隐遁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初则起于匹夫匹妇,终则遍于天地。”⑤后文孔颖达等的疏解中亦多有“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之类说法。西汉刘向《说苑》亦记述齐桓公问管仲:“吾欲举事于国,昭然如日月,无愚夫愚妇皆曰善。可乎?”(《说苑·政理》)“古文尚书”之《夏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之语,宋人叶适云:“‘愚夫愚妇,一能胜予’,禹以为民为可畏若是。”⑥陆九渊曰:“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妇之所与知,而大贤君子不能无蔽者。”⑦杨简在为陆九渊兄弟所作《二陆先生祠记》中说:“道心大同,人自区别。人心自善,人心自灵,人心自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睹乖殊?圣贤非有余,愚鄙非不足。何以证其然?人皆有恻隐之心,皆有羞恶之心,皆有恭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恻隐,仁;羞恶,义;恭敬,礼;是非,智。仁义礼智,愚夫愚妇咸有之,岂特圣贤有之?”⑧
据上可知:“愚夫愚妇”在宋之前儒家语境中,只是一种抽象的群体指称,用“夫”与“妇”的名目来概括“小民”、“万民”,相对于“小民”、“万民”的称呼,这种概括表面上看来更生动些,但实际涵指是一致的。宋以前儒家在以“愚夫愚妇”为话头阐述观点时,多基于政治与道德两种立场,政治立场是站在传统的“保民”、“重民”等民本思想角度阐述统治方略等,道德立场则是强调道德的普泛性与道德修治起点的遍在性;无论是抽象地指称民众,还是基于政治、道德立场阐述观点,此时“愚夫愚妇”、“匹夫匹妇”之类的称呼都体现了士大夫精英阶层的等级优越性。
这里“愚夫愚妇”的指称,透露出的是主流儒家认识。这一用法到了近代仍有沿用。典型者如谭嗣同在《仁学》中说:“吾悲夫世之妄生分别也,犂然不可以缔合。寐者蘧蘧,乍见一我,对我者皆为人;其机始于一人我,究于所见,无不人我者。见愈小者,见我亦愈切。愚夫愚妇,于家庭则肆其咆哮之威,愈亲则愈甚,见外人反畏而忘之,以切于我与不切于我也。”⑨
不过,明代中叶阳明学兴起之后,儒家主流的“愚夫愚妇”观发生了重要转折。王阳明从良知说出发,强调了在良知面前,圣、愚平等:“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⑩循此“平等性”,王阳明又回答了何为“异端”。他说:“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11)这即是说,在良知良能之起点上,圣人与愚夫愚妇是一样的,双方具有“平等性”。差别只在于后天的“致”的工夫,圣人能“致”,愚夫愚妇不能“致”,于是圣、愚可判。
在王阳明看来,圣、愚无间是基于良知良能起点上的平等。如若从“致”的能力而言,圣人与“愚夫愚妇”还是有着明确区别的。也就是说,基于良知说,圣、愚的界限可以逾越,而从现实角度,“圣、愚之间的界限永远是不可逾越的,这种界限还原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即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对立”(12)。岛田虔次也认为:“在阳明那里,人,作为也包含愚夫愚妇的人的一般,实际上只不过是一种超脱主义,还没有逸脱士大夫的限制。”(13)尽管如此,王阳明对于“愚夫愚妇”一定程度上的肯认,毕竟为“愚夫愚妇”在儒家语境中的发展显示了一种转折。
经由王阳明的阐释,在传统儒学的政治视野中,作为创制主体的“圣人”有了某种泛化的倾向。“愚夫愚妇”则走出了抽象的群体指称,具有了明确的现实意义。朱承探讨阳明学的“政治向度”时,就认为王阳明构建的政治乌托邦秩序创制主体期待“似乎更具有现实性和可预见性”,这来自于“愚夫愚妇”的真实存在(14),并且,从理论上说,“王阳明所构建的乌托邦共同体里,独特资质的圣人、贤人并不是必要的前提,满大街良知觉醒的‘圣人’(也就是‘愚夫愚妇’面貌出现在世俗中的饮食男女)足可以担当构建理想社会的责任”(15)。在王门良知说的构建基础上,“愚夫愚妇”的主体地位呼之欲出。
王艮在阳明殁后开创泰州学派,泰州一脉学者循此转折性路向而有了进一步发展,以致形成了平民儒学思潮。虽然平民儒学并未超越传统儒学范畴,但王艮及其后学王襞、颜钧、何心隐、邓豁渠等形成发展起来的平民儒学,与统治阶层讲求的官方儒学及士大夫精英儒学有着明显区别,表现出儒学由传统而向近代转化的发展迹象。这在平民儒学关于“人”的观念与历史实践方面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体现。
二、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从身体到实践
(一)百姓日用即道:平民儒学的崛起
王艮以布衣身份的崛起,继承和发展了阳明基于良知说而对“愚夫愚妇”的肯认,将“愚夫愚妇”的“百姓日用”提高到了“道”即本体的层面予以肯定。他直言“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16),“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17),“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18),“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19)。王艮在认识上突破了“士大夫的限制”,代之以一种明确的平民立场,而他的依据又只不过是王阳明的良知学说:“良知天性,往古来今,人人具足,人伦日用之间举措之耳,所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分定故也。”(20)
王艮平民立场的确立,除了赋予百姓日用的平民生活以“道”的意义,强调“愚夫愚妇与知能行便是道”之外,更强化了那种“为学”、“学道”的简易性,极力主张“简易之道”,这样即在理念上为“愚夫愚妇”政治社会实践提供了某种可能性。王艮认为:“社稷、民人固莫非学,但以政为学最难。吾人莫若且做学,而后入政。”(21)“做学”则当由孝做起,从上到下,“孝”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实践与拓展,最终能够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政治社会局面。这一点,王艮说得很清楚:
盖孝者,人之性也,天之命也,国家之元气也。元气壮盛而六阴渐化矣,然而天下有不孝者鲜矣。……在上者果能以是取之,在下者则必以是举之,父兄以是教之,子弟以是学之,师保以是勉之,乡党以是荣之。是上下皆趋于孝矣。然必时时如此,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岁岁如此。在上者不失其操纵鼓舞之机,在下者不失其承流宣化之职,至穷乡下邑、愚夫愚妇皆可与知与能,所以为至简至易之道,然而不至于人人君子、比屋可封者,未之有也。(22)
以往研究者对于王艮这一认识一般只作伦理学层面的疏解,显然有所不足,其中的政治文化含义显而易见。在这里,“孝”关涉到基本的政治价值、政治教化、政治理想与政治信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王艮的“简易之道”其实并不简易。
王艮的“简易之道”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是其对于理学“格物”说的独到解读,史称“淮南格物”。“格物”之说源自张载,完善于程朱,解说颇为繁复。然而在王艮看来,“格物”的宗旨应落实到“安身”之上,“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因而“身”具有衡量标准的意义。他说:“格,如格式之格,即后挈矩之谓。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矩正则方正矣。方正则成格矣。故曰物格。”(23)这一解读意义非凡。徐春林认为:“王艮一改过去的种种训释,创造性地把‘格物’的宗旨解释为‘安身’,使‘格物’与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活紧紧联系起来,而不仅仅是少数圣贤追求者的活动。”(24)由此,在王艮那里,“愚夫愚妇”的“身”具有了某种主体的意涵,而且具有明确的实践指向。王艮已然意识到作为个体的“身”,其重要性不只体现在道德生活领域,更显现在政治生活领域。他说:“仕以为禄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禄也何有?仕以行道也,或至于害身,仕而害身,于道也何有?”(25)据此,王艮提出了“明哲保身论”:
“明哲”者,“良知”也。“明哲保身”者,“良知”、“良能”也。所谓“不虑而知”、“不学而能”者也,人皆有之,圣人与我同也。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吾身保矣。……以之“治国”,则能爱一国矣。能爱一国,则一国必爱我矣。一国者爱我,则吾身能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一国矣。以之“平天下”,则能爱天下矣。能爱天下,则天下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莫不“尊亲”,则吾身保矣。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6)
这篇文章是送别王瑶湖(27)的,作为对士大夫的勉励之辞,“明哲保身”的政治实践指向治国、平天下。作为主体的“身”在这层意义上具有了社会政治的内涵。
那么,如何进行政治实践呢?王艮将之化作一腔传道激情,通过讲学以致力于道德教化。儒家一脉的道德学说贯穿着政治理念,从现代政治学理论的视角看,道德教化正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诚如吴震所言,“儒家的王道政治或外王理想的实现,其关键并不在于制度法典等外在事业的建设,关键仍然在于如何依靠道德的力量来转化成事业的建设。没有道德的政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道德的缺失,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王道政治。可见,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才是实现外王理想之前提的思路”(28)。王艮及其后学慨然以师道自任,强调“出必为帝者师,处必为天下万世师”(29)。他们向往的“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政治理想,通过讲学传道而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影响。
王艮及王襞、颜钧、何心隐等泰州后学在致力于平民教育方面都有着卓越的表现。这显然是平民儒者在理论上将“愚夫愚妇”个体的“身”挺立起来的结果。岛田虔次认为:“泰州学派显然是夹杂着庶民风气的学派。……在其祖王心斋那里,人怎样地被思考为带有对社会的积极实践意欲。而且其所谓实践所意味着的,在理论上,一定是作为愚夫愚妇也理解的‘百姓日用’,而在原则上,则不一定是指士大夫性的东西。泰州学派的特征,就像已经在心斋那里所见到的那样,在于实践理论和信念的直率性。当这种直率性与‘为生民立命’的淑世精神和认为儒先的道理格式都完全成了道的绊脚石的英雄气概相结合时,在布衣颜山农一派那里,不拘泥于儒家矩镬和士大夫名教的自由奔放活动想必就能开展起来。这时就卷起了‘游侠’之风。”(30)在明代中后期,泰州一脉的平民教育为愚夫愚妇们找到了一个表达政治理想、政治情感和政治秩序希冀的出口,于是解舟放缆,一发而不可收。这终于越出了当权者的容忍限度,乃至出现因讲学而罹难的政治悲剧。
值得一提的是,明太祖朱元璋也曾写过《保身说》之类的东西。其中有云,“大化言天地之气,运用也。世之贤者,特以君政配之,亦谓之大化”,“所以人禀天地之气,全顺其宜而为之,则身安乎荡荡;阻其宜而为之,轻则致殃,重则丧命”(31)。完全是统治者基于统治秩序需要而采取的一种说教,细细玩味,甚至有威胁意味在内——愚夫愚妇如不能顺“君政”之大化,则有“致殃”“丧命”的危险。这与王艮基于愚夫愚妇平民立场的“明哲保身”论显然大异其趣。
(二)萃和会与聚和堂:愚夫愚妇的理想国实践
颜钧(号山农,1504-1596)是泰州后学最具代表性的平民学者之一。他师从王艮的学生徐樾,读书不多,自信狂放,有“儒侠”之称,以布衣终其身。在思想上,颜钧进一步发展了愚夫愚妇的“百姓日用”之学,力图通过讲学教化方式,以实现“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理想社会政治局面。如他在《急救心火榜文》中所言:
一急救人心陷牿,生平不知存心养性,如百工技艺,如火益热,兢自相尚。
二急救人身奔驰,老死不知葆真完神,而千层嗜欲,若火始然,尽力恣好。
三急救人有亲长也,而火炉妻子,薄若秋云。
四急救人有君臣也,而烈焰刑法,缓民欲恶。
五急救人有朋友也,而党同伐异,灭息信义。
六急救世有游民也,而诡行荒业,销铄形质。(32)
其勇于用世、任事的承当固然是直绍祖师爷王艮而来,而其关注由个体、家庭、族群乃至政治、社会的条理之处,更可见颜钧的具体政治社会实践指向。这个指向,颜钧自己阐明是为了“救人心火,以除糜烂,翊赞王化,倡明圣学”(33),这一实践指向的具体表现则是“讲会”。
颜钧早年即在家乡成立“萃和会”,进行讲学教化。如其《自传》所载:“竟为一家一乡快乐风化,立为萃和之会。会及半月,一乡老壮男妇,各生感激,骈集慈闱前叩首,扬言曰:‘我乡老壮男妇,自今以后,始知有生住世都在暗室中鼾睡,何幸际会慈母母子唤醒也。’会及一月,士农工商皆日出而作业,晚皆聚宿会堂,联榻究竟。会及两月,老者八九十岁,牧童十二三岁,各透心性灵窍,信口各自吟哦,为诗为歌,为颂为赞。”(34)颜钧对这次讲学教化的意义是颇为期许的:“惜哉,匹夫力学年浅,未有师传,罔知此段人和三月,即尼父相鲁,三月大治,可即风化天下之大本也。”(35)由此可知,在颜钧看来,愚夫愚妇的百姓日用教化关乎“风化”,意即平民儒者的讲学实践具有重要的政治意蕴;虽是“匹夫力学年浅”,却也能在实践中做出类如“尼父相鲁”这样了不起的政治事业来;讲学教化可以视为风化天下之“大本”,意即有裨于政治和社会稳定,是对“王道”政治的有益补充。颜钧自撰《箴言六章》阐发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六条”(36),所显现的也是这种路向。
颜钧弟子罗汝芳“居乡居官,常绎诵我高皇帝圣谕,衍为《乡约》,以作《会规》,而士民见闻处处兴起者,辄觉响应”(37),他一生讲学,多以《太祖圣谕》、《乡约》、《会规》来对民众进行教化。就这一点而言,罗汝芳确乎承袭乃师衣钵。或曰,平民儒者因讲学而被系甚至罹难,其实另有原因在。
颜钧弟子何心隐(本名梁汝元,1517-1579),初为诸生,闻知王艮泰州之学后,毅然改变了人生志向,“从学于山农(颜钧),与闻心斋立本之旨”(38)。沿着颜钧率性自然、狂放自任的道路,何心隐走得更远。他在《聚和老老文》中,提出了“育欲说”。研究者据此而认定其思想具有“启蒙性”与“平民性”。徐春林指出:“何心隐所倡导的‘欲’是指‘公欲’,它既非立足于‘社会全体’的‘全民之欲’,也非满足个体愿望的个人之欲,而是立足于家庭需要的‘家族之欲’。也就是说,它既非‘宏观’之‘欲’,也非‘微观’之‘欲’,而是一种‘中观’之欲。它是立足于家族利益而提出的,反映了家族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统治者的要求,但又突出地反映了家族成员的利益,是从‘全民之欲’走向个体之欲的桥梁和过渡形式。在实践上,它是为其聚和堂建设服务的。”(39)结合何心隐聚和堂的实践,徐春林的论断是有一定说服力的。
何心隐建立的聚和堂是以宗族为单位而组成的自治团体。在教育、抚养、治丧、冠婚、衣食以及纳税等方面,概由团体统一管理。聚合堂成员平等,集体生活,即所谓“总聚祠”、“总宿祠”、“总送馔”。希图真正做到“老安少怀”。何心隐则“身理一族之政,冠婚丧祭赋役,一切通其有无,行之有成”(40)。这种带有愚夫愚妇空想色彩的聚和堂实践,历时有六年之久,最后因何心隐反对当政者赋外之征被诬入狱而结束。
何心隐的理想国实践是建筑在他对“人”的理解之上的。先秦儒家以道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何心隐继承了这一观点,强调“人则仁义,仁义则人”(41)。不过,何心隐对先贤之论并非简单地承袭,而是超越了君臣父子贵贱尊卑的“差等”局限,具有了包括愚夫愚妇在内的普泛视野。他认为:
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之为大,非徒父子之亲亲已也,亦惟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
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斯足以象义也。
亲与贤,莫非物也。亲亲而尊贤,以致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莫非体物也,格物也,成其象以象其象也,有其无以显其藏也。仁义岂虚名哉?广居正路,岂虚拟哉?(42)
“亲亲而尊贤,以致凡有血气之莫不亲莫不尊”,无疑将“仁义”之为“人”的道德本质观察扩大到包括愚夫愚妇在内的,“凡有血气”的所有活生生的人的范围。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实践,在他看来,“仁义”才不是“虚名”,“广居正路”才不是“虚拟”,一切都可以付诸社会政治生活实践。
问题在于,何心隐的“仁义”主体的“人”,无论是思想也好,实践也好,所认同的政治价值仍然是君权神圣,所认同的政治参与亦仍然是政治教化。在聚和堂实践中,他强调要“上思君之所以善其治者,以有国家之教也;下思民之所以善其俗者,以有乡学之教也”(43)。又强调“养本于君之所赐也”,而合族聚和率养最终要“同乐于尽分以报君上之赐也”(44)。
可见,从王阳明到何心隐,“愚夫愚妇”从身体到实践,从抽象的指称到挺立起来的主体,依然局促于传统儒家君主政治文化的覆盖与笼罩之中,无法实现最终突破。尽管泰州学派平民儒学语境中的“人”,从理论到实践,涵纳甚至标举了愚夫愚妇的百姓日用,却依然牢牢地固着在传统政治价值结构基础之上,未曾动摇。这表明在王权专制社会中,很难自发地一线转出近代意义上的市民意识。
(三)邓豁渠:“学得一个真百姓”
泰州后学中,邓豁渠(名鹤,号太湖)亦是极具“异端”色彩的一位。邓氏受同乡泰州学派重要传人赵贞吉(号大洲,1508-1582)影响,接受“良知”之学,因领悟不深,便参禅以至剃度,四方访问,与阳明学者交流,终生游学,不复走学仕道路。岛田虔次说:“邓豁渠明显是王学左派中人,但没有李卓吾那样的学识和才气,何心隐那样的胆力和气度,可说是内向式的、求道者式的,甚至是愚直的、一条道路走到底的人物。”(45)邓氏之“异”还体现在他甚至为了自己求道而抛弃了现实生活,不葬父、不嫁女、不受子迎,因而备受指责。然而,我们从他传世著作《南询录》中却看到了他关于“愚夫愚妇”百姓生活极有价值的思考。
邓豁渠高度强调了“百姓日用”的价值与意义,认为对于学者来讲,“百姓日用”才真是妥帖的,而“学百姓”也就是“学孔子”,“百姓日用是学得圣人的”,所以学得“一般吃饭”、“一般睡觉”的百姓日用之“常情”,即是学得“真百姓”,“才是一个真学者”。他在《南询录》中说:
学到日用不知,不论有过无过,自然有个好消息出来。……学百姓学孔子也——百姓是今之庄家汉,一名“土老”,他是全然不弄机巧的人。(46)
百姓是学得圣人的,贤智是学不得圣人的。百姓日损,贤智日益。百姓是个老实的,贤智是弄机巧的。一个老实就是,有些机巧便不是。(47)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才是一个真百姓。学得一个真百姓,才是一个真学者,才是不失赤子之心。无怀氏之民也,葛天氏之民也,此之谓“大人”。(48)
学得与常情,是一般吃饭,一般睡觉,如痴如呆,才是好消息。(49)
耐人寻味的是,同样被耿定向称为“异人”,何心隐勇于在“愚夫愚妇”的日用生活当中实践他的政治社会理想,而在邓豁渠这里,尽管把“学百姓”从思想上升华到“学孔子”的高度,高呼“学得一个真百姓”,强调百姓日用的境界与意义,但已不复有那种勇敢的实践精神,而重新又把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付诸抽象的指称。毋宁说,在颜钧、何心隐那里具有走向政治参与实践的“愚夫愚妇”群体生活的外在指向,在邓豁渠这里仅仅是一种具有个人修治内在指向的价值思考。即便如此,邓豁渠“学百姓”观念的提出仍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意义。
我们知道,宋明理学家为适应重振纲纪的社会政治需要,曾树立起“圣人”这一理想人格,试图以普遍提升人们的道德品格来清明政治。他们认为“圣人可学而至”,或观“圣贤气象”,或看“孔颜乐处”,诚敬以之,无不以“优入圣域”为志趣。泰州学派的平民儒者在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初步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开始跃登社会舞台的社会背景下,高揭“百姓日用即是道”之帜,邓豁渠更进而提出“学得一个真百姓”的崭新观念,这当然与倡言“学圣人”的士大夫精英儒学大异其趣。
并且,对于今人来说,邓氏强调“百姓日用”所具有的启发之处,亦在于其并非只局限于儒学内部来理解,而是试图与禅、老打通,以把握其“百姓日用”之学旨。正如岛田虔次所总结的那样,邓氏经常主张抛弃“秀才的旧套子”(50),即试图从儒学中走出来。这里蕴藏的思想价值似可以这样理解:无论是在儒家的话语和思维中,还是在儒家关于人的认识与设计中,“愚夫愚妇”之道、百姓日用的认知与实践始终被禁锢于“旧套子”中,而这“旧套子”所能够容纳的“愚夫愚妇”思想与实践空间是有限的。“愚夫愚妇”的平民儒学要想获得开拓性发展,并进而寻求广阔的实践空间,就必须打破“旧套子”,冲决君主专制政治与精英儒学交织成的网罗。邓豁渠显然未能形成这样的认识。
三、“愚夫愚妇”:异动及其归宿
(一)平民儒者“人”的观念的异动
检中晚明文献,“愚夫愚妇”的话语在阳明、心斋之后在在可见,谓之流行当不为过。如与泰州学派有渊源的耿定向说:“凡道之不可与愚夫愚妇知,能不可以对造化通民物者,皆邪说乱道也。”(51)这无疑是对“圣愚一体”等泰州学派典型认识的高度认同。影响所及,中晚明思想界以“愚夫愚妇”作为话头,成了一种惯常的话语方式。如:
古之为政者,将以化民。今之为政者,愚夫愚妇或从而议之,何民之能化?(52)
有人问我,东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对曰,只是这等大圣大贤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妇也减不得些子,莫轻看了这一拱手,从前不知费许多钻研,方讨得这个模样,从后不知费几许兢业,方保得这个模样。(53)
圣贤与愚夫愚妇千古同体……故曰:尧舜与人同耳,此孟子实言。(54)
纤毫无与愚夫愚妇异者,方为真为己。(55)
王公大人一时之耳目,不能欺里闾愚夫愚妇千载之真心。(56)。
夫不离愚夫愚妇而直证道,真彻上下而言之者,其惟良知乎!(57)
愚夫愚妇各具圣人体段,一觉悟焉,如醉梦得醒,自尔手舞足蹈。(58)
……自外视之,一不识不知之愚夫愚妇而已。呜呼!吾安得志学之士皆为愚夫愚妇哉!(59)
这显然与阳明、心斋,尤其是心斋之后的平民儒者对“愚夫愚妇”、“百姓日用”观念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拓展有关。
然而,遍在的“愚夫愚妇”话语,又让我们遗憾地感受到,“愚夫愚妇”似又重新回归到士大夫阶层对平民的一种抽象群体指称,其中的具体实践内容随着泰州后学平民儒者颜钧、何心隐辈的谢幕而归于消散。就此,泰州学派平民儒者语境中的“愚夫愚妇”观念曲折地透显出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某种程度的“异动”。
首先,人之自由精神的强烈张扬,对传统政治价值形成了某种冲击。
传统政治价值的基本结构由君权至上、父权至尊、伦常神圣、均平理想、明哲保身五个层次构成。其中,君权至上是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中轴,是核心;父权至尊是君权至上的社会保障机制,伦常神圣则主要通过忠孝相互切换的形式,促使君父之间形成价值互补,从而构成了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主体部分,均平理想与明哲保身则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调节机制而发挥作用(60)。泰州学派平民儒学,从“愚夫愚妇”的“百姓日用”出发,对作为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主体部分,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
在传统伦常关系中,何心隐独将朋友一伦提出加以强调,他以为“交尽于友”,只有朋友关系才具有相对平等的意味,其他伦常关系或“比”,或“匹”,或“昵”,或“陵”,或“援”,总之都具有不完美之处。他阐述说:
天地交曰泰,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道而学尽于友之交也。昆弟非不交也,交而比也,未可以拟天地之交也。能不骄而泰乎?
夫妇也,父子也,君臣也,非不交也,或交而匹,或交而昵,或交而陵、而援。八口之天地也,百姓之天地也,非不交也,小乎其交者也。能不骄而泰乎?
骄,几泰也。均之气充盈也。充盈,几也;几,小大也。法象莫大乎天地,法心象心也。夫子其从心也,心率道而学也,学空空也。不落比也,自可以交昆弟;不落匹也,自可以交夫妇;不落昵也,自可以交父子;不落陵也,不落援也,自可以交君臣。天地此法象也,交也,交尽于友也。友秉交也。夫子贤于尧舜,尧舜一天地也,夫子一天地也。一天一地,一交也,友其几乎?(61)
在何心隐看来,五伦中唯朋友关系具有平等性,故以朋友一伦来贯穿昆弟、夫妇、父子、君臣等四伦才是健康而正常的。在朋友关系基础上,他进而强调“师弟”关系,认为:“可以相交而友,不落于友也。可以相友而师,不落于师也。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惟大为泰也。师其至乎!”(62)何心隐的这种观念落实到社会政治组织上,便是强调建立他所谓的“会”,即一种超越家庭与身份之上的组织。“从现存的何心隐的著作来看,我们应该说,他的这种‘会’,从政治性的组织上讲,是一种社会运动的集团。当‘见龙在田’的时候,是师友,当‘飞龙在天’的时候,就是君臣”(63)。
何心隐对人的主体意识张扬,直接落实到伦常关系当中,便是对朋友一伦的重视与阐发,以此朋友一伦来贯穿父子、君臣关系,多少含有一种向君、父争权利的意味,这当然会对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结构形成相当的冲击。
他的此种认识,落实到社会实践中则是“会”的建立。尽管我们知道聚和堂实践与其“会”理论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他的勇敢实践无疑是基于对传统伦常的一种改造,这种改造当然酝酿着一种破坏性的冲击,这也正是他备受诟病的地方。如李贽在《何心隐论》中引述的那样:“人伦有五,公舍其四,而独置身于师友贤圣之间,则偏枯不可以为训。与上訚訚,与下侃侃,委蛇之道也,公独危言危行,自贻厥咎,则明哲不可以保身。”(64)指责恰可以让我们了解何心隐对作为传统政治价值主体内容之一的伦常神圣所构成的冲击。自然,邓豁渠的不葬父、不嫁女、不受子迎而屡被指责,也与他对“伦常神圣”的忽视有关。
其次,“愚夫愚妇”具体社会实践所要求的社会政治空间,对既有政治秩序形成某种冲击。
将思想直接付诸行动,信念坚定,是泰州学派平民儒学标志性的特殊风格,这一点为诸多学者所认同。正因如此,在泰州学派平民儒者这里,“愚夫愚妇”的“百姓日用”才不仅仅停留在观念认识层面,而直接化生为展现一个普通人承当大“道”的具体生活实践。平民儒者的具体社会实践,除了依托于宗亲基础建立的各种“会”、“堂”而外,更多的则是对包括“愚夫愚妇”在内社会普通民众的讲学活动。
明代中晚期的心学思潮与讲学运动密不可分。阳明及其后学正是借讲学而使心学思想风靡一时,耸动朝野。泰州王学诸子生存于斯时,当然热衷于讲学。其间景况甚有可观,他们讲学时从之游者动辄千数百人,获得很大成功。如邓豁渠所记述的王艮之子王襞(号东崖,1511-1587)讲学:
此日起会讲学,陆续来者知渠是与东涯(引者按:即东崖)书的和尚,咸加礼貌。坐下末席,再会坐上末席,三会坐上中席。是会也,四众俱集,虽衙门书手,街上卖钱、卖酒、脚子之徒,皆与席听讲。乡之耆旧,率子弟雅观云集——王心斋之风,犹存如此。(65)
其景象明显是与士大夫阶层讲学不同的。泰州学派平民儒者的勇于实践,以及狂放的个人风格,更将他们的讲学活动推至轰轰烈烈的地步。陈时龙将阳明学内部的讲学分为两系,“一系自王阳明、王畿、钱绪山、邹守益而始,是精英式的、学院式的讲学;一系自王艮始,是庶民式的讲学……学院式讲学的代表人物,通常是进入过仕途甚至在仕途上颇为辉煌的讲学者,他们是政治和讲学的精英;庶民式讲学的代表人物,大多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低级官僚或布衣百姓,在政治上常受迫害,一生命运多舛,像何心隐、邓鹤、李贽都不得善终”(66)。
这种讲学活动具有显明的政治属性。平民儒者的讲学对既有的政治秩序乃至意识形态形成了极大冲击。他们庶民式讲学的特点主要集中在这几个方面:求道的日常化、儒家经典的简易化、圣人权威的通俗化以及讲学对象的底层化等。对底层民众的启发无疑与统治阶层企图通过讲学加强对下层民众的控制具有相当的矛盾性。因之,带有政治社会化意蕴的讲学活动,发展到泰州后学讲学导致“一境如狂”的地步,其空间便不再为统治阶层所容纳,平民儒者讲学活动遭受打压和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愚夫愚妇”——泰州学派平民儒者关于人的观念突破的根芽亦同时夭折了。就此来看,泰州学派的平民儒学,确有一定的启蒙性质。
(二)“愚夫愚妇”异动的限度
“愚夫愚妇”的自我认同,归根结底是建筑在对以士大夫为载体的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基础之上的。他们认识到了自身——“百姓日用”——平民生活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他们对这种价值与意义的评判标准,却又基本上是士大夫式的。他们的自信来自道德修治方面的平等观念,他们的狂放来自对“圣愚无间”的认可。他们的认识呈现出一种悖论:越是在道德上肯认“愚夫愚妇”的价值,就越是将“愚夫愚妇”的认知标准向士大夫阶层贴近。因而他们的异动表现出一种曲折的转向,当碰到传统政治价值结构的硬壳时,便自动退却了。这样,他们思想的发展只能有两种趋向:一是反抗到毁灭,二是认同士大夫阶层到消失自我。“英雄莫比”的何心隐是前者,“赤手搏龙蛇”的王艮及其弟子林春、颜钧等是后者。
按照现代政治学理论,每个人即每一个政治行为者都应该是社会政治主体,但在中国传统君主政治条件下,作为“愚夫愚妇”的平民阶层,实际上被客体化了。他们已经不成其为社会政治主体,而是从身体到意识全方位地受制于政治权力主体——士大夫阶层。
在君主政治条件下,“愚夫愚妇”们既不能作为社会政治主体,也无法提出严格意义上的近代启蒙思想,并在根本上跨越以士大夫为载体的传统政治文化。诚如岛田虔次所言:“在旧中国,本义上的社会,是士大夫的社会,庶民从原理上来说不过是欠缺状态的士大夫,是不完全的士大夫,或者说是士大夫的周边现象而已。心学即使在被说成是开放的、革新的场合,也不能马上以此来作为庶民意识的自觉表现、庶民原理的自觉表白。”(67)岛田虔次还指出:
近世哲学的根本课题本身,在其本质上,是立足于士大夫以前的人的概念上的;泰州学派显著地吸收了庶民的风气,追求独自的自我意识和人的概念;最后到李卓吾,确立了与士大夫的理念完全不能相容的文化批判。然而,就像已经论述过的那样,那决不是觉悟了的新兴阶级的意识之反映,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在原来界限就活动着的士大夫阶级内部统制极度弛缓时所发生的异端现象。士大夫作为学问的独占者、政治的担当者,在其内部要坚信和维持明确的统一体,在这一点上,它是彻底关闭的;但是在其存立和在被科举支撑这一点上,其根本构造在原则上又是开放的,因为其人员的构成是不停地广泛地吸收非士大夫分子、庶民分子的。(68)
他因此而强调:“我们不应该把庶民性的东西马上武断为庶民的阶级性的东西。”(69)究其实质,平民儒者强调的“愚夫愚妇”主体自觉,从根本上说还只是一种道德主体性自觉,并且他们自觉承当的道德义务与责任正是士大夫阶层所宣扬、教化的基本政治价值。换言之,无论是从权力支配社会的君主政治时代的基本社会情形而言,还是从“愚夫愚妇”——平民阶层的自我意识而言,认同当下政治都只能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在传统的道德修身观念的普遍约束之下,人们不是作为权利主体,而是作为道德义务主体参与全部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70),“愚夫愚妇”只能是一种道德主体,而无法成为一种权利主体,无法成为社会政治主体。出于道德自觉主动地对政治价值、政治秩序予以认同,是为士大夫阶层所支持的,因为这正是政治教化的目的,而在有的平民儒者那里,其“愚夫愚妇”观念所体现的对既有政治价值认识的突破,则是士大夫阶层决然不能接受的。如何心隐独重“朋友”一伦,强调君民平等,这种对既有政治价值、政治秩序的冲击已注定了他被镇压的悲剧性命运。一言以蔽之,“愚夫愚妇”必须“止乎礼义”,必须认同既有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秩序,这就是平民儒学语境里关于“人”的观念中某些“异动”的最终限度,也是王权专制社会为儒学划定的历史发展极限。
四、结语
在以士大夫为载体的传统政治文化强势覆盖下,权力支配社会的基本状况限定了“愚夫愚妇”阶层的生活和意识。平民儒学对“愚夫愚妇”阶层身体、生活乃至“政治参与”的思考与阐发,是在君主政治框架下的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我们不能否认其早期启蒙价值。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政治文化给“人”的空间十分有限,“人”作为臣民,只能尽义务,不能言权利,只能在道德上发扬主体性,而不被允许成为真正的社会政治主体。况且,除了个别人士,大部分平民儒者都在发自内心地认同与维护着既有的政治价值与政治秩序。所以,将平民儒学的启蒙价值估计过高也是不切于实际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强势覆盖性与普遍的弥散性严重地桎梏着人们思想观念,难有突破。因此,没有社会的革命性变迁,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是不可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变迁应该是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这首先应体现为“人”的观念的变革。
注释:
①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63-64页。
②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62页。
③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72页。
④宣朝庆:《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74页。
⑤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页。
⑦陆九渊:《与吕伯恭》,《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1页。
⑧杨简:《二陆先生祠记》,《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14-515页。
⑨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98页。
⑩王守仁:《答顾东桥书》,《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9页。
(11)王守仁:《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上册,第107页。
(12)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宋明理学史》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35页。
(13)[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6页。
(14)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90-91页。
(15)朱承:《治心与治世——王阳明哲学的政治向度》,第87页。
(16)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页。
(17)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10页。
(18)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10页。
(19)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6页。
(20)王艮:《答朱思斋明府》,《王心斋全集》,第47页。
(21)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9页。
(22)王艮:《与南都诸友》,《王心斋全集》,第51-52页。
(23)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34页。
(24)徐春林:《生命的圆融——泰州学派生命哲学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64页。
(25)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8页。
(26)王艮:《明哲保身论》,《王心斋全集》,第29页。
(27)王瑶湖(1486-1549),名臣,阳明后学,曾为泰州知府。
(28)吴震:《泰州学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9页。
(29)王艮:《语录》,《王心斋全集》,第39页。
(30)[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57页。
(31)朱元璋撰,胡士萼点校:《明太祖集》,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第320-321页。
(32)颜钧:《急救心火榜文》,颜钧撰,黄宣民点校:《颜钧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3页。
(33)颜钧:《急救心火榜文》,颜钧撰,黄宣民点校:《颜钧集》,第2页。
(34)颜钧:《自传》,颜钧撰,黄宣民点校:《颜钧集》,第24页。
(35)颜钧:《自传》,颜钧撰,黄宣民点校:《颜钧集》,第24页。
(36)即所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条。
(37)罗汝芳:《近溪子集》,罗汝芳著,方祖猷等编校整理:《罗汝芳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4页。
(38)黄宗羲:《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04页。
(39)徐春林:《生命的圆融——泰州学派生命哲学研究》,第110页。
(40)黄宗羲:《明儒学案》,第704页。
(41)何心隐:《原人》,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页。
(42)何心隐:《仁义》,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27页。
(43)何心隐:《聚和率教谕族俚语》,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68页。
(44)何心隐:《聚和率养谕族俚语》,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70、71页。
(45)[日]岛田虔次:《异人邓豁渠略传》,《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46)邓豁渠著,邓红校注:《〈南询录〉校注》,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2-63页。
(47)邓豁渠著,邓红校注:《〈南询录〉校注》,第63页。
(48)邓豁渠著,邓红校注:《〈南询录〉校注》,第64页。
(49)邓豁渠著,邓红校注:《〈南询录〉校注》,第39-40页。
(50)[日]岛田虔次:《异人邓豁渠略传》,《中国思想史研究》,邓红译,第161页。
(51)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卷五《复乔户部》,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刘元卿刻本。
(52)罗钦顺:《困知记》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3)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八下《与东林诸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4)邹元标:《愿学集》卷三《答徐鲁源太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5)邹元标:《愿学集》卷五下《澹台祠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邹元标:《愿学集》卷三《答徐鲁源太常》,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刘宗周:《刘蕺山集》卷九《钱绪山先生要语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曹于汴:《仰节堂集》卷三《张时庵先生八十寿册引》,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潘平格:《潘子求仁录辑要》卷十《笃志力行下》,清康熙刻本。
(60)参见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49、57页。
(61)何心隐:《论友》,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28页。
(62)何心隐:《师说》,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第28页。
(63)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024页。
(64)李贽:《何心隐论》,《焚书·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0页。
(65)邓豁渠著,邓红校注:《〈南询录〉校注》,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0页。
(66)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78页。
(67)[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128页。
(68)[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138页。
(69)[日]岛田虔次:《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甘万萍译,第127页。
(70)葛荃:《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153页。
标签:王阳明论文; 儒家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泰州学派论文; 士大夫精神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传统观念论文; 宋明理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