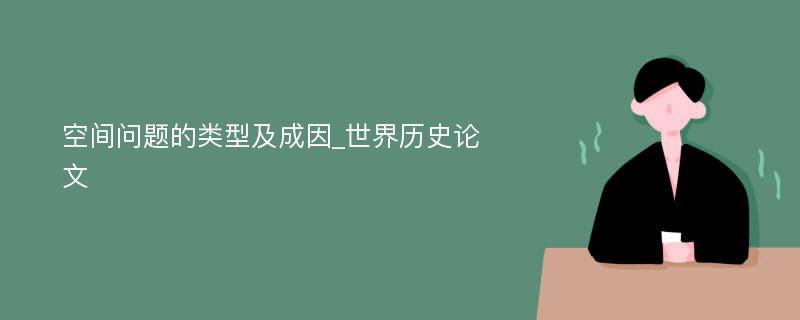
空间问题的类型与形成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因论文,类型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20世纪60年代福柯在他所作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这篇演讲中,预告了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他认为,这个时代与被时间所纠缠的19世纪完全不一样。19世纪的人们迷恋的是时间,对发展、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特别关注;而现在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是一个点对点之间的互相联结、团与团之间互相缠绕的网络。①与此相应,美国学者爱德华·苏贾极力批判以往时代过度强调时间-历史语境,许诺要给空间以显赫的地位。他在自己的一部著作中甚至将“前言”和“后记”放在一起撰写,有意要用这种方式“打破线性文本的正常流动,使其他诸种更为‘侧面’的联系成为可能”,从而将“历史叙事空间化,赋予持续的时间以一种经久不衰的批判人文地理学的视野”。②这是人类思维领域悄然兴起的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这场变革涉及空间问题的种类如何、原因是什么等基础性问题。这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野,对有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 空间问题的基本类型 空间问题概括地说有三个:一是空间与人类实践活动的关系问题,这是空间的本体论问题;二是空间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问题,这是空间的认识论问题;三是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意识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空间的辩证法问题。 (一)空间本体论 空间的本体论涉及的是空间的起源、本质和分类问题,这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空间性”,它表明空间或者空间性是与人类的产生同时“在场”的。人在通过自己的活动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创造自身的同时也把空间创造出来,因为人创造自己实际上就是把自身与其他各种事物区别开来,这种区别就是创造一种距离和差别即空间。 苏贾在《后现代地理学》一书中讨论人的空间意识的诞生时,引用了马丁·布贝尔在1957年的《距离与关系》一文中的观点。布贝尔在文章中提出,空间性是人类意识的开端,是内含于人类意识过程之中的“原初的空间化”。人类活动使世界与自己分离。这是一种借自身的活动使自身突出而对世界进行客观化的举动,这一举动就是创造一种差距、一种距离、一种空间,它界定了人类的处境,并使人类的处境取决于空间性,取决于通过距离的创造并通过空间性才成为可能的分离能力。人类不仅能够使自身与客观事物分离,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自己进一步的活动把自己同世界再度联系起来,并建立与被分离的客观世界的同一性,从而创造存在的意义。分离的不断产生又不断地被克服,就形成了存在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存在的时间性是指从分离到分离的克服,再到新的分离的产生这样一个不断转化的过程;存在的空间性则指“存在的状态”或存在在“生活世界”中的一个位置。关于空间本体论,除了阐明它与存在的这种“原始设置”的特点之外,还有一个要说明的就是关于空间类型即如何理解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或意识空间的问题。 在《空间的生产》这部著作中,列斐伏尔从不同的角度称谓的空间达三十余种之多,但笔者以为真正能够从本源方面进行区分的只能是自然、社会、心理或意识空间三种。即使这三种空间也并非分别存在的三种空间,而只是我们在思维领域所做的区分,现实存在的空间只有一个。在很长的历史时期,自然空间一直占据着人类关于空间认识的绝对主导地位。到了近代,特别是自笛卡尔以来,经过康德、黑格尔的强化,心理空间或意识空间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在各种理论都被这种物质-心理双重性垄断的情况下,社会空间被排斥在外,完全没有自己的地位。这种状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对社会空间的肯定,打破了传统的两重性,推进了人类对空间、时间和存在的物质性进行重新阐释。在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意识空间各种适当的阐释性语境中,“物性的物质空间与人性的意念空间这两者均必须被视为是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因此,每一种空间都需要当作社会生活空间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内容来加以理论化并加以把握。”③这就是说,无论自然空间甚至包括自然本身,不管看起来多么具有客观性和独立性,都与人类实践活动息息相关,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无论心理或意识空间在社会生活空间的形成过程中起到过多么大的作用,都来自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变革,是由社会本身所决定的。社会空间在现代空间哲学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以社会空间为主导的整体空间理论的内容被极大地丰富了。 (二)空间认识论 空间认识论要解决的是空间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问题。空间不是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器”,也不是空间变化转换的一个外部“平台”,空间与社会的关系是相互“熔合”的。不仅空间包含着生产关系及其变化和发展,而且生产关系也塑造着、改变着空间的结构和存在方式。我们在分析和认识空间与社会的复杂关系时,一定要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进行。因为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我们进行空间与社会关系问题研究的对象,而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出来的显著的空间化特点引起了许多学者的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才由以往聚焦于时间而转向空间的。 列斐伏尔认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及其生产的分析,需要从三个特殊层面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将空间看作社会行为的发源地,既把空间看作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又将其视为媒介以及资本主义关系的生成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空间的“生产”乃是它空间中进行生产的相关行为主体加上某种时空秩序后进行的,因而具有限制主体自由的作用。第二个层面是把资本主义主导的社会空间及其生产,看作资本与区域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创立的所谓“第二自然”,即都市化环境与组织结构,这是一种与资本主义相关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空间、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与相互交织的过程,要通过资本的作用将全部社会同质化或一体化并试图摧毁之。第三个层面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把社会空间视为全球范围、国家范围、都市范围内的建构的过程,资本主义要在此基础之上持续不断地进行区域化、非区域化以及重新区域化。“总之,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空间实践目前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发展框架,对当地资本主义的充分理解只有将其摆在全球范围内才有可能。”④ 对资本主义社会与空间关系的分析具有普遍的认识论意义,它要求我们既反对各种各样的总体性、同质化的理论,也反对那种将空间碎片化的操作方式和相应的理论观点,因为那正是资本主义的做法,资本将空间碎片化之后再用它们进行交易,以此来满足资本获取超额利润的需要。 (三)空间辩证法 依笔者看来,空间辩证法主要解决的是与空间本体论相关的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意识空间三者的辩证关系问题。在讨论三者的关系时,我们首先强调物质空间的第一性地位,但必须同时认识到,根本就不存在“自在的物质空间”,任何物质的或自然的空间都“充溢着政治和意识形态、各种生产关系以及富有意味地得到(向其他空间)转换的可能性”⑤;在强调意识空间形成和它表征各种空间的重要作用时,也要防止它有可能掩饰其来源于社会生活的真相,和对物质、社会空间的依赖关系;甚至我们在强调空间的社会本质时,在用社会空间统摄物质的、意识的空间的时候,也要看到它的物质空间的基础,而且它需要意识空间的想象和表征,更要看到社会空间有着向其他空间形式转变的诸多可能性。 几种空间形式的内在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在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阶级、国家、民族、城市、世界市场等进行空间分析时,一定要把自然空间的因素和由意识空间所造就的文化景观、心理因素都考虑进来,就像列斐伏尔在对现代资本主义所作的分析那样。他在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空间分析时,把空间视为一个整体置入自己的分析框架之中的。在他看来,无论是物质的、意识的还是社会的空间都是被资本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纳入生产力与产物之中。都市结构及其沟通与交换的多重网络,成为生产工具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乃是资本的一部分”。⑥除此之外,各种影视产品、大众娱乐节目、理论、学术、文化产品所形塑的空间,也被利用来为资本服务,或被国家利用来对各个地区实施控制,等等。其结果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矛盾,造成所谓的“普遍性的空间爆炸”。资本主义空间的主要矛盾就是它要把所有的地方或空间都变成一个样子,它遵循均质化的逻辑与重复策略,但它很快就发现有一些东西是它无法占有和控制的,“例如自然、场所、地域性(在区域的、国家的、乃至于世界的层面上)”,“资本主义和国家都无法掌握这个它们生产出来的混乱、充满矛盾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在各个层次上目睹空间的爆炸”。⑦资本主义空间的矛盾及其空间爆炸的结果是社会主义空间的诞生。这就是列斐伏尔力图要证明的空间辩证法的运行逻辑。 我们认识到,空间问题是植根于人和社会的开端之中的问题,一切关于人和社会的理论和学说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空间的社会化程度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提高,时代的发展正在实现由时间主导向空间与时间共同主导的转换,任何囿于时间而忽视空间的社会理论和学说,都只能具有传统的意义而非真正有价值的理论。从当代学者引入空间视域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成功分析中,更可以理解到空间认识论和辩证法在解释和批判当代资本主义各种新的现象时所具有的优越性。这一切同时也充分说明,空间研究之所以蓬勃兴起,不完全是一种学术的、理论的原因,实在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空间问题的大量产生和异常突出所致。 二 空间研究兴起的原因 在我们所处的现时代,空间之所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与人类实践活动所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以往传统的社会里,无论在传统的农耕社会还是传统的福特制的工业社会里,人们大都只将自己的实践活动与时间联系在一起。 在漫长的农耕社会里,一方面,人们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与节气、季令、寒暑往来等时间因素息息相关,因此人们对时间的感受和经验相当丰富,对时间之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重要性具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农耕社会人口中的大多数被束缚于固定的场所,极少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流动,由此他们所面对的外部自然环境也就很少会发生变化,这使那时的人们很少将空间与社会的变化发展联系在一起,他们至多视空间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一种不变的背景或容器,虽然它是不可去除的,但却是死板的、僵硬的,这样一种传统的看法也被延续至今。 到了工业社会,人们开始到处流动,但人们的工作地点仍相对固定,福特制的劳动方式讲究的是秩序、规则、统一,它对人们工作时间进行严格计算,劳动者创造的一切价值、资本家获得的利润都用时间来衡量,人们获得的报酬与他们工作的时间以及利用时间的效率密切相关。在时间成为衡量一切的统一标准之后,人们所处的诸如地位、环境、境遇、差别、距离等空间因素也就被遮蔽或者抹掉了。这些都促使人们将社会的发展变化与时间联系在一起而忽视社会与空间之间的内在联系。 这种情况可以用人类对时间认识的深入与对空间认知相对不足来予以证明。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很早就发明了各种精确计时的方法,创制出各式各样的历法,并将其与自己所从事的实践活动联系在一起。从古至今的哲学家对时间一直就具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如赫拉克利特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对时间的一维性特点的揭示;亚里士多德对时间“当下化”的高度关注,认为“没有时间就没有‘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时间;时间也因‘现在’而得以连续,也因‘现在’而得以划分”⑧;还有康德对时间作为“内感知”的合理定位,柏格森对时间“绵延”性质的刻画,以及海德格尔对时间的过去、当下与未来三维特性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分析等,这些都表现出了对时间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相反,一些同样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思想家在提到空间时,却表现出了极为矛盾和困惑的心理。如德谟克利特在论及空间时,因为对它的逻辑特性难以把握,所以干脆将其宣布为“非存在”,当他宣称空间是非存在之后,旋即又称空间具有真正的实在性,后来,“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称空间的概念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用适当的语词来描述的‘混乱概念’”,而贝克莱则坚持认为,“牛顿的‘真实的数学空间’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想象的空间,是人类心灵的一种虚构”⑨;等等。 这充分证明,即使只企图去理解和把握自然空间的感性形式和逻辑特性都十分困难,更不用说去理解和把握社会空间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了。这种状况导致福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西方的哲学传统原先古板地将时间分离于空间,而且在本质上将时间性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到了勾销空间性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重要性的程度。”⑩人们在思想领域对空间的这种理解困难与以往人类将空间与人类实践活动相互分离是相呼应的。这种情况直到传统工业社会解体、现代社会的诞生时才发生根本的变化。 现时代的人类实践是一种“大实践”。所谓大实践所指主要有三:首先,指的是实践活动明显有了扩大和深化,人类已经能够从微观、中观、宏观和宇观等不同层次向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全面进军,这可以称之为人类正在经历的一场空间领域的革命,它必然带来人们对空间的重新认识。其次,指的是随着实践活动的扩大和深化,人类的社会组织也在经历着同样深刻的变化。这不仅表现在大量的巨型城市、跨国公司、高度组织起来的现代化国家和各种社会组织,以及正在构建中的作为理性主体的人类的大批量的产生,而且也表现在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们都有条件和手段来积极参与现代社会和理性主体的建构,这种随实践发展而来的社会组织与结构的变化必然促使人们不再把空间只是视为一种外部环境,而是将其看作社会的一种内在因素。最后,由于人类正在进行的这场大实践是以现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为前提的,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就把大多数人从时间统治中解放出来,从时间中解放出来的人们可以摆脱对系统中心的依赖,获得更多的独立性,有了更多的时间来感受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也必然会改变我们经历时间和空间的方式。总之,极其便利的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产生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全球性的在场”,“空间和时间已经成了思考现代性组织与意义的媒介”。(11) 其二,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发生的最新变化、与现代语言叙事风格的转换同样有着密切的关联。 哲学领域发生的革命性的变革,首先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继而在当代以反对形而上学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诞生,及其在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与恩格斯继费尔巴哈在自然领域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之后,进一步在社会历史领域恢复了唯物主义的统治地位。后现代主义则对一直统治着现代哲学的理性哲学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唯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各式各样的“无空间性”的意识哲学、观念哲学、语言哲学和理性哲学的困境,意味着强调空间的哲学的兴起。历史唯物主义要用物质的原因解释历史,因而就不能不具有广延,因而也就不能不需要空间。后现代哲学的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与重视边缘、差异、偶然性、多样性的倾向,很显然也更具有空间哲学的意味。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历史唯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意识哲学、绝对化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时两相遭遇,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但它们毕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后现代主义只是将资本主义定位于“叙事危机、表征危机和合法化危机”,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至多是一种微观层次的、修修补补的工作,历史唯物主义更强调从整体和宏观上,即从“空间再造”方面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始终坚持和着眼于从实践领域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根本目标。 历史唯物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诞生,虽然为社会空间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但并没有很快引发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从以时间为中心向以空间为中心的转变,其间仍然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究其原因,一方面,正如苏贾所言,是由于唯心主义的空间思想一直都有很广阔的市场,人们仍然用先验意识等来讨论空间问题;另一方面,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僵化、片面的理解,忽视了后现代主义揭示出来的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单向性”、“同质化”的危机状况。当人们把各种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都毫不例外地归之为某种经济必然性,并进而将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毫不例外地视为社会形态依次交替时,情形就是如此。因为如果我们把经济因素视为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因素,不承认历史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或由多种合力推动的结果,如果人们习惯于用一种排除了偶然性的必然性来说明社会生活现象及其发展过程,用删除了各种“附属的”、“侧面的”联系的“主干”来“同一性”地把握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在用一种主观神秘的意识在把握社会和历史。理论意识中的这种历史决定论本质上就是“将空间附丽于时间,而这种时间掩盖了对社会世界可变性的诸种地理解释,扰乱了理论话语的每一个层面,从关于存在的最抽象的本体论概念到关于经验性事件的最为具体的解释”。(12) 其三,与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这里可以考察两种很清楚的事实,一个是国际政治在20世纪前后两半期发生的完全不同的格局或政治生态方面的变化;另一个是一种不同于以往工业化时代的、具有一种新的政治结构的国际性的大都市的崛起。 这两种事实在很大程度上有一种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在20世纪的前半期,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着一个中心,社会主义的世界也有一个中心,或者再往前追溯,在20世纪之前,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一再相互联合形成共同镇压和对付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各种组织,无产阶级也有自己联合起来的对抗资本主义的共同组织如第一、二国际。这样一种由二元对立形成的国际政治格局,是自资本主义发展肇始的全球主义或全球化运动始终存在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在以往大都市的发展中也同样存在,不过那是以城市和乡村、城市中心和它的边缘、富人区和贫民窟、高楼大厦和棚户区等对立为特点的。在这种二元对立中,无论哪一方都不容许存在中间地带,对任何摇摆不定的势力和来自内部挑战的惩罚,往往会比对敌人还要严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这种两极对峙格局的存在。这种对峙最终解决的方式就是战争、屠杀、混乱、消解、重组。20世纪的后半期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从国际政治格局方面看,两极对峙的局面逐渐消解,中心不再存在,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和特殊情况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多多少少存在着的地区主义和民族主义,虽然还有许许多多的争端和战乱,但大规模的屠杀和战争没有出现。新型的、力图避免二元对立的国际性的大都市,在世界各地快速或缓慢地形成和出现。它们尽可能地避免着城市过去出现的那种显著的二元对立,更多地呈现出的是一种无中心或多中心的城市格局,它们“更像由主题公园堆积起来,一个由迪斯尼乐园组成的生命空间”(13)。国际政治格局的这种变化以及现代国际性的大都市的出现,给人们用另一种方式看世界提供了必然性。这就把空间引入对人类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的观察、思考和研究之中。 总的来说,当代空间问题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尤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研究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深入到哲学本体论、辩证论、认识论诸多层面,形成新的哲学视野。这些新问题与新思想的形成,是当代人类实践使然,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所致,也与当代都市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有关。 ①参见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第18页。该书收录了福柯的《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原文出自福柯1967年的一次演讲,福柯从未想到要整理出版这些旧演讲稿。直到1984年,在福柯去世前不久,法国杂志《建筑-运动-连续》将包括这篇演讲在内的一些旧的关于空间问题的演说以《他者空间》为题发表。1986年春季,这些演讲稿又被译成英文,以《他者空间》为题发表在《诊断》杂志上。 ②③⑤⑩(12)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页;第201、202、183页;第184页;第181页;第23页。 ④⑥⑦(11)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17页;第49页;第49~51页;第19页。 ⑧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127页。 ⑨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69页。 (13)迪尔:《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第6页。标签:世界历史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物质与意识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经济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