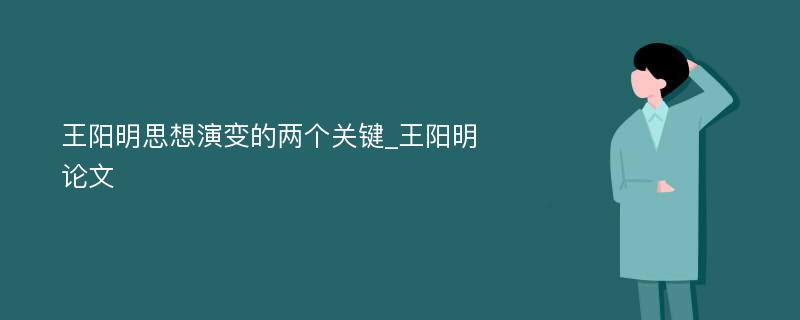
王阳明思想演化的两个关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个论文,关键论文,思想论文,王阳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02(2003)04-0032-07
提到王阳明思想的演化,最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的是“龙场悟道”。“龙场悟道”的确是王阳明心学精神方向最初确立的重要标志。然而,同样重要的一次思想定向——“致良知”宗旨的发明,无疑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所轻忽了。本文意在通过考据说明“致良知”宗旨的发明作为王阳明思想演化的关键,与“龙场悟道”相比较而言,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一、黄宗羲《明儒学案》“前三变”、“后三变”陈说溯源
关于王阳明思想的演变,最经常为研究者所引述的是黄宗羲《明儒学案》的说法:
先生之说,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及至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江右以后,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无有二也。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须假借凑泊,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也。[1])(P181)
这就是“前三变”、“后三变”之说,“前三变”是“凡三变而始得其门”,“后三变”是“学成之后又有此三变”。所谓“始得其门”与“学成”指的都是“龙场悟道”,此所说“前”、“后”也是以“龙场悟道”为划分标准的。黄宗羲这样说,有考据学上的依据,王阳明的弟子钱德洪有类似说法,不过,措辞有所不同。钱德洪所言如下:
先生之学凡三变,其为教也亦三变:少之时,驰骋于词章;已而出入二氏;继乃居夷处困,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是三变而至道也。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变也。[2](P1574)
依钱德洪所说,是“学凡三变”、“教亦三变”。此处“学”与“教”的划分,也是以,“龙场悟道”为标准的。这是黄宗羲与钱德洪所共同的。黄宗羲的两个“三变”,从考据上说,可以归本到这里。但他没有采取“学”、“教”这两种区别,同时“三变”(特别是“后三变”)之具体内容与钱德洪所述也不尽相同。其具体内容,从考据学的意义上讲,黄宗羲另有所本,就是王阳明的另一个弟子王畿在《滁阳会语》中所讲述的:
……先师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再变,而所得始化而纯。其少禀英毅凌迈,超侠不羁,于学无所不窥。尝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其志在经世,亦才有所纵也。及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几至于殒。时苦其烦且难,自叹以为若于圣学无缘,乃始究心于老佛之学。……及至居夷处困,动忍之余,恍然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非自见。……自此以后,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地,……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道德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自江右以后,则专提致良知三字,默不假坐,心不待澄,不习不虑,盎然出之,自有天则,……盖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此知之前,更无未发;良知即是中节之和,此知之后,更无已发。此知自能收敛,不须更主收敛;此知自能发散,不须更期于发散。收敛者,感之体,静而动也;发散者,寂之用,动而静也。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知之外更无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行之外更无知。……逮居越以后,所操益熟,所得益化,信而从者益众。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更无假借凑泊,如赤日丽空而万象毕照,如元气运于四时而万化自行,亦莫知其所以然也。……晚年造履益就融释,即一为万,即万为一,无一无万,而一亦忘矣。……[3]
黄宗羲言“前三变”、“后三变”的具体内容即本于此。细心一点,我们可以看出,黄宗羲所言几乎就是《滁阳会语》的缩写。不过,单从考据讲,其间的差别还是存在的。首先的一点是,王畿没有说“后三变”,只有“凡三变而始入于悟’,与“再变而所得始化而纯”。“始入于悟”是针对“龙场悟道”说的,“再变”之“再”,也是针对“龙场悟道”讲的。“龙场悟道”这一划分标准,是王畿与黄宗羲、钱德洪的相同之处。那么“再变”,在王畿这里指的又是哪一变?观《滁阳会语》之行文,王畿在“龙场悟道”之后,讲到“自江右以后”、“逮居越以后”、“晚年”等,似乎也可以说是“龙场悟道”后的三变,实则只有“自江右以后”足以成为一变,这也就是王畿所说的“再变”。“逮居越以后”与“晚年”都是此“再变”后的进境,都不足成为一变。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看到,王畿在叙述“自江右以后”的阳明思想所使用的措辞如“默不假坐”、“心不待澄”、“收敛”、“发散”、“未发之中”、“中节之和”等等,都是针对其前(即“龙场悟道”后)的“默坐澄心”、“收敛”、“发散”、“未发之中”、“发而中节之和”讲的,其间王畿所述的王阳明学旨确实发生了变化,而“居越之后”与“晚年”都没有这样针对性的说明,只是在描述一进境。很明显,“再变”就是指“自江右以后”说的。其实黄宗羲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故在讲到“学成之后”的三变时,只引述了王畿关于“江右以后”与“居越以后”的两段叙述,而未及“晚年”。以前两者再加上“龙场悟道”后的学旨而成其“三变”。
综上所述,从考据上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黄宗羲所述王阳明思想的演变,有其所本,即我们上面引述的钱德洪与王畿之说。其中,两个“三变”的说法采自钱德洪,但不取其“学”、“教”之变的区分方法。两个“三变”的具体内容则采自王畿,不过,王畿主“再变”,并不以“居越以后”为一变,黄宗羲则以“居越以后”为一变。下面,我们就对黄宗羲所本的钱德洪与王畿的说法做进一步分析。
首先谈谈钱德洪的“学”、“教”三变,以其讲得最简单清楚明白,不过是否就把阳明的思想变化讲清楚了,还当别论。“学凡三变”,指“驰骋辞章”、“出入二氏”与“龙场悟道”,“教亦三变”指“知行合一”、“静坐”与“致良知”。“龙场悟道”是关键,由此而“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与黄说与王说相比,没有讲朱熹之学的问题。并不是钱德洪认为王阳明对朱熹之学的探究不重要,而是讲“学凡三变”其意义有所专业,“辞章”之学与“二氏”之学皆非儒学,“学”之变,正是指由辞章之学而二氏之学乃至儒学这样的变化。朱熹亦为儒学,故讲“学”之变时不及此。而钱德洪在讲“龙场悟道”时也只是说“有得于圣贤之旨”,就是说有得于儒学之真谛,此真谛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他没有说。这就意味着钱德洪以王阳明之“龙场悟道”为其思想确立了儒家的精神方向,此精神方向是在“教亦三变”中展开的。“教亦三变”中最重要的是“致良知”宗旨的确立,观其措辞,则“江右以来,始单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体,令学者言下有悟”,则对“致良知”教法的确立最为重视。就其通篇文义来讲,是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后确立了儒家的精神方向,此精神方向在其教法经过几番变更后,经“致良知”宗旨的确立而最终得以明确。
为什么对钱德洪所述作这样的疏通,因古人谴词造句并不注重语言的严谨。比如说“居贵阳时,首与学者为知行合一之说”,单就这一句话来讲,是没有太多问题的,若把它列为“教”之一变,就有问题。“知行合一”始终是王阳明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居贵阳后提出这一命题,在江右提出“致良知”宗旨后,此命题仍是成立的,谈不上“变”。再如“自滁阳后,多教学者静坐”,这一句话本身就有问题。钱德洪这样讲,在考据上似乎亦有所本。《刻文录叙说》下面即引有王阳明的原话,“先生曰:‘吾昔居滁阳时,见学者徒为口耳同异之辩,无益于得,且教之静坐。一时学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渐有喜静厌动流入枯槁之病。故迩来只指破致良知工夫’。”[2](P1575)观此处所载王阳明话语,“静坐”似乎是王阳明“致良知”提出前所持一重要教法,其实照王阳明所说,也只是一时所发对病之药,王阳明讲“居滁阳时”只是所举一例。考诸王阳明之学说本身,不独在滁阳时(正德8年10月至正德9年4月,即1513年10月至1514年4月)有过教人“静坐”,早在正德4年(1509年)于龙场归途过辰州时即有教诸生“静坐”一事,但遂于书信中申明“静坐”为“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4](P144)如此看来,“静坐”即是一时对病之药,居滁阳时这样讲过,过辰州时也这样讲过,并不仅仅是“自滁阳后”多以此教学者而成为较长一个阶段所持的教法。故足以成为王阳明“教”之一变的只有“致良知”,钱德洪所着重去讲的、且有较深切的义理体会的也正是这一变。
下面再来看看王畿的说法。王畿说王阳明之学,“凡三变而始入于悟”,劈头讲一个“悟”,可见与钱德洪平实地讲“豁然有得于圣贤之旨”的学风之不同。亦因讲“悟”,所以悟前所经历者,有“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有“为晦翁格物穷理之学”,有“始究心于老佛”。观此措辞,也再见王畿之学风,“始究心于老佛”,似以老佛之学方为阳明入悟之正路。姑不论此,“入悟”与“得于圣贤之旨”讲的都是一事,即王阳明之“龙场悟道”。所不同的是,钱德洪对“得于圣贤之旨”并未直接作具体的说明,而是在“教法”之三变(特别是到“致良知”教)中逐渐展开的,王畿则直接对此有一说明,并把“致良知”教归结为阳明思想“所得始化而纯”的“再变”。暂不论其异,不管是归结为“教法”之一变,还是“所得始化而纯”的“再变”,王阳明的这两个弟子对师门“致良知”宗旨的提出是非常重视的。由此,我们得出结论,“龙场悟道”与“致良知”是王阳明思想演化中的两个重要标志,这是王畿与钱德洪都认可的。当然,不仅仅这样,这也是王阳明自己所不断强调的。
值得一提的是,王畿与钱德洪都是阳明提出“致良知”宗旨后才入阳明门下的,(注:钱德洪与王畿及门当在正德十六年辛巳,此时,阳明已得“致良知”宗旨。据钱德洪《刻文录叙说》:“德洪自辛巳冬始见先生于姚,再见于越,……”(《王阳明全集》卷四十一,P1575)则钱德洪见王阳明自正德十六年辛巳知,考诸王畿《绪山钱君行状》谓:“及阳明夫子平宸濠归越(即辛巳年),始决意师事焉。”(《王龙溪全集》卷二十)其后并言师事之事,则师事即自此时始。王畿及门也当在此后不远,观《绪山钱君行状》中“追惟夫子还越,惟予与君二人最先及门。……壬午癸未以来,四方从学者始众”(同上)之语可见。黄宗羲则以王畿为“嘉靖癸未下第归而受业于文成。”(《浙中王门学案二》,《明儒学案》卷十二,P238)不知所据为何。)故对师门“致良知”之旨有比较深切的体会。对此前阳明宗旨就未必有如许深的体会了,故钱德洪在述即“教”之三变的头两变时不免差谬。那么王畿呢?王畿所述“龙场悟道”后的宗旨是否就是对阳明此段思想的得当阐述呢?这里先不作正面回答,因王畿这一段议论实是有所为而发的,有其针对性。所谓“尽去枝叶,一意本原,以默坐澄心为学的”、“有未发之中,始能有发而中节之和”、“视听言动,大率以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这些话,考诸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发明“致良知”宗旨以前的语录、文录中,都有其依据,当然,这些也只是阳明此段思想的一部分,而非全部,王畿为什么特别说到这一部分呢?实则有其针对性,即针对当时与聂豹的辩论。这些观点,正是聂豹在辩论中屡屡提出师门教语以为论据的,对这一部分,王畿是无法提出质疑的,故在此,王畿把它们归于“所得始化而纯”以前的观点,而对王阳明确立“致良知”宗旨后观点的阐述,也往往是针对这些观点而言的。在《滁阳会语》这段议论之后,就是王畿对曲解师门良知宗旨的诸般说法(包括聂豹的说法)的批评,也足以说明这一点。
最后来看看黄宗羲的说法。从上面的结论中,我们看到黄宗羲的“前三变”、“后三变”之说是兼采钱德洪、王畿两家,前、后三变之格套出于钱德洪,具体内容采自王畿,同时,把措辞上明显有王畿之学风者略加改动(如把“凡三变而始入于悟”改为“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把“乃始究心于老佛”改为“于是出入佛、老者久之”),语序上也略有变动,文词亦有简省。不取钱德洪“学”、“教”之划分,则以“得其门”后,“学”亦有变,此“变”也是《明儒学案》对阳明后学的学派划分与评价的一个依据。取王畿所说“龙场悟道”后的宗旨,是为聂豹、罗洪先找其在阳明自身思想中的依据(用意不同于王畿),把王畿所言“居越以后”的进境亦属为一变,则是为王畿及泰州之“荡越”在阳明自身思想中找依据。
由上面的考证,我们可以看到,王阳明的两个弟子都特别提到了阳明思想演变中的两个重要变化,即“龙场悟道”与“致良知”,这也是王阳明自己所经常提到的。
二、王阳明思想演化的两个关键:“龙场悟道”与“致良知”考
关于“龙场悟道”,因为事实较为清楚,研究者的争议也较少,关于此事实较为详备的资料载于《年谱》正德3年戊辰(1508)条下:
春,至龙场。
先生始悟格物致知。……时瑾憾未已,自计得失荣辱皆能超脱,惟生死一念尚觉未化,乃为石椁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忆说》。[5](P1228)
关于此,王阳明自己尚有一个更为平实的说法:
……其后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验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然后叹圣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开窦径,蹈荆棘,堕坑堑,究其为说,反出二氏之下。[6](P127)
学者所学,当非一时顿悟即一了百了的,“龙场悟道”只是王阳明确立自身思想的精神方向的一个标志。故阳明说“再更寒暑”,如何如何。其实何止“再更寒暑”,经此“悟道”后,王阳明一直在探究其为学、立教的根基与立足点,直至开悟“致良知”宗旨,方才得到最终的落实。
关于开悟“致良知”宗旨,没有象“龙场悟道”那样清楚明白地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所以有一些争论的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无论视其为“教”法之一变,还是“学成之后”之一变,还是“所得始化而纯”的“再变”,即无论此“变”的性质如何,这一变都应该受到起码的重视,这对疏通阳明义理有较大的价值。正因为没有受到足够重视,所以在“致良知”宗旨提出的年代问题上,就有一些缠杂不清的说法。从早期资料来看,阳明弟子的说法就有不一致处。《行状》以为在正德9年甲戌(1514):“甲戌,升南京鸿胪寺卿,始专以良知之旨训学者。”[7](P1410)《年谱》以为在正德16年辛巳(1521):“十有六年辛巳,先生五十岁,在江西。……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注:见《年谱二》,《王阳明全集》卷三十四,P1278。《年谱》此说当为钱德洪说。《年谱》为钱德洪主其事,门弟子多参与其事,而未及门之罗洪先是一个重要的修订者。以此说为钱德洪所主,则另有据。《刻文录叙说》中,钱德洪这样说:“良知之说发于正德辛巳年。”下面又说:“……故《正录》书凡三卷,第二卷断自辛巳者,志始也。”可见钱德洪对“致良知”作为“教”之一变的重视,在编辑《文录》时即将此一变化考虑于其内。)《行状》所据不知为何,邓艾民先生以为所据在此:“良知本体原是无动无静的,此便是学问头脑。我这个话头自滁州到今,亦较过几番,只是致良知三字无病。”[8](P105)这里恐怕有误解,以“这个话头”就是“致良知”,故以为“1514年,他在滁州与弟子讲学时,更正式提出了这个学说……”[9](P100)其实,王阳明所说的“这个话头”,并没有限定地说是“致良知”,譬如滁州的教人“静坐”,后来的如何如何,如此变更一番,至今提出“致良知”三字,方觉得无病。而不是自滁州即提起“致良知”话头,其后经过几番变更,至今觉得还是此“致良知”三字无病。《年谱》属之辛巳,则以王阳明给邹东廓的信为证:“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10](P1278)此书未见《文录》中,不过,考诸《文录》中辛巳及辛巳以后与他人书中,亦多有言及此意者。邓艾民也以此说为准。据邓艾民先生,有日本学者山下龙二以正德15年庚辰(1520年)为“致良知”宗旨之始。陈来先生也持此说,我也认为当以此说为准。陈九川录王阳明语录有云:
庚辰往虔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曰:“请问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著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8](P92)
观此段载阳明话语的语气之促迫,当是于“致良知”宗旨有真切体会之初,急于以此开示门人的情形。当然,同“龙场悟道”一样,也有一个长期思考的过程,但至此时,则已有真切的体会。所以王阳明说:“我亦近年来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小欠缺。”邓艾民先生也注意到这一材料,但是以为“1520年他(王阳明)在赣州(即虔州)时期,尚忙于处理平定叛乱的善后工作,并未发表令人印象深刻的谈话。”[9](P101)其实,《传习录》下陈九川所录语录,此段以后,多为王阳明1520年在虔州开悟“致良知”宗旨时的教语。其中,明确标明在虔州的有三条:“在虔……”、“九川卧病虔州……”、“虔州将归……”。考诸《年谱》,王阳明正德15年(1520年)6月至9月大致五个月(是年闰8月)在虔州,而陈九川也确实在此时跟随师侧,《传习录下》陈九川所记在虔语录,当即是在此段时期。而其中关于“致良知”宗旨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谈话”也不在少数。王阳明也曾提及此事,如三年以后(嘉靖2年癸未,1523年),在《寄薛尚谦》书中说:“致知二字,……向在虔时终日论此,……”[11](P199)所谓“终日论此”,可见并非一时兴到的无根之谈。
王阳明此段开悟“致良知”宗旨,尚有一重要见证人,即其弟子邹守益。正德15年庚辰(1520年)9月,王阳明离虔州还省城南昌,曾有书信给邹守益:“自到省城,政务纷错,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者。虽自己舵柄不敢放手,而滩流悍急,须杖有力如吾谦之者持篙而来,庶能相助更上一滩耳。”[10](P1277)则阳明离虔州至南昌后,因政务繁忙,没有象在虔州那样“终日论此”的条件,故有意召其倚重弟子邹守益来更相发明。《年谱》正德16年辛巳(1521)正月载有与邹守益另一书:“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滩,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10](P1278,1279)此有“舵柄在手”之喻,前书有“舵柄不敢放手”之说,若作一大胆的猜测,则此书在前书之前所作,亦未可知。
关于王阳明召弟子邹守益来发明“致良知”宗旨一事,修订《年谱》的罗洪先有清楚的认识:“彼其才力足以特立而困为我者固尚众也,则又极力呼号,冀其偕来以共此乐。”[12](P1359)“冀其偕来以共此乐”,此处之“其”当指邹守益而言。此后,邹守益也确实应召而至南昌,共商此学。正德十六年辛巳(1521年)《与邹谦之》书有云:“别后德闻日至”[11](P178)语。此书《年谱》系之5月,则此前二人确实相见于南昌。在此书中,王阳明再召邹守益相讲于白鹿洞,邹守益二次赴南昌。邹守益《阳明先生文录序》有云:“以益之不类,再见于虔,再别于南昌,三至于会稽,窃窥先师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13](P1569)言“再别于南昌”,就是此两次南昌之行。这里还提到“再别于虔”,考诸王阳明《赣州诗》中有《次谦之韵》数首,当为丁丑、戊寅年间在赣州时所作。陈九川所录语录有云:“在虔,与于中、谦之同侍。”[8](P93)则庚辰在虔讲论“致良知”宗旨时,邹守益也在阳明左右。“再别于虔”语,当指这两次见王阳明于虔州。如此,则虔州悟致良知宗旨,邹守益也是一重要的见证人。而王阳明正德15年庚辰(1520年)9月与邹守益书所说“不复有相讲习如虔中者”,则是对知情人语矣。
从此,王阳明围绕“致良知”这一话头展开其理论架构。此一义理架构,有承“龙场悟道”后之积累而来的,也有迥然不同的鲜明的理论特色。就阳明本人来说,对此一转变是非常自觉的。如在以后的书信中屡屡提及此事,再如门人邹守益欲刻阳明文稿,王阳明嘱以“所录以年月为次”,[2](P1573)其目的即在于“使后世学者,知吾所学前后进诣不同。”[2](P1574)还有一值得一提的事,即王阳明《大学古本》的两个序。
其一,作于正德13年戊演7月(1518):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切,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格物以诚意,复其不之动而已矣!不善复而体正,体正而无不善之动矣!是之谓止至善。圣人惧人求之于外也,而反复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本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支与虚,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幸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罪我者其亦以是矣
其二,改于嘉靖二年癸未(1523年):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平天地之间,则备也。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体也。动而后有不善,而本体之知,未尝不知也。意者,其动也;物者,其事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圣人惧人求之于外也,而反覆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日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则存乎心悟,致知焉,尽矣。[15](P242,243)
我们知道,王阳明一向不注重于著述,而区区一篇《大学古本序》却尝“三易稿”,(注:语见嘉靖3年甲申《与黄勉之》书:“短序亦尝三易稿,石刻其最后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见,未可据以为定本。”(《王阳明全集》卷五,P193)此书作于嘉靖三年甲申(1524年),“石刻其最后者”当指上所引癸未之序,考诸《年谱》,《大学古本》刻于戊寅,则戊寅之序当属初稿,二易之稿为何已不可考。)这确实说明王阳明此时之思想趣向有所变化,而苦于这一变化不为门人所察。其于癸未年《寄薛尚谦》一书有云:“致知二字,是千古圣学之秘,向在虔时终日论此,同志中多有未彻。近于古本序中改数语,颇发此意,然见者往往亦不能察。”[11](P199,200)于此可见王阳明之良工苦心,而编辑《文录》者以癸未之《大学古本序》属之戊寅,似未见戊寅之序,(注:上所引《大学古本》二序,其癸未之序,通行之《王阳明全书》本系之“戊寅”,上海古籍出版社之《王阳明全集》本已察此谬,而于罗钦顺之《困知记》中收集到戊寅之序,收于《全集》之《补录》中(见《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二)。)也辜负了王阳明这一番苦心。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在考据上说明了王阳明成学过程中的两个重要时期,其一即正德3年戊辰(1508)之“龙场悟道”,其二即正德15年庚辰(1520)在虔开悟“致良知”宗旨。在笔者看来,“龙场悟道”可以说是王阳明确立其作为“为己之学”的心学精神方向的重要发端,而“致良知”宗旨的发明则标志着王阳明心学的精神实质的真正确立。与王阳明本人对“致良知”宗旨的重视相比较而言,后来的研究者无疑忽略了这一点。
收稿日期:2003-11-30
标签:王阳明论文; 王阳明全集论文; 龙场悟道论文; 黄宗羲论文; 心学论文; 钱德洪论文; 明儒学案论文; 儒家论文; 致良知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