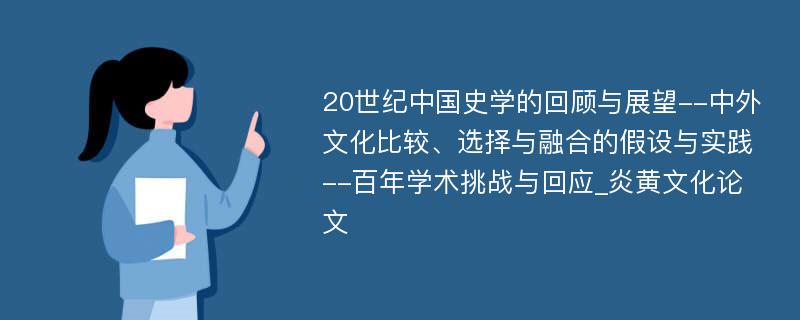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回顾与前瞻——中外文化比较、选择与趋同的假设、实践——挑战与回应的百年学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论文,中外论文,学术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今上溯一百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大清帝国,怎么也无法维系其天朝上国的封闭文化格局。西方文化如决堤的潮水,席卷朝野。“中体西用”说的流行,说明传统的现代转型及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认可。此后,百年来学术界很喜欢用挑战(chal-lenge)和回应(response)这两个词说明中西文化交流的概况。事实上,百年学术也就是以对中西文化,连带对中印文化的比较、选择,及由此而做的趋同假设与实践,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
西方不少社会学家认为,价值观念或规范是创造一个现代化社会、经济与政治体系的先决条件。这实际上就是说,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根本上取决于心理的、文化的以及学术上的超前发展。韦伯索性把现代化称之为理性化的过程。这种理性化的内涵极其丰富,也不全然正确,但无疑包括了对古今各种文化现象进行的理性分析、比较,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传统和异端给予淘沙取金式的扬弃和选择。事实上,自有外来文化传入中国,远溯汉代的佛教,近追明季之西学,学术界早已在比较中选择、吸收,并促进它们与传统的融合了。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便有“格义”之说,近代思想启蒙则有“师夷长技”之论,这些实际上都是在比较中对外来文化的选择。鸦片战争之后,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以此为枕中鸿秘。甲午丧师,更使忧国忧民之士参照西法进行维新。于是,包括政教制度、宗教、哲学等在内的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裹挟在一起奔涌而至。其来势之凶猛,振幅之广大,远非昔日佛教东传可比,几乎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传统的根基因之而动摇,也在陷落,创深痛巨的中国人不能不开始思索中国文化的弱点,由衷地感到传统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于是以夷为师,“尽变西法”,以变应变而图存救亡,汇成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新思潮。另一方面,一些固步自封的道学先生,仍然沉浸在“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圣经贤传以及文化中心自居的心理定势之中,他们对当时“名教奇变”的文化交融,缺乏应有的心理承受能力,总想重振日趋没落的纲常名教而拒斥新思潮的输入。如此,“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张之洞《劝学篇》)。可见,对于奔涌而来的西方文化,初起时或者因其船坚炮利而不加选择地汲取;或因其有损名教而全面拒斥。直到戊戌变法的那一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口号,把“中体西用”的观念系统化为一种学术思想,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理性回应。这一口号,当时之所以“举国以为至言”,一则因其以新旧中西文化要素折衷调和的方式,缓和了矛盾双方的冲突:二则更因其主张认真比较中西新旧之学,不仅要取西艺、西器“以补吾阙”,而且要择西政、西学“以起吾疾”。这种“新旧兼学”、“政艺兼学”的学术指导思想,既肯定了在器物、技艺层面上学习西方的必要性,也指明了在人文制度方面对西方的选择可能性。说简单一点,他主张的是走中西文化会通的道路。中国百年学术大体上是循着这一路向,因革损益而前进的。无论是上个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本世纪初的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新儒家在海外的崛起,包括至今作为全党全国人民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都是在比较中、西、印文化优劣得失的基础上,有所选择,也有所扬弃,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所作的趋同假设,并在政治、学术领域中进行实践的尝试。
百年来,中国几乎有半个多世纪都是在动乱中度过的。但社会的动乱、王朝的更替,使曾经万古不刊、定于一尊的经学也从吓人的高度上跌落下来。特别是在本世纪的头一年,废而复起的科举制被明诏禁罢,这一以四书、五经为核心内容的八股取士之制一旦被废止,自汉以来“独尊儒术”,以经学宰制天下大一统的学术格局也就冰消瓦解了。学者们无论是对新旧中西,还是经子道释,都可以有自己的选择,做各自的比较和阐释。于是,学术界又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
纵观百年学术,不仅有新旧中西的比较和论战,同时还有经学和子学、今文和古文、科学和玄学、文言和白话的比较和争论。另外在佛教文化领域也有新旧唯识之争、典籍真伪之辨,以及发生在30年代前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唯物辨证法论战。包括洋务派在内的维新派,以及国粹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本位文化派、全盘西化派或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派,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新儒家,分别以自己的价值系统对不同文化予以比较和选择。大而言之,百年学术集中表现为对经子、中西、中印文化的反复比较,尤其是从不同角度对中西文化所做的多维比较,而且就如何重建中国文化未来提出了趋同的假设,并予以实践。由于他们所做的趋同假设立足点不同,据此可判析为东方文化中心趋同、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及本位文化趋同三种。
一、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的比较与选择
系统介绍、传播西方文化,并以之付诸政治实践的首推东方文化派代表梁启超。20年代初,又是他传来了欧洲文明危机的信息,明显向传统倾斜,欲重振中国传统于学术界。有人说梁氏对于当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文化方向,有导其先路、确定方位的功绩,足见其会通中西的学术实践功不可没。
对于西方文化的认识,梁启超显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19世纪末,新思潮之输入汹涌奔泻,梁氏对西方各种学说的吸纳,采取的是“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的“梁启超式的输入”。他以进化论为其“善变应天”变易哲学的西方知音,利用可知的一切自然科学成果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科学根据,欲在那“学问饥荒”的环境中,构建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新学问。此时可以说他是立足于传统,面向西方的。20世纪以来,梁启超则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性认识中,大踏步地向传统回归了。
基于面向西方的立场,梁氏原本希望在欧游中“把西洋文明带些回去”,但欧游中的切身体会,又使他修正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念。他首先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差异,进而对中国前此以往效法西方的观念进行了系统的反省。
梁启超认为:“西方文明总不免把理想实际分为两橛”,“科学一个反动,唯物派席卷天下,把高的理想又丢掉了”。而中国文化则固有“心物调和”的传统,在“求理想与实用一致”上下功夫。所以,西方近代文明只是一场“科学万能之梦”。这种“科学万能之梦”,“把一切内部生活、外部生活都归到物质运动的法则之下”,哲学家都投降到达尔文的种源说、冈狄的实证哲学以及新心理学等科学的旗帜之下,终于导致了乐利主义、强权主义的流行。弱肉强食,“仰射机利”,把整个人类卷入了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这位赛先生使“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梁启超《欧游心影录》)。
基于这样的认识,梁氏坚决反对一味效法西方,尤其反对全盘照搬西方文化。在他看来,一是要“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二是借西方文化发展自身的文明,即其所谓的“淬励(砺)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新民说》),如此“化合”成一种新的文明,“一个新的文化系统”(《欧游心影录》)。这一特质“化合”说,正是他关于世界文化趋同的一种假设——东方文化中心趋同。
在向传统折返的同时,梁启超又强调学无“中外新旧之可言”(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它们均可相互辅佐和扩充。由此可见,梁氏对西方文化的态度虽前后有无选择的摄取和批判性吸收的差别,但他那“即中即西”,“学无新旧中外”,“化合中西的新文化”等致力的方向始终是一致的。他对中西文化所做的比较以及文化“化合”的趋同思想对后起的新儒家均有极大的影响。
“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国故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刘师培《自述诗》)这首诗充盈着“用国粹激动种性”的革命意识。以章太炎、刘师培为代表的国粹派显然是要以中国固有的文化唤起民族的自强精神,进而救亡图存,“光复宗国”。但他们同样主张“精研故训,博考事实”,对中、西、印文化从哲学到宗教,从理论到现实,在各个方位上予以比较。他们不仅“究心佛典”,而且“涉猎西籍,以新知附益旧学”(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同样注重“搜集东西前哲各学术参互考核,发扬光大”(刘师培《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尤其是章太炎,其《无神论》一文,全面比较了三大文化的本质。他不仅以佛解庄,于庄子哲学别开一新的天地,而且取康德、柏拉图、叔本华诸西哲之言实证真如,构筑起他那庞大精深的法相唯识哲学体系。另外还有如对进化论的比附和曲意解释,与西人学说和范畴的对照,在其书中俯拾皆是,亦可见梁启超论其“以新知附益旧学”言之不虚。这里所谓的“附益”与梁氏的“化合”同样是一种趋同的假设与实践,不过“附益”较“化合”更突出了趋同中国粹中心的地位。
与梁启超颇为相似的有严复。他先后译出《天演论》等名著数种,数代人都铭记着他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卓著功勋。其后亦如梁氏,欲以传统文化救世。他的译文、著作均有对中、西、印文化的独特比较。起初他认为:西方文化主张平等,“故以公治众而贵自由”,“贵信果”;东方文化“以孝治天下而首尊亲”,“故薄信果”(严复《原强》),传统文化的流弊昭然若揭。以后他审视西方文明,又憎其“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强调孔孟之道“量同天地,泽被寰区”(严复《与熊纯如书》)。文化的优劣得失也就显而易见。所以,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他主张持不问中西,不计新故,“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观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的战略方针。这里的新、故、中、外的“观通”、“计全”,无疑是他的趋同假设。当然这一趋同假设,即使在传播西学的前期,补偏救弊突出的还是“存于人心风俗之间”(严复《原强》)的东方特征,后期尤其强调“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严复遗嘱),“择其善者而存之”(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显然是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的意思。
张君劢上承梁启超科学非万能、物质文明破产的思想,旁采倭铿、柏格森的哲学,就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课题,集中比较了东西学术之异同,为东方文化中心趋同定位并确定了发展方向。
他首先指出:“东西文化之比较,一至难之业”,但“文化之异同,在学术上尤为显著”。他将孔孟以来的学术与近代西方科学相对照,东西文化则判然异途了:“吾国重人生,重道德,重内在之心;西方重自然,重智识,重外在之象。”(张君劢《东西学术之异同》)也就是说,东方学术以人生观为核心,西方文化以科学为基础。而人生是活的,科学所对的物质是死的,因而科学与人生观有客观与主观、论理与直觉、分析与综合、因果和意志、相同和单一五个方面的显著不同,所以,“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由此他进一步指出:西方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好自争斗立论”(同上),“其结果为物质文明”(张君劢《人生观》);中国杨、墨、孔、孟及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好自‘乐天知命’立论”(张君劢《东西学术之异同》),“其结果为精神文明”(张君劢《人生观》)。这一比较的结论显然是从梁启超关于科学、物质,理想、道德、心物、灵肉的比较中导源出来的,甚至有些语言也何其相似。
关于中国文化发展的前景,他同样认为是世界趋同的。他强调中国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当作血清剂,来刺激我们的脑筋,赶到世界文化队伍里”(张君劢《人生观论战之回顾》),而“合东西之长,熔于一炉,乃今后新文化必由之塗辙”。他还指出:“新文化之哲学原理,当不外吾所谓德智主义”,而德智主义就是中国的“道”和“理”,就是在西方变作范畴、论理方法,变作道德、自由意志的“理性主义”(张君劢《思想与社会·序》)。可见这一世界文化趋同的假设本质上是以东方文化为中心的。
至于如何实现这一文化的趋同,他提出了模仿与创造的概念。初起模仿是必要的,如翻译和演讲“当然属于模仿”,以后则要从事独立思想系统之创造,并指出张东荪的“认识多元论”、张申府取英国新唯实派分析法与唯物辩证法之合一,都是“创造”,或者说是趋同的实践。他这里所说的模仿近似于吸收,而创造本质上则是融合。
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终生从事文化哲学和人生哲学的研究,而且特别重视它们在中国的实践,因此致力于儒家伦理与传统文化的复兴。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本世纪中西文化比较的扛鼎之作。
梁氏首先界定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也就是人的意欲选择的生存方式,即生活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他融合了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儒家的伦理精神而抽象出来的文化哲学范畴。基于此形成了他那以意欲为中心的中西印文化比较和趋同的模式。他在哲学、宗教领域,包括形上之部、认识之部、人生问题诸方面,系统比较了中西印文化之异同,指出中国文化“在问题和方法两层,完全同西洋人、印度人两样”。在问题方面,尽管“对于宇宙本体的追究,确乎一致”,但中国人并不讨论呆板、静体的问题而专讲变化。中国的五行绝不能当作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在方法上,中国人注重抽象和虚的意味,“往往拿这抽象玄学的推理应用到属经验知识的具体问题”,所以中国传统不具有西方征服自然、科学方法、民主精神之异彩。而这种差别的形成根本在于意欲的指向不同。他强调:“生活的根本在意欲而文化不过是生活之样法”。所以,文化的不同完全是由于“意欲之所向不同”。据此,他推论出中西印文化发展的路向不同,即西方意欲向前,中国调和持中,印度反身向后。而这三种路向又是文化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它们的差异是时间上的差,而不是空间上的差。西方的现代文明只是现阶段的进步而不是未来文化的楷模。
这一截然划分的阶段论并不排斥其选择、融合外来文化。事实上,他的“意欲中心说”就是吸取西方和印度文化而形成的。在比较中他也特别提到,西方文化“绝不止于物质文明”,“东方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见得就都好,抑实有不及西洋人之点”。所以,他主张“对于西洋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批评的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换句话说,就是以东方文明的根本精神,吸取西方一切精粹的东西,促进中国传统的复兴。
很明显,梁氏的文化哲学及其文化发展阶段论是藉助中西印文化之比较而过渡到中国传统之弘扬的。他说“现代是西洋文化的时代,下去便是中国文化复兴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再下去便是印度文化复兴为世界文化的时代”,实际上就是要在当今复兴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东方文化。他认为西方思想界彰明要求改变人生态度,“趋向之所指就是中国的路,孔子路”(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把他以东方文化为中心的趋同假设表露得清晰无余。而他在河南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以及他的一系列学术活动都是他那趋同理论的实践。当然,把印度文化视为世界文化的最高阶段,是他受佛教哲学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对理想境界的超越追求或终极寄托罢了。现代新儒家化洽中西、平章华梵,以及对生命哲学的探赜索隐,既重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又以内在超越为终极关怀的特征,不能不说与梁漱溟有绝大关系。
不管人们对新儒家的界定如何不同,但不能否认确有一部分学者以复兴孔子之学为已任。他们上承程朱陆王的“圣学血脉”,由“内圣”而开“新外王”的道路。其“新”就新在它既融合佛道,又兼采中西,力图以内圣之学为主干,重建中国文化的未来。所以中西印文化的比较,以及东方文化中心的趋同也就成了他们的显著特点。诸如唐君毅、牟宗三等,从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心理学等处入手,具体比较了中西学术的异同,进一步拓宽了世界文化融合即趋同的道路。
唐君毅在1941年专门辑录其30年代的一系列论文为《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自序中他说:“世界未来之哲学当为中、西、印融合之局面”。这很能反映以复兴儒家为职志的大部分海外学者的文化心态,即在比较、选择的基础上,推进文化的世界性趋同。
唐氏认为:“惟欲以中国为主融摄西洋印度之思想,必须先辨其大方向之异,以辨大异为求更大之大同大通之资。”这一辨异求同的思维方式,引导他们对中、西、印文化做更深层的思索。从宏观上看,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学。具体而言,他不仅比较了宇宙观念,更深入具体地比较了人生观和方法论。唐氏指出:要而论之,中国人之人生态度“由分以体全,其归则不二天人”;西方、印度思想虽也讲“分全合一,天人同轨”,然而他们“先裂而后求合,先有异而求同。吾华则自始不裂,未尝有异”。结果是:西方“重在得,重在立”;印度“重在去,重在破”;中国“重在即去即得,即破即立”。
从方法上讲,唐氏认为西人重知,中国则重行;西方重思辨,中国重直觉;西人重讲习辩论,国人则无讲习辩论之风。
所有这些比较,虽然不能说尽得其要领,但其藉此辨异观同之比较,把握中西文化共同出路的目的还是显而易见的。
当然,包括唐氏在内的所谓新儒家,其趋同的中心无疑是中国儒家的传统。唐氏说:“在世界未来哲学中,中国哲学之精神当为其中心。”(以上引文均见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就是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的意思。至于贺麟,强调“以西洋哲学的挥儒家之理学”“吸收基督之精华,以充实儒家之礼教”,“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贺麟《儒家思想之新开展》),尤其反映了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的倾向。
二、欧洲文化中心趋同的比较与选择
与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相对应的是西方文化中心趋同说,即所谓“全盘西化”论者关于中西文化的比较、融合的学术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佼佼者。
无疑,胡适、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中领袖群伦的人物,他们,尤其是胡适始终被认作是反孔非儒、面向西方、单向选择的“全盘西化”派。其实不然,胡适认为,只是因为传统有太大的惰性,任何民族和领导人都不必担心传统价值的丧失,因此他“拼命走极端”,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方式。他自称为“充分的西化派”。对于传统,他虽然说过中国“百事不如人”的话,但实际上也非一笔抹杀,而且对传统怀有一种深切的眷恋。诚如他在晚年自述的那样:“对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当尊崇的。我对十二世纪‘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的开山宗师的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他还说他“并不要打倒孔家店”,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唐德刚译《胡适口述自传》)。但是,他的确“很不客气的指摘我们的东方文明,很热烈地颂扬西洋的近代文明”(《胡适文存自序》)。所以在评价胡适思想时必须把握这种自相矛盾的内在原因,即复杂的心理活动特点。简单地说,如胡适这一类人的思想,主要出于救时的政治目的而片面强调向西方学习的。他“深信精神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而西洋近代文明的特色便是充分承认这个物质的享受的重要”,所以,尽管他一再强调中西文明不只是物质进步的差异,事实上始终突出的是西方文化“利用厚生”的精神及物质上的便利与享受。所以他所做的中西文化比较,显然带有现实的功利主义色彩。即其所谓的知足、安分与不知足、不安分的差异。也就是说,他关心的首先是人的生存或物质享受的现实利益,“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包括他谓之“衣食足”、“仓廪实”的“利用厚生”精神。所以他主张在器物、技艺方面,至多在物化了的政教制度方面充分吸取西方近代科学的一切成果,因此把系统的、形而上学的术问题具体化为生计的实际问题而使其政治化了。再加上争论中意气相逼,一些偏激的话脱口而出,把原本只是如何引介西方、如何评价传统变成了要不要学习西方,要不要继承传统,因而偏离主题的无对象之争。
全面观察胡适的学术思想,他还是要兼采“中西之长”,“把中西文化的精华融汇贯通起来”,“铸造个崭新的中国文明”(《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注)。用胡适的话概括起来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新思潮的意义》)当然这个新文明决不是穿西服、戴瓜皮小帽的怪物,而是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的基础上,融合东西而产生的一种新文明。其中“重要的一环,便是对我国固有文明作系统的严肃批判和改造”(《胡适口述自传》。很明显,这种再造的文明是以欧洲物质文明为中心的趋同假设,是受其“物质基础”、“利用厚生”的政治观念牵制的学术思想。
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以前,胡适就提出了一种世界文化趋同的模式,即中国、印度和犹太、希腊文化二而一的转化与趋同。他说,初时四大系文化“独立发生”,汉以后中印融合为中国中古文化,犹太加入希腊而成欧洲中古文化。近代儒家复兴,东方支系演变为中国近世文化;欧洲思想也渐脱犹太影响而产生西方近代文化。“这两大支的哲学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五十年后,一百年后,或竟能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
这里他讲的虽然是哲学,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文化。他说“也未可知”,自然是对将来趋同的一种假设。
仍然需要说明的是,就上述模式是看不出他的倾向性的。但由于他在中西文化问题比较上过于侧重物质方面的认同,认为西洋近代文明“建筑在求人生幸福基础之上,确然替人类增进了不少物质上的享受”(同上),因而造成了他的学术思想的局限性,即文化的结构错位,表现出欧洲文化中心趋同的特点。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主张不同文化取长补短,融合而为一种新文化,即第三文明。这一趋同假设与实践,虽然不是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为中心,但选择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俄罗斯的革命文化,所以仍然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趋同。新文化运动中,他们所以能与胡适同在一个营垒,显然与此有关,而且新文化运动确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开荆辟莽的作用。
李大钊首先肯定:“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还把东西文化比作两个面对面挺立的强人,要求青年各以其中之一自命,“竭力划除各族根性之偏执”,“以期尽吾民族对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贡献”。可见,从根本上讲,他也是主张东西融合创新的。
李大钊也是从物质生活入手,尤其是从地理环境的封闭状态来比较东西文化不同的。他由南道文明、北道文明的划分,进而提出“东方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根本异点”。
他首先指出:“欧罗西亚大陆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棹地(Table land),此与东西文明之分派至有关系。”它“亘乎西东,足以障南北之交通,人类祖先之分布移动乃以成二大系统,一为南道文明,一为北道文明”。这里他把文化的生发、特点,直接同地域、交通联系起来是颇有见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当然是南道文明,即东方文化。俄国、德国等欧洲诸国无疑是北道文明,即西方文化。他以受太阳恩惠之多寡,突出东方文化主和解,西方文明主奋斗,同时比较两种文化一系列对应的特点。
他的比较,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也确实把握了两种文化不同的表现形式。总的看来,他的比较仍侧重物质的和制度的,因此他又不无忧虑地指出:“中国文明之疾病已过炎热最高之度,中国民族之命运已臻奄奄垂死之期”,“衰颓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又疲于物质之下”,所以第三文明的产生已刻不容缓。然而解救当时世界危机的出路究竟在哪儿,他也认为是“未决之问题”。或者“二种文明果常在冲突轧轹之中,抑有调和之日,或一种文明竟为其它所征服”,这是不得而知的。但他确认,作为“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的东西文化,“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对于东方文化,我们更要“打破其静的世界观”,“以静的精神享受动的物质制度器械等等”,即“竭力以受西洋文明之特长,以济吾静止文明之穷,而立东西文明调和之基础”。
由上述可见,李大钊认为东西文化取长补短而融合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前景。但东方文化衰颓于静止之中,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扩张之下,只有属于北道文明,也即西方文化的俄罗斯之文明才“足以度此危崖”,“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换句话说,李大钊的趋同假设是以俄罗斯文化(实指俄罗斯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为媒体的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上见李大钊《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
毛泽东在总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比较和选择时,已经把这种趋同假设予以实践了。他说中国人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搬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共和国和政治方案等,但这些东西都相继破产了。“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02-1405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显而易见,他把融汇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中国文化看作中国、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新阶段。
直接参与三四十年代中西文化问题论战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艾思奇在总结民国以来20余年的学术思想时,也曾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他认定“哲学上的各种主要特征也就是文化的一般特征”,指出当时学术界驳乱之表现一是西方哲学的输入,二是传统哲学的复归,也就是中西文化的接触和碰撞。所以他首先还是比较了相互接触的双方的形式和内容。
他认为五四以前,中国哲学相当于欧洲中古的经院哲学,是科学方法建立的时期;五四以后,“部分地颇类似十九世纪后半的欧洲”,是人生问题研究的“世纪末哲学”。他指出:“五四在哲学上表现与欧洲相同点是:两者同是以新的科学方法之建立为基础”,第一次是从经院哲学脱离的培根的归纳法,其次是笛卡儿、霍布士从数学中借来的演绎法,还有斯宾诺莎之于几何学、莱布尼茨之于微积分,都是科学方法的建立。在中国,譬如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得意之人物,并非因其有什么系统的大贡献,而“只是为了实验主义的历史意义和价值”。他还强调,此时虽然“中学”为本,“但‘西学’已取得了‘为用’的地位,足以与中学相抗拮”,所以他说这是“新时代来临”的前兆。
至于五四以后,由于“新思潮辐辏而来,难以有精深的创造,便被逼入另一时期——人生问题研究”。这是因为西方“科学文明遇到‘禁止通行’的挡路牌,社会的物质底发展宣布了资本主义的没落的运命”,东方文化趋同者不敢正视物质的社会,于是“人生问题的研究便代替了宇宙论和方法论的位置”,结果人生问题、心灵问题、道德问题纷然呈现,连蠢头蠢脑的失意政客也厕身于太虚法师佛法讲座的听众之间。他说,自五四至1927年是中国的世纪末,是“封建地主哲学与资本主义哲学之结合”的“退步的哲学”。
接着他又说:此后便是马克思主义和人生问题两大主流“平行”“斗争”发展的时期。“一是叔本华、柏格森、尼采、倭根以至狄尔泰等人的人生问题、道德问题的潮流,一是马克思恩格斯至伊里奇的唯物辩证法的潮流。前者是堕落的资产阶级欲在精神中求慰安的企图,后者是前进的阶层在物质中求胜利的怒潮”。
上述分时段的比照,虽然左右开弓抨击了东西文化,但对东西文化“结合”即趋同的大势还是做了事实上的肯定。当然这种抨击的目的是为了表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体的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上引文见艾思奇《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这一中心趋同论从表现形式上看同样是一种融合的单元文化观。
三、中心趋同说的批判与本位趋同说的建设
上个世纪末,西方的工业革命推动了交通、电讯、图书出版业突飞猛进地发展,整个世界缩小了,时间拉长了,历史凝缩了,文化也就在整合的时空中跨出了封闭的格局,走向了世界。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传播呈现加速度发展的趋势。它们之间不可避免的碰撞,势必触发学术界在比较、选择的基础上创造文化的热情。
以闭关锁国名世,且以文化中心自居的清王朝,自然无法抗拒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现代化潮流。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成果,各种各样的信息,都从打开的闸门奔涌而入。儒家思想稳固不易的统治地位因之而动摇,中华民族共同奉守的伦理原则、道德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均在文化震荡中皲裂。当然,先进的中国人也从打开的大门观察世界,走出封闭。百年学术就是在上述世界性文化整合的背景中变化并发展的。
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学术大规模无拣择地输入,各种思潮纷至沓来;另一方面是历史上各种非儒家的学说,诸如佛学、诸子之学的兴起。前者如胡适所言:“无政府主义者便介绍西洋的无政府主义(Anar-chism);社会主义者则介绍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留学的哲学家则介绍康德、黑格尔、裴斯特等一流的德国思想家。英国留学的则试图介绍陆克、休谟、柏克立(George Berkeley)。更摩登的美国留学生则介绍詹姆士和杜威。”(《胡适口述自传》)当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远不止这些,诸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卢梭的浪漫主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更近一些的还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萨特的存在主义、韦伯的社会学理论等,都曾经冲击过中国的传统,影响过这百年学术思潮。后者则表现为历史文化多层次交叉并存的状态,正象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鲁迅全集》第1卷344页,1981年版)。百年来,既有以今文经学为基础的变法思潮,又有科学新方法建立的乾嘉考据之学;有变异的经学,又有复兴的子学;理学复归,佛学勃起……总之,上述中西交争,新旧并陈的文化格局,迫使学术界必须认真予以比较和选择。于是异说繁兴,诸如“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本位文化”、“尽变西法”、“保存国粹”,以至于“科学民主”、“内圣外王”,不一而足。这些说法虽各不相同,但比较、选择、融合中外文化的运思框架自始至终都是一致的。
然而,导致这一次次中西文化优劣得失之争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原因可以有很多,答案也不可能完全一致。比如,对事物认识的不同,初发动机不同,思维方式与使用工具的不同,都是导致意向分流的障碍。文化的二律背反也是造成臧否不一的事实依据。但文化定位偏向所造成的结构错位,才是这一场场争论的根本原因。张之洞早在百年前评价时人文化研究时说的“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便是定位偏向的具体表现。
首先应当指出,文化既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它属于上层建筑但不等于上层建筑。文化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对于存在(包括物质、精神以及物化了的观念形态,如制度、国家、法庭等)认同的符号。学术研究就是要揭示这一特殊形态的内涵,即其同存在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并予以系统的表述。换个角度讲,不能把文化只看作物力,或者只看作精神活动或政治制度。在学术活动中,把文化定位在任何一个局部,都会造成结构性错位。
从整体上看,百年学术走的是一条中西古今比较参证、融会贯通的道路。作为异端文化的西学,尽管受到传统顽强的抵拒,还是早已取得了“用”的地位,足以与中学相抗衡。继“中体西用”口号之后,德先生、赛先生也开始了它们的风流年华。另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虽然以“打倒孔家店”相号召,但是,“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新儒家的复兴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西学输入的激活,新文化运动“重新评价一切的价值”的推助和反馈。多元并存的文化现象在封闭格局日渐消融的背景中,不断融合,向前发展。
然而,由于对国情的认识不同,关注的内容不同,在对存在认同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定位偏向。
一种是立足于传统“经世致用”的立场,以“救时”为尚。他们把生物进化论引入社会学领域,崇信“弱肉强食”、“落后者挨打”为万古不易的普遍真理,同时又确认西方的科学精神和个人主义是致富致强的根本保证,而这些又是建立在充分发展生产和满足个人物质享受基础上的科学主义;他们相信要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状况,首先要从科学技术学起,“改造物质的环境”(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显然是现实的、功利的,本质上是政治的。所以,他们便把文化定位在物质方面,至多从“民主”这个角度,侧重在物化了的制度方面,由此而造成文化偏离精神理性、道德心性的结构错位。欧洲文化中心趋同就是在这一以物质为终极关怀的文化结构错位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显而易见,这一派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物质生产为“救亡图存”的前提,这也是他们学术思想的核心内容。其长在于促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思想成果之引进,催化传统观念的变异和调适。但这一错位把一切存在都划在了科学的版图之内,把内在的理性活动、道德规范、感情世界、价值观念都归到外在的物质运动的自然法则之下,甚至有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变成简单的社会契约的倾向。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唯科学主义,或者如梁启超早已批评过的“科学万能”的思想。
另一种则对民族危机、国势凌夷自有一番独特的见解。他们以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一致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危机根本上是文化危机,而且这一危机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萌生。其表现不仅仅是传统的僵化,死滞的惰性和禁锢人心、扼杀聪明才智的儒家的大一统地位,更重要的是失去了孔孟的真精神。他们虽不象顽固的守旧派那样视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而予以排斥,但认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并非都是幸福,其“仰射机利,役物自封”,“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严复语)。梁启超曾形象地把给人类“带来许多灾难”的“科学先生”比做沙漠中失路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影子;严复也把“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的西方教化喻为不堪风雨的温室之花,其意均在说明,西方知识扩张的科学主义、个性扩张的浪漫主义,不仅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出路,甚至会把中国拖入不能自拔的地步。所以他们在选择西方文化的同时,又重新向传统折返,要以孔孟的真精神唤起民族的自觉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与西化派不同,保国必先保种,保种必须保教,便是这一学术派系文化救国的逻辑推演。所谓文化救国,就是儒家救国,大而言之便是国粹救国,就是要用孔孟程朱陆王的思想重塑“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这一侧重于心性道德的学术思想,显然是一种偏离物质形态的认同错位。这便是东方文化中心趋同的思维方式。
当然这种思维方式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不过那实在也是文化二律背反的双重价值所导致的义错位。过分强调物质文明的负价值,必然导致文化定位时的偏向。正象欧洲文化中心趋同以物质为前提,以科学为万能一样,东方文化中心趋同以心性为普遍,以道德为全能,各自设想了一种统一的世界文化模式。这两种文化虽都融合东西,兼具心物,但却有主次、中心的不同,都是一种单元文化。
在一场场中西文化的争论中,本位文化趋同的假设与上述鼎足而三,尤其显示出超前的文化意识。
以汤用彤学术思想为代表的本位文化趋同说,集中概括了文化冲突调和的各种理论。他首先指出世界文化“自多元趋一元”(汤用彤《印度哲学之起源》)的趋同方向。这是学术界的共识。但他不采取上述中心说的单元文化观,而是强调:1.每一种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一定的发展方向;2.不同文化接触时影响是双向的;3.文化融合时外来文化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而形成新的文化;4.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国学既非事事可攻,欧美也非文运将终,科学破产,不同文化比较需“精考事实,平情立言”;5.文化乃真理之讨论,是“全种全国人民精神上之所结合”,既不能视科学为全体,也不能以科学纯为实用,对心、物更不能有所取去。
这里,他说明在时空整合的现代社会,不同文化保留自己特点并趋同的必然性。也就是说,在融合的大前提下文化差异存在的可能性。他强调的另一点是学术研究必须对研究对象做深入透彻的了解,对“中外文化之材料广搜精求”。如此比较,才能统计全局,不致偏置,才能得其大体,不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最后一点恰恰说明认同定位的重要性。
学术研究在于把握普遍和永恒,既非物质、精神、科学、道德的本身,更不是它们的一部。全面认同,才能有正确的定位。所谓“在言者固以一已之主张而有取去,在听者依一面之辞而不免盲从”,正是批评文化错位所造成的“固陋”(以上引文见汤用彤《评近人之文化研究》)。
作为学衡派的中坚人物汤用彤,真正以“昌明国故,融会新知,不偏不党,不激不随”为其治学的准则。他以深厚的中西学功力,藉助汉唐佛教、魏晋玄学以及印度哲学往史的系统研究,采用中西合璧的方法,引入了文化移值、涵化等概念,推论中西文化接触、融合的前景——趋同的必然性。如是以古证今,中西兼治,平情立言,在中西文化争论中以并览今古、兼采中西、因革损益、创造性转化的文化系统工程独树一帜,充分表现了他那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和本位趋同的前瞻性。
他强调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但“未必尽同”。印度佛教转化为中国佛教,使传统文化的面目为之一新的历史事实,说明文化虽有承续性,但又具有发展性,所以古今未必尽同。同时他还指出,文化涵化过程,影响虽然是双方的,但外来文化必须对本有文化趋同,“加入本有文化血脉中”。趋同后的文化,也未必尽同。古今未必尽同,中外未必尽同,便是本位趋同与中心趋同说的区别。
当然,仅从中国文化这个角度来看,本位趋同与东方文化中心趋同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他们都说的是在不改变中国文化特质的前提下文化的世界化。但从异国、异族文化的立场来看,他们的差别则是显而易见的。本位趋同设想的是以他们那个文化为本位的趋同,后者描绘的仍然是以我们这个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世界单元文化的蓝图。他们希望的是用中国文化吸收、融会西方文化之精,即所谓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非“西化”而谓之“化西”。用贺麟的话说便是:“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之哲学,与中国孔孟程朱陆王之哲学会合贯通。”追求一种“言孔孟所未言,而默契孔孟所欲言之意;行孔孟之所未行,而吻合孔孟必为之事”(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世界后现代文化。换句话说,本位趋同,未必尽同,同中有异,小异大同;中心趋同则一而化之,似乎染有文化沙文主义的色彩。
不过应当说明,各种趋同说所坚持的大方向是一致的,事实上也都认为文化的这种演变即使在封闭格局解体之后仍然是渐进的。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甚至在意向上有时也难以截然区分。比如梁启超“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文化,本身很难说明其趋同的性质。特别是东方文化中心趋同说在阐明中国文化发展前景问题上与本位趋同的相合之处,更容易引起同类的错觉。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中外文化论文; 胡适口述自传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华夏文明论文; 胡适论文; 物质文化论文; 梁启超论文; 世界文化论文; 张君劢论文; 科学论文; 西洋论文; 东方文化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