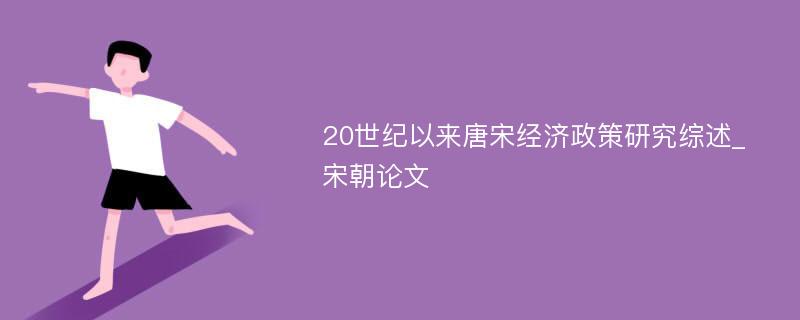
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政策论文,唐宋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唐宋之际,大致是指从中唐(公元8世纪中叶)开始,中经五代十国,延至北宋(公元11世纪)的这段时期,前后大约300余年的时段。从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唐宋之际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化之巨如不亚于、也是仅次于春秋战国之际,此点几成学界共识。早在1910年,日本京都学派的领军人物内藤湖南发表长文《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历史与地理》9-5,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册,中华书局,1992年),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的结束,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揭开了唐宋变革期讨论的序幕。此后宫崎市定着重从社会经济变迁方面,丰富了内藤湖南的学说,其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从部曲到佃户》(同上书,第五册)这篇长文中。自1945年二战结束后,京都学派的上述观点受到东京学派的持续反驳,他们认为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终结,是中世社会的开始。这两大学派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互相诘难,将唐宋变革期这个学术论题突现在学界面前。1954年,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在《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三联书店,2000年,第332页)一文中即已指出:“综括言之,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的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特别是近20年来,关于唐宋变革期的讨论日见激烈,吸引了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经济史等众多学者的参与。
汉唐是同质社会,都以自然经济立国;宋明亦是同质社会,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工商业特别是城市经济和海外贸易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加之自晚唐以降,契约租佃经济取代中古田制经济;经济重心从黄河流域加速向长江流域、特别是向东南沿海地区转移,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长期运行在大陆帝国轨道上的汉唐王朝至宋代开始,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向海洋发展的趋势。工商业文明因子的生长和向海洋发展路向的出现,相对于农业文明来说,都是与自然经济对立的异质因素。正是这些异质因素在农业社会中的成长,使得宋明社会与汉唐社会区别开来,诸如汉唐以门阀世族为主体的贵族政体,至宋演变为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官僚政体;汉唐时期以奴婢、部曲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向平民阶层转化;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的地著体制向迁徙自由的流动体制转变等,均是其时代变化之最著者。笔者曾就《唐宋之际农民阶级内部构成的变动》(《历史研究》1982年1期)、《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等作过一些初步研究。笔者近年申请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唐宋之际经济结构变迁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互动关系研究》(02AJL008),拟从经济和体制层面,探讨唐宋变革的深层原因。本文拟对20世纪以来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状况作一回顾,下面按土地政策、赋役政策、工商业政策、专卖政策和外贸政策依次展开。
一、土地政策研究
唐宋之际土地政策的演变,包含均田制的瓦解、不抑兼并政策的出台、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推行以及土地买卖合法化等环节。
先看均田制的瓦解。一般认为均田制弛坏于中唐开元、天宝间,随着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两税法的出台而正式消亡。陈登原《中国土地制度史》(商务印书馆,1932年)认为,唐均田制中放宽土地买卖限制的政策所促成的豪强兼并和户籍不整,是均田制颓废的关键。陶希圣、鞠清远在《唐代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中则认为国有土地减少、耕地不能增加和不守田令是主导因素。1943年,李剑农完成《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指出“私人田庄的自始存在”、“口分田亦可买卖”为导致均田废弛之“两端”。此后,论及均田制瓦解原因的还有:乌廷玉《关于唐代均田制度的几个问题》(《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1期)、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5期)、唐长孺《均田制的产生与破坏》(《历史研究》1956年6期)、金宝祥《北朝隋唐均田制研究》(《甘肃师大学报》1978年1期)、郭庠林《试论“均田之制”的缘起及其弛坏的根本原因》(《复旦学报》1981年3期)、赵俪生《均田制的破坏》(《天津社会科学》1985年5期)、杨际平《均田制新探》(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武建国《均田制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唐任伍《论唐代的均田思想及均田制的瓦解》(《史学月刊》1995年2期),以及日本学者池田温《中国古代买田买园契的一考察》(《西嵨定生博士还历纪念——东亚史上的国家和农民》,山川出版社,1984年)、山根清志《唐均田制下的民田买卖》(《中国都市和农村》,汲古书院,1993年)等等。上述诸家大都认为土地兼并导致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壮大,土地不敷授田所需,以及战争冲击带来户籍的紊乱是均田制瓦解的主要原因。葛金芳《论五朝均田制与土地私有化的潮流》(《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2期)一文,试图从五朝均田制三百余年的演进趋势中去挖掘其瓦解的内在机制,指出均田制的长期维持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对于人口的严密控制(“农皆地著”),二是地权流转速度的相对迟缓(“摧制兼并”),然而时至中唐,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加之安史乱后版籍漫患,丁口流离,两个条件均不复存在,均田制遂告终结。
再看不抑兼并政策的确立。自中唐均田制瓦解后,历史进入“不立田制”的时代,其标志就是“不抑兼并”成为其后各朝的“国策”。张荫麟《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社会经济史集刊》6:1,1939年)较早切入土地买卖问题的研究。此后有杨志玖《北宋的土地兼并问题》(《历史教学》1953年2期,收入《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李景林《对北宋土地兼并情况的初步探索》(《历史教学》1956年4期)、杨仪《北宋土地占有形态及其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58年3期)等文发表。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指出,宋代“土地买卖盛行的事实表明,土地私有性质确实已经有了增强”,与此同时官田的民田化也日益普遍。但李春圃《宋代佃农的抗租斗争》(《社会科学论丛》1980年2期)则将不抑兼并定性为反动政策。稍后,杨树森、穆洪益主编的《辽宋夏金元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认为不抑兼并政策使得尖锐的阶级矛盾自始至终贯穿于两宋,评价亦很低。
80年代中叶前后,上述观点受到了学界质疑。葛金芳《试论“不抑兼并”》(《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2期)指出,中唐以来不抑兼并政策的出现及其定型化,标志着地主土地所有制优势合法地位的确立,包含着合理的现实因素。不抑兼并政策在土地、赋税、阶级关系等方面引发的新变化,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进入后期的历史阶段。他的《对宋代超经济强制变动趋势的经济考察》(《江汉论坛》1983年1期)将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动和农业生产的经营方式联系起来考察,指出:晚唐以降直至两宋,土地转移率的急剧提高,促使累世相承的主仆名分趋向瓦解;经济性大土地所有制的成长,导致统治权和土地所有权逐步分离;地块分散的土地占有情况导致了部曲制经营方式的日趋衰落。在《唐宋之际土地所有制关系中的国家干预问题》(《中国史研究》1985年4期)中,葛金芳揭示了唐宋之际土地政策演进的五大趋势,一是对土地所有制结构放弃调整,此以田制模式的放弃为标志;二是大量下放官田给民间(包括地主和系官佃农),此以官田私田化政策为标志;三是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干预明显减弱,此以“不抑兼并”为标志;四是对小农土地所有权更加维护尊重,如“逃田”、“户绝田”所有权的保留和处置;五是畅通地权转移的渠道,此以土地买卖合法化为标志。唐兆梅《析北宋的“不抑兼并”》(《中国史研究》1988年1期)与葛金芳持相同观点。另有马兴东《宋代“不立田制”问题试析》(《史学月刊》1990年6期)、姜锡东《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等文发表。
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研究近年来亦有佳作。张星久《关于五代土地兼并问题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2期)对五代土地兼并发展的一般情况、地主兼并土地的手段及方式,以及对地主阶级内部地权运动的影响三个问题进行了分析。武建国《论五代十国的封建土地国有制》、《五代十国大土地所有制发展的途径和特点》(分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1期;《学术月刊》1996年2期)两文指出,当时各类国有土地已大量私有化。此外,赵云旗《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土地买卖的管理机制》、《论唐代土地买卖政策的发展变化》(分见《敦煌研究》1998年3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庆祝韩国磐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年)等文和霍俊江《中唐土地制度演变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云旗《唐代土地买卖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等专著,对唐后期土地买卖的合法化过程有详尽的描述。
最后来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施行。葛金芳在《北宋官田私田化政策的若干问题》(《历史研究》1982年3期)中指出,该政策的执行分为“无偿转化”和“有偿转化”两种形式,其动因在于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该政策有利于小农地权的深化,但后来变成地主攫取官田的门径,因而具有两重性。赵俪生《试论两宋土地经济中的几个主流现象》(《文史哲》1983年4期)将之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富者有资可以买田”,“广置营田”与“尽鬻官田”并存,以及田主对佃户看法的改变。杨康荪《宋代官田包佃述论》(《历史研究》1985年5期)认为,宋代官田实行自由射佃制,既保证了官府经济收入的稳定性,也满足了包佃户追求财货的欲望。宋代包佃主的承佃活动,扩大了当时的垦田面积,同时也促进了游散劳动力与土地资料的结合,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对此,葛金芳连发四文提出不同看法。在《宋代官田包佃成因简析》(《中州学刊》1988年3期)中,认为宋代私人包佃官田制度日趋普遍的基本动因,是土地私有化潮流的持续推动;契约租佃经济占据主导地位是包佃形态得以发展的历史环境,荒田旷土的大量存在则是官田包佃得以繁衍滋生的外部条件。通过《宋代官田包佃特征辨析》(《史学月刊》1988年5期)得出其本质是“品官权贵、形势豪右之家,为转佃取利、谋取差额地租而承佃大段系官田产的行为”。在《宋代官田包佃性质探微》(《学术月刊》1988年9期)中,认为应将形势豪右对于系官田土经营权的封建垄断,规定为包佃形态的本质特征。《宋代官田包佃作用评议》(《江汉论坛》1989年7期)认为,官田包佃之弊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影响官府课入、阻滞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和妨碍土地与劳力结合。
二、赋役政策研究
先看赋税。中唐均田制瓦解后,人丁税性质的租庸调已成无源之水,资产税性质的两税法应运而生。陈登原《中国田赋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指出,浮寄客户的大量增加致使租庸调不得不变而为两税,宇文融括户的办法只能治标,不能行于时。〔日〕日野开三郎《杨炎两税法的实施与土户客户》(《泷川政次郎博士还历纪念论文集》,东京,1957年)亦持此论。袁英光、李晓路《唐代财政重心的南移与两税法的产生》(《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3期)认为,安史乱后南方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发达;交换中钱币的大量使用,又为“按赀纳税”和“以钱为税”准备了条件。陈明光《论唐朝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体制》(《中国史研究》1989年1期)认为,两税改变了前期的单一农业税收结构,采取以两税为代表的农业税与以榷盐为代表的商品税并重的二元结构。吴丽娱《也谈两税的“量出为入”与“定额给资”》(《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1年)认为杨炎两税法是以国家财政需要和支出作为主导和前提。翁俊雄《唐后期民户大迁徙与两税法》(《历史研究》1999年3期)综合诸家之说,指出安史乱后的民户大迁徙减少了国家编户,增多了浮寄客户,土地所有权转移的频率随之加快,以工商为业者明显增加,因而导致了以“税客户”、“税资产”为改革方向的两税法的产生。
在两税的征收内容上,学者们众说纷纭。〔日〕玉井是博《唐代土地问题管见》(《史学杂志》33-8、9、10,1922年)强调两税法是由唐前期资产税性质的地税和产税发展而来。持同样看法的我国学者有鞠清远《唐代两税法》(《北大社会科学季刊》6:3,1936年)、李剑农(前引书)、张维华《对于两税法的考释》(《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4期)、王仲荦《唐代两税法研究》(《历史研究》1963年6期)等。日本有铃木俊《唐代产税与青苗钱的关系》(《池内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座右宝,1940年)、《唐朝的夏税、秋税》(《加藤繁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集说》,富山房,1941年),韩国有金永济《唐宋时代的两税沿革》(《东洋史学研究》34,1990年)等。另一种观点认为两税仍指租庸调。岑仲勉《唐代两税法基础及其牵连的问题》(《历史研究》1951年5、6期)和〔日〕曾我部静雄《两税法与地税、户税无关论》(《东洋学》1959年2期)、《两税法出现的由来》(《社会经济史学》26-1,1960年)即主此说,但应者寥寥。第三种观点认为两税单指户税,不包括地税。代表性成果有〔日〕小林高四郎《唐代两税法论考——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幕》(《社会经济史学》3-6,1933年)、陈登原《中国田赋史》、金宝祥《唐代封建经济的发展及其矛盾》(《历史教学》1954年6期)和《论唐代的两税法》(《甘肃师大学报》1962年3期)等。而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书店,1961年)、张泽咸《论田亩税在唐五代两税法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和沈世培《两税向田亩税的转变及其原因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1期)等持地亩税说。第四种认为两税是由多个税种合并而成。〔日〕吉田虎雄《关于唐两税法》(《东亚经济研究》24-2,1940年)、胡如雷《唐代两税法研究》(《河北天津师院学报》1958年3期)、〔日〕船越泰次《唐代两税法中的斛斗征课和两税钱折籴问题》(《东洋史研究》31-4,1972年)、丁柏传《谈对唐代两税法的再评价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83年2期)为其代表。李锦绣(《唐代财政史》下卷第二分册,北大出版社,2001年)参酌众说,认为“两税得名于夏秋两征”,“两税包括两税钱物和两税斛斗两部分,田亩税是两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说较为公允。
宋代两税,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认为是指“钱”与“谷粟”,并以田亩为征收标准,故有“夏钱秋米”之说,实指“夏税秋苗”。王曾瑜《宋朝的两税》(《文史》总14辑,1982年)仍认为夏秋两征,夏税以征收丝帛、大小麦钱为主,秋税则以粮食为主。各地税额不一;和籴、和买加重了乡村民户的负担;多数地区还残存着一定数量的人头税和各种附加税。漆侠《宋代经济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也认为宋代两税是向“有常产”的“税户”征收的土地税,基本上承袭了后周之制。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根据相关文献对两税征收程序及相关规定作出解说,包括“均田”与“检田”、“两料”与“三限”、“支移”与“破分”、“倚阁”与“带纳”、“揽纳”与“包税”、“预借”和“增借”等。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指出,宋代两税实行夏钱秋米制度的同时,还有不少增税办法。此外,汪圣铎《北宋两税税钱的折科》(《许昌师专学报》1989年2期)认为当时社会还不具备赋税货币化的条件。张熙惟《宋代折变制探析》(《中国史研究》1992年1期)则认为折变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再看徭役。对两税法颁行之后晚唐五代的徭役问题,学界长期注意不够。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专列“两税法时期的杂徭”一节予以深究,指出“杂徭在实施两税法时,曾宣布省并”,但杂役却被改头换面地一直沿袭下来,此后与力役渐趋合流,整个唐代的劳役征发是始终严重存在的。唐长孺《唐代色役管见》(见《山居存稿》,中华书局,1989年)指出,两税法施行后,色役与差科往往并称,亦可谓之杂徭。陈明光《试论唐后期的两税法改革与“随户杂徭”》(《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唐后期的“随户杂徭”,是未被两税法改革方案包括在内的地方性徭役,而不是再生形态。张泽咸《略论六朝唐宋时期的夫役》(《中国史研究》1994年4期)指出,唐宋夫役就其主流而言是丁男承担的力役。
宋代,兵役已成残余,力役渐轻,职役突出起来。何兹全《北宋之差役与雇役》(上、下,《北平华北日报·史学周刊》11、12,1934年)较早探究了北宋时期的役法。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将宋代“职役”分为四类:①衙前;②里正、户长和乡书手;③耆长、弓手和壮丁;④承符、人力、手力和散从,认为北宋前期的役法经历了由差役至雇役的转变。聂崇歧《宋役法考述》(《燕京学报》33,1947年;收入《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对各类职役作出详细考述。此后有朱瑞熙《宋代的科配不是“差役”》(《光明日报》1963年10月23日)、《关于北宋乡村下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4年9期)、《关于北宋乡村上户的差役和免役钱问题》(《史学月刊》1965年7期)和王曾瑜《宋朝的差役和形势户》(《历史学》1979年1期)等文。关于差役的性质,汪槐龄《有关宋代差役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认为差役是乡亭之职向劳役与苛税演变过渡阶段的产物。李志学《北宋差役制度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3年3期)认为,差役的担当在仁宗之际发生了由上户向下户转移的情况,但其性质仍是职役。漆侠《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认为,宋代的差役是前代劳役制的继续,主要由下户负担。王棣《北宋差役的变化和改革》、《试论北宋差役的性质》(分见《华南师大学报》1984年2期、1985年3期)两文认为,北宋的差役可分为州县役和乡役两种,差役的本质就是让私有土地产权所有者无偿提供公共服务。葛金芳(前引书)则认为差役按其性质可分三类:一是州县吏人与乡村政权头目,此其主体;二是各级官衙里的杂差公人,属力役性质;三是乡村壮丁、城镇所由和直属县尉的弓手之类治安人员,属兵役残余,不能一概而论。
关于夫役,梁太济《两宋的夫役征发》(《宋史研究集刊》,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认为出现了从差夫制到雇夫制的变化。葛金芳(前引书)认为,两宋力役从总体上看呈减轻趋势,可用“一代(厢军代役)二雇(和雇夫役)三转化”来概括。所谓转化,是指各类徭役向代役税转化,这是摊丁入亩在宋代的主要表现。葛金芳《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论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3期)指出,摊丁入亩的实质就是封建国家加在民户身上的徭役和人头税逐步向田亩税转化和归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在宋代有两大表现,一是部分力役转化为代役税,二是尚未转化的部分开始依据民户资产摊派。在《两宋摊丁入亩趋势补证》(《暨南学报》1991年3期)中,葛金芳指出,在两宋水利役中依据田亩广狭来征调夫役的办法日趋普遍,且有私约文簿为之约束,此后逐步演变为地方性水利法规,有些地方“计田出丁”渐向“履亩纳税”转化。这是从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的角度,对宋代摊丁入亩趋势日趋扩大的内在机制做出的说明。
三、工商业政策研究
先看手工业。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新生命书局,1934年)、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和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是三部对唐宋手工业作扎实细致研究的专著,多以官府手工业的经营管理为探讨重点。魏明孔《唐代官府手工业的类型及其管理体制的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2期)认为唐代官府手工业工匠职责明确;实行工匠征集制度;对工匠实行培训制度;在大型工程中实行工头技术负责制。刘玉峰《唐代矿业政策初探》、《试论唐代官府手工业的发展形态》(分见《齐鲁学刊》2001年2期、《首都师大学报》2001年5期)指出唐朝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矿业的政策,官府手工业具有很强的政治干预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民间手工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摧残。
有关宋代手工业的研究,漆侠《宋代经济史(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指出,从宋初到神宗时期,矿冶业从劳役制向召募制演变,与此相适应,二八抽分制代替了课役制。稍后王菱菱《宋代矿冶经营方式的变革和演进》(《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论宋朝边疆地区的矿冶禁采政策》、《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宋朝政府的矿业及开采政策》(分见《河北大学学报》1993年3期、1996年3期、1998年3期)和《宋政府的矿产品收买措施及其效果》(《中国史研究》2000年2期)等文有具体论述。葛金芳(前引书)将宋代官府手工业的管理体制概括为“国有、官监、民营、专卖”八个字,并指出其间存在着逐步下放经营权的趋势,而民营手工业占据主导地位。李晓《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认为宋室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纺织业等比较重视,对矿冶业既鼓励又控制,对军工、铸钱等业实行官营垄断,对盐、茶、酒等实行禁榷专卖,对陶瓷、漆器、建筑、造船、印刷、粮食加工等业允许民间自由经营。就纺织业而言,魏天安《宋代布帛生产概观》和贾大泉《宋代四川的纺织业》(两文俱见《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两文值得注意。前者对宋朝获取布帛的科配及和买等政策有所论述,后者着重介绍了宋王朝对丝织品从市买至无偿征收的搜刮政策。姜锡东《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5期)认为从宋初直至哲宗时期,和预买绢对丝织业极为有利。
再看商业。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世界书局,1932年)认为唐中叶以后特别是德宗时期推行抑商政策,商事进行艰难。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也留意到商业、关禁等内容。葛金芳(前引书)指出,宋代商业立法弊端不少,但以“通商惠工”为主旨,目的是攫取商税。戴顺祥、邵兰认为《唐宋时期政府商业政策的变化》(《思想战线》2000年1期)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由重视专卖榷利转向注重征商,商税制度化和规范化,实施扶商政策。李晓(前引书)认为宋代在市场设置、商品价格和商人队伍等方面实行了开放政策,在打击垄断、维护合同和商业经营、统一度量衡和打击假冒伪劣等方面实行维护市场秩序的政策,并加强了对行会、商人和牙人的监控。
在商品流通政策方面,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5本第1分,1935年)认为牛仙客首建和籴,是有唐一代政治隆替之关键。〔日〕铃木正《唐代的和籴》(《历史学研究》10-5、6,1940年)则认为和籴的目的是供军粮。在和籴渊源的论辩中,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主张和籴盛行是唐代财政政策呈“河西地方化”之表现。岑仲勉《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反对“河西地方化”之说。徐寿坤《对唐代“和籴”的分析》(《史学月刊》1957年2期)持岑氏之论,指出和籴在前期是不带强制性的交易关系,安史之乱后才由和买变为强征。卢开万《唐代和籴制度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6期)则糅和陈氏、岑氏之说,认为和籴在西北、关内、中原都曾实行,前期已具有强制性,安史之乱后,和籴性质进一步蜕变。杨际平《试论唐代后期的和籴制度》(《唐史学会论文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强调,和籴军粮有益于抑制藩镇,有积极作用。赵文润《唐代和籴制度的性质及作用》(《唐史论丛》第5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认为,和籴解决了边地军粮供应,在唐中期起积极作用,后期流弊是法制松弛、吏治败坏造成的。
宋代和籴仍是筹粮养兵的重要手段。戴裔煊《北宋便籴制度产生的时代背景》(《现代史学》4-4,1942年)和若璋《宋代的籴政》(《东南日报》1948年1月24日)率先论及宋代的籴政。王曾瑜《宋朝的和籴粮草》(《文史》总24辑,1984年)指出,北宋中叶以前常取“博籴”、“便籴”方式,神宗以后又有“结籴”、“寄籴”、“表籴”和“兑籴”等名目。魏娅娅《宋代和籴利弊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年3期)认为熙宁以后“和籴”演变为科配,成为赋役,但仍不失为国防供应的应急措施。魏天安《宋代粮食流通政策探析》(《中国农史》1985年4期)认为宋代置场和籴,是政府利用民间商业流通组织来补充粮食消费的不足。葛金芳(前引书)认为宋代两税相当于农业税中的“公粮”部分,而和籴则类似于统购统销制下的“购粮”性质。袁一堂《宋代市籴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3期)认为,市籴体现了“国防财政”的特点;他另有《北宋的市籴与民间货币流通》(《历史研究》1994年5期)认为北宋的市籴本身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却更近似于赋税。
在市场管理和行会方面。〔日〕加藤繁《宋代都市的发展》和《唐宋时代的市》(俱见《中国经济史考证》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率先指出唐末坊市制已渐趋松弛,至宋代最终走向崩溃。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阐述了坊市制至北宋中叶毁坏的过程。唐宋行会研究的奠基者,中国有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4年),日本有加藤繁。戴静华《两宋的行》(《学术研究》1963年9期)亦有开拓之功。傅筑夫《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指出宋代的行不能等同于西方的行会。杨德泉《唐宋行会制度研究》(《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则认为唐宋行会在商品质量、训练学徒制度等方面与欧洲一样受行规约束,所以宋代行会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但其性质基本相同。〔日〕日野开三郎《唐宋时代商人组合“行”的再探讨》(《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第7卷,三一书房,1983年)着重分析宋代“行”的市场独立性及内部阶层分化。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和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对“行”亦有涉及。魏天安《宋代行会制度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指出行会是封建性的同业商人组织,并从行商与坐贾势力消长的角度,得出行会形成于宋代的结论。行会具有一定的限制竞争、垄断市场的作用,同时承担政府的“科买”和“行役”。
对商税含义的理解,学界向有不同说法。陶希圣、鞠清远《唐代经济史》指出唐“除陌法”近于交易税。鞠清远《唐代财政史》(商务印书馆,1940年)认为,安吏之乱后的“关津之税”,即是过税。日野开三郎《唐代商税考》(《社会经济史学》30-6,1965年)、〔日〕小西高弘《唐代的客商和杂税——以商税的成立为中心》(《经济学论丛·福冈大学》24-2、3,1979年)亦持鞠说。张邻、周殿杰《唐代商税辨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狭义商税仅指关税利市税,两税法对行商所征之税不是商税,而是资产税。陈明光《唐五代“关市之征”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4期)将商税分为三类,即禁榷(专卖)、关津之税(商品通过税)和市肆之税(商品交易税),后两者亦即“关市之征”。对于宋代商税,加藤繁《宋代商税考》(《史林》19-4,1934年)认为过税、入市税出现于唐中叶,宋代确立了过税和住税制度,税率在2%-3%之间。马润潮《宋代的商业城市》(马德程译,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和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亦同此说。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过税、住税之外,还有翻税和买出翻税,“力胜钱”、“市例钱”等则属杂征横敛。李晓(前引书)指出,在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以前,2%的过税和3%的住税是按商品的实际市场价格征收的,但过税每过一次税务都要征收一次,实际可达10%以上。
四、禁榷专卖政策
先看榷盐。对唐盐专卖施行的原因,鲍晓娜《从唐代盐法的沿革论禁榷制度的发展规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2期)认为禁榷首要目的不是增加收入,而为抑商。齐涛《论唐代榷盐制度》(《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4期)则认为传统赋税政策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也应加以考虑。陈衍德、杨权认为《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必然结果,而安史之乱后农业税不敷政府支出,要求扩大税源,才是最为直接的原因。关于榷盐机构及其作用,〔日〕妹尾达彦《唐代后半期江淮盐税机关的立地和机能》(《史学杂志》91-2,1982年)认为,专卖机构发挥了联结盐户和盐商的作用。在《唐代河东池盐的生产和流通》(《史林》65-6,1982年)中,妹尾氏又指出,河东盐区直接将盐委托给盐商销售,确保了专卖收益。陈衍德《唐代专卖机构论略》(《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89年)指出,唐代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院、监、场三级管理机构,三者职能各有侧重又有重叠。
五代盐政,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认为,五代盐法是对唐盐法的沿袭,自后唐又新增表卖蚕盐制,实为变相人丁税。郑学檬《五代盐法钩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1期)指出五代盐税有蚕盐、屋税盐、随丝盐钱等,具有资产税的附加税性质。郭正忠《五代蚕盐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4期)认为蚕盐法制定于梁唐之交,是政府插手丝蚕业的结果,以榷卖为特色。吴丽娱《五代的屋税盐》(《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1993年)认为屋税盐源于朱梁之末,是蚕盐的补充形式而行于农村。
宋代榷盐的研究较为深入。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1957年)认为宋初大部分地方实行官般官卖制,之后才逐渐发展为官府间接专卖的引钞盐制。张秀平《宋代榷盐制度述论》(《西北大学学报》1983年1期)认为,宋代榷盐制度的主要内容是生产上的垄断与统购政策及销售上的抑配与科买。漆侠《宋代经济史(下)》和汪圣铎《两宋财政史》(中华书局,1995年)都认为买扑法和钞引盐制都属于通商法。郭正忠《宋代盐业经济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和《中国盐业史》(人民出版社,1997年)两书指出,宋代盐的榷卖形式有官府批发或零售、蚕盐和食盐赊购、强制认购、纳盐钱等。商民分销形式又分钞引盐、扑买盐、买卖盐场、合同盐场等,以具有间接专卖性质的钞引盐最为普遍。
再看榷茶。鞠清远《唐代财政史》认为税茶是榷茶的前身,茶税确立于贞元九年(793年)。此后,始税茶之年,争论不休,张泽咸《汉唐时期的茶叶》(《文史》总11辑,1981年)认为唐人对榷与税的使用并不严格,故易混淆。陈衍德《唐代茶法略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2期)认为,“唐代茶法的形成和演变经历了‘课税——全部专卖——局部专卖’这样一个过程”。关于五代茶法,凌大埏《中国茶税简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6年)认为五代一些政权对内实行茶专卖,而外则行通商之策。商岘《一千年茶法与茶政(下)》(《平准学刊》第三辑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认为南方政权茶法政策不一,南唐兼行官收商销和官收官销,楚征税商销,后蜀行茶专卖。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详细论述了宋初到嘉祐四年(1059年)之间交引法、三税法、贴现法的兴废交替,并将茶法区分为禁榷法与通商法两类。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将宋茶法沿革分为三个阶段,即北宋前期禁榷和茶法入中时期、嘉祐通商时期、崇宁年间恢复禁榷行合同场法及南宋的茶引时期。李晓分析了《北宋榷茶制度下官府与商人的关系》(《历史研究》1997年3期)。孙洪升《宋代交引茶制中政府贸易费用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3期)认为交引制切断了茶园户与商人的直接联系,旨在形成官府垄断价格。黄纯艳《宋代茶法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指出,宋代各地茶法虽有不同,但都经历了由通商向政府垄断收购的转变。
最后来看榷酒。鞠清远《唐代财政史》、〔日〕金井之忠《唐代的榷酤》(《文化》7:6,1940年)、〔日〕丸龟金作《唐代的酒专卖》(《东洋学报》40:3,1957年)和〔日〕西冈弘晃《唐代的酒专卖制度》(《中村学园研究纪要》3,1970年)等,研究了唐后期榷酒的性质及变化等内容。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和《唐代工商业》指出,榷酒始于建中三年(782年),有榷曲、征榷酒钱等多种形式。陈衍德《唐代的酒类专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1期)认为,广德二年(764年)即已开始酒专卖,有特许专卖制、全部专卖制、榷酒钱、榷四种形式。董希文《唐代酒业政策探析》(《齐鲁学刊》1998年4期)讨论了唐朝的禁酒、税酒户、榷酒、官酤、纳榷、榷曲等多变的榷酒制度。漆侠《宋代经济史》(下)认为宋代榷酒始于乾德二年(964年),酒制则有许民般酤、官榷和买扑制三种形式。包伟民《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史研究集刊》,浙江省社联《探索》增刊,1988年)认为,宋朝酒法以官酿官卖的官酒务制和民酿民卖的买扑坊场为主体。杨师群《宋代榷酒中的买扑经营》(《学术月刊》1988年11期)、《两宋榷酒结构模式之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3期)等文认为宋代榷酤起步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榷酒机构由都曲院、都酒务、酒务、坊场等构成。酒业买扑初有定额,后实行“实封投状”。李华瑞从1988年开始发表一系列论文,后汇成专著《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河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他指出宋代榷酒的形式通行全国的有三种:官监酒务(属完全专卖,占统治地位)、买扑坊场和特许酒户经营;局部地区亦有三种,即京师榷曲、四川隔槽法和两浙、两湖等地的万户酒。
五、海外贸易政策研究
〔日〕石桥五郎《唐宋时代的中国沿海贸易及贸易港(1、2、3)》(《史学杂志》12-8、9、11,1901年)最早进入这一领域。〔日〕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是由关于海路贸易、贸易港和市舶管理机构的四篇论文汇集而成。孙葆《唐宋元海上商业政策》(台湾正中书局,1970年)和陈高华、吴泰著《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对当时海外贸易的诸层面展开了较为细致的分析。王冠倬《唐代市舶司建地初探》(《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认为唐玄宗开元初在广州设有“押蕃舶使”,唐末则先后在扬州、泉州、明州设立市舶司。林萌《关于唐、五代市舶机构问题的探讨》(《海交史研究》1982年4期)指出,唐代在交州也设市舶使,但各地名称不一。喻常森《海交史札记》(《海交史研究》1990年1期)认为唐只有市舶使,没有市舶司。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年)六月,才在广州设市舶司。
关于市舶制度的具体内容,陆韧《论市舶司性质和历史作用的变化》(《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市舶司兼有海外贸易管理机构、税收机构和外事机构的性质,宋代又增加了舶货变易机构和发送机构两个职能。关镜石《市舶原则与关税制度》(《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将市舶原则概括为,政治上怀柔远人;财政上增加国库收入;严格控制货物进口,维护本国政治、经济利益。漆侠《宋代市舶抽解制度》(《河南大学学报》1985年1期)指出,市舶税率经历了“十取其二”至“十取其一”,再至“十五取一”,又倒退至“十取其一”的变化过程。廖大珂《宋代市舶的抽解、禁榷、和买制度》(《南洋问题研究》1997年1期)认为这些制度是政府控制海外贸易的手段,具有掠夺性;他的《北宋熙丰年间的市舶制度改革》(《南洋问题研究》1992年1期)指出当时的改革是市舶管理过渡到正规化、法典化的标志。章深《北宋“元丰市舶条”试析》(《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5期)则认为其重点是实行贸易垄断。
关于市舶制度对海外贸易的影响,吴泰《试论汉唐时期海外贸易的几个问题》(《海交史研究》1981年3期)认为有促进作用。卢苇《宋代海外贸易和东南亚各国关系》(《海交史研究》1985年1期)将宋代促进海外贸易的措施归结为五条:①大力招诱,奖进海商;②优待来华舶商;③保护舶商的生命财产;④维护舶商正当权益;⑤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陈苍松《市舶管理在海外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亦持此说。连心豪《略论市舶制度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则强调其对民间贸易的掠夺性和危害性。郭宗宝《市舶制度与海关制度比较》(《海交史研究》1988年1期)认为唐代海舶可自由往来通商港口,宋代则通过“公凭”加强了对商舶的监督管理,而且有了查私的内容。黄纯艳《论宋代贸易港的布局和管理》(《中州学刊》2000年11期)指出,宋代对贸易港的管理较为规范:其一,修建停泊码头,建市舶亭或来远亭;其二,贸易港口设有储存货物的仓库;其三,设专门机构来保护港口及入港商船安全。
关于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研究当然不止上述数项,还有人口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亦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限于篇幅,容待后论。仅就本文所涉的土地、赋役、官私手工业、商业、专卖和外贸等政策而言,已是大家林立,硕果累累,以上介绍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论述,所见欠广。若从唐宋变革期角度言之,今后的研究欲更上层楼,笔者以为以下数处尚可加强。一是尽可能打通朝代隔阂,将晚唐、五代和两宋的政策演变作贯通研究,力求以中时段这个尺度来把握其演变规律和演进趋势。二是应将唐宋之际经济政策的转轨与当时经济格局的变迁、经济结构的嬗变、特别是城乡商品经济成分的成长和海外贸易的开拓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以明动因。三是加强区域研究,注意从空间角度把握其时经济政策的地域差异,例如经济重心南移导致东南沿海地区的海洋发展路向日渐明显,加之该地区原本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较高,因此发展商品经济和海外贸易的要求更加强烈,而驻有重兵的西北地区则长期笼罩在战时财政体制的阴影之中,商品经济既受到抑制、又有畸形发展的一面。四是在政策效果和社会影响的层面上,对国家、商人、手工业、农民等所涉各方面进行利益分析,已有学者注意,但尚须加强,因为在政策变动的轨迹背后,确实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利益之争。这种斗争当然是政策变迁的重要动因,而斗争的不同结局也会影响到日后新的利益格局的形成。
标签:宋朝论文; 两税法论文; 中国土地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土地买卖论文; 宋代建筑论文; 均田制论文; 史学月刊论文; 手工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