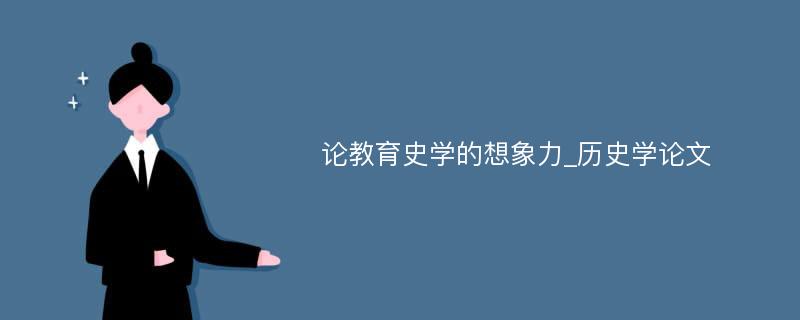
论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想象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一门定位于研究过去之教育的学科,教育史研究需要想象力吗?我们知道,文学、艺术、社会学有其想象力,然而,教育史学是否也有想象力?笔者以为,正因为教育史学的母学科历史学有其想象力,那么,教育史学同样有其想象力。且正因我们之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实际上弥久存在的教育史学想象力,才使得在宏大的社会变革中,教育史的学科研究陷于困境。
一、历史学想象力的三层内涵
在学科研究方法论中,“想象力”(imagination)一词,主要见于文学与艺术学的研究之中,一般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是想象的主体在已有的形象或观念基础上创造出另一个新的形象的能力。它是“灵魂的创造……不是一般的思维能力,而是一种心灵感应、精神领悟,属于人类最神秘的一种精神存在方式”。[1]“想象力”在史学研究中,从广义上来说,其内涵有三层。
第一层含义,是指一种属于历史思维的“形象思维”,又可称为“本质性想象力”。这种形象思维能指导史学研究者在撰述历史事实的过程中,通过思维的考量与写作的构建,从而有述有作地进行历史写作。这一层含义上的“想象力”,应该是根植于史学研究者思维最深层的一种能力。这样的形象思维,既体现在对史实的如实叙述中,也体现在带有一定主观色彩的研究者的撰述风格中。它能够活化研究者思维,使研究者在运用史料并输出历史描述性语言的时候,使语言“活”起来,“栩栩如生”起来,从而使得读者或者说历史知识的受众能“移情”式地理解过去的历史。
第二层含义,是指史学研究者立足于现实的时代问题,同时又在现实社会的认识惯习(或许可以称为具有时代特色的先验性的“成见”)基础上,去认识历史的“认识能力”,也可以称为“回想性想象力”。主要用于重构历史事实,它的指向是往回看。众所周知,在重构历史事实时,史学研究者作为历史认识的主体,必然要借助于某种先验的社会存在(类似于史家所处时代的评价尺度)来进行史料的筛选、考据,从而指点历史迷津、臧否以往,重塑过往的历史。作为“认识能力”的想象力,能够指导史学家从矛盾的历史资料中提炼出历史事实,重构历史。
第三层含义,是指一种已经成型的连接古今、转化历史与现实,同时能进行教育时空穿梭的能力,又可称为“创造性想象力”。它的指向性是既往前看也向后看,且能前后相连、穿梭。这一能力可以赋予历史研究者高瞻远瞩的视野,可以对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进行反思、综合,同时能沟通、联系现实,将历史转化为实践。它还能赋予历史研究者穿梭时空的能力,使其能通过抽象的假设而通达历史与现实,从而走向现实,解决现实问题,以实现历史“经世致用”之社会功能。同时,它也是一种想象的主体带着现实的问题进入过去的历史,来寻求如何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实际上,第三层含义涵括了前面二者。也由此,“创造性想象力”出发,历史研究者应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之间的诸多关系等进行耙梳,从而在分析、归纳和比较史实的基础上做出概括。
上述历史学想象力的三层含义,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文字表述转向理论思考,由写作风格转向思维品质。要成功运用历史学的想象力,这三者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不同重合,但又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当然,史学的想象力这三层意涵特别是第一和第二层所指代的能力,实际上也是诸多史学大家一直在不自觉运用的。比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撰述的历史,就在史料当中加入了想象,从而使这些人物的形象跃然纸上。而司马迁对于史学想象力的运用,便涵括了以上想象力的三层意涵。
二、教育史学想象力之意涵
脱胎于历史学的想象力,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既有上述三层意涵,不过,因为教育史学有着与史学不一样的“教育”特色背景,因此,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明显带有与史学想象力不一样的本质特征,即教育性。故此,笔者特将“创造性想象力”作为本文着重强调的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也即是教育史研究者所应具有的“心智品质”。这一概念主要借鉴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曾提出过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使他们能够看清世事,以及或许就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事情的清晰全貌。”社会学的想象力“可以让我们理解历史与个人的生活历程,以及在社会中二者间的联系”。[2]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是让人们能够理解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并能联系历史、思考当下的一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所拥有的心智品质。
笔者认为,与社会学的想象力相似,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也应该是教育史研究者所拥有的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使得教育史研究者能够利用教育史料增进自己对于人类教育历史整体研究的质感,从而在真实客观的史料之上,看清现实社会中教育变革的全貌,同时能清醒明白地辨析在当代社会变革中教育变革的走向。这是一种历史眼光与当代视角转换与联系的能力。简言之,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是一种能够立足于当下,以整体观和历史感的思维方式联系现实与过去且面向教育实践的能力。
如果这一穿梭教育时空的心智品质能在教育史研究者群体中得到广泛运用,那么,可以预见的是,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便能赋予教育史研究者在宏大的历史社会变革与现实教育变革之间,在教育思想家的思想与教育制度的施行之间,在精英教育阶层与下层民众教育领域之间,在教育公共问题与个人研究兴趣之间穿梭的能力。从而构建一种基于社会整体观和历史全面观的整个教育史的结构性知识,使研究者们能够游刃有余地进行教育史研究,从而提炼与构建研究的新范式与新理论。
三、教育史学与历史学想象力之殊异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教育史学想象力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就其特质展开分析,也有必要将“教育史学想象力”与“历史学想象力”的殊异之处进行甄别。
在西方史学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以德国史学界泰斗兰克(Leopold von Ranke)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派认为,历史学能够而且必须依靠史料弄清历史真相,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来写历史,也即“如实直书”。历史撰述中的客观主义倾向,强调叙述真实的历史事实,忽略或否认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作用。无独有偶,在中国史学界,18世纪至19世纪出现的乾嘉学派的基本要求是整理与考证史料,遵循这一传统的史学家后来也提出“史料即史学”的口号。以至于傅斯年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3]这些历史学家的共同点,主要在将历史资料当作可以反映历史事实的唯一凭证,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事件当事人以及后世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如史家的历史观、方法论等。
然而,实际上早在18世纪,康德就已指出,过去决定我们对于现在的态度者少,而现在决定我们对于过去的态度者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哲学家狄尔泰、齐美尔、李凯尔特,意大利的克罗齐、英国的柯林伍德等人沿着康德的思路,对上述传统的“如实直书”的信念提出了挑战。他们都着重强调研究者在考查历史事实时的主体能动作用。如狄尔泰(Wilhelm Dilthy)怀疑历史事实能够游离于历史学家的意识而独立存在,认为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念的产生都不能超越历史学家内在经历范围。[4]齐美尔(Simmel Georg)认为,历史学家面前所有的一切只是文献和遗迹,历史学家设法从中构造出历史事实,这种事实只能是一种主观的精神构造。[5]所有这些论点,突出了历史学家本身的内在经历、主观精神、价值取向、现实需要对于历史认识的制约作用,这种作用甚至被判断为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毋庸讳言,历史事实不仅仅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同时它还属于认识论范畴。也由此,历史学的“想象力”就在历史学家的历史思维和历史触感中呼之欲出了。克罗齐说,“想象力对于历史学家是必不可少的:空洞的批判、空洞的叙述、缺乏直觉或想象的概念、全是无用的……没有这种想象性的重建或综合是无法去写历史或读历史或理解历史的。”[6]柯林伍德也指出,历史学想象力是史学家所必须具备的,因为“历史学想象力不是装饰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没有它,历史学家也就没有什么叙述要装饰了。想象力这种‘盲目的但不可缺少的能力’,没有了它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知觉我们周围的世界”。[7]
总的来说,柯林伍德等人所说的历史学的想象力,实际就是指面对断裂而非连续的历史以及残缺或非准确性的史料时,历史学家要运用“想象”来克服这些困境。这种“想象”的实质就是要将历史学家自身置于历史时空中,对相应的历史事实或事件进行移情式的理解,进而重构或再造历史事实,使之尽可能接近历史真实。也即是说,西方史学所说的历史学的想象更接近于中国史学上所说的“设身处地”,如王夫之说“取仅见之传闻,而设身易地以求其实。”“设身于古之时世,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8]
述及至此,我们会发现,历史学的想象力实际上主要指的是本文前述想象力三个层面中的第二个层面,也即“回想性想象力”,其主要目的在于如何理解历史。然而,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显然不完全等同于柯林伍德等人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想象力。与之殊异的是,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从目的上来说,它更关注理解当下和面向未来,它是在遭遇当下的教育困境或未来可能遇到的教育困境时我们需要回溯过往的教育历史,并对之进行思考,从而构建有利于当下或未来的教育实践的理论或方法的一种心智品质。也即是说,它在纵向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穿梭时更注重横向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史学的想象力倒更与中国传统史学中如司马迁、司马光等人治史时所具备的想象力接近,“鉴古今之得失”,其目的在于“资之以助治”,这即是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有别于纯粹意义上的历史学的想象力的第一层特质。
这种特质的生成与教育史学科双重母学科的交叉性有关。正因为教育史学的这一特殊性,才会使得其具备历史学纵向关怀的同时,也更强调教育学横向的关怀。由于横向的关怀在于着重关照当下的教育实践,更需要研究者具备一种“转换”与“创造”的能力。如将现实的困境转换至历史的脉络中并在历史脉络中获得理解,或在历史脉络中发现教育的历史事实并将其转换至现实的教育实践从而在现实教育实践情境中进行理解,研究者才有可能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理论或方法的创造或构建,这种转换、创造需要研究者具备更高程度的创造想象力。当研究者在思考现实的教育实践及其历史脉络中的印痕时,不仅在于研究本身要面向实践,还在于研究者应具备建构本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自觉。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在运用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时,其创造性是最为重要的,这构成教育史学的想象力区别于历史学的想象力的又一特质。因此,教育史学的想象力其内涵更为丰富,某种意义上,它脱胎于历史学的想象力,却又涵括了历史学的想象力。
四、教育史学想象力之运用
在对教育史学的想象力进行辨析后,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来运用这一心智品质呢?实际上,这一心智品质主要存在于教育史研究者身上。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史研究者如何来挖掘、培养和利用这一想象力。
第一,教育史研究者必须运用历史整体观,培养历史感以理解过去的教育。这里所谓历史整体观,并非仅仅局限于教育史这一相对狭窄的研究领域。作为一名专门史研究者,教育史研究者必须要有宏大的历史眼光,要能在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之上对教育史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具备一种通达的研究思路,才能真正领悟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教育史研究者不仅要关注人类教育活动这一领域,同时,亦要联系社会的其他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而历史感是教育史研究者在整理和研究史料的过程中长期累积起来的一种质性感觉。同时,历史感亦是建立在当代生活之上的。“历史感的培养并非总是局限于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关当今的知识往往能以一定的方式更为直接地帮助我们了解过去。”[9]历史感能帮助研究者通过史实来找到自己的史识,但这需要教育史研究者在历史整体观的感悟下,“从传统的、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中摆脱出来,运用整体的、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的观点来看待一切历史现象、过程。”[10]从这一角度上看,理解历史是教育史研究者所必须做的重要功课之一。
第二,教育史研究者要立足当代教育,并带着教育问题去研究教育史。年鉴学派大师费弗尔说,“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因为“历史学家总是以自己的时代范畴来思考问题的,并用自己时代的语言来著书立说”。[11]如今,以“问题史学”为指导思想的史著已蔚为大观。这种问题导向也应该引入教育史研究中来。也就是说,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都需要立足当下,从当代的学科领域和知识体系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不能仅仅限定于某个研究领域,不能就教育史研究教育史。由此,教育史研究者就存在一个如何处理自身的现实与所研究的历史之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史学家如同米尔斯所讲的社会学家一样,“同普通人一样置身于这个时代创造历史的主要决策之外”,但却是最有能力也最有必要积极介入教育公共事务的,因为教育史研究者有得天独厚的研究基础:本身就致力于博古通今。“为了重构已消逝的景象,他就应该从已知的景象着手,由今及古地伸出掘土机的铲子。”[12]
因此,教育史研究者应该面向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制度的施行来发言。不仅如此,教育史学家更应具备一种提出公共教育议题、介入社会教育变迁的能力,把用教育史学的想象力所得来的教育历史的经验教训运用到教育实践中去。这种立足现实,并带着问题积极投身于现实教育改革中的教育史研究,才能真正为当代教育抑或未来教育所用。
第三,教育史研究者要将想象力运用于教育史写作当中。教育史的写作,正如历史的写作一样,“不仅是记载、描述历史,更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往往通过这种方式解释社会。”[13]退一步讲,即使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说,综观我们以前的作品,恐怕问题并不在于历史资料的堆砌或研究方法的死板,而是处理历史资料的“想象力”的贫乏。因为太多的知识产品对于内在于中国当下教育现实经验和重要问题缺乏相应的关怀,对于影响当代中国教育弱势群体生存状态的历史和结构力量缺乏必要的反思,对于推动具体的教育结构变迁乃至教育制度变迁缺乏应有的担当。教育史研究者的知识作品,只有与教育现实关联,与当今社会变革主题相关联,才有经世致用之价值。
因此,教育史学的想象力不仅应体现在教育史学者对于研究内容(教育史实、教育场景、生活和制度等)的描述和分析上,还应包括教育史研究作品的结构安排、谋篇布局,即如何让作品更富有灵性之上。教育史研究者如何将教育史学想象力融入研究与写作之中,合理利用人们交予他们的写作解释权,通过研究来指导现实,这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五、结语
本文对教育史学想象力这一问题的探讨,旨在试图探究有没有一种可能,能够使得教育史研究场域中的行动者们,既能在教育史的研究领域中找寻到属于自己的研究领地,同时又能回到当代中国教育的现实语境之中。我们以为,探究教育史与当代教育改革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内在构建,是教育史研究摆脱过往研究范式窠臼的一个可行路径。从而,教育史研究不再“超然于现实教育”,而与当今时代的重大教育议题有密切关联。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对现实教育实践的介入,还是对教育史本身的学术研究,教育史学想象力都会使得教育史学科焕发出无比诱人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