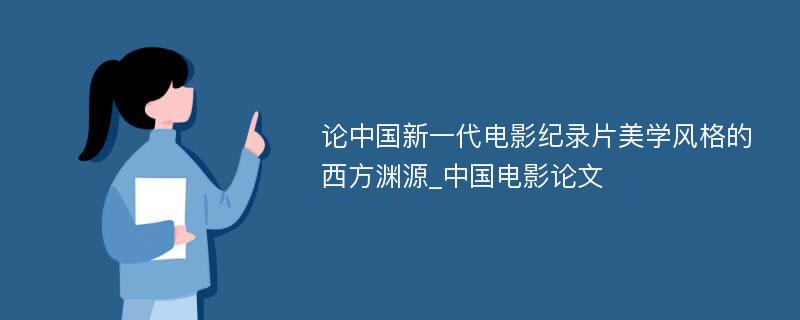
论中国新生代电影纪实美学风格的西方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生代论文,渊源论文,美学论文,中国论文,纪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新生代电影接受西方电影的影响,呈现出一种“世界电影”的特征,这种特征既体现在题材、内容和主题方面的“表现什么”,也体现在形式和美学特征方面的“如何表现”。我认为西方电影尽管流派众多,甚至相互之间还有一些抵牾之处,但整体看来,是以下三个方面深深地打动了中国新生代电影人:其一,表现边缘人生的黑色电影风格,促使中国的新生代电影形成了相同的内容取向与思想取向;其二,反思与批判社会人生,突出人性的复杂性,使中国的新生代电影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其三,倡导纪实的美学表达方式,促成了中国新生代电影的创作特色的生成。
对新生代电影产生重大影响的西方电影,从非理性现代派电影、法国新浪潮电影到新好莱坞电影,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源自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纪实美学风格。这种风格,成为新生代电影区别于中国传统电影的一个突出特征,也是其他两个特征的基础。
纪实美学在西方电影中的流变
纪实美学的形成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发展成熟的标志,其核心是主张人物形象与生活保持零距离的真实,反映现实问题。著名编剧柴伐梯尼曾说:“我讨厌那些多少有点假想成分的英雄人物……今天应该告诉观众说,他们自己才是生活的真正主角……人们会经常习惯于把自己和虚构人物等同起来,这将是很危险的。我们必须认清我们自己的真实面貌……”[1](P126)这就强调了艺术必须表现真实人物,而不是虚构人物,因而,新现实主义提出“还我普通人”的口号,影片主人公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小市民和城市知识分子。影片内容也是反映他们的普通生活,强调从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直接面对严峻的社会形势,用大胆直面的精神而不是回避退缩的态度来揭露生活中的迫切问题。《大英百科全书》的电影史部分认为,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运动表现人类对生存的四个基本问题所进行的斗争:反对战争以及侵入他们国家的那种致命的政治混乱;反对饥饿;反对贫困和失业所造成的困境;反对家庭的解体和堕落。因而,新现实主义电影强调贫困现实而不是好莱坞的梦幻魅力;展示简陋的茅棚等客观环境而不是洁净的家园和时髦的公寓;表现的是普通的、无礼的、世俗的人,而不是好莱坞优雅漂亮的令人想入非非的绅士淑女[2](P84)。如战争前夜的法西斯残余势力对进步抵抗人士的迫害(《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城市工人的失业问题(偷自行车的人》、《罗马11时》)、南方农民的贫困和缺粮问题(《大地在震颤》、《苦涩的米》)……这些现实问题,直接或间接的都与战争和社会动乱所引起的贫困人生主题有关。对待这些问题,新现实主义没有将其粉饰和美化,或者视而不见,而是用几乎等于生活的方式在银幕上加以再现。在新现实主义的标志之作《罗马,不设防的城市》中,“罗西里尼把新闻片与他自己拍摄的具有新闻片效果的镜头结合在一起。他运用平淡无奇的现实主义照明,鼓励演员达到表演的真实自然,并把他的演出场地搬到了罗马大街上”[3](P182)。而在《偷自行车的人》中,“影片没有编造现实,它不仅力求保持一系列事件的偶然性和近似逸事性的时序,而且对每个事件的处理都保持了现象的完整性”[4](P305)。这两部电影批判现实的力量就是真实性。
为了达到真实性的目的,职业演员和非职业演员的混用并一视同仁也是新现实主义的一个显著特色。“大众报刊上的报道文章和新闻消息自然热衷于告诉我们,《擦鞋童》是由大街上的普通孩子演出的,罗西里尼在故事发生的当地临时物色群众演员,在《游击队》的第一个故事中担任女主角的姑娘是在车站上物色到的文盲”。把这些或外貌相似,或经历相仿,适合所扮演角色的非职业演员与职业演员混用,使得“非职业演员表演技巧的幼稚可以靠职业演员的经验来弥补,而职业演员的表演亦可在总的真实氛围中显得更为逼真”[5](P272-274)。
巴赞作为新浪潮电影之父,他高度评价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他首先批判了表现主义的唯美倾向和好莱坞明星崇拜,并高度赞扬了苏联现实主义影片:“爱森斯坦、普多夫金或杜甫仁科的苏联影片,不就是首先具有现实主义的创作意图,因而在艺术和政治上都是革命的,并与德国的表现主义的唯美倾向和好莱坞令人生厌的明星崇拜截然对立吗?”他认为:“和《战舰波将金号》一样,《游击队》、《擦鞋童》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问世开辟了银幕上由来已久的现实主义与唯美主义彼此对立的新阶段。但是,历史绝非简单的重复。”[5](P264)在与其他艺术进行比较后,他认为电影更接近生活,因而纪实性是电影的“第一本性”。“电影是现实的渐近线”,电影应该是“生活在银幕上的流动”。
巴赞的主张在新浪潮电影中得到了突出表现,弗朗索瓦·特吕弗在阐述新浪潮电影的准则时说:“年轻的电影创作者们将以第一人称来表现自己和向我们叙述他们所经历的事情。可以是他们新近的爱情故事、政治觉悟的转变、旅游故事、一场疾病、他们服兵役的情况,他们最后的假期,而且差不多都会从中找到乐趣,因为那将是真实和新颖的……”[6](P13)这个观点强调了电影的内容必须来自于现实生活。而生活本身并非是戏剧性地环环相扣,按照某一起承转合的规律性被安排好的,生活往往是由一些松散的、分不清轻重主次的事件串联起来。因此,在表现方法上,就意味着要放弃戏剧化。戈达尔的《精疲力竭》就充分体现了这样一种特点,影片“虽然有一个大致的故事框架,但事件与事件、情节与情节之间并没有因果式的相互联系。整部影片是一堆拼砌起来的生活碎片。戈达尔对这些碎片所采取的剪辑方式,也没有按照远景、中景、近景的传统程序,而是像影片中的人物行为一样,随意的自由跳接,他运用高度‘机动’的摄影机,给人一种自发性和即兴创作的感觉”[7](P56)。结果,《精疲力竭》却以其看似松散的结构与无意义的故事,真实地表现了生活本身,凸现了法国60年代的社会风貌和青年人的生存状态。
在法国新浪潮电影影响下的新好莱坞电影,取材现实生活,把镜头对准穷街陋巷,对贫民窟青少年生活进行了如实地表现。以《穷街陋巷》为例,影片的故事发生在纽约曼哈顿的下东区。纽约作为“世界上村落的最大集合”,每个社区都令人惊异地保留着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曼哈顿的“小意大利”,蔬菜水果摊、比萨店、面包房、酒吧比比皆是。社区用内部的稳定结构防范大城市的压力。导演斯科西斯在附近街区长大,影片逼真再现了街区独立于外部世界的闭关自守状态。查理和周围的朋友一样,没有正式的工作,靠做黑市生意和给黑手党当喽罗为生。查理、乔尼和托尼穷极无聊,到处闲逛,干起坏事来无缘无故,随心所欲,他们一起喝酒、打架、骗人,在酒吧里目睹枪杀……影片没有多少连贯情节,大量展现的是查理等人没来由的胡作非为,也正是这点让人震惊。新好莱坞电影《穷街陋巷》、《出租车司机》、《午夜牛郎》、《教父》系列、《美国往事》等影片也都贯彻着纪实性美学原则。
中国新生代电影的纪实性美学风格形成
西方纪录派电影理论代表人物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认为:“电影按其本性来说是照相的一次外延,因而也跟照相机一样,跟我们的周围世界有一种显而易见的近亲性。当影片纪录和揭示的物质现实时,它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影片”。“电影可想而知是热衷于描绘易于消逝的具体生活——悠忽犹如朝露的生活现象、街上的人群、不自觉地手势和其他飘忽无常的印象,是电影的真正食粮”[8](P3)。新生代纪录片导演是这种理论的积极实践者,他们“把摄影机扛到大街上”,镜头对准中国社会的角角落落,不饰美、不隐恶,直录芸芸众生的生存环境,饮食起居,掀起了意义深远的“新纪录片运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吴文光的《流浪北京》、《江湖》、《1996——我的红卫兵时代》;时间的《天安门》、《我毕业了》;雎安奇的《北京的风很大》;杜海滨的《铁路沿线》;杨天乙的《老头》;王兵的《铁西区》等。
转型时期影视纪实潮流的兴起,是对中国电视纪录片长期以来“格里尔逊”式的直接解说模式的突破①。李奕明在谈到第六代电影的视听风格时分析道:“如果要探讨第六代视听风格的形成,也许应当提到几部非电影专业人员拍摄的纪录片,如《流浪北京》、《我毕业了》等。这几部纪录片的创作者由于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而又充满热情与真诚,给影片带来的结构散乱、构图失衡、极为混乱、随意越轴、切点不准等等特点,恰恰对几十年来中国式的纪录电影观念形成了致命冲击,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文化中,缺陷与冲击力常常是同时存在的。”[9](P550)这也恰恰说明新纪录片对新生代电影的影响首先是内容,是一种美学观念,而其次才涉及表现形式。正是这场运动奠定了新生代电影的美学基础。
美国奇迹影片公司(Miracle pictures Group,Inc)的创始人何杰民对纪录片的作用有独到的见解②,在谈到大陆电影时曾说:“建议搞剧情片的人,一定要拍些纪录片,学习现代纪录电影的手法。奇迹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以及我们的老师马丁·斯科塞斯都是从纪录片开始进入电影圈。”“纪录片使我们懂得生活,也使我们学会如何真实地表现生活,在分镜头、用光和摄影机调度上怎样与戏剧电影有所区别。这都有利于我们克服舞台化、程式化的虚假感”[10](P225)。纵观新生代电影许多导演,他们都有或长或短的拍摄纪录片的经历,张元的《钉子户》、《广场》、《疯狂英语》,贾樟柯的《公共场所》,余力为的《美丽魂魄》,王光利的《我毕业了》,李玉的《姐姐》、《守望》、《光荣与梦想》等都在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源自于纪录片的反对虚假的纪实美学风格体现在许多新生代导演的作品中。
如果说50~80年代的电影充满了对社会主义制度乌托邦式的激情,那么20世纪末的中国的社会已不完全适合那种单纯赞歌式的电影形式。尤其对新生代电影人来说,不同于主流电视媒体把国家大事、英模人物、好人好事作为主要的选题,而是把目光更多的投向了社会缝隙里的亚文化及边缘人物,通过亲切平等的态度来传达转型期间社会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90年代轻便的DV设备出现后,手提录像机更有利于深入最不同寻常乃至微妙的私人空间,这使得纪录片不再需要庞大的设备和雄厚的资金,体现出更多的私人化和个体化色彩。摄影机不再是仅仅是代表国家机器或革命大事业的新闻片和宣传片的载体,而是个人写作的工具——由主客体一起参与写作。纪录片不像同期的大多数故事片一样,受商业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双重牵制。它狭窄的市场空间和制作者并不远大的市场抱负,使得制作过程相对单纯,编导们可以潜心于艺术的创造,注重细节、过程和即时性,强调主客体间的互动,制作完全意义上的作者电影。
背负历史的沧桑,面对残酷的现实,纪录片所携带的多元歧义容纳了更多异质的文化表达,而正是这些非主流镜像传达出中国大地上转型期平民阶层生存的基本情态,纪实立场成为一种态度,一种年轻人进入电影领域的最容易的选择。在记录当下生活的过程中,记录者直面惨淡的人生,不再回避阳光下庸常的生命状态。他们获得了表达真实情感的智慧和勇气,同时也得到了重新审视自己灵魂,关注底层的悲悯情怀。吴文光在谈到纪录片时就讲到:“它和生活是硬碰硬的。原来指残酷,好像意思它像解剖刀一样解剖社会肢体的某个部分,溅出火花,或者说是像聚光灯一样照亮某种东西,而区别于故事片的温情脉脉,这就是进入到所谓现实的残酷。现在来说,就是包括相对于自己的残酷。做一个片子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解剖自己、照亮自己”。“还有一种残酷是指完成以后,自己很难安稳地在放映后坦然得与别人谈笑风生,或者回忆拍摄经历。因为,在你刚刚拍摄的地方走了一遭,但是回头一看,那地方的人仍然生活在原处,太阳仍然是照不到他们。你转了一圈回到亮处,站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被别人注视”[11](P5)。这种扪心自问的自责自省意识是艺术电影导演和商业电影导演区别开来的一个显著标志,这是中国电影的未来不能缺少的一种意识。
新纪录片在国外纪录片电影展映中屡屡获奖,被国内专业人士和怀揣梦想的艺术青年观摩讨论和效仿,成为他们涉足电影领域的一条“捷径”。标志着第六代电影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的《苏州河》的摄制,就是直接从拍摄纪录片开始的,娄烨曾谈到:“《苏州河》就有这个感觉,我是从纪录片开始的。实际就一个人拿着一个超8,拍了一个月,每天在苏州河边溜达,两岸非常熟悉,从这个开始进入到故事,然后进入到故事的中的我,然后想出来。”[12](P258)张元、贾樟柯、王光利、李玉等新生代电影人都以纪录风格创造出中国90年代有力量的故事片,使纪实性电影进入了这个大转型时代的舆论核心。
以贾樟柯的《小武》为例,影片的环境是真实的,有现场记录的特点:如用嘴吸一下才出水的水龙头、孩子乱跑的派出所、电视台摄像师独特的玉兰花指、理发店刮胡子的“工艺”,这些细节看起来与主题无关,似乎是闲笔,但它们都取材于真实生活。正是大量的细节构成了小武的生活环境。与传统影片不同,在这里环境不是为人物而存在的,也不是为摄影机而布置的,是自在的,是与人物浑然一体的环境。影片的每个角色都是由非职业演员扮演的,他们身上具有浓烈的生活气息。人物对话几乎全部使用方言:有小武及其山西本地人的山西方言,有美美的东北方言,有川妹的四川方言,有歌厅老板的北京方言,只有电视台记者使用的是普通话。由于大量的使用非职业演员,他们说的是地道的方言,他们的语调、说话方式,话语间的停顿却传达给我们更多信息,造成了一种有厚度的环境,语言与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密切相关,传达的信息量又是无穷大的,体现出了9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大而频繁的时代特征。另外,县城中的高音喇叭,汽车的噪音,理发店放的歌曲,街头录音机的歌曲,卡拉OK的声音,叫卖声,录像厅传出的黑帮片的枪战声,乡村的鸡鸣狗叫,村里的新闻广播和广播突然中断后传来的“谁要割猪肉,请到我家来”的吆喝声,营造出一个生活在当代的中国人都熟悉的真实环境[13](P351-354)。
“在对真实性的追求中,人物及故事不再作为政治符号和民族文化的对应物而存在,生命接近存在的真实状态。导演把叙述聚焦在自身经验范围之内,尽量完成对个体生命经验的真实表达,以及对平淡无奇尴尬无助的日常生活的呈现”[14](P33)。以娄烨的《苏州河》为例,在一般人的唯美主义想象中,苏州河历史悠久,见证了大上海的沧桑巨变,以及无数生命的悲欢离合,绝对是一条流光溢彩的河流。而影片中的苏州河却成了与城市人精神生态相对应的象征性意象,河岸上是废弃的楼房,燃烧的破旧轮胎,人们冷漠的从破旧的街道和桥上走过。以水运和打鱼为业者面孔粗陋,在船上洗菜做饭,而且河上还漂浮着垃圾以及载着破烂物件的旧船。当镜头缓慢漠然地扫过这些令人不愉快的景物时,画外音说道:“所有的记忆都堆积在那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这就是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的娄烨感觉中和记忆中的苏州河的面貌。这个开端为整个影片的风格奠定了阴冷灰暗的基调,其后“我”与美美相识后,室内房间的灯泡摇曳不定,墙壁破旧脱落。站在阳台上,对面是吵架的夫妻,街道上破旧的三轮车触目皆是,行人心神不宁,声音嘈杂刺耳。
生活在这个令人不愉快的环境中的,怎能是一些健康的、有生活热情的人?摄影师好长时间没有活干了,酒吧老板啰唆而凶巴巴的,走私酒者发了财就和各种女人鬼混,萧红和老B谋财害命,酒吧女美美冷艳而寂寞,送货员马达整夜看盗版光碟,中学生牡丹失去了母亲,在街上游走……《苏州河》不加掩饰的纪录了这一切。诚如娄烨在访谈中讲到的:“我的摄影机不撒谎……”这既是社会底层的客观反映,也是导演人生体验的强烈表现。《苏州河》主题就是讲传统的信仰和价值失落后的痛苦,以大量的客观镜头描述了底层生活环境和在这种环境中生存者的痛苦。在一组组主观镜头和慵懒低沉的画外音中,一切都显得那么纷乱破败和迷离梦幻。再加上拍摄时晃动不定的镜头,迅速而琐碎的跳接,一种不安、烦躁、郁闷的气氛自始至终笼罩着这部影片。缺少家庭温暖的牡丹和靠送货挣钱糊口的马达由于一桩蓄谋已久的阴谋走在了一起,在长时间的接触中,两颗孤独寂寞的心相爱了。但是这注定是一段如美人鱼童话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无法长久的爱情。牡丹跳河了,马达入狱了,出狱后千辛万苦找到牡丹后两人喝走私酒又死了。作为这件事叙述者“我”,尽管最终知道了这段凄美的故事是真的,但是却不愿回到女友美美身边:“我知道一切不会永远,我想只要我能够回到我的阳台上去,我的这个爱情故事,就可能会继续下去……可是我宁愿一个人闭上眼睛,等待下一次的爱情……”这就是一个当代社会中迷失的人的心态的真实表白。
在《扁担·姑娘》中,镜头大都以暗灰色和青黑色为主,显得冰冷、凄凉,与人物的残酷命运相一致。高平和东子临时住所简陋寒碜,阮红唱歌的地下歌厅幽暗偏僻如地下迷宫,灰蒙蒙的天空,淅沥沥的雨水,再加上东子冷漠低沉的画外音,整个故事的叙述压抑感伤。
这与第六代导演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有关。他们的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他们不像生于50年代的导演经历了“文革”的浩劫,对民族的历史和前途命运有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他们生于60年代,在他们心中,“文革”只是一场看不懂的成年人的游戏,热闹好玩但又惊心动魄和莫名其妙。无论是从个人生活还是艺术创作,近20年来政治经济文化的转型期的无序都让他们无所适从,倍感压抑。
在新生代导演初期的作品中,大都充满着个人内敛而自省的浅吟低唱,弥漫着怪异和孤独。没有对生活盲目的乐观,没有对残酷现实的虚假粉饰和强颜欢笑。他们生活过的小城、街巷、河流都以粗砾和不加修饰的本来面目进入了画面,拍摄手法中规中矩,没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影片中,尽管生活方式不同,但情感和生命体验相近的同龄人也都素面朝天,没有穿上戏衣画上脸谱,没有经过更多的艺术的加工和典型化,一切都力求原生态,导演个人的好恶判断被隐藏起来,客观而不动声色。《苏州河》中的演员表演本色,朴实无华:不怎么漂亮的阮红,其貌不扬的苏武,愣乎乎的东子,黑帮老大尽管吼声如雷但并不是面目狰狞或者老奸巨猾,房东也不是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周围以至于就是我们自己。把人物放在“脏乱差”的环境里也许是单调的、偏执的,但这揭示了人的处境却异常真切。相反,把人物放到所谓的广阔的城市大背景,反映的倒可能是浮光掠影流于失真。在李杨的电影《盲山》中,我们看到人们在人口买卖中的麻木。这种麻木是人口买卖得以存在社会基础。鲁迅先生早在他的作品中就已经对中国人的国民性发出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慨叹。这部影片的艺术震撼力就在于它所揭示的一切,就如此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边,而我们的眼前却恰似有一座挡住目光的大山,视而不见、习以为常。其实,这座盲山绝不只存在于社会,而是存在于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深处,《盲山》只不过从人口买卖这个视角把它揭示出来了而已。在李玉的电影《苹果》中,我们看到高速发展和日益丰富的经济生活的下面,道德底线的崩溃所带来的悲剧。男人世界的讨价还价对于女人权力的不尊重,令人震撼。
纵观中国新生代的许多电影,都具有较强的纪实性,如王小帅的《扁担·姑娘》(1998年)、《二弟》(2002年)、《十七岁的单车》(2000年)、《青红》(2005年),王超的《安阳婴儿》(2001年)、《日日夜夜》(2004年),李杨的《盲井》(2004年)、《盲山》(2007年),章明的《巫山云雨》(1996年)、贾樟柯的《小山回家》(1996年)、《小武》(1997年)、《站台》(2000年)、《任逍遥》(2002年)、《世界》(2005年)、《三峡好人》(2006年),盛志民的《心·心》(2003年),路学长的《卡拉是条狗》(2003年),俞钟的《我的美丽乡愁》(2003年),唐大年的《都市天堂》(2000年),李继贤的《王首先的夏天》(2002年),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2006年),刘浩的《陈默和美婷》(2002年)、《好大一对羊》(2007年),刘杰的《马背上的法庭》(2006年),张猛的《耳朵大有福》(2008年),韩杰的《赖小子》(2006年)等。这些电影在国外获奖无数,所以颇受国外的观众和评论界的青睐,主要是因为西方知识界通过新生代的电影来了解中国当下社会。“中国新生代带有实验性的电影实践成为他们达到这种文化理解的主要窗口。换句话说,中国新生代有实践性的电影实践在西方学者眼中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代表,而老一代的电影(主旋律和娱乐片)要么逐渐淡出,要么是他们关注领域以外的盲点”。中国新生代电影有较强的介入当下生活的能力,“不像以前的许多艺术影片常常把故事置于历史的时空,新生代电影人把他们富于独特价值的人文思考切入到中国社会的当下现实中,常常被称为‘都市的一代’,他们的作品对认识中国当代文化的性质具有重要的价值”[15](P5)。如果说过去的注重电影的功能和社会效应,用典型化手法创作出来的现实主义作品是一种“高于生活”的主观化的“现实主义”(实际上也就是浪漫主义③)的话,那么新生代电影就是一种力图“等于生活”的客观化的现实主义,与新生代作家的新写实小说异曲同工。这是纪实美学原则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
①约翰·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 1898-1973)是“纪录片之父”费拉哈迪的学生,尽管作品只有一部《飘网渔船》,但毫无疑问地成为英国纪录电影学派的创始人。英国纪录电影学派一方面十分强调影片的社会意义,主张纪录片应当是富有创造性的对真实生活场面的处理,是一种直接的宣传手段;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在再现真实生活场面时进行艺术加工。从30年代到50年代末,世界纪录片被美国学者比尔·尼科尔斯称为“格里尔逊模式”阶段,格里尔逊首创的“画面加解说”模式逐渐被演变成“上帝之声”般“自以为是的说教模式”,“由于强调主体的宣谕功能,训诫功能,大量运用画外解说。而且,这种解说以一种全知视觉的方式,居高临下,不容争辩的语气来展开,仿佛执掌着绝对的话语权。在一个日益多元的时代,这种训诫和宣谕越发显得独断和强制。”(陈旭光.当代中国影视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34.)二战结束后,这种模式就“失宠”了。
②在美国电影界,制片人何杰民(A.Kitman He)与奥利弗·斯通长期合作,导演出80年代美国影坛上一系列著名的影片,其中有奥斯卡获奖影片《野战排》、《华尔街》、《生于七月四日》、《刺杀肯尼迪》等,他们制作的影片开创了好莱坞的新时代。
③有研究者认为,注重电影的功能和社会效应,必然不会满足于创作对于“生活”的摹写、“加工”。以先验理想和政治乌托邦激情来改写现实,使电影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浪漫主义”。参见:20世纪中国电影的写实主义传统[A].王志敏,杜庆春.理论与批评:全球化语境下影像与思维[C].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76-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