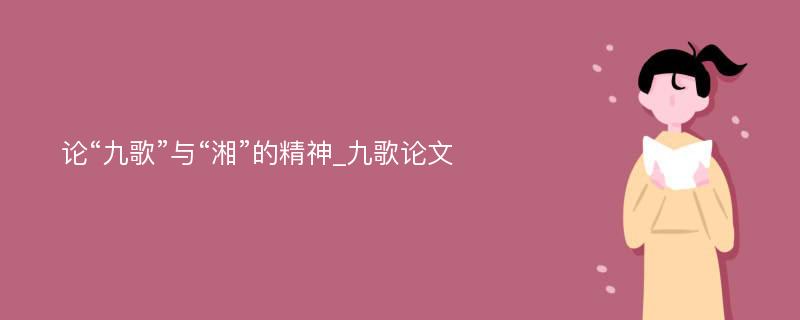
关于《九歌》二《湘》的神灵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神灵论文,九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08)06- 0696-07
二《湘》神灵与“舜、妃”传说无关吗?
在对《九歌》之《湘君》《湘夫人》(以下简称“二《湘》”)主旨的解说中,游国恩、马茂元先生所主的表现“舜与二妃”“死生契阔、会合无期”的恋情说,数十年来在楚辞学界占了统治地位。对此,我在八年前所作《〈九歌〉二〈湘〉“恋爱”说评议》[1]中,曾从与“舜与二妃”的神话传说背景不符、与祭祀神灵的礼俗不符二端,较深入地批评了此说的疏误,并从二《湘》分别为沅湘民间祠祀湘君(舜)、湘夫人(二妃)之祭歌角度,对其内容主旨作了新的阐发。
细心的读者当然会发现,我的批评有一个重要前提,即首先确认在战国南楚所祭二“湘”神灵,已与“舜与二妃”的神话传说有了联系(这也是王逸以来许多楚辞学家所共同确认的)。
但对这一前提,有一部分研究者持怀疑态度。较早的是晋人郭璞,他在注《山海经·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节时指出:
说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从之,俱溺死于湘江,遂号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
此后,明清之际也有一些楚辞学者继承此说,对将湘君、湘夫人神灵定为舜与二妃之说,提出了异议。如汪瑗《楚辞集解》即以为:“然‘湘君’者,盖泛谓湘江之神;‘湘夫人’者,即湘君之夫人:俱无所指其人也。或以为尧之二女死于湘,有神奇相配焉。湘君谓奇相也,湘夫人谓二女也。或以为湘君,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称君;湘夫人谓尧之次女女英,为舜次妃,宜降称夫人。或以为天帝之二女。俱非也。……”顾炎武《日知录》卷八《湘君》条除引郭璞之注以申己意外,还进一步提供了自己的证据:“又按《远游》之文,上曰‘二女御,《九招》歌’,下曰‘湘灵鼓瑟’,是则二女与湘灵,固判然为二。即屈子之作,可证其非舜妃矣。后之文人,附会其说,以资谐讽。其渎神而慢圣也,不亦甚乎!”王夫之《楚辞通释》更斥秦博士以湘神为“二妃”之对为“妄说”:“王逸谓湘君,水神;湘夫人,舜之二妃。或又以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其说始于秦博士对始皇之妄说。《九歌》中并无此意。”
正因为有这些异议,我的好友周建忠对我评述二《湘》“恋爱”说的意见,也作了委婉的批评:“(潘文)直指舜妃悲剧传说为二《湘》神话传说背景,证据似嫌不足,而且还须清理神话发展的渊源线索,一般认为,虞舜与二妃的悲剧是二《湘》创作的背景之一,亦非‘原型’”[2]。已故中国屈原学会会长褚斌杰在其《楚辞要论》中,亦不指名地回应我对二《湘》“恋爱”说的批评曰:
关于湘水神的神话,与舜本没有关系。后来在关于舜的神话历史化中,由于有舜娶尧之二女的传说,恰与《山海经》载洞庭山“帝之二女居之”相同(实际上“帝”乃指上帝)①,从而附合为一,并为楚辞注者所采取。诗人屈原《九歌》,本属在当时万物有灵论的观念下,关于楚地山川的自然神的故事。湘江、洞庭,乃楚境中之大水,势必认为有神,而成为祭祀对象,至于其故事内容,除本诗外,殆已失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基本性质——湘水神男女恋爱故事的确认,……[3]
其实,周、褚对二《湘》神灵的怀疑意见,有许多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某些持疑者相近,而且游国恩当时就作过回答和反驳[4]。只是由于时隔数十年,出现了我批评游先生所主二《湘》“恋爱”说的新情况,他们似乎没有想到回过头去了解一下游先生当年的论述而已。
这样,在我批评游先生所主二《湘》“恋爱”说的时候,我还必须同时回答他当年回答过的一个重要前提:即战国南楚所祭湘水神灵,是否如郭璞以来的怀疑者断言的那样,与“舜、妃”传说没有关系?
秦博士之“闻”:南楚民俗提供的湘神与“二妃”联系之证
在许多情况下,对有关作品与神话传说背景之联系的争论,仅仅回顾古代神话传说的记述资料,还是难以作出准确判断的。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神话记述的散乱和片段,使得人们引述的资料本身就有相互矛盾的地方。
即以“舜与二妃”的神话(历史)传说而言,据王逸《楚辞章句》所述,应是“尧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张华《博物志》也称:“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舜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水经·湘水》注亦记:“大舜之陟方也,二妃从征,溺于湘江,神游洞庭之渊,出入潇湘之浦。”但《礼记·檀弓上》却记曰:“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正因为如此,郭璞在反对王逸之说时,即引此条记述曰:“《记》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明二妃生不从征,死不从葬,义可知矣。”
因此我以为,在文献记述淆乱不清的时候,弄清有关神话传说内涵的最好途径,就是去考察与此相关的古代民俗。因为古代民俗不只是一种文献的记述,它更是一种在古代民间延续数十百年乃至千年的实践活动即客观存在。
解决屈原《九歌》二《湘》所祭神灵究竟为谁的问题,当然也应该走这样的考察途径。令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恰好在这个问题上,《史记·秦始皇本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最有力的南楚民俗佐证——
二十八年……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上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于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赭其山。
这则记述,已被千多年来研究《九歌》二《湘》者征引过不知多少遍了,完全不是什么新出的资料。但我发现,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真意义。以至于连目光锐利的大思想家王夫之,也竟然对秦博士之说嗤之以鼻,斥之为“妄说”。
这则记载的真意义,恰在于秦始皇至洞庭湘山祠所问的湘神,也正是屈原为沅湘民间改写的《九歌》二《湘》所祭的同一神灵。而在博士对秦始皇的回答中,有一个最关键的“闻之”之语,又明白告诉了当代后世的人们,以“尧女舜之妻而葬此”被奉为湘神的回答,并非是秦博士自己的妄想或臆测,而恰是他从当地百姓那里听说的祀神民俗。——也就是说,在秦始皇所到的湘江洞庭一带,当时被奉为湘神而受祭的,不是郭璞所臆测的“斯之为灵,与天地并”而无主名的湘水之神,也不是二千年后的褚斌杰先生所推断的“其故事内容,除本诗(笔者按:此指屈原《九歌》二《湘》)外,殆已失考”的湘水“自然神”,而正是“尧女舜之妻而葬此”的“二妃”。
据《史记》记载,秦始皇“浮江,至湘山祠”之年,是他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即前219年),上距诗人屈原放逐沅湘之间约七十余年。我们知道,在历史上作为民风、民俗而流传的民间祭祀活动及内容,其延续的时间往往会长达数十百年乃至千年。既然在秦始皇二十八年的湘江洞庭,其所祀湘水神灵,乃是与大舜相联系的“二妃”;那么由此上溯七十余年,诗人屈原为此同一地区改作的祭祀同一湘水之神的二《湘》,其所祀神灵毫无疑问也应与“二妃”及舜的传说有关。
我所要强调的,上面所引秦博士之“闻”,决不是后世楚辞注家的牵强附会、胡断妄说,而是秦博士所听说的沅湘民间实际流传的祀神之俗。它所揭示的湘水神灵是谁的答案,已不是一种“学术”见解,而是为沅湘洞庭民间长期以来祭祀的客观事实。见解是可以商榷的,民俗所显示的事实,却是难以用臆测或空论所推翻的!
有了沅湘民间所祭湘神,当与“舜、妃”传说有关的民俗依据,再来对照屈原《九歌》二《湘》,人们便可以发现,二《湘》本文实际上也提供了可与南楚民俗相印证的证据——
《九歌·湘君》云:“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诗中所云“参差”,即传为舜所创制的排箫。应劭《风俗通》载“舜作箫,其形参差,象凤翼。”洪兴祖解此句曰:“参差,不齐之貌……此言因吹箫而思舜也。”可见,《湘君》一诗所反映的沅湘迎神、祭神对象,即当与吹“参差”所“思”的舜有关。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不过是偶合,未必就能据此认定所迎神灵即舜。但我要反问:那为什么在迎云中君、东君、河伯、山鬼等神灵时,却无一处见有“参差”之器呢?可见诗人屈原是熟知“舜作箫,其形参差”的传说,故在祭湘君(此指舜,详见下文)时,也不忘以吹箫(参差)来表达迎神之思。
再看《湘夫人》,其辞有“九疑缤兮并迎”之句。句中提及的“九疑”即九疑山,正是神话传说中的帝舜葬地。王逸注此句意为“言舜使九疑之山神,缤然来迎二女,则百神侍送,众多如云也。”正因为《湘夫人》所祭神灵,当为与舜有关的“二妃”,故诗人想象连九疑山神也“缤然来迎”了。倘若此歌所祀乃与“二妃”无关之神,则又何须远涉舜之葬地的九疑山神?褚斌杰以为:“《离骚》写屈原将从卜远行,复又祈祷于巫咸时,亦有‘百神翳其备降兮,九疑缤其并迎’句,故九疑神未必指舜,九疑山乃楚地名,大约于传说中为楚地众神所居处的地方。”[3]344其实,《离骚》之称“九疑”正与大舜有关:此诗前有“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说明诗人在想象中已来到大舜所葬的九疑山。陈词后的上下求女,也是从九疑山一带出发的(“朝发轫于苍梧兮”)。故当其上下求女失败后想象中的回归和占卜、降神之地,当还在他的出发之地九疑山一带。《离骚》“九疑缤其并迎”之句,正指明了这一点。褚先生为了将九疑山与舜割断关系,因断言“(九疑山)大约于传说中为楚地众神所居处的地方”,这恐怕倒是不顾上下文联系的无根据附会了。
然后再看《湘夫人》之首句:“帝子降兮北渚”。因为当时沅湘民间所祀湘神乃是与舜有联系的“二妃”,她们又是神话传说中的帝尧之女,故可称为“帝子”。倘若当时所祀“湘夫人”,乃是与帝女“二妃”毫无关系的远古水神,则《湘夫人》又何得称其为“帝子”?
可见,以上对二《湘》诗句例证的引述,即使只就本身而言,也已约略可证,二《湘》所祀湘水之神,应该与创制“参差(排箫)”并居处“九疑山”的大舜,以及身为帝尧之女而可称“帝子”的“二妃”有关。而有了秦博士提供的南楚沅湘所祀湘神的民俗之证,则屈原时代《九歌》二《湘》所祀湘神,已与“舜、妃”传说相联系,便更成了铁证而难以推翻了。
由“原型”到“舜与二妃”:湘神受祀对象的变迁
现在,我们再回到为楚辞研究者所反复称引的郭璞之说上来。
郭璞云:“江湘之有夫人,犹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为灵,与天地并矣,安得谓之尧女?……”有了我在上文所引南楚祠祀湘神“二妃”的民俗实证,我们是否可以因此将郭璞之说全部推翻了呢?我以为也不可以。因为郭璞之说,虽不符合战国时代南楚祠祀湘神的实际情况,但若将其推之远古“万物有灵论”时代,则此见解的某些部分,就成了精当的科学判断了。
谁都知道,作为长江在南楚的一大支流,湘水的存在,无疑要比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久远得多。它虽然肯定不会与“天地”开辟的“盘古”时代相“并”,但起码也当有亿万年的历史。那时人类还没有诞生,地球上也不会有标志早期人类认识水平的“万物有灵论”,则湘水之“神”的问题,当然也无从谈起。而当人类出现在古老的中国江河大地上,处于文明以前蒙昧时代的认识水平,他们的思想中就无疑会带有“万物有灵论”的观念。正如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所说,“各异教民族所有的历史全部从神话故事开始”,远古的人们“生来就对各种原因无知。无知是惊奇之母,使一切事物对于一无所知的人们都是新奇的。他们想象到他们感觉到和对之惊奇的那些事物的原因都在天神”,“他们把一切超过他们的窄狭见解的事物叫做天神”。[5]法国学者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也引述提出“万物有灵论”说的学者之意见,以为“(原始人)在一切生物身上,在一切自然现象中,如同在他们自己身上,在同伴们身上,在动物身上一样,统统见到了‘灵魂’、‘精灵’‘意向’。”[6]我国神话学者谢选骏则具体指明了这种认识的特点:“新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之下。这种观念认为宇宙万物都像原始人类一样具有生命甚至‘灵魂’”。而神话传说,就正是人类万物有灵论观念进一步神圣化的产物。故谢先生进而指出,“支配神话的是万物有灵观念”,“(它)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信仰”。[7]
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南方沅湘一带的原始人,自然也会持湘水有神的看法。但他们是否会像后来那样,以为湘水之神有夫有妻,分为“湘君”、“湘夫人”,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在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水神固然亦有夫妇配偶之例,但一般都分属两水,如黄河之神为“河伯”,其妇宓妃则为洛水之神②。也就是说,地处南方的湘水之神,应该早在“舜、妃”神话尚未流传的远古时代即已产生。我们因此也可以从情理上推测,当时湘水民间也应流行着祭祀这位与“舜、妃”传说完全无关的湘神之习俗(虽然我们至今还没有获得这方面的神话传说或考古文物之证据)。
但是在历史发展中,与民俗相联系的某些受祀对象,也往往会发生变迁。这种变迁,一般表现为由后出的历史人物,取代先前受祀的神灵。这后出的人物之所以能取代先前受祀的神灵,其原因一定在于他(或她)的生死,带有极大感动当地百姓心灵的力量。这样的实例无须远求,南方楚、越之地端午节祭神民俗的变迁,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据闻一多考证,南方五月端午的“龙舟竞渡”和“包粽子水祭”风俗,在最早的时候,“与龙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还可以进一步推测,说它就是古代吴越民族的一个龙图腾团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8]而到春秋时期,出现了介子推隐居介山,“抱木而烧死,(晋)文公令民五月五日不得发火”的历史故事,“端午节”在并州地区,就变成了纪念介子推的节日。而在南方,则又有伍子胥被吴王夫差赐死,装入“鸱夷”形皮囊中,抛入姑苏东南江中的大悲剧发生。此后人们因又以伍胥为水神,五月端午便成了吴越地区迎祭“伍君”的节日。只是到了战国后期,楚国的伟大贞臣屈原谏君不从,忠而被逐,为保持清白之节,毅然投汨罗而死以后,“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9]并在此日举行龙舟“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并命舟楫以拯之”(《太平御览》三一引《荆楚岁时记》)。这一习俗在魏晋以后便逐渐固定下来,端午节就演变为专祀屈原的传统节日了。
从端午节祭祀民俗的“原型”及变迁,我们同样可以确定,南方沅湘民间祭祀湘神的习俗,大抵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远古时代,在“万物有灵论”的观念支配下,人们祭祀的湘水之神当时并无特定的祀主,也未必就有“君”与“夫人”之区分。而到有关“舜陟方”而死,葬于九疑,二妃从之,沉湘而死的悲剧流传开以后,为这一悲剧深深感动的湘水一带民间,其所祀湘神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即由“舜”与“二妃”,取代原始的无主名湘神,而变为“舜、妃”共祭的湘水夫妇之神了。
这一变化具体发生的年代,现在已无法考定。但有了秦博士对始皇帝“湘君何神”的回答证据,以及屈原为沅湘民间改作的《九歌》二《湘》之词的印证,我们可以认定:在屈原放逐于沅湘之间的战国时代,沅湘民间所祀的“湘神”,已经不再是原始的无主名水神,而恰是其生死悲剧传说发生在湘江一带的“舜、妃”了。
弄清了湘水之神的“原型”及其变迁,我们便可发现,从郭璞直至当代某些楚辞学者,否定沅湘民间所祀湘神与“舜、妃”传说有关的意见,尽管有其一定的原始依据,但用来解说战国时代屈原为沅湘民间改作的《九歌》二《湘》背景,就犯了极大的时代错位:此时的沅湘祀神民俗,早已由“舜与二妃”之神,取代了被褚斌杰先生称为“殆已失考”的原始“湘神”。则屈原为之改作的二《湘》祭歌之神话背景,也当然就与“舜、妃”传说有了联系。在这个关涉《九歌》二《湘》如何解读的重大争论问题上,我们究竟应该相信秦博士所提供的当时民间祠祀“二妃”的民俗事实,相信屈原自己在二《湘》歌辞中提供的湘神与“舜、妃”传说有关的重要证据呢,还是像郭璞和现代某些楚辞研究者那样,完全不顾沅湘民间湘神祀主已经发生变迁的事实,而相信全凭“万物有灵论”的理论推断,却又于传说事实完全无考的原始湘神的所谓“男女爱情”背景呢?答案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论王逸注文对“湘君”、“湘夫人”的解说
——兼评“湘君娥皇、湘夫人女英”之说
在《九歌》二《湘》的神灵研究中,还有一种意见为某些学者所执持,那就是以“湘君”之神为“娥皇”、“湘夫人”之神为“女英”之说。
上文在引述秦博士答始皇“湘君何神”之语时,只证明了当时民俗祭祀的湘神,已与舜、妃传说相联系。但有一个问题人们虽然没有提出,心中却自会怀疑:按屈原《九歌》,沅湘民间所祀不仅有“湘君”,还有“湘夫人”。秦博士所闻的民俗既以“二妃”为“湘君”,那么“湘夫人”又是谁呢?
西汉大学者刘向在《列女传·有虞二妃》中,也记载了有关湘神的传说:“舜既嗣位,升为天子,娥皇为后,女英为妃。……舜陟方死于苍梧,号曰重华;二妃死于江湘之间,俗谓之湘君。”刘向当然读过《史记》,对秦博士之答“湘君何神”无疑熟悉,故其确认的“湘君”也是“二妃”③。刘向同时又是西汉流传的《楚辞》本子的重要编辑者,他当然也熟知屈原《九歌》中除《湘君》外,还有《湘夫人》,可惜他对“湘夫人”是谁的问题,并没有留下任何解说。
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要改变的,当数东汉楚辞学者王逸。自韩愈以来直至宋人洪兴祖,均误认“王逸以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谓湘夫人,乃二妃”。这一判断,其实并不符合王逸在二《湘》注文中透露的意见。我们且看王逸之注《湘君》“君不行兮夷犹”句:
君,谓湘君也。夷犹,犹豫也。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数百里,群鸟所集,鱼鳖所聚,土地肥饶,又有险阻,故其神常安,不肯游荡。既设祭祀,使巫请呼之,尚复犹豫也。
在这句注文里,王逸对“湘君”究竟为何神的问题,并没有说明。所以根本谈不上洪兴祖《补注》断言的“逸以湘君为湘水神”的结论。但王逸心目中自有答案在,这答案正寓于他对接着的“蹇谁留兮中洲”句的注文中:
言湘君蹇然难行,谁留待于水中之洲乎?以为尧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所留,盖指此尧之二女也。
这句注文,不仅清楚地指明了沅湘民间所祀“湘夫人”之神,乃为舜妻“二女”,而且进一步回答了上文未点示的“湘君”何神的问题:湘君神灵之所以犹豫不来,原来是被“湘夫人”即“尧之二女”留待于水中之洲了。“二女”作为“夫人”,所殷殷“留待”的“湘君”之神,当然不可能是与她们的丈夫无关的其他男神,而应该就是她们的夫君大舜。正如游国恩所说:“按叔师承先秦之旧说,据南楚之传闻,故径以舜事释之,原无不合,特未明言湘君当为舜耳。其意固自以二女为湘君之配也。……夫二女得留湘君于中洲,非以湘君配夫人而何?非以湘君为舜,夫人为二女而何?”[4]128
由上所论,王逸以舜为“湘君”,“二女”为“湘夫人”,这与秦博士所闻“尧女而舜之妻”为“湘君”的情况虽不相同,但似更合情理。因为沅湘民间的“湘神”既然分为“君”与“夫人”,则将“二妃”视为“湘君”,就实在难以解说“湘夫人”又是谁了。而秦博士的回答之所以与王逸不同,我以为可能与秦博士在湘山祠一带询问民间传闻时的特殊情况有关:从屈原《九歌》有二《湘》看,沅湘民间当时所奉湘神,原就有“湘君”与“湘夫人”之分。由于二妃溺死于湘江洞庭,其湘山祠所祀湘神,犹以“二妃”之事为当地人们所乐道。故秦博士问以湘君,民间则可能多谈“二妃”传说。秦博士不知此情,以为只有“湘君”一神,故将“二妃”误作“湘君”而答秦始皇了。所以,唐人司马贞在《史记索隐》注释秦博士之语时指出:“《列女传》亦以湘君为尧女。按《楚辞·九歌》有《湘君》、《湘夫人》,‘夫人’是尧女,则‘湘君’当是舜。今此文以‘湘君’为尧女,是总而言之。”[10]
这当然也只是笔者从情理上所作推测。但不管怎样,自王逸《章句》以“二妃”为“湘夫人”(同时点示“舜”为“湘君”)以后,东汉末郑玄之注《礼记·檀弓》,西晋张华之《博物志》,均不再如秦博士、刘向那样,以“二妃”为“湘君”,而直指“《离骚》所歌‘湘夫人’,舜妃也”(郑)、“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张)了。
将王逸以“湘君”、“湘夫人”为何神的问题辨明以后,我们再回到本节开头提出的课题,即企图根本推翻王逸之说,而将“娥皇”、“女英”分属“湘君”、“湘夫人”的新见解。较早提出此说者,当为唐人韩愈④。其《黄陵庙碑》曰:
……以余考之,璞与王逸俱失也。尧之长女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辞谓娥皇为“君”,谓女英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礼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称“君”也。
韩愈此说后为洪兴祖《补注》所从,并影响到朱熹以及明清、现代的楚辞学家如戴震(《屈原赋注》)、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郭沫若等。
但韩愈此说新则新矣,却既不合情理,也不合他自己所举礼制。
从情理上说,其最大失误在于将“二妃”的丈夫“舜”排除在了“湘君”、“湘夫人”之外。我们知道,沅湘民间关于“二妃”的传说,从来就是与“舜”之南巡而崩的传说紧相联系的。“二妃”之泣于洞庭湖畔,并最终投湘水以死,亦正表现了对夫君大舜生死相随的至性、至情。可以说,如果没有舜之南巡、崩于苍梧,就决没有“二妃”泪洒翠竹、沉湘以死的动人传说。沅湘民间,如果确如秦博士之闻,只传说有“湘君”一神,倒也罢了。但据屈原《九歌》,其所祭湘神明明有“湘君”、“湘夫人”之分。则所传湘神中既有“二妃”,又怎么可能没有大舜呢?韩愈不顾这一神话传说自身结构之二重元素,生硬地将舜从二“湘”神灵中排除,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而且从《九歌》所祀湘水之神有“君”有“夫人”看,其“夫人”与“君”自当为夫妇关系。韩愈却将其变为姊妹关系,使屈原《九歌》显示的湘水夫妇之神,一变为没有夫君的姐妹之神,岂非大背于情理?
从礼制上看,韩愈所举“君”与“夫人”的称呼,也根本不符合“二妃”之作为人帝(或天帝)大舜之妻的身份。《论语·季氏》对“君”、“夫人”的称谓是这样解释的:
邦君之妻,君称之曰“夫人”,夫人自称曰“小童”,邦人称之曰“君夫人”,称之异邦曰“寡小君”,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11]
所谓“邦君”,据《论语正义》当指“诸侯”之君。则此文明确指出,诸侯之妻称之“异邦”才可谓之“寡小君”。而《春秋·庄公二十二年》,则有“葬我小君文姜”之记。那么在史家记述时,亦可称为“小君”。但均得称“小君”而已,却绝对没有称夫人为“君”的。按韩愈关于娥皇为正妃的说法,则应称为“湘小君”,又怎么可以称为“湘君”?同时我们要注意,这都是指称“诸侯”之妻的。而大舜则是传说中的帝王、天子,娥皇乃帝舜之正妃,而非诸侯之妻,又岂得以诸侯妻之“小君”称之?
由此可见,韩愈的以“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之说,也只是不合情理,且于礼制无证的附会之说罢了。
以上我从秦初洞庭一带民间所祀湘神,乃是与舜之传说相联系的“二妃”,证明了与此相去七十余年的屈原《九歌》二《湘》所祀神灵,也当与“舜、妃”有关。并从湘水之神的“原型”及其变迁上,论述了屈原时代所祀湘神,已不再是远古时代“万物有灵论”观念下产生的无主名水神,而已为有主名“舜、妃”之神所取代。在此基础上辨明王逸所注“湘夫人”为“二妃”,“湘君”则为“二妃”“所留”之“舜”;韩愈以娥皇为“湘君”、女英为“湘夫人”之说,乃是既不合情理、也不合礼制的附会。
有了以上这些论述及结论,我便可以更加确信地回到八年前对《九歌》“恋爱”说所作的评议上来:《九歌》二《湘》之神灵,既与“舜与二妃”有关;则游国恩用“舜与二妃”“终无会合之期,至于互相怨恨,而各弃其贻赠之物”、“以示决绝之意”解说二《湘》,就根本不符合“舜与二妃”的神话传说背景。《九歌》二《湘》之神,既然在屈原时代早已摆脱了远古时代无主名水神之“原型”,而已由有主名的“舜”与“二妃”所取代;则褚斌杰先生试图用“殆已失考”、无凭无据的远古湘水神的所谓“男女恋爱”背景,来为《二湘》“恋爱”说圆场,也就变为于事无补的徒劳了。
注释:
①褚先生此意见与郭璞同。但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76页则明确否定郭说:“尧之二女即天帝之二女也。盖古神话中尧亦天帝也。”又同书285-286页。“《山海经》所载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经》‘姑媱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尧,《海外东经》‘帝令竖亥’之帝指禹而外,余均指黄帝。”
②屈原《天问》:“帝降夷羿,革蠥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嬪?”
③游国恩《论九歌山川之神》注引王照圆《列女传》校补,以为原文应为“俗谓之湘君、湘夫人也。”(见《楚辞论文集》127页)但由于古本《列女传》失传,我们对此校补只能存疑。
④今查《全唐文》卷三百四十六所载刘长卿《湘妃诗序》已有此说。但刘长卿乃在韩愈之前,而此序却有“韩愈《黄陵庙碑》曰”之语,可知此文非刘氏之作,当为韩愈以后之人所作而误入刘氏名下者也。
标签:九歌论文; 娥皇女英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屈原论文; 楚辞论文; 列女传论文; 湘君论文; 祭祀论文; 神话传说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