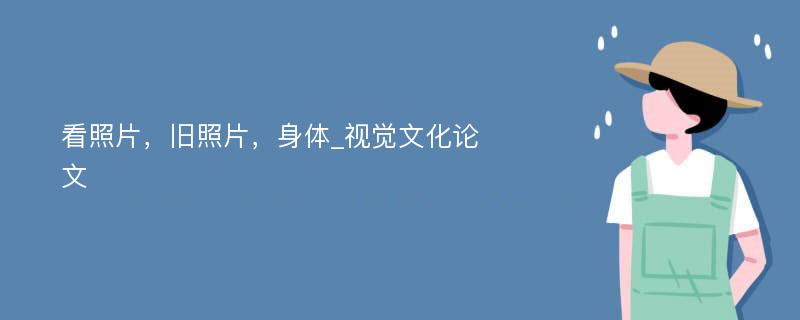
读图,老照片,身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读图论文,老照片论文,身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看与意识形态
观看是人类最自然最常见的行为。
但最常见的行为并非是最简单的。当代哲学和文化研究在“语言转向”之后,又转向了对视觉现象的思考,决非偶然。“视觉转向”不但标志着一种文化形态的转变,而且意味着理论范式的一种递变。
无论从概念上还是从学理上说,视觉现象作为一种文化,核心问题乃是眼睛与可见世界之关系,恰如听觉文化总是与言语和聆听有关一样。当然,眼睛的对象是复杂的,大到洪荒宇宙,小到分子结构,从自然到社会,从图像到文字。心理学的发现证实了一个极其简单却又异常复杂的命题:我们对世界的把握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视觉。
黑格尔说,视觉(还包括听觉)不同于其他感官,属于认识性的感官,所谓认识性的感官,意指透过视觉人们可以自由地把握世界及其规律,所以,较之于片面局限的嗅觉、味觉或触觉,视觉是自由的和认知性的。(注: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31页。)视觉的基本形态是看,看又可以区分为不同状态,在汉语中,我们有无数不同词汇来表述看,诸如凝视,注视,一瞥,浏览,静观……,等等。显然,看是一个主动发现的过程。贡布里希坚持认为,看就是图式的透射,一个艺术家决不会用“纯真之眼”去观察世界,否则他的眼睛不是被物像所刺伤,就是无法理解世界。(注:范景中选编:《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恰如波普尔的“探照灯”比喻一样,眼睛和客观世界的关系,乃是一种“探照灯”那样的照明过程,“照到哪里哪里亮”,事物从纷乱遮蔽的状态中向我们的视觉敞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诗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就是真理的开启过程。雕塑大师罗丹说得更是明白:“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注:《罗丹艺术论》,人民美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5页。)
观看确实是人最自然的行为。眼睛作为造化的产物,天生是用来观看的。但人的观看与动物有许多不同。拉康在论证“镜像”理论时说到,婴儿6个月后便能在镜子中辨认自己,而猩猩决然不能。(注:《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9页以下。)显然,人类看似自然的观看行为,其实是复杂的文化行为。看,就是一个追寻想看之物的过程,看和看到乃是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个中并无深奥学理。然则,在纷繁的人类社会中,在情境迥异的文化中,看与看什么和看到什么均不是一个自然行为,而是有着复杂内容的社会行为。从美学上说,传统的模仿论和镜子说主张,画家写生不过是纪律下所看到的风景而已。但问题决非如此简单!但晚近美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画家的观看不是一个机械记录的被动过程。贡布里希有一个著名论断:“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注:贡布里希:《艺术与幻觉》,浙江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这段看似简单的表述中蕴含了极其深刻的哲理:人的眼睛总是积极主动地寻找想要观看的对象。如果这么来理解,美学上争论不休的“美在主观”或“美在客观”的种种看法,其实都是片面之说。与其说美在心或在物,不如说美是人主动寻找的眼光之发现,罗丹的说法即如是。明代哲学家王阳明说过:“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会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注:《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浙江书局刊本,第27页。)无独有偶,法国哲学家萨特的说法亦有同工之妙:
由于我们存在于世界之上,于是便产生了繁复的关系,是我们使这一棵树与这一角天空发生的关联;多亏我们,这颗灭寂了几千年的星,这一弯新月和这条阴沉的河流得以在一个统一的风景中显示出来。……这个风景,如果我们弃之不顾,它就失去见证者,停滞在永恒的默默无闻状态之中。至少它将停滞在那里;没有那么疯狂的人会相信它将要消失。将要消失的是我们自己,而大地停留在麻痹状态中直到有另一个意识来唤醒它。
看便这样一种“唤醒”过程,是发现和寻找过程,看与被看以及看到的关系非常复杂。在传统的认识论里,看作为一种感知过程,属于感性认识,经由思维和推理的上升过程,感性认识才达到理性的高度。于是,在语言和图像的二元结构中,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而图像是感知的手段,由于思维高于感知,所以,图像也就自然低于语言。难怪西方有“语言即逻格斯”的传统观念。但是,晚近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那就是视觉其实和思维别无二致。思维过程中所具有的种种心理过程在视觉中同样存在:抽象、推理、分析、综合等等。于是,有人提出了“视觉思维”的概念。阿恩海姆写道:“知觉活动在感觉水平上,也能取得理性思维领域中称为‘理解’的东西。任何一个人的眼力,都能以一种朴素的方式展示出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令人羡慕的能力,这就是那种通过组织的方式创造出能够有效地解释经验的图式能力。因此,眼力也就是悟解能力。”(注: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如果我们进入视觉文化研究领域,哲学的和心理学的解释便于文化的解释互相纠结,使得观看呈现出更加复杂的文化意味。对种种观看的行为和类型做了深入细致的归类和分析,揭橥其中所蕴含的复杂“社会意义”,便是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研究者提出,在当代文化情境中,最基本的观看类型至少有如下几类:
1)观众的注视:一个观者注视着一个文本中的形象;
2)内在的注视:一个被展示的人在注视另一个对象(诸如电影中主观镜头);
3)外在的注视:一个被展示的人身处局外地注视其他对象;
4)镜头的注视:它捕捉着种种物像,代表了导演或摄影师的眼睛;
5)旁观者的注视:他身处文本世界之外,注视着某人正在看的行为(电影中经常表现为观众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偷窥行为的注视);
6)回避的注视:被展示的人物回避镜头、艺术家或观众的注意,眼光显得低垂或游移不定;
7)情境中观众的注视:在电影或绘画中画面人物在看着其他,等等。(注:Daniel Chandler."Notes on the Gaze."from www.aber.ac.uk.)
这里,我们不妨设想一个美术馆情境,那里有许多不同的眼光相互作用,因而构成了一个文化含义复杂的“视觉关系场”。其中种种不同目光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有人列举了以下迥异的眼光:
1)你在看画;
2)画中人物在看你;
3)画中人物在彼此看着;
4)画中人物在看其他对象,或是注视空间,或是闭上眼睛;
5)美术馆里警卫在你身后看着;
6)美术馆里的其他人在看你或看画;还有一些想象的观察者;
7)艺术家曾经看过这幅画;
8)画中人物的模特也曾在那儿看过自己的形象;
9)其他看过这幅画的人:买家,美术馆官员等;
10)所有其他没有看过这幅画的人,他们也许只是从复制品才得知这幅画,等等。(注:James Elkins.The Object Stares Back:On The Nature of Seeing,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6.pp.38-39.)
这些不同的目光和观看围绕着一幅画在一个具体情境中遭遇或延宕,值得分析的文化意义委实很多。比如,不同文化背景和地位(教育程度差异,艺术修养差异,社会地位差异,种族差异等等)的眼光聚集在一起,其中必然渗透着各自不同的想法、体验和联想。
由此来看,进一步需要思考的问题便是,种种不同目光是如何观看并理解它的对象?视觉中是否存在着文化上的暴力、冲突和权力关系?看与被看之间是否是可互换的或平等的?无论是看画,抑或看电影、电视,经由特定媒介所建构的观看情境,并不像日常生活那样存在着看的互动,我看别人,别人也看我。这种互动性使得观者不至于沦为被审视或监视的对象,而媒介化的视觉情境中,我们看画,看电影或电视,或广告画面,只是我们在看,被展示的对象并不在真实地看我们。因此有人指出,被纪录并被展示的对象往往和观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观看哪些被记录的形象赋予观者一种“窥视者”的地位。观者的优越性显而易见,而被观者永远处于沉默被动的地位。(注:Jonathan Schroeder,"Consuming Representation:A Visual Approach to Consumer Research,"in Barbara Stern,ed.,Representing Consumer:Voices,Views and Vision,London:Routledge,1998,p.208.)
一种女性主义的电影理论凸显了这一视觉不平等现象。该理论认为,在电影中,女人总是被展示的对象,而男人则总是观看这些对象的载体,恰如猎物与猎人的关系一样。摄影机的镜头、画面、形象和观众之间形成了一种复杂关联,其中隐蔽着某种男性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性别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已被分裂成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决定性的男性注视将其幻想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她们因此而被展示出来。女性在其传统的暴露角色中,同时是被看的对象和被展示的对象,她们的形象带有强烈的视觉性和色情意味,以至于暗示了某种“被看性”。作为性对象来展示的女性乃是色情景观的基本主题。(玛尔薇)(注:Laura Mulvey,"Visual Pleasure and Narrative Cinema,"in Charles Harrison & Paul Wood,eds.,Art in Theory 1900-1990.Oxford:Blackwell,1992,p.967)
如果对玛尔薇的以上理论稍加发挥,便接近我们所要表述的想法了。在看的状态中,包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这些意识形态因素由于文化的遮蔽和常识的掩盖,一方面变得难以察觉了,另一方面又使得种种视觉行为似乎是自然而然的。玛尔薇的解构,的确揭示了观看电影时潜在的不平等性别眼光,揭橥了男女之间看的主体与被看对象的不平等关系。当然,看的事务中复杂的意识形态内容远不只是女性主义所强调的,而是有更加复杂多样的内涵。我以为,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把看陌生化,像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概念所揭示的那样,打碎司空见惯的假象,揭露隐含其中的复杂的意识形态。于是,我们对视觉文化的分析便不可避免地将看(视觉)与意识形态理论结合起来。
阿尔都塞认为,所谓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象性关系的再现。”“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像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注: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in Slavoj Zizek,ed.,Mapping Ideology,London:Verso,1994,p.120.)依照这种思路,意识形态乃是一种我们与其生存状态想象性的关系,这种关系支配着我们的精神。倘使说当代中国己进入一个小康型消费社会,并导致了相应的文化变化,一种“视觉文化”已渐臻成熟的话,那么很显然,个体与社会及其文化之间复杂的想象性关系也已构成。透过视觉文化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瞥见复杂交错的文化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更进一步,意识形态不但是一种想象性关系的再现,它还具有相当的遮蔽性。照理说,任何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存在着由于社会分层所导致的不同群体、集团和阶层的差异,因此,意识形态总是属于特定社会群体及其价值观的。然而,在意识形态的生产过程中,这种局部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往往披上人类社会的普遍性的面纱,人为制造出来的反映了特定群体利益和价值的意识形态,常常以所有人共有的“自然而然的”方式存在。伊格尔顿说得好: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某种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争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是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注:Terry Eagleton."Ideology",in Stephen Regan,ed.,The Eagleton Reader,Cambridge:Blackwell,1998,p.236.)
所谓“自然化”,意指一个遮蔽意识形态的人为性真相的过程;所谓“普遍化”,是指特定利益集团的意识形态被虚假第普泛化为公众共享的东西。通过视觉文化这个特殊视角所要透视的问题,就是对视觉文化的意识形态加以去魅,还其本来面目。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文化符号趋于图像霸权已是不争的事实。电影、电视、广告、画报、卡通这些典型视觉样式自不待言,就是传统的以阅读为主的印刷物,从报纸到杂志,从书籍到其他读物,图像一类的视觉因素比重的急速上升,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难怪有人宣判“读图时代”已经来临。更有甚者,新的视觉方式和视觉对象正在不断被生产出来,进而深刻地改变我们关于世界和我们自身的看法:虚拟的图像、人造的主题公园、MTV、互联网的虚拟世界等等。勿庸置疑,今天,不堪重负的观看状态和富裕过程的视觉形象,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一方面是主体视觉行为的过度重负,另一方面则是人们理解世界越发第依赖视觉行为。我们通过电视新闻来感知世界,通过X光、CT、核磁共振等视觉途径来诊断,通过图像、图标和图例来讲解知识,通过电影、电视剧来了解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甚至通过照片、可视电话、电子图像来交往。一言以蔽之,我们正身处一个人类历史上视觉空前富裕和紧张的时代。海德格尔曾预言:我们正在遭遇一个“世界图像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注: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99页。)
至此,我们可以合理地引申出一个重要结论:看就是意识形态。看与被看以及所看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深刻地昭示了视觉文化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具体说来,本文要分析的问题是:第一,在视觉文化的各个层面中,作为视觉文化主体的我们,想看什么和看到什么?第二,随着视觉文化的兴起,传统的印刷文化及其语言主因受到了挑战,我们在其中面临着什么样的转变?第三,如何解析当代视觉文化复杂现象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以下,我们将从当代视觉文化突出的几种现象入手展开分析,将文化研究指向意识形态分析。
“读”图
“读图时代”这个颇为传神的说法道出了晚近文化的实际变迁。阅读本来是和文字联系在一起的,如今却和“图像”有一种密切关联,个中三昧值得深省。
读图首先呈现为一种出版物的流行导向,除了传统的图画类书籍(从画册到影集等),值得关注的是“插图本”的流行。过去,插图的功能是配合说明文字,使读物更具形象性和直观性。在这种图—文关系中,文主图辅必然导致一个图配文的关系。换言之,在“前读图时代”,文字乃是中心,语言是人们思想和交流的首要工具。“前读图时代”带有文化启蒙和理性主义的特征,通过识字扫盲,通过掌握语言文字,进而达到对科学认识和理性精神。文字—理性—知识—阅读和书写的互动关系,确保了文化的语言中心地位。
“读图时代”的基本特征似乎颠倒了这个局面。在这个时代,文字退居次席,图像僭越为文化主因。在流行的插图本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深刻的转变。比如,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插图本系列中,图像已经占据核心地位,文字反倒沦为辅助性的说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本是一本艰深的历史专著,煌煌巨著三卷本,现被简化为一卷插图本,有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文字在其中似已不再是读者注意力的中心,图像画面超越了文字。全书470页,其中附有黑白图片399幅,彩色图片90幅,平均一页有一幅图之多。诸如此类的印刷物很是流行,诸如山东画报社出版的《剑桥插图中国史》,作家出版社的《传统文明的起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复兴》、《罗丹论》、《人之子》、《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美的历程》、《美学四讲》、《华夏美学》等等。
大致说来,“读图时代”的流行读物有几大类:一类是传统的图像读物,诸如画报、影集、画册等等:一类是流行杂志,带有许多图片。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今时代的印刷物中,图片的急剧增加似乎标志着传统的文字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化已岌岌可危,任何读物,无论是杂志、报纸甚至书籍,没有图像便失去了对读者的诱惑力。图片等各种形象资源的倍增,清楚地表明人们阅读方式的急剧转变。更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过去只限于少数人士阅读的专业书籍,比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罗丹的《罗丹谈艺录》,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与这类插图本相近的是文字读物的“连环画化”或“漫画化”。这最典型地体现在卡通读物和蔡志忠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插图本中。本来,这些专业书籍多以思想深度、文字表达和专业研究见长,语言不但是其传统的表述手段,而且也是进入特定思想探索和思辨的重要途径。然而,在读图时代,此类读物也开始大量地遭遇“图像化”的改造,从传统性型的文字读物日益转向图像支配的图文混杂读物。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李泽厚的《美学历程》的两个版本,即1981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第一版(以下简称“文字本”),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该书的插图本(以下简称“插图本”)。首先是开本的不同,文字本是传统的大32开,而插图本采用了国际流行的开本,170×230毫米的开本,不但尺寸加大了,而且更便于经营安排图片。其次,文字本共213页,外加图版23页。其中收录了黑白图片92幅。插图本共291页,文字和图片混合在一起,且大多是彩色图片。共收录了各种图版214幅。具体数字比较如下:
文字本
插图本
图片数量92 214
文与图所占篇幅的比例(约) 213:23=9:1 150:140=1.07:1
通过以上两组数据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出,插图本无论是在图的数量,还是图与文字的比重关系上,都大大地超过的文字本。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插图本的图像表现力和精致性也大大超过了文字本,如前者的印刷是彩图、铜板纸、高清晰度和分辩率的专业印刷等等。
即使不从图片的数据比较入手,如果我们从阅读两本不同的书的直观感受角度说,显然,插图本读来更有吸引力和更具视觉快感。文字的深意被图像化为直观的形象,而文字也反过来为解说图像服务。在《美学历程》一书中,图像不但诱导着读者对文字的理解,甚至逼促读者图解和简化文字的原意,转向对编者图像意图的揣摩和适应。文字不但沦为图像的脚注,更有甚者,图像不可避免地将文字叙述平面化和直观化了。从美学角度来说,文字和图像本来各具特色,图像以其直观性和具体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抽象性和联想性著称。文字读物可以唤起读者更加丰富的联想和歧义的体味,在解析现象的深刻内涵和思想的深度方面,有着独特的表意功能。图像化的结果一方面将文字的深义具体化和直观化,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图像与文字之间新的“互文性”。毫无疑问,图像给阅读增添了新的意趣和快感,抽象文字和艰深表述和直观形象的图片互为阐发,无疑使得阅读带有游戏性,从文字到图像,再从图像到文字,来回的转换把阅读变成一种观照性的体验。米歇尔认为:在人类文化史上,始终存在着词语和图像的复杂辩证关系:
词语和形象的辩证法似乎是记号之网中的恒定因素,一种文化就是环绕着它自身来编织的。变化的恰恰就是编织法的特性,是经纬关系。文化的历史部分就是图像符号和语言符号之间争取支配地位的漫长斗争的历程,任何一方都是为自身而要求一个可以接近“自然”的特权。在某些时刻,这种斗争似乎进入了沿着开放边界展开的自由交流;而另一些时刻(恰如莱辛的《拉奥孔》)这些边界关闭了,彼此相安无事。所谓的颠覆关系就存在于这一斗争最有趣和最复杂的种种形态之中,在这一颠覆关系中,语言或形象探查着自己的内脏,在那儿寻找着自己潜藏的对立面。(注:W.J.T.Michell,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p.43.)
从中国传统文化史的角度来说,诗与画,亦即言与象的关系始终处在一种和平共处的关系之中,尽管两者时有越出边界互相抵牾,但总体关系应该说是和谐的。当代文化中插图本的兴起,读图时尚的流行,在言与象之间似乎多了一些“颠覆”的可能性。尤其是图像对文字的压制和排挤,使得读图时代的文配图倾向隐含着某种忧虑。换言之,在读图时代,文字沦为图像的配角和辅助说明,从文化对象上看,存在着一个显而易见的图像“霸权”;从文化的主体上说,普通公众更倾向于读图的快感,而冷落了纯粹文字阅读的乐趣,一定程度上揭橥了当代社会文化风气的变迁。尤其是太多插图进入文字著作中,搅乱了文字原有的叙事格局和逻辑,中断了文字的内在命脉,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文字中引向图像本身,客观上破坏了文字的感悟方式,让读者在图一文的混杂交替中得到别一种阅读的乐趣。这种情况在蔡志忠漫画系列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儒家、道家等中国古代的精深思想,被简化为漫画形式,这一方面自然有助于读者接近古代智慧和思想;但另一面的危险也同时存在,那就是将古代思想家博大精深的思想漫画化和简单化。假如读者对古代智慧和思想的了解只限于这些漫画式的读物,那么毫无疑问,留在他们心中的只有滑稽可笑的漫画形象了,这是否会导致古代经典中的深邃意趣的丧失呢?
这种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它还进一步反映在文学作品被影视空前的掠夺和形象化倾向上。显然,将文学名著拍成电影或电视剧并不是读图时代所特有的现象,但在读图时代,由于形象工业的空前扩张和膨胀,越来越多的非形象文化资源被开发和利用,许多古典的和现代的文学名著被搬上银屏。这本来无可厚非。但问题在于,大规模的甚至粗制滥造的影视化,一方面助长了公众对形象媒介的依赖,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冷落了文学文本。尤其在青少年一代中,广泛地存在着只读“图”不读书的趋向。
从对文字读物的崇拜,转向图像读物的青睐,这表明读者的眼睛所追寻的东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当然,转向图像或热衷与图像,并不必然是排斥文字,而是使抽象文字的表达和意义更趋直观感性化。所以,米尔佐夫认为,视觉文化的本质并不在于图像本身,而是在于将生存转化为视觉化或图像化的现代倾向。在这个倾向中,就此而言,“视觉化并不是取代语言的话语,而是使之更易理解,更快捷和更有效。”(注:Nicholas Mirzoeff,ed.,The Visual Culture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7.)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的启蒙始终和识字运动联系在一起。于是,读写能力成为脱离文盲进入文明社会的必要资格(尽管这个任务到目前仍未完成)。在识字运动中,图像常常扮演着重要的辅助角色,即通过直观图像来把握文字的意义。文革中红极一时的农民顾阿陶学《毛选》记日记,就是以图代字。它清楚地说明了图像在文字把握过程中的某种功能。但是,在“读图时代”,图像的功能迥然异趣,它不再是对文字的图解和形象化说明,而是相反,文字沦为图像的注解。在我看来,图像一方面并未取消文字,另一方面图像的确威胁到文字。视觉文化时代的一个显著趋向就是图像霸权的出现。这种霸权不仅对文字构成威胁,而且危及到文字所代表理性主义价值观,使欲望原则伴随着消费社会和文化的出现而成为主因。这里,我们不妨稍加展开,从一些思想资源上寻找解释。利奥塔在其早期著作中强调“话语的”和“形象的”两种不同文化的对立二分,在他看来,“话语的”文化就是现代文化,其特征是理性主义,依据的是“现实原则”;而“形象的”文化则是后现代文化,其特征便是感性张扬,依据的“快乐原则”。拉什将这一区分具体化了,他写道:
在这一语境中,“话语的文化意味着:1)认为词语比想象具有优先性;2)注重文化对象的形式特质;3)宣传理性主义的文化观;4)赋予文本以极端的重要性;5)是一种自我而非本我的感性;6)通过观众和文化对象的距离来运作。相反,‘形象的’则意味着:1)是视觉的而非词语的感性;2)贬低形式主义,将来自日常生活中常见之物的能指并置起来;3)反对理性主义的或‘教化的’文化观;4)不去询问文化文本表达了什么,而是它做了什么;5)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说,原初过程扩张进文化领域;6)通过观众沉浸其中来运作,即借助与一种将人们的欲望相对说来无中介地进入文化对象的运作。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透视“读图时代”的文化转向,那么,有一点似乎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从“话语的”文化转向“形象的”的文化,读图乃是从一种意识形态向另一种意识形态的悄然递变。它与中国当前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快感的深刻变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图像恰好优于语言成为合适的媒介。读图显然比读文字更加惬意直观,更具“审美的”属性和意趣,它与当代社会中世俗化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是一致的。
当然,事情总有另一面。读图时代流行的读本乃是图像为主的书籍。一本书(比如《美的历程》)可以从原先的文字本,再转变为插图本,并大批量地发行,一方面表明该书的形式转换顺应了新的文化氛围和阅读需求,另一方面也表明突破文字本的格局,也就突破了原有的读者群,将一本原先只限于专业人士阅读的书,扩展到更多的阅读大众中去了。这是否会增加人们读文的兴趣,尚是一个不得而知的问题。图像在印刷媒介中大行其道,反映了印刷媒介本身的变化,读图时代不啻是文化“视觉转向”的一个生动脚注。
老照片
改革开放伊始,贫困的中国整体物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摄影作为一个有闲阶级的奢侈玩意儿,是大多数中国人望尘莫及的。近年来,一方面对着照相技术的发展和成本的降低,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准的提升和对文化的关注,摄影已经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记录每个家庭和个人生命活动最普通的见证方式。而视觉文化的流向,自然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摄影为代表的图像文化。
一些社会学家坚持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摄影乃是“中产阶级的爱好”(布尔迪厄等);尽管此说在把一种把行为与阶级地位对应上有过于刻板之嫌,却也指出了摄影与一种生活方式看不见的关联。在中国这个日益“小康”的社会中,一种“小康”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和摄影发生关联。当然,这里我并不想全面讨论摄影与日常生活的诸多层面的联系,而是想着重分析晚近中国视觉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现象,亦即“老照片”的兴起。
近几年,“老照片”一类的印刷物很是流行,个中文化意义值得思量。不少出版社争相出版各种“老照片”系列,以致于为“老照片”的创意和冠名权对簿公堂。什么《老照片》、《黑镜头》、《旧社会》、《老房子》……名目繁多。毫无疑问,照片是一种历史的记录,是一种社会的文化记忆。苏姗·桑塔格曾出色地概括过其价值:
一张照片就不仅仅是像其题材,同时还与其题材拥有一种臣属关系。它是那一题材的一部分,是它的延伸,而且还是一种占有它、控制它的方式。
摄影在好几方面都是有价值的获得物。就最简单的方面而言,我们在一张照片中替代性地拥有了一个珍爱的人或物,这种拥有给照片以某种独特对象的特点。通过照片,我们还与事件,既有那些我们经验的一部分的事件,同时还有那些并非我们经验的一部分的事件——这是为区分被这种养成习惯的消费活动所混淆了的经验类型而作出的划分——形成了一种消费关系。第三种获得的形式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制造影像和复制影像的机器来获得某种东西作为信息(而不是通过经验)。确实,越来越多的事件通过这种媒介进入了我们的经验,而作为媒介的摄影影像的重要性就在于,在提供知识的过程当中,最终只有它们那实际效果的一种副产品从经验中分离和独立出来。(注:桑塔格:《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页。)
如果我们反思老照片的流行,一种不假思索的答案是人的怀旧感使然。然而,从桑塔格对照片的解释来看,其文化意义远比怀旧概念复杂。其实,“老照片”的流行,虽有怀旧,又远不只是怀旧。
从文化上说,“老照片”的流行,其实也是“读图时代”的一个征兆。
老照片的魅力在于其“老”,不同于当下生活写照,老照片凸现了逝去的过去。其题材的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可名之为“正史性的”,多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场景;另一类则可以称之为“野史性的”,多为一些市井日常生活的写照,从不知名的人物到他们的日常起居,服饰建筑,甚至是山川风景。“正史性的”老照片以其历史性和纪念性见长,突出了真实的事件和及其历史意义,彰显出强烈的政治意味和道德价值判断。这类照片通常带有明显的编者“眼光”,意在强调对特定政治事件和任务的评价臧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这种图像的观念价值的诱导性往往左右着读者的理解。对于饱经政治风云洗礼的当代读者来说,这类老照片所以引起读者兴趣,大多是未曾披露的那些场面、事件和人物。较之于前者,后一类“老照片”似乎蕴含了更多值得考量的文化意味。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而且往往是无名无姓的黎民百姓,甚至时间年代也不甚清楚的老照片,却可以激活当代读者的莫大兴趣!
此类读物的典型版本,可举出许多,比如江苏美术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老照片》(两卷本,),羊城晚报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老日子》(四卷本)等。前者分列了“民俗风光”和“服饰时尚”两个主题,着力从各种摄影文献中搜寻晚清到解放的历史时光和影像记录。后者则更加凸现了日常生活面面观,每一册均涉及诸多主题,诸如“婚娶”、“作坊”、“娼妓”、“盐业”、“赶集”、“水患”、“过节”、“祭祀”、“苦力”、“学业”、“摊贩”、“摩登女郎”、“庙会”、“丧葬”、“邮政”、“当铺”、“乞丐”、“码头”、“休闲”、“茶酒”,等等。比如服饰,老照片如同电影一般地展现了从清末凉帽花衣,到长袍马褂,再到西装革履的漫长演变过程:民俗风光则重现了大都市到小城镇的往昔景象,从上海外滩到北平城墙,从厦门港湾到桂林街头;人物形象也是意趣昂然,从肩挑邮袋的乡村邮差,到乡间渔夫,再到驼队和杂耍艺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应有尽有。
老照片现象最简单的解释是所谓“怀旧情结”。无疑,怀旧是人普遍存在的“健康病症”。细细想来,日常生活的“老照片”与当下庶民生存方式较为贴近,加之过去生活的陌生感,很容易引发人们的好奇和兴趣。毋庸讳言,怀旧是老照片流行的一个重要心理原因。文化史上似乎有一个规律性的现象,每当社会急剧变化,传统以空前的速度丢失而新事物应接不暇,而未来又难以预测时,怀旧情结便总会暗中作祟。近代以来,我们已经反复经历过这样的过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老照片”流行的文化意义决非只是怀旧,还有更加深刻的原因值得思索。
首先,日常生活类“老照片”的登场,反映了公共领域里以往摄影志过多地偏重于“正史”记录的倾向,重大历史题材的照片始终是首要乃至唯一的文化记忆,相当程度上被忽略了的是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这类景观是非常淡漠的。图像志留给人们的往往是那些令人敬畏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及叱吒风云的历史英雄。英雄主义的崇高乃是图像志中唯一合法的主题。我们对重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或许可以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过去普通人那平淡生活是什么样的,更难以感受到平民百姓的想法和情感。当代文化的趋向之一是文化的多元化,形象的历史正在从单一的正史记录转向多元记录(诸如生活史,家庭史,文化史等),因而“老照片”显然起到对我们的文化记忆补缺拾遗的功能,进而唤起、丰富和完整当代人残缺不全的关于过去的记忆。桑塔格说得好,一张照片就是对其所属题材(那个生活世界)的“占有”和“控制”,当然,这只是一种想象性地“占有”和“控制”,它意味着我们可以借助照片进入那个陌生遥远年代的生活世界。
其次,当代“小康文化”较之于以前的“理想主义文化”,其政治意义和理想主义性质相对减弱了,而世俗的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意义越升为主因。说教性的图像志不再是唯一合法的文化史,日常生活的“老照片”收到欢迎恰恰反映了这种转变。日常生活随之进入人们的视觉注意力的“期待视界”,亦表明人们关注的不只有历史事件及其政治意义,更有广泛的内容。日常生活“老照片”的匿名性和年代模糊的背景,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和探问。其中丰富多彩的民俗风情,衣食住行,山川集市,不但在题材上切近当前普通人的生活及其体验,而且重现了许多业已消失了的生活趣味。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日常生活“老照片”的流行,说明了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在取代了政治文化的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的客观记录和朦胧的背景,以及贴近现实的普通生活,在淡化政治意味的同时,却又拉近了读者与历史的距离,使逝去的过去成为我们当下的欣赏对象。较之于对正史性“老照片”的重温历史之严肃态度截然不同,欣赏日常生活的“老照片”不必作出什么明确的价值判断,把玩体味即可。于是,欣赏“老照片”也就是欣赏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存在。
再次,日常生活的“老照片”的流行,也标志着当代视觉文化的转向。“读图时代”的到来使图像成为主导,而文字则退化为辅助性的说明。这个特征可以比照另外两个参照系来加以说明。一是过去时代的文字说明,二是过去时代的影视化展现。虽然过去生活的文字叙述作品有不少,但文字在这个时代已不如图像更具诱惑力和更直观。图像功能的提升和文字功能的衰退,使得老照片这种独特的文化表征形式具有某种优越性,因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从后一方面来比较,影视化的表现自然有其优点和特长,不但形象地再现往昔,而且是动态地展现。但照片亦有自己的优势,影视作为动态的艺术瞬间消失了,无法保存,老照片虽是静态的,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影像。用桑塔格的话来说:“照片比移动的形象更具纪念意义,因为它们乃是一小段时光,而非流动的时间。电视是一连串选择不充分的形象,每个形象都会抵消其前在的形象,每张精致的照片则变成了一件纤巧物品的特定的一刻,人们可以持有它并一再观看。”(注:桑塔格:《论摄影》,湖南美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9页。)拥有一册《老照片》,不时地翻阅细读,仔细品味,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审美化”的一种写照!
最后,“老照片”的流行看来还有一个值得深究之处,那就是它不但记录了过去,而且记录了过去记录者的眼光和情感。于是,看“老照片”不但是在看过去的黎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而且隐含了另一种潜在的探求,那就是看到那时的摄影家(无论是专业抑或业余的)是如何观看当时的生活的。看过去的人如何看,便使得老照片的欣赏别具文化意味和历史感。无疑,摄影就像是看,每一种眼光既是一种开启,又是一种遮蔽。所以,照相机的镜头在展现某些影像的同时,也就遮蔽另一些影像。所以,影像就是意识形态,拍摄影像的镜头——亦即摄影家的眼光——更是一种意识形态。摄影家总是寻找他认为值得或应该再现的东西,这必然遮蔽了他认为应挡在在画面之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老照片”既体现了镜头对现实的选择,也揭橥了摄影者的某种价值关怀或情感指向。老照片的摄影家眼光包含了多种意味,有同情者,有鄙夷者,有赞美者,照相机决非纯然客观的记录仪器,而是代表了摄影家的想法和看法。这看法不仅体现在看什么和不看什么,而且体现在怎么看和怎么呈现。阅读老照片在和画面影像交流的同时,读者也在与摄影家的眼光的交流。比如,《旧社会》(羊城晚报出版社200年版)上卷168页上“煮盐”,画面上四个自贡盐工背对着镜头,在热汽蒸人的作坊里赤身裸体地劳作,无遐顾及身后的世界。镜头中坦露了摄影家对盐工辛劳和非人的劳动条件的深切刻同情。
我们看老照片,注视着照片中山川风物,与画面中各色人等的眼光遭遇,我们从这些人不同的面部表情和周遭环境中,读出“老”字纷杂的历史意味。“我们”和“他们”之间不但有一个距离,而且存在着微妙的角色转换。一方面,当下读者以一种“优越”关注着过去的芸芸众生,当代生活的相对安逸与过去历史的危难之间存在着明显差距;另一方面,“我们”在注视“他们”的过程中,想象性地进入了“他们”之中,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设身处地地体验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于是,“我们”又被转化为“他们”。久远的过去,恰如被戏剧化或艺术化的了生活一样,与当下的读者有一种客观的时间距离和主观的心理距离,想象地介入过去的生活世界,距离使得读者处在一种“虚幻而又真切”的情境之中。历史的远眺把过去的一切都转化为一种静观,一种欣赏,一种体验。过去那直接的政治意义和伦理价值由于距离的作用而淡化了,苦痛、悲哀和焦虑也被缓解了,这就是为什么艰难的过去如今可以被我们欣赏的原因所在。
老照片的兴起,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代表了历史再现的多样化。过去,历史多限于文字的记录和解读,或是博物馆里的历史陈列。老照片将历史图像化和感性化,意味着社会对过去的历史记忆将更加丰富和具体。过去不再是几条原则的概括或几份历史文献,而是生动的图像化生活世界。和“老照片”一起流行的还有另一些值得注意的读物,包括“老画报”,“老画片”、“老漫画”、“老广告”等等。视觉文化的兴起,给当代人进入历史增添的更多的途径。
身体
在视觉世界里,除了身外的大千世界外,最常见的形象便是人自己的身体了。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个体在其生命早期阶段建立的镜像,“功能在于建立起有机体与它的实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或者如人们所说的,建立在内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注:《拉康选集》,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92页。)从比较的角度说,人也许比任何其他物种更具自觉的“身体意识”或“身体反思”,人关注他或她自己的身体,并为身体感到焦虑。历史地看,现代人比古代人更关心自己的身体。所以,身体是当代小康社会视觉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
小康文化带有明显的消费社会特征,而消费社会的一个基本标志乃是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人的美学自觉不只体现在对外部生存环境的要求上,而且聚焦于人自身。这种关注越来越趋向于外观和表面,于是,日常生活的“美学化”命题也就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身体“美学化”的追求。
身体社会学认为,人的身体观念是一个二重的观念:物质(自然)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社会学家道格拉斯发现,这两种身体的关系是:“社会的身体限制了自然的身体感知的方式。身体的自然经验又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修正,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自然的身体才被人所知晓,并保持一种特殊的社会方式。在身体的两种体验之间存在着意义的不断交换,结果是各自都强化了对方。”(注:引自Joanne Entwistle,The Fashioned Body,Cambridge:Polity,2000,p.14.)假如只有自然的身体,那么将并不存在所谓的身体“美学化”现象。身体社会学的研究发现,自然的身体总是受到社会身体观念的制约,人是社会交往的动物,所以总是不断地将其自然身体转化为社会身体,亦即转变成社会交往的符号。所以人类学家毛斯指出,人的身体转化为文化符号乃是经过一种“身体技术”而实现的,这种技术教会了人如何在特定社会中使用自己的身体。身体的符号使用一方面使得主体感受到一种身份感,比如中国人对自己黄皮肤黑眼睛的体认,其中就包含了深刻的中国人民族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符号的自觉还是主体体悟到一种群体归属感,青年人对体形的自觉,使之感悟到自己属于青年亚文化的时尚等等。所以,自然的身体向社会的身体的转化,也就是身体的意识形态。
回到身体的“美学化”问题上来,所谓身体的“美学化”,是指当代生活中人们对自己身体外观形态的关切,强调身体符合当代时尚标准,其中关键词是“健康”与“美”。这便与视觉文化关系密切。换言之,把自然的身体当作社会的身体来使用,从传统的对身体的拥有感转向社会性的炫耀展示,从过去对身体的遮蔽到当代日趋曝露,传统的身体文化不可避免地转向当代身体文化。这种转变尤其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当代人对身体的关注,尤其是身体外观的重视超越了以往任何时代。从常识角度说,此乃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结果。温饱问题解决后,形体外观的美化和内在的健康便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二,身体的展示或暴露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这对中国人来说,这是观念的变革。从吊带裙到比基尼泳装,从紧身裤到迷你裙,不一而足。第三,身体本身形成了一种文化,更有甚者,导致了某种“身体工业”的出现。从医学美容到演艺化妆,从形象设计到健美,它不但和千千万万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而且构造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和产业。以上这三个方面都和视觉文化联系在一起,身体的关注说到底乃是视觉的欲望所致,而身体的“美学化”说穿了也就是人对身体视觉快感的苛求。
身体“美学化”的核心观念乃是身体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是通过各种媒介和展示,通过选美小姐、时装模特、演艺明星、体育明星、主持人、青春偶像等种种视觉规范的确立而形成的,又是通过诸如选美、健美比赛、体育运动、广告形象、演艺节目、画册画报、偶像形象等媒介方式塑造并向大众灌输的。比如用于女性身体“美学化”的关键词有:“瘦身”、“美白”、“健康食品”、“健身”等;而用于男性身体美学化的关键词则有:“健康”、“活力”、“健美”等等。当代人发明了古代人无法想象的种种“身体的技术”,用来维护自己关于身体视觉快感的种种规范。这里我们有必要对身体美学化的诸种策略稍加分析。
首先是身体美学标准的确立,它体现为当代强制性的身体美的视觉标准,比如女性的苗条、三维比例、皮肤紧致;或男性的健壮、肌肉饱满和力量。各种身体偶像,从克劳馥德到施瓦辛格,从胡兵到瞿颖,这些真实的个人已经被媒介不断打磨成“虚拟的形象”。身体的“生产”实际上依照某种人为的标准进行的。换言之,当代身体的生产和传播带有明显的标准化性质,它借助媒介和标准的公众认可,在暗中强制性地实施关于身体美的规范,并使得社会公众趋之若鹜地首肯和追随这些标准。其次,在消费社会形态中,身体不只是个人拥有的肉身,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流通符号,更是一个人人“购买”和“使用”的消费品。当代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美学规范,以其时尚的形式,悄悄潜入每个追求现代生活时尚的个体观念中,成为控制其消费行为和取向的观念。身体的消费性突出了社会身体的符号意义和意识形态特性。在小康的社会中,关注身体本身就反映了身体己从自然物转化为商品性的社会存在。恰如法国哲学家德波在分析当代消费社会所指出的那样,“景象的社会”将一切生产、流通和消费行为都转化为形象。“在现代生产条件无所不在的社会中,生活本身就展示为许多景象的高度聚集。那些直接存在物全都转化为表象。”(注:Guy Debord,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1,from www.nothingness.org.)这就意味者,一切现实物均转化为形象,商品的消费己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转向了当代的符号政治经济学。商品的交换价值不只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更有赖于其形象(美学)价值。从表面上看,人们在化妆品、服装、鞋袜、眼镜、甚至汽车等带步工具上投入了财力和精力,消费的是外在的物质产品,但究其根本,乃是对自身身体的消费,是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当代身体工业中去,再生产出社会所追崇的身体类型。另一方面,身体的消费有反过来强化了对身体的意识和苛求。正如马克思所说,生产生产出消费,消费又消费着生产。这种辩证的互动关系把人对自己身体外观的视觉快感彻底合法化了。再次,在身体标准和身体消费日益普及的条件下,身体的技术变得越发重要了。所谓身体的技术,我以为有两个最基本的层面:一是塑造身体的技术,包括当代身体工业的种种发明,化妆技巧、形象设计是身体技术,美容手术等医学手段也是身体技术;第二个层面是运用身体的技术,亦即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使用自己的身体来进行社会交往和传达意义的种种技术,种种身体语言是身体技术,舞蹈、模特猫步、体育运动、演艺动作,甚至日常生活的体态姿势都是身体技术。毫无疑问,由于当代社会中身体越来越趋向于成为商品,成为消费对象,新的身体技术不断被发明出来,转而成为控制我们自己身体的外部力量。
身体美学的合法化,不仅仅限于对身体的外部形态的维持和改造,更有其复杂的意识形态内涵。这里,社会的身体被赋予了某种超越身体外观的意义,标准的、理想的和规范的身体范式的合法化过程,是一个值得分析的文化现象。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表明,局部特定人群的意识形态,通常经过一个“自然化”和“普遍化”过程,脱离了其局部的和个别的意义,转而成为社会公众的普遍倾向和自然倾向。用吉尔兹的话来说:“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体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像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个政治动物。”(注: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Basic Books,1973,pp.217-18.)即是说,理想的身体形态具有范式功能,虽然是当代文化中的身体工业所创造的美的标准,最初只是少数人的理想和追求,但在这个标准的广泛传播中,这些范式不可避免地被普泛化了,成为绝大多数人甚至普天下人类所共有的身体美的规范。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无论是西方抑或东方,身体“美学化”的准则似乎是不变的,自然的,普遍的。什么“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是人的共同追求”等等表述,意在淡化特定时期特定文化甚至特定人群的人体美准则的潜在意识形态内容,转而使之成为一种自然的和普遍的美的观念。这就是身体美学化合法化过程。
身体的技术作为实施身体标准的手段,是透过镜像和自我监视来实现的。身体技术的使用首先是一种身体意识的自觉。这种自觉意识不断迫使个体关注自己的镜像。对身体镜像的注视就是一种个体的反观。镜像不只是个体对身份的认同,而且是对一种关于身体的文化标准的比照,因为面对个体自己的镜像,既是在看自己,同时又在将自己的身体与身体的时尚标准进行比较。看自己的动机隐含潜在的暴力,那就是如何使得自己的身体符合某种人为的外在规范。于是,我们在这里触及到身体“美学化”反观所具有的隐蔽监视性。自我的镜像就是自我监视的对象,而“身体的技术”则是缩小自我形象与理想标准差距的主要手段。每当个体面对自我镜像,发现自己与人体美学标准有所差距时,便必然产生一种心理学上所说的“认知不和谐”状态。一方面是身体的美学规范形态,另一方面是自我尚不完美的体形或面容,两者的差距越大,便越容易导致焦虑和不安;反之,当两者距离缩小时,便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认知和谐的快感。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身体工业必定要制造出这种差距,因为普遍的焦虑和认知不和谐,正是身体工业及其种种身体技术赖以存在的根据,是身体消费的目标行为的内在动因。当代身体工业将少数人才能达到的美学标准合法化和普遍化时,就是将一种关于身体的强制规范转化为无数个体的内心需求,只有这样,身体的美学才有可能缔造一个潜力巨大的消费市场。身体的视觉快感转化为内心需求,而认知不和谐又为这种快感的合法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文化角度来看,身体便越出了自然的范畴,越发带有社会性,最终,身体从自然的造物,演变为一种文化象征。美的身体和面容是稀缺的,所以,总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这个为了虚拟的美之形体而斗争的宏大产业中去。
另一方面,人体美的当代标准的普泛化和自然化,身体意识形态的普遍化和自然化中又潜藏着一种局部性和特殊性。恰如前面说到的现象,身体的关注其实就是要消灭自我与美的典范之间的差距,而差距的消失或缩小,则为个体认同一种身体文化创造了条件。身体的标准不但是普遍的美学产物,而且同时也是特定阶层和群体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体现。“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象性地被赋予的。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注:Judith Williamson,"Meaning and Ideology,"in Ann Gray and Jim McGuian,eds.,Studying Culture:An Introductory Reader,London:Arnold,1997,p.190.)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体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形体外观问题,而且与精神的控制和修炼相关。福柯所说的身体的“监视”和“规训”在这里成为可能。一方面我们不断地“监视”自己的身体,时刻注意它与美的身体规范的差距,暗中起着“霸权”功能的乃是一种看不见的文化权力;另一方面,在“监视”中,我们又不得不时刻通过种种技术“规训”自己的身体,心甘情愿地接受一种身体的“暴力”:隆胸、抽脂、去毛、种毛、拉皮、染发、节食、运动……。当代身体工业发明了无数“虐待”、“戕害”身体的“技术”,恰如阿多诺对启蒙的忧虑一样,启蒙在征服自然的同时,把对付自然的方法反过来对待人自身,于是,启蒙走向了它的反面——野蛮。当种种“人体技术”把技术理性和手段转而用于人自身时,当医学从救死扶伤转向针对人的身体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时,“野蛮”的一面是不容轻视的。更有趣的是,普泛化的身体标准在暗中实施着局部的策略,亦即强调身体时尚乃是一种关于人自身的理性主义原则的胜利。诚如鲍德所言:
在我们的文化中,强制性的节食和身体塑造中存在一个重要的意义连续统,它揭橥了现代女性富有魅力的形象为何容易在以下两种形象间摇摆:削瘦的“极少主义”的外貌和结实的、有力的和健美的形体。这些看起来迥然不同的形象的并不意味着如今形象空洞而迥异的后现代世界已经成为主宰,而是表明,这两种理想形态尽管表面上不同,却在对付共同敌人——疲软松懈的、多余赘肉的斗争中结成一体。我们的文化(印使是对女性而言)也完全允许拥有必要的体重和肉块,但必须严格加以控制。(注:Susan Bordo,"Reading the Slender Body,"in Nicholas Mirzoeff,ed.,TheVvisual Culture Reader,London:Routledge,1998,p.216.)
在这个艰苦的“身体战争”中,人们企求的不但是身体趋近美的典范,而且带有一种进入较高精神境界和生活状态的标志。诸如“新派女性”,“个性自由”,“偶像认同”,“独一无二的个性”等等,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形象表述。通过强调个性,自由,偶像崇拜或独特性,来强化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趣味的理想化。一旦个体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及其追求,一旦把自己的身体投入媒介所炮制典范无穷修炼之中,也就仿佛具有了一种新的生活和新的自信,这无疑是一个当代的身体“神话”。
据报载,南美诸国美女辈出,秘诀之一在于旷日持久的身体改造。今年巴西小姐桂冠得主弗朗西妮披露:整形手术是她获胜的法宝。她不喜欢过去的自己,因为镜子中的自己缺乏魅力。经过大小整形手术23次之多的塑造,完美的三围和迷人的脸庞使她技压群芳,一举夺魁。如下数据统计更是让人诧异:去年巴西全国接受整形术的人数高39万人,平均每人花在整形手术上的费用更是超过了美国,居世界之冠,这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这不禁让人想到古老的“削足适履”的谚语。从时装模特到封面女郎,从广告明星到演艺大腕儿,从选美大赛到媒体亮相,风姿绰约的美女们确证着同一个标准和法则:按照一个标准造自己的身体!结果是,人们在一种虚幻的满足感,身体美学化的规范也许是一种“恐怖标准”,而把这种标准当作幸福的追求,是在是令人困惑!每当文化只有一个标准时是很危险的,而身体的“美学化”的标准合法化,其潜在危险决不亚于一场灭绝身体多样性的战争。一个疑问是,统一标准的身体工业会不会扼杀我们身体形态的无限多样性呢?
解读身体美学化的意识形态,我们不难发现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社会解放了身体的束缚和遮蔽,给身体的展露和交往带来了新的自由;另一方面,身体“美学化”标准的合法化和普遍化,又不可避免导致了对身体的压制和暴力。
